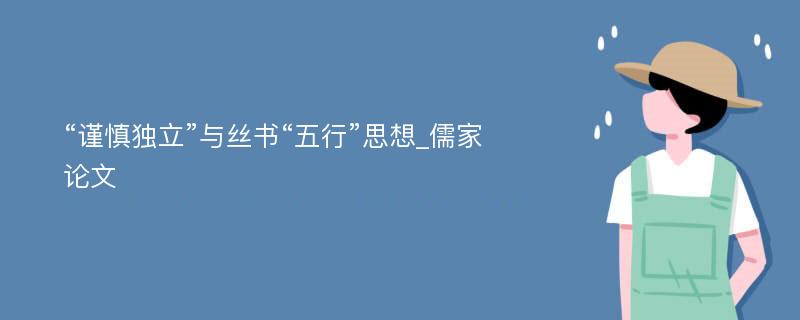
“慎独”与帛书《五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慎独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作者曾提出,帛书《五行》篇的经部为子思所作,说部为孟子所作,并以竹简《五行》篇文本为据,专门就经部作为子思的思想进行过综合分析。① 本文在此基础之上来讨论帛书《五行》说部思想与孟子的关系,力求在揭示说部思想特点的同时,进一步说明帛书《五行》篇说部为孟子所作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为方便起见,本文引用帛书《五行》文字与分章,皆据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
一、慎独说
帛书《五行》篇经文提出“慎其独”,但无说明,说文部分对此作了较多解释,且很有特色,涉及到早期儒家的功夫论。②
《经文7》中两次引《诗》而论慎独:
“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
“婴婴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
在经文对第一首诗的运用中,很强调“一”,把慎独看作达到“一”的途径。说7对于第一句引诗的处理,也是先解释“其仪一也”和“能为一”,然后解释“慎其独”说:
“君子慎其独”。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夫为□心也,然后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③
为集中起见,我们先来看慎独的讲法,把一、德、天的问题放在后面讨论。根据这里的说法,“慎其独”主要是指“慎其心”的功夫,而慎其心的功夫是以“舍夫五”的方式进行的。关于“独”和“舍夫五”,说7在这里并无解释,但在该章的最后总结慎独说时指出:
独也者,舍体也。
可见说文的特点是以“舍体”解释慎独。此处的“舍体”应是上面所说的“舍夫五”;“独”当然是指“慎独”的独。魏启鹏认为慎当训为顺,可从。④ 同时,照这里所说,舍体是“独”的方式,也是“独”的结果。根据舍体的说法,可知“舍夫五”的五当指身体的五官,五官为小体,故称舍体,这种“舍夫五而慎其心”的功夫就是舍去五官的各自悦好而专顺其心。顺其心即顺其心之所好,心所好乃为仁义(说22言“心也者,悦仁义者也”,参本文第6节大体说)。在这个意义上,慎其独就是顺其心,就是舍去其它的知觉所好而专顺一心。⑤
《说8》也谈到舍体:
“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有与始者,言与其体始;无与终者,言舍其体而独其心也。
虽然《说8》并非专门解释慎独,但处处与“体”有关,而这里的“舍其体而独其心”明显就是说文作者对慎独的理解。在以上两段中,“独也者,舍体也”,表明独和舍体有关,“舍其体而独其心也”,表明舍其体和独其心密切关联,可见独和舍是一体的两面。换言之,这里对慎独的理解包含两方面,即舍其体和独其心。所以,“舍夫五而慎其心”,也就是指“舍其体而独其心”,这两句话是完全对应的:“舍夫五”就是“舍其体”,舍在这里是舍去,体是指身体五官⑥,舍体就是不让身体五官的作用影响心;“慎其心”与“独其心”一致,独其心即独从其心之所命、独从其心之所好。也就是使心独自地、不受身体五官影响地发挥其功能。从语词上来说,在“独其心”这里,独成为动词,与经文“慎其独”的独字的用法已有了差别,这是诠释的结果。同时可见,“体”与“心”相对,而五行并不是体,故“舍其体”的意思肯定不是舍五行;“舍夫五”既然是舍去,又是舍体,所以舍夫五是不能解释为五行和合的。
以上主要分析了说文对经文7第一句“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的解说。其实,经文7的第二句“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也是讲慎独的,说文7对此的解释是:
差池者,言不在哀绖;不在哀绖也,然后能至哀。夫丧,正经修领而哀杀矣。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
这是说,诗的意思是,参加丧礼或其他从事守丧活动,不把心思放在丧服的形式上,才能完全表达出哀痛的心情。若把心思放在讲究丧服的形式上,哀心就势必减弱了。所以,人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外部,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心,这就是慎独。五官是向外的,舍去五官向外的知觉作用,转向内心,这就是慎独。这与对第一句诗文的解释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慎独舍体的功夫是以“内—外”关系为焦点,以求内不求外为导向的。同时也可见,仅仅是专一,不能充分说明慎独之义,专一必须是专诚于内心,专心于内;仅仅使心独自地、不受身体五官影响地发挥其功能,也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慎独是不受五官影响而专心于内,才是慎独。所以我们必须把说文对经文的两次引诗的解释结合一起,才能更全面理解说文关于慎独的思想。⑦
根据以上的解释,《五行》说文的“慎其心”的心概念,在这里特指道德心,其慎独功夫强调专诚向内,排除感官的向外追求,这些与《孟子》书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为—说
以上我们清理了说文关于“慎其独”的思想。现在我们回到“一”的问题上。事实上,由于说7中关键字缺损甚多,关于“一”的问题已成为说文中比较费解的问题。
《说七》首先解释引诗“其仪一兮”:
鸤鸠在桑,直之。其子七也,鸤鸠二子耳,曰七也,兴言也。(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淑)人者□,(仪)者义也,言其所以行之义之一心也。⑦
这是把“其仪一兮”的“仪”解释为义,解释为行义之心;把“其仪一兮”的“一”解释为一心,一心即心之专一;认为“其仪一兮”整句话是指心专一于义。事实上,以专一解释此诗的意旨是汉代学者的共识。⑨ 有学者把这个一解释为五行合一,这实际上是把“一”解释成为“和”。⑩ 但我们知道,诗中的“其仪一”是相对“其子七”而言,即“一”是相对“七”而言;故后来的诗传也都把这里的“一”解释为相对于众多的单一,专一之一亦由乎此而来。而相对于众多的“单一”,与多样性的“合一”,二者是不同的。因此,从“一心”的提法来看,如果这里是指专一于行义的心,就不能是五行和合的心,而且五行和合并不就是心。何况,经文若要强调“和”,没有必要借助“一”来表达,正如经文已经多处使用的“五行之所和”、“四行和”等;另外,以当时人对《诗经》称引的高水平来看,经文若要引诗表达五行之“和”,也决不会引含“一”字的诗,必然会引含“和”“同”字的诗。说文对此应当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文的解释中也没有出现“和”。
以下接着解释“能为一”:
“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11)
诗赞美了“一”,经文要人们在实践中做到一。那么,什么是一?人怎么能做到一?说文指出,一与多相对,一就是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就是化多为一。而联系此句下紧接的论慎独的“舍夫五而慎其心”的说法来看,这里的“多”具体来说当是指“五”,故以多为一即“以夫五为一”。“五”指五官,心之所用者五官,“能为一”就是使五官所用专于一。可见,“能为一”就是使心之诸多所用皆专一于一处。这合于汉儒对此诗的解释。也有学者主张把五解释为五行,然而,“能为一”是从“其仪一也”而来的,如果“其仪一也”的“一”是专一,则“能为一”的“一”当然也是专一。从而专一一心所相对的多或五,就不能是五行,也就不可能解释为五行和合。(12) 同时,要了解这个“一”,还需要与“独”联系起来,把“为一”和“慎独”联系起来。经文说“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也。”可见,一和独是相通的概念,根据前面所作的分析,一是指心的专一,独是指心的独自主宰,而一和独都是为了使精神从外转向内,专注于内心。(13)
由于慎独是为“一”服务的,所以说文在论释慎独之后,又谈到一:
(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夫为□心也,然后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
独是舍去五官向外的作用,所以能慎独自然就能促进一。照这一段的说法,独而后“一”,一乃是德,德即是天,在这个意义上,一不是认知的状态,而是标志德的境界,而且,德体现了天,天体现于德,德和天是一致的。然而,如果我们前面对“一”的解释无误,那么说文在这里显然有一种跳跃,即把“一”等同于“德”,而这在前面的论述中是不能直接推出来的。我们只能说,人能排除感官向外的作用,专注于内心,这种慎独所得的内心状态也就是“德之行”五者和而未分的状态(也就是中庸所谓的未发),亦即德的状态。(当人诉诸行为的时候,五行必然分化,行义便是行义之心,行仁便是行仁之心。)五行形于内而协和,体现了天道的和谐,故说德合于天道。这里出现的跳跃也应是庞朴等以“五行和”解释“一”的缘由所在,即:从“一”直接等同于“德”的结论,向前追溯,用“德”去解释前面的“一”和“舍五”。其实,在竹简古文献中这种跳跃很为常见,古人的文字亦不注重逻辑,我们必须把其中的跳跃弥补出来,而不是无视它所预设的中间过程、简单地利用其结论。在解释实践上,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一个概念出现的具体上下文环境中来认识其意义,而后考虑如何在整体上加以贯通。
最后,我们想指出,上面所说的“一”与“同”亦有类似处:
同者,(犹)约也,与心若一也,言舍夫四也,而四者同于善心也。同,善之至也。(说19)
约是通约、减省,也是化多为少的意思。这句话本来是讲四行和、和则同,照这个讲法,同是指四行的同,同也是与舍有关的,同就是舍夫四而达到“同”于善,就是说,在“同”的境界上,四行不再分别,不再分别就是舍去分别,而不再分别也就是一(与心若一),亦即达到浑然之同的善心,亦即一浑然整体不分化的心。在说文这里,“四行和”的四行是指形于内的仁义礼智,仁义礼智如皆形于内,便不是彼此分离的个别德性,而内在地共同构成了善心。这个善心是一体化的道德意志。
应当承认,经文和说文的慎独、为一的说法都比较复杂,不易得到明确理解,这应当既是孟子后来放弃此类说法的原因,也是思、孟受到荀子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德气说
帛书《五行》的经文中有3章,用“不…不…”的语式,强调仁、义、礼的道德行为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心理过程:
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10)
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11)
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12)
经文以亲爱论仁,以果敢论义,以恭敬论礼,其中对仁和礼的理解与春秋以来德行论相同,而对义的理解,有其特点,即强调正直、果敢、断制,已表现出与春秋时代的不同,这种理解和《礼记》记载的孔门七十子及其后学对义的理解也是有所不同的。(14)
在说文中,对仁、义、礼三种道德德行的解释,则引入了“气”的概念,这是很有特色的。如说10:
“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
在经文中,变和勉都是“仁”这一德行在内心的发端,而在说文这里,把作为内心发端的变和勉解释为”仁气”,这是说部的发明。
不仅对仁是如此,义、礼皆然。
说11:
“不直不肆”。直也者,直其中心也,义气也。
说12:
“不远不敬”。远心也者,礼气也。
“不尊不恭”。恭也者,(用上)敬下也。
“恭而后礼”也,有以礼气也。
在经文中,作为仁之端的变、悦、戚、亲、爱,作为义之端的直、肆,作为礼之端的远、敬、严、尊、恭,有的是作为情感,有的是作为意向,有的甚至是心态,但都是还未达到明确的仁、义、礼道德意识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变、悦、直、肆、远等这些概念所表达的都是“前道德意识”的内心状态和意向表现。仁、义、礼才是明确的道德概念。而相对于已经实现的仁、义、礼行为,从变的意向到仁的意识、从直的意向到义的意识、从远的意向到礼的意识,都可以说是“前道德行为”的阶段。说文把这些前道德意识和前道德行为的阶段都称作气,表示作者对德行的理解,不是仅仅将之理解为行为,而是用气来表达行为之前的心理状态和活动,如“仁”不是仅仅指一种现实化了的行为,行为未曾现实的时候,内心已有仁气的活动发展。因而,这种说法无疑也是一种把德行的理解内在化的说法。
不仅尚未达到明确的道德意识的内心状态是仁气、义气、礼气,在作者看来,一切正在现实化的行为都依据于气,故也都可以用气来表示,因为一切行为都是气所支持和鼓动的。
说18:
“知而行之,义也。”知君子之所道而杀然行之,义气也。
“知而安之,仁也”,知君子所道而恧然安之者,仁气也。
愀愀然而敬之者,礼气也。
这里的“知而行之义也”,“知而安之仁也”都是指正在实现出来的行为,“知君子之所道而杀然行之”,和“知君子所道而恧然安之”,也都是正在实现的行为。作者认为它们也是气。我们把这种思想称作德气说,即用气来说明德行的心理动力机制和德行的进行时态。杀然、恧然、愀愀然,都表示行为是在某种动力性心态支配下实现的。
说19:
“见而知之,智也。”见者明也。智者言由所见知所不见也。
“知而安之,仁也。”知君子所道而恧然安之者,仁气也。
“安而行之,义也。”既安之矣,而杀然行之,义气也。
“行而敬之,礼也。”既行之矣,又愀愀然敬之者,礼气也。
所安所行所敬,人道也。
在说文的这种解释中,对于仁、义、礼、智、圣五行,是有所区别的,在解释仁、义、礼的时候用仁气、义气、礼气,但解释圣、智的时候却从不使用圣气、智气的说法。作者也未说明其理由。圣智与闻见关联,闻见不是实践德行,或者用中国哲学的说法,闻见偏于“知”,而不属于“行”,故不宜用“气”来说明;仁、义、礼之行超出知觉成为行动,故用“气”加以说明。“圣”、“智”指向知天道,“仁”、“义”、“礼”指向行人道,前者是理智德行,后者是实践德行。我们知道,希腊哲学中区分了理智德性与实践德性,看来,《五行》的作者对理智德行和实践德行的理解有所不同,实践德行的现实需要气的参与,理智德行则无需气的参与。古代儒家哲学用“气”来表达其对理智德行和实践德行的区别,这是很有特色的。它也表达出,道德行为不仅是道德意识的直接现实,也需要某种动力性的身心要素的参与和支持。《孟子》书中讲的浩然之气,正是扮演了这样的角色。(15)
气是动力性的存在,内心的情感情绪及诉诸行为,都是含有某种动力性的活动。而气不仅可以作为行为的要素,也可以表示前行为的内心状态,以便于说明德行从发端到完成是一内外连续的动力过程。从现代哲学的角度看,德气说不是把理性看成道德行为的惟一原因,而是充分注意到现代哲学所说的“理性之外的心理原因”(戴维森)(16),表明儒家哲学对实现道德行为的诸要素有着比较完整的把握。
《五行》篇关于仁、义、礼的区别和对仁、义、礼各自特性的把握,与春秋以来的德行论是一脉相承的,从不同的内心趋向和活动特性来把握仁义礼诸德可谓《五行》的特点,而这一点在《孟子》书中,通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表达得更为清楚了。
最后简单提一下说文对“不……不……”论述的解释,经文10说“不变不悦”,在说10中这样说明:
“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悦而后能戚所戚。戚而后能亲之。亲而后能爱之。爱而后仁。
说文的特点是,把带有逻辑关系的陈述形式“不……不……”,把必要条件的陈述形式,都明确变为“而后”的时间先后关系的叙述。说文作者在其他几种论述中的解释也有这样的特点,如说14:
“亲而笃之,爱也”。笃之者厚,厚亲而后能相爱也。
“爱父,其杀爱人,仁也。”言爱父而后及人也。
此外,经文6论仁之思安、温、悦、戚、亲、爱,是无对象的心理情态;经文10的变、悦、亲是无对象的心理情态,戚、爱是有对象的心理活动,而说文的解释是:
变者而后能悦人,戚人,亲人,爱人,以于亲戚亦可。(说10)
在说文中把悦、戚、亲、爱都说成悦人、戚人、亲人、爱人,这就把《五行》经文从内心发端到外化为行为的过程的时间性更明确地展开为一种对象性的道德意识,同时,把属于仁的悦、戚、亲、爱都与“人”直接挂钩,这可以说是受到了《中庸》和《表记》所谓“仁者人也”的影响。
《礼记·乡饮酒义》曾提到“温厚之气盛于东南,此天地之仁气也”,但是《礼记》的“仁气”“义气”的说法是与古代方位说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哲学的概念,这与《五行》中的德气作为行为的心理动力是不相同的。《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提出:“信气中易,义气时舒,智气简备,勇气壮直。”也是把德行和气联系起来,与这里所说有一致之处。
四、大体说
帛书《五行》说文的大体小体论,也与孟子思想相同。见于说22: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耳目也者,悦声色者也。鼻口者,悦臭味者也。手足者,悦佚愉者也。心也者,悦仁义者也。此数体者皆有悦也,而六者为心役,何也?曰:心贵也。有天下之美声色于此,不义,则不听弗视也。有天下之美臭味于此,不义,则弗求弗食也。居而不问尊长者,不义,则弗为之矣。何居?几不胜也,小不胜大,贱不胜贵也哉!故曰心之役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体之小者也;心,人体之大者也,故曰君也。
经文指出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和心的关系是使役者与被使役者的关系,说文认为,心贵于六者,心是使役者,支配六者的活动,六者是被使役者,服从于心的指挥。心与六者都是“体”,心是人体之大者、贵者,可称为大体,六者是人体之小者、贱者,可称为六体。心与六者的这种关系,特别体现在六者之所悦必须服从心之所悦,说文作者认为,耳目等六者追求的是对于感性对象的悦乐,而心的特点是悦仁义,即道德理性;六体的审美活动是在心悦仁义的主导下,如果享受感性的悦乐有违于道德理性,心就会加以制止。
《孟子·告子上》: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以与我者。
虽然,《五行》所论基于个体的人,《孟子》所论重在不同个体的同然,但《五行》说文的基本思想,完全同于孟子,其论心悦仁义,即孟子所谓礼义之悦我心;其论体之小不胜大,贱不胜贵,论体之小者和体之大者,与孟子体有贵贱、有大小、及大体小体之说完全相同。
又如《尸子·贵言》篇:
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不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弗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
孔子早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此种思想在战国时代也颇多见(17),而《尸子》的这些说法与《五行》相当一致,很可能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至于心为君的说法,《管子·心术上》提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其年代当与孟子接近或在孟子前,故可知这种说法在战国前期已经流行。
“和则同”。和也者,小体变变然不患于心也,和于仁义。仁义,心也。同者,与心若一也。□约也,同于仁义。仁义,心也,同则善耳。(说22)
这里指出,所谓“和”,就是小体不患于心,而和于仁义。特别是,这里还提出“仁义,心也”,这是很有标志意义的命题。传统德行论可以说以“仁义,行也”的思想为之预设,故说文以仁义为心的思想强调化德行为德性,正是对于传统德行论的重要进步。
让我们再来看一段论仁义之心的材料,见于说23:
循草木之性,则有生焉,而无好恶。循禽兽之性,则有好恶焉,而无礼义焉。循人之性,则巍然知其好仁义也。不循其所以受命也,循之则得之矣,是侔之已。故侔万物之性而知人独有仁义也,进耳。……文王源耳目之性而知其好声色也,源鼻口之性而知其好臭味也,源手足之性而知其好佚愉也,源心之性则巍然知其好仁义也。故执之而弗失,亲之而弗离,故卓然见于天,箸于天下,无他焉,侔也。
故曰侔人体而知其莫贵于仁义也,进耳。
学者往往把五行此段和《荀子·王制》“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相对照(18),其实,这里的思想在根本点上与荀子不同,《荀子·劝学》说:“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好之有天下”,以心之所好为有天下;而《五行》说文则明确指出人之性好仁义,这与荀子完全不同。而且《五行》说文认为万物中只有人之性有仁义,并指出人之性也就是人心之性,这显然是上述心悦仁义说在人性论方向上的发展,是与孟子性善论思想相契合的。虽然《五行》篇中没有出现“性善”的说法,但我们可以说,在这里,人性善的说法已经呼之欲出了。
我们已经指出,荀子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谓之“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如果竹简《五行》是子思所作,那么,很明显,荀子说的“子思唱之”,就绝不是指《中庸》而言,而必是指《五行》经部而言。换言之,用《中庸》的隐微的仁义礼智圣说去证明“子思唱之”是远不够的。由此也可知,荀子说“孟轲和之”,也绝不是指《尽心》篇的一句话,而必另有所指,用《尽心》篇的一句去证明“孟轲和之”是远不够的。既然荀子指名批评子思、孟轲,必有二人明白倡导五行说的作品为之根据,换言之,荀子应看到过帛书《五行》篇的文献,而且他知道此篇乃子思唱之于经,孟轲和之于说,所以他才有这样明确的批评。子思作五行的经文,孟子作五行的说文,此一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篇,应是荀子作出如此批评的主要根据。(19) 本文则希望从思想和文句的比照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孟子作《五行》之说文,盖在其中年,则对《五行》说文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孟子前期思想的发展的各个侧面,也有助于更深地理解孟子书本身的许多提法的背景和来由,更可看出孟子思想的形成也曾借助于古典文本的诠释,从而使我们对孟学的认识更为拓展。同时,由于在我们看来子思和孟子具有被诠释和诠释的关系,这使得所谓“思孟学派”具有了更加直接的承续关联,从而,有关“思孟学派”的传承和内涵也都可借助《五行》而获得一新的肯定。
注释:
① 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孔子研究》2007年1期;《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2期。
② 已有相关论文可参看:李景林《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载《人文杂志》2003年6期。廖名春《慎字本义及其文献释读》,载《文史》2003年3期;《慎独本义新证》,《学术月刊》2004年8期;以及张丰乾在网上发布的《慎独之说再考察:以训诂哲学的方法》。
③ “之谓”后缺字,魏启鹏补作独。“然后一”前独字原脱,庞朴与魏启鹏皆补作独。八○本(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原文“夫五夫为□也”,魏启鹏以为有脱衍,订为“以夫五为一也”。
④ 见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11页。
⑤ 这里的分析稍涉复杂,如果“独”就是舍体,则“独”在这里成为动词。但若“慎其独”的独也是用作动词,则慎便是副词了。而且,既然“慎其独”即慎其心,则独似乎便可说是心了。而照以上所说,舍体之独并不是心,是舍去五官作用而后仅仅守其心。此外,独然后一,则慎独以一为目的。
⑥ 魏启鹏云:“此处体与心对举,体即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32页。
⑦ 关于《五行》的慎独说,已有若干讨论,可参看简帛研究网所载梁涛的论文《关于慎独的训释》等与钱逊的文章《是谁误解了慎独》等。又庞朴曾引《荀子·不苟》、《礼记·中庸》、《礼记·大学》、《礼记·礼器》各篇慎独之说,指出,“儒书屡言慎独,所指不尽相同”。见其《帛书五行篇评述》,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164页。
⑧ “淑人君子”至“仪”字,阙字皆庞朴所补,见其所著《竹帛五行篇校注》,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39页。
⑨ “其仪一也”诗句出自《诗经》曹风,古书常见称引。与本篇说文解释相近者,如《说苑·反质》:“诗云: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传曰:尸鸠之所以养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万物者,一仪也。以一仪理物,天心也。五者不离,合而为一,谓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结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又,《毛诗》鸤鸠序曰:“鸤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集传》:“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专一。”皆以“专一”释此诗。以上诸说分别引自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41页;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30页。
⑩ 以一为五行和的观点可见于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载《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41页。池田知久亦以“一”为仁义礼智圣五行的调和、统一,及自心的一体化状态,见其所著《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213、226页。
(11) 八○本已补“五”字。
(12) 说文最后一章即说28中有一处以五为一的说法:“闻道而乐者,有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闻君子道而以夫五也为一也,故能乐,乐也者和,和者德也。”(说28)这里的“以五为一”应当不是指专一,这里的“以夫五为一”可以理解为单一化、同一化。庞朴认为这里解释好德者的“以夫五为一”和前面解释能为一的“以夫(五)为一”,都是指以仁义礼智圣五行和合为一,五行和合为德。然而,解释必须内在于上下文的脉络,从这点来看,庞朴这种五行和合的解释作为“闻道而乐”的说明是合理的;但作为“能为一”的说明,则和《说7》本身的“一心”的解说似不合。“能为一”的“一”,就是“其仪一也”的“一”,故说文用来解释“其仪一也”的“一”的“一心”,也必然主导着“能为一”的“一”的解释。这个一就是一心一意的专一。所以,我们不能无条件的用说28的讲法来为说7补字并解释说7的意思。
(13) 说文又说:“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夫为心也,然后得之。”在这里,独字是今人所补,若所补无误,“独然后一”应是指只有心独自地、不受五官影响地发挥作用,才能做到一。独然后一的一是什么呢?“一也者,夫五夫为心也”,按后句不通,魏启鹏认为应作“以夫五为一也”,这应是依据上文“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而推定的,然而,其所依据的“言能以夫(五)为一也”旬中之“五”字已经是学者根据说文最后一章(350行)所补,故此说究嫌改字过多,原文究竟如何,仍难确定。
(14) 按《礼记》中无以果简论义之说,《中庸》云“义者宜也”,这是《礼记》各篇论义的主流,惟《乐记》“义以正之”、《聘义》“有义之谓勇敢”略近《五行》所说,然终不同。
(15) 庞朴在其《帛书五行篇评述》中已经指出:“很自然令人想起孟子的类似观点。孟子有夜气或平旦之气、浩然之气,以及守气、养气之论。”见上书,167页。
(16) 罗蒂对戴维森此说有中肯的评论,参看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31页。
(17) 可参看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495页。
(18) 如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513页。
(19) 参看拙文:《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君子慎独论文; 五行论文; 孟子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中庸论文; 慎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