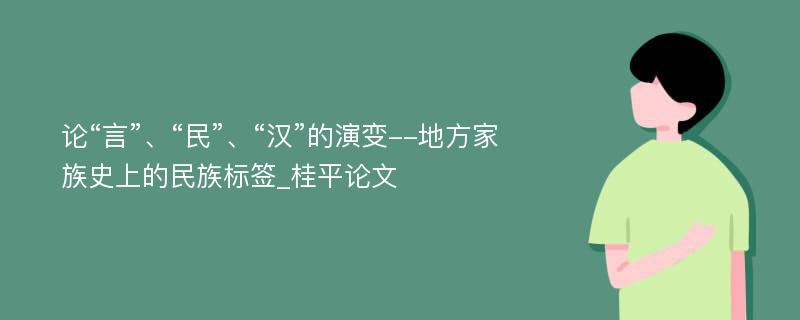
试论“猺”、民、汉的演变——地方和家族历史中的族群标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试论论文,家族论文,标签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处广西中东部的大藤峡地区在明代发生了持续近百年的“猺乱”,文献记称当地的主体居民为“猺”。本文考察的崇姜里(今桂平市南木镇)正位于大藤峡入峡口,即文献所记的“猺乱”核心区。不过,现今却发现这里的人大都被识别为汉族,自称也为“汉族”,而言及祖先的来历时大都云“来自广东”。事实上,类似大藤峡地区这种文献记载的土著“消失”不见,被自称来自广东的人群取代的情形在广西沿西江流域地带相当普遍。
这事实令人不禁追问:“猺”人何在?土著何在?明清时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是族群标签的改变,还是真的有过人群整体时空位移的历史?
人类学家关于族群建构的理论告诉我们,族群身份的建构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族群的分类和标签是他者界定和自我认同的过程。①一些华南研究者则特别注意到国家正统文化对族群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并强调要在具体历史进程中诠释族群标签的流动变化。②本文的写作即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尝试通过勾勒明清时期大藤峡地区的历史进程及人群身份标签的变化来探讨上述诸问题。
一、明代大藤峡“猺乱”及地方族群由“猺”到“民”的变化
大藤峡地处西江流域中段(此河段称为浔江),广义上以明代广西浔州府为中心,地域六百余里;狭义上指位于黔江中下游,由武宣勒马滩至桂平驽滩长约75里的航道,异常险要。而祟姜里正位于浔江北岸大藤峡入口之处,控扼着让人望而生畏的峡江沿山地带,故乾隆桂平县志列其为府治要区,言其“罗洞岭岈,藤峡险隘,紫荆虎踞,黄水蛇蟠,地分表里,府治要区”。③
明朝在浔州府设流官,不过,在明前期,并非府区内所有住民都为编民,大体上,州县可控制者为县城及周围平原之村落。其时大藤峡山区的主要居民被称为“猺蛮”,所谓“万山之中,猺蛮盘踞,各有宗党,而蓝、胡、侯、盘四姓为之渠魁,山多缦田,土沃而敏树,诸猺皆侧耕危获,不服租庸”。④即大藤峡腹地山居的“猺”是不负担赋役的群体,自有酋长和松散的社会组织。文献还称这些“猺”时常在峡江两岸四出勾掠,田汝成追记嘉靖以前大藤峡的情况云:
曩者,江介诸摇,凭据利地,厚其徒党,裒凶鞫顽。官司一切因循,为苟且姑息之法,掊掣商贾,瓦器、鱼、盐公为赍给,如以赂贻,名曰“常例”,以致狼贪无厌,骄焰益张。白昼横江杀人剽货,舟揖孔道隔阂不通……。旧规,峡江上水,商船大者纳盐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纳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银一钱八分……原属浔州卫收贮,转给各猺,名为埠头常例。⑤
此为嘉靖年间的追述,无法判断是否为明前期的实态,不过,由于大藤峡江道水急滩多,异常险峻,而世代生活于峡江两岸的土著则深谙江中的急流险滩,能导引船只顺利进出。因此可以推想,他们一直就是江道的主人,并在渠魁们的操纵下把持峡江,收取通行费,这种做法得到官司姑息,浔州卫参与其中,若有不遂,“猺”人则横江阻道。故在明代,大藤峡被视为“猺贼渊薮”。
不过,大藤峡江道是广西西部和北部食盐运输的必经通道,盐税又是明政府在两广最重要的税收来源,⑥因此,保证江道畅通成为明朝廷及两广地方最关注之大事。明初,浔州府设浔州卫,沿江设递运所,以卫所兵保护船只通航。⑦不过,军方报称屡有“猺”沿江劫杀,阻挠江路,故洪熙年间顾兴祖举兵征剿。⑧军事行动后,朝廷用向化土人充任副巡检以加强管理,正统十一、十二年(1446、1447)在广西增设了74处巡检司及土副巡检,新增巡司多位于西江及支流,以确保江道畅通。⑨明代巡检最初由流官出任,而上述土副巡检则从巡检司就地佥点的弓兵中直接选拔,被任用者是“平昔夷民信服,才能可用”之地方土著。⑩就在此阶段,大藤峡入峡口处也设置了靖宁乡巡检司。(11)
不过,巡检司及土副巡检之设似未达到预期目的,文献记称大藤峡“猺乱”反而愈演愈烈,著名的侯大苟之乱初见于正统七年,而在正统后期至景泰初已变得无法遏制。(12)靖宁乡巡检司因屡被“贼”劫不得不迁至远离江口的甘村,副巡检一职也缺员年久。成化元年(1465),朝廷遂派韩雍率土狼官军大举征剿大藤峡,平定乱事后,韩雍任命任真为新的靖宁乡副巡检,并将巡检司重新迁回驽滩。(13)万历《苍梧总督军门志》记载靖宁乡的土副巡检为薛思聪和任真。(14)任真是成化二年任职,而此前靖宁乡巡检司缺员年久,故首任土副巡检薛思聪很可能是正统年间朝廷大规模任命广西土副巡检时授职的,而其时土副巡检是从当地弓兵中直接选拔。因此,薛思聪的身份应为靖宁乡土著。
韩雍平乱后,朝廷主要依靠桂西的土司狼兵维持大藤峡江道,大量狼兵进驻当地。不过,峡江瑶人依然活跃,冲突也时时激化。因此,在正德、嘉靖年间又三次征剿大藤峡,而每次大征后,均招抚“叛猺”以调整地方秩序。比如,韩雍平乱后就“招其流冗千余人,编为民户”。(15)嘉靖初年,王守仁平乱后开始推行里甲,他要求地方官“亲至已破贼巢各邻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抚恤……若彼贼果有相引来投者,亦就实心抚安招来之,量给盐米,为之经纪生业;亦就为之选立酋长,使有统率,毋令涣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开立里甲,以息日后之争”。(16)即在给予土著投抚者盐米外,还为其立酋长,编里甲。王守仁还颁布《告谕新民》要求善待受抚之瑶僮“新民”,言曰:“告谕各该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后各要守法安分,务以宁靖地方为心,不得乘机挟势,侵迫新、旧投抚獞、猺等人。”(17)从“十冬里老”的称呼可见大藤峡地区确已编制里甲。而一旦受编,在官方文献记载中,土著瑶僮的身份便会脱去代表“蛮”的意味的“猺”、“獞”标签,而成为“新民”。只不过,其时这些“新民”的归附还不稳定,其身份标签也因在里甲体制内外而变化:里甲之内者为“民”;一旦逸出于里甲之外则成了“猺”、“獞”。
嘉靖十八年(1539),大藤峡乱事再度加剧,翁万达、田汝成率军征讨,此次征剿深入至土著山民之老巢,而且翁、田在战后提出善后七策并获批准推行,(18)最终使保甲制度真正在崇姜里得到实施。善后七策中的首策“编保甲以处新民”是对地方社会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举措。此款内容有三:
一是“令江北一带,西自碧滩,东连林峒,皆南渡蓼水,垦作便田。江南一带,东起蒲竹,西绕河源,亦托处平原,远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训辞”。即是将浔江北岸大藤峡腹心地的碧滩到林峒一带山区的“猺”转迁至沿山平地,安置于蓼水(即今桂平南渌江)南岸、浔江北岸的大沙洲上垦田种植,这个大沙洲即是崇姜里。二是将新民编入保甲,即是将新归附的“猺”单独编制,自成保甲体系。据其时兵部尚书毛伯温所言“丐降、听抚者二千九百有奇。咸自犁故巢,挈迁旷原,以就编隶”(19)看,编保甲之策得到实施,受抚之“猺”由深山迁至旷原编入了官方体系。乾隆地方志明确提到在平乱后大藤峡内碧滩等地招人耕种,并编制了保甲,这些被招来者即是“向化良猺”。(20)之所以将“猺”另行编制,是为妥善处理大藤峡通航问题。为此规定:编入保甲的土著每保每月轮派一个总甲长以承当官府差役、护送出入峡江的船舶、调解“猺”人纷争;总甲长下设保长征催赋税;充当保长、总甲长者为“稍有恒业、能通汉音者”。值得关注的是,通过上述措施后,土著已归入到国家管理体制中,在官府掌控下,以服役的方式出入峡江,要向国家交赋纳税。三是规定在近郊和府城设立墟市,招“诸猺”贸易。这一规定使土著可通过正当贸易途径获取必需日常用品,而不必再依靠沿江抢劫的武力手段。
一直以来,朝廷解决大藤峡问题的首要目标是为保证峡江通畅,而嘉靖年间的善后七策则巧妙地通过上述措施,将原来游离于国家体制外、不赋不役、阻挠通航、被标示为“猺”的人群转变为国家体制内由县官管辖、交粮当差的编户齐民,从制度上消除了“瑶乱”产生的动因。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非常成功,此后,文献上鲜见大藤峡“猺乱”的记载。到万历年间,在官方编撰的《殿粤要纂》桂平县图中,崇姜里这一“猺乱”核心区已全部被标注为“民村”,(21)当地那些原被称为“猺”的人群至此遂成为“民”。
二、清代国家正统化秩序的确立与祖先故事的书写
在翁、田将峡江两岸被称为“猺”的土著编保甲,使之成为国家编民时,崇姜里是受编土著最主要的集居地。不过,笔者目前在崇姜里收集到的族谱及口碑材料,人们大都称自己为汉人(少量自称壮族),几乎无人自称瑶人。那么,清代这一地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现今田野调查所见人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呢?
(一)清代国家正统化秩序的确立
清代大藤峡沿江平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国家正统礼仪秩序在地方上的确立。明中期以来,王朝政权在当地进行军事征剿并将土著招抚为民的同时,还通过建学校、兴科举、推广正统神明崇拜等方式建立正统礼仪秩序。不过,有关明代崇姜里住民读书科考的资料甚少,唯一相关者,是万历《广西通志》记载有浔州府举人薛文于正德八年任国子助教的资料,(22)这与本人采集的崇姜里薛氏日凤公支旧谱中所记第三代薛惟深于正德八年中举、官国子助教的记载相一致。(23)其时朝廷对大藤峡是剿抚并用,归服者或许确有科考中举的可能。只不过此族谱是清后期修撰,而薛惟深作为族谱记载的唯一举人,却既无后代亦无人承祧,是绝嗣。因此,也不排除薛氏编族谱时抄录通志的可能。而可以明确的是,即使真有薛惟深正德八年中举之事,对当地人群也几乎没有实质影响,因为嘉靖年间这一地方又陷于动乱,在官方文献记载上,崇姜里大部分住民还是被称为“猺贼”。
正统化礼仪秩序在当地的真正确立是在清朝政局稳定后。这一秩序的建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地方社会主动参与的结果。位于崇姜里和社墟(今南木镇和社村)的宾山寺是清代崇姜里全里庙宇中心之一,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寺里至今保留完好,涵盖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民国时期的系列碑刻31通。这些碑刻时间基本接续,内容以庙宇多次重修的捐款题名为主,恰好提供了我们观察清代崇姜里地方人群身份及信仰意识变化的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人群日益表现出对正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他们之中读书应考并获功名者越来越多,并主动接受国家祀典神明、将地方神改造为正统神明,还在当地创建宗族。(24)而在此过程中,土著人群的身份认同也悄然发生了改变。
崇姜里对文昌神的奉祀是表明地方对国家礼教主动认同的典型例子。由寺中的碑刻可知,当地对文昌神的奉祀经历了由加奉寺中到独立建祠两个阶段的变化。据康熙六十年(1721)的《重修碑记》(25)记载,宾山寺初名仙沙寺,寺中最初奉祀大士观音,至康熙重修时,加祀了文昌神。从捐款题名碑看,列于最前者为浔州府各级官员,明显体现官府“神道设教”之意。紧随其后者为地方缘首及绅衿,多为有功名之人,他们应是重建此庙和倡导加祀文昌神的主体,表明加祀文昌神与该里科举事业发展之相一致,显见国家教化对当地的渗透。不过,此块宾山寺年代最早的碑刻也仍让我们窥见一些国家礼教未及而遗留的土著社会痕迹。其一,紧随缘首绅衿之后人数众多的男性村民捐款名单中,有诸如薛帝护、薛火帝、薛玄祖、薛禅应、薛帝保、薛帝木、黄玄经、赖帝茂、韦法象、张师严明等名字,此类命名方式与瑶人的宗教信仰传统密切相关,(26)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他们的土著身份。其二,排在最后的名单非常特别,是一独立于男性的女性捐款名单:
缘首 莫门区氏二两 林门谭氏六钱 薛门林氏囗钱 甘门薛氏四钱
信女 罗门谭氏七钱 罗门陈氏四钱……薛门覃氏三钱(下略)
最引人注目者是她们有自己的缘首,表明这是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女性群体的组织。这种女性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传统,显然不同于清代标榜儒学正统礼教的所谓“汉文化”对于女性抛头露面参加社会活动的限制,而属于华南地区那些被称为“猺”、“獞”的土著人群的传统。
乾隆年间,随着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崇姜里士绅的力量有了更大增长,因此,需要为文昌神建立专祠,乾隆四十年(1775)的《建文昌祠魁星阁碑记》记曰:“宾山在浔江之北,主思陵而峙东塔……为桂平八景之一,名曰‘宾秀特朝’。……夫山之胜可以壮丽观,而神之灵更以培士气,以故前人奉文昌像于其间。……暨魁星掌桂籍,主禄位,而乃寄于浮屠氏之居,或非所以振文风而崇儒道。会集好义之士,慨然乐输,议迁于原山之半,建新祠,立魁阁。”(27)即是认为文昌没有专祠而寄于浮屠之居不利于地方文风,也非尊崇儒道所为。因此,增建了文昌专祠和魁星阁,既表明地方士大夫要以礼教改造地方的努力,也是他们人数增加、力量发展后意欲借此取代佛教及原有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控制的举措。与康熙年间主持修庙者为无功名村民不同,此次工程的总缘李正阳为郡廪生。参阅其他碑刻可知,李正阳还主持了乾嘉年间该寺的重修、创办保正义田及驽滩甘王祖庙的重修等事。(28)可见以李正阳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已成为地方事务的代言人。此次改建,李正阳还将仙沙寺更名宾山寺,此命名有很重要的意蕴:原名仙沙寺是一个具宗教意义且比较土俗的名称,而宾山之名则取自该庙在地理上相对于桂平思陵山主山而处于宾从地位之意,是乾隆年间桂平知县吴志绾列该寺为桂平八景时所命名,可见更有官方性质、更符合士大夫的雅致韵味。而在此次捐款名单中,再也不见康熙碑中“薛帝护”之类表明土著信仰传统的命名方式,全部名字均已十分规范且符合儒家文化意味。更重要者,是自此之后直至民国,宾山寺的碑刻都再也不见女性独立筹款并自有缘首的组织方式。
地方的正统化过程还体现在宗族建设上。明清华南的宗族得到较大发展,在浔州府,虽然时间上较珠江三角洲晚,但亦可见此一历史过程。尤可注意者,当地的宗族建设最初多见于落地生根的粤东商人家族,其后才扩展至地方土著家族。而此一现象背后其实正是浔州府在清代经历的另一重要历史过程,即两广米粮贸易引起的地方开发及粤东商人对当地社会的重大影响。
(二)“来自粤东”的祖先故事的书写:以崇姜里薛氏为例
明清时代,带动广西经济开发的最重大事件是两广米粮贸易,浔州府正居于贸易网络中转站及市场辐射中心的重要位置,加上该地区的冲积平原是广西少有的优良稻谷生产基地,因而成为两广米粮贸易最重要的依托。清代,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当地平原的迅速开发,大批粤东客商沿西江进入浔州府,其中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户籍,定居当地,进而参加科举考试,完成了本地化过程。
更重要的是,其时的米粮贸易得到朝廷及两广总督府的大力支持,粤东商人因而在经过与土著的冲突调适后得以成为地方事务的主导力量,其文化习俗因而深刻地影响土著群体。学界的研究表明,粤东的士绅化进程及宗族建构早于粤西,事实上,就笔者在浔江地区所见,本地化的粤东商人也是当地最早开始宗族实践的群体,如桂平宣一里王举村的谢氏、宣二里王谟村的刘氏等均在清前期就开始编族谱、建宗祠。(29)
粤东商人创建宗族的行为遂成为土著效法的榜样。清中期之后,此类行为愈来愈普遍,一些土著家族也致力于宗族建设,崇姜里薛氏即为其中之一。薛姓在崇姜里的分布集中于新宁、古楞、黎村和三鼎等村,现今这些村子的薛姓均自认同宗,并在新编族谱中以来自广东顺德龙江村的日经、日明、日凤三兄弟(简称“三日公”)为入乡始祖。(30)不过,仔细比对旧谱,却发现对广东始祖“三日公”的认同恰恰与崇姜里薛氏创建宗族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前文言及正统年间靖宁乡土副巡检之一为土著薛思聪,不过成化之后不再有关于薛思聪族人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中期,当地一直有薛姓人群在活动。笔者采集的薛氏日经、日凤公支族谱对其始祖定居当地的时间记忆,一在成化,一在正德,并言因地方乱事而导致先祖定居生活几度被中断,嘉靖时才基本稳定下来(详后)。而成化、正德、嘉靖恰是朝廷对土著瑶人大规模剿抚时期。因此,族谱中的始祖定居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薛氏在里甲体制内外流动,并与崇姜里其他土著一道,最终接受朝廷招抚和安置的事实折射。
从现在保留的旧谱看,标注时间最早的薛氏族谱为浔江南岸(简称南江)社坡镇伏化村日明支七房保留的《宗支部》两本,为乾隆二年薛廷璋手立,谱中记言:“再始之祖世荣公,葬在北江珠砂岭。始祖日经公,妻陈氏,同葬在甘棠村面前。积浩公,妻罗氏,同葬在本村堂屋岭。胜集公,妻陈氏,葬在堂屋岭。”(31)北江珠砂岭在崇姜里新宁村附近,故此份《宗支部》是与崇姜里薛氏相关的旧谱。谱中以世荣公为最始祖,日经公为始祖,值得注意的是,此份谱本并无三兄弟之说,也无始祖来自广东顺德龙江的提法。当然,此谱内容简略,只记录各代祖先及配妻名字、葬地,还不是近代意义上之联宗族谱。
关于广东“三日公”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嘉道年间,其时,桂平薛氏开始编写首部联宗族谱,谱序称修谱之目的为“收族睦属”,故可视为薛氏宗族创建的标志。正是此谱序首次出现了“三日公”自广东迁居桂平之说:“吾祖迁住粤东广州府顺德县龙江村,至日凤公与兄日经、日明,在明成化年间,客游粤西浔州府桂平县安居乐业,至今十余世矣。”谱序中还特别强调薛氏为粤东血脉,确有所本,在编谱则例中提到“是谱粤西向来无有,祗以各家誉注年庚,用以联络贯通”,故可知此为桂平最早薛氏联宗族谱。(32)不过,谱序没有说明“三日公”定居何处,因此并无证据可说这个最早的广东祖先故事与崇姜里薛氏直接相关。
可能在此谱编修的同时或稍后,崇姜里薛氏有了自己的宗谱,并且明确使用了薛氏祖先来自广东龙江的说法。其中古楞村日凤公支族谱云:“日凤公与兄日经、日明自明朝成化年间由粤东广州府顺德县龙江村迁移桂平,三人同胞共住,始在三鼎村阳江边经营乐业,后因藤峡寇乱,日凤公与日明公迁往伏化,尚未觉平宁,日明公遂迁于容县,后方回伏化,日凤公又迁于黎村居住。”(33)而新宁村日经公支薛嘉模修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族谱则云:“太祖考讳进杰,字守常,号日经。于明正德六年辛未,广东盗贼窃发,南海十三村负固为乱,四出侵掠,民不聊生。由广州府顺德县之龙江与太叔祖日明公、日凤公同迁至广西浔州府桂平县姜里之三鼎村肚。逾年,日明公复迁往南江吉大里之伏化,日明公遗下一子,后复散处同里古楞、黎村。”上述两谱均明确记载薛氏最早定居三鼎村,后分居古楞、新宁、黎村和南岸伏化村。而现今古楞和新宁正是薛氏最集中的居地,亦各言为“三日公”后裔,两谱所记各代名字基本连续,清代祖先名字多有与宾山寺碑刻名单相一致者,故此两份旧谱大体可视为清代崇姜里薛氏情况的反映。
分析上述与崇姜里薛氏相关的三份旧谱,可以发现族谱所记大体覆盖了崇姜里现今薛氏分布的村落和人口,表明崇姜里薛氏大都已共享祖先是来自广东“三日公”的故事,不过,三个谱本关于祖先的来历相互抵牾之处却不少。其一,与崇姜里薛氏直接相关的最早的乾隆谱本的祖先故事并无来自广东的“三日公”的说法。而嘉道年间记载了薛氏来自广东“三日公”的桂平薛氏最早创建宗族的谱序,却无证据表明在最初出现时即与崇姜里薛氏相关。其二,两份清后期形成的薛氏日经、日凤旧谱对“三日公”的入桂原因和时间记载大有出入:日凤公谱言成化时来桂经营乐业而定居,而嘉模谱记述因南海贼乱不得已于正德六年(1511)迁桂,且称日经生于1481年,按日凤谱推算,即使在成化最后一年,长兄日经也才年仅6岁。其三,乾隆谱记日经妻为陈氏,葬地在甘棠村,子、孙称为积浩和胜集。而嘉模本记日经妻为文氏,二人葬于河山岭大坟咀,日经生伯梁、仲梁、孙梁、季梁四子。因此,虽然名号均为“日经”,但显然完全是不同的人,并有不同的传承后裔群体。
记载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最始祖世荣公的存在。最早版本的《宗支部》记载了这个始祖,且事实上,世荣公的墓地珠砂岭正位于新宁村附近,据调查所见及2004年薛氏新谱记载,世荣公考妣墓正是现今崇姜里各村薛氏历来祭祀之墓,每年农历八月二十日薛氏族人集中祭墓并席地设宴聚会(俗称饮粥众山)的习俗已相沿数百年。这都表明世荣公确是崇姜里薛氏共认的始祖。但在日经、日凤支旧谱却只记广东“三日公”而不记此位实际一直受拜祭的始祖。正因为如此,现今的薛氏后裔在编修新谱时感到无所适从。笔者注意到,2004年的薛氏新谱称为《桂平薛氏日经公、日凤公宗支部》,只记“三日公”之两支,而缺日明公支。而日明公支缺席新谱正是因为在祖先来源的说法上与日经、日凤两支有严重分歧。日经与日凤支后裔主张三兄弟的始祖是世荣公,而日明支后裔薛宗源在其1992年主编的薛氏族谱中,却声称日经三兄弟就是广东龙江宝善堂元图系《薛氏家谱》所载的第八世鸾、凤、经三人,此三人的父祖辈均居广东龙江且世系清晰。薛宗源的说法使崇姜里薛氏三兄弟与广东的薛氏接上了关系,给了崇姜里薛氏一个清晰的“广东来历”,但是却否定了被崇姜里薛氏历来祭拜的始祖世荣公的存在,因此引起日经与日凤支后裔的不满。双方为此从1997年始就争执不停,多次开会协商无果,于是日明公支后裔退出了2004年族谱。(34)
由此可见,薛氏关于祖先的来历其实相当模糊,不同谱本的祖先故事反映出不同薛姓人群对于祖先的来历各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因此而引起祖先来历故事的各种歧异。而且,在桂平薛氏的祖先故事中,广东“三日公”的故事并非最早版本,而是在清后期伴随着薛氏宗族的创建和桂平薛氏联宗族谱的编修,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直至最后完全垄断了薛氏祖先来历故事的话语。因此,笔者认为,谱中记述的来源各异的薛氏人群体应有很大部分是明代以来当地的土著。或许由此可“证伪”某些薛氏族谱关于祖先来自粤东表述的证据。当然,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辨别族谱之真假,况且,如果将族谱视为编谱者及其代表的群体对自己身份的历史记忆的表达,则不存在族谱的“假”与“真”的问题。当人们在族谱中对自我身份的表述(或称自我历史记忆)与其他文类的记载以及调查所见的地方社会状态有不相一致的情况时,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去追问导致这两者之间不相一致的历史动因。
由此,有意义的问题是:薛氏旧谱是在何种情况下被编写出来,是什么人在编,编写的目的是什么?下面即以保留最完整的道光嘉模所撰的谱本为例加以说明。
此份族谱属新宁村薛氏。此支薛氏原居崇姜里三鼎村,康熙末年第七代薛胜标迁居新宁村。胜标元配黎氏生显猷、宏猷、建猷三子;继配杨氏生德猷、最猷、敬猷三子。至此,迎来了薛氏发展的转机,尤其是杨氏所生三子,谱载:“(德猷)尝倡造都椰江木浮桥,千万人来往,皆如履坦途。……与五、六弟分而复合,父手分居不过八九斗种,兄弟合后种子五六千,时人称‘难兄难弟’,同居四十余年。”其时,德猷与两位弟弟由分居到复合同居四十余年,历经艰难,终使家业获得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参与地方公益活动,倡造都椰江浮桥,热情参与宾山寺的改建。乾隆五十四年《建文昌阁碑记》记德猷捐银六钱,所捐银两排在捐款榜前列。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文昌祠魁星阁碑记》有薛最猷、薛德猷、薛敬猷和薛岐山捐银捐米的记载,亦排在捐款榜靠前。而在嘉庆三年《创置保正义田二碑》中第九代耀扬、岐杨、秉扬均为首事,嘉庆中期《重修宾山寺院碑》中秉扬、歧彩、岐扬则为缘首。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宾山寺碑记》中薛氏为两名总缘之一,另有副缘一名,首事11名。薛氏积累资产后对科举也有了更多投入,开办了薛氏家塾。于是,薛姓有了佾生、登仕郎。(35)九世薛岐瓒更于嘉庆初中式庚申科乡试第27名举人,成为崇姜里薛氏首位确切的举人。正是在经济获得发展,科举取得成功后,德猷之孙云英、曾孙嘉模开始了编修族谱之举。
此份由读书人书写的族谱有相当突出的特点,即是:习儒受教成为反复被强调的主题,营造出一种薛氏热衷儒业,深受礼教熏陶的景象。在薛嘉模笔下,薛氏已是非常士绅化的家族。他先在谱序追述自黄帝以来历代薛氏著名人物,特别颂扬了出类拔萃的商代仲虺公和明代文清公(从祀孔庙的薛暄),以表白崇姜里薛氏要“绳其祖武”的向学之心。然后,将各位薛氏先祖描绘成致力于读书进学的“士大夫”形象。兹举几例如下:
太祖考讳进杰……集子孙讲明修身为己之学。在乡党中,与父子言慈孝。与兄弟言友恭,劝人为善,诱人读书。……三世祖考讳时习……平素业儒,无书不读,无物不格。……四世祖考讳文田,字书香,号砚池……从父业儒,中年督耕。上事祖父,课子读书。一庭之中,四代同堂,书声喧而机抒闹。……五世祖考讳正鼎……男勤耕读,女勤纺织。尝谓:“读书而惑于他歧则终身无由入圣人之室,耕织亦然,是以业必精勤而戒荒嬉。”……六世祖考讳善寓……一生慕道,口不出非道之言,目不视非道之色。尝谓:“吾宗自文清公之后,圣道之统,鲜有系者。”故笃志业儒,以圣贤为必可学而至,文习六经诸子,武习孙吴韬略,每谓子侄辈曰:“穷经将以致用,故文章之与经济,并行不悖者也。”然数奇,终身困场屋。
以上描述显然有刻意修饰的成分,因为就族谱所记,薛氏此支直至六世祖时仍未见有取得生员身份者,第六代善寓皓首穷经,亦仍与科举功名无缘。
两相比对,明显可见,薛氏族谱呈现的崇姜里薛氏均为来自广东龙江“三日公”后裔的情形,所营造薛氏士大夫化的景象,与前文所述明代崇姜里人群的历史显然大相径庭。前文出现的土副巡检薛思聪、康熙末年仍使用瑶人宗教信仰习俗命名方式的人群均已消失不见;明代“猺乱”与平乱后安置的历史、清前期宾山寺捐款题名碑中土著妇女自我组织参与庙宇事务的情形,所有这些历史,都在由读书人用文字书写出来的谱本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因此,可以认为,族谱所呈现出来的,更大程度上只是地方土著人群礼仪习俗的改变以及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改变,而并非真的是地方人群整体时空位移的历史再现。最典型的礼俗改变是祭祖仪式的变化,如前所言,以世荣公为始祖的薛氏原有的祭祖礼仪是每年拜祭世荣公墓后“饮粥众山”,此传统相沿至今。而在地方正统化过程中,编族谱、在祠堂拜祭祖先这一套被认为符合国家正统性文化议程的礼仪,在清中期后逐渐推广,诚如前辈学者所言,宗族的发展其实是明代以后士大夫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正统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乡村社会以礼仪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的统一。(36)于是崇姜里薛氏,不管是真的来自广东,还是原本就生根于当地的土著都卷入其中。在广东“三日公”故事形构过程中,崇姜里薛氏对世荣公的选择性“失忆”,将崇姜里薛氏与明代大儒薛瑄等名人的勾连,描摹的士大夫化族人景象,这一系列行为均典型地折射出地方创建宗族背后所隐含的正统化诉求。反过来看,既然宗谱编撰是以表明自己的文化正统性为主要目的,族谱本身是推行教化的产物。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即使原被称为“猺”的群体在编谱时也不会自认为“猺”,而是千方百计将自己与开化更早、文化更发达的某个地方拉上关系,寻找一位出身正统的“祖先”。在浔州府,在广西西江中游,一水相连而又开化稍早的广东遂成为最便利的选择。就笔者目力所及,上述地区大量族谱的祖先故事确实往往都有“来自粤东”一类的叙事结构。(37)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通过读书应举、创建宗族等方式建立与正统文化相联系的过程其实甚为艰难曲折。薛氏清代只有唯一一名举人,此位举人甚至无钱参加乡试,得到其他房支的资助才成行,中举后又因无钱而错过会试,还因没有正式祠堂而不得不将文魁匾悬挂在伯父的宅门上。(38)类似情形可能在崇姜里比较普遍,崇姜里沿江村黄姓老人和泰宁寺张、黄姓缘首言:“旧时我们这里无祠堂,也无族谱,姓姓都没有。现在张姓刚刚修好族谱,薛姓是今年刚修好。赖姓修了几次没修成。我们黄姓现在也没有。”(39)与此类说法相印证,在当地确实少见祠堂,难见族谱,尤其是旧谱,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士绅化以及宗族建设进程之艰难,另一方面更表明修谱建祠并非崇姜里地方之固有传统。
至今行走在崇姜里一带,对于当地的底层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认知会更为形象。时至今日,在沿峡江一带主要村落,如古楞、新宁、三鼎、黎村等村,薛姓均为大姓,而当地村民这样描述薛姓人群:“最早是姓薛的住在这里,整个岭都是他们的,后来姓黎的搬来,我们黄姓也搬来,据说我们阿太用10斤粟从姓薛那里要得一个岭住了下来,姓赖的人也是用10斤粟换得一个岭住下来的。村里姓薛的撑船佬最多,撑船佬一定是本土的,在北河上上落落,一代代传下来。”(40)概言之,村民认定薛氏为崇姜里最早住民,属“本土”人;山岭原归薛氏所有;薛氏以撑船为业,是峡江的主人。笔者还注意到,村民称三鼎村的“大庙”为盘古庙,并称直至民国时,盘古庙都是三鼎、古楞等村的中心庙宇,有例行的祭祀和游神仪式。(41)另外,笔者在新宁村跟踪五谷庙游神时,听庙缘首陈仙姑说,村里的社公以前安放的是个石狗,后因修洪防堤迁址,才新建了社公、社婆塑像取代石狗。(42)
有拜盘古、拜狗的习俗,又被周围村民称为“本土人”,新中国成立前多以撑船为业,这就是现在的薛氏族人。点点滴滴之中,依然可见其与当年这块土地上那些被称为“猺”的土著群体的千丝万缕的关联。
三、结语
大藤峡地区由“猺贼渊薮”到明中期以后的“猺”、“獞”、“狼”、“民”多族类共存,再到后来的汉族为主体的居民结构,可视为广大华南等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演变的缩影。不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展开?族群的分类如何界定?族群由谁来标签及如何标签?这一系列问题既引人入胜又很难清楚地阐述,而本文所描绘的明清以来大藤峡地区人群身份变化的个案,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这个复杂的过程。
明代的崇姜里是大藤峡“猺乱”的核心地区,居住于当地的人群,无论当时他们如何自我认定,也无论其后来的族谱如何描述自己的来源与身份,在其时征“猺乱”的军事将领眼中及官方文献记载中,他们均被标示为“猺”;嘉靖年间,当崇姜里被称为“猺”的土著最终接受朝廷招抚,安置于“民村”后,遂相应获得了“民”的身份;明后期至清朝,随着地方的士绅化,崇姜里的人们通过崇祀国家正统神明、参加科举考试、创办宗族等方式,确立了国家正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其通过修谱来表达正统化诉求的行为,也在落地生根的粤东商人影响下逐渐兴起。于是,我们看到类似崇姜里薛氏族群身份随着上述历史过程而不断流动变化的情形:明代有薛姓土副巡检,明中期有随战乱而不断流徙而后编入“民村”的薛氏人群;康熙年间有以薛火帝此类体现瑶人宗教信仰方式命名的人群;乾隆年间薛氏致力于奉祀文昌神;嘉、道族谱展示的薛氏是尊奉文清公为先辈楷模、宣称祖先来自粤东、致力于科举事业的士大夫形象;现今的薛氏则是有着拜盘古、拜狗习俗,被当地村民称以撑船为生的“本土人”,又被识别为汉族,自我认定也为“汉族”。
崇姜里的案例生动地表明,族群的身份是流动变化的,族群的分类不能以僵化的标签来对应。族群标签的背后往往包含着对文化资源和权力的操控,与地方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动荡、宗族语言的运用等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动相联系。当族群认同的标签在不同时候被不同人制造出来时,其背后所反映的其实是地方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43)就浔州府而言,明中期以来就形成了“猺”、“獞”、“狼”、“民”等族类共存的格局,清朝,随着粤东等地人群的移入,又有被称为“东客”、“来人”等的群类,族群互动异常复杂,族群标签也随着地方社会进程而不断演变。而所有这些人群分类的形成和变化,包括清末发生在当地的太平天国首义群体的“客家人”身份,都是本地区社会变迁与国家秩序建立的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就本文而言,正是明清以来国家正统文化秩序的确立,以及两广米粮贸易引起的地方开发的历史,塑造了浔州府乃至西江流域的土著人群对自己土著身份的失忆、“来自粤东”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因此,我们应当从探究地方所经历的系列历史过程出发,来理解这些特定历史过程中由特定的文化行为和经济活动制造出来的族群和社会认同。
注释:
①参见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in Fredrik Barth(eds.),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9,pp.9-38;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美]郝瑞:《族群性,地方利益与国家:中国西南的彝族社区》,《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②如对“蛋民”、“粤人”、“客家”等的研究,参见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
③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卷3《崇姜里》,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40页。
④(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断藤峡》,《四库全书》第3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19页。
⑤(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断藤峡》,《四库全书》第352册,第626-629页。
⑥明洪武年间规定广东盐场之盐先运至广州,再运至梧州,然后沿浔江分销柳江及左右江地区。明清盐的运销有变化,不过,浔江一直是最重要的盐道则毋庸置疑。参见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9-54页。
⑦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04,永乐八年五月壬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校印本,第1350页。
⑧参见《明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辛卯条,第0111-0112页。
⑨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48、155,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癸卯条、十二月六月甲子条,第2906-2907、3024页。
⑩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36,正统十年十二月丁巳条,第2705页;嘉靖《广西通志》卷31《汛防·巡司》,第393页。
(11)参见《明英宗实录》卷148,正统十一年十二月癸卯条,第2907页。
(12)参见《明英宗实录》卷319,天顺四年九月辛巳条,第6646页。
(13)参见(明)韩雍:《议处广西地方事宜疏》,汪森主编:《粤西文载》卷5,《四库全书》第1465册,第502页。
(14)参见(明)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卷8《兵防五·巡检司官兵》,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滇桂卷影印万历七年重修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第110页。
(15)(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3《断藤峡》,《四库全书》第352册,第621页。
(16)(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18《别录·公移三·绥柔流贼》,《四库全书》第1265册,第519-520页。
(17)(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18《别录·公移三·告谕新民》,《四库全书》第1265册,第823页。
(18)善后七策的具体内容,《炎徼纪闻》卷3《断藤峡》中有全文,《苍梧总督军门志》卷29收录的明人翁万达《处置藤峡事宜议》中也有全文。两者有出入,前者被较多征引,不过,笔者注意到后者保留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故笔者在下一段中引文未注其他出处者均引自后者。
(19)(明)毛伯温:《平断藤峡碑·在柳州》,汪森编:《粤西丛载》卷46,《四库全书》第1466册,第455页。
(20)参见乾隆《桂平县资治图志》卷3《崇姜里》,第441页;(明)翁万达:《处置藤峡事宜议》,第383页。
(21)参见(明)杨芳编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卷3《浔州府图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2)参见万历《广西通志》卷15《选举》,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收入《明代方志选》(六),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324页。不过此条并未记明薛文是府属何县何村人。
(23)崇姜里古楞村日凤公支《薛氏族谱》,参见薛恒邺主编:《桂平薛氏日经公、日风公宗支部》,第47页。
(24)通过神明塑造而推行国家正统文化意识的问题,前辈学者已有深入讨论,早期最有影响者为华琛(James L.Watson),他在"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Empress of Heaven)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960-960"(in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l,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92-324.)一文中通过天后崇拜的例子指出,国家通过敕封地方神使其权力与意识形态被贯彻到地方,地方庙宇也通过供奉朝廷认可的神明表明对国家权威的认可。近期更深入的研究参见《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年10月第6卷第1、2期合刊中科大卫、刘志伟、贺喜、唐晓涛、谢晓辉和陈丽华的系列文章。
(25)碑存桂平市南木镇宾山寺。
(26)据调查,瑶人的小名是在小孩出生后由家人请师公打答获得。小孩未满16岁前若有生病、不爱吃饭等情形,会被认为命不好,生身父母无法担保,这时要为他行改名仪式,即拜阴间神明、自然事物或外人作祭父母以祈求其力量担保小孩,并给小孩改小名,通常会在小名中置入所拜神物名称,如拜三清者取名“清”,拜阴阳师父者取名“师”等。参见陈玫妏:《从命名谈广西田林盘古瑶人的构成与生命的来源》,《清华人类学丛刊》八,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4、99-106页。上述薛帝护之类的命名显然属于此类传统。
(27)碑存桂平市南木镇宾山寺。
(28)参见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文昌祠魁星阁碑记》、嘉庆三年《创置保正义田碑》,两碑均存桂平市南木镇宾山寺;嘉庆初年《重修驽滩祖庙序》,碑存桂平南木镇驽滩甘王庙后竹林废水池。
(29)关于两广米粮贸易及粤东客商对浔州府影响的讨论,参见唐晓涛:《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猺乱”到太平天国》,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3-205页。
(30)笔者采集的崇姜里薛氏族谱有新旧两类。旧谱为新宁村日经公十一世孙嘉模于道光二十二年所修,手抄本,前后几页破损但主体部分完好,下引日经旧谱内容均出自此谱;新谱是2004年薛恒邺主编的《桂平薛氏日经公、日凤公宗支部》,此谱照录了编谱时收集到的旧谱内容。
(31)桂平薛氏日明公《宗支部》,桂平社坡伏化村日明公支七房收录手抄本,笔者于古楞村薛安辉处采集到复印件。
(32)此谱序和则例均收录在古楞村日凤公支《薛氏族谱》(撰修年代不明,日凤公后裔1950年续抄本)中,不过并非古楞村日凤公族谱的原序。
(33)崇姜里古楞村日凤公支《薛氏族谱》,参见薛恒邺主编:《桂平薛氏日经公、日凤公宗支部》,第40页。
(34)参见薛恒邺主编:《桂平薛氏日经公、日凤公宗支部》,第448-460页。
(35)以上薛氏名单所引碑刻均存桂平市南木镇宾山寺。
(36)参见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7)粤东商人在浔州府的本地化及结构性祖先故事版本的问题,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详加讨论。
(38)薛恒邺主编:《桂平薛氏日经公、日凤公宗支部》,第70页。
(39)笔者2006年2月4日调查笔记。其中关于薛氏族谱讲者记忆错误,薛氏谱在2004年已修好。
(40)笔者2006年2月4日调查笔记。
(41)笔者2005年11月16日调查笔记。
(42)笔者2007年10月7日调查笔记。
(43)参见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标签:桂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