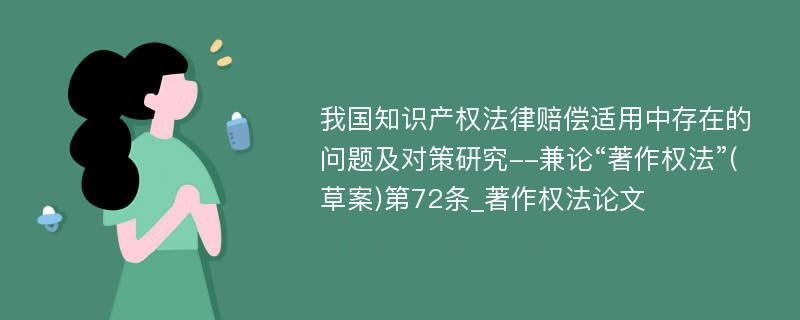
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情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兼评《著作权法》(草案)第72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权法论文,草案论文,知识产权论文,情形论文,对策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产权法定赔偿(以下简称“法定赔偿”),是指在法定条件下,法官在预先规定的额度内综合法定参考因素合理确定赔偿数额的赔偿额计算方式。目前,我国《著作权法》48条、《商标法》56条、《专利法》65条皆对法定赔偿的适用作了一个顺序上的限定,但并未形成系统的适用情形规则,因此,各地方高院为了增强审判上的可操作性,发布了不少关于法定赔偿的具体“适用情形规则”,但各地方高院的审判指导意见并无法律强制力、普遍适用性,也并未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规则,且各地规定并不相同,有的甚至冲突。笔者拟借《著作权法》修改之际,对法定赔偿适用情形进行系统地研讨。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著作权法》(草案),其中,关于侵犯著作权赔偿的第72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参照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和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均难以确定,并且经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登记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应当根据前两款赔偿数额的一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由此可见,在著作权侵权赔偿领域,适用法定赔偿的前提条件很有可能被确定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均难以确定”且“经著作权或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转让合同登记”,与修改前的《著作权法》相比,多了“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和“经著作权或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转让合同登记”两项条件。
由此,引发出笔者这样几个疑问:第一,“通常的权利交易费用”以著作权侵权赔偿的第三顺位计算方法出现,是否代表在法定赔偿之前不会出现第四顺位、第五顺位的计算方法?第二,“经著作权或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转让合同登记”的要件是否必要?《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①的规定能否移植、扩展到整个著作权领域?第三,适用法定赔偿计算赔偿额时“一百万元以下”是否不可逾越的界线?如是,则如何理解其与《著作权法》(草案)72条第3款的关系?第四,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通常权利交易费用、法定赔偿这四种赔偿额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是否固定不变,当事人有无权利直接选择某种计算方法?如用前两种方法可以确定部分损失额时,法定赔偿可否与其他计算方法并用?
带着这样几个疑问,笔者通过对《著作权法》(草案)72条、《著作权法》48条、《商标法》56条、《专利法》65条及相关的条例、各地方的“审判指导意见”进行综合梳理,在系统研究法定赔偿适用情形的基础上,本文将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分为一般适用情形、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并列适用情形和不适用情形四类。其中:一般适用情形是学者通常所讨论的法定赔偿适用条件;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是当事人约定优先适用的情形,是一般适用规则的例外;并列适用情形是法定赔偿与其他计算方法并用的情形;不适用情形是从反向的角度来确定法定赔偿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情形存在的问题
法定赔偿无论是在一般情形下的适用、当事人约定情形下的适用、并列适用,还是排除法定赔偿的适用情形都存在着理论与实务上的困境,虽然司法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已经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相继发布了一些“审判指导意见”予以说明,但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一般适用情形”之适用顺位困境
一般适用情形即法定赔偿通常在什么情形下能够适用。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法定赔偿一般适用情形的探讨都集中在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制度适用的顺序上,主要存在“末位说”②与“平行说”③。
而关于法定赔偿计算方法与其他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之争,导致了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在实务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统一,法定赔偿与其他几种赔偿额计算方法的关系在各单行法中并不一致:《著作权法》适用的是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法定赔偿的严格顺序,《商标法》适用的是侵权利益或侵权损失、法定赔偿的顺序,《著作权法》(草案)和《专利法》适用的是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益、专利许可使用费、法定赔偿的顺序。可见,尽管现行法皆采取“末位说”,但“末位”的条件并不一致。另外,地方司法对权利使用许可费的规定也并不一致:有的将其规定为独立的赔偿额计算方式,而有的只将其视为某种赔偿额计算方式的确定方法之一,如《北京高院著作权损害赔偿指导意见》第7条将“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作为计算“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的方法之一。当然,《著作权法》(草案)通过之后,北京高院“指导意见”的该条自动失效,但笔者认为,这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地位是否只能通过法律认定才能排在法定赔偿之前?在法定赔偿之前除了侵权损失、侵权获益、权利许可使用费之外,是否一定不会出现第四种、第五种顺位的计算方法?
(二)“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之效力困境
本文所探讨的“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并非专指遵循适用顺位规则后当事人对适用法定赔偿制度有无请求权,而更多地关注于当事人有无权利直接选择适用法定赔偿制度。《最高院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5条第1款、《最高院商标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16条第1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法定赔偿”,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当事人对法定赔偿的适用有请求权,但却忽视了该条设定的“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前提条件,该款规定的是在前两种方式无法确定时当事人有权选择、法院可以依职权适用法定赔偿。可见,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在遵循适用顺位规则的基础上,当事人对法定赔偿的适用具有请求权。
但现行法并未就当事人是否可以突破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的顺序直接适用法定赔偿给予明确回答,只有部分地方司法实务进行了初步探讨。比如,《浙江高院专利权适用法定赔偿意见》第4条第1款规定,“权利人可以在起诉时或法庭辩论终结前,请求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似乎是明确赋予了权利人适用法定赔偿的选择权。但该“意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地方“审判指导意见”并无法律强制力、普遍适用性,其效力存在疑问;第二,该“意见”关于法定赔偿与其他几种赔偿额计算方法关系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第1条规定,“在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或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时,可以适用法定赔偿方法,在1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即,第1条认为,只有其他方法不能计算赔偿额时,法院才可适用法定赔偿,法定赔偿是最后的选择。而第4条第2款规定:“权利人未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人民法院应予以释明,要求权利人明确。权利人不作选择的,人民法院可适用法定赔偿方法确定赔偿数额。”即,如权利人不选择计算方法时,法院可直接适用法定赔偿,该规定将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益、权利的许可使用费这三种计算方法都超越了,既未按顺序适用,又似赋予了法定赔偿在适用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与第1条规定的精神不符合,并且,该规定在“权利人未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时,“人民法院应予以释明,要求权利人明确”,这诚然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但问题在于:如果权利人选择直接适用法定赔偿,是否构成对第1条所规定的适用顺序要求的违背?可见,尽管浙江法院在探索法定赔偿制度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道路上走在了前列,但囿于我国现行法的适用顺位规则,该规定并未能在法律层面有效地确定“当事人约定”优先适用规则,也未能理顺法定赔偿与其他几种赔偿额计算方法的关系。
(三)“并列适用情形”之选择困境
“并列适用情形”探讨的是法定赔偿与其他几种赔偿额计算方法能否同时适用的问题,即,权利人能否主张:对于有证据证明的部分用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额;对于未有足够证据证明损失额的部分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额。我国现行法并未明确规定各种计算方法能否并用,各地方高院却出台了不少的规定。
比如,《浙江高院专利权适用法定赔偿意见》第3条“不适用法定赔偿方法”中的第4项就规定,尽管“权利人虽不能举证证明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具体数额”,但根据相关证据,“可以确信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明显超过100万元”时,不适用法定赔偿。即,该意见反对将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制度并用。诚然,法院最后可以依相关证据确定一个超过最高限额的赔偿数额,但此时,由于“不能举证证明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的具体数额”,可以肯定的是,最终确定的赔偿数额不能达到完全赔偿的目的,不能充分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而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设计目的即为了充分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但浙江高院为了严守最高限额的“法定”关口,将该情形列为不予适用情形,易导致赔偿不充分。相反地,《江苏高院定额赔偿指导意见》第23条第2款的规定在有证据显示因侵权原告所受损失或被告所获利益高于最高限额时,“而原告非唯一请求适用定额赔偿办法的,可以参照其他赔偿原则在最高限额以上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即,如果原告同时请求“法定赔偿”和其他赔偿额计算方法,法院可以将两种计算方法结合使用,确定一个在最高限额以上的赔偿数额。《重庆高院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指导意见》第18条也规定在有证据证明但又无法确定具体数额时,法院可以突破50万元的上限确定合理的赔偿额。
可见,浙江严守最高限额的“法定性”不予突破,而江苏允许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额计算方法并用,重庆允许突破最高限额。诚然,根据浙江、江苏、重庆的规定,权利人皆可能获得最高限额以上的赔偿数额,但问题在于:法定赔偿制度最大的特色即为在法定限额内酌定赔偿额,如今动辄允许超出法定限额,是不符合法定赔偿制度“法定性”制度精神的。
综上所述,将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额计算方法完全割裂开来的作法面临着两难的困境:选择浙江严守最高限额防线的规定,则权利人难以获得充分赔偿;选择江苏、重庆的规定,允许突破最高限额,则有违法定赔偿“法定性”之制度精神。
(四)“不适用情形”之诉权平衡困境
本文所探讨的“不适用情形”着重关注的是权利人的诉权、权利人与侵权人诉权的平衡问题,而非通过列举的方式罗列不适用法定赔偿的具体种类。比如,权利人主张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赔偿额但无足够证据支持时,法院有无释明义务?释明后,权利人坚持用法定赔偿外其他方法时,法院有无权力直接适用法定赔偿?权利人主张适用法定赔偿时,侵权人有无相应的抗辩权进行对抗?这些问题都是在诉讼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但我国现行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尽管部分地方高院的“指导意见”对此进行了探讨,如《浙江高院专利权适用法定赔偿意见》第3条规定了不适用法定赔偿的5种情形,但并不全面,且存在着效力无法认定的尴尬问题,因此,有必要从诉权平衡的角度予以探讨。
三、我国知识产权法定赔偿适用情形的完善对策
(一)“一般适用情形”的重构
关于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与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之间到底有无先后顺序,两者与权利使用许可费的关系如何确定,这三种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与法定赔偿的关系又是如何,目前在我国尚无定论。笔者认为,除当事人双方另有约定外,在计算知识产权赔偿额时,首先应按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与侵权人因侵权所获未计入实际损失之内的利润计算,在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与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等同或不存在未计入实际损失之内的侵权利润时,按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计算;在前者无法确定赔偿额或确定的赔偿额明显不当时,按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计算;通过前两种方法无法确定赔偿额或确定的赔偿额明显不当时,按权利使用许可费的合理倍数计算;通过前三种方法无法确定赔偿额或确定的赔偿额明显不当,并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合理确定赔偿额时,按法定赔偿计算。
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从约定,这是私法的基本精神,其理由笔者会在下文的特殊适用情形中加以论述。下面,笔者对当事人约定之外的赔偿额计算方法适用顺序逐一进行解释。
1.“侵权损失+损失之外的侵权利益”优先适用
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与侵权人因侵权所获未计入实际损失之内的利润④计算方法,应排在当事人约定之外的首位,理由有如下三点。
第一,赔偿的立法目的要求“侵权损失+损失之外的侵权利益”具有优先性。法律设立赔偿的目的就是为了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因此,在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实际损失能够确定时,应优先适用之。另外,为了防止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而不当得利,应将实际损失之外的侵权所得利润归于权利人。其实,在实务中,法官们也意识到严格按侵权损失优先的做法可能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北京高院著作权损害赔偿指导意见》第5条规定,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如有证据表明被告侵权所得高于原告实际损失的,可以将被告侵权所得作为赔偿数额”,其采用就高不就低的方法来确定最终的赔偿额数字,就是为了防止侵权人不当得利,从而加大赔偿力度。但这种规定与《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不符,在实际运用中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程度也不如“侵权损失+损失之外的侵权利益”的计算方法。
第二,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法定赔偿也是围绕着“侵权损失+损失之外的侵权利益”来确定赔偿额的,在后者能够确定的情况下,没有适用前者的必要。这就好比在本人能够完成的情况下不必使用替身。即便在将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制度并列规定的美国,法定赔偿的适用也大多是在实际损失不能精确计算的情形下适用的。比如,在1984年的“唱片公司”案件中法院曾指出:“但由于法定赔偿大多是在实际损失不能精确计算的情况下使用的,就不能希望两者准确一致。”⑤“除版权人自己愿意选择采用‘法定赔偿额’原则外,美国法院大多是在无确凿证据证明版权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侵权得利的情况下,才采用法定赔偿额来赔偿的。”⑥
第三,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法定赔偿只是对“侵权损失+损失之外的侵权利益”的一种推定、拟定、酌定,是无法确定后者时法律所做出的利益选择,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假定,是在后者无法确定时假设后者应然数额的确定方法,其确定的数额在准确度和可靠度上必然不如后者,因此,为保证审判结果的精准性,在后者能够确定时必须不能选择其他计算方法。
综上所述,“侵权损失+损失之外的侵权利益”的计算方法具有优先性是知识产权立法目的和立法宗旨的必然要求。在适用顺位上,笔者认为,以与权利人侵权损失的接近程度为标尺,以侵权所获利益、权利使用许可费、法定赔偿为适用的先后顺序。
2.“确定的赔偿额明显不当”应适用排除规定
每一种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都有其适用优势,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漏洞,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利益,防止侵权人不当得利,加大侵权打击力度,有必要规定一些例外情形排除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规定。
第一,依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计算赔偿额存在漏洞的可能性。依侵权所获利益确定的赔偿额明显不当,不能作为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由于侵权人自身原因导致侵权实际获益与一般侵权预期所获收益不相当;一是由于侵权人主观原因,通过做假账、逃避审查等方式导致计算的侵权获益与一般侵权预期所获收益不相当。无论是因侵权人主观故意还是事实上的客观结果,如果侵权人因侵权并未获益甚或亏本,侵权获益当然不能作为赔偿额的计算方式,但如果由于侵权人主观上的原因或客观上受能力、市场环境等限制导致侵权获益与侵权所造成的后果极不相称,此时如果仍然坚持按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的方法来计算赔偿额,则对权利人明显不公。
第二,依权利使用许可费计算赔偿额存在漏洞的可能性。权利使用许可费如果畸高或畸低,以此为计算依据可能造成对侵权人或权利人的不公。有时权利人为取得高额赔偿,故意串通其他主体订立许可费畸高的许可合同,此时,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计算赔偿额,侵权人的责任将无端增加。有时,由于权利人与被许可人有着利益关联或其他关系,因而权利使用许可费用订得畸低,如果以该数额作为标准来计算赔偿额,对权利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对权利许可使用费的真实性、合理性等予以审查,而不能径直拿来一个数据就作为计算标准来确定赔偿额。
法律调整的是一般社会关系,但也不排除对例外情形的规范。因此,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适用顺序的例外规定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笔者同时认为,排除条件不能随意设定,《著作权法》(草案)72条的一大亮点是为法定赔偿的适用限定了“经著作权或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转让合同登记”要件,无此要件,即排除法定赔偿的适用,但“登记”要件的添加确无必要。首先,法定赔偿只是知识产权侵权的一种赔偿额计算方法,与登记与否并无直接、必然联系;其次,法定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是强化权利的保护,使权利人在诉讼中达不到一般证明标准时亦可获得赔偿,登记要件的添加大大地增加了实现该立法目的的难度;再次,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权利的许可使用费、法定赔偿皆为赔偿额计算方法,何以单独在法定赔偿的适用上要求登记为必要条件?果如“草案说明理由”所言,登记为必需,亦应在适用赔偿额其他计算方法(至少在侵权损失、权利许可使用费)时添加登记前提,方显公平;复次,赔偿本为保护权利,今权利尚未获益,须得先支付若干费用,否则有不获保护之虞,逻辑上难以通顺,且登记程序增加了维权路上的荆棘,客观上打击了维权的积极性,变相地助长了侵权的气焰;最后,无论国内其他知识产权单行法或国外,鲜少有以登记作为权利保护前提的,即便是《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也只规定权利人“可以”要求登记。
3.“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合理确定赔偿额”的兜底规定
之所以规定“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合理确定赔偿额”的兜底限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定赔偿自身存有弊端,应谨慎适用。适用法定赔偿时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确定的因素过多,参考因素的详细种类、比例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防止法定赔偿的滥用,一方面要尽快制定法规明确适用法定赔偿时数额确定的具体依据,另一方面对法定赔偿的适用要持谨慎态度,限制法定赔偿的随意适用,防止法定赔偿变为随意赔偿、任意赔偿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有出现侵权损失、侵权利益、权利使用许可费之外能够较准确、合理地确定赔偿额的可能。“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合理确定赔偿额”是一个兜底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其他确定赔偿额的合理方式,并且比法定赔偿的准确度要高、不确定因素要少,此时,自然应将其排在法定赔偿之前。比如,随着专家估算制度的完善,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其做为知识产权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之一。
尽管法定赔偿在一般情形下处在知识产权确定赔偿额计算方法的末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定赔偿绝对不能优先于其他计算方法适用,其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也可以打破适用顺序的规则直接适用。
(二)“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的明确
尽管已有部分地方的司法实践展开了对“当事人约定情形”研究的尝试,但笔者认为,该尝试仅以“审判指导意见”形式出现,且仅在部分地区适用,并无普遍适用效力。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赔偿额计算方法适用上是有顺序限制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适用”情形的优先性:无论当事人双方是在诉讼前约定还是在诉讼过程中达成选择法定赔偿作为赔偿额计算方法的协议,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法院都应当尊重并优先适用;在当事人对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有约定时,无论其约定了何种计算方法,法院都应直接按其约定所导致的举证、质证、认证的要求引导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无权主动适用另外的计算方法。即,当事人的约定可以破除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的法定适用顺序限制,在诉讼过程中具有优先适用性。
知识产权领域应当尊重私权自治。“在私域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⑦其实,相关知识产权法规也将当事人协商放置于纠纷解决方式的首位。《商标法》第53条、《专利法》第60条都规定侵犯知识产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只有在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时,才可能由行政部门或法院处理。《最高院著作权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5条第3款、《最高院商标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16条第3款也规定当事人按法定赔偿的规定就赔偿额达成协议的,法院应当准许。笔者认为,这些规定中体现的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可以作为当事人约定优先适用情形的价值指导。
(三)“并列适用情形”的设定
笔者认为,权利人的损失部分能够确定、部分不能确定的,对于不能确定的部分,可以主张适用法定赔偿,适用法定赔偿得出的赔偿数额与确定的赔偿数额相加可以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但适用法定赔偿部分不能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即笔者主张法定赔偿与其他赔偿计算方法能够并用。理由如下。
第一,客观上存在侵权损失或侵权获益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情形,不采取并用模式不足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侵权损失或侵权获益超过100万元或50万元的上限的情形,如果严格按照每一计算方法单独适用,则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按照法定赔偿之外的方法无法达到完全赔偿的目的;按照法定赔偿计算的赔偿额又不足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因此,有必要对能够确定的损失采取其他方法确定,而法定赔偿只适用于其他计算方法不能确定的损失,如此,则最终可以确定高于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赔偿额,但又不违反法定赔偿“法定性”的精神。
第二,适用法定赔偿的一般前提要求采用并用模式。笔者认为,通常情形下法定赔偿的适用前提是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确定赔偿额,如果权利人的损失能够通过其他方式确定,那就不能适用法定赔偿。法定赔偿的适用范围只能限于权利人损失不能确定的部分,而不能及于已经确定的部分,如此要求,是为了尽可能限制不确定因素的适用范围,最大程度降低法定赔偿的负面效果,以保证裁判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三,适用法定赔偿的弊端要求采用并用模式。法定赔偿适用时不确定因素过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大,其偏离赔偿额确定基准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对法定赔偿的适用应持谨慎态度,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一般只在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确定赔偿额时才适用。当权利人的部分损失能够确定时,对该部分的损失就不应也不能通过法定赔偿来确定。
此外,理顺《著作权法》(草案)72条第2款与第3款的关系也需要承认并用模式。该条第3款规定,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权的,以已确定赔偿额的1-3倍确定赔偿额,而第2款规定,适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为100万元。如坚持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为100万元,但假设通过法定赔偿确定的数额乘以3倍后超过100万元的,应如何处理?或者,应理解为,以1-3倍确定赔偿额意味着法定赔偿最高限额变为300万元?笔者认为,无论哪种方法都不能确保法定赔偿的“法定性”与对权利的周全保护,只有坚持法定赔偿与其他计算方法并用的方法才以解决这一问题:采用其他计算方法计算赔偿额的部分,可以以1-3倍确定赔偿额;采用法定赔偿计算赔偿额的部分,亦可以以1-3倍确定赔偿额,但该部分总额为100万元以下,即最终的赔偿额可能超过100万元,但适用法定赔偿部分最高限额为100万元。
(四)“不适用情形”的确定
在现实中,侵权人可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比如在侵权获益远超过100万元时,建议法院采取法定赔偿计算方法确定赔偿额,此时,法院不能直接同意或拒绝,应征询权利人的意思,如果权利人同意,视为双方关于适用法定赔偿确定赔偿额达成协议,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如果权利人不同意,也勿需说明理由,法院应按正常程序审理。之所以如此设定,是因为赔偿请求权是权利人所拥有的权利,而非侵权人。那么权利人作为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是否可以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赔偿计算赔偿额呢?
笔者认为,当权利人主张直接适用法定赔偿时,应赋予侵权人相应的抗辩权,以平衡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果通过其他计算方法能够确定赔偿额,但侵权人未主张的,视为侵权人同意,当然可以直接适用法定赔偿。但如果侵权人不同意,应在立法上赋予其相应的抗辩权,以对抗权利人的请求权。毕竟,法定赔偿的酌定性太大,与其他计算方法相比,其参考因素、参考标准、参考区间不是十分明确,即使是明确了参考因素的种类与比例、参考的基准,其需要酌定的因素仍然过多,与其他计算方法相比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仍显过大,因此,对法定赔偿的适用应十分慎重,而不能根据权利人单方的主张直接适用之。⑧
此外,笔者认为,权利人主张,侵权人反对但理由未为法院所确认的,推定为侵权人同意,体现立法偏向保护权利人的价值取向。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如果侵权人坚决反对适用法定赔偿,则其会积极主动收集采用其他计算方法可以确定赔偿额的证据,但结果仍是“未为法院所确认”,可以推定,即使权利人主张以其他计算方法确定赔偿额也行不通,此时适用法定赔偿符合正常的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的适用顺序。
第二,如果侵权人只提出了一种法定赔偿之外的赔偿额计算方法的证据,而对其他的在事实上可以确定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不举证的,视为侵权人放弃采取其他的计算方法,比如,权利人提出适用法定赔偿,侵权人提出反对,其理由是侵权损失可以计算,而未主张侵权获益或权利许可使用费,那么,在权利人主张的侵权损失未为法院所确认时,视为其同意使用法定赔偿来确定赔偿额。
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赔偿是请求权,如何计算,应由权利人在法定或约定的顺序内主张,法院不能主动适用某种计算方法。法院在赔偿诉讼中的职责是在权利人请求范围内,依据权利人主张和法律规定,通过证据规则的运用,确定赔偿额,而不能替权利人选择赔偿额计算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在不能通过其他计算方法或通过其他计算方法确定的赔偿额明显不合理时,法院不能依职权适用法定赔偿,此时,法院所负担的只是释明职责,其可以告知权利人所拥有的权利、权利实现途径和方式以及相应的后果,至于是否行使权利,由权利人自行决定,勿需法律和法官代其决定。
因此,笔者主张,在审判人员阐明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及后果后,权利人仍然主张适用其他知识产权赔偿额计算方法的或明确拒绝适用法定赔偿的,审判人员不能主动适用法定赔偿,此时,应依证据规则来处理,由权利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注释:
①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三)关于著作权和相关权登记”部分。
②参见曾玉珊:《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学术研究》2006年第12期,第76页;参见王文起、矫玉增:《侵犯知识产权法定赔偿解说》,《中国市场》2006年第48期,第21页。
③程永顺:《专利纠纷与处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董天平、郃中林:《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讨会综述》,《知识产权》2000年第6期,第38页。
④将“侵权人因侵权所获未计入实际损失之内的利润”与“权利人因侵权所受损失”一并作为赔偿数额确定基准的理由,笔者将另文撰述,不复赘言。
⑤RSO Records,Inc.v.Peri,596F.Supp.849,225USPQ407(S.D.N.Y.1984).转引自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页。
⑥何家弘主编:《当代美国法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⑦李建华、许中缘:《论私法自治与我国民法典——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4条的规定》,《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3期,第145页。
⑧参见李国强、孙伟良:《民法冲突解决中的利益衡量——从民法方法论的进化到解释规则的形成》,《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1期,第64页。
标签:著作权法论文; 法律论文; 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论文; 知识产权侵权论文; 知识产权法院论文; 赔偿协议论文;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论文; 著作权登记论文; 法制论文; 限额设计论文; 商标法论文; 专利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