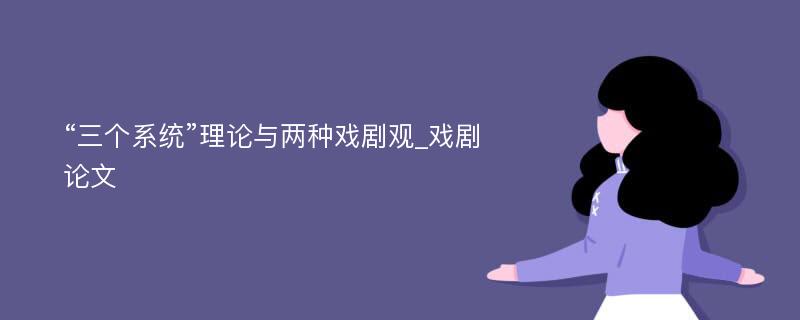
“三大体系说”与两种戏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三大论文,戏剧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这三位戏剧大师作比较研究的,始于我尊敬的黄佐临先生。他在1962年春天的“广州会议”即“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作过一个重要发言,后以《漫谈“戏剧观”》为题发表于当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 他的发言旨在拓展艺术创作视野,打破话剧舞台上的单一沉闷现象。展现在佐临面前的世界戏剧千姿百态,他在文中却只选择斯、梅、布三家来立论。那是为什么呢?我以为原因也许有三:其一,话剧史上的各种经验有好坏之分,而梅、斯、布的艺术实绩属于值得保留的优秀之列;其二,为了开阔眼界,倡导多样化,必须寻找不同的艺术经验进行比较评介,而梅、斯、布的戏剧艺术正是特色鲜明,各具风姿;其三,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举出这样三家,容易为上下各阶层所接受。正如佐临所说:“梅、斯、布都是现实主义的大师,但三位艺人所运用的戏剧手段都各有巧妙不同。”佐临还称此三家为“艺术观上的一致,戏剧观上的对立”。
由于历史的原因,佐临的文章在当时未能产生应有的作用。十九年以后,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大体依旧的文章,题为《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此文原为英文稿,发表于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京剧与梅兰芳》一书,后由梅绍武翻译为中文,在 1981年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次却引发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有关“戏剧观”的争鸣,影响深远。
佐临的文章用意十分明确。他在前后两文中都说了一段意思相同的话:“为了便于讨论,我想围绕三个绝然不同的戏剧观来谈一谈……目的是想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和根本差别,探索一下三者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推陈出新的作用,以便打开我们目前话剧创作中只认定一种戏剧观的狭隘局面,”他称选择三个戏剧观只是“为了便于讨论”,可见并没有标举“三大戏剧体系”的用心。道理很简单,佐临深知世界上的戏剧体系、观念、方法、流派无比繁复,并非仅此三家。在他本人的历史上,就曾先后迷恋过莎士比亚、萧伯纳、皮兰德娄、格托托夫斯基等戏剧家。而且我始终认为佐临于六十年代初期提出戏剧观问题,与苏联剧坛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戏剧观念多样化思潮不无关涉。当时苏联革新派剧人的心目中倒是真有“三大戏剧体系”的,不过那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和布莱希特。佐临对于这些自然十分清楚。但他在讲三个戏剧观时,却以此梅氏(梅兰芳)替换了彼梅氏(梅耶荷德),这一方面表现了佐临的民族自豪感和理论独创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化精英所特有的谨慎深致的心曲。
但中国的一般剧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世界戏剧状况所知甚少,佐临的前后两文就成为许多人了解世界剧坛的范本。于是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不少人接过佐临的话头,冠以“三大体系”,作为一种颇为流行的方便用语。
在我的印象中,真正着力著文论说“三大体系”的是我的同学孙惠柱先生。他在《戏剧艺术》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题为《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的长文。该文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斯氏体系”“特别着意于真”,“布氏体系”“特别着意于善”,而“梅氏体系”则“主要是着意于美”。这是一篇很有创见的结构精巧的论文,曾为多种戏剧书刊全文选载,影响相当大。我觉得此后有不少剧评人正是由于读过此文,才渐而把“三大戏剧体系”演用成一种通用话语。直至1986年,孙玫先生还著文题为《三大戏剧体系述评》(发表于《宁夏艺术》1987年第三期)。该文虽已指出斯、梅、布三氏“仿佛是三个并不一一对应的复杂的多面体”,但还是肯定地称他们是“三大戏剧体系”。
这两位孙先生先后都赴美国攻读博士。出国后,他们的认识肯定起了变化。孙惠柱似乎再不谈“三大体系”事,孙玫则于1993年岁末于美国檀香山著文对“三大戏剧体系说”提出商榷(发表于《艺术百家》1994年第二期)。该文为自己以往信奉过并在文章中引用过“三大戏剧体系说”而进行检讨,认为那种理论“对世界戏剧历史和现状的概括和描述是不准确的”。
我赞赏孙玫的“商榷”。这正体现了九十年代中国学人对八十年代的学术的一种检讨与升华。
而今我们再来研读佐临先生的两篇文章,觉得他“为了便于讨论”而提出的三个戏剧观,其实主要是在说两种戏剧观。他的前后两文都郑重指出:“二千五百年曾经出现无数的戏剧手段,但概括地看,可以说共有两种主要的戏剧观:造成生活幻觉的戏剧观和破除生活幻觉的戏剧观,或者说,写实的戏剧观和写意的戏剧观。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写实写意混合的戏剧观。”在佐临看来,这些不同的戏剧观,其区分点集中在一处,即如何看待舞台上的所谓“生活幻觉”亦即“第四堵墙”这个问题。佐临写道:“他们三位的区别究竟何在?简单扼要地说,最根本的区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要推翻这堵墙,而对于梅兰芳,这堵墙根本就不存在,用不着推翻。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戏剧一向具有高度的规范化,从来不会给观众造成真实的生活幻觉。”佐临从中国实际出发,为了推动中国话剧的多样化,并使中国话剧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就偏重于对“破除生活幻觉”亦即“写意”的戏剧观的推介。于是,他在前一文中突出介绍布莱希特,而在后一文中则更着重于论说中国戏曲。佐临把中国戏曲的内在特征概括为四个“写意性”:生活写意性、动作写意性、语言写意性和舞美写意性。
虽然余上沅于二十年代中期就曾把中国戏曲表演称为“写意派”,佐临先生于三十年代留学美国时亦已萌生“写意”意识,但那时的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佐临经过半个世纪的艺术追求,思路逐渐清晰,原来他执著寻求的,是一种融合中西而又独立于世的中国式的“写意”戏剧。他晚年精心执导《中国梦》,不无自得地标称为“写意话剧”。他把自己毕生著述编为一本书,然后大笔一挥,自题曰:《我与写意戏剧观》。
斯人已逝,然其功不可没,其“写意戏剧观”则已无胫而行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