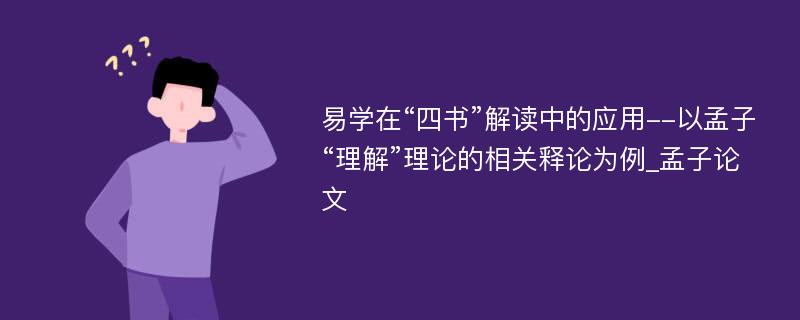
《易》在《四書》詮釋中的運用——以《孟子》“盡心知性”說的相關詮釋爲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心知论文,四書论文,詮釋中论文,相關詮釋爲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國古典學史上,入宋以後,一個重要變化是《四書》的成立。①從《六經》(準確地說是《五經》)之學到《四書》之學,標誌著學術範式的轉移。然而,《四書》之學與《五經》之學卻並非從此兩途,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一個值得注意卻常常爲人忽略的現象是《易》(包括《易經》與《易傳》)在《四書》詮釋中的大量運用。本文擬以《孟子》“盡心知性”說的詮釋爲例,對此現象做一探討。
“盡心知性”說見《孟子·盡心上》第一章:“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13.1)如何理解“盡心”,如何理解“知性”,以及如何理解“盡心”與“知性”的關係,是對這段話進行詮釋時所遇到的主要問題,歷代學者看法不一,其中,朱子以《大學》的“格物致知”思想來比附《孟子》的“盡心知性”,其說獨特,招來物議。②另一方面,從程伊川到黄梨洲再到焦里堂,不斷有學者援《易》入《孟》或本《易》解《孟》,其得失利病,尚待檢討。以下且觀其詳。
一
程伊川對《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的理解,明顯可以看出其受《易傳》“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一語的影響。
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其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心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矣。(《孟子精義》卷十三,791頁)
一方面,伊川對“盡心知性”的讀法跟常規一樣,即按其字面順序,以“盡心”爲“知性”之因。另一方面,他又認爲,“盡心”、“知性”、“知天”之間的關係與《易傳》所說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情况類似:如果說這三者之間給人感覺有某種先後之序,那也只是語勢使然,其實三事一時並了,不分軒輊。伊川在解說“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時即作如是觀。
(1)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纔窮理便是盡性,纔盡性便至于命。(伊川語,《遗書》卷十八,《二程集》,193頁)
(2)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外書》卷十一,《二程集》,410頁)
(3)或曰:“窮理,智之事也;盡性,仁之事也;至于命,聖人之事也。”子曰:“不然也。誠窮理,則性命皆在是。蓋立言之勢,不得不云爾也。”(《粹言》卷二,《二程集》,1255頁)
在伊川看來,窮理、盡性、至命這三者之所以是一事,是因爲理、性、命是一回事。“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這樣的話顯示,真正具有工夫意義的只“窮理”一端而已。③
與此相應,伊川把心、性、天也理解爲一個東西,從而,纔盡心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1)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④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遺書》卷二上,《二程集》,15頁)
(2)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遗書》卷十八,《二程集》,204頁)
(3)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遺書》卷十八,《二程集》,204頁)
(4)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忍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如數一百,少卻一便爲不盡也。)大抵禀于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矣。”(《遺書》卷十八,《二程集》,208頁)
從伊川的用詞來看,“心便是天”,“心即性”,明顯地,他有將心、性、天等概念等量齊觀之意。而他將“在天爲命”、“在義爲理”與“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或“論其所主委心”等說法連在一起的做法暗示,他已經把出自《易傳》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與出自《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打成一片。
在形式上,“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與“盡心知性知天”確實有一個共同的概念——性。但是,前者是討論理—性—命的關係,而後者則是討論心—性—天的關係。即便就兩者共同包含的概念——性而言,其差异亦不容忽略:前者說的是“盡性”,而後者說的是“知性”,一“盡”一“知”,並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如果要在後一個說法當中找一個與“窮理”比較接近的概念,那也應該是“知性”而不是“盡心”。然而,即便如此,二者的意旨依然相侔:前者是從窮理出發,後者則是從盡心出發,换言之,窮理不再是後者的出發點。對于一向以窮理爲工夫下落且有意用窮理之說觀照《孟子》“盡心知性”論的伊川來講,這種情形不免有些尷尬。也許是這個原因使得朱子在詮釋“盡心知性”時没有完全照搬伊川,而是轉用《大學》義理作爲新的坐標系。
雖然《孟子集注》收録了伊川有關性心一理之說:“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孟子集注》卷十三,349頁)但在具體解釋“盡心知性”時,朱子對伊川的“性心一理”說卻有所保留,而更推崇張子、邵子的心性理論。
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某觀之,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卻似包著這性情在裹面。故孟氏語意卻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橫渠得知,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朱子語類》卷第六十,1423頁)
朱子對孟子“盡心然後知性”的解讀,固然以其“心包性情”的心性觀爲依據,但他也爲這種解讀在《孟子》中找到一個成例。
(1)李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朱子語類》卷第六十,1422頁)
(2)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自分曉。尋此樣子亦好。”(《朱子語類》卷第六十,1423頁)
從經典詮釋的角度看,雖然朱子的解讀與《孟子》原文字面順序相反而顯得奇特,但較之于伊川的“援易入孟”,朱子的“以孟解孟”反倒更名正言順一些。⑤
二
有明一代學術,雖中期以降陽明學在民間取得巨大影響,但在官方依然是朱子學的天下。陽明學與朱子學的争鋒在四書學上亦有體現,陽明對朱子《大學》詮釋不遺餘力地駁正即是著例,而在《孟子》詮釋上,蕺山師徒對朱子的詮釋則時有商榷,按之《孟子師說》可知。
梨洲在《孟子師說》的“題辭”中開宗明義地表示,他已經厭倦四書學上單純“述朱”的做法:
《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于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孟子師說》“題辭”,48頁)
從性質上說,《孟子師說》其實是梨洲本人作品,但由于他聲稱書中觀點來自先師:“羲讀《劉子遺書》,潜心有年,粗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七卷……”(《孟子師說》“題辭”,《黄宗羲全集》第一册,48頁)故不妨將之視作蕺山—梨洲師徒的共同主張。《孟子師說》最後一卷也論及“盡其心者”章,茲將其中對于“盡心知性”的解說具録于後。爲便分析,逐段抄釋。
1.孟子所謂擴充、動心忍性、强恕而行,皆是所以盡心。性是空虛無可想象,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則空虛之中,脉絡分明,見性而不見心矣。如孺子入井而有惻隱之心,不盡則石火電光,盡之則滿腔惻隱,無非性體也。(《孟子師說》卷七,148頁)
梨洲對“盡心知性”次序的理解一如字面,即認爲“盡心”而後“知性”。梨洲以心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類,這是用《孟子·公孫丑上》的“四心說”來解釋“心”。這種理解並不鮮見,前揭伊川語録即有之:
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羞忍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數,只是盡心便了。纔數著,便不盡……”(《遺書》卷十八,《二程集》,208頁)
伊川不贊成將“盡心”之“心”坐實爲“四心”,認爲那樣一來,“盡心”就局限于盡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不能真正地做到“盡”。觀梨洲之意,似乎正是將“盡心”理解爲盡此四心而已,所謂“心之在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以認取”,“將此可以認取者推致其極”。揆諸伊川之論,似可說梨洲尚有一間未達之處。
在梨洲看來,“心”實而“性”虛(空),所謂“性是空虛無可想象”,言下之意,性以心爲體,這跟程朱對心性的理解完全相反。
問:“程子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爲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裹面穰肚稻草。”(《朱子語類》卷第六十,1426頁)
朱子將程子“心無體,以性爲體”解釋爲“心虛性實”,可謂要言不煩。反觀梨洲,既以性爲空虛,又言“空虛之中,脉絡分明,見性而不見心”,不知所謂。然梨洲之解“盡心知性”又似程子之援《易》入《孟》,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2.《易》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者盡其心也,心既(疑當作即——引者注)理也,故知性知天隨之矣;窮理則性與命隨之矣。《孟子》之言,即《易》之言也。(《孟子師說》卷七,148頁)
《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易傳》說“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從形式上看,兩者不乏相似之處,差別主要在于,一個是說“盡心”,一個是說“窮理”。而在梨洲看來,“心即理也”,所以,“窮理”也就是“盡心”。從而,《孟子》之言與《易》之言實際說的就是一回事。
導致梨洲做出“《孟子》之言即《易》之言”結論的關鍵在于“心即理”一說。然而,無論是《孟子》,還是《易》,都没有“心即理”這樣的說法。“心即理”說最早是陸象山對《孟子》“心”論加以個人發揮的結果。
人非草木,安得無心?心于五官最尊大。《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⑥又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⑦又曰:“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⑧又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⑨又曰:“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⑩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11)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謂失其本心”。(12)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13)四端(14)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15)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其見乃邪見,其說乃邪說。一溺于此,不由講學,無自而復。故心當論邪正,不可無也。以爲吾無心,此即邪說矣。(《與李宰》,《陸九淵集》,卷十一,149頁)
從《孟子》中固然可以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卻不能因此就推到“心即理也”,因爲在《孟子》“是心”或“此心”是指仁義之心或四端,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心。用《孟子》的話說,“是心”或“此心”是“本心”。如果說“本心”即“理(義)”,《孟子》大概不會反對。可是,如果說“心”即“理(義)”,那就與《孟子》之意不相符了。因爲從《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這樣的話看來,“理(義)”與“(我)心”顯然不是一回事,這就像“芻豢”不是“(我)口”一樣清楚。其實,《孟子》中說得明明白白:理、義是人心之所同然:“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孟子·告子上》11.7)
需要指出的是,“窮理”意義上的“理”的用法在《孟子》中從未出现。(16)象山將“心”與“理”聯起來說,已非純然《孟子》家法,而是摻雜了來自《易傳》的“窮理”因素。
象山對窮理說的使用:“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再次證實,“窮理”在宋季已成爲知識人的公共話語(17),不但程朱這些理學學者用之,象山這樣的心學學者亦用之,只不過,象山以“盡心”解“窮理”的路綫,與程朱即物窮理的路綫,迥乎兩途而已。
將梨洲的“窮理者盡其心也,心即理也”與象山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諸語做一對照,會發現,二者幾乎如出一轍。(18)在理論上,“心即理”與“性即理”針鋒相對。從“心即理”的觀念出發,梨洲對朱子以“性即理”爲基礎的“盡心知性”詮釋做了不點名的批評。
3.先儒未嘗不以窮理爲入手,但先儒以性即理也,是公共的道理,而心是知覺,知得公共的道理,而後可以盡心,故必以知性先于盡心,顧其所窮,乃天地萬物之理,反失卻當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矣。人心爲氣所聚,其樞紐至微,勿忘勿助,此氣常存,稍涉安排,則霍然而散,不能自主。故必須存,存得恰好處便是養,不是兩件工夫。《易》言“成性存存”,可知是一也。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所謂存久自明而心盡矣。(《孟子師說》卷七,148~149頁)
依梨洲,心學、理學之判不在窮理與不窮理,而在對窮理之理究竟作何解釋:一謂“性即理”,一謂“心即理”。雖然梨洲没有點名,但瞭解朱子“盡心知性”詮釋的人都知道,堅持“性即理”而又認爲“知性先于盡心”的正是朱子。然而,梨洲對朱子心性論的把握不無偏差,朱子固然贊成“性即理”,但他主張“知性先于盡心”的理由卻主要不是“性即理”而是“心包性情”說,前已述及,此不再贅。不過,朱子本人對于這種批評的產生也負有一定的責任,因爲他曾經用《大學》的“格物致知”來比附《孟子》的“盡心知性”,這種比附確實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它讓人誤以爲“盡心”主要就是“認知”活動,而實際上朱子所說的“盡心”是指充分實現人的道德實踐能力,朱子後來對此也有所覺察,遂改用“誠意”來比附“盡心”。(19)
梨洲所謂“當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其說繚繞,如果說“心即理”,那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即可說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理,又何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之理”?直有疊床架屋之嫌。既說“當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如何又擔心會失卻?
梨洲這段評論的後半截是解釋存心養性事天,與“盡心知性”本無直接關聯,不過,其中有兩點卻值得一提:(1)梨洲援《易》解《孟》的特點在此再次顯露。梨洲在說明“存心養性”時引到《易傳》,“成性存存”語出《易·繫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2)梨洲之說與陽明學的淵源宛然可見。“天下之理,皆非心外之物”明顯係化用陽明語録:“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傳習録》上,《王陽明全集》卷一,2頁)
三
焦循(字里堂,1763-1820)著《孟子正義》當其晚歲,時《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已成,遂得傾其全力爲趙歧《孟子章句》做疏,采摭顧炎武以下六十餘家之言而斷之以己意,可謂集有清孟學之大成。在理氣性命方面,里堂多取戴震(東原,1724-1777)、程瑤田(讓堂,1725-1814)之說(20),更以其所得于《易》者加以融會貫通,卒成一家之言。(21)關于里堂援《易》入《孟》的解經方法,前人已做過一些研究,本文擬略人之所詳,詳人之所略,著重就焦循對“盡心知性”說的詮釋進行分析。(22)
里堂引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以疏“盡心知性知天”節趙歧注,引瑤田《通藝録·論學小記》以疏“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節趟歧注,其倚重東原、瑤田之性理說如此。所引東原之說專釋“盡心知性知天”,所引瑤田之說卻不限于止釋“夭壽不贰修身以俟”,亦涉及“盡心知性”之理解。里堂對東原、瑤田之說的具體處理方式又有所不同,其引東原後未置一詞,引瑤田後則加按語附議。里堂之按語即其對“盡心知性”之正面解說。今欲研究里堂對孟學之認識,則不能不將其所引瑤田之說與其按語一並抄録。
里堂所引瑤田說甚長,爲簡行文,只録其與“盡心知性”句直接相關者:
程氏瑶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于吾之身,物則即具于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
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正義》卷二十六,878~879頁)
瑤田對“盡心知性”的解釋在基本方向上與朱子相通:(1)盡心是由于知性,所謂“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是非先有以知其性不能也”。(2)知性猶格物,盡心猶致知,所謂“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不過,瑤田對心物關係的理解——“物具于心”,當非朱子所能認同。(23)
至于“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云云,“性”與“盡心”之間何以有此關聯,瑤田並没有說明。下文“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于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呈現了從“盡己之性”到“盡人之性”再到“盡物之性”最後到“心盡”這樣一個過程,其内在關聯,瑤田同樣没有說明,似乎視之爲理所當然之事。這裹,瑤田顯然是用《中庸》義理對《孟子》進行解說。(24)然《中庸》所論只涉及“盡性”問題,並未談到“盡性”與“盡心”的關係。除非像王陽明那樣認爲“盡心就是盡性”(25),否則,《中庸》有關“盡性”的思想無法直接運用于解釋《孟子》“盡心”之說。(26)綜上,瑤田對于“盡心知性”的解釋並無新義,且多囫圖。里堂卻對瑤田之說甚表肯定。
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羲之“通德類情”,黄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教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赞君之治,以成君之功。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夭壽窮達智愚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即所以修身使天下皆歸于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爲其心以存之養之修之,爲性也;立命,至于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孟子正義》卷二十六,879頁)(27)
跟瑤田一樣,里堂亦從《中庸》“盡性”說獲得靈感,在解釋“盡其心”時將之與“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直接挂搭。然里堂詮釋與瑤田异大于同,其最大不同在于里堂本《易》解《孟》:其一是將“盡其心”與伏羲之“通德類情”、黄帝堯舜之“通變神化”相聯;其二是說《孟子》此章發明《易》道。其說究竟有何根據,以下一一觀之。
伏羲之“通德類情”係對《繫辭傳·下傳》第二章有關伏羲(包犧氏)事迹的概括:“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通德”與“類情”分別是“通神明之德”與“類萬物之情”的省稱。黄帝堯舜之“通變神化”則是對《繫辭傳·下傳》第二章有關黄帝堯舜事迹的概括:“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而,“盡其心”與“通德類情”、“通變神化”何干?里堂在此未作解釋。從《繫辭》原文來看,“通德類情”是說伏羲作八卦的目的,而“通變神化”是說黄帝堯舜爲了使民不倦與宜之而動用的手段,兩者與“盡其心”似乎都無關係。另就後文來看,“通德類情”、“通變神化”之說不再出現,里堂轉用《說卦傳》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對“盡心知性”加以比配。看來,單靠本段文字,無法瞭解個中奥妙。
實際上,里堂此說,一本其將《孟子》性善說歸結爲《易》之思路,蓋里堂以爲:
孟子“性善”之說,全本于孔子之赞《易》。伏羲晝卦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28)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情不可以爲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貞,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于情之可以爲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于此,明揭“性善”之旨在其情,則可以爲善,此融會乎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29),是也。情欲之爲不善,“有師法之化,禮儀之道,即能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30)此孟子所謂“可以爲善”也。荀子據以爲“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爲“性善”,孟子深通于《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31)是爲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32)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視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以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33)可以無大過,即是可以爲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謂其能由不善改而爲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爲善,决其爲性善。伏羲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争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使之均歸于倫常之中。瞽叟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爲善之情也。可以爲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孟子正義》卷二十二,755~756頁)
此一大篇文字乃是疏《孟子·告子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一章(11.6)。里堂對孟子“性善”說的理解比較獨特,他非常强調“情”的作用,認爲人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所謂情可以爲善,是指情能由不善改而爲善。人情何以能由不善改而爲善?是因爲人情可以“旁通”“變通”,“通”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人皆有神明之德,二是伏羲等聖人教人“通”。里堂之所以斷定孟子“性善”之說來自于《易》,就是因爲《繫辭傳》中有很多講“通”之處:諸如伏羲“通德類情”,黄帝堯舜“通變神化”以及孔子言“旁通情”。按里堂的理解,整個《易》道無非一個“通”字。(34)
至此,何以里堂將“盡其心”與伏羲之“通德類情”、黄帝堯舜之“通變神化”相聯,涣若冰釋。在對孟子“盡心知性”說詮釋的基本方向上,里堂跟瑤田一樣,都接受朱子的盡心是由于知性的思路。里堂還從《易》那裹爲這種讀解找到一個根據:伏羲“通德類情”,黄帝堯舜“通變神化”,皆是出于對人性善的瞭解(即所謂“知性”),纔願意“盡其心”以教之的。其論證已如前揭:因爲人性中本有神明,人情可以旁通,所以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里堂這個說法爲其“盡心知性”的整個詮釋定下一個基調,那就是將其一律理解是對聖人而言,“盡其心”是聖人“盡其心(以教之)”;“存心養性”是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事天”也是聖人“事天”。王陽明曾將“盡心知性”理解爲“生知安行”的聖人之事,里堂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將整個“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修身立命”都視爲聖人之事。陽明之說已不能令人無疑,里堂此論恐怕更難服人。
里堂的結論“《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是建立在之前他將《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存養事天修身立命”與《易傳》“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比配的基礎之上。首先,里堂將“知性知天”劃歸“窮理”範疇。其次,里堂將“盡心存心養性修身”均納入“盡性”範疇。最後,里堂將“立命”等同于“至于命”。將“盡心存心養性修身”與“盡性”比配,給人感覺尤爲不類。本來,在《孟子》原文當中,“盡心知性知天”與“存心養性事天”、“修身”分別屬一、二、三節,無論從工夫還是境界上說,它們都不應當屬同一層次。里堂將其打並爲一,于理難通。站在里堂的立場上考慮,他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在他看來,“盡心知性知天”即所以“事天”,而“存心養性”即所以“修身”,换言之,“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以及“修身”這三者之間存在緊密的因果或順承關係。儘管如此,里堂關于《孟子》此章是發明《易》道的觀點,似乎更多出于一廂情願。
本文依次分析了伊川、梨洲、里堂三人對于《孟子》“盡心知性”說的詮釋,可以看到,雖然秉持不同的哲學立場(理學、心學、樸學),他們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易》作爲詮釋的主要資源。本來,以經解經在中國古典解釋學中是比較常見的做法,可是,其詮釋效果則依賴于具體文本而定。就“盡心知性”這一個案來看,以《易》解《孟》的做法並不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詮釋者僅僅根據一些字面上的相似就在兩者之間進行比配,而對不同經典之間的義理差异缺乏更精微的分疏。這種詮釋上的“誤讀”帶來兩個後果:在消極的意義上,它不利于對不同經典的義理系統做出深入辨析,從而影響到詮釋的準確;而在積極的意義上,這種誤讀卻往往開啟了一種新的理論可能。就後一點而言,《易》對近世(35)性理學的形塑作用實際超過人們想當然的程度。《易》在《四書》詮釋中的運用,是一個大的論域,本文所做的僅是一個初步的勘探而已。然而,即便是這一“淺嘗”,已經使我們認識到:给予《易》對性理學的形塑作用及其表現方式以更多關注,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注释:
①關于這一變化的思想史背景以及具體成立過程,已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晚近的中文論著有:邱漢生:《四書集注簡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徐洪興:《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章權才:《宋明經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陸建猷:“宋代四書學產生的歷史動因”(《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01年4月);劉澤亮:“從《五經》到《四書》:儒學典據嬗變及其意義——兼論朱子對禪佛思想挑戰的回應”(《東南學術》2002年第6期);王銘:《唐宋之際“四書”的升格運動》(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束景南、王曉華:“四書升格運動與宋代四書學的興起——漢學向宋學轉型的經典詮釋歷程”(《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蕭永明:“北宋心性之學的發展與宋代四書學的形成”(《中國哲學史》2008年第1期);朱漢民、蕭永明:《宋代〈四書〉學與理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蔡方鹿:《中國經學與宋明理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郭曉東:“《大學》的升格運動:從‘五經’系統到‘四書’系統”(《先典新識(名家人文與經典演講録第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詳見筆者“朱子對《孟子》盡心知性的詮釋”一文(宣讀于2012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國際四書學學術研討會”)。
③伊川對“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如上解讀不盡符合《易傳》原意。照此讀法,《易傳》這句話當作“窮理盡性則至命”,因爲既然窮理就是盡性,盡性就是至命,那麽說了“窮理盡性”之後再加上“以至于命”,就顯得多餘。事實上,伊川的詮釋在當時已不能令人無疑,張子就明確表示反對:“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窮理便是至于命’,子厚謂:‘亦是失于太快,此義盡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並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于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于命,盡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洛陽議論》,《遺書》卷十,《二程集》,115頁)。橫渠强調“知命”與“至命”之別,係受《論語》“五十而知天命”之說影響:“知與至爲道殊遠,盡性然後至于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即是戕賊,不可至于命。然至于命者止能保全天之所禀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不容有不知。(《橫渠易說》,《張載集》,234頁)簡言之,如果說二程奉行的是一種同時論,那麼橫渠堅守的則是一種先後說。“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外書》卷十一,《二程集》,410頁)可爲前說之概括,“窮理盡性,然後至于命。”(《正蒙·三十篇第十一》,《張載集》,40頁)、“既窮[物]理,又盡[人]性,然後至于命”(《橫渠易說·說卦》,《張載集》,235頁)則爲後說之寫照。
④據朱子《孟子精義》所載,此說爲横渠所持:“横渠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住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孟子精義》卷十三,《朱子全書》第七册,791頁)蓋橫渠以爲,“盡心以知天”可理解爲:“盡心”的結果將導向“知天”,但“盡心”本身並不就是“知天”。伊川對“盡心”“知天”的看法與橫渠不同,在他看來,盡心、知性、知天,與窮理、盡性、至命一樣,三事一時並了,“纔盡心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知天”,所以,伊川批評橫渠將以心知天比作居住京師往長安有將盡心與知天割裂爲二之弊(所謂“此猶是言作兩處”)。然而,“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于理不通,因爲當時的京師並不是長安。朱子對伊川的這個評論也不太滿意:“其議張子京師長安志說亦至論,但其所譬恐未的,若曰猶居開封而識京師則庶矣。蓋性只是心之理,天即理之自然處,初非有二物也。”(《孟子或問》卷十三,《朱子全書》第六册,995頁)
⑤對朱熹詮釋的詳細析評,見筆者“朱子對《孟子》盡心知性的詮釋”一文,此不再贅。
⑥《孟子·告子上》11.15。
⑦《孟子·告子上》11.8。
⑧《孟子·告子上》11.7。
⑨《孟子·離婁下》8.28。
⑩《孟子·告子上》11.10。
(11)《孟子·離婁下》8.19。
(12)《孟子·告子上》11.10。
(13)《孟子·離婁下》8.12。
(14)《孟子·公孫丑上》3.6。
(15)《孟子·告子上》11.7。
(16)“理”字在《孟子》中共出現六次,作動詞用一次:“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盡心下》14.19),趟歧注:“理,賴也。”作名詞用五次,其中,出現在“條理”一詞中三次(《孟子·萬章下》10.1),出現在“理義”一詞中一次(《孟子·告子上》11.7),作爲一個單字詞出現僅一次,而且是與“義”同時出現的:“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孟子·告子上》11.7)
(17)其他例子尚有:“人但知入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测至理,不其難哉!”(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六);“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四);“人情雖難知,然亦有可見之道,在窮理而已”(《續資治通鑑長编》卷二四二,“熙寧六年正月”條,王安石對宋神宗語),詳鄧克銘《宋代理概念之開展》(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第一章“事理與性理概念之開展”,尤其9~20頁。另,關于歐陽修“理”的思想,可參土田健次郎《道學的形成》(東京:創文社,2004年)第一章“北宋的思想運動”第二節“歐陽修——中央的動向”,尤其41~51頁。關于王安石的性理思想,可參鄧廣銘《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附說理學家的開山祖問題》一文(收入《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270~288頁)。
(18)陽明對梨洲的影響自不容低估,實際上,“心即理”不僅是象山的觀點,也是包括陽明在内整個心學的共識。不過,在對“盡心知性”說的具體詮釋上,梨洲並不取陽明之解,後者以《論語·季氏》的“生知”、“學知”、“困知”之說(16.9)以及《中庸》“安行”、“利行”、“勉行”(第九章)來解讀《孟子》“盡心知性”章,將《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分別對應于《論語》、《中庸》之說:“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傳習録上》,《王陽明全集》卷一,第5頁)陽明此解,與《孟子》本文甚難牽合,頗遭後世學者詬病,如牟宗三即認爲此種比配“極爲不類,滯之甚矣”(《心體與性體》第一部第一章,上册,25頁),黄俊杰亦嫌陽明之解纏繞(“《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漢學研究》第10卷第2期,114頁)。
(19)詳拙文“朱子對《孟子》盡心知性的詮釋”。
(20)據李明輝統計,焦循在《孟子正義》一書中徵引《孟子字義疏證》達十八次之多,尤其在注釋與心性論有關的章節時更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參所著“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及其方法論問題”一文,《孟子重探》,78頁。
(21)有關焦循著《孟子正義》的過程與時人評價,可參沈文倬爲《孟子正義》所寫的“點校說明”,中華書局標點本卷首。
(22)前人研究主要有黄俊杰:“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漢學研究》第10卷第2期,1992年12月);李明輝:“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及其方法論問題”(《孟子重探》,48~109頁)。黄文主要以焦循對《孟子·告子上》第六章“乃若其情,則可以謂善矣,乃所謂善也”、第一章“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梧倦乎”以及《孟子·離婁下》第二十六章“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的詮釋爲例說明焦循本《易》論孟的特點,對焦循本《易》來解“盡心知性”的有關命題並未展開具體分析,而是一筆帶過,略謂:焦里堂《正義》釋本章云:“盡其心,即伏羲之‘通德類情’,黄帝、堯舜之‘通變神化’,孟子此章,發《易》道也。”這一段文字具體顯示里堂本乎渠所詮解之《易經》以解釋孟子之思想,其事極具探討之價值(115頁)。李文則是在分析焦循對《孟子·告子上》第一章以及第六章的詮釋時指出其以《易》解《孟》的特點的,完全不涉及焦循對“盡心知性”的詮釋。
(23)瑤田解《孟子》“萬物皆備于我”(13.4)爲“萬物皆備于吾之身”,又據“心者,身之主也”,最後推出“物具于心”的結論。“心爲身主”說,朱子亦有之:“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觀心說”,《文集》卷六十七,《朱子全書》第二十三册,3278頁)。“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朱子語類》卷九十八,“張子之書一”,2514頁)。然朱子解“萬物皆備于我”不作“萬物皆備于吾之身”,而取“理具于性”說,“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细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孟子集注》卷十三,《四書章句集注》,350頁)。“物具于心”的觀點在朱子那裹是難以想象的。
(24)“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25)“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傳習録上》,《王陽明全集》卷一,第5頁)
(26)單從“盡心”與“盡性”關係的理解來看,瑤田似乎是受陽明影響。但瑤田對“盡心知性”的總體闡釋更接近朱子,說詳正文。而陽明對朱子用“格物致知”訓“盡心知性”的做法明確表示反對:“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傳習録上》,《王陽明全集》卷一,第5頁)
(27)標點有所改動。原文最後一段標點明顯有誤,現將誤處用下劃綫標出:“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修之,盡性也,立命至于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點校者不瞭解焦循此處係用《易傳·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來比配《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餋性修身立命”,遂導致斷句錯誤。今徑爲改正。以往研究者不曾注意及此,如黄俊杰即照抄而已(見“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113頁所引)。
(28)《易·乾·文言》。
(29)《荀子·性惡第二十三》。
(30)《荀子·性惡第二十三》。
(31)《易·說卦傳》。
(32)《易·說卦傳》。
(33)《論語·述而》7.17。
(34)這種理解有一定的文本根據,《易》之論“通”處,除了上述,尚有:“《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繫辭傳·下傳》)論者已注意到里堂易學此一特色:“里堂治易,其最主要之發明在其所謂旁通、時行、相錯、比例之悟。而旁通一義,尤爲其易學之擎天一支柱,其他諸說莫不由此基礎引申而出。”(何澤恒:《焦循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頁198。轉引自黄俊杰:“孟子盡心上第一章集釋新詮”,117頁)
(35)本文所用“近世”係指宋元明清這個時段。關于“近世”概念的分疏,可參陳來師:《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增訂版)》“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2010,1~2頁。
标签:孟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心即理论文; 伏羲八卦论文; 国学论文; 二程集论文; 中庸论文; 伊川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