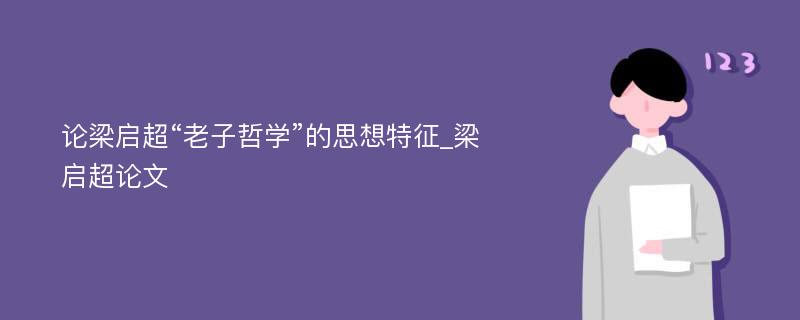
论梁启超《老子哲学》的思想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哲学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4-0066-07
打开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的1920年著作目录,本年学术著作,除《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为写《中国佛教史》所准备的多篇文章外,《老子哲学》、《孔子》、《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以及《论孟子》则显得较为突出。其中,《老子哲学》讲于本年和写于本年,其发表则在次年5月和8月的《哲学》第1、2期上。[1](p.196)该文一改早年评老子“弱我民志”、“坏我民心”,因而“毒天下久矣”之论调,居然批评人们以“厌世”评老子,是对老子的曲解。他说:“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语。他若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位最热心、热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2](p.22)
今天,我们分析该篇,不仅要注意梁氏评老为什么前后变化这样大——这一点,所有认真研究过梁启超的人都注意到了,而且更要注意他在该篇中,为何要以“我注六经”的方式“曲读”原典,将老子客观的、作为物质实体的“道”解读为佛家之“真如”;而当他将老子的道视为类似于“真如”的精神实体后,整个《老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体系,《老子》的著述宗旨是什么?我们将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向人们展示晚年梁启超的思想特色。
一
《老子哲学》是梁启超1920年“欧游”回国后在清华学校的一篇讲稿。“一战”结束前后的这次实地考察,在他思想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就是数十年来一直被先进的中国人奉为“老师”的西方人,因为这次世界大战使得“科学”与“自由”思想的负面影响大暴露,竟然研究向中国学习以整治其民族的心灵来。在《欧游心影录》中,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对西方“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梁启超说:“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近代以前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是封建制度、希腊哲学和耶稣教,如果说哲学“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 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的话,那么,宗教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这个标准。十八世纪前的欧洲,就是靠这个过活”。然而,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动不居,而内部生活也飘摇不定,人们本可以用哲学和宗教固定人心,哪知哲学首先举手向科学投降,实验心理学家们把人类的精神看成一个心理过程,做种种实验来测算它,“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是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有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大大小小的科学原理倒是天天出,今天认为是真理的,明天就变成谬误,一个权威还未树立起来,另一个就要拉起架势争席。“所以,全社会的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科学万能带来了物质的进步,却又把人变成了“沙漠中失路的旅人”,“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了。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写到此处,梁启超加了一个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3](pp.10-12)
梁启超的这段话以及这个自注非常重要,它几乎决定了他晚年治学的基本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科学知识必须学习和掌握,但它应该也必须为造就健全的人格服务;能够造就健全人格的学术除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外,最为直接的还有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并辅之以宗教哲学。所以,归根结底,科学虽不应、也不能摒弃,但它必须与人生哲学(含宗教哲学)一起,为提高人类的自由意志服务。而仅就研治“国学”而言,那就是要用科学的和内省躬行的方法,体会出一个“真我”来。所以,在回国的路上,他就与自己的朋友一起,商讨了建立学会,整顿杂志,涉足学校,联络教界(主要是佛教界)的各种大计。而当他在1920年3月回国后反观中国的学术界时,科学与民主、自由的呐喊仍不绝于耳;与他已经建立起忘年之谊的青年学术领袖胡适之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版再版,风靡东西南北;而梁启超读其书后,既为这位青年学人的学术成就所倾倒,同时又为其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知识主义倾向深深忧虑。他在同年10月18日《与适之老兄书》中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4](p.922)“欲批评者甚多”,是指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1922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所的演讲中找到答案。他在那次题为《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演讲中说:“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但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5](p.51)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实际上不是知识的学问,而是做人的学问:“我想,我们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令人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与宇宙融合为一’。这个问题,是儒家、道家所同的,后来佛教输入,我们还是拿研究这个问题的态度去欢迎他,所以演成中国色彩的佛教。这个问题有静的、动的两方面。道家从静入,儒家从动入。道家认宇宙有一个静的本体,说我们必须用静的工夫去契合他。”[5](p.60)如果我们粗粗看一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很难看出梁启超批评的“知识主义”的痕迹。而若仔细分析,这种痕迹还是有的。例如他说:“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方哲学的自然法。”何谓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6](p.50)这清楚地表明,在胡适眼里,老子的天道,自然法,实际上是自然界的法则。相比之下,梁启超恰恰是在“‘性’法”上解释天道和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参不得一毫外界的意识。‘自然’两个字,是老子哲学的根核,贯通体相用三部门,自从老子拈出这两个字,于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发深入人心。”[2](p.12)很清楚,梁启超正是从“自性”来解释老子的“自然”。胡适重客观、梁氏重主观,胡适重知识主义而梁氏重人文关怀,而这种人文关怀中,又含有佛教哲学的色彩。
二
以上可以理解为梁启超撰写《老子哲学》的具体背景。五千言《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在可感的万有世界之上,存在不可感的“无”的境界,同时给它一个“名”——道,断言正是这个不可见的“道”包有和产生了万事万物。而当老子将这个包有和生出万有的“无”命名为“道”的时候,立即与社会上所公认的伦理之“道”在意义上发生冲突,于是,他又从认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出发而走上了否定伦理之道的道路。就其《老子》的本来意义,实为“君王南面术”,《韩非子》之二《解老》、《喻老》对此理解得最直接、最清楚;只是由于他在万有之上立出一个玄妙的“无”,结果被后来的道教奉“真经”;又因他否定可见之道,所以成为视万法(可近似地理解为万有)为虚幻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的媒介。而到了近代,章太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明确提出《老子》“五千言所包亦广矣,得其一术,即可以君人南面矣”。[7](p.199)而梁启超执意要把老子放入“怎么能够令人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与宇宙融合为一”的思想家之列,因而把《老子》看作是相似于佛教哲学的“人生哲学”。事实上,我们阅读梁启超的《老子哲学》,立即就可发现它不过是“道家版”的《大乘起信论》之简本而已。
《大乘起信论》是署名马鸣著、真谛译,于南朝梁开始在中土流传,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被日本学者考证为中国人托名自著的佛教典籍。[8](pp.18-26)全论以“真如缘起”说为中心,建构了一个由“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所谓一心,即众生心,宇宙心,真如,如来藏;二门乃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三大就是体大、相大、用大。而梁启超在《老于哲学》中引了《老子》的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后解释说:“这一章是全书的总纲,把体相用三件都提絜起来,头四句讲本体,他说:‘道本来是不可说的,说出来的道,已经不是本来常住之道了:名本来不应该立的,立一个名,也不是真常的名了。’但是,既已不得已而立些‘名’,那‘名’应该怎样分析呢?第五六两句说道:‘姑且拿个无字来名那天地之始,拿个有字来名那万物之母罢。’上句说的就是《起信论》的‘心真如门’,下句说的就是那‘心生灭门’。然则研究这些名相有什么用处呢?他第七第八两句说:‘我们常要做无的工夫,用来观察本来的妙处;又常要做有的工夫,用来观察事物的边际。’他讲了这三段话,又怕人将有无分为两事,便错了,所以申明几句说::这两件本来是同的,不过表现出来名相不同,不同的名叫做有无,同的名叫做什么呢?可以叫做玄’。这几句又归结到本体了。”[2](p.9)”很显然,梁启超是按照《大乘起信论》的体系和思想来解释老子哲学。
首先,梁启超以《大乘起信论》的本体论来解释老子的“道”。梁说:“心真如门是说本体,心生灭门是说名相。”[2](p.5)佛家之真如,“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即为万法之原;而老子的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亦为万有之原。佛家之真如不可以“识”得,因而只能“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才能证得“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之真如;老子的道何尝不是如此:“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人们只能勉强描画它的面貌。(注:《老子》中确实包含着“道深”而平常人难以认识的思想,如开章“道,可道,非常道”即是。但梁启超此处所引述的《老子》十五章的原文当是:“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显然,原意是对“得到了‘道’的人称赞”,说这样的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因而,说“道不可识”,只是转意。)佛家之真如是“无”吗?当然不是,而是“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即所谓“有无双遣”,“不着一边”;而老子的道同样如此,别看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似乎是讲“道”就是“无”,其实如果从名相论来看,“‘无’决不能生‘有’,老子的意思,以为万有的根,实在那‘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的本体,既已一切俱非,所以姑且从俗,说个‘无’字。”[2](p.12)总之,从本体论来说,老子的道与佛家真如“同性”。《老子》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梁启超解释说:“究竟道的本体是怎么样呢?他是‘寂兮寥兮’‘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如实空’;他是‘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如实不空’;他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他是‘可以为天下母’‘似万物之宗’‘是谓天地根’的东西,像《起信论》说的‘总摄一切法’。《庄子·天下篇》批评老子学说,说他‘以虚空不毁万物为实’,这句话最好,若是毁万物的虚空,便成了顽空了,如何能为万物宗为天地根呢!老子所说,很合着佛教所谓‘真空妙有’的道理。”[2](p.7)这样,梁启超便把老子客观的道解释成主客观“合和为一”的真如了。而这一解释,倒也十分合乎“人的思想、人的生命与宇宙融合为一”的命题。
其次,梁启超用佛家“名相论”来解释老子对万有之相的论述。名相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概念,“名相论”即是认识论。《大乘起信论》认为:除了真如实体之外,万法无自性,即纯粹是因真如不守自性而生出无明,无明妄念执著,方才产生出生灭变幻的大千世界。亦可以这样来概括《起信论》的这一观点:万法虽“缘”于真如,但却直接“起”于无明妄念。用通俗的话来说:大千世界由人们的妄念、分别心而生出的。《老子》一书,不仅讲到了“道”,同时也讲到了被道生出的万有之相。但这个过程,是客观的自然过程,即如《老子》四十二章所说:“道生一,一二生,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有了万物之后,当人们借助美丑、高低、大小、久暂、善恶、祸福诸如此类“名”来了别和认识它们的时候,就加进了主观的成分。而《老子》一书恰恰是常将有生于无的客观过程与人类以其概念分辨、了别这一过程状态的相对性混在一起谈,这便让一些人从认识的相对性走向否定客观过程的绝对性。例如《老子》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对于这段话,如仅从道的客观性来解释它就是:“天下的人都知道怎样才算美,这就有了丑了;都知道怎样才算善,这就有了恶了。所以,有无由于互相对立而产生,难易由于互相对立而形成,长短由于互相对立而体现,高下由于互相对立而存在,声音由于互相对立而谐和,前后由于互相对立而出现。”[9](p.63)这一解释,强调了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然而,梁启超却抓住老子关于概念相对性、不确定性的论述,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视为“万物由妄念分别心所生”,所以他便将《老子》第二章作了如下解释:“怎样能知道有‘美’呢?因为拿个‘恶’和他比较出来,所以有‘美’的观念同时便有‘恶’的观念;怎样能知道有‘善’呢?因为拿个‘不善’和他比较出来,所以有‘善’的观念,同时便有了‘不善’的观念。所谓‘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等名词,都是如此。”他(即老子)以为,宇宙本体是绝对的,因这分别心,才生出种种相对的名,所以他又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意谓“人类既造出种种的名,名一立了,永远去不掉,就拿名来解释万有。我们怎么样能知道万有呢?就是靠这些名。”(注:在《老子》一书中,确实包含着“道常无名”、“始制有名”的思想,认为儒家观念(“名”)为社会动乱之根源,因而要破除儒家伦理观念(“名”),如《老子》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及《老子》三十七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等。但梁启超所引《老子》二十一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的解释并不合原意。原文是说“道”虽然恍惚窈冥,但“从古到今,它的名字不能废去,根据它,才能认识万物的开始。”参见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看来,对于“名”,老子并没有根本否定。)《楞严经》说的“无同异中炽然成异”,即是此意。[2](p.10)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是一个客观过程,可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不同,对于万物的差别性有不同的认识,强以自己的认识为标准让社会服从,就会造成混乱。然而,梁启超却不顾道生万物客观过程的论述,沿着老子认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的思路走向佛家名相学说,竟得出大千世界各种差别全由“我相”所引起的结论。梁说:“老子以为这些(指高下、长短、美丑、善恶,以及仁义礼等)都是由分别妄见生出来,而种种妄见,皆由‘我相’起,所以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这是破除‘分别心’的第一要著:连自己的身都不肯自私,那么,一切名相都跟着破了,所以他说:‘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所谓无名之朴,就是把名相都破除,复归于本体了。”[2](p.14)
“复归本体”也就是“道法自然”,让人在心灵中显示出“道”的自然而然之性。这个自然而然之性又是何状呢?梁启超解释说:“老子以为宇宙万物自然而有动相,亦自然而有静相。所以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复’字是‘往’字的对待名词,‘万物并作’,即所谓‘出而异名’,都是从‘往’的方面观察的;老子以为无往不复,从‘复’的方面观察,都归到他的‘根’。根是什么呢?就是‘玄牝之门,绵绵若存’的‘天地根’,就是‘橐籥’,就是‘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2](p.12)就像将“有无双遣、不着一边”之状,“姑且从俗,说个‘无’字”一样,“归根”之静,亦是有动有静、非动非静的,所以亦可姑且从俗,说个“静”字。梁启超所解释的这段话、这层含义,很像《起信论》“一心有二门、二门归一心”的思想逻辑:“往”就是“真如”不守自性而生出无明妄念,无明妄念执我而又生出宇宙万法;而“复”就是由识转智,认识到万法唯识,皆由无明妄念所生,从而证得涅槃,也就复归于“真如”本体上来。这个本体对于万法之动而说,也是寂静的。很明显,梁启超讲解了老子,同时也宣传了《大乘起信论》“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的思想。
再次,用“无之以为用”解释老子的“作用论”,导人进入“无我”之境。梁启超认为,破我相、灭妄见,返璞归真,复归本体,实是《老子》一书之根本目的。他说:“五千言的《老子》,最少有四千言是讲道的作用。但内中有一句话可以包括一切,就是:‘常无为而无不为’。”[2](p.15)人们只知道可以看得见、能被自己占有的物质性的东西有用,其实,在老子看来,那些只是一时之利,最有用的是看不见的“道”,比如,《老子》第十一章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道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如何来发挥它的作用呢?《老子》四十二章曾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就是说,履道要从“逆”世人偏见开始,走不争、不为、不占、不有之路。梁启超特别欣赏老子这样一类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梁启超说:英国人罗素很欣赏老子的这一思想,认为这是用人类创造的本能来克服占有的本能。“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专提倡创造的冲动,所以老子的哲学是最高尚而且最有益的哲学。”[2](p.16)
以上就是梁启超《老子哲学》之大体。观其大体,其思想特征在于通过破除人们的偏见来除灭人们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欲,而回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本性上来;这是道家之思想,也是大乘佛教之精义。就其治学特点来说,则讲大意而不局于小节,而小节之错,不误大体。
三
从前边我们所立的两个注解中可以看出,梁氏解《老子》,是借《老子》的文句,阐发自己的思想观点,而不管这些文句在原章语境中的含义,更不关心原章章义。其实,要深究该文,梁氏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离体发挥的地方很多。下文再择其特别重要者略举一二。
首先,关于本体的“不可思议”问题,梁启超把佛与《老子》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旨趣强拉在一起。由于佛家唯识宗认为万法唯识,即宇宙万物为妄念所生,要领会真如本体,是“不许思议”的。这是“因为一涉思议便非本体,所以《起信论》说‘离念境界唯证相应’”。而梁启超说:“老子说的也很有这个意思”,即是说“道”的本体也是“离念境界”。他举的例证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四十七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十八章)须知,《起信论》的“离念境界”,不是不要知识,而是将知识转化为更高级的智慧,即所谓“转识成智”的。所以此处之“离念”,用现代认识论的语言来说,是对感性认识的扬弃。而如果我们把梁氏从《老子》中引出的这些例证放回原章中去理解,是读不出扬弃感性认识的意味的。
其次,关于老子对待名相、概念态度问题,从《老子》全书看,他对儒家的仁义礼一套道德规范是彻底反对的,然而,对于一般的社会制度,老子只是主张限制它的范围并非根本摒弃。如《老子》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句话是老子认定“名”有一定作用、让其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明证。然而,梁启超遵从胡适的校勘,将此章改为“……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即将王弼本中的“止”改为“之”、将“殆”改为“治”(注:参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8页。按:胡适并没有读懂王弼的注,其校勘是错误的。),其用意是站在“名是知识的利器”的立场上,加强对老子“废名”思想的批判;梁氏虽不同意胡适对老子的批判,但却赞成他的校改和解释。因为胡适这样一改,老子便成为彻底的反“名”主义者,这正好满足了梁启超将老子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变成佛学名相说之需要。所以他特别声明本条引文从胡适,并顺便解释道:“既制出种种的名,人都知有名,知有名便不治了。”[2](p.13)这种解释,离老子原意相当远了。
其实,以梁启超国学之功力和为学之智慧,他是不应该产生这些“硬伤”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梁启超采取“我注六经”的手法借老子发挥己意。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说:刚刚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由于看到了欧洲人失落了宗教感情后的恶果,所以在1920年当年最为大量的学术活动便是撰写多篇“中国佛教史”的文章。他在研究印度佛教初传中土的路线时,特别强凋南海路线,目的是想证明佛教教旨与老庄之学有着内在的亲密关系。(注:见梁启超《佛教教理在中国的发展》诸文,《饮冰室合集·专集》58,中华书局,1989年版。)此时的梁启超,表现出以科学立教、以“无我”铸造人生的强烈目的,从事中国佛教史的研究。现在,他直接讲述《老子哲学》,当然想借老子哲学,顺便宣传一下佛学经典,特别是中国人自产的《大乘起信论》。后来,在他来东南大学讲述《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时候,间隔虽只有一年的时间,但他进一步领悟到佛家真如更贴近于庄子的“道”而与老子的“道”多有相差,所以他对老子的论述变得客观多了。
比如,在《老子哲学》中,梁启超以“自己如此”来解释老子之“自然”。而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他则说:“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彼宗盖深信‘自然法’万能”、“彼宗不体验人生以求自然,乃以物理界、生物界之自然例人生之自然”等等[10](pp.99~105),还老子的道以本来面目。然而,梁启超毕竟不是胡适,他不会因此而就会走科学主义和知识主义的路。他在讲述老子之道的意义时,仍从人生哲学方面立论。他说:“其一,彼宗将人类缺点,无容赦的尽情揭破,使人得反省以别求新生命”,这是指老子哲学有揭露人性之伪的功能;“其二,道家最大特色,在撇却卑下的物质文化,去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在教人离开外生活以完成内生活”,而所谓“完成内生活”者,是因为人类追求奢欲则侵害了自己的“天机”,所以《老子》用“去甚、去奢、去泰”的方法来救治,要人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和“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精神来创造理想的人生。[10](p.107)因而,说到底,梁启超不可能通过对《老子》的真实面目的揭示而放弃其铸造美好人生的宗教感情。
为了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梁启超的这一学术特色,我们不妨引述一下晚年胡适对老子哲学的“再认识”。1959年胡适发表了《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一文。他说:“这个新的原理叫做‘道’,是一个过程,一个周行天地万物之中,又有不变的存在的过程。道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也是自然如此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自然主义宇宙观的中心观念。”“自然主义本身最可以代表大胆怀疑和积极假设的精神。自然主义与孔子的人本主义,这两极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同等重要的。”汉代的王充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下,以“疾虚妄”为著书宗旨,而他对于神学的批评,用的就是“老子与道家的自然主义”。至于王充自己,“用人的理智反对无知和虚妄、诈伪,用创造性的怀疑和建设性的批评反对迷信,反对狂妄的权威。大胆的怀疑追问,没有恐惧也没有偏好,正是科学的精神。‘虚浮之事,辄立证验’正是科学的手段。”[6](pp.555-559)胡适讲老子时,想的是科学,他把老子看成中国提倡科学精神和建立科学方法的奠基人。与胡适的老子相比,梁启超的人生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的老子,其形象不是同样的鲜明吗?
(作者附言:本稿的背景部分,使用了由我本人参与讨论、蒋广学教授主讲的《先秦子学在近代的新角色》讲义中的材料,特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