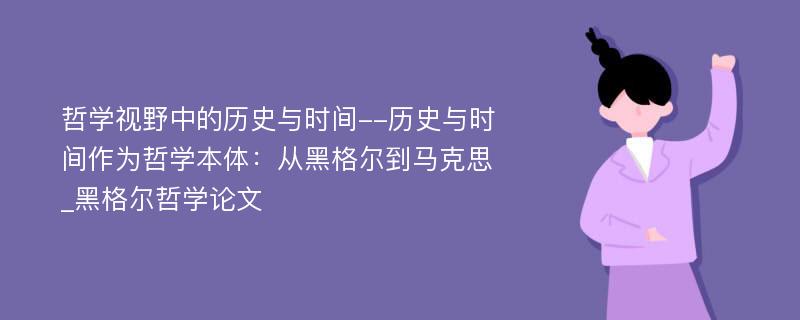
哲学视域中的历史与时间——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与时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哲学论文,视域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作为一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规定性,它不等同于历史学(历史编纂学)中的“历史”。一般而论,历史学研究,是对象性地认识过去曾经存在的对象的历史领域;而历史性方法则大多是指观察的历时性视角(或过程性)。而哲学本体视域中的历史(性),是与辩证法具体的生成性规定一致的。从思想史上看,“历史”作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的。在他那里,世界的本体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赫拉克利特形象地称它为永远燃烧着的“活火”。在这里,生成性一开始就是与辩证法相关联的。可是这种本体意义上的生成性起初并没有被指认为历史性。维柯和赫尔德都体认过历史过程性,可是历史又并没有能够上升到本体的逻辑层面中来。康德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指认过物自体的历史样态(现象)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以特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这种呈现是一种“此岸”现象的历史性构成,而恰恰不是本体的生成。费希特已经注意到了“创造了客体”的行动主体之基始性作用,但他也没有真正将分裂的世界重新弥合起来。
生成性与历史的联结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中完成的。在黑格尔这里,“生成性”是由内趋力所导致的创造性的本体的历史(时间)性生存。在“有”与“无”的辩证法转换中,变易生成(“流动变化”)成为第一个重要的逻辑基始规定。青年卢卡奇正确地看到,黑格尔的历史规定,即是“实际内容的生成”(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221页。)。历史的真正主题是世界特定的产生和消失。历史当然意味着具体生存的有限性,这是辩证法之根。所以,历史又必然是一种建构性的辩证总体。在此,历史性生成就是历史辩证法的一元论。也只能在统一的历史辩证法中,“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的对立的扬弃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219页。)。 可是,在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这里, 这个一元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即主体行为创造的历史,别的历史是没有的。所以,第一回外化为外在的“物”时,“历史”是不存在的。自然自然界没有历史(生存时间)(“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只有持续性,即被指认为物相的僵死的现存和持存。只有自我生成的“观念”才造成了外在自然(物相)本体性的历史生存。第二,在黑格尔看来,只是观念的历史性生成,才造成了人类主体的历史(时间)性存在。当人类个体分有观念的历史本体时,人的有限“定在”才可能真实地被建构出来。由此,人的存在才必然是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第三,而在黑格尔这里,历史表现为历史主体自身的中介对自身的认识(主体的自我反思),于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是统一的(即后来列宁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只是在历史主体的一定时限中自省到自身本质的主体。
依我之见,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历史规定并不是一种纯主观性玄想的产物,而是他深刻地对法国大革命和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具体说,即工业文明所创造的社会生成(时间)才是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真正基础,相对于农业生产把自然视为一种抽象的物,工业生产将自然第一次变成对象,并在人类主体的创造性物质实践中给予其历史性的存在(自然对象经过人的生产实践所设定和中介)。但在黑格尔那里,他是用一种复杂的唯心主义思辨外壳将其神秘地包裹起来了。
我已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工业文明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注: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带有本体意味的历史性存在,而不是一般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观。最初,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里注意到“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别。他发现,不动产最有历史持续感却无历史性,这是因为自然经济方式的农业生产是内封闭的循环过程(没有生成性时间的生存方式)。从不动产到动产,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工业生产中,社会存在不再是“物”,人的动态的社会生存活动成为在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交换的现代经济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黑格尔、马克思是站在同一出发点之上。不过,历史性生存是如何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被建构出来这一问题,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解决的。
首先,马克思发现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了自然物质的第一性,但这个自然物质却被设定为是可以直接达及的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则要告诉我们,人类视域中的自然界总是历史的(青年卢卡奇将这一点夸大成“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就造成了某种本体论越界,简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则是其逻辑必然。马克思的原意并非如此,他只是想说明,自人类产生以来,进入实践境域中的客体自然对象只能是随着人的历史情境逐步呈现出来)。由此,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本身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一切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直观物质都是一种非历史的主观假定。此时马克思认识到,历史从来不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或抽象的持续存在的实体,它只能由特定的生产活动去建构。马克思这里的“历史”主要是工业生产之上的人类主体主导的历史情境,即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新的社会存在。这不是工业以前那种人只是周围自然过程的一个被动因素的生存。这个“历史”规定的经济学基础不是农业社会,甚至不是重商主义的,而是古典经济学所认可的工业和工业之上的现代经济过程。在大工业生产以前的社会生活中,人只是自然活动中的一个能动因素,人还是在土地上优选和协助自然物质生产。而工业才第一次创造了人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新存在。财富的主体不再是外部自然的结果(“自然财富”),而直接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社会财富”)。所以马克思此时眼里的实践主要是工业的。工业实践也是一种新的物质存在,人类自己是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我以为,这个“历史”是经过马克思重新设定的“本体性”规定。
在这里,马克思有一个理想的原初关系的设定,即把生产活动当作是适合于所有存在的一般基础(他设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能够适合于一切人类存在,可他自己在此处采用的却是近代工业生产所指向的历史性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性生存是一个动态的功能关系体。社会历史生存的基本内容,由四种活动去建构:生产(第一个历史活动)、再生产(第一个历史性活动)、人本身的生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特定的历史所建构)。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吃喝穿住这样的物质条件。人与动物的区别,不是对自然物的现成采用,而是创造性的物质生产。这是历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历史原初规定中首先是人的客观能动性。这是人类生存的本体与基始。不是笛卡尔——黑格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里当然有本体和基始性之意。这也是马克思历史话语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人类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是人类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的变革构成的历史时间。对于这一点,本雅明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的存在所填充的时间”,这种时间恰恰是由打破抽象的连续性而获得的(注:本雅明:《历史哲学文集》,转引自刘北城《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所以, 马克思这里的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海德格尔后来的《存在与时间》正是建立在这个深层本体逻辑之上的)。马克思此时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系统的改变之上的生产进步,才是历史时间性的根本。这种生产性的时间建构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过程的根本,这是比观念的时间、政治的时间、文学的时间要更真实的历史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