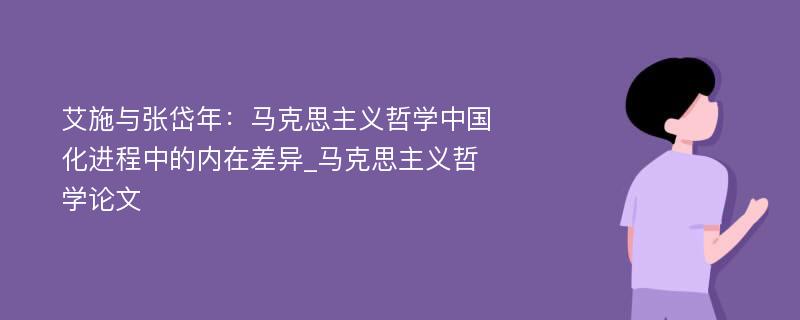
艾思奇与张岱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内部分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歧论文,过程中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张岱论文,艾思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12-0031-06
张岱年与艾思奇同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唯物论者,艾思奇的影响自不必说,张岱年也曾在大学讲堂里讲授辩证唯物论,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其阐扬新唯物论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曾把艾思奇和张岱年看作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两盏明灯。[1](p.42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艾思奇与张岱年都赞同新唯物论,但他们的思想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就二者都是新唯物论的赞同者和支持者而言,这是一种内部分歧。
一、艾思奇与张岱年在20世纪30 年代的一场争论
1935年4月,张岱年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指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除了应是辩证的、唯物的以外,还应是批评的、理想的;要产生这样一种新哲学,就必须对中外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综合创造。该文发表后不久,艾思奇就在《读书生活》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对张岱年(季同是张岱年的曾用名——作者按)的观点提出批评。
张岱年之所以提出创造新哲学的主张,是因为他认为没有现成的、适合中国当时需要的哲学。在他看来,中国的旧哲学不能适应中国当时的需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西洋哲学也无法适合中国当时的需要。一方面,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他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可能完全契合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本性相结合,方能深入人心。他认为,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2](p.238)既然没有现成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哲学,就要进行综合创造。这种综合创造的哲学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能融汇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点而成为一个大系统;第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第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第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
但艾思奇认为,张岱年的主张实际上是强调了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哲学的一般性。他说:“中国的新哲学,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学体系中,用不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夸大,否认了一般性啊!”[3](p.140)为什么张岱年会夸大中国新哲学的特殊性呢?艾思奇认为,这是不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所致。中国实践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呢?是民族领土的完整及争得民族的解放。中国需要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是“能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的哲学。[3](p.140)艾思奇认为,中国当时的实践,需要一种能够成为民族奋斗行为的指针的哲学,新唯物论恰恰是我们民族奋斗的指针,因而也就是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在艾思奇看来,由于不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张岱年综合创造的哲学主张失去了现实基础,其“精粹”与“优点”的选择标准无法确定,同时也无法说清鼓舞国人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的“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这样一来,所谓中国需要的哲学就只是半空中说话,是一种缺乏针对性的臆想、一种“哲学者会客室内的谈玄”。[3](pp.138-140)
问题在于,张岱年是不是如艾思奇所说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呢?应该承认,在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上,也许张岱年不及艾思奇,但他在文章中也曾指出,当时的中国,国家与文化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人们或失其自信,或甘于堕落,最大的一国竟若不成国,最多的人民竟若无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一种使人勇猛奋斗、精进不息的哲学,才能使民族复兴、文化再生。[2](p.237)应该说,这正是中国当时的现状和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说,张岱年与艾思奇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了解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在于他们所认为的适合这种需要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以及有没有现成的、合乎这种需要的哲学。张岱年认为,没有现成的这样的哲学,因而需要综合创造;艾思奇则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哲学,这就是新唯物论。
张岱年认为,现有形态的新唯物论还不能完全适合中国需要,因为在“批评的”与“理想的”这两个维度上新唯物论做得还不够,需要改善和发展。对此,艾思奇明确地持反对态度。
首先,艾思奇认为,张岱年提出新哲学应是“批评的”,实属多此一举。他认为,新哲学是战斗的,要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指挥残酷的战争,所以自然不会忽视批评。[3](p.140)但事实上,张岱年所说的批评与艾思奇所谓的批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张岱年所说的“批评的”是指对各种思想和学说的一种辩证的态度。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批评的就是不武断的;二是批评的即是分析的。张岱年在30年代时常论及“批评”之不武断的一面,而在40年代的著述中,则比较强调批评之分析(解析)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在张岱年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批评的就不是武断的,而要做到不武断,就必须是分析(解析)的。“哲学必须是精密的,即必须是充分的‘哲学的’;因而,必须是批评的。批评即武断之反,如不愿是武断的,便必须是批评的。用一名,必须有其明确的义界;立一说,须有其精严的论证。不能证者不立,不可验者不持。二义不可表以一名,两意不可混于一辞。无当辨而不辨者,无日用而不知者。可再分析即再分析,可再细求即再细求。哲学务在求真知,原必须是极其矜慎谨严的。”[2](p.241)张岱年认为,无论是就批评的“不武断”的含义还是就批评的“分析的”含义而言,当时的新唯物论者做得都是不够的。
在发表于1933年的《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一文中,张岱年指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任何学说自囿,不能受学派的局限,对于任何学说都要保持批评的态度。[2](p.149)如果具备了批评的态度,“则必能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学派学说的地方;而现代它派的哲学亦非皆无所见,即古代哲学,西洋的及中国的,亦都非可完全排弃。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亦非无缺欠,而其它任何一派哲学都非无缺欠。”[2](p.150)但在张岱年看来,当时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的就是这种批评的态度。一方面,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2](p.149)另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则采取类乎宗教信仰的墨守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2](p.278)张岱年认为,这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
在哲学应是分析(解析)的这一点上,艾思奇与张岱年也有分歧。张岱年认为,逻辑解析是批评哲学(与玄想哲学相对)的方法,而要肯定逻辑解析,势必就要肯定形式逻辑的作用。这与艾思奇在30、40年代对形式逻辑作用的否定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1936年)中,艾思奇说:“我们并不是说用形式逻辑研究会全无所得,但形式逻辑只能看见静止的一面,并且会夸大了这一面,而忘记了根本的动态。既然有了辩证法,能够为我们抓着全面(形式逻辑的一面也包摄在内),那我们就不必仍然要用形式论理学来把握它了。”[4](p.308)张岱年则认为,包含形式逻辑方法在内的逻辑解析方法是哲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它对于新唯物论本身的发展完善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唯物论,涵义则丰,形式则粗。若干概念皆无明晰之界说。若干原则又未有精察之论证。而一般言新唯物论者,如析辩证法的内容为数条,则每每此条以方法言,彼条以规律言,混糅不判,实不为小过。”[2](p.134)不仅如此,当时的许多新唯物论者对自然、社会、思想之规律未加区分,这都是缺乏逻辑解析所致。他认为,辩证法为通贯自然、社会、思想的共同规律,但自然、社会、思想是有区别的,它们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如不加辨析地以社会、思想的规律加于自然之上,或反其道而行之,都是不恰当的。此外,许多新唯物论者包括艾思奇都赞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是一事”的主张,张岱年则认为:“辩证法一方面为客观规律,一方面为研究方法。其研究方法一面固为逻辑之一部分,其为规律方面则何尝不然?辩证法与认识论尤不得不判,不可视为等一,固有辩证法的知识论,而辩证法非即知识论。”[2](p.134)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当成一事,在张岱年看来,是一种由于缺乏逻辑解析而产生的笼统的观点。因此,形式逻辑或说逻辑解析不仅不能被辩证法所替代,相反,它在辩证法的运用中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是完善唯物辩证法的工具与手段。
总之,在张岱年看来,无论是就“批评的”不武断的维度还是就分析的维度而言,新唯物论都有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其次,艾思奇认为,张岱年提出新哲学应是“理想的”也属无谓。“不错,新哲学的内容应是‘唯物的’,对理的,但为什么要加上理想的呢?这不是反把视线扰乱了么?”[3](p.140)艾思奇认为,唯物、对理的自然就包含理想。新哲学指导着改变现实的实践,当然包含理想的维度,所以张岱年所谓唯物与理想的综合是无的放矢。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己任,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所以不可能不包含理想的成分。事实上,张岱年也对新唯物论的人生理想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正式提出过一个完整的人生哲学系统,但是他们的学说中却蕴涵着伟大的人生哲学。”[2](p.200)在发表于1934年的《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一文中,张岱年从人的本质、克服环境与改变人性、自由及理想、道德、改善生活与道德革命几个方面,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他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是社会的、革命的、实践的人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辩证的,唯物的人生哲学。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辩证唯物论的人生论的歪曲。“一般人谈起唯物的人生观来,总觉得这是专求物质享乐、毫无理想、粗浮贪鄙的人生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2](p.209)在张岱年看来,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现理想的途径;既注重客观的物质情况,更思所以改变之、克服之,所以是一种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活的人生哲学。
既然新唯物论包含人生理想论的内容,且其中不乏合理成分,为什么张岱年还要特别提出新哲学应是“理想的”呢?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在张岱年看来,新唯物论虽谈及人生理想,但对人生理想的重视及研讨却是不够的。哲学中研讨理想的部分,属于人生论或人生哲学。张岱年对人生哲学十分关注,甚至把它看成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这与艾思奇明显不同。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探讨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问题,却没有专门的章节论及人生论。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1933年)中,他更是将人生哲学研究看成是历史的倒退,认为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以人生问题的研究为主流的哲学是世纪末哲学。“以人生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是民族资产阶级堕落以后的退步的哲学,其发生,宣示了资产阶级已不能再成为社会发展的推进者了。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在一九二七年后掩蔽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又才显露头角。”[4](pp.64-65)艾思奇把这种情况与欧洲的情形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在欧洲,黑格尔可算是资产阶级的前进哲学之顶点和没落点,此后便是两大潮流平行的斗争的发展。其中,一种潮流是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倭根以至狄尔泰等人的人生、道德问题的潮流,另一种潮流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至列宁的唯物辩证法的潮流。“前者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欲在精神中求安慰的企图,后者是前进的阶层在物质中求胜利的怒潮。”[4](p.66)这里,艾思奇在某种程度上是把人生哲学与辩证唯物论对立了起来。这种态度张岱年是不赞成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艾思奇对人生哲学问题毫无涉及。他在《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1935年)、《共产主义者与道德》(1938年)等文章中对主观与客观、意志自由与因果性、人生的目的性、道德问题等做了探讨。但总体看来,他认为主观性是人生观的中心问题,而这种主观性是可以用客观性加以说明的,所以人生观问题本身也就失去了某种意义。“社会科学能以客观的物质条件说明主观的能动性,因此,也能说明人生观,说明各种各样的人生观是发生于怎样的物质基础,说明它的局限性和不完全性,并能找到什么是更完全的目的。在这一切的意味上,科学的法则是能够说明人生观,支配人生观,改正人生观而且应该让它来改正的!”[4](p.98)
第二,张岱年认为,在人生理想论上,中国传统哲学及西方哲学中的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甚至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要扩充、完善新唯物论中本不充分的人生论内容,就要借鉴各派哲学的合理因素。张岱年按核心范畴的不同将哲学分为物本论、心本论、生本论、理本论、经验论五种。与艾思奇将唯物论以外的哲学归入唯心主义而加以拒斥不同,张岱年认为,“一个哲学家之工作,如非全属虚耗,则必多少有其所得。故不同类型之哲学,虽皆非全真,而必各有所见。”[5](p.10)在人生理想问题上,他对传统哲学及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西方哲学中的心本论哲学与生本论哲学均有所肯定。他认为,心本论与生本论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我们扩充、完善新唯物论的人生论具有借鉴意义。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在生活理想方面的研究、研讨也是卓有成效的,对此,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或加以贬斥,而应当继承、修正而发挥之。[2](pp.262-263)艾思奇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唯生论与生命哲学是二而一的东西,同样标榜既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生。以生命,生活,人生为研究对象。实则仍只是化过装的唯心论,是唯物论的死敌。而在中国的唯生哲学,也和以前的人生问题时期一样,内中仍混有封建的传统哲学之要素。又是一度的封建幽灵之复归!”[3](p.7)这段话既体现出艾思奇拒斥唯生论、唯心论的决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对传统哲学中人生论内容的否定态度。
总之,艾思奇认为,“理想的”是新唯物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张岱年认为,无论是对“理想”的重视程度还是对“理想”的探讨,新唯物论都是不够的,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就要对其他学派的哲学有所借鉴。
二、“艾张之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内部分歧
艾思奇与张岱年的上述争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分歧,这是一种内部分歧。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艾思奇的观点与张岱年的观点的区别,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向度来理解。艾思奇批评张岱年夸大了中国的特殊性,忽视了辩证唯物论哲学的一般性。他认为辩证唯物论即是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可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似乎就是将一般性的理论拿来运用即可,根本谈不上“中国化”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冯契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之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就必须使它取得民族的形式,使它与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6](pp.482-483)由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解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的传统相结合。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这两个方面还是各有侧重的。可以说,张岱年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而艾思奇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中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p.534)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点,势必不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哲学。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1939年)中也提到,哲学的中国化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经验与教训。”[4](p.420)但摆在面前的迫切的历史任务却使艾思奇等人无暇完成这种对传统哲学进行系统地批判继承的任务,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现实的关注上。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严酷的现实斗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两个向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张岱年而言,他不是没有看到新唯物论一般性的指导意义,也不是没有看到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他只是侧重强调了民族精神的特殊性;而对艾思奇而言,他也不是没有看到中国需要的哲学的特殊性,只不过他所强调的特殊性体现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而已。
其次,张岱年的观点与艾思奇的观点的区别可以理解为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陈卫平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他表性成果是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一种是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性成果是张岱年的“解析唯物论”。[8](p.85)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及社会存在所发生的作用,所以,它必然更加关注现实,关注理论对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但它更加关注理论本身的一致与圆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一种批评的态度,需要和其他理论与思想之间互相争鸣。
当然,这样讲并不等于说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理论的圆融、完全没有批评的态度。艾思奇曾说道:“辩证法唯物论是人类哲学史最高的总结,一切哲学对于它都有相互的贡献,对于其他的哲学,它并不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它会以它的极大的包含性吸取一切哲学的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成为中心的理由。论争是不是容许呢?自然容许的,而且也是不可免的,然而在存精去芜的立场上,论争是有善意的、互相发展的作用,而不是绝对的互相排斥。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法唯物论是最和实践一致的哲学。”[4](p.388)表面上看,这似乎也合乎张岱年所谓的批评的态度,但一经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艾思奇将辩证法唯物论视为人类哲学的最高总结,那么其他思想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只具有“史”的意义、只具有佐证的意义,这与张岱年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张岱年认为:“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2](p.132)其他学派的存在并不仅仅具有“史”的意义。“俄国在革命前后,有马赫派之产生,吾以为此实非偶然,实因马克思兼综了佛耶巴赫之唯物论与黑格尔之辩证法,而对于实证主义,完全忽视,结果实证主义之进一步的发展即马赫哲学中的一部分真理,终于吸引去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惜此部分人过于被马赫所吸引,竟至遗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若干根本原则。不能纠正马赫的唯心倾向,而反落入唯心的泥潭中。列宁则能起而矫正之,然后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乃大白。”[2](p.133)这里,且不论张岱年对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的评价正确与否,单就其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态度而言,他显然不像艾思奇那样认为其他哲学流派仅具有“史”的或“佐证”的意义。可见,他所谓的批评的态度与艾思奇对论争的“宽容”,内涵是不一样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方面与社会存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总的来说,在20世纪30、40年代,艾思奇强调的是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存在的互动性,张岱年则更多地关注其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与其他哲学思想的互动关系。这一方面导致了两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哲学的“批评性”的理解产生差异。艾思奇所理解的“批评”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批评,张岱年所理解的批评则主要是对其他哲学思想的一种辩证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取得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的时候、在现实急需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学派的存在表现出一种排他性,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让位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批判遮蔽不同思想间的争鸣,提高让位于普及,这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当成一种常态,便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在1949年后表现得尤其明显。1949年至1950年,张岱年曾在大学里开设过“辩证唯物论”、“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但后来发现,讲辩证唯物论哲学,必须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共党史,而我对于党史及当时政策都缺乏信息来源,难以联系实际,以后便决定不再讲辩证唯物论课程了”。[9](pp.602-603)对此,张岱年曾对刘黄女士(张岱年先生的儿媳——作者按)解释说:“我不是党员,不敢和艾思奇争。”[1](p.420)当被问及他与艾思奇讲课的区别时,张岱年说:“我讲得比艾思奇深刻,他讲得比较浅、比较通俗。”[1](p.420)陈卫平在《理论创新·评价公正·知识普及》一文中说:“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被党和国家领导人用以指导治党治国的实践,所以有关的阐释权和创新权主要归属于他们也在情理之中;而对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创新,主要是着眼于学科知识和专业学理的,所以只有具有有关的专门知识和从事专门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胜任。……这两类创新成果的创新主体是不可能互换和替代的。”[8](p.85)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谈到,哲学事实上以两种形态存在于我们中间,一种是消融在实际问题的讨论中的存在,一种是脱离实际的空理论的存在。后一种存在“大部分是存在在书斋里,是存在在一些故意回避现实、对现实麻木、或不能适应现实的学者教授们的书斋里。这里的哲学是以直接的面目出现的。然而也就是苍白的,没有现实的血流贯注着的空理论,基本上也就是一种观念论”。[4](p.385)虽然我们不能把艾思奇所说的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陈卫平所说的两种马克思主义完全对应起来,但根据前面我们所论及的艾思奇对张岱年的批评,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艾思奇把自己的哲学看成前一种形态,而把张岱年的“解析唯物论”看成了后一种形态,并且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同为新唯物论的支持者,艾思奇与张岱年还是存在着许多分歧的,这种分歧和争论反映出理论与现实、理论与理论及论争者之间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与分歧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这些矛盾以一方压制另一方的形式解决,就不符合理论本身的发展逻辑,同时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艾思奇论文; 张岱年论文; 辩证唯物论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