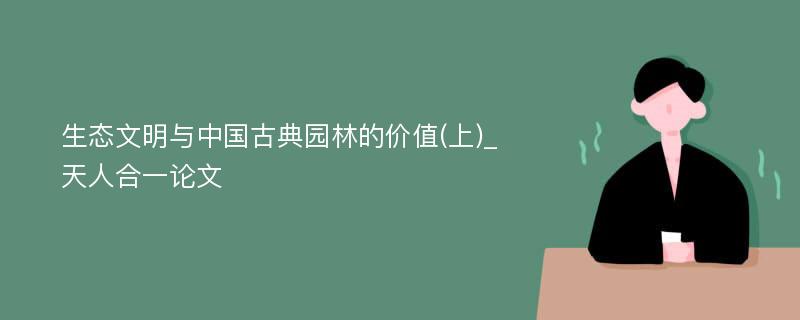
生态文明与中国古典园林的价值(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典论文,园林论文,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看,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传统工业文明时代与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之交。这个时代之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类从非生态时代、不可持续发展时代,向生态时代、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嬗变。
因此,对中国古典园林美的研究,必须根据新世纪的急需,重点更新理念,力求面向生态危机的世界,面向生态觉醒的现实,面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其中包括我国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之一的生态文明。在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对当代和未来的意义,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应吸取其有益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启示”,而这“绿色启示”,又离不开“天人合一”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的、美学的思想渊源,否则,研究就必然会脱离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深层地发掘中国古典园林美真正的生态学价值乃至未来学价值。
一、哲学寻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观
本文所论“天人合一”,其概念亦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此外,当然还包括它在审美意识上的表现。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因为如此,文化哲学、园林美学的任务是必须首先深入探究和较全面地概括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的种种学说,澄清多年来人们对它的偏见和误解,进而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以利于今天的园林美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
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天人合一”,曾被有些人误解为是涵盖古代中国全部哲学思想的一种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其实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首先,应指出和辨析的是,在中国的“天人关系”论之中,就存在着与“天人合一”相对的“天人相分”的观点。而所谓“天人合一”,也并非百分之百都是合理的;所谓“天人相分”,也不应全盘否定。这里先说后者。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就是杰出的“天人相分”论者,其《天论》中就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他明确地划分了天、人的界限,认为人应该控制自然,利用自然。这一论述,和西方某些思想家的观点相近,这对于人类彻底告别原始的、屈从自然的被动状态,对于认识自然,掌握规律并进一步合理地加以利用,无疑都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创造物质文明和人类福祉,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至于“天人合一”,古代各家说法又有所不同,这里主要从董仲舒论起。
董仲舒是汉代大思想家,是儒家哲学在汉代的重要代表。他力主“天人相类”式的合一说,其《春秋繁露》中的《人副天数》认为,人的三百六十骨节副合于一年的天数,五脏、四肢副合于五行、四时之数……这确实是牵强附会,但它又“猜”到了“人”对“天”不可分离的依附关系。如果揭去董仲舒连自己也说不清的神秘外衣,其本质上不自觉地含茹的“天人同构”——“人体与自然同构”之说,不能认为没有可取之处。马克思曾经科学地把自然和人体联系起来描述,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②。这是以人的身体为喻证,深刻揭示了人对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生命维系关系。当然,董仲舒牵强附会的同构合一说,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系统学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董仲舒又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相应于春夏秋冬四季(《为人者天》),其荒谬中也隐含着合理,如加以去伪存真的透视、扬弃和改造,颇契合于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文赋》),“春秋代序……情以物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等精彩的论述;至于在中国古代画论中,此类论述更多,如“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妆,冬山如睡”(恽格《瓯香馆画跋》)……此不赘引。
董仲舒在大量荒谬不经的“类比同构”思想体系基础上,一再强调了他的“天人合一”观:
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服制象》)
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循天之道》)
为人者,天也。人之(脱一“为”字)人,本于天。(《为人者天》)
身犹天也……故命与之相连也。(《人副天数》)
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离,即“附”)水,一也。(《天地阴阳》,苏舆《义证》:“人在天地之间,犹鱼在水中。”)
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天人之际(际,交会),合而为一。(《深察名号》)
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循天之道》)
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阴阳义》)
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较早出现、并最早建立在初步完整体系基础上的“天人合一”论。它的合理内核是:天地自然作为人的生存环境,它生长万物以供养人,人可以“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人是由天生成的,一刻也离不开天;人必须依靠自然,“循天之道”,“与天地同节”(《循天之道》),天人应和谐相连,合而为一,否则就会酿成灾乱……。这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谐观的提出,不管怎么说,对于人类的永续生存——可持续发展是颇有启发意义的。
当然,董仲舒的整个理论体系是荒谬的,其中还渗透着浓重的封建意识和天命色彩。但是,对其“天人合一”论决不能全盘否定,因为前人由于种种局限,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没有必要以苛求去加以彻底否定;相反,只要发现其中有合理内核,就应该加以肯定。例如黑格尔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错误也极其明显。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却肯定地指出,黑格尔著作中“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③。对于董仲舒也不妨作如是观,其“天人合一”理论纲要也有可供后人吸取和借鉴之处,虽然其体系也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可是,从上世纪对传统哲学的现代研究来看,中国哲学史上包括董仲舒在内的所有的“天人合一”观,均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连续数十年的严厉批判和全盘否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李泽厚以及刘纲纪先生才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可贵的学术识见,进行深入的挖掘、认真的梳理和出色的阐发,从而将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予以高度的评价。这主要见于如下两段文字:
“天人合一”或“天人相通”的思想在中国起源很早……孔孟也曾涉及天人关系问题,特别是孟子所谓……“君子”能“上下与天地同流”等等说法,就包含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而为后来的《中庸》进一步加以发展。……这一类的思想,近几十年在我们关于古代思想的研究中,一般都是被当作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来加以批判的。不错,这一类思想的确常常包含有唯心神秘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与自然不应该相互隔绝相互敌对,而是能够并且应该彼此互相渗透,和谐统一的……我们认为,坚信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乃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的优秀传统,并且是同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不可分离的……
在距董仲舒的时代有两千年的今天,我们认为已不必多花笔墨去嘲笑它的错误和荒谬。值得注意的反倒是董仲舒认为人的情感的变化同自然现象的变化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存在着某种“以类合之”的思想……几千年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通”,实际上是中国历代艺术家所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尽管他们不一定像董仲舒那样唯心地理解这一原则……④
这番论述不但概括了我国“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传统,而且符合于中华民族审美和艺术的历史事实,具有历史首创意义,给人深刻的多方面的启示。
再从中国思想史上看,表达过天人合一观点的,不只是董仲舒一家。在儒家学派中,除《礼记·中庸》里的“[人]可以与天地参”等以外,被西方哲学家称为“中国人一切智慧的基础”的《周易》,也是重要的一家。例如: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文言》)
与天地相依(依作“似”),故不违。(《系辞上》)
这本质上都是指出了人与天地相感相类,相依相合,而不应违反天时规律,其含义是极其深刻的,不过没有从字面上提出“天人合一”的明确纲领和建立完整思想体系而已。
在道家学派中,天人合一的观点更为突出,如: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为,是为“玄德”。(《老子·五十一章》)
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与天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庄子·大宗师》)
人与天一也。(《庄子·山木》)
人仅仅是“四大”之一,应该尊重和效法更为重要的天道自然;不应横加干涉万物的自然生长,致使其受到伤害或夭折;不占有,不自恃,不主宰,这才是深层的“道”与“德”;必须顺应四时的自然规律,人不应与自然争优胜,而应消除对立,进而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这些理论,均极有价值。《庄子》还说:“贤者伏处嵁岩之下”(《在宥》);“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这对于尔后中国的隐逸文化和崇尚自然的园林美学思想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于佛家特别是禅宗,对天人关系很少从理性上论证阐释,而是以意象感悟方式直指本心。见于语录载体的,如:
天上地下,云自水由。(《永平广录》卷十)
日移花上石,云破月来池。(《中峰语录》卷十七)
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五灯会元》卷一)
清风与明月,野老笑相亲。(《五灯会元》卷十二)
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五灯会元》卷十二)
数片白云笼古寺,一条绿水绕青山。(《普灯录》卷二)
上引第三条,与《庄子》观点略同。除此以外,基本上都是禅意盎然的“无人之境”,呈示了天地间的白云幽石、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清风明月、池泉古寺等自由清静的形象,其中隐隐然皆有佛在,可说是以佛对山水,以禅悟天地,亦即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大殊禅师语录》),而其景象又酷似园林美的境界,这正是佛家作为“像教”的一种“天人同一”观。
在中国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董仲舒有较完整体系的《春秋繁露》,以及茹含佛家智慧的零散语录……它们关于天人合一的论述虽互有异同,却构成了一条互为补充、互为深化的重要思想发展线索,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的文化史、哲学史、美学史和造园史。检点和梳理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确实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这种“坚信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乃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优秀传统”。当然,这仅仅是主要线索和传统,而并不是中国思想史的全部。
此外,和中国“天人相分”论不无负面影响一样,中国的“天人合一”论也有其负面成分,如果一味像庄子学派那样顺应自然,以至无所作为,而不去能动地利用自然,有为地进行创造,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甚至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而,《周易》就不一样,它还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辞》),这又是“泰初有为”的哲学了。
二、西方的历史反思与东方的生存智慧
从牛顿的发现和发明开始,西方历史进入了新的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中,人们凭借着科学理性和科技手段,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使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物质文明和经济繁荣,给人类生活不断带来了幸福欢乐,这首先应予高度的肯定性评价。
但是,事物发展是复杂的,它往往包含着自己可能走向的反面,或者说,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可用富于辩证意味的东方哲学著作《老子》的话来概括,是“进道若退”,或者是“福兮祸之所伏”(第四十一、五十八章)。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确实凸显出一系列“进道若退”的负面现象。从主流观念的层面上看,正如美国社会学人类学家查尔斯·哈珀在《环境与社会》一书中准确地概括的工业社会的“主导社会范式”——“自然环境被评价为是生产产品的资源;人类支配自然;而经济增长比环境保护更重要”;“剥削其他物种以满足人类需求”;“财富最大化以及为这一点值得冒风险……对科学和高技术的信念是有利可图”;“假定增长没有物理(真正的)极限;伴随资源短缺和人口增长所出现的问题,可以被人类的技术发明所克服”;“人类对自然没有严重破坏”;“强调效率……快捷的生活方式”……⑤ 这些“主题范式”作为命题,无一不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多少年来,它们不断地恶性膨胀,愈演愈烈。
极端的经济增长癖、狂妄的科技拜物教,使人们利令智昏,不懂得科学的发展观,不懂得人与自然综合协调的全面发展观,把经济的重要性和科技的优越性绝对化了,也把人的眼前利益唯一化了。这种与天人合一整体观截然对立的狭隘机械论,无视于全人类发展的宏观的、久远的利益,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如全球气候变暖,四时往往失序,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酸雨污染,垃圾泛滥,癌症患者激增,怪病流行,土地的沙漠化和盐碱化,沙尘暴频繁,水土流失,水源枯竭,农田大量减缩,森林成片减少,植被退化,动植物的种群灭绝加剧,多样性丧失,人在生物圈里愈来愈孤立,人口激增,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满足不了人们无限掠夺、永不知足的物欲……据此,美国学者里夫金、霍华德指出,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又带来了有害于人类的严重恶果:“我们的周围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无处没有的污染:从地面冒出来,在江河里渗透,在空气中滞留。它刺痛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的皮肤变色,肺功能衰退……我们陷入了泥潭,社会陷入了泥潭。”⑥ 这段描述,是对工业文明片面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进道若退”现象的真实揭露。人们的极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环境的生态结构,使其失去自组织、自调节、自恢复的生态功能,于是,自然界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统失去了平衡。人类既然迫使自然发生异化,同时也就取消了自己在自然界永续生存的前提和权利,走上了通向自我毁灭之路。U ·梅勒在《生态现象学》一文中痛切地说:“大地母亲已经躺在特护病区的病床上”!并引一位专家的控诉:“人已经失去了预见和预防的能力,他将毁灭在他自己对地球的毁灭之中”!⑦ 真可谓祸莫大焉,惨莫重焉!
正因为如此,如何认识、制止和逐步消除这类全球性的公害,如何使人类不再自食恶果,不再玩火自焚,这是严峻地摆在全人类面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
(未完待续)
注释:
① 这是金学智教授《中国园林美学》(增订新版)前言的一部分,该书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题目和文字均有所改动。
② 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第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
④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484—486、489页。
⑤ 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第60—61页。
⑥ 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1—2页。
⑦ U·梅勒,《生态现象学》,载《世界哲学》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