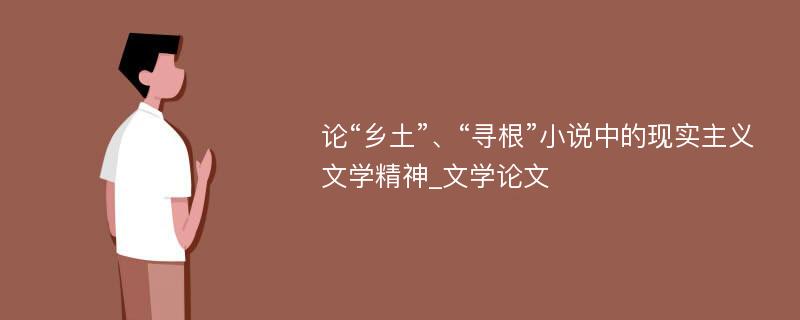
论“乡土”与“寻根”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乡土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飞扬与流动”的视景下,对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与80年代的“寻根小说”进行了互为参照的比较分析,在较为宏阔的文化背景上,对这两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文学现象,作出了某些新的开掘与阐释。
王喜绒:女,文学硕士,兰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从表面看,无论20年代的“乡土小说”,还是80年代的“寻根小说”,作者注目的大都是时代潮流冲击圈外的生活,这就与从火热时代斗争氛围中取材的作品,在现实主义精神上拉开了距离。然而透过选材的表象看本质,这两类小说却正是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飞扬与流动”的视景中,既凸现了各自的流派特色,又对当时的文坛做出了某些有力的拓展与刷新。本文正是从这里切入,试图通过互为参照的比较分析,在较为宏阔的文化背景上,对此作出一些新的阐释与开掘。
一
从文学与时代和现实人生的关系上讲,无论“乡土小说”还是“寻根小说”,都是一代作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积极拓展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的结果,而这一点正是衡量现实主义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以“乡土小说”论,在它涌现之前,文学创作要为人生,并要改良这人生的旗帜,虽也高扬在了新文坛上,众多作家通过创作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但就总趋向看,这人生在诸多作家的作品中,还只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子,要么囿于抽象人生问题的讨论,要么局于学校生活和青年男女的恋爱问题。再加上“自我小说”、“身边小说”盛行,更使不少创作沦于咀嚼个人小小悲欢,而且就看这悲欢为大世界的倾向,真正触及农村题材的只占极少数。这种人生面的狭窄,不仅直接影响着作者看取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文学为人生的效果与质量。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始终占大多数。如果农民生活得不到充分反映,那文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的联系,就只能浮在表层。而且,对当时极待变革的中国来说,农民的觉悟与否还直接关乎着革命的成败与祖国的前途,辛亥革命的失败早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20年代中期已由城市逐渐扩展到乡村,由知识分子圈子扩展到了农民中后,文学创作对农村生活的反映与干预,就愈加现实和急迫。在此种情势下,乡土作家把关注目光转向农民,就不仅使新文学更加贴近此一时期的中国现实土壤,与现实生活的联结更加深广;而且就作家言,从一味关注个性解放到关注人民大众的解放,从浪漫的讴歌理想转向更现实的探索,无疑也意味着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深化。以“寻根小说”论,诸多作品展示的艺术世界,诚然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因为探索和思考意向乃至范围,确实更多地联系到了民族的过去。但正如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关心历史总要带着自己的介入,绝不会超时空地与历史接触。寻根作家把笔触伸向远古年代,伸向更深层的文化思想之中,其动力也正来自他所处的时代:一方面,80年代的中国正向现代化迈进,可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华民族承袭来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素质,却往往缺少为其催生助产的力量和激情。于是,如何越过衰老的病态文明,从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重新找到民族腾飞急需的精神动力,就成了时代赋予作家的崭新课题。“寻根”作家们正是在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入探索中,由政治的批判、经济的思考,推及文化上的俯视,从而也就获得了一种新的洞观人生的方式与批判角度。这就正如韩少功在谈及“寻根文学”的倡导动机时所说的:“这是改革由治标到治本的过程,文学需要促进民族的文化启蒙和文化积累”,“文学家对浅薄政治的疏远,正是从更深层关心现实的一种成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当人们从自我封闭中走出,反叛传统,纷纷探首国外——特别是从西方世界取现代化之经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不少西方学人中正在兴起的东方文化热。①这就促使他们回过头来,对民族文化给以尊崇与反思。而在我国,“五四”以来坚决彻底的反传统,特别是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又使50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两代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民族文化层断裂的切肤之痛。于是,追求民族文化之根,以便赓续民族文化、反思民族文化,就成了寻根作家们所能做出的最佳选择。因为昨天的不仅对昨天才有意义,而且对今天乃至明天仍有意义。不仅人类的历史是持续的、绵延的,人类的精神状态也是继承的、积淀的。所以,寻根作品貌似跳开了与眼前政治经济变革的胶着状态。实际上却是从更深层干预着现实。比如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虽然着力塑造的是一系列“最后一个”的形象,可由于作者始终怀着一个当代目的,即试图在过往的旧人旧事与今天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读者视线得以延伸,这就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拓展。
其次,从文学背景上说,“乡土”与“寻根”小说既是各自文坛上有背于现实主义的某些文学发展趋向的反动,也是现实主义内在发展需要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文学现象,这就使它们自然而然地要在现实主义的主航道上乘风破浪。以“乡土小说”论,它之前以文研会为代表的“为人生派”的创作,虽然高揭起了现实主义旗帜,但不少作品却存在着主观性与理论性过强的弱点,往往热衷于从某一观念出发,去寻找可以体现其既定观念的生活材料。纵使大获成功,也常常不是靠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把握与如实描绘,而是由于敏锐地提出了为全社会成员深切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主题先行”,篇篇小说竞在提出热点问题,就使概念化的毛病也随之突现。纵使文研会的一些骨干作家,创作也往往表现出“二重性”:当着重表现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时,便带有注重个性、注重表现一己主观情感的主情色彩,有的还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而当作品重在揭示人生丑恶时,又采用客观描写手法,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现实主义的发展,使当时众多名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实际上并未形成完整的现实主义。再加上浪漫主义色彩浓烈的“自我小说”、“身边小说”的风行,就更从手法上对现实主义的创作,形成了有力挑战。“寻根”小说崛起之前的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与冷落。随着横向借鉴的逐步深入,种种逆现实主义而动的思潮与艺术手法应运而生。有的人甚至完全照搬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一味排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鄙薄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主张“面向自我,背对现实”,强调时代精神的淡化,致使一时间玄妙的“空灵感”被当作文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对现实的“超脱把握”被视为作家“精神自由”的最高体现。就连过去一直遭人垢病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被某些理论家加以肯定。但是,“乡土”和“寻根”小说却以自己的独特努力,直接推进了各自文坛上的现实主义发展。以“乡土小说”言,作品就大都是从感受最深、不免时时“撞击心头”②的生活回顾中提取素材的。由于写作动机并非急于提出问题,而是在浓烈的乡思驱使下重新咀嚼和再现故乡生活,因而作品不仅以真实生动的乡土生活画面,成功地“跨过了学校生活和恋爱关系这狭小而用滥了的范围”③,为新文学开拓出了一个极富审美价值的题材领域;而且一扫前期面壁虚构的概念化毛病,首先在坚持创作从生活出发、如实反映生活这一点上,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既比初期“问题小说”的作者观察生活的视野视开阔得多,又较当时方兴未艾的创造社抒情小说抒发的情感更为切实。“寻根小说”虽然往往不是此时此地真情实景的真切再现,而是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有机融合。但由于作家每每都是“用写最具体的来表现最抽象的”④,特别是把创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和地区文化中,重在写出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历史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素质,这就使创作既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又把对人的审美观照由传统的单一政治视角转向综合的文化视角,这对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促使人物形象塑造由传统的“扁平”向“园形”转变,自然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可以说这简直是我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上的一场革命,它的开拓意义和重要性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将会日甚一日地表现出来。
然而同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思潮,由于产生的社会背景同中有异,这就使二者在现实主义的层次上又有明显差别:“乡土小说”侧重单纯再现作者的感情真实与印象真实;“寻根小说”在大多数作家那里却往往呈现出“写意现实主义”的风貌。由于前者几乎全是身居闹市的“流寓者”思乡的产物,笔触所向尽是从小生活其中、格外熟悉现在又格外怀恋的故乡热土中的生活画面,所以不仅真切生动,就连流贯其中的情绪色彩,也全是作者彼时彼地的真情实感,没有丝毫矫饰与造作。与“寻根小说”比,也许大部分在内涵与手法上都显出了“浅”,然而却浅而清,以一清见底的真切同样获得了打动人心的魅力。而“寻根小说”一方面如王安忆所说:“我写的东西全都有真实故事的,即使是听来的,也要与自己的生活进行碰撞的”;⑤另一方面,又要用写最具体的来表现最抽象的,自觉地在源远流长的深层文化结构中对待今天的创作,希望寻求到现实关系中深层或潜在的文化意识。这就使创作既充溢着当代性的沉雄博大的当代小说美学风貌,有了深邃的历史纵深感——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明显不同于乡土作品所追求的一个个个体的感觉特征,而是对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中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深刻表述。莫言的《红高梁》也是顺着祖辈血脉寻根究源,迫近了民族精神的底蕴;又因理性目光的强烈渗透和过分张扬的哲学思辩色彩,直接影响了读者层的接受与理解,每每显露出了创作主体蓄意“玩深沉”的痕迹,导致本为关注现实的作品,却常常难与一般人民群众的审美情感相通。
另外,在创作主体的感情渗透上也有明显差异。“乡土小说”握一把苍凉,弥漫着“隐现着乡愁的伤感故乡风”。⑥这是因为从客体方面讲,20年代的中国农村衰败残破,劳动人民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现实进入一代对故乡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视野中,激起的自然是惆怅、感伤,甚至是凄凉的情绪反映;从主观方面讲,乡土作家群不佳的心境状态与获得的时代最新觉悟,也在无形中大大强化了这种美学风格:一方面如鲁迅所述,他们都是被生活驱逐到异地的“侨寓者”,或者为“五四”新思潮激励,或同时为农村的破败所迫,从家乡流落到北京等大城市。然而身居闹市后,却饱受磨难。乡土文化的厚重积淀既使他们难以迅速认同城市文化,城市文化也很难迅速接纳他们。再加上“五四”落潮所带来的巨大思想冲击波,都使他们心里无不充溢着彷徨、凄楚,甚至是悲凉。用这样一种心绪过滤可爱故乡的种种令人心碎处,就更冲荡着凄楚的心,使其更加悲凄不已;另一方面,身居城市文化中心后,耳濡目染所接受的时代最新觉悟又使他们重新看取故乡生活时,不能不更深地感受到那里的无边黑暗。于是“古老的悲哀与崭新的忧虑”,就共同铸就了作品的伤感审美情调。但是,“寻根小说”却少有这种风格特点,它的一个鲜明美学追求就是生命意识的激扬。尽管寻根者的具体目标与方法不尽相同,但其主流却是有意识地从自然律动中,去寻找民族血统中曾有过可后来却被封建文明驯顺退化的健壮生机与自由精神——也就是“被封建文明阉割了的生命之根”,⑦以便重新激扬起民族的青春活力,构建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型文化。比如著名的《红高梁》系列中,莫言对人生世界的把握与再现,就是从生命的角度切入的。作者通过着意表现高密东北乡那块黑色土地上繁衍着的生灵尚未泯灭的生命本性,象红高梁一样高拔健迈、象高梁酒一样浓烈酣畅的生命性格,呼唤着民族生命意志力量的勃然释放。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也是通过由生命的意志和生命的规律主宰着的那个原始而神秘、野蛮而自由的独特世界的再现,张扬在文明社会的秩序规范下所失却的生命精神。寻根作品对人的生命现实存在和生命本性本能的专注,不仅使改革大潮中民族振兴渴望力和胆、历史蜕变渴望动力打破僵死规范的时代情绪,在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文化上的寻根走向生命之根,也使文学创作成功地避免了狭隘的政治角度,强化了多角度把握生活的自觉意识,这对促进现实主义创作向纵深发展,自然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二
从现实表层的揭剥转向深层的钻探,从政治层面的激情批判进到文化层面的冷静审视,这既是两个十年中文学观念一次突破性进展,也是“乡土”与“寻根”小说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飞扬与深化的又一突出表露,它所体现的正是我们民族要求变革自身的时代精神与激情。
20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风情特异的选材,在现代意识辉映下,实实在在展示我国农村长期停滞造成的落后、贫困、沉闷,以及封建文化陶铸下的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和冷漠,对乡村古老的群体生存方式——既包括生态,也包括心态,作出深刻的剖析与批判。那些表现点缀着冷酷、野蛮习俗的作品,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比如《菊英的出嫁》(王鲁彦)表现的浙东乡间的“冥婚”风俗,《烛焰》(台静农)描写的“冲喜”、《惨雾》(许杰)中的村落间“械斗”《河鬼》(彭家煌)中的“小女婿”现象、《红灯》(台静农)中的“鬼节”放河灯安慰死者、《赌徒吉顺》(许杰)中的“典妻”、《水葬》(蹇先艾)中的将小偷沉入水中等。作者满怀痛苦与愤懑,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了这些习俗中或冷酷、野蛮的一面;或原始、迷信的一面,并透过这种种世道习俗,对落后的社会心理进行发掘。其中最让作者痛心的是这样一种悚目惊心的现象:自觉维护并把这些野蛮吃人习俗坚决付之实践的,往往既不是统治阶级,也不是某种政治力量,而是并非坏人的民众自己,是他们在用自己的手给亲朋和乡邻制造着灾难。这样,作者便通过落后习俗的描写,把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提到了人们面前。20年代的鲁迅更是这方面的旗手和典范,他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鲜明态度,率先在《呐喊》和《彷徨》中为读者勾勒出了落后而又不觉悟的旧中国农民典型形象系列:阿Q、闰土、祥林嫂、爱姑……,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灵魂麻木的社会原因,给后来的作家以久远的影响。可以说,中期的乡土作家在揭示落后的国民性方面,正是继承了鲁迅之风,只不过远未达到那样的忧愤深广罢了。
“寻根小说”虽然没有集中渲染种种落后、野蛮的民间习俗,但诸多作品同样渗透着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体验及观察角度。作家们或把艺术审美视角转向过去的年代,通过着意表现具有蛮荒色彩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对落后、贫困、愚昧的人生环境及其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氛围做出否定性的价值判断;或直接深入到种种文化积淀之中,通过审视被生活表象掩盖着,但又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态的那种更深层的东西,揭露国民心理的病态,批判诸种曾经发生过而现今还尚未绝迹的生存状态及社会文化现实。比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神鞭》等,就把锋利的解剖刀伸向了传统的带有封闭型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出这种心理场中的历史惰性。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则深入民情风俗、世态人情、伦理传统等文化积淀中,揭露国民心理的畸形与病态。即使对传统文化表示认同的诸多寻根作品,认同的目的也仍在于批判精神的张扬,因为认同本身就蕴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某种不满和对社会变革及重建中国新文化的热切渴望。而且就总体上把握“寻根小说”试图把人重新归入远古的自然文化序列,以解决文明的精致与自然的粗粝这日益剧烈的冲突,及冲突所导致的现代人的心态危机,其本身就使“寻根小说”关于改造国民性的呐喊,较之“乡土小说”要响亮得多。“乡土”与“寻根”小说断然走入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集中开掘、展示被传统文化培育出的这个世界中的沉重色彩,就在有意无意中把两个十年里人们格外关注的“人”的主题与文化的主题,深深地叠合在了一起——因为是人创造了文化,可反过来,又是文化把人塑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人的活动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直接制约之外,又更直接、深刻地受着特定文化规范的困扰和制约。于是,这一开掘不仅在文艺的对象问题上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思考领域,也使小说表现世界的范围与层次顿然扩大和加深。
不过,寻根作家虽然接上了乡土作家曾经执着过的文化命题,但又绝非其创作心路的简单重复,在有所承继的同时,又作出了属于自己时代的独特开掘。与“寻根小说”比,乡土作家适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统治不仅导致了广大农村的蒙敝与落后,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长期箝制,也导致了他们精神上的普遍麻木。再加上创作主体在“五四”落潮期的苦闷彷徨,这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共同导致了他们所写的乡土小说,从主题所向上讲,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因而改造国民性的意蕴,都是通过揭示乡村文化中的负面价值,特别是通过暴露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荷和性格弱点来突现的。然而“寻根小说”在回溯文化源流、文化传统时,却既有批判,又在这种富有批判精神的否定中,透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某种认同。可以说,诸多寻根作家正是立足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筛选、继承和发展,才将文学的思考上升到现代哲学对人的本体思考的范畴,从而通过这种认同,意欲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比如着眼于原始生命力的开掘与赞美的寻根作品——象《异乡异闻》系列、《远村》(郑义)和《老井》等,就是在充满原始情调的氛围中,于溶化在生活的原始形态的文化现象中,以一种现代意识,充分发掘农民心灵中带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财富。莫言、韩少功的不少小说也是通过对蕴含着民族蓬勃活力的蛮野自由的乡风民俗的大力讴歌,从中找寻既是传统的又属于现代文化心理的成份。着眼于民族优秀传统再发现的寻根作品——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通过展示秦汉文化的独特丰彩,努力开掘农民身上蕴藏的虽然极其古老、传统,但却可在现代社会中发扬光大的文化心理、品格,写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民族古老精神人格的创造性转化,使传统农民的传统品格——特别是女性的传统品格,在现代性的再发现中重放光华。正由于此,“寻根小说”虽与“乡土小说”一样,重在表现生命的某种存在状态,重在用现代意识的理性之光观照中国的传统人生,但“乡土小说”呈现的往往只是理性之光烛照下的一个个急待改造的古老灵魂和一片片急待注入现代文明和风的乡土。而众多“寻根小说”却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传统生活,从而使传统因为作者思考的现代化而赋予了现代价值,每每放射着与现代理想人格相通的光辉。这就使它在对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念的探索上,对风土民情的描写上,不仅比过去的“乡土小说”更富历史感和时代感,也使改造国民性的努力更趋现实和合理,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往往会出现的偏颇。
三
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飞扬与流动”的视景中,“乡土”与“寻根”小说呈现出的第三个颇为相似的层面,就是描写氛围大都有着鲜明而厚实的地域生活特色。这不仅包括该地区独有的山川名胜、语言系统、风俗习惯,还包括民族精神文化特征。表现在“乡土小说”中,作家的审美视野大都集中在熟悉的某一地方的生活现实:蹇先艾描述着闭塞的贵州,许钦文注目于古老而又沉闷的江南水乡,许杰再现的是民风强悍的原始性山区……。而在这些独特地域生活的描写中,作者都把地方风物和风俗画的描绘,放在了十分醒目的位置,它对烘托、渲染地方色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许杰的《惨雾》关于环溪村和玉湖庆的描写,就鲜明映出了一派江南的绮丽风光。许钦文的《疯妇》通过双喜妻子的褙锡箔,也生动地勾勒出了一副绍兴特有的风俗画面。彭家煌的《怂恿》等,则用颇具地方色彩的民风民俗和人物带着乡音的土话,点染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鲁迅的《故乡》、《社戏》、《风波》等,更是将风景画和社会生活的风俗画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既突现了江南水乡特色,又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表现在“寻根小说”中,作家们也是通过表现各种序列的文化所独有的文明特征,有意识地强化着作品的地域特色。比如首先提出文学寻根问题的韩少功,就带着“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疑问,终于“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族所分布的重山峻岭里”找到了它的流向。⑧阿城的创作则通过北国边陲雄浑、苍劲的地理风光、山川景物及民情民俗的勾勒,将一种只属于该地域的特有风情色彩、氛围和情调,深深地烙印进作品中,从而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北国风情画。其它象商州系列中的秦汉文化色彩、葛川江系列中的吴越文化气韵,以及“西部文学”、“岭南文学”等等,都以各具特色的文化渊源和色彩,显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特色的呈现,不仅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乡土”与“寻根”小说不同于其它流派创作的独特的色调和艺术氛围,使“任何时间跨度内的事物都不同程度地蒙上空间区域的色彩,被空间的特征同化了,淹没了”⑨;而且也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各自文坛上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准。以“乡土小说”言,就构成了对20年代初期“问题小说”的明显超越。在执着现实方面,“问题小说”虽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完全相通,但由于一般置于描写中心位置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人物和场景,这就使作品往往只能给读者提供一个颇为粗略的故事梗概,缺乏使人仿佛置身其中的真实环境和场景,缺少现实主义创作所要求的细节的真实性,导致“问题小说”在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相通的同时,又从手法上每每对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冲击。“乡土小说”尽管除鲁迅等大家外,还极少有人能在作品中塑造出非常典型的人物形象,但对地域特色的突出,却使创作明显有了典型环境的构设与具体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作家们通过细腻刻画某一地区独有的山川风貌和世俗民情,就为农村生活的描写与人物塑造提供了真实的环境氛围,使乡土气息得到了进一步醇化。再加上作为地域特色的重要成份——地方化语言的运用,也克服了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学生腔”与欧化倾向,使作品的艺术真实性大为增强。正是在这些方方面面,“乡土小说”建树了它独特的流派品格,提高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水准。以“寻根小说”言,通过展示各种地理文化所独有的文明特征而突现的地域特色,就有力地矫拨了当代文学中典型环境的再现,往往只传注于政治氛围的变迁,而忽视相对恒定的整个文化氛围描述的缺陷,这不仅为人物的塑造提供了一个更加接近生活原生态,因而也更真实的典型环境,极有利于作者从各方面去刻画人物的丰满性格,立体地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而且文化意识、文化眼光的渗透,也有力地消解了自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以来,小说中的政治内容便越来越压倒一切,广泛的文化内容日益被排斥在小说视野之外,以致小说作品常常沦为某些政治概念、政策和路线的单纯图解物的偏颇。这种创作上的突破对于推进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度与广度,无疑意义深远。
此外,“乡土”与“寻根”小说中厚重的地域特色,又使他们同时具有了比较浓郁的民族特色,这对两个十年初期创作中一度出现的“西化”倾向,无不起到了有力的矫拨作用,而这种矫拨,既对促进小说创作回到民族化的道路上来极具意义,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因为这里的浓郁的民族特色,也就意味着作品中描写的自然之真,而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又是现实主义艺术最基本的原则。以“乡土小说”论,将创作植根于故乡的文化土壤上,力图展示古老中国农村的某一生活形态,既使“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创作较好地克服了一味“拿来”与借鉴所导致的欧化倾向,为新文学向民族化迈进创开了一条新路;同时,对地方色彩、地域特色的着意浓化和展现,又使作品因为一个个生动、真实的物像,大大加浓了现实主义的成份和艺术容量。以“寻根小说”论,作家们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地区文化之中,用东方的感知方式来把握世界与人生,既以内容上的地地道道的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对促进新时期的创作战胜盲目西化的倾向,重新回到民族化的道路上来产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也有效地遏制了因为西方现化派的长驱直入而引发的淡化现实,淡化背景的淡化趋向,大大强化了文学创作与中国现实人生的密切沟连。
注释:
①详见张炯:《新时期文学格局》,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版。
②蹇先艾:《关于我的短篇小说》。
③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导言》。
④⑤《关于<小鲍庄>的对话——陈林致王安忆》,《上海文学》,1985年第9期。
⑥详见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3月版。
⑦见张德祥:《悖论与代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⑧参阅韩少功:《文学的“根”》。
⑨见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0月版。
标签:文学论文; 乡土论文; 乡土小说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寻根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