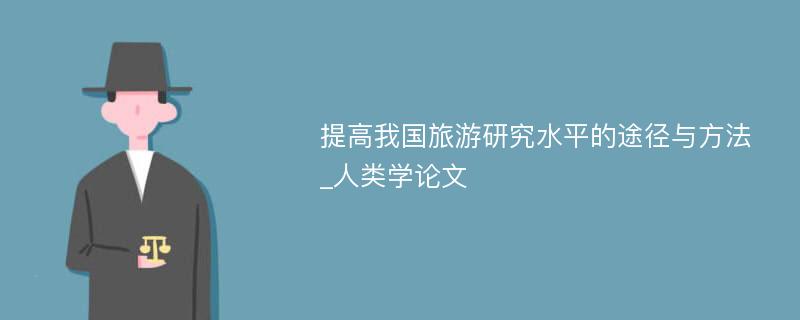
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水平的途径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途径论文,水平论文,旅游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旅游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在旅游学界各位同仁及其他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现代旅游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表现为旅游研究方法由相对单一到趋于相对丰富和复杂、研究领域由相对狭窄到日趋广泛、研究队伍由相对弱小到日益壮大、学科交叉现象愈益明显、理论和应用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等。然而,与国外旅游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现代旅游学研究还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旅游研究方法论体系尚未建立,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相对滞后,这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旅游学研究发展的步伐。基于此,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实际,分析了目前中国旅游学在方法、理论及边缘学科方面与国外比较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缩小差距的对策,旨在抛砖引玉,唤起人们对旅游学方法、理论及边缘学科研究的重视与兴趣,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水平。
一、深化旅游学方法研究,构建旅游学方法论体系
方法和方法论是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因素,是学术研究的先导,因为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问题都需要凭借具体的方法去解决,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去指导。伴随着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研究必须加强学科的整合。所谓的整合就是站在学科交叉的地方,利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探索研究[1]。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愈来愈大、重要性日渐突出、研究深度日益加强、旅游学科的复杂性、边缘化现象愈来愈明显的大背景下,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深化旅游学方法研究,构建旅游学方法论体系,对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旅游学方法研究相对落后的现状,决定了中国旅游学研究必须深化旅游学方法研究,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
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北京大学地理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陈传康和郭来喜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在对旅游进行研究时就已经涉及了旅游研究方法,如介绍与描述法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旅游研究方法也随着旅游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科交叉愈益明显、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而丰富发展起来。据有关学者对发表在《旅游学刊》、《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和《自然资源学报》等刊物上的旅游论文所用研究方法的统计,目前国内学者从事旅游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已涉及到描述性方法、概念性方法、构造模型法、数理统计法、传统定性方法、现代定性方法、基础统计分析、复杂统计分析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2]。
客观地说,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内旅游研究方法渐趋复杂和多元化,但国内旅游学方法研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吴必虎、党宁、程占红等一批北大旅游学者,为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体系作了不懈努力(如2005年底由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范中心牵头举办了“旅游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并编辑了《旅游学研究方法与模型》一书,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旅游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但迄今为止,有关旅游研究方法论、旅游研究方式、旅游研究具体方法与技术的科研成果却相当少;中国的旅游研究方法有趋向于逐步定量化的趋势,但是幅度不大,许多研究仍停留在定性分析的水平;中国旅游研究的技术水平和手段还很有限,在资料的来源上,通过问卷、观察、访谈获取的资料并不多,实验资料几乎没有;甚至在为数不多的“旅游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上,人们还会听到“旅游研究是采用定性方法好还是采用定量方法好”、“以单纯的旅游学方法还是综合其他相关学科方法来构建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之争论。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内学者对旅游学方法之研究还不够。
深化旅游学方法研究,关键在于构建旅游学方法论体系,因为方法体系的完备性体现了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一般说来,旅游研究方法论体系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即方法论(指导旅游研究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研究原则、研究逻辑等)、研究方式(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也称研究法)、具体方法与技术(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方法、工具和手段)。
在国外,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其标志有二。一是涌现出了一系列关于旅游研究方法的专著和论著。国外现代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初始阶段,大多数研究工作还属于概念性和描述性的范畴,旅游研究的方法也比较简单。20世纪60、70年代,旅游研究逐步走上学术规范的道路,其标志是1974年《旅游研究纪事》的正式创办。20世纪80、90年代是旅游研究的方法问题普遍受到重视的时代,由此涌现出了一系列关于旅游研究方法的专著和论著,如80年代有《旅游现象现场调查的方法》、《旅游分析手册》等2部旅游研究方法论的专著出版;此外还有一本非常实用的旅游研究分析方法汇编《旅行、旅游与接待业研究——管理和研究手册》问世;90年代除了有一本系统介绍旅游定性研究方法的专著《休闲与旅游研究方法——实用指南》出版外,还有一本涉及旅游研究方法的论著《投入—产出分析的研究方法》问世。二是《旅游研究纪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刊出了旅游研究方法的专辑,在撰稿和编辑上采用了一些新的原则和方法。可见,在国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且呈日臻完善的势头。
反观中国旅游学方法研究,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国,虽然《旅游学刊》、《思想战线》等刊物,也曾经刊载过一些有关旅游研究方法的文章,但此类文章大多停留在介绍国外旅游学研究方法这一层面上,如《旅游人类学再认识》一文中,以“关于人类学的方法论体系”为题,介绍了西方旅游人类学家经常借用的“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3];又如《西方旅游人类学与中国旅游文化研究》一文探讨了“西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理路”[4];《文化人类学研究与旅游规划》则在论述“文化人类学在旅游规划工作中的应用”时,介绍了西方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田园调查、整体论方法、主位研究法、比较法等,并强调了人类学方法对旅游规划的借鉴意义[5];《西方事件与事件旅游研究的方法》介绍了西方人在研究事件旅游时的视角与方法[6]。刘迎华、朱竑以“从《旅游学刊》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比较看中外旅游研究的异同和趋向”为题,对2000年以来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学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揭示中外旅游研究方法的差异之基础上,介绍了国外数理统计等多种研究方法。在著作方面,情况也大致如此,主要以翻译、介绍国外旅游学研究方法为主,如南开大学旅游学系翻译出版了斯密斯的《旅游决策与分析方法》,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国外旅游学分析研究方法[7],但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本系统探讨旅游研究方法的专著问世。为满足日益发展的旅游教育需要,旅游教育出版社曾于2001年推出了《旅游应用文写作》一书,该书虽然涉及一些具体的旅游研究方法与技术,但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性质上都与旅游研究方法论著相差甚远[8]1-239。《旅游学研究方法与模型》一书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旅游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但严格地说,该书只是重点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旅游研究方法,并未对如何构建中国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作深入地探讨,且迄今未见该书正式出版。
基于此,对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各个要素进行系统研究非常必要。
首先,要对旅游方法论进行系统研究。旅游研究的方法问题,首先是与方法论有关的哲学问题,即如何用一个科学的观点来认识旅游现象和旅游学科的问题。最初研究者是用经济学的眼光来审视旅游,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种误区表现出许多问题。旅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旅游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旅游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旅游研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能完成的,而是由不同学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多学科研究。因此,旅游研究提倡跨学科、多层面的研究风格。
其次,要对旅游研究方式如描述性、解释性、探索性、横剖研究、纵贯研究、实地研究、实验研究、比较研究等进行系统探讨。
最后,要对具体的方法与技术,尤其是新方法与技术进行系统研究,如定量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回转半径法以及新技术如网络技术等。
只有对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各个要素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和出版堪称旅游研究方法经典的专著,才能深化旅游学方法研究,构建旅游学方法论体系,从而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水平。
二、深化旅游学理论研究,构建旅游学理论框架
如果说方法是学术研究的先导,那么理论则是反映学术研究水平的一面镜子,因为理论是一门学科的基础,只有把理论的基石夯实打牢,旅游学这座独特的综合型学科大厦才能建成。
中国旅游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比,其发展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旅游研究的初创阶段,由于从事旅游学研究的人不少是政府官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旅游经济学、旅游资源开发等领域,加之过多地强调旅游能带来诸多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少部分探讨旅游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之外,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围绕旅游业的发展,即旅游应用层面的问题展开的。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旅游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旅游业迅速从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变,被界定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但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由于人们把旅游发展的目光主要集中于地方旅游的开发与管理上,加之功利因素的作用,使得旅游研究仍带有很强的应用性,大量研究成果都集中在对旅游现象的经济层面之探讨或者从管理的视角进行规范性研究,因而旅游学理论研究成果仍然很少。有关学者对《旅游学刊》从1990到1999年10年间的文献所作的综述分析表明,在总共1026篇文献中,除了极少数文献可以划归到旅游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外,多数都属于旅游应用性文献[9]。吴必虎等对《旅游学刊》从1986到1999年14年来所发表的文献(共计1435篇)的分类统计,也证实了这一点,涉及旅游应用性的文献为810篇[10]。这种研究领域上的严重倾斜,虽然是中国旅游研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适应产业发展实践的迫切要求而做出的必然选择,但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旅游研究向纵深发展,此种状况直到9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随着旅游业向纵深层次的发展,旅游应用研究因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指导而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态势,因而90年代末国内旅游学界开始了加强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对旅游地发展、旅游规划、旅游形象、旅游文化、旅游影响、主题公园、生态旅游等人们较为关注的热门课题中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11],并取得了较多的理论成果。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旅游学理论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国内旅游经济学、旅游行业管理学、旅游文化与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环境学等旅游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还处在形成之中,有待人们深入探讨,因此,国内旅游学总体理论框架尚未建立。以旅游人类学理论研究为例,西方旅游人类学研究理论框架已经形成,且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如对旅游人类学的重要内容——旅游文化的研究,西方旅游人类学家不仅对它作了界定(认为人们为迎合游客而制作发明或改变文化及其内涵,这一过程就叫旅游文化),而且还对旅游文化制作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化真实性、文化涵化、文化商品化、文化传统的再创造和再发明、文化变异性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而在国内,虽然有人对“旅游文化”这一概念作过探讨[12]10-11,但对与此相关的理论却研究得不够。
二是基础理论研究还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面上,有的甚至还未涉猎。如对旅游人类学中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民族旅游这一概念,在西方就有多个旅游人类学家作过界定。国际著名的旅游人类学研究家柯恩将民族旅游定义为:“针对在政治上、社会上不完全属于该国主体民族的人群,由于他们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特征或独特性的旅游价值,而进行的一系列观光旅游。”布鲁诺认为,民族旅游涉及这种情形:“国外或国内的旅游者通过旅游可以观察其他群体,而这些群体不仅被认为有明显的自我认同、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且他们通常被贴上诸如种族、国家、少数民族、原始、部落、民俗或农民的标签。”史密斯则指出:“民族旅游主要是以奇异的风土人情来吸引游客。”[13]36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旅游人类学家并未停留在对“民族旅游”概念的界定上,他们还对因民族旅游而引发的“旅游民族”的身份重塑、族群认同意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与此概念相关的“民族志旅游”作了深入的探讨。而在国内,虽有文章涉及此概念,但仍停留在引进介绍这一层面[14],尚未见文章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又如对商务旅游理论之研究,英国人约翰·斯瓦布鲁克与苏珊·霍纳在《商务旅游》一书中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商务旅游的定义、历史发展进程、需求与供给、宏观环境、商务旅游对经济、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物质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产品营销、开发与管理等商务旅游理论各个方面[15]1-267,而在中国,由于迄今为止尚无系统探讨商务旅游理论的论文与专著问世,因而不少商务旅游理论问题仍无人探讨。
可见,中国旅游学理论研究与国外相比已经严重滞后,因此,加强与深化旅游学理论研究,构建中国旅游学理论框架,在当前显得至关重要。
一是深化基本概念的研究。自旅游学研究兴起以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对旅游学的基本概念进行过探讨,但总体看还不够,这不仅表现在不少旅游学概念如旅游文化、文化旅游、商务旅游、会展旅游、游憩等尚无统一的定论,往往给人以模糊不清之感,还表现在有的旅游学概念如旅游社会学、旅游环境学尚无人涉猎,有待人们深入探讨。
二是加强旅游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近几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虽然对旅游学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旅游系统理论、旅游供需平衡理论等进行过探讨,但这种探讨大多停留在介绍的层面上,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加强旅游学重大理论的系统研究,以缩小与国外理论研究的差距。
三是加强旅游学理论模型研究。随着旅游科学的发展,大量数理定量分析模型已经运用到了旅游学研究之中,它包括了数学、经济学、地理学、系统理论、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心理学多学科的内容。对于这些对旅游科学研究有较高应用价值的数理模型,如人工神经网络、面板数据模型、需求系统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受限回归模型、PLS回归模型、结构方程模型、计数模型等,应该在大力引进国外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三、拓展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
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旅游的实际水平之高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旅游和非旅游专业的学者对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表现出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与热忱,在各学科研究人员的广泛参与下,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之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涌现出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大大拓宽与深化了旅游学研究。中国则不然,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旅游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旅游研究逐步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跨领域的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现象也已初露端倪,但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以遗产学与旅游学交叉学科——遗产旅游的研究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批世界遗产公布后,遗产旅游(heritage tourism)作为一种新的具有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双重特性的旅游产品,就被西方国家加以培育和营销。20世纪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出现及其盛行,推动了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化趋向,由此激起了人们对文化遗产及其所承载的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强烈兴趣及实际的旅游行动。以文物古迹资源作为主要旅游吸引物的文化遗产旅游因此在西方世界流行开来,并成为推动世界旅游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遗产旅游逐渐成为西方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并出现了《旅游者和国家财产:保护澳洲遗产措施》、《新西兰和澳洲的遗产管理》、《不协调的遗产:冲突中作为一种资源的旧式管理》、《遗产专题讨论:遗产解说的社会表现》、《遗产地附近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等有关遗产旅游的著作、论文集和研究报告;另外据统计,1987~2003年,国外共有38篇遗产旅游研究文章发表。
这些研究成果内容广泛,涉及遗产旅游的定义[16]、遗产旅游个案研究[17]、遗产旅游者的行为和体验研究[18]、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19]、遗产旅游管理研究[20]、遗产旅游消费研究[21]、遗产旅游价值研究[22]、遗产旅游影响研究[23]、遗产旅游的解说研究[24]、遗产和后现代旅游的关系研究[25]、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26]等各个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旅游研究纪事》还给予了遗产旅游研究以特殊的关注,在第二季刊中刊发了“遗产旅游特别专题”。自1992年2月17~22日在埃及召开了“旅游、遗产和环境”国际遗产旅游研究专题讨论会以来,国外多次召开国际遗产旅游研究会议,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近十次之多。这些高层次的会议,既有遗产旅游实践工作的交流,也有遗产旅游理论学术问题的研讨。可见,国外的遗产旅游研究伴随着遗产旅游的兴起与发展,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研究迅速细分化,科研成果数量快速增长,无论是具体案例的分析,还是基础理论的探讨,都已有相当的深度,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局面,目前正朝着世界遗产旅游地针对性研究方向发展,使研究能够直接指导遗产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遗产旅游研究则不然,在研究成果的数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还相差甚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国内有关世界遗产的文章不时见诸于杂志和报端,但专门论述世界遗产旅游的论文和著作不多,从1987至1988年,国内发表的有关遗产旅游的论文年均只有1.5篇左右,有趣的是,1988年以后,此类论文越来越少,且这些研究成果大都局限于具体地方的个案情况,或者仅就遗产保护与开发体系的子因素进行阐述,对整个世界遗产旅游体系进行综合审视的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较为鲜见。同时,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指导上具有明显的地域局限性。近几年来,有关世界遗产的著作在国内虽然时有出版,但从内容上看,这些著作中除了陶伟的《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张朝枝的《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等少数著作部分涉及遗产旅游内容之外,还尚无一部系统阐述遗产旅游的著作问世,甚至就连一部完整的“世界遗产旅游”译著也未见出版,朱路平所译《文化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虽然阐述了旅游与文化遗产管理之间的关系,但并未涉及世界自然遗产旅游,对文化遗产旅游其他内容也涉及不够。
除遗产旅游之研究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外,国内对其他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环境学、商务旅游等,同样与国外相差甚远,因为从此类研究的现状看,无论是研究人员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还远不能与国外相比。
针对国内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相对滞后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要充分认识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对促进国内旅游研究整体发展的重要性。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的相对滞后,制约了中国旅游学研究的总体水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旅游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因为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不仅是旅游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旅游研究需要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与生态科学等学科参与,需要综合各学科研究人员的力量进行跨学科、综合的边缘研究,旅游研究才能整体发展。
第二,要成立全国性的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会,加强区域与校际合作。前者可通过成立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会、世界遗产旅游研究会等,将国内有志于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学者、专家集合在研究会的旗帜之下,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推进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与发展;后者可通过合作翻译、编写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著作与教材、申报硕士点和研究课题等途径,促进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如中国遗产旅游方法与理论的构建、中国遗产旅游研究范围、特点、遗产与旅游的关系、遗产旅游对东道主的影响等,进行专题研究与探讨,以深化国内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
第四,要多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过去的岁月中,《旅游学刊》曾发表了一些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的文章,为推进中国旅游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旅游学刊》应继续本着“大力扶持新生学科”的宗旨,通过向国内旅游专家约稿、举办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专栏、出版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专辑等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发表高质量的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文章,以缩小中国在这一领域与国外的差距。
第五,针对国内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尚有较大争议的问题,如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概念的界定、研究的方法与范围,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的特点等,国内旅游杂志和旅游网站可通过合作或单独开辟“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论坛”的方式,吸引国内众多学者、尤其是非旅游专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从而澄清人们对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有关问题的模糊认识,推动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学研究与国外相比,已经呈现出明显落后的迹象。要想迎头赶上国外旅游学研究的步伐,使旅游学研究能够满足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之需要,必须花大力气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水平。从中国旅游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看,加强与深化旅游学方法与理论研究、拓展旅游边缘与交叉学科研究,从而构建旅游学研究方法论与理论框架体系,形成跨学科、综合的边缘研究格局,既是提升中国旅游学研究水平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旅游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