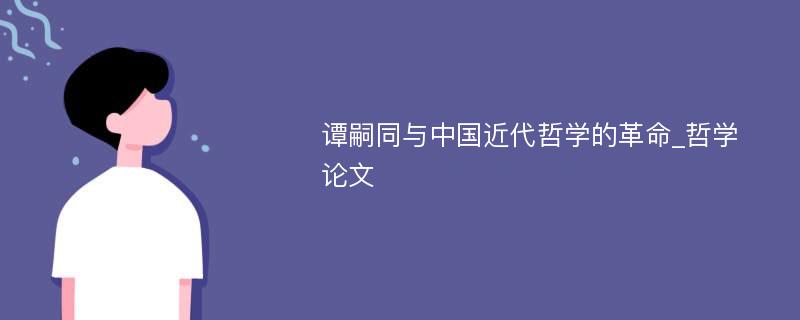
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哲学论文,谭嗣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2)04-119-04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已故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提出的范畴。指的是受中国近代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制约和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突破了中国古代哲学,获得了近代哲学的特征,先后形成了指导中国旧民主义革命时期的进化论哲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中,近世湖湘哲人起着主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魏源是将中国古代哲学推向近代哲学的先驱,而毛泽东则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作了历史总结,王闿运、谭嗣同、李石岑、易白沙、杨昌剂、李达、金岳霖等都是近代哲学革命不可逾越的环节。正是因为近世湖湘哲人的殚精竭虑,前呼后应,才上演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活剧。本文拟就谭嗣同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推动作初步探讨。
一 “华夷之辨”的近代诠释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准则,“华”即中原的汉族;夷即周边的少数民族。华夷之辨形成的原因是在奴隶社会后期和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原文明在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汉族人特别是以汉族为主的统治者形成了“华夏文化优越论”、“华夏中心论”的观念。他们极力主张“以夏变夷”,也就是以汉族同化少数民族;反对“以夷变夏”,也就是反对以少数民族同化汉族。
满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为古代的华夷之辨所不容,遭到了汉族士人“攘夷”的非难。满清贵族以理学君臣之义、父子之伦和“有德者居天下”作了回应;同时执行民族高压政策,屡兴“文字狱”,把汉族士人的“攘夷”意识残酷地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一系列措施较快地抚平了汉族士人心中的不平,冲淡了传统的华夷之辨,使“华夏”的主体逐渐从专指汉族扩展到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从而使满族取得了华夏正统的地位。到了雍乾时期,清代前期的华夷观念已基本形成,并呈现两大特点:其一,认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天朝上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二,西方文明特别是近代工业文明毫无用处,甚至有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这种夜郎自大观念支配下,清王朝在雍正时期就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隔断了中西交流。
魏源在中国近代史上率先对传统的“华夷之辨”作出了新的诠释。鸦片战争的的失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给了“天朝”自居的清朝腐朽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面对这一痛苦变局。作为近世中国睁眼看世纪的第一人,魏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华夷之辨作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中国的失败是由于技术落后。但他认为中国的“道”仍然优越于西方国家,只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等技术,就能重新自强,反过来重新节制诸“夷”。正是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他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承认落后于夷狄,主张向夷狄学习,这就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中“中国中心论”等井底之蛙的见解,掀开了近代华夷之辩的序幕。但学习的内容是船坚炮利等器物层面,而且学习的目的是要赶上、超过夷狄,制服夷狄,也就是以夏变夷,这又保留了传统的华夷之辨中以夏变夷的内容。因此,魏源的华夷之辨是古代向近代的过渡环节。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东瀛小国日本,使中国蒙受了更大的的耻辱,也促使知识分子对中国腐败、落后的封建制度进行更彻底的反省。谭嗣同就是这样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扬弃了魏源的“华夷之辨”,对它作出了合乎时代特征的要求的解答。
首先,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以及东方的日本,再把这些国家称作未开化的夷狄是自欺欺人,贻笑大方。他说:“‘知己知彼’必先求己之有可重,而后可以轻人。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并列于夷狄犹不可得,遑言变夷耶?”(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可见,在谭嗣同看来,“华夷之辨”已是老黄历,应该抛弃。
其次,主张“尽变西法”,即全面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的长技,还要学习西方根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后,沦丧为一只待宰的羔羊,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谭嗣同认为唯有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才能求得民族兴旺、国家独立。他以全新的态度来处理中国与“夷狄”即西方国家的关系,他将西方近代文明当作“先生”,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学生”。对于西方文化,他主张:“彼给予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里看不到以“夏”变“夷”的踪影,流露的是以“夷”变“夏”的观念。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苦苦思索对策,“当馈而忘食,既寐而累兴,绕室徬徨,未知所出”,“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6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也就是主张全面变法,全面向西方学习。
谭嗣同认为全变最根本的是“道”要变,而“道”变又首先体现为伦常变。伦常中最重要的是君臣一伦,他赞美西方的“民主”“犹为至大至公”,斥责“中国秦以后尊君卑臣”的封建专制,认为两者“相去奚止霄壤。”(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9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体现了谭嗣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立场。
接着才是器和法的变。谭嗣同主张从根本变起,具体说来就是要废科举,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练海陆军,筑铁路,办矿务商务,制机器,除弊政。要而言之,中国从道到器到法都不如西方,因而要尽变西法,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可以看出,谭嗣同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体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
谭嗣同变法的理论依据是王夫之的“器体道用”、“器变道亦变”的理论。他认为:“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道存而器不亡。”他还从王夫子对“道器”关系的阐述中概括了“无其器,则无其道”的结论。而器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器属性的道当然会随着器的变化而变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9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近代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而“中国向何处去”在文化领域主要体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致经历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三个阶段。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口号,主张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逻辑起点和必经环节以及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必经环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据,对华夷之辨作出了不同于魏源的回答,主张中国人不但要学习西方的“器”,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就是主张学习西方制度层面。但在他们看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优越于西方,无须向西方学习。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主张全盘西化。因此,康、梁、严等人的观点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二个环节。而谭嗣同对华夷之辨作出了更为激进的解答,认为器变道应跟着变,主张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的器,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更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制度。这样,谭嗣同就把学习西方推进到了文化层面,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第三个环节,推动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二 高扬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
“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陆王心学更把主体之“心”作了本体层面的规定,断言“心”是宇宙的本原。谭嗣同继承了陆王心学的这一思想,对“心”作了本体意义的理解,断言:“一切唯心所造。”(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1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换言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心”派生。
然而,谭嗣同的侧重点不是把心理解为世界的本体,而主要是以力言心,把心理解为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内在驱动力。他把心力即心之力推崇为能够创造世界万事万物的精神力量,“人所以灵者,以心也。人力或作不到,心当无作不到者……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无不如意。”(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4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心是不可见,也不能被描绘得十分形象、具体。“心力可见否?曰:人之所赖以办事者也。吾无以状之,以力学家凹凸力之状状之。愈能办事者,其凹凸力愈大;无是力,则不能办事,凹凸力一奋动,有挽强持满,不得不发之势,虽千万人,未或能遏之而改变其方向也。”(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6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谭嗣同用物理学上的凹凸力来界定心力,但这种界定是不恰当的,因为心力不是物理力,而是主体精神范畴中的能动的创造力,主体的意志力。
心力的具体作用体现在道德和历史活动两个领域中,在个体的道德实践中,心力首先表现为专一的特性,“盖心力之用,以专以一”(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6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只有意志专一,执着,坚忍不拔,才能不为外界纷扰,造就理想人格。其次,心力主要表现为主体自主选择的自由性。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心力则主要表现为对历史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这种促进或阻碍作用通过愿心和机心两种形式表现出来。愿心是视人为我的仁爱之心。它是历史进化的动力,能兴乐拨苦,普渡众生,能够挽“劫运”,不仅能够拯救中国,而且能够拯救世界,实现天下大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意志。机心则是区分人我,以理智算计智巧之心。机心带来“劫运”,是妨碍历史进步的消极意志。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就在于中国人多机心;为了改变落后局面,心须去掉机心,崇尚愿心。
谭嗣同崇尚心力,其着力点不是用它来渲染个体的感性欲望,而是把心力理解为一种具有目的性的理性化意志。他认为“慈悲”为“心力之实体”,“盖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57~35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慈悲为内涵的心力,本质上是一种善良意志,它以“仁”为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
谭嗣同认为心力即主体的意志力无所不能,过份渲染主体意志的创造力,具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倾向,将近代中国哲学由龚自珍首倡的唯意志论思潮推向了新的阶段。
中国传统哲学在“天人之辨”上“天命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天命论主张具有人格的“上天”的命令、旨意主宰人事的吉凶祸福,人们在天命面前无所作为,只有服从天命的安排。天命论完全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彻底否定了一定条件下人们意志的自由选择,严重阻碍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妨碍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进程。
近代伊始,一股唯意志论思潮在中国哲学界兴起。龚自珍首先石破天惊地提出:“自我”即个体的意志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一命题的提出,突破了天命论的樊篱,为自由意志的觉醒扫除了障碍。谭嗣同则在此基础上借用西方的自然科学成果,揉和佛教的大无畏精神,把“心力”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心力有无限的创造力。谭嗣同的心力说强调个体的意志自由,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具有反天命论、独断论、权威主义的启蒙作用。自袭自珍始,经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毛泽东等,一股绵延不断的唯意志论思潮对传统的天命论发起了持续的冲击,天命没落,个体意志自由彰显,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肯定。
传统哲学中天人之辨上的天命论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对象之一,谭嗣同的心力说把心力即主体的意志力、创造力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彻底否定了天命的存在,宣告了天命论占统治地位时代的终结,片面强调主体意志创造力的唯意志论思潮时代的到来,使中国哲学从整体上对天人之辨作出了新的诠释,推动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谭嗣同片面张扬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是受谭嗣同思想的影响才投身革命的。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是以坚强的意志为动力,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邹容说过:“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注:杜承祥:《邹容》,第24,青年出版社民国35年出版。)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将谭嗣同的遗像放在座位旁,并在遗像之上题上一首自勉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恢。”(注:邹鲁:《邹容传略》,《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242页,中华书局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非常崇敬谭嗣同,他曾对蔡和森等人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注:《张昆弟日记》1917年9月22日。)
谭嗣同的心力说蕴涵着二重性昭示:意志力量的张扬可以在特定的时期起着巨大的激励和凝聚作用,但它毕竟是片面张扬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心主义学说,不可能长期有效地指导实践。
三 以太说:本体论的近代建构
哲学家大抵会对世界本源的本体论问题作出解答。谭嗣同赋予西方近代物理学的“以太”概念以本体论的含义,构建了颇为独特的“以太说”。
“以太”是英文单词"Ether"的音译。它是西方科学家于17世纪后设想的一种机械媒质,用来解释光的传播以及电磁和引力相互作用现象。20世纪初,随着相对论的确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证明了光的传播和一切相互作用的传递都是通过各种场,而不是通过机械媒质,这样,以太就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而被淘汰了。大约19世纪80-90年代,“以太”随同西方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一起传入中国,并被当时不少思想家所接受。谭嗣同不但接受了这一学说,而且建构了以它为基础的本体论。
他指出:“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大’。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9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谭嗣同对以太性质的界定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以太是物质实体,充满宇宙的是以太,以太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实体,也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具体说来,他认为声、光、电等都是“浪”,即波动。波动的实体是什么呢?《以太说》对此作了回答:“动荡者何物?谁司其动,谁使其荡,谁为其传?曰:以太。”(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43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天体之间有离心力、向心力,造成牵引之势。那么,“牵引者何物?谁主其牵,谁令其引,谁任其吸?何以能成可睹之势?曰:以太。”以太是“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的实体,其功能体现为波动、力、质点、脑气的活动。另一方面,以太又是心力,是精神实体。“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9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在他看来,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悲、基督教的灵魂都是以太的体现。
谭嗣同借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以太”概念来代替中国传统哲学的“气”范畴,将本体论建构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是中国哲学近代化的一种尝试。哲学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它必须不断回应自然科学提出的新问题、新理论,才会有生命力。但中国古代哲学家大多在自然科学领域没有什么成就,也不注意概括、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使得中国古代哲学缺乏自然科学基础,体现出重伦理、重思辩的特点,不能指导人们有效地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这一特点到了近代有所改观。康有为用“电气”、“星云”等来说明中国近代哲学的“元气”范畴,开了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成果改造中国古代哲学的先河。严复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有着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因而很注意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来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借用“以太”对物质实体以新的规定,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气”就是“以太”,气是构成宇宙的始基,运动是物质自身的运动。二是用牛顿力学的“质力相推”来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事物内部吸力和斥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上两方面都表明:严复看到了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是事物自身的运动,否定了神创说。但康有为、严复都只是借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概念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一般范畴,而没有用它们来构造自己的哲学体系。谭嗣同则把“以太”概念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了以“以太说”为本体论的哲学体系。
谭嗣同率先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建构哲学体系,促成了本体论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型,推进了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遗憾的是,谭嗣同的这一作法没有为尔后的中国近代哲学家所继承,中国近代哲学没有注意结总、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使得它缺乏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中国近代哲学家不像西方近代的哲学家那样使哲学与自然科学结成紧密的联盟。西方近代的许多哲学家诸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等同时又是很有造诣的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注意结合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探索哲学问题,使得哲学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对当时的自然科学也作了深入的哲学研究。正如冯契先生所指出过的,中国近代哲学家由于“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最具迫切性的政治问题,也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非常薄弱,所以,他们并没有能给哲学提供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注: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第708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3月版。)章太炎、孙中山、胡适等资产阶级哲学家是这样,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这样,职业哲学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贺麟仍然是这样。
中国当代哲学家依然没有解决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结盟的问题,因此,在新的高度上解决谭嗣同曾给予极大关注的这一问题,可谓任重道远。
标签:哲学论文; 谭嗣同论文; 华夷之辨论文; 谭嗣同全集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哲学史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