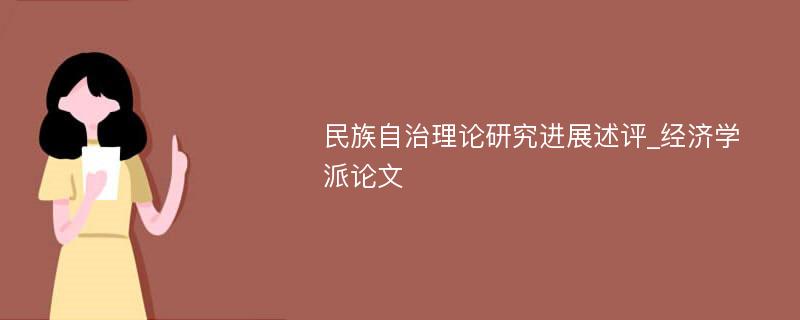
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进展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自主性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界重新兴起对国家的研究兴趣,国家学派形成,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是其重要的研究内容。国家能否形成其独立偏好并成功实践,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和成败。在实践当中,有一些国家成功具备了自主性并实行了干预,比如20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还有一些国家被束缚在社会网络之中,无法推动社会经济转型,比如印度。因此,国家何时具备自主性、何时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回顾国家自主性的相关研究,围绕三个问题比较和梳理,总结其发展趋势。鉴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复杂关系,①本文的侧重点是国家自主性,但也会涉及国家能力的相关研究。 一 国家自主性:国家的固有属性还是国家与其他力量博弈的结果? 研究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素,首先要明确国家自主性本身的性质。有一些研究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因而也是普遍的,是所有满足条件的国家都一直具备的;有的研究则认为,国家自主性是变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特殊的,能获得也能丧失。 1.普朗查斯和米利本德的相对自主性研究 普朗查斯和米利本德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两人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做过重要研究。两项研究都侧重从规范意义上考察国家自主性,都倾向于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特征。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环节的特点决定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相同,不需要政治因素进行干预即可顺利运转,因此政治环节脱离了直接的经济内涵而获得了相对独立性。②米利本德认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如果国家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国家无法做到超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灵活地行使阶级的任务。③因此,新马克思主义或从结构上认为国家必然具有相对自主性,或从统治需要上认为国家应然具备相对自主性,但很少观察现实政治中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相对自主性的条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研究中,即便这种自主性具有普遍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属性,但这种自主性最终仍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具有的只是相对自主性而非后面斯考克波所说的完全自主性。 2.诺德林格的民主国家自主性研究 与新马克思主义相似,从诺德林格的研究来看,整体上,民主国家自主性是普遍的。诺德林格专门研究了民主国家的自主性,认为民主国家有很多自主性提升的机会和能力,能够抵消大部分与国家偏好不同的社会偏好,④因而,国家或者能够逆社会偏好而行动,或者能够将社会偏好转化为与国家偏好一致,国家拥有显著自主性。诺德林格的论证角度主要在公共政策决策官员身上。他总结了一系列决策官员能够采取的提升自主性的战略,⑤并分析了在具有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政治制度安排的民主国家中,为什么决策官员都有采用这些战略的机会和可能。比如,诺德林格认为,虽然美国的权威呈碎片化和分散化,导致社会力量有更多机会影响国家,但这不必然损害国家的自主性,因为社会行为者的小团体与国家官员个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⑥他的结论因此被斯考克波认为是“乏味”,因为国家自主性仅仅成了“政治领导力的创造性练习”⑦。 因此,诺德林格的结论实际是,无论社会如何企图对国家施加影响,决策官员都有机会和能力采用策略,化解这些影响,提高国家自主性。这本质上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无区别,两者讲的都是国家在理论上拥有自主性,有能力拥有自主性;只不过两者对国家的定义不同,诺德林格将国家定义为决策官员的集合(在后面会提到),新马克思主义视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3.国家学派和米格代尔的研究 国家学派鲜明地提出,国家自主性可能获得、可能失去。斯考克波提出的完全自主性超越了资产阶级利益的束缚,是高度自主的,因而也不是国家恒常具有的性质,而是受历史传统、国内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政策领域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以美国农业部为例,它借助危机获得自主性;而当利益集团的力量过大,它的公共政策再也无法成形。⑧米格代尔也描述了社会力量是如何制约国家自主性的。国家因无法在领土内制定单一的规则,受制于地方强人,国家因而缺少自主性,无力进行社会控制。⑨ 4.小结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到,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解逐渐从国家的不变属性这一常量转变为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变量。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之所以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是普遍的,是因为它们没有考察现实中其他因素对国家自主性产生的影响;而诺德林格的研究特殊性在于,他引入了社会力量,并承认社会力量有能力对国家施加影响,但是最终的结论却是,民主国家有机会凭借决策官员采用自主性提升策略化解社会施加的影响并拥有自主性,因此其自主性也是理论上的和普遍意义的。如果对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言,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的基本性质,那么,对诺德林格而言,国家自主性是民主国家决策官员化解利益集团压力的功劳。诺德林格研究令人遗憾的地方在于,他无法说明国家自主性是民主国家官僚特有的本领,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官僚有机会采取这些策略。如果他能够更充分地证明是民主国家特有的因素,比如政治制度,决定了其决策官员有机会采用自主性提升战略,那么他的研究会更有启示意义。 但是普朗查斯、米利本德和诺德林格都无法解释国家自主性现实当中时有时无的变化,这一点恰恰是国家学派首先做到的。斯考克波就明确指出,研究国家何时具备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⑩要解释变化,就要考虑影响变化的因素。斯考克波总结的影响国家自主性变化的因素有历史传统、国内国际环境、社会结构、政策领域等。换一个角度来看,按照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第一,不经过社会直接施加到国家本身的因素,比如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国际制裁,都可能直接刺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国内国际环境属于这类因素。第二,通过社会力量作用到国家的因素,比如利益集团、地方强人的游说和反抗,社会结构就属于这一类因素。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对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展开的自主性研究做简要回顾。 二 国家自主性:国家独立于谁,统治阶级还是社会? 对国家自主性的研究并非起初就围绕国家—社会的关系展开。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国家自主性的研究是如何最终被放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研究的。 1.普朗查斯和米利班德的研究 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基础上,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理论,以普朗查斯和米利本德为重要代表。(11)普朗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自主性指国家独立于统治阶级的相对自主性,米利班德的定义与之类似,认为国家自主性指国家独立于任何阶级(包括统治阶级)的自主性。二者论证的角度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而国家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其自主性只能是相对自主性。 2.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自主性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国家不再仅仅相对于统治阶级而具有自主性,而是独立于整个社会而具有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研究也开始在更宏大的国家—社会关系背景中展开。与之前的多元主义研究不同,国家学派的出现肯定了国家在社会集团压力面前保持自己独立偏好的能力。 在诺德林格的民主国家自主性的模型中,国家和社会被明确区分,且各自具有偏好,只要国家没有按照社会的偏好行为,就具有自主性。但他的定义有太过宽泛之嫌,他认为国家因为内部分歧无法做出决策时,也不算失去了自主性。(12)斯考克波更明确地突出了国家相对于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行为体的地位。她认为,当国家追求的目标独立于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时,国家具有自主性。(13)米格代尔考察的是没能建立权威的第三世界国家,国家失去对地方的控制,一定程度的国家自主性有助于国家控制社会,维持基本秩序,推动社会转型。(14) 此外,从国家—社会关系考察国家自主性的一大贡献是使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得以进一步深入。第一代国家学派学者将国家自主性简单地等同于国家能力。第二代学者发现,因为缺少国家与社会的合作,通过国家与社会隔离获得的自主性不一定能很好地转化为国家建制性能力;而有些国家有良好的国家—社会合作,但是国家因此易被社会影响,不具备很好的自主性。(15)维斯和霍布森的研究是这两种情况的平衡。他们认为,在国家拥有隔离性自主性的前提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嵌,能够成功将自主性转化为国家能力。(16) 3.小结 结合上一部分可以看到,将社会引入国家自主性的研究是重要一步,它不仅使得国家自主性不再是国家的普遍特性,而且还使一系列考察社会与国家竞争博弈、国家能力等的研究继续深入。但应该看到,虽然这部分引用的研究都在研究国家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但是结论却迥然不同,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学者对国家的理解不统一。下一部分将回顾国家自主性研究中对国家的理解。 三 如何理解国家:独立行为体还是解构后的碎片? 韦伯式的国家定义只是诸多理解中的一种,且最初是根据欧洲的国家经验而提出。本部分主要讨论对国家理解的演变,以及对国家的理解是如何影响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解的。 1.国家学派的韦伯式国家定义 斯考克波不满足于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不完全自主性,将拥有独立目标的国家看做独立的行为体,具有完全自主性;并且,她认为,也只有国家确实能够提出独立目标时,才有必要将国家看做一个重要行为体。(17)国家从此不仅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束缚,还超越了一切社会集团。如果说多元主义陷国家于囹圄,斯考克波的新国家主义则让“国家”这个概念得以极大膨胀;她不仅“找回了国家”,甚至“踢走了社会”(18)。这个国家或拥有韦伯意义上的团结一致的精英官僚,或存在与社会压力高度绝缘的高层决策者,或保留着在公共政策决策上民政官员较利益集团、政党而言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历史传统;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那至少也遇上了一次让“弱国家”临危受命的大危机。所有这些条件把国家打造成一个对外坚定不移、对内协调一致的行为体。 2.米格代尔对国家的解构 米格代尔则毫不留情地对斯考克波的理想国家进行了解构。在观察了大量第三世界“弱国家”的实践后,他发现,在国家没有能力在领土范围内建立推行统一规则时,地方政治受制于地方强人,国家领导人无法动员群众获得支持,被迫将高层政治转化为“生存政治”;这方便了国家投入的资源落入地方强人囊中,反过来使国家在地方的权威进一步恶化。(19)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已经被各自独大的地方强人,被迫与地方强人妥协的地方官员和政策执行者,以及贪腐的高层官员撕扯得四分五裂,中央的政策敌不过地方强人的地方规则,中央政府无法在地方甚至其他中央机构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米格代尔认为,应当先将国家分解为第一线分支机构、分散于各地的下层机关、部门的中心机构、最高层领导机构等不同成分,(20)这些成分在它们的所在层次与其他社会力量争夺规则制定权的过程中创造了国家本身,国家与社会不断相互改造。(21)可以看出,米格代尔对国家的理解是动态而非静态的,侧重过程而非结果。 3.诺德林格的中间道路 相比前面两者,诺德林格的国家定义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和斯考克波类似,诺德林格也声称自己采用韦伯化的方式定义国家,(22)但二人对国家的定义却大相径庭。诺德林格认为,国家是指所有那些占据公共职位的个体,他们凭借职位的授权或自身赋予的权力做出、执行对社会各部分都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更明确地说,国家就是那些被授予决策制定权的个体,而且仅限于此。(23)这一定义虽然也是从国家的组织机构角度出发,但是最终落脚点在决策官员个体,或部分决策官员和机构,而非作为一个整体的决策官员。因此,斯考克波对于国家的理解与诺德林格的不同,它虽然也以国家组织机构为基础,但是超越了官员个体,形成了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行为体,在整体而非分散意义上讨论国家。 但另一方面,与米格代尔相比,诺德林格对国家的理解也有不同。首先,诺德林格采用了韦伯式定义,但米格代尔反对韦伯式的国家定义;因为他认为韦伯式定义太过强调国家的官僚主义特征,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改变,忽视了社会力量改变国家性质和目标的能力。(24)其次,诺德林格对国家的解构不像米格代尔那样彻底。(25)虽然诺德林格提到了美国政治决策点的分散导致了决策官员变为权力的争夺者,(26)也提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制衡设计,但是没有详细讨论不同国家机构之间是如何相互竞争、妥协和制衡的。因此其对国家的分解是若隐若现的。 因此,诺德林格的作品本身是中间道路的、过渡性质的:其笔下的国家既非斯考克波笔下的国家那样完整,又非米格代尔的那样破碎;其笔下的社会能够通过众多否决点影响决策进程,却又由于决策官员的自主性策略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诺德林格对国家的理解决定了他的自主性更像是国家官员的自主性。这条中间道路让他的研究充满争议。《民主国家的自主性》出版于1982年,正是国家学派兴起的时间,而且这部作品强调民主国家并非像社会中心论者一直所声称的那样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毫无自主性,因此,这一研究有时被认为与《找回国家》一样同属国家学派的作品。(27)同时,由于其本质上未从独立行为体的国家意义上解释自主性,斯考克波将这一研究当作多元主义的作品,而且是“将多元主义假设扩展到概念的极致”(28)。 4.小结 国家学派出现之前,多元主义对民主国家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约束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各种各样社会结构下,社会集团是如何限制国家的。(29)国家自主性研究者首先将社会引入,国家学派采用韦伯式的国家定义,又将国家作为独立行为体引入。西方经典的国家、社会两个要素至此齐备,国家自主性的研究终于被放置在国家—社会的框架下进行,回归到了经典的西方国家—社会二分的传统上。但随后有许多研究针对独立行为体的国家概念,用东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进行了质疑和挑战。 对国家的解构将国家自主性的理解扩展到国家学派鲜有关注的领域,即国家内部分裂与国家自主性的关系。诺德林格认为,即使国家内部无法达成一致,不能出台政策,只要没有按照社会偏好行事,忠实于国家自己的偏好,也不算国家没有自主性;而斯考克波的研究实际将这一问题简单处理了,国家如果没能形成偏好,根本不会被当作独立行为体,也就谈不上国家自主性。这样的处理将国家内部分裂导致国家无法形成统一偏好的情形忽略了,但是在现实中,这确实是导致国家失去自主性的原因之一。此外,米格代尔的研究更是展现了国家横向和纵深的多面复杂维度。国家在地方的失败会传导到高层政治,高层政治沦为生存政治又反过来使国家在地方的力量更为脆弱。这样的解剖使国家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构成,大大拓展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研究空间。 四 总结和展望 1.国家—国家研究框架 根据上面的回顾,可以看到国家自主性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扩张的发展过程,视角从最初的国家与统治阶级,扩展到国家与整个社会的互动,细化到国家内部的分解。如果说国家—统治阶级、国家—社会都是理解国家自主性的框架,那么解构国家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国家—国家能否作为另一个框架从国家内部考察国家偏好的形成和执行。因为国家自主性并非仅仅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结果,相反,国家和社会的博弈引发的国家内部的横向纵向博弈,同样能对国家自主性产生影响。事实上,已有的研究对此也有所涉及。比如,诺德林格的研究如果能不拘泥于决策官僚,进一步剖析国家的制度制衡设计,也许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美国最高法院在某些时候至高无上的决策权是如何帮助国家形成和捍卫自身偏好的。 2.国家自主性研究的适用性 对国家的解构在拓展国家自主性研究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对其适用性提出了挑战,其最核心的问题是:分裂的国家还存在统一的自主性吗?在将国家分解为不同层次后,米格代尔指出,研究者必须首先探究国家各种成分的自主权,因此国家的完全自主性未必是研究国家的最好起点。(30) 更大的挑战并非来自于米格代尔这类国家分解者。米格代尔虽然解构了国家,但毕竟还承认国家的存在;而根据东亚经验的国家研究,“国家”是否存在都是一个疑问。在《发展型国家》一书中,康明斯回顾了关于亚洲国家的研究,显示了亚洲国家的特殊经验,其中谈到,萨缪尔斯认为日本的国家是在协调而不是在领导,这部分由于国家能力的局限,部分由于达成相互赞同的政治运作(the politics of reciprocal consent),他因此认为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边界模糊不清,评判国家自主性比较困难,并由此转向了可以明确认定的国家能力的考察。(31)沃尔夫伦更甚,干脆指出日本无国家。他认为,日本无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决策者和责任者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只有“系统(system)”,而无国家。(32)因此,根据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维斯和霍布森的国家建制性能力虽然仍有用武之地,可以用以解释东亚的公私合作,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无国家,那么国家自主性也就无从谈起了。也正因为如此,基于东亚的国家研究有时需要下沉至政策过程和公私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从讨论独立行为体的国家入手。 以上的讨论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国家自主性概念适合什么样的国家?对于国家无权威的弱国家和国家权威不明显的国家(比如一些东亚国家)真的无国家自主性可言吗?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国家?当国家自主性概念没有解释力时,国家能力的概念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随着我们对不同国家经验理解的深入,会有更全面的理解。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国家能力缺失,治理水平低下,腐败、教育、卫生医疗、公共安全等面临着严峻考验;在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被利益集团绑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曹海军、韩冬雪:《“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 ②张勇、杨光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 ③同上。 ④[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6页。 ⑤同上书,第86-87页。 ⑥[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第173页。 ⑦[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3页。 ⑧同上书,第17-18页。 ⑨[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⑩[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第10页。 (11)张勇、杨光斌:《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脉络》,《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5期。 (12)[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第65页。 (13)[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第10页。 (14)[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朱海雷、隋春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5)曹海军、韩冬雪:《“国家论”的崛起:国家能力理论的基本命题与研究框架》,《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 (16)[澳]琳达·维斯、[澳]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17)[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第10页。 (18)[澳]琳达·维斯、[澳]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分析》。 (19)[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第60-129页。 (20)同上书,第122-126页。 (21)同上书,第132页。 (22)[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第10页。 (23)[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第10页。 (24)[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第116-117页。 (25)这客观上也与两者选取的国家不同有关。诺德林格研究民主国家,国家权威相对完善;米格代尔主要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国家权威没有很好地建立。 (26)[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第174页。 (27)同上书,译者序。 (28)[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美]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第42-43页。 (29)[美]埃里克·A.诺德林格:《民主国家的自主性》。 (30)[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第122页。 (31)[美]布鲁斯·康明斯:《无蜘蛛之网,无网之蜘蛛:发展型国家的系谱》,载[美]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77页。 (32)Karel van Wolferen,"Chapter 2:The Elusive State",i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New York:Aflred A.Knopf,1989.标签:经济学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