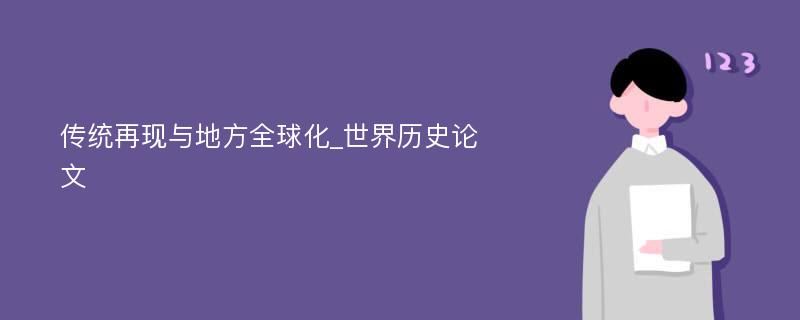
“申遗”:传统与地方的全球化再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申遗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5—0046—07
一、引言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热衷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申报自己地方上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内外的许多院校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各种相关的学术讨论频繁举行。这样的氛围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地方再建构运动,许多地方都热衷于通过彰显所谓的传统来突显自己。其实,这种情况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纪初年推出文化多样性宣言之前就已经存在,只不过许多相关活动都是“自发”的。称其为“自发”,乃因潜隐其后的动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换言之,当事者在如何塑造地方的问题上与后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遗产和多样性宣言毫无关系。追求利益的本性使人类下意识地知道获取象征资本在全球化时代里的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言是在已经形成的气候下提出的,它无疑表达了对全球化可能带给世界某种以美国文化为蓝本的一致性文化的担忧。[1](P1~10)尽管这种担忧已被证明是一种现代神话,[2](P1~38)但是,这样的宣言在这么一个特定的时期里出台,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交通成本的下跌、冷战结束,以及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和世界劳务市场分工的重新结构,造成了国际间人口流动的现象,主要体现为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向发达国家外流。除了纯粹因以赚钱为目标引起的跨国人口移动(transnational migration)之外,原先有闲阶级才享受得起的跨国旅行也在许多国家中的一般民众中盛行起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地遂出现了最初以招徕游客为目的的强调地方文化的传统振兴运动。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由于缺乏实质性和稳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之专业人士的匮乏,发扬和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章法紊乱。毋庸讳言,对一些地方的当政者而言,传统或文化遗产可以是某种获利的工具。它们被改造成专供异乡、异国游客消费的商品,在这样的情形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文化多样性宣言,无疑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自身文化遗产认识,理解它们对人类精神生活和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
今天,传统或文化遗产已然成为重新建构地方认同的重要资源。但是,在当下的地方叙事里,有些所谓的传统实际上早就失去了生命力。然而,出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却重新被再创造。①本文就传统、地方,以及传统的再创造等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并试图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对“申遗”进行解读,以期理解这一现象所产生的“传统再生产”意涵及其在地方认同上的建构意义。
二、传统与现代
传统是社会人文科学领域里的重要概念。社会科学兴起于19世纪,当时的主导性话语是建立在进步观念上的演化说。其时,英法两国的学者都相信,他们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在这样的假说之下,当时的学者大多热衷于考察人类社会文化是如何发展的,最流行的做法就是把已知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按一定的标准进行排序,依次勾勒出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谱系。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眼界大开,遭遇到了许多不同的文化,见到了许多不同的种族。在欧洲人看来,这些不同的文化都是人类演化过程中的“孑遗”(survivals),具有活化石的意义。他们相信,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代表着人类朝欧洲文明的方向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3]
学术界往往把现代社会科学的诞生与社会学的出现相提并论。虽然,社会学并不以传统作为它的研究对象,但传统这个概念却在许多社会学家的著述中频频出现,这是因为社会学从诞生伊始就被认为是研究“现代”的领域。[4](P47)由于社会学家研究的主要是现时的社会问题,他们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总难免提及“过去”,于是现代与传统两个概念的对立意味,可能随着社会科学体系的确立和发展走入民众的话语世界。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传统与现代两分的始作俑者。
实际上,“传统”一词原先缺乏它在晚近以来所承负的大部分意涵。中文的“传统”首见于《后汉书》,指的是某件东西的过渡移交,尤指皇位的递嬗和某种学理或说教的继承。无独有偶,在英文里,“传统”来自拉丁文tradere,也是指物件、财产的代际传递并因此而得以保存。在罗马法里,tradere涉及继承和继承者有责任呵护的所继承之物。显然,无论在中文或者西文里,“传统”最初是作为一种法律意义的用语而存在的,除了其中所包含的“传承”的含义之外,它缺乏许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内涵。然而,传统的核心问题与传承息息相关却是古今不变的。
有学者指出,在西方社会,今日意义上的“传统”其实是过去两百年来的产物。而过去的两百多年正是现代性出现并扩散开来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尼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启蒙主义运动,等等。再往前一段时间则有宗教革新和文艺复兴。在17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一场称之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论战。这场争论发生在所谓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之间。根据古典主义者的观点,古代和经典的文体模式应当继续沿用,而现代主义者则持相反的看法。当时的思想家如笛卡尔(Descartes)、培根(Francis Bacon)、蒙田(Montaigne)等人都试图通过宣扬理性来辞别古风;拒绝文艺复兴以来对古代经典的盲目崇拜。在这一争论中,现代性的代表是理性主义和有关“进步”的思想,而古典的权威和来自过去的野蛮风俗,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5]
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欧洲人“发现”了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这些被认为“野蛮”的民族在成为基督教传播福音的对象和遭受殖民剥夺的同时,也成为现代主义者有关进步尺度上的标识。他们成为了“过去”的标本,并因此构成了人类“传统”的一部分,并由此而成为“过去”的空间表达。大部分的这类发现都被用来论证欧洲中心说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与当时的权力关系和欧洲殖民者自身的经济、政治、宗教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了助长了“欧洲中心”的世界观之外,这些发现和随之而来的进一步的殖民扩张实际上缔造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言说“现代”,“现代”于是在这样的一种权力和文化比较的背景下被概念化了:除了作为时序的类别将欧洲文明的早期形式排除之外,现代还成为一种空间类别(spatial category),把西方文明与同时期的非西方社会文化加以区别。由于这些非西方的社会文化被认为是人类单线进化过程中不同时期的代表,因此,尽管它们与欧洲文明同时存在,却也有了某种时间指向——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被冠以“传统”或“原始”(primitive)的头衔。
甚至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性进化观念的影响。在欧洲,下层阶级,尤其是乡民和其他边缘性群体的文化也成为“发现话语”(discourse of discovery)的对象。许多对民间和乡民的研究采取的是历史学的取向,目的在于重新建构有关过去的社会知识,这种知识生产过程在产生现代性的政治语境里承负了建构历史的使命。许多民间的仪式、特别的物件、选择出来的一些边远或边缘群体的文化,在现代主义者的表述里都成为了“发现”的对象。这意味着欧洲文化的“过去”也同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一起构成了走向现代的一环。
可见,“传统”实际上是现代性的造物和“他者”,[6](P57)总是被用来表达“现在”(the present)与“过去”(the past)的割裂与接续关系,并几乎成为后者的代名词。这是传统在时间上的意义。我们在谈论传统时,指的一定是过去的东西。正因为人们常常把现实社会里存在的一些物质或非物质东西认定为传统的,传统又有了空间上的意义。换句话说,传统在时间上的意义必须在空间里表达,即便是精神性的东西也必须通过“现在”可感知的个案或文本作为载体而得以体现。传统的空间意义还有另外一层意思,由于西方霸权的缘故,人们往往把现代与西方联系起来,因此,传统在空间上又代表了非西方。由于现代化又有都市化的指向,乡村自然也成为传统的空间体现。
三、传统与地方
在人类学的话语里,社会脉络简单的“地方”(locale)是与五方杂处的“都会”(cosmopolis/metropolis)相对的概念;在现代主义的话语里,两个概念又分别成为传统与现代的隐喻。地方代表了空间上的闭塞、经济上的单一、文化上的落伍。都会代表了开放的空间,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与多元。同时,都会流涌着青春的骚动而不安分,地方则宁静与本分。换言之,都会充满了张力——如同茅盾在《子夜》里用夜上海的霓虹灯来作为“摩登”的隐喻那样——迸发着光、热、电。地方则处于对立的一端如同日渐失去活力的老者那样,显得迟钝而呆滞。这样的两分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城市与乡村的观念。城市代表了商业与平民,乡村则是农人和贵族的天地。当现代主义在城市里滥觞之际,乡村代表了传统,贵族成为传统和旧秩序的维护者,而现代主义的布尔乔亚们所要推翻的恰恰是他们。随着现代性的蔓延,诸如地方与都会、城市与乡村的两分概念也进入了中国,并渐为国人所接受。在以茅盾为代表的一批左翼作家的笔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成为他们既爱又恨的对象。在西方消费主义的侵蚀下,上海的纸醉金迷摧毁了地方乡绅的心理防线。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都会是如何地与“地方”格格不入。
文学作品里表现的这种对立,反映了建立在复杂社会脉络之上的都市与地方之分及其所产生的意涵。这种区分完全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在中国的过去,如此的两分是不存在的。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以降,资本的力量使这样的两分在中国成为现实,而现代主义的文人学者则通过他们的描写,在人们的观念上加深了都会与地方的区隔,以及有关这种区隔的想象。然而,就传统主义者而言,商品和消费堆砌起来的都市代表不了“文化”,甚至没有“文化”(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人抱怨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么)。因此,真正的文化必定得到地方上去寻找。于是,“礼失求之于野”也有了新的内涵。地方,俨然成为国粹之所在,是为寻找传统文化的宝藏和源流之所。
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看到。有意思的是,到地方上寻找文化往往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我们同意这么一种说法,即:由于民族主义着意于通过传统主义来表达现代民族国家诉求,从而它本身是一种现代性所导致的后果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性与传统并不总是矛盾的。如前所述,传统是现代性创造出来的“他者”,在概念的层面上,传统通过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来为现代性服务。在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那些被定义为传统的东西往往被用来为现实服务;传统完全可能在许多方面服务于现代性,民族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中欧、东欧、北欧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兴起了民俗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都试图确认:民族国家的文化之根已经扎在丰厚的传统里。在日本,以及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确认和追寻自身传统的运动,往往发生在外来的、被认为是现代的东西,与固有的习惯和价值观念激烈碰撞之际。民族主义的激情催生了如柳田国男那样的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推动了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老北大的一批知识分子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民俗学团体——“歌谣研究会”。当年的这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看来,都不失为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都深入自己国家的许多地方搜寻、发掘各种能够丰富民族内涵,并称得上是“传统”的素材。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发明”了“传统”。
“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指的是民族主义者或族群民族主义者(ethnic nationalists)为了政治目的而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进行建构。[7]在塑造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过程中,民族主义者总是将民族国家刻划为一种文化单位,为此,他们总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来宣称民族的源远流长和独一无二,因此他们必须在他们声称所代表的族群的文化里寻找资源,并将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将之发展成为民族国家叙事的文化表述。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民族主义者“发明传统”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塑造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过程。
在世界历史上和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一开始总带有反抗霸权的意味——无论这种霸权是殖民地宗主国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主宰世界的超级强权。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与全球化有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的15世纪。换言之,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经济全球化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来,始于对殖民地的扩张与资源争夺。[8][9][10]几百年来,世界霸权星移斗转,渐次形成今日格局。显然,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本的扩张所引起的市场需求,都市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取代了乡村成为了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自此,以乡村为代表的“地方”不仅在民族国家的大叙述上,而且在现实的国家生活中,遭到了冷落。现代性的蔓延和扩散,在开始时,往往给乡村带来萧条和颓败;而它对既定的秩序的冲击,又必然招致守旧的贵族和乡绅们的抗拒。在现代主义者的眼里,乡村遂成为阻碍进步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代表着他们所要摒弃的传统。然而,迟滞的乡村确也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有关“过去”的真实。法国历史学家尤金·韦伯(Eugene Weber)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资产阶级革命如此彻底的法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农民仍然没有一个法兰西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11]尤金·韦伯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另一个空间,揭示了以民族国家为叙述单位的通史(general history)给人们所带来的虚幻与不实。
然而,也正是由于乡村或“地方”的这种迟滞,我们才得以真切地感受到何为传统,即:旧有的,在都市生活中日渐失去的精神和物质表现。传统因此是具象化而可以感知的,也因此具有了模式的意义——它代表了固有的生活或文化模式。我们把某种生活方式认定是“传统的”,乃是因为我们往往可以在“今天”还体察到它的存在:它通过代际传承,所以必须通过“当代”来表现。传统的这种时空特性表明,它可以指所有现存的“前现代”的东西。因此,在现代主义表述里,传统往往与“地方”相联系。20世纪70年代,就有法国学者认为,唯有地方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12](P113~127)如是说是对现代史学的批评,因为忽视了地方的现代史学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地方往往被当做都会的他者来为现代性作陪衬。所以,任何民族国家语境里的通史或史志(historiography)都无法反映区域历史构成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取决于不同区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历史、自然、社会,等等。英国学者史密斯(Anthony Smith)指出,文化和认同的命运取决于内在固有的因素与外在的不寻常条件,而这种内在与外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同等的。[13](P3)换言之,文化变迁有其内在机制,其重要性绝不低于来自外部的影响。史密斯的这一论断使我们很容易回到“传统”的概念上来。按史密斯的逻辑,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自身也具有内在的驱动力。既然是“内在”的,那就是“固有”的;既是固有的,那不啻是“传承”的。英语里面代表过去的某种存在和余绪的heritage,可以至少有两个中译,它们是具有某种内在精神价值含义的“遗产”和“传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史密斯说的并不只是所谓的“变迁”而是“命运”。命运是变迁的方向,也是变迁的结果。如果这么来理解的话,那么,传统的意义就至关重要了。换言之,传统可以是抵御变迁的动力,但也可能与新的、外来的变迁动力出现“共谋”,或者产生互惠。但是,无论传统在变迁中扮演什么角色,推动它的都是韦伯(Max Weber)称之为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既定”(the given)秩序的信守,所以总是带有某种怀旧(nostalgia)的感伤。传统主义者坚持的是“既定”的东西并拒绝改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Amish)就是传统主义的极端之例,这些祖先来自德国的清教徒至今仍拒绝使用19世纪以来的任何现代科技产品,维持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这种传统主义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原则上的,它同在现代性刺激下出现的传统主义——如民族主义者的传统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民族主义话语里,“怀旧”的情绪往往宣泄在历史的叙述上;这种叙述总是与对乡土的讴歌和礼赞联系在一起。所以史密斯才说,自然景观和历史是民族主义叙事的载体。这或许是为什么那些被认为带有民族主义激情的作曲家,如肖邦、西贝柳斯、斯美塔那,以及拉赫马尼若夫等人总是在礼赞自己的国土山川,他们的作品可以让人感受到那种时而沉重,时而悲怆,时而热情似火的复杂情感。在过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寻找”和界定,就是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激情的激发下开始的。因此,在通往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地方”,或者“乡土”(homeland)俨然成为定义“民族”或“国家”之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是因为,宣称代表主体民众的民族国家必然要寻求“草根”来编织它的正当性表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民族主义运动都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
四、“申遗”与传统的再生产
今天,“地方”再度引人注目,并成为国际社会人文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出现这一现象的国际背景在逻辑上与20世纪初期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状况有些类似。如果说,当年的民族主义运动通过对“地方”和传统的强调与肯定的目的在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因此是为了对抗那些已经瓜分世界市场的霸权,那么,当今世界各地对地方和传统的重新重视则与全球化脱离不了关系。所不同的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对地方与传统的张扬,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反抗霸权的意义。市场的力量使得全球化语境里的地方——民族国家,与跨国资本流动的力量发生了“共谋”。在近些年来大量的学术出版物里,有关地方的各种讨论往往与全球化、跨国主义等现象联系起来,以求在更大的视野中理解地方对相关人类社区形成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人们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影响。
全球化使我们生活的星球成为所谓的“地球村”。资讯的发达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使所有的主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出现了某种主权缺失的现象,也使得原先遮蔽在民族国家屏障内的“地方”得以通过各种渠道为外界所认识。[6]几乎在所有国家所辖的区域,甚至区域之下的“地方”,都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自主与外界直接发生联系。费孝通先生在21世纪初期对珠江三角洲当地企业的走访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概念已经过时。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国际产业结构和劳务分工的变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地方在对外商贸上的自主性增强。各个地方急欲突出自我,力求在市场中占据主动,招商引资。按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被认可(recognition)或被重视是一种象征资本(symbolical capital),是一种以某些合理的要求表现出来,从而不易为人所察觉的权力,寻求的是来自他人的欣赏、尊重、敬意,以及提供其他服务等等。[14](P112~121)
这种突出“地方”的活动在中国显得十分醒目。如果把目前与保护传统为名的各级地方上所出现的“申遗”活动也考虑在内的话,这类活动在我们的国家大体上可以粗略地分为各有不同内容的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许多地方政府兴起了所谓“形象工程”是为其一。这个阶段持续了十多年(在许多地方,目前仍在继续),留给人们的印象主要反倒拆除“传统”——大量的老的建筑、街区被推倒为所谓能体现新的精神风貌的现代建筑让路。许多地方热衷于搞什么“标志性”建筑,说是要使这些建筑成为所谓的“地方的名片”或“城市的名片”。在福建泉州,许多存在了数百年的街道在景观上实现了毫无个性的“现代化”;全国的大部分城市的原有风貌正在迅速地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在江苏,南京原先的那种静谧温馨的气氛荡然无存。宁夏银川是人口不多的中等城市,但却为了迎接中央访问团的所谓“心连心”活动,兴建了与该市规模极不相称的城市广场;沿着广场还拓了一条宽度几乎可以起降波音747飞机、一眼望不到头的通衢大道。市井间对诸如此类的形象工程的称呼是“面子工程”,这实在是贴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这种工程后面那种“皇恩浩荡”的封建主义心态和官本位体制下所特有的那种只对上负责的心理残疾。
除了在争相向上邀功请赏的动机之外,许多地方的形象工程建设也与全球化有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的一些官员就意识到,如果能够让地方体现特色,必将能引起外界的关注,从而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由于泉州历史上曾有大量的外国穆斯林逗留当地从事海上贸易,许多人同当地妇女通婚并终老于此,从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因此,当有官员知道在《北京周报》上有伊朗专家的文章提及泉州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意义之后,即要求厦门大学的人类学者赴泉州展开调查,以发掘当地的伊斯兰历史和社会文化资源。伊朗专家的那篇文章提出,坐落于泉州东郊灵山的“圣墓”在伊斯兰世界很可能是继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和伊拉克的阿里清真寺之后的第三个穆斯林朝圣之所。显然,当初政府官员要求人类学者调查当地与伊斯兰有关的文化遗存与社区时,已经有很现实的考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泉州的地方叙事——无论是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就已以强调地方的文化多样性为主旋律,泉州之地也因此以保留有伊斯兰文化传统而声名远播。伊斯兰文化于是与南音等地方文化传统一起,成为泉州重要的地方名片。
地方政府带有利益追求的取向影响到了地方上的民众。随着越来越多的对地方上伊斯兰遗产的关注,当地回民群众也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了他们的认同建构运动。这些活动以重新确认他们的外国穆斯林祖先为主要形式,在他们的话语里,传统成了关键词。为了重新确认他们的穆斯林认同,有必要恢复据说曾经有过的传统。在这里,传统当然是有选择的。我们从居住在泉州陈埭和惠安百崎的丁姓和郭姓回民的族谱可知,他们的先祖确乎严格地实践伊斯兰信仰,如果要回复到祖先的生活那就意味着对伊斯兰重新皈依。这显然做不到。所以,今天,在这两个回民社区,我们所看到的伊斯兰传统更多的是一些外在的物质表现,以及通过陈列馆所进行的表达。这两个回民社区20世纪80年代晚期起,出现了多座带有异国风情的建筑。百崎是福建省唯一的回族民族乡,为了突出所谓的民族风格,当地的公共建筑,如乡政府行政大楼、医院、学校等,在建筑表现(architectural representation)上都追求西亚的伊斯兰国家的建筑风格——除了在建筑上加上某些异域装饰之外,都在屋顶上加上穹顶。乡政府的行政大楼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除了巨大的橘黄色的穹顶之外,大门和窗框都采用了洋葱状的弧形设计。整幢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清真寺。尽管当地回民并不认可这些建筑,但在当地地方官员的眼里,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设计反映的是当地回民的伊斯兰传统。[15](P43~61)[5]
这种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来自不同文化的成分来强调自己族群的文化特定性,实质上是传统的再创造。传统的再创造还包括为了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而对地方和群体自身的文化历史遗产添加一些有意义的成分。传统再创造实际上在传统的承继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经历了再创造的传统传到了下一代,就成为既定的了。我们目前的许多被认为是传统的东西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旗袍现在被视为中国的传统服饰,它的原型来自满清旗人,但原来并没有腰身设计。现今的所谓“唐装”也是传统再创造的例子,其原型——汉装,也不是汉族原有,而垫肩的设计则与我们的传统服饰毫无关系。换言之,这些今天被许多人所认可的传统实际上是后人发明、创造,或再创造出来的。但如果说它们是从无中生有,却也不尽然,在发明、创造,或再创造它们的过程中,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与外来的元素进行组合,或者,传统的元素被重新组合。今天出现在回族地区的伊斯兰建筑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构成回回民族叙事的许多元素,如宗教、外国穆斯林祖先,等等,都在设计中被考虑进来,并且还将当今非伊斯兰社会对伊斯兰世界的想象因素增加了进来。尽管在外在形式上,人们很难认为那些建筑是中国回族的传统,
突出地方的各种项目与活动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最醒目之处在于对地方传统和文化遗产的重新确认与强调。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热衷于寻找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认可的地方传统和文化遗产。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种情形的出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纪初年提出的宣言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样的宣言的出台则与全球化所带来的隐忧直接相关。该组织关于保护音乐多样性的文件有这样一段话:
有许多因素已经威胁到音乐多样性。尤其是通过强大的市场运作支持,西方制造的风格大致相同的流行音乐与全球化浪潮一起席卷全球,这些音乐能够取代各个地方的民间音乐传统。从乡村生活环境孕育出来的地方音乐传统会因为乡村生活的变迁,或随着乡村人口迁往城市而削弱。许多国家的政府在面对国内的民族多样性时,也会为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寻求将它们同化以确立单一的文化认同。[16]
笔者认为,西方文化实际上难以摧毁不同文化传统。它倒可能与某些传统的元素结合而产生新的传统。文化变迁重要的外在动力是文化接触,它直接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采借。今天,美国的流行文化就包含了美国黑人的街头文化和英国蓝领工人社区文化;而整个西方流行音乐实际上掺杂了大量的非洲音乐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个“再西方化”的过程。而且,这种过程从海外殖民地开拓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今天,除了北美国家之外,主要的西方国家也都接纳了大量来自原来的殖民地的移民,这些移民为西方文化的多元化注进了血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历史条件,才使西方的知识界率先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多样性的主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保护地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言就是这样的主张的结果,但它更多地强调了原生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就是说,它所希望的是保护文化原有的风貌。
毫无疑问,这样的主张是有价值的,至少它提请了人们对迅速流逝的一些非物质、口头文化遗产的重视;对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但毋庸讳言,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地方的功利追求。对此,国内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批评,对所谓纳西古乐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有些学者就物质文化保护所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阮仪三就指出,“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为了参观”。[17]可见,许多地方已经把文化遗产当作可以生财的资源进行发掘。这种情形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常见。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经常把保护和发掘文化遗产同发展旅游业的设想结合在一起,期望文化遗产可以转化成为丰厚的旅游资源。申报地方的文化遗产可以获得来自上级的重视,这也应当是如此之多的地方热衷于“申遗”的原因。
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所申报的遗产的“本真”(authenticity)如何。任何遗产都被声称来自过去,但问题的要害在于,你是如何去解读它。例如,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有人认为它充分反映出阿拉伯文化和中原文化交融的特点。这样的说法不知其根据何在。这种用当今民族国家叙事来作为对文化遗产定调的做法,在本质上仍然是对多样性的消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把认可的遗产冠于“世界”,目的就在于强调这些遗产属于全人类,它既属于某一国家又属于全世界。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
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a.口头传统和表述;b.表演艺术;c.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传统的手工艺技能。[18]
在这一定义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可使有关的群体或者团体滋生认同感和历史感,但是,正因为它们来自过去,尽管经过各代人呵护而不断得以创新,它们的历史性(historicity)不应被随便界定。历史性是后人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裁定,它并不总是符合历史的本真。任何试图以今天的国家认同叙事为基准去解释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人物、事件,并为之定性,都不符合历史的本真。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面对“申遗”和传统再创造问题所应注意的。
五、结语
“申遗”在当下已然成为一种现象。然而,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以及支持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却鲜有人进行讨论。本文认为,“申遗”现象与全球化直接相关,在逻辑和方式上,“申遗”与认同建构运动是一样的,彼此都是利用历史和文化资源来突出自我。换言之,认同,一般说来,必须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追踪来达到对“他者”的排斥来实现,“申遗”在某种程度上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但是它的目的并不在于激起地方民众的认同感,而在于通过发掘出地方上的历史和文化资源来刻画地方;通过给予这些资源中的某些东西以某种权威性的认可,来确认地方对被认可之物的权威性解读。这样,对“申遗”的讨论必然要落实到对“传统”和“地方”的解释和理解上来。而从事“申遗”的机构或者地方的主要工作,就在于使他们对某种地方文化传统的解释具有权威性;对这种“权威”的拥有,从长程的眼光看,将或迟或早对地方的进一步开拓与发展带来某些积极的影响。然而,在通向拥有这种权威性解读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解读与被解读之物的本真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而对这种“紧张”的理解,有必要就“申遗”的关键词,如“传统”、“地方”,以及它们的对应词等进行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传统”,以及经常被用于代表传统的“地方”,在社会文本的意义上,是现代性和造物,被用来衬托“现代”与“文明”。概言之,诸如“传统”或者“地方”是“过去”的隐喻和时间、空间的表现形式。
本文从讨论传统与地方这类概念发展的社会史出发,试图理解这些“过去”隐喻为什么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得以再现和如何再现。笔者认为,全球化本身无法带来同质性的文化却可能导致文化多样性的生产和再创造。因此,如果说,传统是现代性的对应物或“他者”,那么,在当下的语境里,地方必然与全球化互为“他者”。所不同的是,地方是“有意识”地与全球化进行互构,它必须通过全球化来显现自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申遗”成为这么一种互构的途径。
注释:
①祭黄帝陵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之一。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