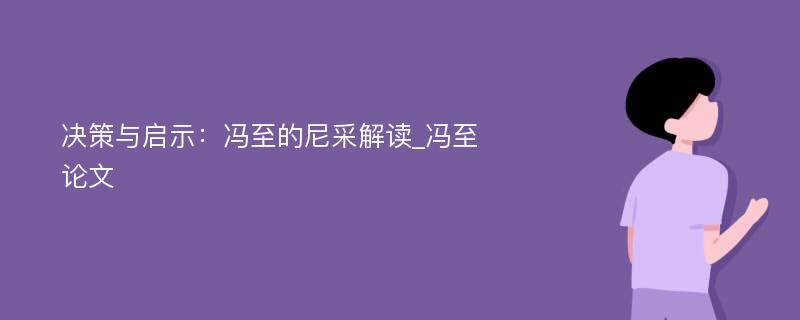
决断与启蒙:冯至的尼采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决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2-110-4
一、尼采情结
20世纪20-40年代,诗人、学者冯至多次介绍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F.Nietzsche)的思想、文体,征引尼采的语句,翻译尼采的诗歌,表现出对尼采的浓厚兴趣。
冯至最早接触尼采著作是在1924年。这一年10月3日,还是北京大学德语系二年纪学生的他在给好友杨晦的信中说:“我回到北京,无意中,买到了几本好书,‘Zarathustra’、希腊传说,一本浪漫时代非常好的小说,荷马字典,以上都是德文的。”[1](P25~26)Zarathustra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930年10月留学德国之后,冯至不仅阅读了尼采更多的著作,还在海德堡大学听过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关于尼采的系列讲座。后者于1935年将这些讲座以Nietzshe-Einführung in das Verst? 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尼采哲学思想引论;中译本题为《尼采——其人其说》)为题出版。他在《谈读尼采》(1939)里提到“我前几年在海岱山(通译海德堡)读尼采”一事,并表示自己向读者推荐的读尼采之法一半来自“那里的雅斯贝斯教授所警戒”。[2](P284)1939-1945年,在西南联大任德语教授的冯至先后发表《谈读尼采(一封信)》(载《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7期)、《〈萨拉图斯特〉的文体》(载《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24期)与《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载《自由论坛周刊》1945年第20期)等3篇文章,系统介绍尼采的思想与文体。此外,他在《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1942)、《批评与论战》(1948)等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尼采。
作为诗人,冯至对尼采的诗歌情有独钟。1937年初,任教于上海同济大学的他翻译了尼采的11首诗,同年以“尼采诗钞”为题分别发表在该年度的《文学》8卷1期与《译文》新3卷3期上(前者6首,后者5首)。1987年他在《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中回忆说:“在四十年前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歌德、里尔克、尼采的著作也曾给我不少的鼓励。那时中国文化界对德国文学还相当生疏,我起始试译歌德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席勒的《审美书简》,尼采、里尔克的诗”。[3](P193)
二、理性阐释
冯至对尼采思想与文体的介绍与阐释集中在《谈读尼采》、《〈萨拉图斯特〉的文体》与《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等3篇文章里。
《谈读尼采》是给一位年轻尼采迷的回信,主旨是介绍阅读尼采著作的方法。首先,冯至认为尼采著作的读者“最容易犯”割裂与盲从的毛病。他告诫那位青年:尼采著作中“充满了相反的意见”,“当你想引证尼采的一句话时,你就要提防在他另一部或另一页的书上有一句意义相反的话在等待你的反对者来引用。……最好是把他对于某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聚集起,把不同的来比较,追溯这些意见不同的原因,同时不要忘却整体。……不要把他的著作任意地割裂。”[2](P282)他还表示自己的担心:“怕你把尼采当作教主,看成先知”,而事实上,“尼采不希望读者成为他的信徒。……他不但让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而且教我们在读尼采的时候处处要防备他:‘我要唤起对我最深的猜疑。’……尼采不要求信徒,他最怕有一天被人称为圣者。”[2](P281-282)接着,冯至指出,要真正读懂尼采的书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不顾及他的生活”。尼采的生活经历很特别,“他没有家,没有职业,没有团体……他是一个永久的漫游人,在人生万象中他是一个旁观者:人类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件不映入他明朗的眼中。他常常患病,病使他的思考深沉。”[2](293)即是说,尼采的“漫游人”和“旁观者”生活经历使他遍览人生万象、深沉思考人生问题。二是“要忌讳执着”。冯至指出:“尼采在希腊文化里发现了Dionysos(即酒神)的精神,而为舞蹈唱过赞歌。舞蹈在他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流动的人生。……人生如此;他的书,也无处不在流动”。[2](P284)“执着”是指静止的眼光和生吞活剥的态度。冯至认为,惟有避免“执着”,才能把捉尼采思想的活灵魂。
《〈萨拉图斯特拉〉的文体》讨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体特点。冯至首先指出,翻译该书“不很容易”,“意义上没有错误,并不能说是对于《萨拉图斯特拉》译者的最后要求;把它特殊的文体,下一番文字上的功夫,重新表现出来,才算是我们理想的译品”。[2](P285)那么,此书的文体“特殊”在何处呢?冯至引用尼采的原话:“我的文体是一种舞蹈;一种各样均称的游戏,又是一种对于这些均称的超脱和嘲讽”,然后指出:“他的文体有时均称,有时又要打破这均称,正如美妙的舞蹈一般,时而齐整,时而散乱,更由于母音的选择使这舞蹈得到和谐的伴奏”。[2](P285-286)冯至在分析3个具体例子后指出,尼采的“舞蹈文体”包括3项内容:一是音乐性:“尼采运用母音,这样自如,确是超越过语言的界限,达到音乐的化境”;[2](P286-287)二是舞蹈性:“意义相反、韵脚相谐的骈句,在《萨拉图斯特拉》里层出不穷。我们会想到双人的舞蹈,一个黑衣人和一个白衣人,或是一男一女,伴着和谐的音乐,踏着齐整的步奏,于相反中求得相成,矛盾中求得谐和”;[2](P287)三是游戏性:“文字到了尼采的手里,正如一块块的积木一般,任他游戏的心肠,堆聚出多少新鲜的花样。”[2](P288)此外,冯至特别提到此书文体与《圣经》德译本文体的类似:“在《萨拉图斯特拉》里我们处处见到的是路德圣经的文法,路德圣经的语气。我们若是读过《旧约》里的诗篇……再读《萨拉图斯特拉》,便不难择出许多类似的句子。”[2](P288)
《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曾被冯至作为“学术精华”收入《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此文讨论尼采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3个推测。第一个推测是关于“德谟克拉西(民主)的道路”的。尼采预测民主在未来有3种命运:“第一个可能性是一个有秩序的、分配均匀的世界,各国家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在这联盟里一切问题都将要按照理性的原则解决。……这个将来的德谟克拉西‘要尽其可能地创造人格的独立’,并且使世上没有与这个独立为敌的事:贫穷、富有、政党。”“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社会主义征服了国家。如果这样,社会主义就要努力于‘国家势力的丰满’与‘一切形式上的个人的消灭’。”“第三个可能性……也可能由此而消灭国家的组织。”[2](P250-251)第二个推测是关于“各国民族在世界政治上的发展”的。冯至用尼采的话概括其预测:“美国人也许是一个将来的世界权威”,英国已没有“充足的强力,再继续五十年演他的老角色”,“法国是意志衰损了”,“俄国人走进文化世界是下世纪(20世纪)里的一个重要事件”,“德国人还不是什么,但他们将要成为一些什么。”[2](P251-252)第三个推测是关于“人的精神本质的改变”的。冯至指出:“对于将来的人类,尼采有一段话最使人感到惊奇:‘人类在新的世纪里也许由于支配自然而获得更多的力,比他所能消耗的多……’但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和知识的扩充,也会产生这样的危险:文化在它的方法上沦亡。如果科学种下许多许多不愉快的因素,人为了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又不得不求助于形而上学与宗教,到那时生活也许会感到很大的失望。他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科学凋零,人又回到野蛮状态;人类必须又重新开始’。”[2](P252)这段话表明,尼采已预感到科学与文化、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内在张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文信仰迷失的可能性。
在上述文章里,冯至还扼要提到尼采的其他思想主张。如《谈读尼采》提及尼采反基督教、反欧洲现代文明、“超人”、“向力的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可译强力意志、权力意志)。[2](P283)如《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称“超人”在尼采那里“不过是一个理想,一个象征”,[2](P252)说尼采标举的“战争”是广义的,“最大的规模里是学术的,同时也是民间的”,它争取的统治权“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思想的”。[2](P251)这些介绍虽然简略,但精当、到位。
三、诗性阐释
冯至用诗歌来书写尼采的情绪与思想,不妨称为“诗性阐释”。
首先,冯至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作里常常叙写尼采式漂泊母题,抒发孤独情绪。鲁迅曾经指出,沉钟社时期的冯至常常发表“幽婉的名篇”,因为他的心情“热烈”中夹杂“悲凉”。[4](P5-6)如冯至的《蛇》(1927)以蛇为意象,表达了一种绵长、挥之不去的孤独心绪:“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静静地没有言语。《吹箫人的故事》(1927)塑造了一个“走过无数的市廛”、“走过无数的村镇”的“流浪无归的青年”吹箫人形象。《北游》(1929)描绘“我”这个“远方的行客”形象。
冯至描述的漂泊母题及其传达的孤独情绪受到尼采身世与著述的影响。冯至知道尼采是一个“从这里迁到那里,从那里迁到这里”的“永久的漫游人”,也熟悉尼采那部描写“漫游人”查拉图斯特拉遭遇与思想的名著。郭沫若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于孤独的悲哀与疾病的困厄中乃凝集其心血于雅言的结晶。[5](P2)该书《漫游者》(Der Wanderer)一章中,查拉图斯特拉宣称自己的“命运就是漫游和攀登”,“必须走最艰难的道路”,“必须开始最孤独的漫游”。[6](P403)尼采也创作了一些以漂泊为母题、以流浪者为主人公的诗歌,冯至就翻译过他的《旅人》、《怜悯赠答》。冯至笔下的“吹箫人”、“远方的行客”之类形象,就有尼采《怜悯赠答》里那位“走向无言枯冷的沙漠被惩罚于冬日的行程的流浪者[7](P384-386)的影子。
其次,冯至在自己的诗歌里表达尼采式生命观,抒写生命的狂欢、向上与抗争意识。他曾多次说过自己的诗歌是生命意识的结晶。在《〈北游及其他〉序》(1929)里,冯至说该诗集是“从我生命里培养出来的小小的花朵”[9](P252)、“从生命里蒸发出来的一点可怜的东西”[9](P255)。在《〈十四行集〉序》(1948)里,诗人又说自己抒写的是对“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人、事、物的激情[9](P257)。他20年代的一些诗篇就描写了生命的狂欢,如《夜半》就是如此。
到了40年代的《十四行集》,这种形而下的生命冲动逐渐升华为形而上的生命哲学,既揭示生命的短暂与永恒、渺小与伟大之间的辨证关系,又融生命体认与“路的哲学”于一体,表达积极向上、奋勇抗争的生命观。如第1首《我们准备着》通过彗星的倏忽来去、狂风的乍起乍歇尤其是“那些小昆虫,/它们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表达了生命的短暂与永恒之间的辩证法第13首《歌德》通过飞蛾扑火、爬蛇蜕皮以求新生的经历揭示:歌德名言“死和变”“道破一切生的意义”。第4首《鼠曲草》则阐述生命的渺小与伟大的辨证关系。再如第17首《原野的小路》、第16首《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由原野上的道路联想到践踏出这道路的人的生命。而第9首《给一个战士》塑造了一位宛如“古代的英雄”的“战士”形象,他“超越”“堕落的城中”“堕落的子孙”,追求“向上”的精神与“旷远”的境界。
冯至所宣扬的狂欢、向上与抗争的生命意识也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多次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扬生命的狂欢:“我的道德是跳舞者的道德”,“我常常舞动双脚在狂喜中跳跃”,“我常常欢笑”。[6](P531)冯至也非常熟悉尼采的“路的哲学”。他在《谈读尼采》里引述过尼采“你只要忠实地跟随你自己吧:——那你就是随从我了”、“这就是我的路——哪里是你们的呢?——我这样回答那些向我问路的人”的原话。[2](P282)。德国汉学家顾彬(W.Kubin)认为“冯至十四行诗的一个重心,是挖掘鲁迅关于路的哲学”的断言[10](P190)有些生硬、武断,因为冯至完全可以通过自己阅读尼采著作而接受“路的哲学”。至于“战士”品格,则与冯至翻译过的尼采《最后的意志》一诗所表现的那位战士“最后的意志”相通。[8](P392-393)
四、决断意识
“决断”是冯至1941年在阅读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S.Kierkegaard)《一个文学的评议》(1846)一文时提取出的概念。基尔克郭尔对19世纪中期的欧洲感叹:“我们的时代根本是中庸的、考虑的、没有深情的、在兴奋中沸腾一下,随后又在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凝滞下去的时代。……在考虑中的人不会感到‘决断’的需要,也就是感不到生的意义”。[2](P244)冯至在《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1942)里以基尔克郭尔式语调写道:“在一个没有深情、只有考虑的时代里,多少生存中根本的问题都被遗弃了!……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谁还能有所‘决断’呢?……要克服一切内外的考虑,勇于‘决断’,又拾起那些已经失落的严肃的冲突、沉重的问题——这是基尔克郭尔对于他的时代、他的后世的呼吁。”[2](P248)此文的写作年代正是中国军民对日作战最艰难的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对前途感到迷惘,整日处于观望与“考虑”之中,冯至想用这篇文章来警示他们摆脱作壁上观的陋习,呼吁他们早日“决断”,积极投身抗战洪流。
冯至后来在《批评与论战》(1948)一文里又将基尔克郭尔的“决断”意识深化为“论战”意识。所谓“论战”意识,就是“负有宣示这个真理,坚持这个真理,彻底攻击与这真理相反的事物的责任”、“负担这个战斗的命运,热情饱满,思想充沛,同时对人类有强烈的爱”,[11](P122)就是“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而不肯放弃他们所信仰的真理”[11](P124)。
“决断”概念虽然是从基尔克郭尔那里提取出的,但在冯至看来,尼采及其思想主张更是“决断”意识的重要源头。他曾经指出:尼采勇敢地作出了“绝对地否定基督教”的“决断”;[2](P244)尼采具有强烈的“论战”意识,他“对于德国的教育、哲学和整个的基督教”猛烈攻击,“他否定一向被认为是好人的人们和一向被认为是好的道德的道德,他重估一切的价值”[11](P126),并把这些视为自己宿命,所以自豪地向世人解释“我为什么是一个命运”[11](P122)。不仅于此,冯至还以尼采为例说明“决断”意识形成的前提是保持自立与超脱的态度。他从尼采身上拈出“正直”(Redlichkeit)这一品格:“当尼采把许多道德观念重新估量而加以否定时,他却认定一种道德基本是确凿不可移的:正直。在他看来,我们只需要纯洁,不管是哲人也好,或是舞台上的一个小丑也好。这种对于纯洁的要求,便是尼采所谓的正直。只有心怀正直的人,才能放开眼光,广看万象,而万象也赤裸裸地映入他的眼中。”[2](P283-284)即是说,惟有“正直”、“纯洁”,才能“放开眼光,广看万象”、洞察人生与社会!而尼采的漂泊、流浪甚至患病恰好有助于“他对于人生下犀利的批评,有独到的解释”。[2](P283)
冯至本人对尼采的阐释正体现出了鲜明的“决断”意识。一方面,他推崇尼采,称尼采为“近百年来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其著作常使读者“感到一种新的刺激,新的启发,新的战栗”;[2](P281)认为尼采“具有畸人特有的慧眼透视一切,挖掘人的灵魂到了最深密的地方,使一切现成的事物产生不安,发生动摇”。[2](P242)他也为尼采受人误解鸣不平:“一部分被人‘拿去’,一部分被人‘污毁’,而整个的尼采遭了‘冒渎’”。[2](P282)他针对中国知识界认定尼采是“法西斯的代言者”、“革命运动的明目张胆的反对者”明确指出:“在他的全集里边,并没有‘德意志能够支配世界’的主张”[2](P250)。另一方面,他对尼采又有所保留。他说:“尼采是一片奇异的‘山水’,一夜的风雨,启发我们,警醒我们,而不是一条道路引我们到一座圣地。”[2](P284)即是说,尼采思想可以引人遐想与思考,但不是到达圣地的现成道路。他也明确承认尼采“有些推测当然可能是错误的”。[2](P250)如对尼采认为社会主义“要努力于‘国家势力的丰满’”,就必然导致“一切形式上的个人的消灭”,[2](P251)就没有附和。
五、启蒙诉求
决断主要是个体的明辨是非,体现的是个体的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启蒙则主要是为众人去蔽,向众人揭示真相、宣示真理。
冯至的尼采阐释有着强烈的启蒙冲动。他总是不忘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向世人揭示真相、宣示真理。当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解放区流行的《辩证法唯物论辞典》(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米定.易希金柯著)断定尼采是“一般革命运动和劳工运动的明目张胆的反对者”、“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时,冯至就站出来告诉读者:“这里边所说的前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情形,是正确的;但是说尼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则未免失当。”[2](P249)冯至陈述这一观点的1945年,正是尼采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法西斯化的时候。当时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主流也纷纷将尼采与纳粹、法西斯挂钩。张子斋《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与优生学》(1941)、曹和仁《权力意志的流毒》(1942)等就不仅抨击战国策派,也涂黑尼采思想。而他们据以批驳战国策派与尼采思想的材料多取自当时被译介过来的两位国外学者的著述,即L.凯迪的《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申谷译,1939年11月《理论与实践》第l卷第1期)与勃伦蒂涅尔的《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批判》(段洛夫译,上海潮锋出版社1941年版)。唐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学术界普遍流行的却是勃伦蒂涅尔的批判的见解,等到1941年他的《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从日文转译过来,尼采哲学等于法西斯主义,尼采是法西斯的预言者和代言人等等,也就成为定论,压倒所有不同的意见。”[12](P2)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将尼采视为“法西斯代言人”或“战争狂人”就是凸显“强横的尼采”形象,乃是一种彻底的“误解”(misinterpret)。[13](P79-80)冯至在当时一边倒的情形下指出真相,体现了他强烈的启蒙诉求。
尽管冯至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不仅错批了胡适,甚至称尼采是“德国最反动的哲学家”,[14]但那完全是在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说的违心话。冯至在新时期又发出欣赏尼采的“先声”。他在1983年5月5日改定的《诗文自选琐记》里既认为尼采用彼拉多指称耶酥的“看啊,怎样一个人!”一语作自传标题显示了“尼采式的傲慢”,又坦承自己选辑诗文时“越来越想到彼拉多的那句话:‘看啊,怎样一个人!’”。[9](P3)表面上的保留掩饰不住实质的欣赏。这种对尼采的欣赏态度比张汝沦发表《一个被误解的哲学家——尼采学说之我见》(1985)、周红发表《尼采的形象是怎样被扭曲的》(1986)以恢复尼采的本来面目要早两三年。
冯至的尼采阐释深受对尼采哲学持公允之论的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如他明确表示雅氏“论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2](P249),并模仿雅氏“针对那些纳粹分子”“去唤醒思想界”[15](P1)的做法呼吁中国民众正确认识尼采及其思想。
阿拉伯裔美籍学者萨义德(E.W.Said)曾经宣称:“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可译为陈词滥调、套话)和化约式的类别。”[16](P2)“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16](P25)在萨义德看来,不盲从“刻板印象”、“简单的处方”与“陈腔滥调”、坚守“批评意识”,乃是知识分子的追求、操守;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先行者,其宿命就是启蒙民众、引领潮流。萨义德认为,即使在启蒙与救亡发生矛盾时知识分子也不能背弃启蒙的诺言:“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使得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评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16](P39)冯至坚持拂去覆盖在尼采与尼采思想躯体上的灰尘,消除一切对尼采的误解与摸黑,而对尼采作尽量客观、公允的介绍与阐释,正是履行知识分子的启蒙诺言。
因为有启蒙诉求,冯至才会告诉人们尼采不仅不是法西斯思想的先驱,而恰恰是“一个人类的关心者,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段不涉及人的问题”;[2](P253)因为有启蒙诉求,冯至才会告诉人们应该怎样阅读尼采、怎样理解尼采。
标签:冯至论文; 尼采论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