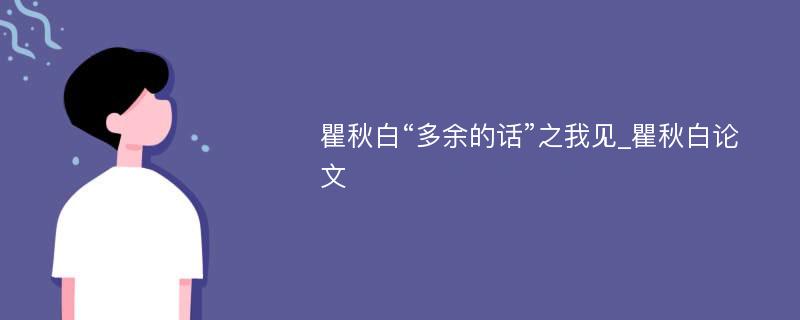
瞿秋白《多余的话》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多余论文,瞿秋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瞿秋白去世前二十多天,曾写下《多余的话》一文。
《多余的话》说:“当我出席政治会议……,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都觉得很麻烦”。“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这不是很逍遥的吗?”。[1]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向人们诉说了自己平时总是厌倦政治。瞿秋白类似这样的诉说,贯串于《多余的话》的始终,成为《多余的话》的主要内容。
那么,该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这种诉说?不言而喻,要想实事求是地评价瞿秋白的这种诉说,首先就得准确体会他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应当认为,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不至于是“自暴自弃”“自嘲自贬的自我否定”。这是为什么?其理由是:
第一,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始终坚定不移信仰马克思主义。《多余的话》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智上“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也就是说,在理智上“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2]
第二,他的厌倦政治,只不过是他小时候就开始出现,他从事无产阶级政治工作之前就已经潜伏的自发心态。《多余的话》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者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又说:1917年春,“我……,孑然一身跑到北京……。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对于考进俄文专修馆,只“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3]“不知怎样”这四个字,道出了他的厌倦政治心态是不自觉中自发产生的。
第三,他曾用自我压制的方法,跟自己潜伏的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进行过积极的自我思想斗争。《多余的话》说: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无产阶级意识与绅士意识“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4]所谓“绅士意识”,其中包含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也就是说,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是“绅士意识”的一种成分。[5]
第四,他被俘后,还是念念不忘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念念不忘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多余的话》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站自己的脚步”。[6]
第五,他进行这种诉说时,依然肯定自己的工作成绩。《多余的话》说:“从1923到1927年,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这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进步”——显著的成绩。[7]
第六,他进行这种诉说后,觉得新生的、斗争的、勇敢的事物更加美好了。《多余的话》在结尾部分说:“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8]
第七,他进行这种诉说,是需要勇气的,对得起他亲人的。《多余的话》说:对于潜伏着绅士意识,“我自己早已发觉……;但是……,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露一点口风……,没有这样的勇气”。对此,现在“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对不起我这个亲人”。[9]“隐忍”二字,道出了他早就想说,但由于当时缺乏勇气而没有说的隐衷。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告诉人们:他早就想向人们诉说自己潜伏着绅士意识,只不过是当时由于缺乏勇气才没有进行这种诉说。他后来觉得以往没有向他爱人杨之华彻底进行这种诉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亲人。这从反面上表明:他进行这种诉说,是需要勇气的,对得起他亲人的。
那么,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看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进行这种诉说的思想前提。
第一,他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曾出现过消极倦怠;他被敌人俘获后,对自己的这种消极倦怠感到惭愧。《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一切工作只要交待得过去就算了”。也就是说,对于政治问题“我……不加思索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10]显然,瞿秋白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曾出现过消极倦怠。
《多余的话》竣稿后六天——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曾写信对郭沫若说:“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11]无疑,瞿秋白被俘后,对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
瞿秋白对此感到惭愧,并不偶然。因为1931年初之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肆意发展,致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最后致使革命濒临十分危险的境地。瞿秋白在这革命危急关头,却在政治斗争上消极倦怠了——在党内,却没有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进行斗争了。[12]严格地说,他的这种消极倦怠,对革命间接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之后的“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这种责任比起“以前几年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13]既然瞿秋白认识到他于1931年初之后没有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努力奋斗——没有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进行斗争的责任,比起以前几年他本身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责任,以及他间接的负着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责任,[14]都更加加重了;那么,他对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就不偶然了。
第二,他曾认为他潜伏的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是导致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的一种自我原因。《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就开始政治斗争上“我的脱离队伍”。之所以出现政治斗争上“我的脱离队伍……,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15]
第三,他还认为自己的错误,必须得到深刻无情的揭发。《多余的话》说:“1929年秋……,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16]认为自己的错误没有得到深刻无情揭发是一种不幸,当然也就是认为自己的错误必须得到无情揭发。这种认识,体现于这里援引的他这段话之外,还体现了他以往的许多实际表现中。
可想而知,瞿秋白在以上这种思想前提下进行这种诉说,其动机不是别的,而是他想用自我揭发潜伏的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让自己潜伏的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曝光的方式,来向人们自我检讨导致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的一种自我原因。
瞿秋白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的消极倦怠,主要表现了他没有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斗争。因此,他自我检讨导致自己于此期间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的自我原因,主要就是自我检讨导致自己于此期间没有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斗争的自我原因。[17]
二
毋庸置疑,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深寓着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强烈不满;他的这种诉说,有着值得肯定的积极因素。
然而,文革后发表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却认为:瞿秋白的这种诉说,“集中地反映了”他“思想中过多的灰暗、伤感、颓唐、消沉的情调”。[18]也是文革后发表的《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一文也认为:瞿秋白的这种诉说,“集中地反映出”他“思想上的动摇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反映出”他“在对待革命、对待自己、对待生和死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有严重错误”。[19]
《重评》、《全评》的这种观点,主要建立在他们以下这些论述基础上。这里拟就他们以下的这些论述,逐一作些商榷。
《重评》说:瞿秋白被敌人俘获后,“感到彻底改造自己绅士阶级思想的机会已经不会有了,因而在‘多余的话’中,他放纵自己思想中颓唐的一面,甚至不惜违心地自暴自弃、自嘲自污”。[20]
人们知道,一个人自我改造思想是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只要他有决心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瞿秋白既然把改造自己绅士阶级思想看成是一种机会,那么他怎么会感到这种机会已经不会有了呢?他撰写《多余的话》自我检讨潜伏的绅士意识,岂不就是这种机会吗?再说,他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表明过,他曾感到这种机会已经不会有了吧。
《重评》又说:瞿秋白“没有搞过工农运动,也没有搞过军事斗争,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太少了”。“于是,当他被敌人俘获,身居囚室,回首往事,他的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绅士意识便强烈地表现出来”。[21]
人们还知道,没有搞过工农运动与军事斗争,未必就一定不能彻底改造绅士意识。何况瞿秋白曾经搞过工农运动与军事斗争。事实表明,瞿秋白曾参与领导制定党的“八七”会议上通过的工农运动方针与军事斗争决策,还曾参与领导我们党发动“八七”会议后一段时间的工农运动与军事斗争。参与领导制定工农运动方针与军事斗争决策,参与领导我们党发动工农运动与军事斗争,难道不能算是搞工农运动与军事斗争吗?
《重评》还说:瞿秋白在“灰暗、伤感、低沉、颓唐的情绪”“支配下”,在《多余的话》中“说了不少的过头话”。[22]《重评》为论证他的这种观点,被援引作为首例的是这段话:
“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23]
这是过头话吗?只要仔细琢磨《多余的话》就会体会出,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叛徒”,是指他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的消极倦怠。[24]这段《多余的话》的意思是:
瞿秋白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狱中慷慨激昂而死,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不过,现在他这样而死,只能算是革命“罪人”避难就易的一种装模作样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31年初之后,在革命事业极其需要他挺身而出去阻止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肆意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却畏难而在政治斗争上消极倦怠了。严格地说,他的这种消极倦怠间接地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莫大损失——他间接地成了革命“罪人”。虽然他现在这样而死很壮烈,但是无法以此来挽回给革命事业所造成的那种莫大损失。因此现在他这样而死,只能算是革命“罪人”避难就易的一种装模作样而已。他不敢这样装模作样地来骗取烈士称号。因为让革命同志把革命“罪人”误认为烈士,是大大不应该的。他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这段《多余的话》,分明是流露了瞿秋白对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并不是什么“过头话”。至于被《重评》援引作为论证所谓《多余的话》“说了不少的过头话”其它例子,[25]都是流露了瞿秋白的这种惭愧感,都不是什么“过头话”。
《全评》说:瞿秋白撰写《多余的话》时,“思想上却由于出狱无望而更为消极”。[26]
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瞿秋白撰写《多余的话》时,分明是已经充分做好了在敌人狱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就义的思想准备,怎么能说他思想上“消极”呢?
《多余的话》说:“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指他就义后的尸体——笔者按),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27]
这表明瞿秋白撰写《多余的话》时,已经充分做好了在敌人狱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就义的思想准备。《多余的话》竣稿后二十天左右——1935年6月12日前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两名中统高层特务,专程从南京赶到福建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当这两名特务在瞿秋白跟前夸奖叛徒顾顺章叛变为识时务时,瞿秋白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们认为他这样作是识时务,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28]是年6月18日,瞿秋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一天,他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走上刑场后,他“向在场的人作了十多分钟的演讲,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是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世界,使人人都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他相信这个理想迟早一定会实现,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29]等等。演讲后,他神态自若地等待刽子手枪杀。在刽子手扳动枪栓前的一刹那,他回头向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30]说完,饮弹身殒。这表明瞿秋白原先已经充分做好在敌人狱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就义的思想准备,是真实的。
《全评》又说:瞿秋白《偶成——集唐人句》绝笔诗“悲观的情调”,“印证”出《多余的话》“思想上的灰暗是主要的”。[31]
《全评》连瞿秋白的绝笔诗都理解成情调“悲观”,这就难怪他们会认为《多余的话》“思想上的灰暗是主要的”。其实,瞿秋白的绝笔诗思想健康,是无可非议的(参看笔者《评瞿秋白绝笔诗》一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全评》还说:瞿秋白“把投身于革命斗争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说成“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这“真象是一个‘忏悔的战士’的死前自白”。[32]
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是这样说的:“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33]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分明是把自己带着“文人结习”——潜伏着绅士意识投身革命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说成是“历史的误会”;并不把自己投身于革命斗争并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说成是“历史的误会”。瞿秋白“历史的误会”的说法,是对自己潜伏着绅士意识进行无情的自我嘲讽。这种嘲讽,流露了他对自己潜伏的绅士意识的鄙视与憎恶。
由是观之,《重评》、《全评》以上的这些论述,都很难令人置信。因此,他们主要建立在以上这些论述基础上,认为瞿秋白的这种诉说情调消沉,或者思想动摇、意志衰退的观点,也就很难令人置信了。
注释:
[1]瞿秋白《多余的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永祥编《瞿秋白年谱》,第145页。
[2]《瞿秋白年谱》。
[3]《瞿秋白年谱》。
[4]《瞿秋白年谱》。
[5]《瞿秋白年谱》。
[6]《瞿秋白年谱》。
[7]《瞿秋白年谱》。
[8]《瞿秋白年谱》。
[9]《瞿秋白年谱》。
[10]《瞿秋白年谱》。
[11]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致郭沫若信》。
[12]《瞿秋白年谱》。
[13]《瞿秋白年谱》。
[14]《瞿秋白年谱》。
[15]《瞿秋白年谱》。
[16]《瞿秋白年谱》。
[17]《瞿秋白年谱》。
[18]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19]王维礼·杜文君《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0、21页。
[20]《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21]《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4页。
[22]《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2页。
[23]《重评》援引的,是这段《多余的话》中的某几句话(《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24]《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33页。
[25]《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0页。
[26]《瞿秋白年谱》。
[27]转引孙克悠《瞿秋白之被捕与就义》,《人民日报》1985年7月26日。
[28]宋希濂《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经过》。《革命资料》第二辑,第205页。
[29]《瞿秋白毕命纪》,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
[30]《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1页。
[31]《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20页。
[32]《瞿秋白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