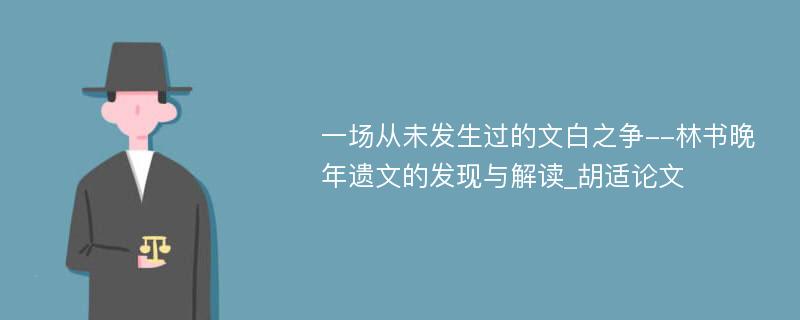
一场未曾发生的文白论争——林纾一则晚年佚文的发现与释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发生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020-08 晚年佚文的发现与作者认定 近日受托整理、校注林纾家书,在合作者、负责联系林纾后人的包立民先生打包寄来的文稿中,发现了一篇题为《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的文字。此文作者署名“张铭”,经阅读原文及末后所附林仲易致林圣明函,始知此乃一则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文白论争的林纾晚年佚文。 其实,早在2008年写作《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时,笔者已注意到有此一文,并因林纾在与林仲易末后一信中嘱其“摧烧之”,而遗憾此举“却使我们今日少了一份可贵的论争文本”①。如今见到这份原稿历经沧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于世,实在大为欣喜。此稿连同林仲易四十年后所写信札,均盖有“圣明藏书”印,可知其为林纾侄孙林圣明的收藏。而其流传经过,在林仲易函中亦有交代: 得六月十六日来函,知近与孟銶兄同访伯森,并为诊察,由足下破费也。四十年前,藏有琴叔托登北京《晨报》一稿,未为发表。老人有两函寄我,前曾抄寄孟銶兄,备选入书牍,足下可借阅。原稿托名张铭,实老人自拟,文中更改及圈点皆老人亲笔。特以寄赠足下藏之。其中所言“伯森”,即福州文史老人萨伯森(1898-1985),与林仲易有戚谊,称林为“表姊丈”;“孟銶”疑当为孟玺,即林纾弟子胡尔瑛别字,与萨氏为好友,胡尝辑抄《畏庐尺牍》一卷,现藏福建省图书馆。林圣明亦居福州,业医②。由信中所言可知,大抵是为了感谢林圣明为萨伯森治病,多有破费,林仲易故将珍藏四十年的此稿相赠。 这篇《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全文如下: 余从琴南师廿年,学画山水。师每日必译书三千六百言,成书一百五十三种。读者多,诟者亦有,其寔于师无毫末之损益也。近读《益世报》阑中有芸渠《偶谈》一则,谓林译《声影录》,写一俄国穷妇,作古文腔调祈祷,大为世诟,不期哑然失笑。师不会俄文,既以文言适译,自然是古文腔调;若径抄俄文,何必用译。譬如直隶人译广东话,若仍作广东腔调,何人能懂?自然以直隶之词,达广东之意,有何可诟?至云“拂袖而起”,“拂”字当是“挽”字之讹。即言“拂袖”,亦不过一时语病,何至将一百馀种之文,因兹一言,概行抹煞。吹毛求疵,弄些小聪明,此所谓“寸朽弃连抱”也。无聊不平,敬以《偶谈》一阑,褒贬间出,上之吾师。师笑曰:有趣极矣。他说余倒霉,吾本来是倒霉人,何用他说!且吾力谶[诫]名誉,即有百个胡适之,亦扶不起;即有千个某杂说[志],亦踩不倒。今日到清闲无事,不妨与他说说。他说吾七十老翁,卖文为活,至此当自嗒然。然我不嗒然,我的奴子,周四,他到欣然。吾每译小说,与舌人对分,一月不过六百元。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周四随封加一,岂不欣然?他既欣然,我也不嗒了。《偶谈》中却说到洛阳纸贵,方今吴子玉用武力统一,那有功夫瞅字?即传抄吾书一万年亦说不到,况吾书悉用洋纸,不用洛阳之纸。且洛阳并不出纸,商务馆掌柜。岂肯白跑到洛阳,蹈空而回?此着又废话矣。若提起《茶花女》一书,是我四十年前游戏之作。今有了《新茶花》,上海人呼吾书为“老茶花”。“老茶花”不走运,《新茶花》却有坤角演唱。前此骂我之人,今乃寻觅此书不得。我意寻《老茶花》是死的,无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还有趣。未知觅书诸君,以为何如?至胡适之比我为司马迁,几乎嚇我老大一跳。司马迁是没有东西的人。我前年患癃闭,拉不出尿,比司马迁更糟。幸亏西医克利,中医陆仲安,合治而愈,至今视这个东西,为极大忌讳。而胡君忽提起司马迁栽我身上,我只好战战兢兢,写一个心领谢帖,挡驾完事。此外又蒙欧人温彩嗣先生,为我辩护,说林先生为当代作家,感极感极!唯律师辩护,例有酬劳。当择吉日,在六国饭店,购三数瓶香槟酒,恭候台光,即请胡君作陪,或能赏脸也。吾师说至此,仍大笑不止。予拾而记之,以供芸渠先生一粲。因此引发的问题是,此文何时所写?为何署名“张铭”?是否出自林纾之手?芸渠所作《偶谈》对林纾有怎样的批评?林纾抱着什么心态写作此文,以及文章最后因何未能刊出?最终所要探究的是其中透露的林纾晚年心事。 前述林仲易致林圣明书,已言及林纾为此稿曾“有两函寄我”。此二函已收入商务印书馆1993年出版的《林纾诗文选》,原未署写信时间,编者说明为林纾“1924年所作”。查其中所言“廿二日六小儿行娶,吉帖想已收到矣”及“余七十有三之年”③,“六小儿”指大排行为第六子、小排行为第四子的林琮。据《贞文先生年谱》民国十三年(1924)记,“春二月,为四子琮取马逸高之女淑端”④,且林纾是年正为七十三岁,则系年无误。 更进一步,由春二月廿二日为林琮结婚日,可推知《益世报》芸渠文的大致刊载时段以及林纾的回应时间。因林纾与林仲易书开篇即提到,“昨读《益世报》,中有《偶谈》一节”⑤,可见其文乃是读报之后,即刻援笔写作。而锁定1924年阴历二月,即西历3月的时段查找,果然在《(北京)益世报》当年3月10日的“益世俱乐部”中见到了这则《偶谈》短文。因此可以确定,《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一文写于1924年3月10-11日,林纾此札也可精确到3月11日所作。 作者“张铭”为何许人,抑或是林纾的托名,在林纾3月11日所写信中也可找到答案。所谓“经敝徒性甫作论辩驳”,《林纾诗文选》亦注出:“性甫,即张汤铭,号烟樵,画家。福建闽侯人。”⑥《林氏弟子表》记林琮言,称其“为先公画弟子中佼佼者”;张氏挽林纾词亦有“侍笔砚有年”,“病榻弥留,遗属丁宁传画册”等语。后者乃指林纾病重时,书《遗训十事》,亦特意交代:“四王吴恽画,送性甫。”⑦显然,其人为林纾爱重的绘画弟子,形同子弟,故于专言家事安排的遗嘱中也不忘道及。 既然此文乃张汤铭“作论辩驳”,何以林仲易指为林纾“自拟”?这在林纾写与仲易的信中也有揭晓。不过,前后两函所言略有不同:3月11日称,因张氏的驳论“搔不着搔[痒]”,“余率性作白话一篇,将他奚落”,是明言其全为林纾自撰;后一信则言,“张生不平,以文抵御。下半余改为游戏之文”⑧,又仅承认后半篇才是越俎代庖之作。如查看原稿,可见全文字迹为别一人手笔,且显系誊清稿,或即为张汤铭抄写;至于“文巾更改及圈点”处,确如林仲易所言,乃林纾“亲笔”。据此可以断定,因张汤铭的原作不得要领,未能令林纾满意,于是林亲自出马,故而此文至少大半篇幅,即“师笑曰”以下均为林纾草拟。这从文章起初用文言,林纾自拟部分转为白话亦可见出。全文既经林纾改写、点定,自当认作是吐露了其心声。 由《偶谈》引出的五年前《新潮》公案 惹恼林纾及其弟子的《偶谈》,若仔细阅读,其实笔锋所向,主要是针对胡适。文章不长,却以花线分隔为三小节。第一小节主要批评世人大多凭借耳食,故“一社会之势力,常为一二天才家所独占”,因其总揽了引导舆论的话语权。对林纾以古文译小说的批评构成了第二小节,而其概述的林译小说几年间由冷落到热销的局面,最终被归结为由于胡适近来褒扬林纾古文所致。故第三小节的结论为:“社会上之文学评论空气,亦时为一二天才家所左右,此亦‘以耳代目’之类也。”仍然回到了开篇“诮鄙夫无识,嗤为‘耳食’或谓之为‘以耳代目’”⑨的感叹,意在指责引导文学风气的胡适言论失当,产生了不良后果,背离了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初衷。 林纾最关切的自然是第二小节的文字: 林译小说,五年前曾以古文腔调,大为世诟。某杂志称其译《社会声影录》,写一俄国穷妇,作“古文腔调”之祈祷,藉使俄之穷妇,人人皆能作古文腔调,则《社会声影录》可以无作矣。又译侦探小说,用“拂袖而起”一语,经人指摘,令人阅之,不觉失笑。是后林译书,销路大落,竟无过问者。七十老翁,卖文为活,至此当自嗒然。今则畏庐小说,市摊上又累累满架。游人常三五游谈,语及《茶花女》,叹赏累日,或攒目[眉]互语,叹林译小说,何竟走遍市廛无处购也。此中人多三五年前痛骂林纾译书挦扯不伦类者,今竟视为瓒[瑰]宝!五年前之林琴南,今又洛阳纸贵矣!林纾对此节文字的总体感受是“于余身上若嘲若讽”,让他颇感难受⑩。 这里先说“五年前”的公案。根据下文引述,“某杂志”可以落实为北大激进学生所办的《新潮》。在1919年1月的创刊号上,发表过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而下半篇“对中国译外国小说的人说”的“四条意见”中,有两条关涉到林纾,正与《偶谈》文字相应。意见第二条认为: 欧洲近来做好小说都是白话,他们的妙处尽在白话;因为人类相知,白话的用处最大。设如有位俄国人把Tolstoy的小说译成“周诰殷盘”的俄文,请问俄国还有人看吗?俄国人还肯拿“第一大文豪”的头衔送他吗?诸君要晓得Tolstoy也是个绝顶有学问的人,不是不会“咬文嚼字”呢!近来林先生也译了几种Tolstoy的小说,并且也把“大文豪”的头衔送他;但是他也不问——大文豪的头衔,是从何种文字里得来!他译了一本《社会声影录》,竟把俄国乡间穷得没有饭吃的农人夫妇,也架上“幸托上帝之灵,尚留余食”的古文腔调来。(11)《社会声影录》为林纾与陈家麟合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内含两篇作品。罗家伦所批评的部分出自第一篇《尼里多福亲王重农务》(英文译作名为A Morning of a Landed Proprietor)。此书列入“说部丛书第三集第廿二编”,商务印书馆1917年5月初版,封面大书“俄国大文豪托尔司泰著”,并印有托氏大幅图像。 罗家伦的第四条意见是: 译外国小说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可更改原来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国的意思。须知中国人固有中国的风俗习惯思想;外国人也有外国的风格习惯思想。中国人既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外国人也不是愚下不移的庸夫。译小说的人按照原意各求其真便了!现在林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而且加入“某也不孝”,“某也无良”,“某事契合中国先王之道”的评语;不但逻辑上说不过去,我还不解林先生何其如此之不惮烦呢?林先生以为更改意思,尚不满足;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他所译的侦探小说中,叙一个侦探在谈话的时间,“拂袖而起”。所以吴稚晖先生笑他说:“不知道这位侦探先生所穿的,是以前中国官僚所穿的马蹄袖呢?还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大礼服呢?”其余这类的例子,也举不胜举了!林先生!我们说什么总要说得像什么才是。设如我同林先生做一篇小传说:“林先生竖着仁丹式的胡子,戴着卡拉Collar,约着吕朋Ribbon,坐在苏花Sofa上做桐城派的小说。”先生以为然不以为然呢?若先生“己所不欲”。则请“勿施于人”(12)可以看出,罗家伦在这里还是抱着与人为善的“建设”态度。不过,关于吴稚晖的批评,恐怕是罗氏误记,此一出典还应着落在其师胡适身上。 此前一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也拟了三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第二条谈的是坚持白话文的立场:“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举例中即包括了林纾的翻译:“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实则,商务印书馆1907年出版的“侦探小说”《圆室案》,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述”,与林纾无干。罗家伦以及包括芸渠先生在内的读者之所以发生误会,实在是因为胡适在此例前后,评说的对象均为林纾。但如果细味接下来的几句:“又知[如]林琴南把Shakespeare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Shakespear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13)则胡适在林纾与《圆室案》的译者之间还是作了区分。 不过,张汤铭,甚至林纾在辩解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批评的张冠李戴,反而甘愿代人受过,只辩称“拂袖”当为“挽袖”之笔误。由此侦知,林纾其实并不清楚其说原始出处,故不惜大包大揽。更重要的是,胡适与罗家伦对于林译小说的不满,根本在于其不用“活”的白话,专取“死”的文言,走失了原作的口吻与精神。张、林却搁置此白话更宜于翻译小说的前提绝口不论,实在也是因为对外文的语体毫无感受能力。辩词的出发点于是落在认定以古文译小说为既成且当然的事实,论题也转弯成为译文语言风格的统一,与对手并未接上榫。 与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纠葛 还须考述的是何以五年间,林译小说出现了从“无过问者”到“洛阳纸贵”的巨变。芸渠认为,那根由端在胡适不负责任的表彰: 胡适之《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推崇林纾备至,谓林纾为有文学天才的人,甚至谓“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后,都没有林纾这样的成绩。”可谓将林抬到天上了。 温彩嗣Wenchester谓文学须有永久的价值,一时毁誉,无伤毫末。林先生要为当代作家,却是自胡适这几句话一把他抬起来,他才不倒霉了,又要走运了。其实这里所说抬高林纾的只是胡适。至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温彩嗣,又译温彻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此前一年,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他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中译本(14)。芸渠撮述其意,在此乃偏重“誉”之无用,即谓胡适虽“将林抬到天上”,林译照样不具“永久的价值”。实则温氏本人连同其书,与林纾毫不相干。不过,林纾明显发生了误会,他没有注意或不了解新式标点中句号的功能,以为已经去世四年的温氏曾称道他,为之辩护,故言“感极感极”,甚至说要在六国饭店设宴酬谢。此话当然是戏言,但还是反映出林纾对外国“知己”的感恩心情。 而让芸渠大为不满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本是胡适1922年3月为《申报》创办五十周年专门撰写的一篇长文,收在申报馆1923年2月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纪念专刊中,次年又出版了单行本。其中对于林纾最高的评价,乃是与严复对举,许为:“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说到林译小说,胡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他(指林纾)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读原文;但他究竟是一个有点文学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书的文学趣味往往比现在许多粗能读原文的人高的多…… 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这是胡适站在文学史家的立场,对林译小说所作的历史评定,自有合理性。芸渠却只顾坚守白话本位,因而对历史人物与文本缺乏必要的同情。何况,胡适在上述赞语之后,立刻表示:“但这种成绩终归于失败!这实在不是林纾一般[班]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因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15),从而透显出以白话为“活文学”仍是胡适论述的归宿与一贯主张。芸渠有意无意忽略了此点,对胡适的本意不免有所歪曲。 关于文言与白话的“死”、“活”,倒使林纾念念不忘,并假托茶花女之老书新戏,调笑一番。林纾自嘲其初涉译坛的成名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老茶花”,乃是因有时事新戏《新茶花》自晚清以来一直以京剧、话剧等形式在上海舞台热演。于是,针对芸渠所述时人“语及《茶花女》,叹赏累日,或攒目[眉]互语,叹林译小说,何竟走遍市廛无处购也”,林纾故意调侃:“我意寻《老茶花》是死的,无可言晤;不如找《新茶花》是活的,可以吊膀,到还有趣。”只是,这样的嘲笑在林纾固然颇为自得,然而已有些无聊。 更有甚者,胡适称赞林译小说对于古文的应用,取得了司马迁以来所没有的大成绩,本是诚心言好;林纾反而就此发难,用司马迁的受宫刑与自己1922年8月间的大小便不通(16)类比,称为“极大忌讳”,“只好战战兢兢,写一个心领谢帖,挡驾完事”,表示拒绝。尽管林纾自白,“有时称许不伦,颇为难受”(17),应是其回应胡适诸言率性而出的原因,但迹近恶俗仍不免是笔者读后的印象。而如果稍微留心胡适所说,不难发现,其并未犯下林纾嘲讽的“比我为司马迁”一类的错误。只是,林纾对司马迁实在是高山仰止,研读有年,故翻译小说时,也会发出“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18)的感叹,以致错会了胡适文意,引司马迁自比。实则,林氏对自家古文已有定位,所谓“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19)。正因有着这样的高度自信,林纾才放出“即有百个胡适之,亦扶不起;即有千个某杂说[志],亦踩不倒”的豪言。根本说来,林纾始终最看重的是其古文,而非翻译小说,按照老友陈衍的说法,那情形竟至为“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20)。无怪乎胡适的好心,因赞的不是地方,林纾并不领情,反会生气。 而真正让林纾最动怒的,应该还是芸渠所挖苦的“七十老翁,卖文为活”,故“师笑曰”最先承接“不倒霉”的话头,就此展开。林纾先后诞育七子五女,家累甚重,又常接济族人及故交,日用开支很大。翻译小说以获取稿酬,确为其重要的养家之道。甚至1913年准备搬家时,地点的选择也兼顾到距口译合作者较近,“便于译书也”(21)。在写给三子林璐的信中,因其游惰成性,林纾每常叹苦,故要求其“当念尔父百般劳瘁,所为何来?切须学好,用功做人”;语气中甚至不乏恳求:“一钱来处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须从俭为是,亦以体贴老父,即为孝子。”由于长期劳累,林纾的身体早已出现病状。在训子书中亦不妨说得明白:“吾年已六十有四,在理喘嗽之病日相侵寻,亦是老年常事。而吾蒙天之佑,常能耐劳,试问吾身尚有何望?”所望者即在儿子们的自立(22)。为子女笔耕不息的林纾老人,也正有值得人尊敬处。郑振铎于林纾身后,誉之为“实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实可算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23),相当中肯。与此相比,芸渠的讥讽不免失之尖刻。但其说仍不过是沿袭了傅斯年五年前在《新潮》对林纾反对白话文学心理的揣测:“苟不至于如林纾一样,怕白话文风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说卖不动了,因而发生饭碗问题,断不至于发恨‘拼此残年’,反对白话。”(24)这也是浅之乎视林纾了。 而由芸渠“洛阳纸贵”一语带出的“方今吴子玉用武力统一,那有功夫瞅字”,实为《书后》文中惟一关系时事之言。吴佩孚(字子玉)为直系军阀首领,当时在北洋各系中军事实力最强,驻守洛阳,操控政局。1923年4月,吴在洛阳大做五十寿庆,有人出多金请林纾作画,林“却之弗为”,《贞文先生年谱》谓为“久不直其骄横佳兵也”(25)。但其间亦不排除林纾亲近的徐树铮为皖系军阀的缘故。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皖系落败,徐亦被通缉。林纾或不无衔恨,故在此顺便偶刺之。 不过,在林纾的反唇相讥中,倒也透露出其当年真实的谋生情况:“吾每译小说,与舌人对分,一月不过六百元。今舍译卖画,一月到得千元。”可知,起码到1924年,卖画已成为林纾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按照1913年所收女弟子王芝青的回忆:“晚年求画者甚多,先生自定润笔,与其他画家不同的是索画先付润笔,茶几书架上常常堆满了纸绢,直到病榻上难以握管还在纸上摸索,他死后还欠了许多画债。”(26)老友陈衍的记述更为传神:“纾有书画室,广数筵,左右设两案:一案高将及胁,立而画;一案如常,就以属文。左案事毕,则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饮外,少停晷也。”故陈衍“戏呼其室为‘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27)。如此辛劳,仍是为了儿辈。以至在去世前,林纾已病势沉重,“犹日作画数事,自谓以分诸子也”(28)。 至于林纾的翻译情况,此文也作了总结:“师每日必译书三千六百言,成书一百五十三种。”前者可视为林纾与合作者通常约定的译书字数,后者则为其自家认定的译书数目,尽管我们现在知道的林译小说成书已超过此数。而谓为“总结”,实在是因为此时距林纾病逝之日——1924年10月9日已经不远。 游戏文中的正经事业 《读〈益世报〉芸渠〈偶谈〉书后》完成,林纾将其寄给林仲易,附信曰: 方今盛行白话,余率性作白话一篇,将他奚落。不便付与他报,祈吾侄登在附张,与白话文及白话诗一堆混去,略略开心。余近来身子极健,故有此闲情。(29)在此先要说明的是林仲易的身份。林氏本名秉奇(1893-1981),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父亲林作舟与林纾为友,林纾曾因仲易之请,为其父撰《清奉直大夫阳山县知县长乐林君墓志铭》。1917年冬,林纾在北京开设古文讲习会,林仲易亦来听讲。故1918年林赴日留学时,林纾为作《送林生仲易之日本序》(30)。1920年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林仲易即加盟北京《晨报》,并专任次年创办的《晨报副刊》编辑,编发了大量卓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31)。而撰写《偶谈》一文的芸渠应为北京《益世报》编辑王芸渠,该报“益世俱乐部”即由其主编(32)。可想而知,有此一层关碍,林纾的反击文章自不便在北京《益世报》发表。于是,交给以刊发白话文学为主的《晨报副刊》编辑、弟子林仲易,便是最合适的选择。 此文的出之以白话体,在林纾也有戏谑意,算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林纾并非反对白话文,而是反对“尽弃古文行以白话”(33)。因此,早在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上,林纾即发表过白话道情多篇(34)。1922年8月9日至9月15日,《晨报副刊》刊出署名“淑兰女士”撰写的《晋鄂苏越旅行记》,林纾也致函林仲易,大赞其文“用语体,字里行间,成有卷轴之气,闲闲以白描之笔,写南中山容水态,均栩栩欲活”,以为“必如是始成语体文字”。既极称其为“不易才”,故特意探问:“未知为何处人,吾贤曾否认识此人,可否介绍与老人相见。”(35)爱才之情溢于言表。而林氏也果然有眼光,此“淑兰女士”即为日后的著名学者冯沅君。于此亦可见出,林纾实将书卷气视为白话文必须具备的质素与底蕴。 而这篇师生合作的戏仿白话文终究没有刊出。据林纾事后写给林仲易的信中“伏卢先生识高于顶”一语可知,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反对发表此文;而“吾侄见事,良有卓识”,说明林仲易也赞同孙氏的意见。虽然孙伏园令林纾“拜服无地”的“持平论”现在不得其详,林仲易的劝解信亦未现身,但二人不愿挑起文坛新事端的息争之意还是可以明白体会出的。林纾回应林仲易“卓识”的“余那顾与此辈争雄头[斗]角”,以及针对孙伏园“持平论”所说“余七十有三之年,何必与人争无为之气”,都在剖白此点。尤其是《书后》文中对胡适的讥讽,在林纾说来,是既有些得意亦有些不平的“且胡适之经余指斥,而尚以谀词加我,本不必呶呶与辩”(36);若在旁人如孙伏园与林仲易看来,可能生出的倒是不识好歹,甚至好心当作驴肝肺的感觉。 自我解释作文的目的与心态,林纾初时的“颇为难受”与“将他奚落”显然更本真;后来辩解为“如方朔之《解嘲》,以博阅者一笑,并无诋谰之词”,起码孙伏园并不相信。不过,寻“开心”、“游戏”为文,确也是林纾前后二书一致的表白,只是后信于此更多强调,且言及与性情相关:“然好游戏之作,效颦作白话一篇。”(37)采用调侃语气作文,自然可降低或缓和论争中的敌意,使其处在若有若无之间。但分寸其实很难把握,戏谑也很容易从善意的调笑滑向恶意的讽刺。但无论如何,林纾的性喜“游戏”并非遁词。熟悉其人者,多对林纾自认的“好谐谑”印象深刻。《福建文史资料》第五辑登载过两篇回忆文章,对此竟有相同的记述。世交子吴家琼(其父吴畲芬与林纾同任教于北京五城学堂)称:“林琴南平日风趣洒脱,快言快语,不存芥蒂。”晚年亲近的弟子胡孟玺亦说:“先生性极诙谐,居常以隽永洒脱之辞,作深入浅出之语,其脍炙人口者不可胜纪。”(38)只是,这样的隐情细节不可能为人人道,并期待人人知。为避免引发新一轮的文白之争,想来也有为林纾老人不致惹火烧身、安度晚年计,《晨报副刊》因此决意“不登”这篇“游戏之作”。林纾此时或许也觉得孟浪,不愿此文再现于世,故信末嘱林仲易“摧烧之可也”(39)。 虽说是笔墨游戏,在林纾其实也相当郑重。此稿篇首本有林纾所写“登出此文时,祈将贵报送我一分”的嘱咐,分明有留存意。如果放在林纾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来看,更可见其为延续古文命脉而拼死努力的悲壮心态。这场最终夺去林纾性命的大病起于1924年6月10日。其间,林纾曾扶病去孔教大学讲授《史记》中《魏其武安侯列传》一篇,随即辞讲席,并作《留别听讲诸子》诗: 任他语体讼纷纭,我意何曾泥《典》《坟》。驽朽固难肩此席,殷勤阴愧负诸君。 学非孔孟均邪说,话近韩欧始国文。荡子人含禽兽性,吾曹岂可与同群?(40)留给学生的遗言,仍与1919年致蔡元培信中对“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41)的忧惧相同。临终前一日,林纾已无力说话,“然犹以指书子琮掌曰:‘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42)这已是真正意义上的遗嘱,其中凸显的是林纾对古文至死不渝的关切。 一篇游戏文,关联的仍然是林纾一生倾力的古文事业。 *收稿日期:2014-10-16 注释: ①夏晓虹:《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现代中国》第10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②均参见萨伯森著,萨本珪编校:《识适室剩墨》,福州:自印本,2003年,第369、356、482页。 ③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寄林仲易(三)》,李家骥、李茂肃、薛祥生整理:《林纾诗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34、335页。 ④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62页。 ⑤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第334页。标点有调整,下不再注。 ⑥⑩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 ⑦朱羲胄述编:《林氏弟子表》,第13页;《贞文先生年谱》,第65页。 ⑧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 ⑨芸渠:《偶谈》,《益世报》(北京)1920年3月10日,第2张第8版。感谢博士生宋雪代为查找此文。 (11)(12)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卷1号,1919年1月,第113-114,115-116页。 (13)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第305-306页。 (14)温彻斯特著,景昌极、钱堃新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上海:申报馆,1924年,第18、23-24页。 (16)参见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54页。 (17)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 (18)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朱羲胄述编:《春觉斋著述记》,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26页。 (19)(20)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旧文四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94,91页。 (21)林纾:《训林璐书》(1913年4月7日)。 (22)林纾:《训林璐书》(1913年4月20日、约1916年、1915年秋)。 (23)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小说月报》15卷11号,1924年11月,郑文第3页。 (24)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第914页。 (25)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61页。 (26)王芝青口述,范文通整理:《我的绘画老师林琴南》,《人物》1982年第2期,第177页。 (27)陈衍:《福建通志·林纾传》,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学行记》,上海:世界书局,1949年,第4-5页。 (28)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64页。 (29)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林纾诗文选》。 (30)林纾所撰二文分别收入《畏庐续集》与《畏庐三集》中。 (31)参见闽客、张正宇:《林仲易与二十年代的北京〈晨报〉——访旧京〈晨报〉总编辑林仲易之女林薇女士》,《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2期,第318-321页。 (32)蹇先艾《向艰苦的路途走去》提及:“在我投稿的初期中,我不得不提到几位认识或不认识的编辑先生的奖掖,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之忱。在北平《益世报》的《益世俱乐部》中刊登我的处女作《人力车夫》的编者是王芸渠先生……不久就到山东教书去了。”(《蹇先艾文集(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此条材料由宋雪提供,特此致谢。 (33)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原载《文艺丛报》第1期,1919年4月;录自林薇选注《林纾选集》(文诗词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34)参见郭道平:《〈杭州白话报〉上林纾的白话道情》;胡全章:《林纾“白话道情”考论》,《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35)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一)》,《林纾诗文选》,第333页。 (36)林纾:《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第335页。 (37)林纾:《寄林仲易侄书(二)》、《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 (38)吴家琼:《林琴南生平及其思想》;胡孟玺:《林琴南轶事》,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106页。“好谐谑”出自林纾文言小说《庚辛剑腥录》,述“吾乡有凌蔚庐(按:谐音林纾之号畏庐)者……其人好谐谑”;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中亦有引例(《旧文四篇》,第69、92页)。 (39)林纾:《寄林仲易(三)》,《林纾诗文选》。 (40)(42)朱羲胄述编:《贞文先生年谱》,第62,65-66页。 (41)林纾:《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畏庐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