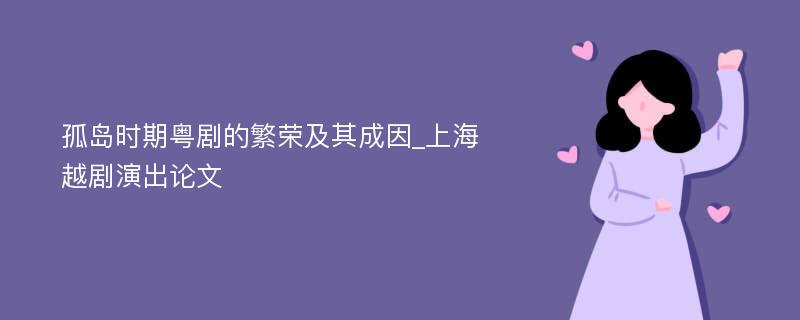
孤岛时期越剧的繁荣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剧论文,孤岛论文,繁荣论文,时期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3-0108-05
越剧,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髦儿小歌班、绍剧、嵊剧,1925 年9月17日《申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出现。本文是以1930年代末上海“越剧 ”为研究对象,这一名称当时并未统一,在各种刊物中有“绍兴女子文戏”、“女子的 笃戏”、“越剧”等多种称法。本文则延用当时报刊中的称法。
一 孤岛越剧之繁荣景象
1938年1月31日,已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月,上海租界平静依旧。除了源源不断 从火车站、汽车站涌出的外乡人,似乎感受不到战争的气息。这天,从浙江嵊县来上海 躲避战火的女子绍兴文戏班——越升舞台的全体演员,正在北京路泥城桥附近的通商旅 社,精心排练。此时演员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戏班中挂头牌的是姚水娟,二牌是小生 李艳芳(艺名时髦牌),三牌是老生商芳臣。此外还有袁金仙、邢竹琴、吕福奎、范瑞娟 等20余人。从1月29日起,剧院就开始在《新闻报》刊载广告,以“海上唯一女子绍兴 戏班”吸引观众。这是战后第一个来沪演出的女班,引起了当时一些沪上江浙人的注意 。戏评人蔡萸英知道家乡绍兴文戏中小有名气的“三花一娟”姚水娟,以及老生商芳臣 将来演出,十分高兴,立即送花篮以示祝贺。地方戏曲演出,送花篮捧场在当时是“史 无前例”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二天他又在报纸上发表了《女子的笃戏初看记》一 文,对通商旅社内姚水娟等人的演出给以赞扬。(注:高义龙《越剧史话》,上海文艺 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正值农历新年,看戏的人颇多,连连满场,又使得通商 旅社的女子绍兴文戏演出更加轰动。从头场“打炮戏”开始,连连客满。时人报道中记 录了当时盛况“自从今年农历元旦越剧皇后姚水娟在通商旅馆登台后,一鸣惊人,女的 笃班的形势极盛,唱做表情,处处胜人一筹,通商日夜客满,几无隙地。大中华竟千方 百计,以重金聘去。天香大戏院开办之际……又以更大的包银邀到。”(注:笔花《从 绍兴戏说到的笃班(七):源源本本…记载出来》,《申报》,1938年12月19日第4版。) 姚水娟在上海一炮打响,女子的笃自此不做流动的短期演出,开始在沪上固定场所内演 出。于是,被战火惊吓返回家乡的女班又接踵返回。
接着“四季春”和“素凤舞台”两班同时来到上海。他们演员阵容强大,《新闻报》 广告上刊登的领衔演员有竺素娥、王杏花、袁雪芬、黄笑笑、任伯棠、傅全香、钱妙花 、邢月香、张桂莲、钱彩云、施彩香。(注:广告《新闻报》,1938年2月12日第10版。 )1938年2月15日开始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海小剧场公演,3月3日转至老闸大戏院。老 闸大戏院有491个座位,原为绍兴大班的演出基地。自女子文戏在此上演以来“每次演 出,场场座无虚席”。(注:六龄童《取经路上五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页。)筱丹桂领衔的“高升舞台”随后也来到上海。1938年4月30日开始在恩派亚 大戏院与观众见面,首演剧目是《大赐福》、《三本铁公鸡》、《盘夫索夫》,同台演 员还有小生张湘卿、老生筱灵凤、小丑贾灵凤、老旦钱苗香。
越升舞台上海滩演出的一炮打响,声誉鹊起,与戏院签约达八个月。来沪的女班越来 越多。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王明珠、陈苗仙、许菊香、庞天红、刑竹琴、毛佩卿 等,当时浙江女子文戏班中比较有名的艺人都来到上海。到1938年7月底,上海的女子 越剧班已有8个:越吟舞台、四季春班、高升舞台、越剡舞台、天蟾凤舞台、第一舞台 、心心剧社、越升舞台。(注:卢时俊、高义龙主编《上海越剧志》,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7年版,第12页。)1939年9月出版的越剧杂志《越讴》统计,规模较大的女子文戏 班已经有13个:水云剧团(姚水娟、魏素云、商芳臣)、素娥舞台(章杏云、尹树春、屠 福香)、天蟾凤舞台(陈苗仙、尹桂芳)、四季春(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第一舞台( 施银花、屠杏花、钱秀灵)、越吟舞台(竺素娥、邢竹琴、袁金仙)、越舞台(王明珠、王 桂英、金香琴)、高升舞台(筱丹桂、贾灵凤、张湘卿)、心心剧社(庞天红、叶香厅、袁 爱花)、越升舞台(赵瑞花、姚月明、李艳芳)、天蟾舞台(王艳秋、许菊香、张松娟)、 群英舞台(姚月花、邢月芳、魏梅招)、东安剧社(徐玉兰、汪笑真、小荷花)。统计显示 ,当时女子绍兴文戏中几乎较有名的演员、戏班,都荟萃黄浦江边。事实上,除了这些 戏班,各处还有一些小戏班在演出,加上游乐场内演出的小班,数目就更多。1941年11 月6日《越剧日报》统计的数字显示,上海女子越剧戏班有36家之多,在上海各剧种中 ,剧团数量、演出场所数量跃居第一位,超过了京剧和上海本地的申曲。
从1938年1月第一个女子绍兴文戏班在上海登台演出,至1941年11月的36个戏班,仅用 不到四年时间。地方戏曲能在非发源地如此快速发展,可见人们对该剧种的欢迎程度。
作为地方小戏,越剧初来时登不上大雅之堂,只能在500人以下的小型剧场演出(包括 茶楼和游乐场在内)。随着越剧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对其接受程度的变化,30年代后 期开始,越剧女班渐渐在700人以上的大中型戏院演出。这种变化正是在孤岛时期内出 现的。1938年4月,女子文戏出现在上海舞台不到3个月,筱丹桂领衔的高升舞台,就在 700座的恩派亚大戏院演出;1939年5月,由赵瑞花、李艳芳、王明珠、孙妙凤等为首的 四个女班,联合在拥有1914人座的更新舞台演出。
上演越剧的剧院数目也是猛增。1938年8月上海的固定演出场所中,平剧(即京剧)有12 个,话剧2个,申曲3个,昆曲1个,大鼓1个,女子越剧则有12个。到1939年9月,固定 女子越剧演出场所增加到20多个。据《上海越剧志》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8年至1941 年,新开辟的越剧演出场所有46个。而从1917年第一个绍兴戏班进入上海,出现第一处 越剧演出场所,到1937年底为止,共有59处剧院曾经演出越剧。短短4年间出现的场所 数量几乎和前20年相差无几。
孤岛上的人们对于越剧的观看,是十分热爱。从各家报纸对越剧的报道篇幅中,同样 看出越剧的繁荣状况。当时《申报》每天的广告中,都能看到越剧上演的消息。《申报 》上还有这样的报道:“七家绍兴戏院因此天天满座,更新舞台会串盛况,座价卖到五 元,日夜客满”(注:笔花《从绍兴戏说到的笃班(一):源源本本…记载出来》,《申 报》,1938年12月2日第4版。),比之最初“绍兴戏初次来到上海……地点在北京路关 青阁码头戏院……售价只一角二角”(注:笔花《从绍兴戏说到的笃班(二):源源本本 …记载出来》,《申报》,1938年12月4日第4版。),绍兴文戏受欢迎的程度有了明显 的变化,更是出现了“的笃班,即绍兴文戏,现在已经风行一时,风头之健,绝非若干 年前的的笃班可比”。(注:笔花《从绍兴戏说到的笃班(五):源源本本…记载出来》 ,《申报》,1938年12月8日第4版。)
从1938年2月开始,每期《新闻报》上都有越剧的广告。从1月的通商剧院一家,到7月 通商、大中华、大来、老闸、长乐等,直到1940年越剧广告几乎占满了《新闻报》的娱 乐广告版面。《力报》是上海众多娱乐报之一,就刊登了许多关于越剧的报道,在1940 年间还开设“每日越剧”专栏。(注:“每日越剧”版,《力报》,1940年10月1日~19 41年1月31日第3版。)各种专门的越剧刊物不断出现。据《上海越剧志》统计,1938年 至1942年间出现的越剧报刊有13种;从1936年第一份开始有专栏报道越剧的刊物《影与 戏》,至1949年出现的越剧刊物只有26种,出现在孤岛时期的就占一半以上。
从越剧女班日渐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中也体现出越剧的盛行。1938年11月,为上海时疫 医院筹款,越剧女班在更新舞台举行女子越剧“七班会串”。《申报》上是这样记载的 “……发动全沪越剧界力行举行首次联合大会串,参与者计大中华、大来公园、天香、 永乐、老闸、通商等七大名班全体优秀坤伶,定于本月十日,假更新舞台,开演名剧, 券资计五元、二元、一元、五角,各大公司及各越剧场均有代售。”(注:时疫医院演 剧筹款》,《申报》,1938年11月7日第3版。)接着几天的《申报》中都有关于演出的 文章。1938年11月12日《申报》第二版,上海时疫医院刊登大幅公告:敬谢参加越剧会 串演出的艺人和观看演出的观众。(注:广告,《申报》,1938年11月12日第2版。)次 日《申报》上就有对越剧会串演出的评论文章:“前日(十日)上海时役医院假座更新舞 台筹款。特请七班越剧会串……日夜客满,盛极一时。打破越剧卖座纪录。”(注:汤 笔花《越剧会串杂评:七班会串…人才济济一堂,唱做俱佳…越剧成功有望》,《申报 》,193年8月11至13日第4版。)接着1938年12月23日《申报》第三版,刊登了上海难民 救济协会和市民组劝募委员会,为筹募认养难民的经费在当月31日举行“各大电台联合 播音劝募大会”的大幅广告中,绍兴文戏(即女子的笃班)名列演出阵容的名单中。(注 :广告,《申报》,1938年12月23日第3版。)
1939年2月,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与绍兴旅沪同乡会,在黄金大戏院联合举办女子越剧大 会串,筹募捐款。当时《申报》上有题为“女子越剧会串筹款——定期在黄金大戏院开 演”的文章刊载,此时票价最高达到五元。参加的艺人有“如姚水娟、竺素娥、商芳臣 、赵瑞花、李艳芳、马幛花、袁雪芬、施银花、屠杏花、筱丹桂、张湘卿、贾灵凤、王 明珠、喻汉香等都是女子越剧中的杰出人材……票价分五元二元一元五角四种,日夜一 律……”,(注:花《女子越剧会串筹款:定期在黄金大戏院开演》,《申报》,1939 年2月6日第4版。)与当时花三角钱即可买得三寸长黄鱼的物价相比,十分昂贵。(注: 《沪市菜价昂贵》,《申报》,1938年10月17日第3版。)第二天《申报》上接着又刊登 了题为“女子越剧会串排定戏目”的文章,(注:《女子越剧会串排定戏目》,《申报 》,1939年2月7日第5版。)将即将出演的剧目一一公布。接着同月14、15日《申报》上 又刊载这次筹款汇演的情形“未及十二时已告客满,其盛况不亚于上次更新舞台,女子 越剧之魅力,足见一斑”。(注:笔花《黄金更新义务戏:越剧平剧卖座俱佳》,《申 报》,1939年2月15日第5版。)
1939年7月间,越剧界马樟花、傅全香首次被邀请到好友电台播唱特别节目,现场演出 ,又被三友实业社聘请做广告。1940年8月1、2日,女子越剧八班在卡尔登大戏院,进 行“劝募绍属平粜捐”会串演出。8月13日,上海救济难民儿童教养院假座新新玻璃电 台、中西电台、国华电台、明远电台,举行播音宣传大会,越剧界马樟花、袁雪芬等人 前往参加。
到了1941年,越剧界的社会活动更多。1月3日,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募捐运动在新新电 台举办“全市女子越剧大会串”,施银花、屠杏花、姚水娟、竺素娥、筱丹桂、马樟花 、袁雪芬、尹桂芬、竺水招、徐玉兰、商芳臣、李艳芳、邢竹琴等38位演员,参加播音 演唱。1月21日“全沪越国红星十班大会串”在浙东大戏院进行,沪上有名的女越剧演 员都参加演出。1月22日至23日,嵊新女子越剧团劝募故乡灾款的游艺大会,联合在大 来、天香、卡德、民乐、永乐、南洋、同乐、浙东、万国等戏院的演出团体,在更新舞 台进行会串演出。当时《绍兴戏报》上刊载了当时戏票价格“包厢:120元,官厅:10 元/位,正厅:5元/位,月楼:1元/位,花楼:5角/位。”(注:《嵊新女子越剧团更新 舞台价目》,《绍兴戏报》,1941年1月22日第1版。)几天后,报纸上刊登了此次演出 筹款的数目“销票成绩:浙东大戏院:8850元,大来剧场:8415元,卡德戏院:7970元 ,南洋戏院:4290元,同乐戏院:3290元,民乐戏院:2980元,天香戏院:1960元,万 国戏院:1600元,永乐戏院:400元。”(注:《大会串销票成绩》,《绍兴戏报》,19 41年1月30日第1版。)从统计数字中,可见前往观看越剧演出的人数之多。
最后,这时知名越剧女艺人几乎齐聚沪上。1938年到上海的女艺人,就有被称为“四 大名旦”的“三花一娟”——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还有女子越剧所有知 名科班的主要演员,还有日后以“十姐妹”(即尹桂芳、徐玉兰、竺水招、筱丹桂、袁 雪芬、张桂凤、吴小楼、傅全香、徐天红、范瑞娟)著称于世的后起之秀,还有当时著 名的生角:马樟花、李艳芳、商臣芳、钱妙花等。1941年1月3日的播音活动中,出席的 有38位越剧女艺人。以上种种现象,显示出越剧在孤岛时期的上海非常兴盛。
二 越剧繁荣之因探究
任何一种戏曲形式,必须在民间生活的土壤中孕育生长。戏曲的分布状况受到区域的 经济地理、政治环境、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注:罗苏文《论近代戏曲与都市居民 》,《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207页。)19世纪50 年代越剧的雏形阶段和早期发展阶段都在乡间,观众以农民为主,念白或是演出形式都 以适合乡间农民为标准。农民没有固定的闲暇时间,艺人演出的时间因此也十分短暂和 不确定,这种演出方式使得越剧这一戏曲形式很长时间内都无明显发展。
上海自1842年开埠以来,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伴随着他们的来到,各种文化 、各种地方戏曲也一同出现在上海。此时上海已是“中国第一繁盛商埠”,基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生活,使人们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脱离了自然的束缚,开始步入现代 机器工业中的都市生活。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自然状态,转变为依 时间上班、下班的现代都市型生活,来自各地的农民也演变为新型社会群体——市民群 体。他们的闲暇时间开始固定,家庭收入开始固定,娱乐消费于是逐渐走进了市民群体 的日常生活。
1907年5月13日,小歌班艺人首次在上海十六铺演出。不断改进演出技艺之后,1919年 小歌班艺人开始在上海立住脚。因此乡间学戏的人逐渐多起来。1935年的调查显示,当 时仅有40万人的嵊县,外出演戏者有2万多人,女班则有200多个。这种战前大量演员的 出现为孤岛时期越剧在上海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充足的人员准备。1931年底女班开始出现 在上海的茶楼和小剧场,但未产生影响。
在孤岛时期之前,越剧女班演出地还包括江浙地区。大范围的演出市场使演出没有竞 争。1938年后江浙地区大批人口移居上海,越剧女班也纷纷来到租界,演出市场骤然减 小,竞争加剧,促使越剧女班不断提高技艺。如姚水娟聘请新闻记者为之编写的新戏《 花木兰》便是竞争中展露的优秀剧目,受到上海各界欢迎。《戏报》、《梨园世界》都 为该剧演出发行特刊。华兴电台在该剧演出第二天播讲花木兰的故事,听众还不断点播 。英文报《大陆报》在演出前一天(1938年9月11日)在“本地表演”栏发表评论文章, 把花木兰比作欧洲十字军时代的圣女贞德,同时刊登姚水娟一手执钢枪、一手持马鞭的 戎装剧照。上海的外文报纸介绍越剧,这是第一次。
正是在竞争中发展了越剧,在竞争中扩大了越剧的声誉以及受欢迎程度。
第一,在竞争中越剧表演剧目有了变化。传统越剧剧目大多讲述的是传统社会下,痴 男怨女坎坷的恋爱故事。到上海后,为适应新的都市环境,戏班也开始上演连台本戏、 新编剧目等。受欢迎的剧目,内容仍以爱情为主,剧目的思想、情节简单,正适合上海 社会里普通市民的欣赏口味:以消闲为主。越剧因它的通俗倍受欢迎,越剧也在受观众 欢迎中带有了浓厚的商业气息。人们看越剧是因为所花的代价有相应地回报——听“懂 ”了,这对于看戏观众来说很重要。爱情故事的剧情,正适合一些文化水平偏低、中等 生活程度家庭中的妇女喜好。“女子为越剧之拥护者,此言不独为太太奶奶小姐,即妓 女、舞女、向导女亦然”,(注:《越讯一束》,《力报》,1940年11月2日第4版。)从 一个侧面透露出上海都市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某些变化,都市娱乐消费中女性比例 的增加。女性观众欣赏以女性为叙述主角的越剧,也反映出当时都市妇女对于女性在婚 姻、家庭中角色的关注。
1940年上演的《蒋老五殉情记》(姚水娟主演)改编自当时的社会新闻,连续上演63场 ,报纸刊载“霞飞路上之耆者张燮堂;廿一晚在皇后听(非看也)姚水娟之蒋老五,据云 一双青眼,略可看见少些。”(注:《越讯一束》,《力报》,1940年10月25日第4版。 )可见该剧受欢迎程度之深。筱丹桂主演的《杨贵妃》更是连续上演132场。如此的成绩 对于地方戏曲而言,是过去传统戏上演场次无法相比的。这两场受到人们极大欢迎的剧 目,都有一个区别于传统戏的特点:剧情都是大家熟悉的。《蒋》所讲述的故事就发生 在数年前的上海,曾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更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 。1938年后在上海的演出剧目中,这一类新编剧目日益增加,《花木兰》、《冯小青》 、《天雨花》、《燕子笺》、《卧薪尝胆》、《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孔雀东南飞》 、《胭脂》、《梁祝哀史》……《泪洒相思豆》等新编剧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何 以在战争之时,不听乱弹之《忠孝传》?不听平剧之《杨家将》?而独独来看越剧这种通 俗之言情故事?其时人们身处战争包围中,生活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不再有安定的环境 ,时时处于紧张状态。越剧对于普通市民而言,通俗易懂,又能在剧中实现美好愿望, 不啻为一种寻求精神放松的娱乐方式。
第二,越剧的表演与舞台变化吸引着更多的观众。布景方面,演出时姚水娟首先采用 京剧舞台上的“绣花大幕”,在舞台上增加实物布景,并逐渐地更新为立体布景。1940 年樊篱在《越剧漫谈》中写道“向来越剧戏院,租赁布景每月只花一百余元租费,现在 居然肯花二三千元资本在一本戏中做布景了。”(注:《上海戏曲菁华》,上海文史资 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30页。)并且“光是布景考究,还不 算数,还要配用灯光,外加来上几套变戏法的机关布景”。(注:煌莺《女子越剧红的 理由》,《绍兴戏报》,1941年1月13日第3版。)舞台布置不断改进,不仅是追求更好 的舞台效果,也为适应上海市民求新、求异的心态,吸引更多的观众。除舞台布置外, 演员行头也有很大变化:“不仅头牌非有好的行头不可,就是二、三牌的角色,对行头 也不肯马虎”。(注:煌莺《女子越剧红的理由》,《绍兴戏报》,1941年1月13日第3 版。)演员的扮相也是影响戏曲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剧由清一色女演员演出 ,且多数是年轻女性。跻身上海娱乐圈内,女性演员自以塑造女性形象为己长。不仅优 美抒情的唱腔风格吸引观众,女演员的演出服装在演出市场中更加时尚、漂亮。当时越 剧的演出服装色调多用中间色,纹样装饰多用花边,辅以多种佩带,显得色调丰富而淡 雅柔和,使演员在剧中扮相总以“风流倜傥”、“惊艳美丽”等俊美形象出现。与乡间 演出时大红大紫、浓妆重彩的扮相不可同日而语,逐渐成为当时上海女性模仿对象。以 越剧闺门旦人物造型为样板的戏装照,曾是上海照相业的一项特色服务。(注:罗苏文 《论近代戏曲与都市居民》,《上海研究论丛》第9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版,第227页。)
越剧各班竞争同时,孤岛的跳舞业、电影业、京戏等其他娱乐形式也在瓜分着孤岛上 的消费群体。尽管“京戏院的生意也好到了极顶”,但“越剧也是这时在孤岛崛起的” 。(注:魏宏远《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学术研究》,1998年第5期,第80页。 )越剧在同其他娱乐形式的竞争中无疑也显示出其自身的优势。
其一,越剧源自浙江,其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浙江方言。“所谓上海白者,大抵均宁波 、苏州混合之语言”(注: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因此在上海演出越剧,市民十分易懂,加之剧情的通俗,更是不存在艰涩唱词。 “至于浙江省以外的外省朋友们也喜欢看越剧,这是什么道理?而我经过许多次的咨询 ,他们都回答说:女子越剧,原原本本有始有终,演来容易懂,我们花了代价欣赏戏剧 ”,(注:樊篱《越剧漫谈(十):她的风行完全是一个懂字》,《力报》,1940年10月2 8日第4版。)“而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个‘懂’字,否则还有什么要求?女子越剧所说的话 ,是非常易懂,不若其他戏剧都是文质彬彬,词藻气太重,唱起来都是用平常嗓子,出 口成章,虽则俚俗,却是易懂,不若其他戏剧小生旦角,用小嗓子唱,咦咦唔唔,辨别 不清。”(注:樊篱《越剧漫谈(十)》,《力报》,1940年10月29日第4版。)
其二,一种戏曲形式能否发展下去,要看它是否拥有自己的观众群体。江浙移民在上 海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之大,正为越剧在上海的繁荣提供了观众基础。上海作为移民城市 ,自开埠起,各方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1843年上海人口20万,1947年时已有超过400 万人口。如此数量巨大的移民,迅速改变上海人口的构成。据公共租界和华界对人口的 分省籍统计,上海外来移民的人数中,第一是江苏,第二是浙江。(注:熊月之《略论 上海人形成及其认同》,《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第57页。)抗战爆发后,大批 移民迁入租界,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居民、富户纷纷寓居上海。因此在上海有着越剧天然 的观众群,为孤岛时期越剧在上海的繁荣提供了关键因素。有需求才会有演出市场,才 有戏曲发展的空间。
孤岛时期越剧观众群体的变化是惊人的。1940年10月的《力报》刊载到“一班观众中 ,漂亮女性,已占多数,而西装的男性,却也不少,至于数量之中,若是分析它的籍贯 ,当然以宁波人最占多数,大约可占百分之五十,绍兴人占百分之二十,杭州人占百分 之十,其余百分之二十,是上海人和苏州人甚至北平人山东广东的老乡都有,可见盛况 。”(注:樊篱《越剧漫谈(十):她的风行完全是一个懂字》,《力报》,1940年10月2 8日第4版。)1941年的《绍兴戏报》上有一篇题为“越剧观众”的文章,写道“绍兴戏 的笃班,惊动了整个上海滩,从前越剧团里的观众,越人占七成,甬人占二成,其他占 一成,到现在情形大大的不同了,越人只占四成,甬人占三成,其他占三成,可以说各 处的人都有,碧眼儿看越剧的,各剧场都有……”(注:樊篱《越剧漫谈(十):她的风 行完全是一个懂字》,《力报》,1940年10月28日第4版。)可见观众群体已不再局限浙 江人,北方人士,甚至外国人都成了越剧观众。扩大的观众群体正是越剧行业红火发展 的消费基础。
除了越剧自身的发展变化、观众群体因素外,孤岛时期特殊的经济社会状况、人们的 战时社会心态,也是影响越剧——包括其他娱乐形式——在孤岛繁荣的因素。
1937年11月12日,华界沦陷,租界当局宣布相对中立,致使各地难民蜂拥而来,都希 望在这“安乐世界”躲避战火。然而因封锁,米奇缺;因中立,人奇多。孤岛缺吃少住 的境况,正常的生活脱离了轨道。日本人、汉奸、亲日派、国民党势力、租界当局、抗 日人士等都在孤岛发表言论,极其复杂的社会状况使人们的思想开始混乱。人们的工作 不再正常,时时担心战争何时会波及到自己身边。未来变得极为不确定,人们心态开始 消极,开始采取各种方式缓解自己的担忧,寻找心灵的寄托,以消除战争带来的恐慌。 许多人开始醉生梦死,及时行乐成了流行语。
越剧的出现恰好为孤岛社会中一部分人提供了心灵寄托。一是在越剧观众中,多数为 宁绍籍人士。当他们背井离乡来上海躲避战乱时,伴随着对战争的恐慌外,还有对家乡 的思念。越剧以浙江方言念白,让他们倍感乡音的亲切,带给他们的是一味珍贵的慰藉 心灵的良药,暂时消除了他们被战争包围下的恐慌。二是剧中多为普通人的故事、最终 总有美好的结局。对躲避战火的市民而言,这些故事使人的内心得到安慰:生命平安、 家庭美满的愿望得以寄托。越剧也受到非宁绍籍人士的欢迎。(注:1941年以后,非宁 绍籍的观众已经占到越剧观众的60%以上。(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戏曲菁英(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5页。))战时社会心态的产生,促使人们喜爱越剧,越剧观众的增加, 则直接导致越剧艺术在上海急速繁荣。
越剧的繁荣还得益于上海独特的文化环境。上海因开埠出现租界,因租界出现多元文 化。租界内外的侨民和各地的移民共处,形成上海独特的多元文化特质。多层次的公共 娱乐场所是容纳多元文化的重要载体。(注:罗苏文《近代上海:多元文化的摇篮》, 《史林》,2002年第4期,第9页。)各种娱乐场所使居于其中的各色群体有更多的娱乐 选择,被纳入到商业规律中的各种娱乐形式因市场逐渐迸发生机,逐渐形成多元文化的 和谐共处。各地的移民在多元文化的陶冶中,也形成对待新事物宽容渐进的态度。“战 前为绍兴各地所不兴,政府且县有禁律,禁止演出,时至今日,越郡各地,凡遇酬神敬 主,尚在摒弃之列却能为上海人这样赏识,风行一时,不但高腔乱弹班,反被漠视,且 有销声匿迹可能,即平剧亦大受其威胁”(注:《畸形发展之上海的笃班》,《越剧报 》,1946年9月22日第3版。)这段战后报纸上刊载的一段文字,正是上海多元文化气质 下宽容渐进态度的验证。越剧在上海呈现出的繁荣,是上海“海纳百川”精神的结果。 上海文化的博采众长、拿来主义特点,给了越剧发展的自由空间。不论从前如何而论今 后之发展、成长如何;不论现在如何而论拿来之后发展如何。越剧从乡间小调发展成为 一大地方戏曲,上海宽容的文化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