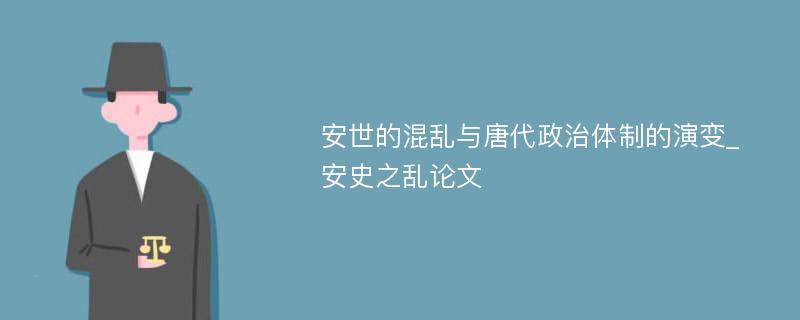
安史之乱与唐代政治体制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史之乱论文,唐代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入,古代帝国的政治体制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目前已经出版的著作,基本还没有触及到整个中国帝制时代长时段的体制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有许多关键的环节,标志着政治制度划时代的变革;也有许多影响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造成了某种划时代的变革。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演进过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期,而唐代本身的制度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安史之乱被认为是将唐代历史划分为前后两期的转折点,其对于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战争是影响政治制度演进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学界以往很少关注安史之乱及此后的战争环境对唐帝国在制度层面上变革的意义。实际上,它为唐代制度的演进促生了许多新的因素,并使得高宗武则天以来尤其是玄宗时期制度的调整(注: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制度的调整,是唐代制度变化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本文论证的前提。可参看拙文《论唐高宗武则天一对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新的形势下出于战争的特殊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安史之乱及其后直至德宗建中(公元780—783年)年间的战争环境,在由唐制向宋制的过渡之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
一、战争带来的新问题及使职体系的形成和巩固
使职产生的原因是统治形势的变化导致的新事务的出现,由于制度上规定的官僚体系基本是具有固定机构和固定职掌的,而国家事务却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临时性的使职派遣就成为许多王朝都具有的现象。但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出现的使职差遣,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行政机制,临时派遣的使职演化为固定的职务,并逐渐形成一个按照新的机制处理政务的体系。与原有尚书六部行政体系相比,使职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本司之官不治本司之事,要差遣他官来判决;即使本司之官要治本司之事,也需要特别的授权(注:参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9页。)。唐代的使职差遣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很普遍,但使职体系的基本形成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制度的变化归根到底是国家政权统治形势变化的结果。安史之乱的爆发为唐王朝的统治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而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巩固。
战争带来的新问题首先表现在财政供应方面。本来在天宝年间,由于土地兼并及其引起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破坏,新的赋税征收原则尚未完全确立,国家的赋税收入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财政问题凸显,财政使职不断扩大;而杨国忠以其特有的经济之才以及特殊的背景,先后以度支员外郎、郎中兼领十数个使职,并以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取得了总理财政收支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财政总管。而这种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由一人总管财政的制度,由于战备供应的需要,在安史之乱后被继承和巩固下来。战争之初,第五琦至蜀中奏事,向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职任,使济军需,臣能使赏给之资,不劳圣虑。”玄宗大喜,即日拜监察御史,勾当江淮租庸使。寻拜殿中侍御史。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迁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迁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注:《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据《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度支使条,“韩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河南五道度支使”。其时当在迁司金郎中之后、户部侍郎之前。又《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户部侍郎条,“至韩元元年十月,第五琦改户部侍郎,带专判度支,自后遂为故事,至今不改。”)。从第五琦的仕历可以看出,战争使得整个官僚机构遭到破坏,更加不可能由原有户部诸司来承担赋税征敛和战备供应的任务,而是直接继承了开元、天宝以来发展起来的使职制度,即依托于御史系统派使勾当,并由一人总官。然其阶官尚须寄托于户部,随着第五琦所领的使职越来越多,他的阶官也从司金郎中、度支郎中做到户部侍郎,说明户部职官已经演化成为寄托财政使职品级身份的阶官了。
由一人以判度支的使职身份总理财政的制度,在使得财政事务的管理完全使职化的同时,也为唐代财政管理体制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唐前期的财政管理体制是户部四司按照土地户籍与租调征收、国度支用、库藏出纳、仓储出纳等不同环节分工管理的,其中尤以户部根据户口丁身确定岁入为基础,以度支制定国度支用计划(即财政预算的编制)为中心(注:参见李锦乡《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8页。);而安史之乱以后的财政管理,其发展方向是通过使职按照钱谷来源的种类或地域划分进行的(注:参见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两种体制转换的前提, 是经过战争强化了的判度支总揽财政的制度,它以一人总管的制度打通了财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其后由度支使、盐铁转运使和户部使三司分掌财政的制度,只不过是将原有判度支的职权进行平面的分割而已。
战乱还造成了官员人事档案的丢失以及由此带来的铨选和考课的混乱。这种混乱局面要到德宗贞元四、五年间才开始得到整顿。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八月的吏部奏文中, 已经指出了这种状况:“伏以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欺诈。分见官者,谓之擗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甲,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比来因循,遂使滋长。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实资检责,用甄泾渭。”并因此提出了整顿的办法:“谨具由历状样如前。伏望委诸州府县,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样通状,限敕牒到一月内毕,务令尽出,不得遗漏。其敕,令度支急递送付州府,州府待纳状毕,以州印印状尾,表缝相连,星夜送观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驿递驴送省,……其状直送吏曹,不用都司发。人到日,所司造姓攒勘合,即奸伪毕露,冤抑可明。”(注:《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在这次对铨选的整顿中,吏部直接指挥州府,其间又通过度支使的急递系统,并由观察使将管内州府应有出身以上者的由历状汇总上报,直接送到吏部,而不通过尚书都省。这就反映出使职在沟通中央和地方政务方面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尚书省内部都省地位的下降。如果说,铨选的整顿并未在行政体制上造成多大影响,因为选官管理体制在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即已基本调整完成;那么,安史之乱后对考课混乱局面的整顿,则使得考课事务中的使职有了发展。考课的混乱局面和流于形式化的弊病,正如《唐会要》卷五八考功郎中条所指出的那样,“自至德以来,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使,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据《唐会要》卷八一《考》上记载,还在宝应二年(公元764 年)正月,根据吏部考功司的奏请,设立了京、外按察司,“京察连御史台分察使,外察连诸道观察使,各访察官吏善恶。其功过稍大,事当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状报考功;其功过虽小,理堪惩劝者,按成即报考功,至校考日,参事迹以为殿最。”这是考课机构和监察机构在对于官吏考核事务中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中由考课向考察发展的重要环节(注:参见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这种结合是以使职的形式出现的。《唐会要》考功郎中条所谓“贞元二年九月二十日停考使”,颇疑即指上述京、外按察司,在贞元初年的制度整顿中,放弃了宝应二年设立京、外按察司即由考课机构和监察机构联合组成使司进行考核的做法,根据安史之乱以前“其外官考,……每年定诸司长官一人判校,京官即考功郎中自判”的传统,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考功员外郎不掌贡举的情况下,改为由考功郎中校京官考、考功员外郎校外官考,即“其考课付所司准式授定,遂令员外郎校外官考”。
战争带来的另外一个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一大批在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期间被胁从的受伪官。肃宗收复两京后,这些人都相率待罪阙下。为了审理这些人,经过反复讨论,“竟置三司使”。这是由御史台、大理寺和刑部官员组成的“三司使”制度化的完成(注:《旧唐书》卷五○《刑法志》:参见拙文《唐代司法“三司”考析》,《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战争还造成了礼仪制度的混乱,不仅出现了家礼散佚和私家礼仪逾制的问题,就连皇帝在南郊祭天的圆丘和李唐皇室的太庙亦毁于兵火,造成了国家大礼陵寝之礼和郊祀之礼的停废和紊乱(注:参见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载《敦粕粕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是对礼仪制度的整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开元以来派使检校礼仪、祠祭之事的做法得以延续(注:《唐要会》卷三七《礼仪使》。)。掌管礼仪之事的机构也逐渐由“掌天下礼仪、祭享之政令”的礼部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的太常寺转变为以礼仪使为首的,以整顿礼制、制定仪注为主的太常礼院。
以上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新问题从而造成行政制度上使职进一步发展的几个明显的方面。正是由于使职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冲击原有尚书行政系统的职权,进而造成尚书机构的逐渐闲废和新的行政体系的形成和巩固。
二、使司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与调整
严耕望先生撰有《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的长文(注:初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3年第24本,后经补订,收入《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其下篇专论唐代后期尚书省职权地位之转变与坠落。文中指出,尽管在安史之乱以前尚书省之地位与职权本已有逐渐降落之势,然“及安史之乱,戎机逼促,不得从容,政事推行,率从权便。故中书以功状除官,随宜遣调,而吏、兵之职废矣。军需孔急,国计艰难,权置使额,以集时务,而户部之职废矣。至于刑工之职亦不克举。诸部之中,所职未废者惟礼部贡举;然事实上亦一使职耳。”文中引用唐人于邵在大历元、二年间上表中所说:“属师旅之后,庶政从权,会府旧章,多所旷废。惟礼部、兵部、度支,职务尚存,颇同往昔;余曹空闲,案牍全稀,一饭而归,竟日无事。”(注:《文苑英华》卷六○一于邵《为赵侍郎陈情表》。时间根据严耕望先生的考证。)进而认为,“大抵军旅始兴,吏部失职最甚,刑工次之。军事期间,兵部尚有若干职权,财计诸使亦未完全脱离户部之控制。”亦即随着战争带来的财政问题、军事问题的突显,户部度支司(实为依托于度支司的使职)和兵部的职权(主要是武官的选举和管理)稍有保留。而其余诸司如“省中司门、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闲简无事。时谚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注:《南部新书》丁篇。)所以说,尚书省部分机构被闲废,是过于强调整齐划一的尚书六部体制在统治形势变化中的必然结果。
不过,安史之乱以后,尚书机构闲废的趋向,是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这可以从许多材料得到证明。所谓“自至德以来,诸司或以事简,或以餐钱不充,有间日视事者。尚书省皆以间日”(注:《唐要会》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条。)。《旧五代史·职官志》也说:“自天宝末,权置使务已后,庶事因循,尚书诸司,渐至有名无实,废堕已久。”即如户部司,随着其职权的闲废,本来在天宝年间建造得很宏丽的户部郎中厅、员外郎厅和户部考堂,“乾元以后,毁拆并尽”,成了一片荒芜的“户部园”(注:《唐要会》卷五九尚书省诸下户部郎中条。)。正如严耕望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大体在于邵上表二十年之后,陆长源对于尚书六部的职权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官曹虚设,俸禄枉请。”(注:《全唐文》卷五一○陆长源《上宰相表》。)这就是说,不仅是过去的闲司更加闲简无事,即使如兵部、户部,亦成虚设。严耕望先生认为,兵部的失权,是由于“方镇跋扈于外,宦官擅兵于内”;而户部的失权,则是由于“财政诸使位权日重,形成所谓三司制度”。
然而除此之外,更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而不应仅从不同官职间职权的转移来分析。高宗武则天以来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破坏,赋税征收方式的转变和募兵制的出现,势必造成“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的情况。因为唐前期的户部本来就无“版图”,《唐六典》谓户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旧唐书·职官志》谓其“掌天下田户、均输、钱谷之政令”,而不言“版图”事。在唐前期以租庸调为主的赋税制度下,征收标准以户口丁身为主;而均田制下政府并不掌握各地的实际耕地面积,户部统计的全国田亩数也只是根据“百亩授受”之制的理想而确定的“应授田”数,而不是实际耕地面积(注:参见《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55页。)。版图在唐前期并不成为问题。所谓“版图”的概念,是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割据和其它形式地方分权的出现而出现的,指的是两税法实施后赋税征收标准由以户口为主变为以土地财产为主,中央政府对各地土地的实际控制,亦即版图变得至关重要。如元和七年,“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发生军乱,都知兵马使田兴被兵众推为留后,其令军中士卒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注:《资治通鉴》卷二三八。《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作“以六州版籍请吏”;《新唐书》卷一四八《田弘正传》作“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并谓其“图魏、博、相、卫、贝、澶之地,籍其人以献”。)此版籍指的即是版图和籍帐。又,唐前期的兵部也不管“戎帐”,即不负责实际统领军队。《唐六典》谓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图,厩牧甲仗之数,悉以咨之。”《旧唐书·职官志》谓其“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唐代前期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负责统领军队、指挥战争的也不是兵部,主要是诸卫大将军和将军以及由皇帝临时指派的行军元帅、行军总管等。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以后,军队的统领体制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节度使为主的地方军将专兵及其后中央宦官统领禁军的局面。但不能说是节度使和宦官夺了兵部之权,因为这是在原有兵部职权之外新出现的事务。实际上,战争造成的军事问题的凸显,并不意味着兵部军事职权的强化,而是造成了宦官和宰相掌兵权,而这种权力在唐前期基本上是由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同样,财政问题的凸显,则导致了财政使职的膨胀,以及宰相掌财权。这是宋代最高行政权一分为三,即由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分掌民政、兵政和财政的制度的滥觞。
新形势下不断增加的新事务,导致了使职系统的发展和尚书六部在行政事务中地位的下降。但是,旧有的制度模式和政治体制在制度转型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由此暴露出来的政治体制的弊端,促使人们对开元、天宝时期的制度进行反思,在没有找到新的制度模式之前,恢复开元前期以前的制度便成为理想的目标。而事实上不断发展的使职大都因事而设,或表面上仍依托于六部体系,或权宜济急而毫无章法,从而导致实际政务运行中的混乱。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不同官僚的实际利益依托于不同的体制,对于制度的整顿就成为高层权力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很快开始了以恢复尚书六部和九卿之职权为目的的制度整顿。前引严耕望先生文中谓“代宗大历中及德宗初年,君相深惜旧章之坠失,屡敕规复旧章,重建尚书省之地位与职权”,并对此有详细的论证,此处不烦赘引。惟《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条所载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及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都强调了尚书省的“会府”、“政源”地位以及政治体制中六部九卿与使职系统的本末关系,透露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即谓尚书六部犹如《周礼》六官之分掌国柄,“犹天之有北斗也”,是“法天地而分四叙,配星辰而统五行”。制度变革过程中的这种指导思想与安史之乱以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托古改制(注:关于托古改制在制度变革中的意义,笔者另在拙文《北周官制与南北朝隋唐间政治体制的演变》(待刊)中进行了论证,此不赘述。)。建中、贞元年间杨炎、刘晏和崔造、韩滉围绕着罢使和还职六部的斗争,以及关于尚书省官员是否每日视事的争论,都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另外,严耕望先生未予论及的九卿之职权与地位的恢复与整顿,其实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展开。如前引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敕中,即强调了“九卿之职,亦中台之辅,大小之政,多所关决”。《唐会要》卷三七礼仪使条又载,“大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敕,停礼仪使事,归太常。”或此二者本为同一敕,都是强调使职还权于九卿。
不过,由于使职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产生的,自有其合理性。在新的行政机制尚未确立之前,不可能由原有的尚书六部完全加以取代。形势的变化使得制度不可能发生简单的回归。如贞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两税钱物,委本道观察使、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等并停;其度支、盐铁,委尚书省本司判;其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注:《旧唐书》卷一三○《崔造传》。)其目的,除了权力斗争之外,还是想罢使而还职尚书六部。但到年底,崔造的改革导致了“事多不集”的后果,由于“诸使之职,行之已久,中外安之”,使职体系得以恢复(注:《资治通鉴》卷二三二。)。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使职的发展、使职行政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引起的使职与尚书六部和九卿职权的冲突,并非能够在短时间内调整过来的。这种调整的完成,实际上就意味着两套行政体制转换的完成。这个过程延续了很长时间,晚唐至北宋还有过许多次关于还职六部九卿的争论和改革,直至宋神宗元封年间的官制改革,才将新的使职差遣机制注入原有六部行政体制之中,以六部职权的扩大和完善而最后完成。
三、中枢体制新格局的演进
随着行政体制的变化,以君主和宰相关系为核心的中枢体制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开元时期形成的中书门下为决策行政合一的机关、宰相与三省分离的中枢体制(注:参见前引拙文《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转变》。),在安史之乱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宰相职权的进一步政务化,相权与君权进一步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翰林学士和宦官政治地位的上升。
宰相职权的政务化,是政治权力不断世俗化的表现。随着国家形态的不断成熟,政治权力对于沟通天人、调和阴阳的职能在逐渐萎缩。自秦汉以来,关于宰相职权的政治观念不断地有所变化,正体现出宰相职权的逐渐政务化这样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明显趋势。汉初陈平认为,“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注:《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后来丙吉也认为,宰相不亲小事,三公典调和阴阳(注:《汉书》第七四《丙吉传》。)。到唐代,这种意义只是体现在徒有虚名的三公身上,故《唐六典》称:“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而唐代的宰相,是要掌管具体事务的。这种观念的变化与整个政权观念的变化有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尚书省成为宰相机构,在帮助皇帝进行决策的同时,还是执行政务的最高领导机关。到隋唐之际的三省体制下,尚书省左右仆射作为当然宰相,也还是掌管具体的行政事务的。所以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左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遐,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注:《贞观政要》卷三《择官》。)这说明此前宰相是在受辞讼、听符牒的,即使其后仆射不关掌尚书省细碎务,而主要是助君求贤、处理冤滞大事,那也是具体的政务,只不过是小事和大事的区别而已。
随着尚书省退出宰相机关,仆射退出宰相行列,大抵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出现的中书、门下两省长官通过兼任尚书省官员而掌管具体行政事务,以及出现于中宗景龙年间的中书省官员裁决地方政务的情况,在玄宗时期开始制度化。随着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形成了宰相机构兼掌行政事务、中书门下为兼掌行政决策机关的格局(注:参见罗永生《唐前期三省地位的变化》,《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如果说开元、天宝时期尚书省已经完全退出了决策系统,尚书省的长官未经特别授权便不是宰相,中书门下成为裁决政务的宰相府署,形成了《唐六典》卷一所谓“其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即指中书门下),八座之官(指尚书省官员)俱受其成事而已”的中枢体制;那么,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使职的进一步发展,在行政运作中以使职系统为主导,尚书省不仅不预决策而且也不处理实际政务以至逐渐闲废,而使职跨越尚书六部直接上承君相,宰相通过中书门下对于行政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甚至直接下行过去由尚书六部处理的事务,宰相的职权进一步朝着掌管具体事务的方向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六部尚书尤其吏部、兵部尚书和重要的财政使职已经多由宰相兼领,但是,诸司官知政事者,“不复视本司事”(注:《新唐书》卷二○六《杨国忠传》。),严耕望先生因此认为,这是尚书省诸司官因参政而废本职,表明八座之官成了用以酬勋的虚衔,尚书省因此职权坠落(注:参见前引《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而安史之乱以后,由财政使职和吏部、兵部尚书入相或宰相兼领财计以及兼任吏部、兵部尚书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在当时人看来,被认为是宰相之任等同于有司,即诸司官知政事者在不归本司视事的同时,等于把本司之事带到了宰相府署中书门下进行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中书门下的主要职能即在于掌管选官、贡举、财政等具体事务,取代尚书省成为新的行政枢纽,形成了中书门下指挥使职和州县的行政体系。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 尚书左丞庾准上奏文中指出了这种情况,说:“省内诸司文案,准式并合都省发付诸司,判讫,都省勾检稽失。近日以来,旧章多废。若不由此发勾,无以总其条流。其有引敕及例不由都省发勾者,伏望自今以后,不在行用之限。庶绝舛缪,式正彝伦。”(注:《唐要会》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尚书省条。)庾准奏行的这种改革,是在大历、建中年间恢复开元以前制度努力的前提下出现的,这种改革的背景是在将政务由直接听命于宰相的使职还归尚书省之后,尚未将省内诸司文案归总由都省发付勾检,而这种权力仍然在宰相府署中书门下。不过代、德时期恢复尚书省职权的改革措施很快就被废弃,尤其是尚书都省始终没有恢复其早已失去的称为“政源”、“会府”的行政枢纽的地位。所以前引贞元二年(公元786 年)崔造奏请恢复尚书省职权之时,仍请将尚书省六职令宰臣分判,即将政务汇总于中书门下,中书门下成为行政枢纽。
行政权是国家政权中最基本的权力之一,没有行政权就不能构成完整的宰相权力。在唐初三省体制下,三省以其不同的作用在不同环节上共同构成完整的相权,其中尚书省的行政是基础。随着尚书省长官退出宰相行列,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府署,其作为行政中枢的地位就是不可取代的。由于在中枢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新体制下的宰相是由过去完整相权中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中书门下不断获得完整的行政权就成为这种新体制完善的方向。这个过程自玄宗时期即已开始,安史之乱以后有所强化,但也经历了一些反复。不过,宰相的职权朝着掌管具体事务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不可逆转之势。贞元三年李泌入相后,德宗根据宰臣分判尚书六职的制度,对李泌说:“自今凡军旅、粮储事,卿主之;吏、礼委(张)延赏;刑法委(柳)浑。”即以三宰相分判六部之事。而李泌则认为,“宰相之职,不可分也。……至于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注:《资治通鉴》卷二三八。)李泌的观点只是一种理想,尽管这种理想不断得到一些士大夫的支持,如直到文宗时期,因令宰臣分镇户部、度支之事,给事中郭承嘏还上书论之曰:“宰相者,上调阴阳,下安黎庶,致君尧舜,致时清平。俾之阅簿书,算缗帛,非所宜也。”(注:《旧唐书》卷一六五《郭承嘏传》。)但是,宰相之任等同于有司,已经是一种难以改变的客观情况,并且形成了宰相判事的具体规程和专门的文书,即如《唐国史补》卷下所谓:“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宋人沈括也说:“唐中书指挥公事,谓之堂帖子。经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礼也。”(注:《梦溪笔谈》卷一《故事》。)可见,中书门下已由过去作为宰相议事之所的政事堂,演化成为一个指挥百官百司处理政务的兼有决策行政职能的机关。宋人朱礼指出,唐代“宰相下行尚书省之事,尚书卿监上任宰相之权,此所谓无定制也。”(注:《汉唐事笺》卷三,《粤雅堂丛书》本。)这是将新体制下宰相的职权与过去的尚书六部和诸寺监简单的类比,这种类比很不确切,是宋人对唐制理解偏差中典型的一类。从中枢体制由三省制向中书门下兼掌决策行政体制(实际上是一省制)的转变来理解宰相职权的这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新体制下宰相职权的特点。
宰相的职权转化为以掌政务为主之后,虽然还参与决策,但主要表现在对于具体政务的裁决;或个别专权的宰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事实上也已经等同于天子的私臣,即必须经过天子的特别授权,而不是作为宰相在制度上所固有的权力。尤其是德宗在经过建中时期军事上、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之后,到贞元时期更加不任宰相,造成了宰相之间的排挤争夺,宰相的议政决策之权严重削弱(注: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第五章第三节《政事堂议政性质之转变》,列举了德宗时期宰相之间互不与闻国政、互相推委不敢决事以至群相轮流知印秉笔以及一相专政其他宰相禁止发言等情况,正可说明德宗不任宰相和宰相决策权力削弱的问题。此不备举。)。这种情况要到宪宗元和时期才有所改变。宰相具有一定的决策权,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德宗时期中枢体制的某些特征,是体制转型期所特有的。
由于宰相议政决策之权的削弱,君、相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导致了中枢决策体制的不完善性。而战争环境中又需要中枢决策机密而迅速,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正如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 年)针对李辅国专权的制书中所说:“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一。)所以,在开元以来以“知制诰”为标志的起草诏令之职逐渐使职化的情况下,以翰林学士供奉敕旨的做法得以继承下来,翰林学士的权力在特殊背景下扩展至极致。代宗、德宗时期,多次敕令罢除使职以还职六部九卿,恢复开元以前的行政制度,但对于中枢体制却少有论及。因为以翰林学士掌内诏,符合加强君主专制的时代需要。而制度调整的反复也还只是停留在行政体制的层面上,中枢体制却在朝着其固有的方向发展。
《旧唐书·职官志二》载翰林学士的演变为:玄宗即位,将张说等人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王者尊极,一日万机,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故尝简当代士人,以备顾问。至德以后,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尤择名士,翰林学士得充选者,文士为荣。亦如中书舍人例,置学士六人,内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从中可以看出,玄宗时期的翰林待诏是在国家事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一些文学之士召入禁中,帮助皇帝批答表疏,检讨宸翰,以备顾问,但也只是“或诏从中出”,即尚未完全取代中书舍人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和起草制敕的权力。而到安史之乱以后,则是“深谋密诏,皆从中出”。应该说,正是战争的环境使得翰林学士的参谋出令权得以凸显,并且逐渐在制度上固定下来。唐人论翰林学士之权重,都强调这是至德以后的现象。如陆贽在贞元三年上疏中所说,“肃宗在灵武,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注:李肇:《韩林志》,南宋洪遵编《翰苑群书》本。)元和年间韦处厚撰《翰林院厅壁记》,也说:“逮自至德,台辅伊说之命,将坛出车之诏,霈洽天壤之泽,遵扬顾命之重,议不及中书矣。”(注:《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谓“议不及中书”,指的就是翰林学士取代了宰相的机密谋议之权,填补了因为君、相在决策环节上分离之后的权力空间。而“权宜济急,遂破旧章”,更道出了由中书舍人起草制敕到翰林学士掌书诏的制度的转变,实因权宜济急的战争环境而完成。陆贽本人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说明,他在德宗时期之所以能够在军国大事的决策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以至于被称为“内相”,关键在于“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是特殊背景下使得翰林学士的权力扩展至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并未把翰林学士的这种权力视为合法的制度,而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如陆贽本人后来也说:“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又说:“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又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注:《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到元和以后,随着宰相决策权的恢复,翰林学士在军国大事谋划中的作用逐渐降低,并始终没有超出天子私臣所具有的权力范畴。
宦官在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亦因战争的特殊环境而造就。随着高宗武则天以来君、相在决策环节上的分离,便必然产生沟通君相的渠道。玄宗时期的高力士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注:《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被认为是唐代宦官充任枢密使制度的萌芽。安史之乱爆发后,“深谋密诏,议不及中书”,皇帝在内廷的决策机制逐渐形成,宰相的决策权力大为削弱,君相之间的沟通问题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宦官负责机密文书出纳传递的执掌被继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宗时期开始将宦官的这种职权称为“掌枢密”,永泰二年,用宦官董秀掌枢密,史言“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注:《册府元龟》卷六五五内臣部恩宠。)。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体制的转换过程中,宦官适时地填补进来,充当了皇帝与宰相的中介。这就为元和、长庆年间枢密使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加上宦官因为特殊的机缘获得了统领禁军的权力,随着贞元年间左右神策中尉的设立,宦官专权的局面因此形成。
综上所述,经过安史之乱及其后的战争环境的冲击和促进,唐代的政治体制逐渐地由前期的三省六部制向后期的中书门下和使职差遣体制过渡,并基本稳固下来。尽管在安史之乱以前使职的差派就已经很普遍,但正是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使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职体系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取代尚书六部成为政务的主要执行者。在尚书六部和使职系统职权的冲突与调整的过程中,经历过一些反复。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原有行政体制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行政体制的转换,不是简单的不同官职之间职权的转移,最终也不可能通过对原有行政机构职权的转变来完成;而必须产生新的机制,形成新的行政体系。安史之乱以后使职体系与尚书六部职权的冲突和调整,正是这样一个行政体制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经过晚唐五代延续到北宋前期,直到宋神宗元封年间的官制改革才最后完成。
中枢体制的演进也因此顺着此前的发展趋势展开,宰相与皇帝在决策环节上的距离越来越大。当宰相也逐渐成为统领使职的具体政务裁决者时,翰林学士作为内廷决策的主角,其权力发展至极致;但随着宰相决策权力在元和以后的逐渐恢复,翰林学士的决策权又有所下降。宦官作为沟通君相的枢机人员,也逐渐取得了其在制度上应有的职权。但宰相具有一定决策权,是皇权官僚政治体制的内在要求。安史之乱以后宰相的职权朝着掌管具体政务的方向发展,是行政体制转换带来的中枢体制转换的必然结果,并不能等同于三省体制下尚书六部和九卿的职权,更不是中书门下与尚书六部和九卿职权的简单替换。而宰相在裁决政务方面权力的发展和划分,也就成为后来政治体制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向。
标签:安史之乱论文; 尚书省论文; 六部尚书论文; 唐朝论文; 历史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旧唐书论文; 唐会要论文; 唐六典论文; 尚书令论文; 东汉论文; 隋朝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