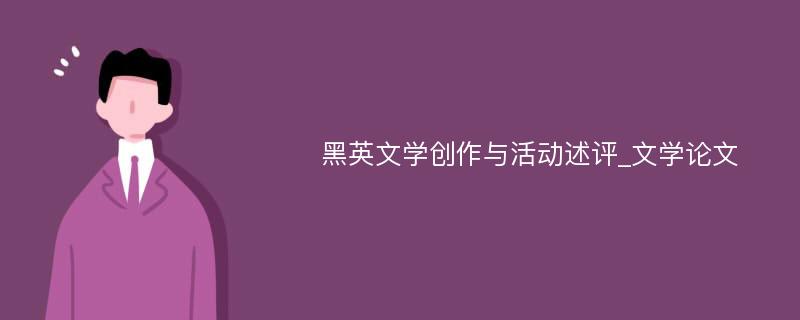
黑婴的文学创作与活动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黑婴,广东梅县人,原名张炳文,又名张又君,黑婴是他的笔名。此外,他的笔名还有伐扬、天马、高子里等。1915年黑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父亲是当地华侨商店的职员。7岁的时候, 他被送回家乡梅县念书,13岁回到棉兰。1932年,黑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于是,他告别了亲人回到祖国,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诗意也是最富于浪漫色彩的大学生活。同时,他也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处女作《使你的生活充实吧》(诗)发表于1932年2月1 日出版的《新时代》月刊2卷1期(无名作家专号)。
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叶紫组织的“无名文艺社”,积极参与各种文艺活动,参与筹备出版文学杂志《无名文艺》。1933年2月5日《无名文艺》旬刊创刊号出版,叶紫(1910~1939年)任主编,由上海新新印刷公司印刷,无名文艺社自办发行。后来为了扩大影响,《无名文艺》由旬刊改为月刊,改版后的《无名文艺》月刊创刊号于1933年6月1日出版,上海现代书局代为发行。在这一期的刊物上,黑婴发表了短篇小说《没有爸爸》。
小说《没有爸爸》以南洋华侨生活为背景,写了一位生长在岛国海滨的一位纯情少女维娜与一位外国水手的一次性邂逅。维娜为那位外国水手献上一位少女的真挚情怀后得到的回报是生下一个“没有爸爸”的私生儿小查利。而维娜姑娘却陷于爱情理想幻灭后的孤独与痛苦之中,在世人的冷眼与歧视里以泪洗脸,度日如年。小说展示的是爱情追求与欲望满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小查利对于姑娘而言那是爱的产物,但对于飘然而去的水手来说,则只是一次欲望满足的结果。故事暴露出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女性的不幸。小说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在哀婉缠绵的叙述中体现了年轻作者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和关注。
叶紫在《无名文艺》第一期的《编辑日记》记下了他与陈企霞于 4月8日(1933 年)到真茹拜访黑婴时读到《没有爸爸》时的感受:“全篇的技巧新颖,写来尽是些南国风味”。在此之前,叶紫还在3月23 日的《编辑日记》中写道:“读完黑婴的长篇创作《赤道上》,我觉得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作品,作品是部分的抓住了时代的核心”,并“决计从第二期起先行在本刊发表,然后再出单行本,编入丛书。”可见,黑婴与叶紫的不同寻常的文学交谊。但是,《无名文艺》月刊只出了一期就停刊了。连载《赤道上》的计划也就自然落空。笔者所知单行本也未出。
后来黑婴有篇名为《赤道线》的中篇小说在《中国文学》一卷二期至六期(1934年3~6月)上连载,或许这就是叶紫所说的《赤道上》。
《赤道线》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马来半岛上的一家华侨工厂为故事背景。主人公作新是一位丧母失怙的华侨青年,作品以他为中心展开叙述,意在反映“九·一八”之后,海外华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奋起反抗抵制日货,配合祖国抵御日军侵略的斗争,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海外华侨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对中国人的懒散、缺乏锐气、缺少凝聚力的民族根性也多有批判。由于作者缺乏实际斗争生活的经验,在表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时显得生硬、粗糙,初学写作者的激情抒发代替形象塑造的通病,极为明显。人物性格模糊,理念胜于形象,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倒是一些描写男女幽会的片断显得特别生动而富有生活气息,显露了作家的艺术才华。
作家第一次用“黑婴”作笔名是在发表短篇小说《帝国的女儿》时。《帝国的女儿》刊载于《申报月刊》第2卷第3期,小说写的是一个日本女郎在中国以零售肉体和青春为业的屈辱生活。作品的侧重点不在于日本妓女生活的艰辛或遭遇的不平,而是有意突出中国水手在民族积怨和肉体诱惑之间的冲突,展示现代都市生活中灵肉分裂的病态人格。
这灵与肉的冲突,和他后来创作中关于爱情与性欲对立的叙事模式,是黑婴早期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譬如,《不属于一个男子的女人》、《七日的玫瑰》、《咖啡座的忧郁》、《女人》、《冬天的呢帽子》、《爱》、《生活在桶中的人们》、《新加坡之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创作,当然其中还应包括前面提到的《没有爸爸》。这些创作汇入了30年代海派文学性话语模式之中,成为研究30年代上海文化的重要文化文本。
黑婴创作勤勉,很快成为一颗引人注目的文坛新星。1933年12 月1日出版的《矛盾》文学月刊2卷4期上推出的文坛新人中就有黑婴,而且还刊登了他的照片。他的创作结集的不多,主要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他还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化史上有过广泛影响的《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经常撰稿人之一。在《自由谈》上,他发表过许多诗歌、散文和小小说,而且数量颇丰。以至于半个世纪之后,著名文学史家唐弢先生还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在《自由谈》的经常撰稿人中“在速写、小小说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各各表现了他们熟悉的富于乡土色彩的生活图景”(注:见唐弢为《申报·自由谈》影印本所写的《序》,上海图书馆1981年影印出版。)的就有黑婴等人。
“富有乡土色彩”一句已经提示我们,黑婴创作的另一方面内容——那就是“乡土之恋,故园之思”。他几乎是疯狂地病态般地呼唤着他心中的故乡和亲人。“白发的祖母”、“微笑的母亲”、“天真的妹妹”,是他亲情的萦绕。他常以虔敬诚挚的孩子之心,“呼唤着母亲”、“祝祷祖母的健康”,日里梦里,都生活在对故乡的憧憬之中,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牵动他的神经,以至于感怀不已:
海边也有挺直了身子的椰子树。那儿的市上有怪味的榴莲的。……太阳是炎热的。
风是带着盐味的。静静的晚上有静静的月亮,静静的河畔有静静的歌声(注:《南岛怀恋曲》,见小说集《帝国的女儿》,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3月出版,第34页。)。
类似这样富有诗意的笔触总是高频率地出现在黑婴的笔下。
黑婴产生浓重的“怀乡情绪”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他自小在南洋岛国和山地的梅县家乡长大。乡村农业文明形成的阿波罗式的文化模式,塑成和凝定了他追求平和宁静生活的心性特征,当他以“地之子”的单纯和天真,质朴和厚道进入快节奏、讲效率、少温情、重实利的城市中时,不免有如掉进了一个魔窟一般,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异己感、荒谬感和怪诞感,与心理上的不适感随之而来的就是深刻的感伤和孤独,寂寞与颓唐。他说:“在大学里本来是不该喊寂寞的;那么多青年男女在一块儿生活着。但是我是寂寞的”(注:《再归国途中》,《新时代》月刊4卷2期,1932年3月出版。)。可见,在“城”与“人”之间, 他是显得多么地格格不入。作为生长在殖民地的一个侨民的儿子,他本来就有一种漂泊无根的悬浮感和无所归依的放逐感,他说:“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哪儿是我的祖国”,“我的脑子里并没有祖国的观念”(注:《再归国途中》,《新时代》月刊4卷2期,1932年3月出版。)。 可见,他渴望找回属于自己的根!但是,30年代半殖民统治下的祖国却让他深刻失望,经历了像闻一多从美国带着憧憬回来,却“发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一般的深刻失望!“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他怎能不黯然神伤?因此,可以这么说,他的感伤既在于他未回国之前,更在于他已回国之后。想象中的祖国与实际身处其中的祖国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不免感到惶恐与困惑!心灵的荒芜与孤独,使他不断努力寻找情感和心灵的栖居之所,以求获得内心的根源感和行动的自信心。因而,他的心远离“恶浊的都市”,飞往“诗意的乡村”,黑婴“怀乡情结”盖源于此罢(注:参看拙作《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载《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黑婴的创作在技巧上从一开始就受到新感觉派的影响,尤其是被称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对他影响尤为明显。黑婴在还没有回到上海之前就已经读过了穆时英的《公墓》,他“很喜欢它那抒情、带着淡淡哀愁的情调”(注: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到了上海后黑婴还曾去拜访过当时已是声名鹊起的穆时英,他后来回忆说:“穆时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作家”。这位银行家的儿子还请黑婴一起去饭馆吃饭,后来,他们还成了朋友(注: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茅盾很早就慧眼独到地指出,说黑婴的“作风同穆时英非常相像”(注:茅盾:《社谈:新作家与处女作》, 见《文学》月刊创号刊, 1933年7月1日出版。)。他这话虽是针对发表在1933年7月1日出版,由郑振铎、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创刊号上黑婴的短篇小说《五月的支那》而言的,但根据我们前面述及黑婴与穆时英的关系和黑婴作品的实际情形看,茅盾的评价非常中肯。
我们还可以在黑婴小说中看到他对新感觉派的有意模仿和效法,其对刘呐鸥、穆时英小说文本技巧的直接借鉴尤为明显。1934年4月, 上海出版的通俗画报《良友》第87期,刊登了黑婴的一篇《当春天来到的时候》,文中像携带一枝手杖似的挽着路旁的少女的比喻就取自刘呐鸥的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而用惊叹号“!!!!!!!!!”构成画面来加强惊讶感的视觉效果的做法,又是对穆时英的小说《黑牡丹》中的类似技巧的创造性的移用!《黑牡丹》里有一个都会的巡礼者自觉乏味的生活“琐碎到像蚂蚁”。那“一只只的蚂蚁号码3 字似的排列着”,如“333333333333……没结没完的四面八方”地爬过来。《当春天来到的时候》开头两段和最后两段几乎完全重复,只是句子的顺序以回文般的方式倒转过来,开头: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
这暖和的季节是最适合在外面散步的。念着我的第一句诗,轻快地在黄昏的街上走。
阳光带着难舍的恋情吻着二十二层的摩天大楼顶;夜雾已经慢慢地在都会里弥漫起来。
小说的结尾只略去了“黄昏”两字:
夜雾已经慢慢地在都会里弥漫起来,阳光带着难舍的恋情吻着二十二层的摩天大楼顶;轻快的在街上走,念着我的第一句诗,这暖和的季节是最适合在外边散步的。
“当春天来到的时候——”
这种写法,也是脱胎于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在穆氏的小说中有两段描绘夜总会舞厅场景的文字:
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g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的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
女子的笑脸和男子的衬衫的白领。男子的脸和蓬松的头发。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飘荡的袍角,飘荡的裙子,当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呜呜的冲着人家嚷,那只saxophong伸长了脖子, 张着大嘴。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
以上两段,文字本身只作了很小的改动,而几个句子却以相反的顺序重复了一遍。这种重复,从文字内容看,似乎毫无新意,但这循环往复的形式本身却颇有意味,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生活的琐碎乏味,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单调——任何努力与挣扎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现代都市人对生活感到无聊、厌烦、倦怠的情绪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创作主体对现代都市人的存在方式和自身生存状态的把握被用本文的形式加以突现,它将有力地强化受述者的感觉印象,极大地加强小说文本的艺术张力。其表现技巧无疑具有极其鲜明的先锋性和实验性。
黑婴无疑可以归入新感觉派名下。而且,现在的一些研究者也逐步形成共识,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由严家炎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一书就收入了黑婴的小说《五月的支那》,吴福辉在《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1995年,湖南教育出版社)中则干脆就称他为“新感觉派后起之秀”,中国的“横光利一第四”(注: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第80~81页。)。另外,30年代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以现代主义艺术作标榜的《现代》月刊,也是青年黑婴爱读的刊物,他说,除了穆时英的作品外,“也很喜欢《现代》这本刊物”(注: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若从黑婴创作的小说本文考察,我们会发现在构建现代都市文学文本形式和建立新的小说范型上,黑婴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譬如他的一些小说,采取以地点的位移和变换推动故事发展的空间性叙事,一改过去以时间为发展线索的平面直线型的传统叙事模式;譬如非直线逻辑的组合、连缀、电影蒙太奇的拼贴技巧的运用等,为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艺术质素,重要的还在于“他找到了与自己的创作心态相对应的文本形式,这在现代小说创作上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尝试”。
当然,黑婴的创作不只局限于都市荒诞、怀乡情愫和性与爱的对立等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强烈主观感受的内容。他甚至还对人们把他划在新感觉派作家麾下不以为然,他说:“我受了穆时英《公墓》的影响,写过《五月的支那》那样的作品,忝列新感觉派的骥尾”(注: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他的自谦和不以为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他写这篇文章时(1988年国庆前夕)人们还没有从既有的历史框架中跳出来重新认识新感觉派,另一方面也确是因为新感觉派并不能涵盖他的全部创作,因此,他还说:“其实,我不断在探索,作品风格也不尽相同”(注:黑婴:《我见到的穆时英》,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这确是事实, 就此也道出了他渴望得到全面公正评价的个中之苦。
我们以为,黑婴有些作品的确极富写实味。它们非常贴近30年代的主潮文学——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如我们在前所述《赤道线》和后来的中篇小说《青春》、短篇小说《私货船》等,以及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后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卷》(1927~1937)中的《小伙伴》,均属此类。
抗战全面爆发后,黑婴回到印尼,在《新中华报》任总编辑。他一边编报一边创作,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抗日宣传的各种活动。
1941年7月, 黑婴由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到爪哇岛的雅加达(原叫巴达维亚),在董寅初夫妇创办的《朝报》作记者、编辑,继续致力于抗日宣传。1942年3月,爪哇岛全面沦陷,4月,由于汉奸告密,黑婴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雅加达市干东圩监狱。在此挨过近一年的铁窗生涯后,被转移到爪哇最东部的雪冷监狱,不久又被送往万隆集中营。这里关着大约八万多名欧美侨民,全部是男性。与黑婴同时或稍后关进去的华侨也足有八百多人。在万隆芝玛圩集中营,黑婴因正值青壮年(27岁)被定为一等劳务,每天都得参加高强度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下地耕种,车站卸货,等等,稍不如意皮鞭就抽到身上来了。在集中营熬过近三年,终于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 盟军在爪哇登陆,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占领统治的历史。1945年的9月15日, 黑婴和被监禁在集中营的八百多华侨难民,终于逃离了地狱的门槛,从死神的唇边获得了新生,恢复了自由。第二天,他和许多难友一样,登上了返程的列车,回到雅加达。后来,他和进步华侨一起共同创办《生活报》,自任总编辑。
黑婴离开上海返回南洋以后,其文学观念、创作姿态、创作方法和创作的兴奋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和转移,显现出向现实主义皈依的明显特征。从现在能够找到的他在集中营出来之后出版的以集中营生活和华侨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时代的感动》和中篇小说《红白旗下》来看,他几乎完全摆脱了新感觉派的艺术旨趣和文本技巧,一改过去的风格而变为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家了。他的这种变化和穆时英由倾向现实主义到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向转换,正好成反方向运动。这倒是一个极其有趣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1951年,黑婴独自一人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经香港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光明日报》任副刊编辑,主持文艺部的工作。次年,他的妻子蓝凤娇带着三个女儿也回到北京,离散的一家终于得以团聚。
“文革”期间,黑婴也惨遭迫害,被关押、揪斗,后来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黑婴重返工作岗位,任《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高级编辑,主编文艺副刊《东风》。虽然年事已高,但编辑之余,仍然笔耕不缀。出版了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和散文随笔《作家剪影》、《文海潮夕》(注:法国巴黎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国汉学家克劳汀·苏尔梦1982年3月18日致张又君的信。)。
长篇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由《山之恋》和《海之涛》两部既互相联系,又可独立成篇的中篇构成,前者原题为《漂流异国的女性》,曾在《海峡》杂志刊载,出版单行本时改现名。小说以南洋马来群岛为背景,以廖洁和袁丽萍两位华侨女青年为主要人物,着重展示主人公由背井离乡逃往异地,谋求生路到最后自觉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的生活经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南洋华侨的生活和斗争以及他们的爱国思乡之情、反侵略求独立的抗争精神,全书充满着爱国主义的高昂热情。这是作家一生中的最后一部小说。
法国一位汉学家认为,他“多注意华人社会内的妇女问题”(注:参看《黑婴早期创作年表·附录》。)。将前面所述的《没有爸爸》和黑婴在“文革”结束,重返文坛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漂流异国的女性》作个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一前一后的两部作品,尽管所写内容有很大的不同,但关注妇女命运的主线仍然清晰可见。法国汉学家的话,大体上抓住了黑婴后期小说创作的核心。
《作家剪影》和《文海潮夕》两本随笔集写的主要是现当代文坛的轶事、趣话或随想,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往事,大多是作家本人亲身经历或目睹,因而显得真实、亲切、可信,它可以帮助广大文学爱好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文坛的世态人情和作家经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参考资料。其文笔清新、活泼,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984年,黑婴从《光明日报》离休。1992年10月13日凌晨6 时在北京友谊医院病逝。遗孀蓝凤娇女士现居北京,哲嗣张燕先生现任职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四个女儿均随母姓,她们现居北京。
黑婴生前是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中国致公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中,黑婴以其富有个性的创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在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吸纳和借鉴,以及现代都市文学文本形式的建构和新的小说范型的建立等方面,黑婴都为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艺术质素,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学的创作,在新文学史上无论如何都应该记上一笔。
*本文于1999年3月31日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