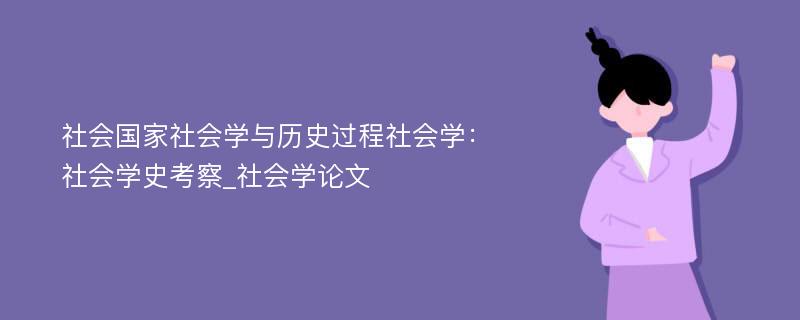
社会状态的社会学和历史进程的社会学———个社会学史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历史进程论文,状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社会学”这一词汇的发明者孔德在上个世纪为这门研究社会的专门科学——他心目中所有科学的皇后——规划知识体系时,他倾向于将其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从静态的角度对社会有机体进行解剖式分析,找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结构;二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进程。他将前者称为社会静力学,将后者称为社会动力学。但是,今天我们若回头印证于社会学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孔德所构想的社会学的这两个知识部门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同步平衡的发展。大体上说来,上个世纪的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近代西方工业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无论是孔德、斯宾塞、托克维尔、滕尼斯,还是马克思、韦伯,这些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们基本上都是从历史的视野或者说发展进程的角度来提出他们各自的问题和命题的。社会发展变迁进程的性质和动力是他们共同关注的核心课题,虽然他们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具体切入点各有不同:孔德从人类理性的发展分析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从技术和科学的劳动组织方面来说明现代工业社会的诞生;托克维尔研究了民主(社会平等化)的发展及其后果;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来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而据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命运;而韦伯则以探讨考察近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化过程及其前景为其一生之学术工作的核心主题。即使是涂尔干这位通常被看作是社会学中功能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方法的始祖,也表达了对于社会发展进程问题的关切,虽然他表达的方式与马克思、韦伯等人有所不同。(注:Bellan,R.N.,'Durkheim and Histor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24,1959.)但是,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当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后,十九世纪学者们的上述学术兴趣却发生了明显的转移。二十世纪专业社会学家当中的主流团体,其关注的焦点已从历史的架构中转移,转向了现代社会的系统性研究,对于动态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探索已为静态的社会状态分析所取代。恰好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指出的:“如果说前一阶段(指十九世纪——引者)的社会学持的是赫拉克利特的基本观点,即一切都是流动的——所不同的是,人们几乎理所当然地把社会发展这一条河看作是朝着越来越完善的方向、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流动的——那么后一阶段的社会学所持的则是埃利亚学派的观点。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埃利亚把箭的飞行视为由一系列的静止状态所组成的。”
(注: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三联书店1998版,第15页。)在二十世纪的数十年间占据着西方社会学霸主地位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便是上述以状态研究取代过程研究的代表。帕森斯理论观点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基本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基本的组成部分中区别概括出所谓的“模式变量”(如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泛布性-专门性、情感性-情感中立性、自致性-先赋性、自我取向-群体取向),用一系列两相对立的概念把事实上正在形成和已经形成的社会现象分解为仿佛与生俱来的两相对立的状态,这些对立的状态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各种类型的社会之中,就象化学物质组成的混合物那样。在帕森斯看来,社会就象某个玩牌者手里的一些纸牌,每一个社会都是纸牌各种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在帕森斯的理论模式中,历史变化的具体复杂过程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他也不能不涉及到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即使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他也把变化简化为状态。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在通常情况下都处于一种稳定不变的平衡状态。只有在社会规定的义务被忽略、当相互适应的状态被打破的时候,这种平衡的社会状态才会发生变化。即社会变化通常只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制度在外界干扰下出现的一种偶然现象。并且,按照帕森斯的观点,这种受到干扰的社会将会重新力求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迟早会形成具有另一种均势的“体系”。与那种认为应该以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为前提来研究处于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观点相反,帕森斯认为应该以那些在观念上通常被视为处于静止状态的社会为前提来研究一切变化。于是,社会便被视为一种“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又被视为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即使是一个有着多种形态的“高度发展”的社会,也常常被看作为一种静止的、孤立的状态。他并没有把这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究竟为什么、怎么会发展成这种具有多样化状态的问题视为社会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按照这种主流的、静止的体系理论,社会变化、社会进程和社会发展,包括国家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都只是一种“附属的东西”,在对短期的社会状况的研究中常常只是被当做一种“历史的序曲”。对于理解“社会体系”及其“结构”和“功能”来说,并不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被当代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概念本身,如“结构”、“功能”,就已经打上了把过程简化为状态的这种思维
方式的烙印。
而帕森斯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除了结构功能主义,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特别是社会学知识生产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后所发展起来的许多理论方向都具有上述这种非历史性的特征。在《社会学中历史取向的复兴》一文中,茨托姆卡(P.Sztompka)指出,二十世纪在美国发展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方向,如社会行为主义、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以及结构功能论等等,都“自觉”其本身是从“社会事实的历史方向”抽离出来的理论,是非历史性的或者用茨托姆卡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历史的社会学”(sociology without history)。(注:Sztompka,P.,'The Renaissance of 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Sociology',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1986,No.3.)
二
为什么十九世纪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曾热衷于长期社会进程的研究,而在二十世纪却一下子转向了非历史的状态研究了呢?对此现象,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解释。史蒂芬·梅内尔(StephenMennell)曾从社会学所接受的知识影响来分析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主流社会学研究中非历史性倾向的成因。首先是人类学的影响。一战以后,功能主义分析方法经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之手而在人类学中大行其道,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学,特别是成为帕森斯社会学理论的主要解释工具,而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正是为了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进化论者在说明无文字社会的习俗时总是求助于“臆断的历史”的做法而逐步形成的一种对实地研究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进行“非历史性”的“共时”关系分析的方法。除了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来自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的影响也助长了社会学的非历史性倾向。相对主义本来也只是一种理解异种文化的思想和生活模式的方法论概念,但是到三十年代却逐步地演变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甚至是意识形态,它将对它的任何质疑都指责成是“种族主义”,从而,文化相对主义在拒绝对不同社会文化进行优劣评价的同时也拒绝了任何连续发展变迁的观念,哪怕是多线论的发展变迁观念。其次是横剖调查方法(cross-section survey motheds)和变量分析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事实上,梅内尔指出,如果不是与横剖调查方法和变量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相结合,功能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非历史化转向的影响也就不会那样大。正如阿多诺在与保罗·拉扎斯非尔德(Paul Lazarsfeld)的论争中所指出的那样,横剖调查方法本身内涵着这样一个假设,即社会现实可以通过它的构成元素——个体的性质而得到解释。除此之外,梅内尔最后还指出,法国的结构主义(特别是列维-斯特劳斯力图从不断流变的表面底下找出人类精神中之永恒不变的特性的学术取向)和英国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尤其是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书)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学研究的非历史性倾向,鼓励了从历史性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向静态的状态分析的转移(注:Mennell,S.,'The sociological Studyof History',in:C.G.A.Bryant and H.A.Becker(ed.),What HasSociology Achieved,The Macmillan.Press Ltd,1990.)。
梅内尔的上述分析解释,如果说只是在强化了二十世纪社会学之静态的状态研究的意义上而言,则无疑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假如从因果而言关系,那么,社会学对于梅内尔所提到的上述这些知识影响的接受,与其说是从历史性的社会发展进程研究转向静止的社会状态分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它的结果。是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制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选择,而不是相反。因此,关于研究兴趣的转向的根源还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上文提到的茨托姆卡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说明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学之非历史性的根源,认为社会改良主义、实用的现世主义、经验主义和具体研究中的微观策略相结合,导致了那种“没有历史的社会学”。(注:Sztompka,P.,'The Renaissance of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 Sociology',InternationalSociology,vol.1,1986,No.3.)不过,在此最应该一提的,笔者以为还是埃利亚斯的分析。埃利亚斯认为,从十九世纪的长期社会进程研究转向二十世纪的社会状态研究的最明显、最表面的原因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家所提出的有关社会长期发展的理论模式所赖以建立的某些假设和信条,在二十世纪掌握了更为丰富的材料的社会学家看来是值得怀疑和不可接受的,如社会必然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变化发展的观念,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眼中便属于意识形态的教条,是把“社会所应该成为的和人们希望它成为的”当做了实际存在的事实。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对于旧的发展模式的某些观点的拒斥并一定导致对探讨长期社会发展进程的社会学理论的拒斥。真正的原因,埃利亚斯认为,跟十九世纪的进步主义一样,还是意识形态在作祟。“如果说,关于社会应该成为的和人们希望它成为的模式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导致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学家把主要兴趣放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方面,那么另外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则导致了二十世纪社会学领域里主流理论家特别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的客观状态,导致了他们不重视社会形态的形成以及对长期的社会进程和对由这两方面的研究所带来的新的解释不感兴趣。”(注: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三联书店1998版,第15-16页。)在十九世纪,一些工业国家中的社会学家表达了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的社会信念、理想以及希望,这部分声音逐渐地压倒了另一部分旨在巩固封建王朝和贵族权力、旨在维护和保存现有社会制度的声音。因为前者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所以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的理想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因此他们*
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感兴趣。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和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联合在一起力图说明人类确实是朝着他们所向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工业国中的工业阶层最终替代了王朝时代的贵族和军事实权派而成为国家的统治集团;与此相应,已成为国家统治集团的工业阶层除了阶层意识之外,民族意识也越来越强烈,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都把组织成国家的民族的现状视为最高价值。历史的变化只涉及表面的东西,人民和民族是不变的。“民族思想”把人们的目光从变化的东西引向了现存的不变的东西。在老牌工业国家中,进步的理想为保持和捍卫现状的理想所替代。“在社会学的理论中,原来地位显赫阶层的理想曾为逐步强盛之工业社会理想所压倒,而现在,后一种理论又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已经上升并稳定了的阶层的理想所代替。”(注: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三联书店1998版,第25页。)社会学家的关注焦点从流动的社会历史进程转向了静止的社会状态、体系结构。
三
不过,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大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等)击破了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视社会现状为平衡协调、和谐静止的理想化状态的幻觉。与此相应,在社会学研究中,一方面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的霸主地位的逐步走向终结和其他理论流派如批判理论、冲突理论等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上述静态的状态分析模式开始经历人们的反思和批判。早在1959年,美国左翼激进社会学家米尔斯(C.W.Mills)在其《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即对西方社会学研究中的非历史性倾向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他具体指出了这种社会学的三种错误倾向:1、阉割历史。有些社会学者的历史理论“变成了一种阉割历史的压模机,它塞进历史的材料,吐出人类未来的图景(其色调往往是灰暗的)。”2、形式主义。形式主义者“把历史完全抛置脑后,而系统地论述人类和社会的本性。”3、杂烩式研究。有些社会学者把当前的现实“变成一系列互不相关而往往无甚意义的社会背景”。(注:米尔斯等:《社会学和社会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6页。)米尔斯认为,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应该是社会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他把这种思维方式具体解释为:跳出自己的范围,专心致志地认识社会的依存关系,认识历史的变革动力。这种思维方式的客观依据在于,每个个人及其特征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和一定的历史时期之中,人们的个人问题,无论是失业、贫困等物质问题,还是工作无意义或异化等心理问题,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
可以说,米尔斯以激进的姿态开了对非历史性的社会学研究进行批判反思的先声。自那时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视野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其结果,则如霍尔顿(B.Holton)所指出的那样:“近二十年来,西方社会学的研究,已见证了历史视野重新被导回社会研究范畴。反历史的结构功能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已逐步被削弱。……其结果是社会变迁性质的概念化和解释工作,已开始复苏。”(注:Holton,B.,'Histor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E.P.Thompson',TheAustralian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7,1981,No.1.)对于那种认为可以透过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系统研究来指出各种社会关系的通则的信念,人们越来越拒斥。而同时,人们越来越清晰自觉地认识到:无论是对于理解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而言,还是对于理解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模式而言,“历史”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这是因为:“过去的社会关系及其残余,不管是物质的、意识形态的还是其他,都会对现今的社会关系产生约束,而现今社会关系的残余也一样会影响下一个时期。……社会的演变过程是取决于路径的”(注:查尔斯·蒂利:《未来的历史学》,载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999年版。);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模式是代代相传的,这些模式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并且也被纳入现代制度的结构里。”(注:哈瑞特·布雷特利:《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变迁和连续》,载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因此,社会学家如果想彻底了解这些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生长发育出来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行为和思想模式的话,就须走入历史的领域。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指出:“社会行动者是历史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场(social field)的历史的产物,是特别的次场内某条通道中积累的体验的历史的产物。”而在说到“场”的结构的发生时又指出:“一个充分的、完整的社会学应当清楚地包括各种结构的历史,而种种结构的历史是在特定时刻的整个历史性过程的。……写一部结构的历史是必要的,这种结构的历史将会在每一个结构状态中发现:以前的斗争的产物会改变或保存结构;同时,通过构成结构的矛盾、紧张与权力关系,还能发现随之而来的变革的起源。”(注:P.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3、121-122页。)对于布尔迪厄的这番话,今天恐怕很少有人会不以为然。
社会学中历史视野的复兴也改变了社会学对历史学的态度以及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前,社会学家通常以一种轻慢的态度来界定他们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如埃尔伍德(C.Ellwood)说:“历史学是一种明确的、记述式的社会科学,其目的在于建构过去的社会图像。社会学则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化的社会科学,关注那些支配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法则和原理。……对社会学者而言,当代的社会生活确实比历史事实更要紧,就社会演进或其动态面而言,社会学或可视为某种历史哲学,因为它至少尝试为历史学具体描绘的社会变迁提供科学理论。”(注:Ellwood,C.A.,'Social Problem and Sociology',New York:AmericanBook Company,1935,P18.)英克尔斯(A.Inkeles)也说:“历史学者常常以细节的明确、具体为荣,此即历史学的特征。社会学者却经常从具体的事实中抽象、分类、推论。他们所关心的不仅是对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为真,而且是对许多不同民族的历史亦皆为真的原理原则。”(注:Inkeles,A.,'What is Sociology',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64,P21.)一言以蔽之,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就仿佛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生产普遍法则,历史学则消费普遍法则。这种关系状态对于社会学——且不说历史学——的影响显然是不利的。由于缺乏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以社会通则的生产者自许的社会学者在研究中不得不面对过去的历史的时候,通常要么就象米尔斯所说的那样“阉割历史”,要么就只好依赖于虚构的、神话式的过去或者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注:在此,社区研究就是一个例证。瑟恩斯特罗姆在《重访扬基城》(Thernstrom,S.,'Yankee City Revisite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30,1965.)中就批评华纳(L.Warner)关于扬基城的一系列文章,认为其中缺乏构成历史证据的批判性认知,扬基城系列中所呈现的有关过去的种种记载都是“神话式的过去。”受到指责的不仅有扬基系列,而且还有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其中还包括林德夫妇著名的中镇研究。(Bahr,H.M.andBracken,a.,'The Middletown of Yore',Rural Sociology,vol.48,No.1,1983.)但是,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中历史视野的复兴,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上述关系已有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卡尔(E.H.Carr)的观点,认为:“社会学变的愈像历史学,历史学变的愈像社会学,对两者而言都比较好。”(注:Carr,E.H.,'What is History',Harmondsworth:Penguin,1961,P62.)人们已认识到:“历史*
学或社会学的方法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如果只单独使用历史学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可能会对研究现象产生错误理解。”(注:哈瑞特·布雷特利:《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变迁和连续》,载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而一个奠基在历史学基础上的社会学对社会学将会有两大贡献:“第一,它可以将社会学的研究历史化,并将其研究积淀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第二,它也为我们提出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存在于历史研究或真实的历史中,但却始终为社会学家所忽略。最值得注意的是,它能迫使社会学者去检验:某一时间点上的行为的残余是如何束缚了接下来的行为。”(注:查尔斯·蒂利:《未来的历史学》,载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四
历史视野的复兴以及社会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转变已经导致了一门历史社会学的诞生。就重新恢复了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注而言,历史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古典社会学的一种回归,但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今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已扬弃了在十九世纪的学者中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出现的那种“西方中心论”倾向和埃利亚斯所说的那种“理所当然地把社会发展这一条河看作是朝着越来越完善的方向、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流动的”信念,与此相应,今天的学者也不再相信单线发展论和历史决定论。此外,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也不再采取以前经常采用的那种致力于在所有人类经验中找出一种普遍的时间模式(temporal pattern)的“后设史学”(metahistory)的形式,而是致力于对于相对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行真正“社会学的”叙述、考察和分析。
具体地说,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注:Mennell,S.,'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History',in:C.G.A.Bryant and H.A.Becker(ed.),What Has Sociology Achieved,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0.)第一种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关于过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past),学者们用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对生活于过去的某个特定时期的某个特定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行为进行深入地研究考察。属于这一类型的研究在研究规模上有大有小。微观的研究如K.T.爱里克森的《刚愎的清教徒》(WaywaardPuritans,1966)、L.戴维多夫(L.Davidoff)的《上流社会》(TheBestCircles,1973)等,前者研究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越轨行为,后者则考察了十九世纪伦敦上流社会的行为。相对宏观的研究则如摩尔(B.Moore)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1966)以及斯考珀(T.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1979)等,这类研究往往对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可比较的侧面和事件进行考察分析,以图概括总结出历史中类似的情形。还有更为宏观的、力图全面地再现过去历史上某个社会的全景的研究,如布劳代尔(F.Braudel)的《地中海和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1976)。
不过,上述这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更容易引起传统的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好评,而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一般会更加关注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第二种类型,即那种试图建构社会的长时段发展进程的模式(models oflong-term developmental processes)的研究。(注:当然,这两种历史社会学研究类型的区分也非绝对,如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从其研究的对象而言,无疑属于第一类,但从其研究目的而言,则又属于第二类。)这种类型的研究在此可以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和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为代表。在迄今已出版了两卷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沃勒斯坦以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系统论为指导理论,采用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和素材,对1450年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从而提出和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和基本逻辑。而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则从剖析西欧11世纪到18世纪的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人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的影响入手讨论了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结合社会结构变迁和个体层次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过程,提出了一种关于文明进程的理论。除了埃利亚斯和沃勒斯坦,还有其他许多学者如琼斯(E.L.Jones)、沃尔夫(E.Wolf)、麦克内尔(W.McNeill)、安德生(P.Anderson)等的一些研究也都可以归入此类。需要指出的是,象埃利亚斯和沃勒斯坦这种关于社会的长时段发展进程的理论通常总是力图揭示历史的进程是如何在一联串前后关联的事件的连锁作用中展开的,揭示目的性行动的非目的性后果如何又构成了接下来的目的性行动的非目的性条件。这使得关于长时段发展进程的理论总是与社会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social development)联在一起,而这常常可能被批评为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观念。不过,对此,历史社会学家们却有自己的理解。在《什么是社会学?》一书中,埃利亚斯指出,必须在某种社会变迁的必然性和这种变迁充分条件之间作出区别。(注:Elias,N.,'What is Sociology',London:Hutchinson,1978,PP158-174.)同样,在《历史社会学》一书中,埃布拉姆斯(P.Abrams)也指出,必须对两种不同意义上的“不可避免性”作出区分:“一种是对于某事物的存在来说那些不可缺少的条件都已具备这一意义上的不可避免性,另一种则是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已排除这一意义上的不可避免性。”(注:Abrams,P.,'Historical Sociology',Shepton Mallett:Open Books,PP145-146.)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明论证前者,但很难拥有足够的知识来证明后者。换言之,历史社会学能够建立一个前后关联的序列,以说明社会组织的前一种模式是后一种模式,出现的先兆,如果前者已经包含了后者得以出现的所有必要的条件的话,但是,这和能够预言前一种模式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后一种模式的出现不是一回事。
标签:社会学论文; 埃利亚斯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明的进程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