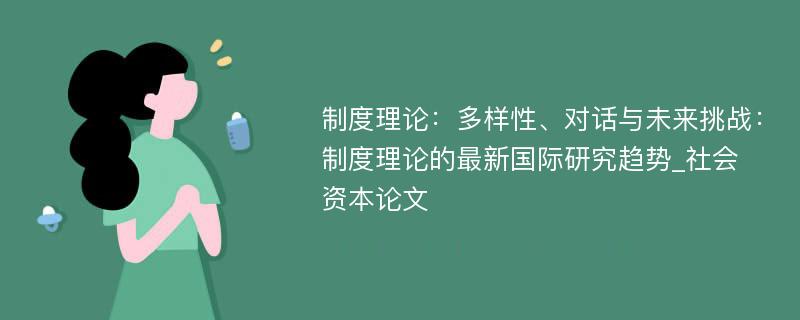
制度理论:多样性、对话和未来的挑战——制度理论国际最新研究动态介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制度论文,多样性论文,未来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制度(institution)现象一直是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关注的重点。在某些学科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抑或相当完善的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有些理论在其各自学科体系内甚至已被发展成主流的一部分。例如,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运动中,以科斯(Coase)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异军突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且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流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North)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这一流派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在西方,有人甚至把新制度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埃格特森,中译本,1996)。
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制度设施的重要性从未受到过怀疑,且一直是研究的中心问题。如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分层、社会群体、集体行为、家庭等诸问题的研究都是以制度设施为基本出发点的”(周雪光,1999)。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学界更是掀起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热潮,至90年代,以制度为主题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成为国际社会学领域内最为活跃且最富于成果的一个分支。
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领域亦然,传统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新(政治)制度主义都已成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流派,为分析各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当然,还有其它形式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在此毋需一一赘述。可以说,制度理论是社会科学界多年来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
去年,笔者从母校(丹麦Roskilde大学)获悉,在Klaus Nielsen教授的带领下,该校社会科学系正联合该系参与“制度、角色、制度化”这一长期研究项目的13位学者和丹麦其他大学的5位学者,以及一组走在该领域前沿的国际著名学者(包括诺斯在内,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瑞典、挪威、冰岛等国著名大学)组成了一个研究网络以履行一个历时3年的跨学科制度理论研究项目(注:参见http://www.ssc.ruc.dk/Research/projects/network-inst.html)。笔者及其研究生随即对该网络进行了跟踪研究。本文试图在检阅我国制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通过解剖该制度理论国际研究网络个案,向我国相关学科理论界介绍制度理论研究国际层面一些新的动向、主题、进展及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论尝试:通过不同学科、不同理论视角和共同感兴趣之交叉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促进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期待对促进我国跨学科制度理论研究有所启迪。
二、动因分析:介绍制度理论国际最新研究动态的必要性
介绍制度理论国际最新研究动态的必要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第一,系我国制度理论研究相对落后性使然。我们详细查阅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理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多种学术期刊后发现,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放弃有关制度理论的研究。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越来越关注和涉及制度问题,大量介绍、引进西方的制度理论和最新研究成果,并努力尝试运用相应制度理论分析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现象和问题,把有关制度的研究与中国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为改革提供了迫切需要、具体而又有针对性的理论准备和指导。但我们同时也发现,就制度研究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在许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如一些学者所评述,西方的制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同学科领域多个制度学派的萌芽和兴起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界新近演变的重要特点。其绝大部分研究的理论性都很强,有着明确的理论假设、研究设计和验证逻辑。研究选取的学科角度、课题和研究方法则多种多样。然而,纵观我国的制度研究,除少数领域、少数人外,相当多的研究仅停留在介绍和述评层面,虽然也在努力运用相关制度理论分析各种制度现象(经济学领域尤为如此),但许多理论解释缺乏力度,有时给人“生搬硬套”之感。社会科学学科中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成体系的制度理论用以解释具有独特背景的我国社会的制度现象。研究选取的学科角度、课题和研究方法则显得单调、重叠和薄弱,许多名为研究的论文其实仅系就某一思路、观点或侧面所进行的主观表述。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有些领域的制度理论研究还相当滞后。如政治学科,虽然制度现象从来都是其研究的重要主题,但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不管是理论的引进、改造还是建构都不充分。由于这些差距和滞后的存在,我们不能对制约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全面发展的制度因素作出富有效率的理性分析,进而也不能提出更多的促进全面发展的制度安排。也正是这些差距和滞后的存在,构成我们撰文介绍制度理论国际最新研究动态的第一、亦为最主要之动因。
第二,系时代需要新的理论突破使然。正如下文所会提及,当前在多个社会科学学科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制度理论的困境。“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人类的进步、发展方式和观念形态都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全球化、信息革命、知识经济等旋风迅疾地席卷、渗透进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已有的制度理论并不能全然“自由”地解释发展现状。要回应社会实践的巨大变化,必须发展一种进化的理论,对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设施进行分析验证,为新的制度安排提供理论准备和现实指导。而就目前来看,理论界似乎还有点措手不及。这是整个国际制度研究学术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我国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由于我国社会制度设施及改革道路的错综复杂都是独特的,加上当前又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时期,制度理论界所要研究的课题更为多样和复杂,更需要新的理论突破。
第三,笔者深感该研究网络的理念——通过对话和合作促进制度理论的发展——很值得国内学术界借鉴。怎样走出各种各样制度理论的困境,该研究网络寻求的途径是对话和合作。这种对话和合作不仅在同一学科不同理论流派间、还在不同学科相异学派间进行,不仅包括相同挑战主题、也包括不同研究方法的交流。诚然,我们也常常提及对话和合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提出“要重视经济学和社会学交叉的趋势”。在1997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折晓叶等多位学者提出了对话的重要意义:“显然的是,提倡学科对话,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可以说,我们正处于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冯小双、李海富,1997)以上说明我国学术界并非没有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意义。但是,据笔者所了解,我们缺少像这一研究网络所秉持的那种全面、深入的交流和碰撞。论及制度理论界,笔者注意到我们鲜有真正意义上的不同领域的对话和交流。
三、个案分析:制度理论国际研究网络简介
这一部分即是对该国际研究网络之简要、非全景式介绍。根据本文需要,笔者从所掌握的资料中选取了4个相关内容——背景和目的,对话、交流的典型代表及其必要性,研究目标,以及研究主题——加以介绍。
(一)背景和目的。近年来,在西方数个社会科学学科中出现了多种制度理论的困境(dilemma)。不同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几个相异阶段的发展,Dimaggio最近在《Journal of l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上撰文将其区分为三个阶段:即从“积极分离”(constructive disengagement)经“相互批判”(mutual criticism)到目前阶段——研究者围绕共同的两难困境发现了相同兴趣。基于这一事实,该研究网络全体成员达成这样的共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或许能从围绕相同理论挑战和交叉主题的对话和合作中获益。此外,也许力图使不同领域的方法论和解释目标达成综合并不恰当,但试图克服不必要且过时的学科边界以及在交叉与共同感兴趣的主题、挑战和困境的不同方面共同努力却是个好主意。有鉴于此,该研究网络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理论学派(尤其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相应学派)在共同感兴趣的交叉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来促进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二)对话、交流的典型代表及其必要性。该研究网络包括以下5个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内的制度主义典型流派: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NIE)、旧制度经济学(ol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OIE)、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ology,NES)、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theory,NIO),以及传统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HI)。
新制度经济学(NIE)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某些对新古典经济学挑战已获得广泛成功的领域,NIE甚至已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可视为旧制度经济学(OIE)传统复活的制度演化经济学。最近,新经济社会学(NES)已发展为社会学中很有希望的分支领域,它对经济学和社会学所传统关注的劳动分工理论公开提出了挑战,就像NIE一样。其他许多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从事组织研究者,则将他们的理论界定为“新制度主义”(NIO)。除了这4个学派(2个来自经济学,2个来自社会学),传统制度主义(HI,政治科学中一种制度理论)也包括在研究网络中。
旧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在许多方面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方法,就解释目标而言也是如此。然而它们来源于分离的学科,即使现今它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是很有限的,更多的交流有助于澄清许多问题,并更好地解释现象后面的本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分别代表了一种理论,是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内相应的主导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建构制度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相联系的。就方法论和解释目标而言,两种理论的分离是实质性的。然而,即使是处于分离领域的学者也不断地发现相同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其各自的认知范式内都不能得到满意解决。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家(如North)指出: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认知模式被社会构建的,而新制度社会学家则力图整合诸如交易成本等概念,并在产权、契约和代理问题等方面从经济学文献中吸取养料。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打开了整合认知和规范事项的大门,也为与始终强调这方面重要性的旧制度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当前政治科学中有三种形式的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新(政治)制度主义”和“传统制度主义”。前两种在这一研究网络中间接地出现: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类似于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制度主义在许多方面难以与新制度主义(NIO)相区分。而第三种,即强调集体行动和团体冲突的传统制度主义(HI),可视为政治学领域制度主义的典范。这一研究网络之所以包括HI,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HI同时整合了来自NIE和NIO领域的多种要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介于这两种理论中间的思想方法;第二,就试图在不同理论间架设桥梁而言,HI领域的学者已明显取得主要发言人的资格。
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交叉和共同的挑战,还应指出需要对话和合作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不同理论的概念,如“网络的外部性”、“革新系统”、“规制模式”和“商务系统”等,当前已作为试图理解经济和组织发展中的“路径依赖”、“互补性”和“背景依赖”特征之共同努力的范例开始出现和传播。这种理解特殊性的理论努力在许多方面有极大的帮助。然而,建立在一定基础上的为打破一般和特殊之间平衡的共同努力可能也都有自身的价值,这一基础就是分析、整合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历来被不同程度强调的制度之管制、规范和认知角色或抑制、迫使角色。
(三)研究目标。合作研究期望达成三大目标:第一,形成一个对各种制度理论多样性和交叉性方面的最新理解;第二,在有前景的共同主题、问题和未来挑战等方面发展一种艺术性的陈述作为未来合作的基础;第三,在选定的主题和问题上作出共同努力,以促进制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前两个目标将通过一系列专题讨论会(seminars)、网络的出版物,以及最后的论文交流大会来达成,而围绕选定的4个主题在研究网络存续期间所组织的4个国际研讨会(workshops)将用来实现第三个目标。
(四)研究主题。对话和合作有许多共同的兴趣领域和有望取得成果的主题。前述提及Dimaggio的文章列出了供未来共同努力的3个基本挑战:如何发展一种进化的(evolutionary)理论;如何将社会概念化为“构建的现实”(constructed reality);如何看待各种各样网络(networks)的流行以及它们同其他组织(institutions)的关系。以下研究网络所涉及的4个主题或多或少整合了这三方面的挑战。下面,将对每一主题进行简要说明,重点放在与研究网络中所涉及的制度理论流派相关性及其贡献、以及能进一步发展我们理解力的未来合作前景方面。
1.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认知模式和制度。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相联系,可以理解为行为主体不能预料决策之结果或不能推测确定结果出现概率的某种状态。主观经济学家和理性预期学派的专家们将不确定性看作概率性风险。可以这样说,在面对着具有非概率不确定特征的随机结构时,经济学既不能维持其最大化假设,也不能维持其均衡模型。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性的真实含义方面,经济学理论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有关投资和革新的分析领域。在不确定状态下,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由认知模式(mental models)引导的,而这种认知模式却又依赖于经济的制度框架。NIE和OIE领域的经济学家们所作的贡献已拓展了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知识。
在社会学领域,可以说不确定性问题为正统经济学的社会学转向提供了一个突破口(例如法国习俗学派,the French convention school)。NES的任务似乎是发展多种概念和从事有关自在、理性主体是如何在不确定状态下作出决策的实证研究,以取代已往的视角:关注于角色如何自愿地背离由非理性原则引导的利己目标。社会学家通过强调社会相互作用的不可避免来解释和理解不确定性和这种状况下的协同行为。因为行为的实际效果不能被充分预料,所以不确定性使得角色不可能根据其偏好来推断他们的行为,因此,当行为主体为了使其收入最大化,在不确定状态下进行决策时,注重他们所依赖的认知、结构和制度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以模糊(ambiguity)为特征的情况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挑战。有时候偏好和目标并不是稳定不变或始终一致的,而是变化和模糊的,因为偏好和目标是由难以明晰的组合和排序的要素构成的。进而,事实的解释以及相应的行为后果通常并非总是明白无误,而是相当模糊的。即使个体层面上存在着理解、偏好和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当涉及到决策团体是由许多不同个体构成时,模糊的问题也许更突出。在组织理论研究中模糊现象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由于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与其众多股东之间存在着多样性和各种价值观、目标和解释的冲突,所以组织常常会面临模糊决策。聚集于认知模式角色和处理模糊问题之制度作用的研究成果可视为组织理论的新贡献。在信息和决策间令人难以捉摸的联系使得我们有必要关注由认知系统和制度框架导引之信息处理的实际程序。这一研究网络包含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学派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内涵界定上似乎不谋而合。由不确定和模糊状况的不定性导致之偶然性,诸如层级结构、嗜好、惯例等,系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致力找出处方予以降低的对象,而他们的理念是与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社会学理论相联系的。因此,在此阶段,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更多的直接合作是有益的。
2.社会资本、信用和网络。近年来,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信用(trust)等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备受瞩目。运转良好的经济,其制度框架似乎是建立在共有信用,或更一般地说,社会资本存在并发生作用基础之上。是否以及如何创造信用和社会资本?对该重要问题的回答牵涉到经济治理的成败。而各种各样的网络(networks)则在此类问题中居于中心位置。
社会资本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根据一个广为流行的定义,是“指社会组织中能够通过促进协同提高社会效率的各项特征,如信用、规范和网络等”(Putnam)。非确定世界中促进交易、合作与学习等活动需要一种粘合剂,而“社会资本”术语即为这种粘合剂的概念化达成。社会资本一部分内化为个人利益(即人际网络中参与者之间的互惠),而另一部分则具有公益特征,如规范和普遍化信用。
信用是一种双向的期望,指在交互行为中任何一方都不会去利用对方的缺陷或漏洞。新制度经济学中机会主义(opportunism)概念的前提假设是信用的普遍匮乏。在不同社会,信用具有不同的基础,如家庭型、地区网络型,以及建立在更普遍和广泛基础上的信用,这被看成产生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原因(例如,见福山,Fukuyama)。与此相类似,在动荡不安之全球经济环境中出现的独特的地区聚合特定模式,被视为由于地区作为局部学习过程角色之功能日益增强所致。当然,这一切也有赖于由地区制度所造成的共有信任。
不同的社会资本数量和与机会主义相对立的信用普遍程度可以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对此人们没有异议。但是,对于信用是否可以被创造、社会资本是否能通过某种方式扩张,却争论不休。目前一种流传很广的宿命论观点认为,信用能够被发现但不能被创造。同样,从长远来看,规范常常是变化的,这种变化与社会干预和改革没有任何直接的或可预见的关系。社会资本的最新要素是网络,网络或许最易于被构造。也有一些作者认为信用能被创造,例如,通过建立新的互动形式,以及采用新的解释和认知模式作为干预变量。
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如Bourdieu和Coleman)概念化,并经由政治学家Putnam的著作得以普及。近来它已被不少经济学家所采用,并成为世界银行分析报告中的重要概念。Granovetter等社会学家的贡献在于指出经济交往中网络地位的至关重要性。接着,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开始频繁地应用网络这一概念。这样,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似乎存在着较好的理由以进行更多的对话和合作。
3.知识、学习和制度。近年来,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学习经济(learning economy)等概念开始日益普及。对于知识和学习的强调形成了新的视角和焦点,即从关注于给定之稀缺资源的分配转移到如何创造、分配和利用新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注重于经济变化又对制度日益感兴趣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制度毕竟常被理解为产生限定和规范行为的现象,导致稳定和秩序,而不是变化和学习。然而,新知识的形成,也即学习过程,是互动的社会性行为,这一过程有赖于经济的制度安排。
学习是一系列包括直接学习、间接学习和遗忘的复杂过程。知识和学问可分为4个类型:“知何物”(know-what)、“知机理”(know-why)、“知诀窍(know-how)和“知人际”(know-who)。从原则上看,前两种类型知识具有明晰、具体、可以物化并在市场上交易的特点;而后两种则是蕴涵性(tacit)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不能买卖,需要非市场机制来进行分配(例如,组织内部,在公司内部网络单位间的合作,或在私人主体与公共机构间的合作等)。物化性知识和蕴涵性知识之间的关系似乎正在发生变化。在现代经济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物化性知识日趋重要,这当然并不降低蕴涵性知识的重要性。举例来说,如今信息的获取较为方便和廉价,这使得在选择和使用信息方面之蕴涵性知识才能比以前更为重要。Lundvall认为,有关学习最基本的问题也许就是把蕴涵性知识转化为物化性知识,然后再运用于实践,由此发展出更多的蕴涵性知识。
许多新理论把促进合作、尤其是学习过程的制度要素概念化,从而产生了诸如“创新体系”(innovation systems)、“商务系统”(business systems)、“网络的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等新的概念。同时,“信用”和“社会资本”等概念也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以理解这些重要的制度特征。
学习也可被看作是组织适应环境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像在组织理论中曾占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所认为的那样,学习只是简单的“刺激-响应”性适应,决策是由稳定的偏好和因果逻辑决定的,这个主题就很不重要了。然而,在组织学习理论领域,行为主义者的“刺激-响应”模式已让位于“刺激-认知-响应”模式。此外,NIO已经指出,规则(rules,包括程序、组织形式、规范、惯例等)构成组织行为的基础,也就是说,与既定规则相关的适配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至少应与因果逻辑一样重要(见March & Olsen)。因此,组织学习理论强调组织行为者的认知过程,规则的作用,以及松散结合型组织中学习的互动过程。
组织中的学习过程已成为组织理论中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并在NIO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然而,就将其整合进知识和学习经济的研究而言,这还仅仅是开端。可以预见,该主题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富有成效的合作与沟通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壤。
4.认知过程、价值和制度变迁。认知模式(mental models)不仅在完全不确定状态下很重要。如果认识到信息常常是不完整的,那么很显然,个人有关经济选择的洞察力一般是有偏差的,因而认知方面的问题就成为重要的分析对象。西蒙(Simon)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用认知的有限性解释了“满意(sub-optimal)决策”原理。然而,这种有限性被看成某一种假如不是在实践中、原则上能够被克服的状态。这一解释已经招致来自OIE领域学者(例如Hodgson)的批判,他们认为应重视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影响,以及制度在感官数据经一些信息发展成知识这一复杂转换过程中的作用。Hodgson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非常强调认知的文化特异性(specificity)和通过预先建立的解释(interpretative)机制产生信息。
继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分析以后,NIO发展了多种决策模型,包括打破理性神话的所谓“垃圾筒”(garbage can)模型(注:见Laudon,K.C.& Laudon,J.P.: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New 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 & Technology.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renticeHall,1998.p.137.所谓“垃圾筒”(garbage can)模型系指许多失败和消亡组织通常使用的决策模式。在这些组织中,决策是非理性而随意的,问题、情形和决策之间通常没有内在联系,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其方案仅仅出于偶然的原由。在这类组织中,充斥着“方案寻找问题和决策者寻找工作”的现象。)。
North断言理性必定有缺陷,不断发展的思想(ideas)和意识形态(ideologies)对其产生影响,而制度在决定思想和意识形态之影响程度方面又扮演了主要角色。个人赖以解释周围世界和作出选择的认知结构(mental structures)是由思想和意识形态决定的。制度有意无意地提高或降低了建立在思想基础上的行为的代价,因此影响到认知结构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模式。North认识到意识形态的核心作用,并发现经济学既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又缺乏单独分析这一角色的理论能力。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使用“价值”(values)的概念强调类似的机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层面的认知过程,都被看成是价值在起基本性决定作用。NIO分析了组织中冲突和模糊的价值集合之处理过程及其结果。认知过程的作用以及与制度变迁相关的价值是特别重要的主题。如果经济行为在通常情况下主要被看成是由嗜好(habits)、惯例(routines)和规模(norms)所导引,但该机制又随机性地不时被新鲜事物、变化和创造所打断,那么研究认知结构在这方面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思想的作用以及思想、交往(interaction)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主要由HI领域的政治学家(如Hall和Campbell)所研究。当然,社会学家(如Dobbin)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对中国制度研究现状及国外相关个案剖析之目的是推动国内制度研究、尤其是跨学科制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上述研究网络除了在理念、共识和方法论等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外,其研究主题也可圈可点:几乎囊括了当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管理学领域内相关分支学科所共同关注的前沿热点问题,应该说对国内制度研究课题的选取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我国独特的制度变迁、改革经历和具有本国特点的制度安排为制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实证条件,正在不断深入的改革实践又为验证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这在西方学术界已引起相当程度的重视。如何继承、借鉴、应用、改造和发展人类制度研究领域的共同瑰宝,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极大地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同步成长的制度安排,是我国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制度研究工作者面临的挑战。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社会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模糊理论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