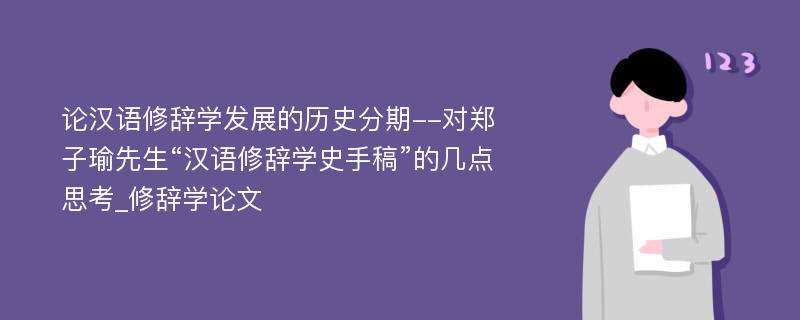
关于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读郑子瑜先生《中国修辞学史稿》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论文,读郑子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发展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因此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成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讲到文学发展史,总有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修辞学作为一门学术,由于它是以文学的语言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与研究材料,因此它与文学的血肉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正因为如此,修辞学史的研究也有一个历史分期问题,分期的恰切与否,反映出研究者对于研究本体认识与评判的正确与否,因此,在中国修辞学史的研究中,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期也就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了。
对于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国际知名学者、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先生在其巨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中首次进行了科学的历史分期研究。郑先生认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即先秦时代是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两汉时代是中国修辞思想的成熟期,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期,隋唐时代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宋金元时代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时代与清代是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郑先生这种历史分期,不仅顾及到了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等发展的独特背景,而且确是恰切反映了中国修辞学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根本特点。可以说,郑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是理所当然的一家之说。
先秦时代,中国文学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但明确的修辞学思想与修辞学研究还未开始。虽然老子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说,孔子有“辞达而已矣”、“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等观点,孟子亦有“言近而旨远”的说法,但仔细研绎其辞,皆不是明确的为修辞学目的而阐发的观点,其修辞学思想还不明朗。即使是对于修辞意义的看法,虽然《墨子》、《荀子》以及《易经·系辞下》中都有所强调,但是从未有人提出象汉人刘向“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这样明确的修辞观点。至于具体的辞格研究,更是难以见到了。因此,郑先生将先秦时代定为中国修辞学思想的萌芽期,无疑是很精当的。
两汉时代,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臻至成熟与中国哲学、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修辞学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修辞学无论是在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皆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如宏观方面,刘向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他“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的主张,充分强调了修辞的作用与意义。至于修辞上的“华”与“质”问题,虽然汉人司马迁、桓宽、扬雄、班固、荀悦等人各有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观点,但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能态度明朗,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探求真理的热情与勇气。又如微观方面,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春秋》一书用辞的深究,贾谊在《陈政事疏》中对避讳修辞手法的论述,王逸在《离骚经序》与王符在《潜夫论》中对譬喻的论述,还有王充在《论衡》中对夸饰的论述,虽然并不系统、完整,但确是明确的汉语辞格研究的规模。很明显,相对于先秦时代,中国修辞学在这一时期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可讳言,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家并没有解决更多的修辞学理论问题,对汉语修辞如语体、风格等各方面皆未有深入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修辞学并没有发展得很充分,所以这一时期也只能说中国修辞学处于思想成熟的时期,而不是修辞学发展的成熟期。可见,郑先生将两汉时代名之曰中国修辞思想的成熟期是很恰当的。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形式主义文风盛炽的时期,虽然这有悖于中国文学“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受到了许多有识见的文学批评家的严历批判;但是,中国文学创作的形式主义风气却客观上促进了汉语修辞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期,在宏观修辞理论方面,晋陆机《文赋》所论及的“意”与“文”、“新”与“陈”、“庸”与“隽”等关系问题的见解,晋葛洪、梁萧统、梁沈约等人对“文”、“质”等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论述,北周颜之推对“理致”、“气调”、“事义”和“华丽”之间关系的观点,都值得注意。在微观修辞学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成就更加可观。如南朝钟嵘之论赋比兴、用事等,晋陆机之论警策,北朝颜之推之论用事、避讳、仿拟、歇后等辞格,其范围与深度远非先秦、两汉两个时期所敢梦想。又如曹丕、陆机、挚虞等人的文体风格论,陆机、沈约、钟嵘之论声律修辞,皆是前此时代所未有。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它不仅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比喻、丽辞、夸饰、事类、谐隐、隐秀等多种辞格,论述了修辞与声律的关系,论述了文体风格等内容,而且还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诸如“为情而造文”、“变通适会”等修辞的根本原则。从而将这一时期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后代汉语修辞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这些事实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印证郑先生将魏晋南北朝时代看成是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期是恰切的,符合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事实。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为强盛的时代之一,亦是中国文学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伴随着文学的发展,隋唐时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也有了巨大进步。这一时期,在宏观修辞学理论方面,韩愈的“辞事相称”论、柳宗元的“文道并重”论,杜牧的“以意为主”论、皇甫湜的“文奇而理正”论、李翱的“创意造言,皆不相师”论、李德裕的“光景常新”论等,皆颇有创见,值得重视。在微观修辞学的研究方面,如辞格研究,唐人对于对偶、比喻、仿拟、婉曲、用事、双关、回文、离合、镶嵌、倒辞、叠语、夸张等十余种辞格皆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在广度与深度上均较前代进步。特别是对诗论修辞的研究,成就更大,如白居易、桂林淳大师、皎然、徐寅、元兢、王睿、司空图等人的诗论修辞学说,皆是中国修辞学史上有名的。除此,唐人刘知几的史论修辞也自备一格,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有其独到的意义。由此可见,隋唐时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又在魏晋南北朝的已有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因此,郑先生将这一时期名为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是很有见地的,符合中国修辞学这一发展时期之实际的。
宋金元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另有新的景观,修辞学也相应得到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宏观修辞理论方面,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说,苏轼的“辞达”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适用”说、黄庭坚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陈绎曾的“的当”、“自然”说,还有叶梦得的“意与言会,言随意遣”说、刘攽等人的“以意义为主”说、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说、王若虚的“以意为主,字语为之役”说等,皆颇有性格,可成一家之言。微观修辞研究方面,字、句、篇章修辞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辞格创新的成就更引人注目,如“比拟”、“错综”、“设问”、“飞白”、“转品”等新辞格的论述,都是这一时期的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部修辞学专著,这便是南宋陈骙《文则》的问世。《文则》不仅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积极修辞以及消极修辞的各种手法,研究了各种文体风格的特点,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修辞的原则。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比较法、归纳法,近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将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比《文心雕龙》更高的科学层次。很明显,这一时期的中国修辞学发展实绩又超过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两个时期。因此,郑先生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是正确的。
明清时代,中国修辞学在长达六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除了诗文修辞论得到了大发展外,戏曲、小说修辞论的研究异军突起,为这一时期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别添了一种景观。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总体水平较宋金元时代有了进步,只是这一时期修辞学重文辞而轻语辞的现象很严重。基于这一发展特点,郑先生将此一时期名曰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这也是有道理的。虽然这种以发展特点分期的作法与前几个时期以发展水平分期的作法不一致,似乎有标准(原稿不清)嫌,但是若与后一个时期即中国修辞学的革新期(现代)相提并论,则又是标准严整统一的。所以,郑先生将明清时代名为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尽管并不十分贴切,但亦未尝不可。
至于现代,由于是西方科学与思潮影响中国至深至切的时期,中国修辞学发展的新旧两派之争势所必然,而最终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一时期出现的《修辞学发凡》等现代修辞学专著,无论在方法的科学化,理论的体系化方面,皆表现出一种与前此各个历史时期大相异趣的风格。因此,郑先生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修辞学的革新期,这是再恰切不过了。
虽然《中国修辞学史稿》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在材料的完备、理论体系的完整上有所欠缺,但其历史分期的总体框架则是相当精密的,值得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上是笔者学习郑先生《史稿》并结合自己几年来学习研究与写作《中国修辞哲学史》一书的体会后对《史稿》历史分期框架的一点粗浅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