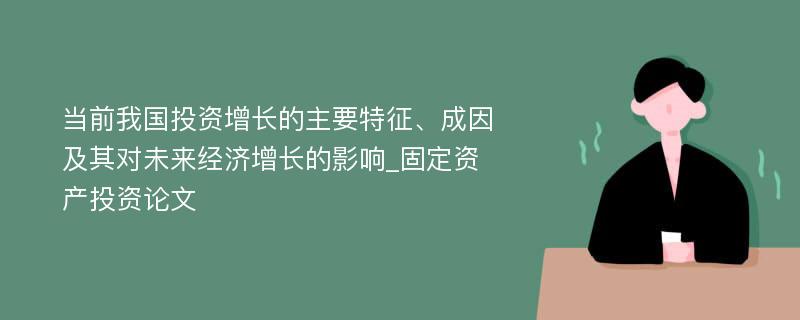
当前我国投资增长的主要特征、原因及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主要特征论文,当前我国论文,原因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特征
(一)非国有经济是新一轮投资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历两次高速增长。其一是1984-1988年期间,由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集体经济投资快速增长引致的。其二是1991-1994年经济过热期间,由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的快速增长引致的。此后,受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及结构性供过于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1995年后大幅度下滑,到1999年降为5.1%。2000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恢复上升趋势,但与前两次不同,本轮投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投资快速增长拉动的;国有经济投资增速上升缓慢,远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速迅速提高,分别从1999年的3.5%、7.9%和5.3%提升到2002年的13.4%、20.1%和36.2%,由此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1999年的5.1%提升到2002年的16.9%。200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5%,其中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分别增长30.6%和24.7%。鉴于2003年前三季度利用外资增速同比大幅度提高,200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度提高,也是由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快速增长拉动的。因此,非国有经济是本次投资恢复快速增长的主导力量。
(二)政府投资的诱导作用弱化,市场约束力增强。与1984—1988年和1991—1994年的两次投资快速增长不同,本次投资恢复快速增长,政府投资的力度增强,但其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诱导作用明显下降:在1984—1988年和1991—1994年期间,国家预算内资金年均增速分别只有4.92%和7.74%,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高达27.16%和39.37%。1998年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政府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规模从1997年的696.7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3160.96亿元,年均增长35.32%,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只有11.77%,国家预算内资金或政府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诱导作用明显下降。从固定资产投资的其他资金来源看,除利用外资外,1994年以前国内贷款、自筹和其他资金的增长波动趋势与国家预算内资金基本同步,说明在预算软约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旦政府控制放松或政策取向调整,企业投资就会迅速膨胀。但1995年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和短缺经济格局的结束,企业投资与政府投资波动趋势发生了逆转,在国家预算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递增的情况下,国内贷款、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并没有随政府投资的扩张而大幅度增长,1998-2002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年均增长35.32%,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投资增速最快的时期,但同期国内贷款、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年均增速只有13.12%和12.6%。这说明,在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之后,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力不断增强。
(三)企业技术改造意愿增强,更新改造投资相对快速增长。1991-1994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房地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快速增长拉动的。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及中国经济的突出特征是房地产投资严重过热。但本次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较快增长,最为突出的特征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更新改造投资相对快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5.1%提高到16.9%,增速提高11.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3.37%,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从4.5%提高到19.2%,增速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2.36%,房地产投资增速从13.5%提高到22.8%,增速提高9.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3.83%,而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速从-0.7%提高到14%,增速提高14.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4.6%。2003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度提高到30.5%,增速比2002年全年提高13.61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分别增长29.1%和32.8%,增速分别比2002年全年提高9.89和9.99个百分点,而更新改造投资增长37.2%,增速比2002年全年提高23.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固然与房地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恢复较快增长有关,但更新改造投资增速的大幅度提高起到了更为重要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工业企业,前三季度更新改造投资3926亿元,同比增长49.3%,比2002年全年增速提高20.66个百分点,其增幅远超过基本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幅,说明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意愿增强。
(四)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提升。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产业分布状况看,本轮投资恢复快速增长的重要特征是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投资相对快速增长。1990年以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中所占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逐年提高。但这一趋势在200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恢复上升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工业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出现加速增长趋势,在基建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9年工业和制造业投资在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的比重只有37.55%和17.58%,是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2000年以后工业和制造业投资比重恢复上升趋势,到2002年已上升为40.2%和23.02%。同时,受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的影响,1999年以后第三产业投资在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但第三产业中的社会服务业投资继续保持相对快速增长态势,其投资在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中所占比重从1999年的9.35%递增到2002年的11.52%。从各国经济工业化的一般发展规律看,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的这一变化特征,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在经过多年的调整后,已进入以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为特征的新工业化时期。
(五)投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进一步提高。1953年以来我国投资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53年我国投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只有20.66%和11.12%,1980年提高到34.9%和20.16%,2002年进一步提高到39.4%和42.49%。这一水平远超过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各国工业化时期的一般水平,已接近马来西亚、泰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1990-1997年期间的历史最高水平。但与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或固定资产投资率不同的是,我国投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波动幅度较大,出现过多次快速上升、然后深度下调的时期,最近的快速提升发生在1990-1993年,随后进入深度下调阶段,从2000年开始又进入新的提升阶段,投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分别从2000年的36.4%和36.8%提高到2002年的39.4%和42.49%,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进一步提高到43.42%,是1953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投资率和固定资产投资率已进入新的快速提升时期。
二、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一)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恢复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增强、企业预算约束硬化,政府投资在本轮投资恢复快速增长过程中的诱导作用相对弱化,市场约束力增强,但并非说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对投资增长没有影响。由于贷款利率调整、银根收紧(信贷控制)、贴息贷款、税收优惠等宏观调控政策的改变,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投资资金来源,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行为。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有效地遏止了1997年以后的投资增速下滑,也对2000年以来投资恢复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1)1998年政府采取的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财政预算赤字、扩大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等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提高16.33个百分点。(2)1999年政府采取的两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将财政赤字从1998年的918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759亿元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等主要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引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3.29个百分点。(3)2000年政府调整了宏观调控政策的结构,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稳健,但财政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增强,财政赤字由1999年的1759亿元增加到2491亿元,同时在投资、消费、出口、进口、财政收入等方面采取了多种综合性政策措施。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引致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4.45个百分点。(4)2001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扩张力度减弱,在继续采取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未增加财政赤字的规模,但鼓励出口和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措施力度比2000年明显增强,由此引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2.12个百分点。(5)2002年政府再次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扩张力度,在下调利率的同时,大幅度增加财政预算赤字(比2001年的实际财政赤字增加625亿元)。这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措施引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8.65个百分点。
(二)供求状况改善和投资收益提高是投资恢复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投资行为日益市场化,供求状况、投资收益、企业经营效益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强。而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完全市场化的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基本上由供求状况、投资收益、企业经营效益状况等市场因素所决定。从1995-2002年工业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增长波动情况与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波动情况看,工业投资的增长波动趋势与反映投资收益状况的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波动趋势是完全一致的,与反映供求状况的产品销售率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具体看,1995—1998年期间,随着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利税率或总资产贡献率的持续降低,工业投资增速也持续大幅度下降,从1995年的15.92%下降到1998年的1.76%;1998年以后,投资收益率提高,供求状况改善,总资产贡献率从1998年的7.12%提高到2002年的9.45%,工业产品销售率从1998年的97.15%上升到2002年的98.02%,工业投资增速也从1998年的1.76%提高到2002年的24.1%。2003年前三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97.67%,同比提高0.07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54%,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进一步提高34.1%、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总之,供求状况的改善,特别是投资收益的持续提高是近年来投资恢复快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三)投资增长已进入周期性波动的扩张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存在明显的短周期和中周期波动现象。我们以1978年到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作为样本进行对数回归,得到短期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和中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发展趋势值,并将发展趋势值作为投资周期性波动的中值进行分析可看到:(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1999年以后进入短周期波动的复苏期,2001年的短期增长率仍低于其发展趋势值,仍处于复苏阶段;但2002年的短期增长率已超过其发展趋势值(约高出4个百分点),说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进入新一轮短周期波动的扩张期。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增长率进一步提高,达28.29%,比其发展趋势值(14.5)高近14个百分点,说明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处于其短周期波动的扩张期。从短周期波动平均波长5年、扩张期2年左右的一般发展规律看,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即将达到其新一轮周期性波动的波峰,从2004年开始有可能进入周期性波动的收缩期。(2)固定资产投资中期增长率从1998年进入中周期波动的复苏期,2002年中期增长率只有11.55%,仍低于其发展趋势值(14%),说明从1998年到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中周期波动的复苏期。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中期增长率提高到16.6%,已超过其发展趋势值2.6个百分点,说明从2003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已进入其中周期波动的扩张期。从中周期波动平均波长8年、扩张期2年左右的一般发展规律看,2004年应是固定资产投资中周期波动的波峰,从2005年开始有可能进入周期性波动的收缩期。综合判断,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经过1994-1999年长时间的收缩与衰退和1999-2002年的复苏与调整之后,在投资自主性增长机制不断增强的作用下,2003年已进入新的快速增长的扩张时期,2004-2005年投资增速会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仍将保持15%以上的较高增速。
(四)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引致投资需求大量增加、投资率进一步提高。从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结构与增速变化看,1990年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90-1993年工业化和重工业快速提升阶段。1990年以后我国工业化和重工业程度迅速提升,1993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投资率分别达到40.8%、59.33%和43.5%,比1990年分别提高3.8、9.96和8.2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仅次于1954—1957年期间的幅度,也是第二次出现投资率超过工业化程度现象的时期(第一次是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时期)。由此,经济进入严重过热状态,产业结构再次失衡。(2)1993-1998年期间的工业化和重工业化调整阶段。受前期产业结构再度失衡的影响,1993年以后轻工业和重工业进入在发展中进行结构优化调整的新阶段。重工业总产值增速大幅度下降,轻工业增速相对提高,1993-1998年期间轻工业总产值和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9.54%和5.13%。但由于1993年重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加,这一时期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94年以后仍持续上升。(3)1998-2002年期间重工业化程度稳步提升阶段。经过1993-1998年期间的优化调整,1999年以后我国经济工业化进程再次进入重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98年的42.6%稳步递增到2002年44.4%的同时,重工业产值和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分别由1998年的54.29%和60.22%递增到2002年的57.54%和62.56%。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由1999年的5.1%提高到2002年的16.89%。2003年工业出现加速增长趋势,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长16.5%,同比提高4.3个百分点,是1995年以来前三季度工业增加值的最高增速;其中2003年前三季度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3%,比2002年重工业增加值增速提高2.5个百分点,比2003年前三季度轻工业增加值增速高3.5个百分点。这表明2003年我国经济发展已再次进入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程度快速提升阶段,固定资产投资也因此而出现加速增长趋势。
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经济增长进入周期性上升阶段,投资与GDP将持续快速增长,但短期内不会出现严重经济“过热”现象。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看,经济出现严重过热现象主要发生在短周期、中周期和中长周期均处于扩张期的波峰重合时期,如1993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商业周期、短期和中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长周期等均处于周期性波动的波峰,多种扩张性因素的叠加,使各种经济活动的扩张效应放大,加之政府管制放松、市场自发的约束机制尚未形成,导致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过热现象。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又进入周期性波动的上升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不断增强,经济增长速度上升。但本轮经济周期性上升不会引发严重的投资或经济过热现象,主要原因是除经济运行机制发生重大改变外,各种主要经济活动的周期波动未发生重叠:2003年商业周期处于周期性波动的波峰,预计2004年上半年以后将进入收缩期,会对短期经济增长的上升趋势形成抑制作用。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进入短周期波动的波峰和中周期波动的扩张期,但2004年进入短周期波动的收缩期后,投资增长的扩张势头也会弱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周期性波动正处于中长周期复苏期的初始阶段,上升趋势不断增强,但还不足以引发严重“过热”。因此,短期内我国经济出现严重“过热”现象的可能性很低。但在2005年以后或2006—2008年期间,当商业周期、投资周期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长周期等主要经济活动周期均进入其周期性波动的扩张期或波峰重叠时,有可能会再次出现严重的投资与经济“过热”现象。
(二)市场机制日益完善,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经济的自发调节能力增强,投资与经济“过热”的体制性因素弱化。1991-1994年期间发生的严重投资与经济“过热”现象,与当时特殊的经济体制密切有关。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从“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但相应的市场硬预算约束机制尚未形成,国有企业仍存在很强的盲目扩张冲动,计划经济时期“一放就乱”的体制性因素尚未消除,因此,政府管制放松后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的盲目投资成为当时经济严重“过热”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机制与90年代前期相比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断增强,企业经营活动面临着很强的硬预算约束,投资行为已基本市场化:从经济活动的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1990年的66.11%下降到1995年的54.44%和2002年的43.4%,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54.6%下降到1998年的49.6%和2002年的40.8%,完全市场化的非国有经济企业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看,中小型国有企业已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造,大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也已进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造,基本成为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规避市场风险的市场化经营原则约束下,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自我约束机制不断增强,预算软约束等体制性扩张因素日趋弱化。因此,当生产能力的结构性过剩缓解、经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后,企业投资等经营活动也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而扩张,但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扩张行为与90年代前期盲目的扩张行为有本质区别:在市场需求的硬性约束下,即使企业投资行为的改变比市场需求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出现一定程度的投资过度,但不会引发严重的投资“过热”或经济“过热”。
(三)新一轮重工业化有坚实的需求基础,投资快速增长不会引发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在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中,历次工业化程度的快速提升均引致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其根本原因是工业化或重工业化的快速提升不是建立在需求结构提升的基础上,而是片面追求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后,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已逐步纳入以市场需求为基础的轨道,政府为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也是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之上。本轮工业化和重工业化进程加快,即是建立在消费需求和出口结构大幅度升级基础之上:(1)在解决衣食等温饱问题后,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快速提升,1991-2002年期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提升12.6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远高于1978-1990年期间分别为8.9和3.3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200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恢复快速增长和重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与近年来居民消费热点从家电转向住房和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密切有关。如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的房地产投资主要是由住宅投资的快速增长拉动的,住宅投资占房地产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48.43%递增到2002年的67.1%,住宅销售率也从1997年的57%提高到2002年的76.6%。即1997年以来房地产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居民住房需求快速增长基础之上的,与1991—1994年期间由投机和炒地皮引发的房地产投资“过热”有本质区别。(2)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7年的86.9%提升到2002年的91.23%,机械运输设备等重工业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7年的23.91%大幅度提高到2002年的39%。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特别是重工业化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对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总之,本轮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程度的大幅度提升有比较坚实的需求基础,这种由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拉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投资快速增长,不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投资率或固定资产投资率不断提高是经济工业化进程中的客观规律。近来部分国内外学者以中国目前的高投资率作为中国投资出现“过热”或投资效率低的评判依据,这是很不科学的观点。如1997年印度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4%,中国1997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是33.49%,但印度的工业化程度远落后中国,1997年印度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0.14%,比1997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9.18%)低19个百分点,仅相当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当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不足15%,投资率不足20%。目前中国的投资率或固定资产投资率远高于印度,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印度。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看到,我国投资恢复快速增长态势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投资的相对快速增长拉动的,是经济增长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和工业化与重工业化程度再次提升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市场机制日趋完善,自我调节能力不断增强,各种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趋势的不一致会部分抵消投资增长的扩张趋势,本次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需求基础比较坚实,投资的快速增长引发严重经济“过热”现象的可能性很低。基于这一判断,我们认为短期内政府不宜采取过度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应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化宏观调控机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础上,采取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看,政府应抓住经济自身增长机制不断增强、中长期内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速的良好机遇,将工作重点从短期宏观调控转移到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收入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重大结构性矛盾上:(1)抓住目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有利时机,加快税制改革进程,尽快解决长期困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企业税负不均、征税环节错位、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合理划分等财税体制问题。(2)适时缩减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减少财政赤字预算规模,逐步收缩近年来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缩减建设性财政支出规模,加强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支出,加大力度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4)加快宏观调控方式的改革步伐,减少行政性直接干预,增强信息服务,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调整对企业预期的影响力,避免不当的政策措施加剧经济增长的波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