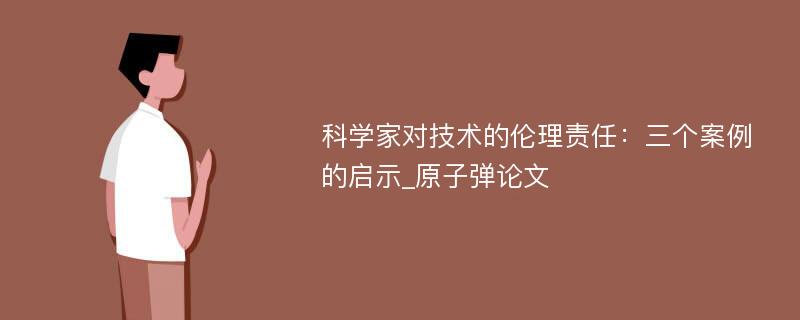
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三则案例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科学家论文,启示论文,案例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家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因其与技术的密切关系,他们理应在承担技术的伦理责任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然而,从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实际承担以及整个技术伦理学的实际效能发挥来看,并未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好。正如德国学者格鲁恩瓦尔德所说的:“但直到目前为止——也没让人看出它们对技术发展有何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技术伦理学一直未能跳出毫无实践意义的动听说教的圈子。”(注:A.格鲁恩瓦尔德:《现代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可能与实践意义》,《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有鉴于此, 我们试图从二战时期“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的失败,美国科学家对日本在中国使用细菌战的态度以及《罗素—爱因斯坦宣言》遭受的挫折这三个案例出发,具体探讨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阻碍了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发挥?探讨这一问题,无疑对科学家对技术伦理责任的承担以及技术伦理学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这三则案例的有关情况。
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是现代和平运动的序幕,它起因于原子科学家意识到美国政府可能对日本实施核打击,企图用游说和请愿的方式阻止这一军事计划的实施。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西拉德、拉宾诺维奇、弗兰克、爱因斯坦、巴特基等。他们先后以杰弗里斯委员会的“核子学展望”备忘录、西拉德3月备忘录、弗兰克委员会报告、 西拉德两次请愿书的形式开展活动,游说美国政府。他们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理由除了基于科学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外,也考虑到了美国的利益。正如西拉德在其3月备忘录中警告的,美国不可能长期垄断核武器, 而美国又是一个都市化国家,是未来核战争中最易被攻击的对象。为了提醒政府谨慎从事,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向政府提出三种选择方案:①在无人居住的岛上,在同盟国及日本代表参加下显示它的威力,并告诉日本如果不投降就将原子弹用于日本;②暂时不用原子弹,把它储存起来,以创造合作的气氛;③与联合国达成协议,在联合国批准的条件下使用原子弹。然而不幸的是,1945年6月6日,一个由政治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共同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否定了这一方案,作出了“关于马上使用原子弹的建议”。建议作出后,西拉德并未放弃希望,他又于7月3日和7月17日发起了两次签名请愿运动。遗憾的是, 杜鲁门还未读到请愿书,8月6日原子弹就在广岛爆炸了。
日本二战前用中国人做细菌武器实验,二战中又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残酷的细菌和化学战,令世人唾弃。然而,正当欧洲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用人做实验的德国战犯作出判决的时候,有美国细菌学专家参加的审讯,却让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石井四郎(日本关东军731 部队的首领,细菌武器实验及细菌战的直接实施者)轻易地逃过了国际法庭的审判。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是当代两位最伟大科学家以“人类代表”而非个人身份发表的废止核战争、呼吁世界和平的宣言。宣言由罗素于1955年4月5日起草,4月11 日爱因斯坦首先在宣言上签名(两天后爱因斯坦患重病,4月18日就逝世了)。除罗素和爱因斯坦外, 签名的还有美国的布里奇曼、缪勒和鲍林;英国的鲍威尔、罗特布拉特;法国的约里奥—居里;波兰的英费尔德;日本的汤川秀树;西德的玻恩。他们绝大部分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签名活动一波三折,在罗素于1955年4月初同爱因斯坦商议的拟请签名的15名科学家中就有10 人没有签名。这份宣言在遭到如此冷遇后直到7月9日才由罗素在伦敦公开发表。
从技术伦理学角度看,这三则案例至少给我们三大启示:一是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无论在态度还是在承担方式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二是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如果得不到其他技术相关者的广泛同情、支持与配合,其作用将会十分有限;三是主动承担起技术的伦理责任是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整个人类的共同的事业。这里我们把科学家作为技术相关者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上述三则案例的分析,来具体探讨一下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科学家对技术伦理责任的有效发挥。笔者认为,重要因素有七。
第一,科学家对技术的评价维度的差异,导致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在态度及承担方式上的差异,难以在技术伦理责任方面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从而使其活动能量大打折扣。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结果,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高度统一。人们对技术的评价也往往采取了自然和社会这两个维度。所谓自然维度,就是对技术的科学判断与评价,其实质就是寻求自然科学规律在技术上的证明;所谓社会维度,就是对技术的社会价值的判断与评价,它又可分为功利评价与伦理评价两个维度。功利评价着眼于技术局部的、眼前的、直接的、暂时的、利己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等价值;伦理评价则立足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着眼于技术的根本的、长远的、社会—生态整体的社会价值。科学家对技术的评价维度不同,必然导致他们对技术的社会控制所持的态度不同,从而使得科学家在对待技术的伦理责任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这一点在上述案例中都是明显存在的。拿第一则案例来说。在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中,科学家阵营明显分裂为三派:以西拉德为代表的大部分科学家所主张的,考虑的是全人类的前途和利益,在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生存的原子弹问题上,他们主要采取了伦理这一评价维度;以奥本海默为代表的少数人所主张的,考虑的是个人名利以及美国的暂时利益,他们主要采取的是功利主义的评价维度,正是他们与军事家、政治家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作出了“马上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以费米为代表的部分科学家,他们只对“纯粹科学”感兴趣,对技术主要采取的是自然的评价维度,他本人作为专家组的成员,在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的会议上,“没有做出任何有背于官方意图的表示,而且他对科学家的活动一直不感兴趣”。(注:王德禄、刘戟锋主编:《科学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76页。)因此,我们认为,科学家群体对技术评价的价值分裂是导致科学家技术伦理责任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第二,功利主义的诱惑是导致科学家道德责任感淡薄的重要原因。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一方面,它具有巨大的社会功利性;另一方面,技术对科学家本人来说,它作为科学家研究的成果又会为科学家带来直接的名和利,因此又具有极大的个人功利性。正是技术的这种双重功利性,才成为人类不断创新技术,推动技术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然而技术的功利性并不能掩盖其现实或潜在的负面效应,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它集巨大福利与巨大风险于一身,如果只顾眼前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的功利,经受不住功利主义的诱惑,势必导致科学家道德责任意识的淡薄。在第二则案例中美国对待日本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态度就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细菌战中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石井四郎为什么能轻易地逃脱国际法庭的审判?其中主要原因是有些科学家出于其极端的利己主义考虑。当时参加审讯的美国细菌学专家在研究了供词后就认为,总的说来,美国在有关细菌武器的研究方面比日本人先进,但日本在取得人体材料上,特别是大量的病理切片,则是十分难得的,在研究细菌的种类上已大大超过了美国。他们为了把从200 多名人工感染各种疾病致死的中国人身上切取下来的8000张病变组织切片的资料据为己有,竟然认为一旦把这些人推上国际法庭,则一切材料都将公开,无密可保,这样做对美国不利。(注:王德禄、刘戟锋主编:《科学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61—64页。 )正是这些科学家受狭隘的功利主义的诱惑,导致其道德责任意识的淡薄,才使石井四郎得以逃脱国际法庭的审判。
第三,惟科学惟技术的狭隘的科技观念也是影响科学家自身不能很好地发挥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重要原因。惟科学惟技术的科技观认为,技术的误用与滥用与科学家无关,追求真理才是科学家工作的永恒目标。无疑,这种科技观是狭隘而又危险的。如果科学家只注重寻求对技术的科学证明,忽视对技术的社会判断,这不仅会造成科学家道德责任意识的淡薄,而且还会导致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完全推卸,其后果无论对社会还是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正如巴伯所言:“这种态度的危险是,社会可能会把科学家认为是一个无责任感的群体,为保护社会本身,必须反对该群体。”(注: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73页。 )反观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斗争的失败及《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所遭受到的挫折,我们不能说与当时科学家的这种态度无关:西拉德的第1份请愿书, 化学家几乎都未签字;《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罗素与爱因斯坦拟请的15位科学家中就有10人拒绝签字。
第四、政府和企业的压力是抑制科学家承担技术伦理责任的强大力量。由于科技开发的高风险性和高投资化,政府和企业便成为当然的科技投资主体。这样,政府和企业对待技术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左右科学家的态度和行为。而政府和企业对技术最优先的考虑往往是其功利性,特别是当技术成为企业与国家竞争的焦点的时候。这一点在第一则案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拉德这位在美国原子能计划中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因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有悖于美国政府的原子能政策,经常受到由军方控制的原子能委员会的限制、怀疑和责备,以致最终被排斥在原子能委员会之外。而作为专家组成员的康普顿、劳伦斯、奥本海默和费米在对待弗兰克委员会报告和是否使用原子弹的讨论会上,他们并没有理直气壮地表达大部分科学家的思想,而是尽量去迎合政府的意图。其中康普顿的矛盾心态更能说明问题。康普顿因1927年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在科学家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作为原子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在科学家与陆军部的矛盾中,他往往并不站在科学家一边,常常与军方代表格罗夫斯保持一致。在决定是否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讨论会上,他虽然没有勇气谈论大部分科学家的观点,但他毕竟总是个科学家,当整个讨论气氛一边倒的时候,康普顿还是鼓起了科学家的道德勇气问道:“为什么不能用原子弹进行非军事演习,这样日本可能得到强烈的印象,他们会发现继续战斗是无用的。”但此建议被当成了耳边风,科学家仅有的一点道德良心也被军方压制住了。至于奥本海默,当时正是他官运亨通的时候,与官方及陆军的交往已使他与科学家缺乏共同的思想,他认为投放原子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费米作为流亡科学家,能参加如此级别的会议已让他感到受宠若惊,为报答对他的信任,在会上未做出任何有背于官方意图的表示。劳伦斯在此会议上是最后一个放弃非军事演习设想的,在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迫于无奈,他也只能在使用原子弹的建议书上签字。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我们不得而知,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受到了压抑恐怕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政府的压力外,各私人公司(如杜邦)也在军方的支持下对科学家进行限制。(注:王德禄、刘戟锋主编:《科学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73页。)
第五、科学家和广大公众的隔绝,使科学家的正当呼声得不到民众的响应,有时甚至形成敌对(当部分科学家对技术的滥用或负面效应不愿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也是影响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发挥的重要因素。科学家与公众的隔绝除了工作性质、职业习惯、文化背景外,最为关键的是对科技参与程度和对知识了解深度的差异。如何缩小这一差异,除了努力提高民众的科技素质和人文素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对技术的选择与评估外,更为关键的则是科学家应该主动承担起向公众披露科技事实真相的责任。正如拉宾诺维奇所言:“只有公众了解核子学的发展隐含着可能的灾难,必要的道德发展才能防止滥用核能,因此公众就会给予要求防止危险的决定以支持。”(注:王德禄、刘戟锋主编:《科学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68页。 )拉宾诺维奇的这一观点当时在科学家中是颇为流行的,但终因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与广大公众的隔绝而没有形成有广大民众支持的社会的道义力量,使得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斗争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拉宾诺维奇战后为教育公众做了许多工作,包括编辑著名的《原子科学家通报》。
第六、科技保密制度使科学家面对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左右为难,这既使科学家承担道德责任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又在科学家与公众有效沟通间设置了一道很难逾越的屏障。由于科技投资主体(政府和企业)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他们对科技成果总是会采取各种保密手段加以保护,而国家出于鼓励创新的目的,又使之合法化。但科学家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他必须向公众披露事实真相,而这样一来,就将触犯法律,并损害投资主体的利益,这使得科学家左右为难。如西拉德在其游说政府的过程中,一再声明自己是在“没有泄露任何事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可还是被格罗夫斯污蔑为泄密者,说他把一些秘密材料泄露给贝尔纳斯。虽然以西拉德、拉宾诺维奇及22个冶金实验室的领导人在阿里森鼓动下联合上书反对过保密制度,他们要求向美国及世界公众宣布曼哈顿计划的存在、原子弹的毁灭能力和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但这一活动以毫无结果而告终。
第七、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相互不理解,这也是削弱自然科学家对技术的伦理责任感的一个因素。在上述案例中,无论是原子科学家反对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斗争还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人文科学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舆论及实际行动上的支持。这除了自然科学家没有主动联络、发动人文科学家外,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与两者的长期隔膜与互不信任有关。这一点从布里奇曼对技术的伦理责任的态度上可窥一斑。在科学技术的使用上,布里奇曼是一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他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积极支持者,但他对一些人特别是部分人文科学家把技术的社会责任强加给自然科学家、让自然科学家独自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感到强烈不满,他告诫自然科学家别承担“轻率强加的责任,这种承担对于我来说有过多的让步的味道,并且也是缺乏自重的”。(注: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