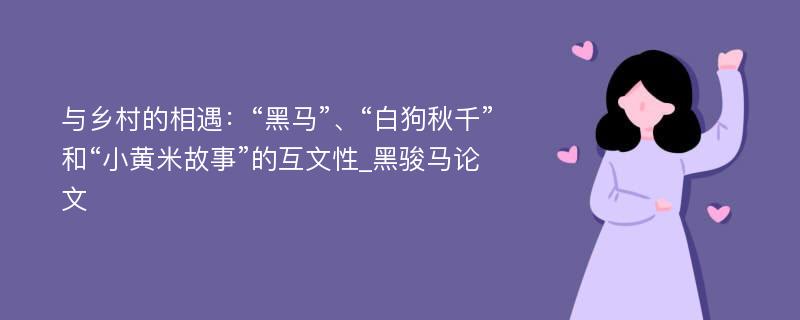
遭遇乡村:《黑骏马》《白狗秋千架》《小黄米的故事》的互文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米论文,骏马论文,乡村论文,故事论文,秋千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与农民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最重要的两类形象,而知识分子与农民/乡村的关系也一直是新文学生生不息的重要命题。根据笔者的研究,尽管不同历史阶段对这一命题有不同的表述,却常见一个共同的表述模式,那就是这一命题常常被纳入两性关系中来展开①。因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历史阶段几乎都会出现一些涉及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之间两性关系的著名文本,如1920、1930年代柔石《二月》、郁达夫《迟桂花》,1950-1970年代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②,1980年代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古华《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路遥的《人生》、张承志《黑骏马》、莫言《白狗秋千架》、贾平凹《浮躁》,1990年代王安忆《叔叔的故事》、贾平凹《高老庄》、铁凝《小黄米的故事》、21世纪初年贾平凹《秦腔》、毕飞宇《平原》、阎连科《风雅颂》、葛水平的《地气》、董立勃《米香》等等。笔者曾多次著文探讨过这一表述模式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想象之间的深层关联性。③本文选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黑骏马》④《白狗秋千架》⑤《小黄米的故事》⑥三个文本,通过对文本细节及其互文性的细读并联系三个文本所赖以产生的知识背景,探究其中所牵涉到其他层面的文化内涵。“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⑦那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文学研究就是对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正是从互文性中我们才得以窥见隐秘的文化逻辑。这正是本文的学理基础。
一、似是而非还是戏仿
张承志发表于1982年的《黑骏马》和莫言发表于1985年的《白狗秋千架》,两篇小说在情节、结构、叙述人称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如,都包含了游子返乡赎罪的原型,都叙述一个阔别乡村多年的游子返乡寻找青梅竹马恋人的故事,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人“我”讲述的故事。“我”自幼生长在草原/小村庄,与清纯美丽的草原/乡村少女索米娅/暖青梅竹马,后来“我”离别草原/乡村,去城市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而在“我”离去后,索米娅/暖历尽磨难,嫁了一个粗暴彪悍没文化的丈夫,生下一大群孩子。索米娅的丈夫是个粗野的赶车人,而暖的丈夫则是一个粗野的哑巴农人。多年后“我”重返故乡,重逢在贫穷与劳作中苦苦挣扎的索米娅/暖,激起心灵的震撼。两篇小说都有一个与主人公相依为命通人性的同时又贯穿故事始终的动物形象,在张承志笔下是一匹名叫钢嘎哈拉的神勇的黑骏马,而在莫言笔下则是一只白狗。两篇小说的题目都来自这个动物形象,一黑一白,互相对称。⑧
尽管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但不难看出,《黑骏马》俨然承袭了二世纪非常典型的原乡想象脉络,在《黑骏马》中,原乡是作为一个人性、道德、审美的高地而呈现;而《白狗秋千架》则是对这种想象的彻底颠覆,甚至让人怀疑是对《黑骏马》的刻意戏仿。这样的颠覆或戏仿主要来自两个乡村女性主人公形象之间的似是而非。在《黑骏马》中,索米娅虽然历经磨难、贫穷、厄运,但依然保持高贵的内心,对命运的承受与包容、对苦难的淡定与坚忍、对草原、孩子、亲人、世间一切的博爱,俨然是地母的化身。记忆中那红霞般的草原少女沙娜(索米娅的小名)虽然已经逝去,但眼前的草原母亲索米娅依然美好,“我”偶尔还能从她的脸上看到“复活的美丽神采”。面对眼前的索米娅,“我”依然一往情深,最后“我”在心里深情地喊道“再见吧,我的沙娜……让我带着对你的思念,带着我们永远不会玷污的爱情,带着你给我的力量和思索,也去开辟我的前途……”
《白狗秋千架》中,“我”记忆中的暖一如《黑骏马》中“我”记忆中的索米娅一样美好,但眼前的暖却截然不同了。小说一开始就写到离开故乡多年后返乡的“我”与劳作中的暖在故乡桥头狭路重逢的情景。当认出“我”之后,暖“用左眼盯着我看,眼白上布满血丝,看起来很恶。”而接下来的情景更加残酷:
“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吧?”我嗫嚅着。
我看到她耸起的双肩塌了下来,脸上紧张的肌肉也一下子松弛了。也许是因为生理补偿或是因为努力劳作而变得极大的左眼里,突然射出了冷冰冰的光线,刺得我浑身不自在。
“怎么会错呢?有饭吃,有衣穿,有男人,有孩子,除了缺一只眼,什么都不缺,这不就是‘不错’吗?”她很泼地说着。
我一时语塞了,想了半天,竟说:“我留在母校任教了,据说,就要提我为讲师了……我很想家,不但想家乡的人,还想家乡的小河,石桥,田野,田野里的红高粱,清新的空气,婉转的鸟啼……趁着放暑假,我就回来啦。”
“有什么好想的,这破地方。想这破桥?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她说着,沿着漫坡走下桥,站着把那件泛着白碱花的男式蓝制服褂子脱下来,扔在身边石头上,弯下腰去洗脸洗脖子。她上身只穿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衫上已烂出密麻麻的小洞。它曾经是白色的,现在是灰色的。汗衫扎进裤腰里,一根打着卷的白绷带束着她的裤子,她再也不看我,撩着水洗脸洗脖子洗胳膊。最后,她旁若无人地把汗衫下摆从裤腰里拽出来,撩起来,掬水洗胸膛。
汗衫很快就湿了,紧贴在肥大下垂的乳房上。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这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我于是问:“几个孩子了?”
“三个。”她拢拢头发,扯着汗衫抖了抖,又重新塞进裤腰里去。
“不是说只准生一胎吗?”
“我也没生二胎。”见我不解,她又冷冷地解释,“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像下狗一样。”
让我们对照一下《黑骏马》中“我”重逢索米娅的情景:
她变了。若是没有那熟悉的脸庞,那斜削的肩膀和那黑黑的眼睛,或许我会真的认不出她来,毕竟我们已阔别九年。她身上消逝了一种我永远记得的气味;一种从小时、从她骑在牛背上扶着我的肩头时就留在我记忆里的温馨。她比以前粗壮多了,棱角分明,声音喑哑,说话带着一点大嫂子和老太婆那样的、急匆匆的口气和随和的尾音。她穿着一件磨烂了肘部的破蓝布袍子,袍襟上沾满黑污的煤迹和油腻。她毫不在意地抱起沉重的大煤块,贴着胸口把它们搬开,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又红又粗糙。当我推开她,用三齿耙去对付那些煤块时,她似乎并没有觉察到我的心情,马上又从牛车另一侧再抱下一块。她絮叨叨地和我以及前来帮忙的炊事员聊着天气和一路见闻,又自然又平静。但是,我相信这只是她的一层薄薄的外壳。因为,此刻的我在她眼里也一定同样是既平静又有分寸。生活教给了我们同样的本领,使我们能在那层外壳后面隐藏内心的真实。我们一块儿干着活儿,轰轰地卸着煤块;我们也一定正想着同样的往事,让它在心中激起轰轰的震响。
《黑骏马》中的“我”因为不能忍受城市势利、庸俗,才回到草原寻找那“红霞般”的草原少女沙娜(索米娅小名)。虽然现在的索米娅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沙娜,饱经岁月磨难,容颜已经美丽不再,但却焕发出另一种的诗意,淡定、包容而慈爱,这是一种母性的诗意光芒。正是这种诗意光芒照亮“我”的返乡之旅。而《白狗秋千架》中,“我”的返乡之旅却因为现在的暖而黯淡无光。尽管“我”与暖之间同样有着诗意的过去,但过去的诗意已经荡然无存。葬送“我”对故乡、往昔美好怀想的不仅是眼前暖的“恶”与“泼”,更重要的是她的丑——外形的巨大改变,她的独眼、她的邋遢,尤其是她毫无顾忌地暴露出的丑陋不堪的肥大下垂的乳房。“看着那两个物件,我很淡地想,这个那个的,也不过是这么回事。正像乡下孩子们唱的:没结婚是金奶子,结了婚是银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而《黑骏马》中虽然“我”也注意到索米娅外表的不再美丽,——“袍襟上沾满黑污”,“手指又红又粗糙”“声音喑哑”,这些细节始终与性无关,而且“我”也更关注索米亚的神情,而不是身体。如果说,过去红霞般的少女沙娜是一首诗,那么,现在地母般的索米娅则是另一首诗,或者说是一支苍茫的古歌,在辽阔的草原上低回流转。这无疑折射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文主体的诗意内涵。而《白狗秋千架》中的“我”对眼前的暖身体的评议表明“我”相当世俗化的身份。这样的世俗化还体现在另两个细节上,如“我”对自己在城里高校将被提为讲师的前景非常憧憬,一见面就特意和暖提起这事,而且此次返乡还特意穿一条标志城市物质现代化的牛仔裤。“知识分子”身份显然只是“我”的职业身份,并没有赋予“我”多少精神性的内涵。这个身份也可以被置换为京城大学的准讲师。标志这个身份的是校徽(返乡也佩着)、牛仔裤、送给暖的哑巴丈夫和儿子的自动伞、高级糖等等外在物质性的、世俗化的现代化物件。而《黑骏马》中我们始终看不到从城里来的“我”身上有任何提示城市、知识分子世俗身份的物质标志,相反的,“我”对城里的一切充满厌倦,但精神性诉求却非常强烈,整部小说充满男主人公丰繁细致的内心感受,感伤、抒情而浪漫,一种典型知识分子根性。同是创作于1980年代前期,但两篇小说的这些惊人差异着实让人震惊。
需要隆重提到的是,两篇小说结尾对两位乡村女性主人公的描写更是似是而非。在《黑骏马》结尾,“我”翻身上马即将离去的一刹那,索米娅突然抓住了“我”的缰绳,急切地说出了她最后的请求:
“我有一件心事,不,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是不是该说——”她满怀希望地凝视着我的眼睛,犹豫了一下。突然又用热烈的、兴奋的声调对我说:“如果,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弃的话,就把那孩子送来吧……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懂么?我养大了再还给你们!”她的眼睛里一下涌满了泪水。“你知道,我已经不能再生孩子啦。可是,我受不了!我得有个婴儿抱着!我总觉得,要是没有那种吃奶的孩子,我就没法活下去……我一直打算着抱养一个,啊,你以后结了婚,工作多,答应我,生了孩子送来吧!我养成人再还给你……”
而《白狗秋千架》中暖也在“我”离去的半道截住了“我”,向我提出最后的请求:
“……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索米娅与暖的请求从表面上看似乎大同小异,都是想要一个孩子。不同的是索米娅是要求替“我”抚养孩子,当然是“我”与别的女人(城市女人)生的孩子,养大了再送还“我”,而暖的要求是要和“我”生一个孩子。同样都是要求一个孩子,但索米娅的请求被叙述成一种地母般的品格、母爱的本能——“没有那种吃奶的孩子,我就没法活下去……”,没有任何现实的实际目的。而暖的要求则非常现实,她想要一个正常的会说话的孩子,她已经和哑巴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了。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这个问题,她抓住了“我”对她旧情、愧疚,以此作抵押,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容拒绝。而这一要求的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仅深度拷问了“我”对她的情义,也将知识分子/男性与乡村/乡村女性的关系这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命题推向了死角。小说并没有写“我”听完暖的请求后的反应,就戛然而止。这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答案。而在《黑骏马》的结尾答案是非常明确的:结束返乡之旅,“我”从索米娅、草原(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身上悟出了生活的真谛:“让我带着对你的思念,带着我们永远不会玷污的爱情,带着你给我的力量和思索,也去开辟我的前途……”这同时也是作者对现代化前景的激情、浪漫想象——汲取了乡村营养的现代化必然更加美好。
二、想象还是发现原乡
在1980年代前期的文化语境中出现《黑骏马》《白狗秋千架》这样两个似是而非却又截然不同的文本真是匪夷所思。《白狗秋千架》创作于1984年的冬天,这个时节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诗意原乡几乎是所有中国作家乡村叙事的重要内涵。在政治层面上写改革给乡村带来希望、生机,如贾平凹《小月前本》《黑氏》《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张炜《声音》《拉拉谷》《一潭清水》《芦清河告诉我》;与此同时,也出现久违了的对乡村文化传统的守望,书写乡村山民古朴自在的生存方式,如汪曾祺《大淖记事》《受戒》、贾平凹《商州初录》等等,或把上述两种主题互相穿插。而莫言竟然毫不留情地终结上述种种原乡想象的诗意,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正如王德威在评价莫言这篇小说时说到,“《白狗秋千架》未必是莫言最绚丽最炫目的作品,却能切中寻根、乡土情结的要害”。他特别提到“我”与暖在桥上重逢的那段场景:“当代文学里,再没有比这场狭路相逢的好戏更露骨地亵渎传统原乡情怀,或更不留情地暴露原乡作品中时空错乱的症结。”⑨《白狗秋千架》出现在莫言大红大紫的成名作《红高粱》之前,在当时并在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莫言却非常看重这篇小说,声称这篇小说对他的整个创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⑩这其中大有深意。这篇小说游离出了20世纪乡村叙事的所有传统,指示着,乡村不仅不是政治改造、文化启蒙的对象,不是文化寻根的对象,甚至不是心灵皈依的对象,从而还原出了一个自在的乡村面貌——乡村是美好的,乡村也是丑陋的、世俗的。这就是后来《红高粱》中那句著名的话,“我”的故乡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同时也是最王八蛋”之地。这是乡村的发现,也是民间的发现。当然,在《红高粱》中,乡村的美丽连同丑陋一起被神话化、传奇化,莫言还是走上营造、建构原乡传奇的道路,而且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因为全球化时代需要这样的原乡传奇,它可以抚慰现代性带来的文化乡愁。全球化是对地方感的最大威胁,出于对这一威胁的克服引发了持续不歇的对地方特色的建构。对“地方”的象征性建构正是19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以来的乡村叙事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诉求。“高密东北乡”便是这方面典型例子。如果说在《红高粱》中莫言发明了原乡——建构了一个能够提供强烈地方感的传奇神话之地,那么,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实际上是发现了原乡,一个与知识者种种原乡想象全无干系的自在之地。主人公的返乡之旅实际上是发现之旅,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暖”这一非常特别的乡村女性形象上。
五四以来乡村女性形象一般有这样的几个谱系,乡村之痛的象征,愚昧落后乡村的投影,启蒙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对象,如鲁迅《祝福》中祥林嫂、《明天》中的单四嫂,叶绍钧《这也是一个人?》中的像牛一样被出卖的“伊”,台静农《烛焰》被逼嫁给弥留之际的男人冲喜的乡村少女翠姑,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被典租的春宝娘,启蒙叙事中的乡村女性大凡都属这一类型;乡村之美的象征,质朴纯洁人性形式的象征——如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旺盛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如许地山《春桃》中的春桃,郁达夫《迟桂花》的莲姑;含辛茹苦、博爱、母性/地母的象征,如《黑骏马》中的索米娅、莫言《丰乳肥臀》中上官氏;柔情似水又深明大义妻子——如孙犁笔下的水生嫂们。当然,上述分类常常是交叉的,很多乡村女性形象同时兼具上述几种象征意义,如索米娅的形象兼具质朴纯洁人性形式(少女时代的索米娅)与含辛茹苦、博爱的母亲象征意味(中年索米娅)。而暖的形象却很难被纳入上述任何类型,她不具有上述种种乡村女性的本质化特征——这些特征其实是被建构出来的,本质化的乡村女性是本化原乡的载体。而暖的出现却宣告了这样的原乡想象的虚妄。如果说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实际上是发现了原乡,那么,这一发现源自对乡村女性暖的发现。
祛除一切象征诗意之魅,游离出知识分子(男性)的种种原乡想象的惯例之后,暖呈现出一个女性个体真实的生命欲求——身处四个哑巴包围中的暖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要个会说话的孩子”。暖对孩子的要求并非出于索米娅式的母性本能、地母情怀(这是乡村女性最经常被赋予的“本质”,像多年之后的《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那样),她不是只要一个孩子而是要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一个对话者和倾听者,“哪怕有一个哑巴,和我作伴说说话”,她要求的实际上是一开口说话的权利。她知道尽管自己是正常人,具有开口说话的能力,但是如果没有对话者和倾听者,也就无从真正拥有话语权。而“我”的到来让她看到了实现这一愿望的可能性,她不顾一切抓住这个可能性。暖的主动献身也并非出于性爱本能(像多年之后的《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和女儿们那样,这也是乡村女性经常被赋予的一种功能、“本质”),更与同时期张贤亮笔下的马樱花们不同,后者出于对知识、知识分子的膜拜,实际上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知识分子对自我身份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暖的“主动献身”恰恰无情终结、嘲弄了这种想象。“我”在暖眼里只是个具有优越生育条件的男人,身体健全没有残疾,比她的哑巴丈夫强,而且完事之后就消失走人——回到遥远的北京,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这比在村里找其他男人更合适。从来都是男人将女人视作传种的工具,知识分子将农民视作传种的工具(如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中秀才租用农妇为自己传种),而这回暖竟然企图借用男性知识分子“我”来为自己生育一个健康的后代。这是暖向“我”主动献身的全部原因,它彻底粉碎了“我”一直潜在的知识分子身份优越感。暖看起来惊世骇俗的行为恰是对命运的不甘与挣扎,从而呈现出一个特殊的主体位置,一种另类主体性。由此可见,不同的空间位置对女性的主体性有着不同的模塑。乡村女性暖不再是知识分子“我”身份想象的衍生物,而是一个自在自足的主体。
三、身份误认
如果说在《黑骏马》中,知识分子“我”当年的出走源自对草原/奶奶/索米娅的误解,他无法理解奶奶和索米娅所代表的古老的草原生活法则,将它们判定为愚昧、落后,那么,许多年之后的返乡之旅不仅是赎罪之旅,同时也是理解之旅。“我”重新理解了索米娅和奶奶,并在精神上皈依她们所象征的草原。而《白狗秋千架》的返乡之旅则是一个误解之旅,不仅眼下暖的所作所为大大出乎“我”对她的想象,而且,暖对“我”的身份也充满误认。从京城的高校返回愚昧落后的穷乡僻壤,“我”原本是带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的,但万没料到“我”在暖眼里只不过是个比她的哑巴丈夫健全、生育条件良好的男人,至于“我”自己最看重那些文化方面的优越性,暖则根本看不见,抑或视而不见。十年后铁凝的《小黄米的故事》却以另一个故事再一次呈现了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相互间的身份误认,这表明这一叙事逻辑并非偶然。
《小黄米的故事》叙述了一个发生在城里来的画家老白与山区公路路边店从事色情行当的17岁乡村女孩之间的故事。当地人管从事这一行当的女孩叫“小黄米”。整个情节的展开,实际上就是老白和小黄米互相对对方身份进行误认的过程。首先,在画家老白的想象中,乡村女性茁壮的身体,是“人的最美的瞬间”,是人性美的极致,如同古希腊的“掷铁饼者”。并构思了一个“炕头系列”油画框架,为此不惜风尘仆仆地来到深山公路的路边店,企图在小黄米们身上寻找素材。但他付了钱让小黄米赤裸着身体摆出各种造型,拍了整整一卷胶卷,却始终没发现他一直心仪的“最美的瞬间”。他让小黄米假装缝被子,小黄米随口答道,“现时谁还缝那个,买个网套一罩不得了?”眼前的小黄米所作所为俨然与老白的想象大相径庭。小说显然无情地朝讽了知识分子对乡村女性本质化想象的虚妄。
而小说似更细致地写了小黄米们对老白身份的误认:老白一出场,小黄米还有对面店里的另一小黄米就立即认定他的身份,他神色的迟疑,说话不懂行,让她们一准认定他是个初入港的客人。紧接着出场的老板娘对老白的身份更有一番精彩的认定,“反正不是领导干部。您没车,你这衣服当领导的也不穿,他们穿西装,清一色的鸡心领毛衣,还有您这包,里面准有照相机。”老板娘虽然一眼辨识出老白的知识分子身份——“……还有您这包,里头准有相机”,但在她眼里带着照相机的人的规格显然不如领导,没有任何优越性。老白反复表明自己只是要小黄米摆摆姿势,拍拍照,并不想做别的,“希望她们能理解‘他的事业’”比她们想象的事要高尚得多,但她们谁也没有理会这种声明。她们坚定地认为他和来到这里的任何一个客人并无差异。这让人想到《孔乙己》中的细节,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孔乙己一心想让人看到他是站着喝酒的客人中唯一穿着长衫的,因此与众不同,高人一筹,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也是站着喝酒,与众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他那件破旧的长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及至老白进入小黄米做生意的房间,开始实施他自以为“高尚”的事,要小黄米摆出各种造型拍照,小黄米不仅不觉得这比一般客人直接“办事”高尚,还非常不耐烦,觉得他远不如其他客人简单干脆,始终在等待着他像其他客人那样开始正儿八经地“办事”。最后老白拍完照,不“办事”就给钱走人,小黄米更是觉得匪夷所思。从小黄米房间落荒而逃的老白,彻底陷入身份危机中。首先是小黄米粉碎了他一贯的有关乡村女性身体有着“人的最美的瞬间”的艺术理想,平白无故地浪费他一卷胶卷。再者,虽然并没有“办事”,只为高尚目的而来,但在老板娘特殊的注视下,老白便“觉得自己倒真像位刚办过事的人”。就这样,老白陷入嫖客不像嫖客、画家不像画家身份暧昧中。
事实上,老白的形象一开始就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那些体恤底层、带有民粹倾向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大相径庭。他并不为公共关怀而来,只为了收集自己的“炕头系列”油画素材而接近小黄米,他是一个敬业的职业画家,专业人士,而不是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老白对小黄米们的生活并不关心也不想关心,更没有要启蒙、拯救小黄米的意图。显然,老白的出现,预示着一个世俗化时代的到来。(11)而小黄米也不需要这样的启蒙、拯救。她并没有因为老白的知识分子身份就对他格外优待,她甚至根本不关心老白的社会身份,在她眼里,他只是一个有奇怪要求的客人。她关心的是老白最后给的一沓钞票。老白和小黄米,彼此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尽管偶然相遇,但互相隔膜,互不沟通。小黄米有自己的生活世界、生存方式,不会因为老白的到来而有任何改变。在这个层面上,《小黄米的故事》似乎有意与1980年代张贤亮《绿化树》形成深刻的对照。《绿化树》中的马缨花原本也是一个地下的“小黄米”,经常接收村里一些男人暧昧的馈赠,但一旦遇见章永璘,她立即重新做人,开始另一种人生。为他守身如玉、为他含辛茹苦,对他顶礼膜拜,只因为章永璘有知识、有文化。显然,不难看出,在这点上,《小黄米的故事》有意无意地解构了《绿化树》一类的叙事。
如果说,《黑骏马》以诗意感伤笔调延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那种将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关系纳入两性关系的叙事传统(12),那么,无论是《白狗秋千架》还是《小黄米的故事》,都是对这个传统的戏仿,这样的戏仿不是要诉说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背叛(像许多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那样),(13)而是呈现两者之间的毫无干系。背叛,从来都是相对于忠诚而言的,而毫无干系的两者之间就无所谓背叛。当然,在这两篇小说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到底还是发生了一些干系,那就是彼此都想将对方当作可资利用的资源,暖企图将“我”是当作生育健康后代的工具,而老白则企图将小黄米当作完成“炕头系列”油画的材料。结果谁也没有得逞,这可能是这两篇小说区别于同类题材小说的意义所在,它宣告了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关系这一新文学生生不息的重要命题也许压根就是一个伪命题。
附带要提到的是,这三个文本实际上还牵涉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叙事原型,即“外来者故事”:一个从外面世界/城市空间返乡或路过乡村的知识分子/外来者,与乡村人事间发生种种纠葛。笔者曾多次著文讨论过这一叙事模式及其所隐含的文化意义,(14)在此就不再赘述。
①这其中隐含这样的文化逻辑: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缺乏一个足以影响并制约政统的学术道统,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社会缺乏一个鼓励独立运用知识的评价体系来确认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只能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依附于政治文化体系中获得身份认同。这个政治文化体系就是民族、阶级的政治,其核心能指就是民族国家,以此为中介,知识分子才可以获得明确的身份。五四以后处身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被认为是构成民族国家的主体、现代性社会运动主要承担主体。于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之间的关系,作为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实际上就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建构/想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相关论述可参见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135~136页。
②《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的主题并非探讨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关系,但其中人物关系都涉及到将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关系纳入两性关系描写中这个叙事传统,如《三里湾》中,中学毕业生范灵芝选择没什么文化程度不高,但热爱集体、政治进步的王玉生,《创业史》中徐改霞虽然只有高小文化,但身上颇有知识女性的色彩,可她就是喜欢“泥腿子”梁生宝,《艳阳天》想当诗人,对革命充满幻想的回乡知青焦淑红最后选择文化程度不高,但“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党支部书记萧长春作自己的恋人。类似这样两性关系模式在这一时期小说中十分常见。
③笔者曾从不同侧面论述过这一命题,参见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4~55、第135~137页,《改造+恋爱叙事模式的文化权力意涵》,《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在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启蒙叙事的一个支点》,《南开学报》2011年第4期。
④张承志:《黑骏马》,《十月》1982年第6期。本文修改成文之际,因想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白狗秋千架》的原载刊物,这才发现竟也有人将《黑骏马》和《白狗秋千架》进行过对照,即胡斌《〈黑骏马〉与〈白狗秋千架〉比较——兼及两部小说的电影改编》一文,《电影评价》2008年第22期,浏览内容后发现,拙文与胡文并无内容上的雷同,研究对象的雷同实属巧合,鉴于时下混乱的学术秩序,为避免误解,特此说明。
⑤莫言:《白狗秋千架》创作于1984年冬天,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4期。
⑥铁凝《小黄米的故事》,《青年文学》1994第4期。
⑦这是索莱尔斯对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重述,转引自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和流变》,《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⑧这两部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的之处就是都在多年之后被著名导演改编成电影,并多次获得国际国内大奖。即谢飞的《黑骏马》(1995)与霍建起的《暖》(2002)。《黑骏马》获1995年第18届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996年俄罗斯第五届圣彼得堡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奖等5项奖;而《暖》获得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电影《黑骏马》基本忠实于原著,而电影《暖》与原著天差地别,它所呈现的原乡想象形态恰恰是小说《白狗秋千架》极力要解构的。
⑨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1页。
⑩莫言:《感谢那条秋田狗——日文版小说集〈白狗秋千架序〉》,《西部》2007年第9期。在此文中,莫言还提到,正是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字样。有论者误认为“高密东北乡”最早出现在发表于1984年第8期《奔流》的短篇小说《秋水》中,是因为《白狗秋千架》发表的时间迟于《秋水》。
(11)学界一般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而1990年代正是公共知识分子被专业与媒体知识分子所取代的年代。参见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知识分子的转型实际上源自时代的转型,相对于1980年代,1990年代的到来意味着一个世俗化时代的到来,因此,老白的形象的出现实际上有着典型的时代意义。
(12)这篇小说不仅延续了将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关系纳入两性关系中这一新文学绵延久远的叙事传统,同时还牵涉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汉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之间复杂的文化权力纠葛,提示着在现代性实践中,似乎不能一味地将古老的文化形态简单地判定为愚昧、落后,文明与愚昧、现代与传统之间并非单向度的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兼容。这实际上隐讳地质疑了当时的时代主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在当时实属可贵创见。
(13)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频繁出现知识分子对乡村/乡村女性背叛的书写,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如乔以钢:《近30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南开学报》2011年第4期、孟繁华:《新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14)相关论述参见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151-172页,王宇:《另类现代性:时间、空间与性别的深度关联——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外来者故事”模式》,《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等。
标签:黑骏马论文; 白狗秋千架论文; 小黄米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互文性论文; 红高粱论文; 原乡论文; 丰乳肥臀论文; 创业史论文; 绿化树论文; 艳阳天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