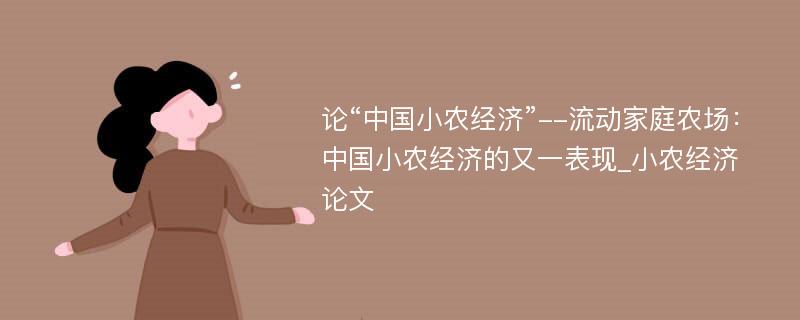
笔谈: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流动性家庭农场:中国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笔谈论文,流动性论文,中国论文,农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庭农场是新词,但却不是新事物。流动性家庭农场,作为家庭农场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较长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来讲,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更为接近,是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也可以说,流动性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的延伸和升级。同样,流动性家庭农场作为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在农业劳动力匮乏地区,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对于粮食安全和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积极意义。
一、何为流动性家庭农场?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动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决定,明确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手段,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一时间“家庭农场”成为了国内理论界和政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关于什么是家庭农场,至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大致来说家庭农场被界定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政策的扶持下,各地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事实上,真正的“家庭农场”早已经出现,不过它是以“流动”的形式出现。
所谓流动性家庭农场是指,相对于特定的经营者来讲,经营的土地具有不固定性,是“流动”的;从经营形式来讲,他们属于家庭农场,但是由于其流动性,他们是家庭农场的特殊形式——流动性家庭农场。相对于土地原承包人而言,经营者为“外地人”(参考外地农民工,这里的外地是指跨县),他们是外来的承包户,俗称“外地包地农”。流动性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其经营的土地不固定,根据各地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对盈利状况的评估,人和地可能随时发生分离。因此,从动机上讲,流动性家庭农场有被动和主动之分。无法取得土地经营权,是被动流动;基于盈利状况的评估而产生的流动则是主动流动。本质上,农场之所以“流动”,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规定,农村土地归村级所有,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土地可以进行自发流转,但是流转具有一定期限。因此,对于流入方来讲,土地的经营权并不是永久的,具有阶段性。这就造成人和地只是暂时的结合,外地人经营的家庭农场,由于地块的变动,家庭农场具有流动性。流动性家庭农场的出现,不是来自于政府的扶持,它有着较长历史和发展阶段。
二、发展与历史演变
从目前来讲,由外地人构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具有了相当数量,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早,工业化程度高,农业的相对利润低等特点,从分田到户以后不久,本地人就开始自发地进行土地流转。外地人构成了这些地方农业经营的主力军。虽然没有全面的统计资料,但是从有关的研究得出的数据已经颇为可观。华东理工大学相关研究指出①,上海市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显示,2006年,全市共有经营耕地农户64.04万户,其中本地户为59.98万户,占户籍总人口的93.7%;外来户为4.06万户,外地人占6.3%。但是外来户户均经营规模远远大于本地户,外来户为7.88亩,本地户均2.18亩。如果换成经营面积,外来户经营耕地面积为32.99万亩,占农户耕地总面积的20.15%。到2010年底,上海本地农业人口下降到37.09万人,只占户籍总人口的2.63%(来自上海统计网)。2009年,上海外来菜农数量就有9万人。研究者还根据调研蹲点的材料指出,N镇2002年外来务农人员有656人,2011年达到了3765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外地人构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以笔者长时间调查的安徽某地区为例,农民外出务农代替了外出务工,成为了流动性家庭农场的重要流出地。此地区,有四个乡镇的农民集中外出务农,当地农民说,“在盛桥镇上买房的十有八九都是包地的,我老家,青山区(被合并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数过去80%都在外包地”。从笔者蹲点的S镇所在的苍头村为例,外出包地的劳动力占到村庄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左右。经过笔者统计,以户为计算单位,外出包地农户占总户数的26%②。苍头村17个自然村,苍头咀、大骆、大张、河东、洪庄、黄店、金元、沐桥、沙龙、上陈、上田、田上、兀东、下田、小蒋和小张,外出包地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分别为:35%、29%、17%、10%、0、14%、16%、14%、24%、30%、18%、40%、100%、31%、6%、30%和33%。由于统计上是人均3.5人的小家庭,因此,很多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并不均具有进入市场的劳动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出包地农民如果按劳动力结构来算,比例会大大提高。换句话讲,本地外出包地替代了外出务工,成为农民生计的主要来源。虽然没有官方统计,据乡镇干部估计,每个乡镇外出包地规模在100万亩左右。可以说,外出包地形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不是个案,也不是局部性事件。
流动性家庭农场不是偶然性的,它的发展有着较长历史。大致来讲,可以分为5个阶段:(1)80至90年代初期,流动性家庭农场零星开始出现。此时,伴随部分农民到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打工,少数人开始转向农业领域,以“代耕农”的形式出现。此阶段的特点是,种地规模小、无租金或少租金,包地人数少。(2)90年代初,流动性家庭农场逐步兴起。一些农户开始认识到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人数开始增多,种植的面积在数十亩到100亩左右,不过还是以传统农耕为主,机械化程度低,有少量收割机,地租不多。(3)90年代末到税费改革时期,流动性家庭农场经营的高风险时期,有部分回流。此阶段,粮食从计划经济中退出,粮食保护价格尚未形成,价格波动幅度大。1996—2000年之间,粮食价格从一元到四五毛不等,给规模种植的家庭农场造成了非常高的风险,一部分农户从中退出。(4)2003—2012年,流动性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时期,外出包地农民数量已经相当庞大。此阶段,由于税费免除,粮食价格稳定,各种粮食补贴到位,再加上农业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的不断推进,流动性家庭农场的数量迅速上升。此阶段的特点是,土地地租不断增加,土地经营面积加大,机械化程度高,收入较为稳定。另外,由于地租和国家政策的干预,农场的“流动”性质更为明显,“找地”,从沿海到内陆,成为了流动性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生存策略。(5)2012年,流动性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经营主体,而成为家庭农场的一种特殊形式。2013年,党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手段,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一时间有关家庭农场的发展,确权登记和扶持政策在各地开始陆续出台。
三、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经济
目前从农业经营主体来讲,农业可以分为小农农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大户以及企业农场。流动性家庭农场是家庭农场的一种特殊形式,与政府等扶持的家庭农场相比,流动性家庭农场的农业经营形式与小农经济更加贴近(区别于资本农业),是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农业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
(1)在劳动力方面,自我劳动开发程度高,雇工比例极低。雇工比例,一直是小农农业和资本农业的重要区别,与完全依靠雇工的资本农业不同,流动性家庭农场几乎完全使用家庭劳动力进行农业经营。比如,笔者在安徽繁昌P镇的调查中发现,上千亩以上的种植大户,完全依赖雇工,其中还使用了代管的分级管理模式;而由政府扶持起来的本地家庭农场,平均雇工人数是1.5人/亩(以小麦-水稻套种模式为主),而由外地人形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的雇工率是0~0.5人/亩,比如张大哥,46岁,23岁外出包地,目前夫妻两人在繁昌P镇经营土地200亩,雇工情况具体为,撒稻2个工、施肥4~6个工、收割时20个工,拔草偶尔请工,年雇工30个左右,即0.15人/亩。流动性家庭农场依靠自身劳动力经营,用农民的话讲,“请人就划不来,挣的是辛苦钱、汗水钱”。
(2)从农业积累来看,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农业一致,积累主要用于家庭再生产和消费,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积累是否用于扩大再生产,也是资本农业区别与小农农业的重要变量。资本农业高度依赖雇工,农业经营的规模不受劳动力的限制,而小农农业完全依赖自身家庭劳动力,因此,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流动性家庭农场和小农的农业剩余,都用于家庭再生产和消费。对于流动性家庭农场而言,一对年轻夫妻经营土地200亩,每年的利润在5万~10万元左右,也就相当于一对夫妻的务工收入。5万~10万元/年的收入,在现有人均收入情况下,基本维持家庭的自身消费。因此,土地经营的规模,不仅受制于农业的积累剩余,更受制于家庭劳动力结构。目前由老人、妇女构成的小农农业与青壮年构成的中农和流动性家庭农场,构成了农业中自耕农的主体。
(3)从农业经营组织来讲,其基本单位是家庭。流动性家庭农场,在农地规模上稍大于小农,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流动性家庭农场的规模并没有无限扩大,而始终是以家庭劳动力结构为基础。家庭劳动力构成了获取农业剩余的主要因素,这区别于资本农业,主要通过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来获得农业利润。对于流动性家庭农场来讲,农业规模具有伸缩性,小的数十亩,大的有400~500亩,集中在200~300亩,这是因为家庭劳动力的不同。比如,60岁以上的老人包地,通常的面积不会太大,可能就在100亩上下。但是,如果年轻夫妇外出经营家庭农场,他们的规模不会低于200亩;而一些老人和孩子组成的联合家庭外出经营家庭农场,面积就可能达到400~500亩。对于流动性家庭农场而言,经营土地的规模是“适度”的,这个适度是指,在已有条件的约束下,人和地(劳动力和土地)生产要素配置的比例适度。在这一点上,比起当前老人、妇女、中农等小农农业,流动性家庭农场对劳动力的开发程度稍高。但是本质上,他们都是以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其中,“中农”在劳动力的利用上与流动性家庭农场最为接近。
(4)从资金来源来看,流动性家庭农场获取土地和购置生产资料的资金基本都来自于农业积累,而非工商资本,资本性质不强。流动性家庭农场的经营主体,大多数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具有多年的种植技能,很强的农业管理能力,依靠长期的农业剩余积累而达到数百亩的面积。这一点上,流动性家庭农场不同于大量种植大户和企业农业——依靠工商资本大肆进入农业领域。流动性家庭农场也是发育于小农,从种植数亩不等的农地开始,依靠辛勤劳动致富。与政府大力提倡的资本农业相比,流动性家庭农场很少获得国家的政策性扶持。虽然是家庭农场的一部分,但是与本地人所构成的家庭农场相比,由外地人构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常常受到当地政府的排挤,在政策扶持上受到忽视③。从此意义上讲,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一样,依靠自身劳动力开发而获得农业剩余。
(5)从土地生产率来讲,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农业接近。与企业等资本农业不同,流动性家庭农场,不涉及农业经营的层级管理和农业雇工的监督问题。大量的研究者指出,农业不同于工业,不能使用标准化的管理。农业的季节性和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农业最适合家庭经营,避免农业中的磨洋工现象。一对夫妻经营200亩左右的土地,在繁昌的调查得出,流动性家庭农场的亩产在1000~1300斤/亩,与当地的小农经营相近,比本地家庭农场高100~200斤/亩,比种植500亩或者上千亩的大户农业,要高数百斤。流动性家庭农场的经营者,长期从事农业,对农业管理精细,对生产资料的成本控制严格,因此亩产盈利最高。也就是说,从粮食安全来讲,流动性家庭农场可以保证粮食产量,与小农的精耕细作类似,远远好于大规模种植。
从雇工、农业积累的分配、经营组织单位和资金来看,流动性家庭农场与小农农业几乎一致。与小农一样,流动性家庭农场依托于家庭劳动力进行农业经营;家庭劳动力开发程度较高,雇工比例极低。农业经营单位是家庭,根据家庭劳动力结构调整经营结构。生产资料的购置来自于长期农业积累,非工商资本的转移,资本性质不强。从土地生产率来讲,它能与小农农业匹敌。总之,在本质上,流动性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
四、流动性家庭农场对小农经济的延伸与补充
流动性家庭农场在很多方面与小农农业相似,另一方面,流动性家庭农场也可以说是小农农业的延伸。从小农—中农—流动性家庭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序谱,流动性家庭农场在一些方面是小农农业的升级版。比如从单位劳动生产率来讲,流动性家庭农场会更高。因为流动性家庭农场可以根据家庭人口调整土地规模④,人均种植的土地面积较大,而且充分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手段,流动性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很高。在机械化使用上,流动性家庭农场更加积极。在技术更新和农业管理方面,流动性家庭农场的探究欲望和创新能力更强。在职业化程度方面,流动性家庭农场更高,兼业的农户少,农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样来看,流动性家庭农场延续了小农农业的一些优点,在技术发展、人地结构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改造自身,显示出“小农”持久的生命力。
有人说,积极发展家庭农场,会影响小农农业的发展,但是,笔者认为流动性家庭农场的出现并没有影响小农农业。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小农农业的补充。从流动性家庭农场的出现来看,它的生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形成,这是大多数流动性家庭农场形成的主因。流动性家庭农场大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的相对利润率低,当地农业劳动力出现短缺,于是出现了零租金的土地,致使流动性家庭农场开始出现。分田到户后的三十年中,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和对土地制度的渐进改革,流动性家庭农场持续发展。由于其单位土地生产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较高形成的可观利润,导致了当地农民要回土地自己种植的情况。流动性家庭农场获得的土地是在农户自愿下达成的协议,因此,与小农的关系是一种并存、补充,而非竞争。二是种植大户或农业企业破产间接形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前面提到,农业经营不同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具有时空分散性,必须对自然环境的微小变化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农业最适合的是家庭经营。种植大户和农业企业由于雇工成本较高,监督成本高和管理不善等,在实践层面上,往往盈利微薄或者亏损。在安徽繁昌P镇,1000亩以上的农业大户纷纷转包或者分包为200亩左右的家庭农场模式,无一例外。这也导致了当地形成了大量外地人构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这些外地人,由于没有稳定的地权,同时考虑到农业利润,往往经营一块土地不久,就要寻找新的土地,因此形成了流动性的家庭农场。
与政府扶持下催生出的家庭农场不同,流动性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常常在政策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比如,在政府主导的流转方面,外地人形成的流动性家庭农场常常受到当地人的排挤,他们往往成为二包或者三包,地租被层层加码;在农业政策的扶持上,大户补贴、农机补贴等被大户截取;在应对自然灾害的农业保险上,他们也要完全依托于作为一包的种植大户。这一切都来源于流动性家庭农场较难与农户或政府形成稳定的土地合同关系。只有在政府未大力提倡的地区,流动性家庭农场才能和当地的家庭农场一样得到较为公正地看待。也因此,流动性家庭农场更像小农一样,通过自身劳动力的开发从农业中获取剩余价值。
五、小结
贺雪峰教授认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持续的奥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小农经济具有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作为补充,流动性家庭农场在农业劳动力匮乏的地区,同样形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在中国劳动力结构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这一趋势变得更加的突出。
总之,不同于其他农业经营形式,流动性家庭农场在本质上最接近小农农业,并且,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小农农业的升级版,是小农农业的延伸。只要不是政府力推或者主导,流动性家庭农场并不会和小农形成竞争关系,相反,它是小农经济的另一种表达和补充。中国地大物博,目前仍然是小农经济主导的农业制度中,流动性家庭农场有它的根基和合理性。在局部地区和有条件的情况下,外地农业劳动力弥补当地农业劳动力不足,进而形成流动性家庭农场,是一种理性小农的表现。这样来看,小农农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小农经济的道路,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注释:
①关于外地农民务农的研究,华东理工大学有相关研究。
②苍头村4423人,1280户,户均人口约3.5人,那么显然这是核心家庭人口统计数据。按照户籍上的统计,大学生、参军人员等都独立为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出包地农民按户民籍户数的统计的比例偏小。如果按照联合家庭,或者按照劳动力所占比例进行计算,外出包地农民所占比例会高出许多。按照村委会计的估计,外出包地农民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将会达到一半以上。
③比如,在繁昌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流动性家庭农场经常作为二包或者三包(从承包大户那里再流转土地)。在土地租金、农业保险、农技服务和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受到歧视,地位与当地家庭农场存在很大差异。华东理工大学的研究者也发现,在上海,由外地人经营的土地在政策上受到一定的歧视,参见叶敏等《驱逐小生产者:农业组织化经营的治理动力》,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④不同于村庄中自发土地流转,中农等农业经营主体依靠的是村社中的人情、面子来获得土地,土地的规模受制于社会关系;流动性家庭农场的生产资料——土地通过市场地租获得,因此,土地的规模不受制于社会关系,而受制于土地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