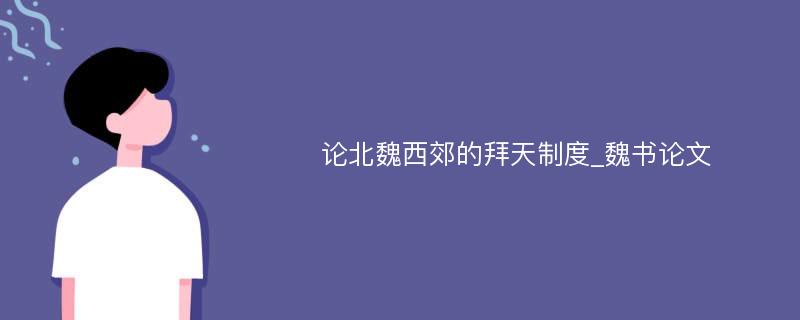
论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西郊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2)02-0056-07
北魏平城时代(注: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序章[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统治者祭天的主要形式是西郊祭天。 西郊祭天是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习俗与汉族的郊祀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郊天制度,它正式确立于太祖天兴元年(398年), 完善于太祖天赐二年(405年),显祖献文帝对它进行过微调,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诏令废止。西郊制度从开始确立到最终废止, 前后实施了近百年,几乎跨越整个北魏时期的三分之二。在此期间,汉族的南郊祀上帝之礼尽管也实行着(注: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874.19。),但与西郊祭天相比较,它的重要性几乎微不足道。西郊祭天被统治者规定为“岁一祭”制度,北魏君主频频亲临西郊之礼,这些显示重要性的礼遇,南郊上帝都很难享受到。
主宰北魏祭天之坛百年之久的西郊祭天,不仅在北魏的祭祀文化中别具一格,即使把它放到整个魏晋南北朝祭祀长廊里,它也因与汉族传统祭天的迥然之别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然而,研究北魏历史的古今中外学者却很少谈及西郊之礼,即使偶尔涉及也多以“夷礼”(注:阎镇珩.六典通考[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30.523。)加以鄙视。有感于此,笔者很想在这方面做些补缺拾遗的工作。本文探讨的西郊祭天制度只是西郊祭天现象的一个小问题,对西郊祭天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方家。
(一)西郊祭天制度的萌芽
祭天场所与时间的固定是北魏西郊祭天制度确立的标志。《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夏四月,“帝祠天於西郊”(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这是史书中关于北魏西郊祭天的最早记录,太祖天兴元年也因而是北魏西郊祭天制度正式确立的时间。在此之前,拓跋鲜卑祭天大概是在地点与时间的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魏书》中有关史料能予以证明。
(始祖力微)三十九年(258年),迁於定襄之盛乐。夏四月, 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注:魏收.魏书[M ] .北京:中华书局,1974.3。)
(太祖)登国元年(386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 建元,大会于牛川。(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
(登国六年)夏四月,祠天。(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上述三次祭天发生在‘三个不同地点、两个不同时间。由此可见,在西郊祭天制度确立前,拓跋部落的祭天在地点与时间的选择上还保留有原始部落祀无定址与祀无定时的随意性特点,它与拓跋部落建国前及建国初期“还过着游牧的生活”(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14。)的社会状况相适应。
西郊祭天制度确立前,也即迁都平城以前,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尽管祀无定址,却有定向。这种祀有定向习俗与北魏平城时代祀天于西郊关系密切。从祀有定向向祀有定址的转变,是北魏西郊祭天制度确立的关键。
拓跋传统祭祀习俗中有西向祭祀的传统。《魏书·礼志一》载太祖登国元年祭天事云:“西向设祭,告天成礼。”(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4。)不仅祭天采取西向方位,迎亡灵也采取同样方位。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元丕与孝文帝谈论迎亡灵事宜云:“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改。”(注: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4301.)“迎神于西”是拓跋鲜卑的传统习俗,从引文“自皇始(即太祖)以来,未之或改”的意思可以推知,这一传统习俗早在太祖以前即已存在。“西向设祭”与“迎神于西”显然是拓跋西向祭祀传统在祭天与祭祖上的表现。
拓跋鲜卑西向祭祀的传统大概可以上溯到两汉时期的鲜卑时代。作为一个混血的部落民族,拓跋鲜卑是汉魏时期“鲜卑与匈奴融合之后形成的”(注:周伟洲.敕勒与柔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81。),故拓跋鲜卑与两汉鲜卑有着极其密切的血缘继承与文化传承关系。两汉鲜卑与乌桓同出于秦汉时期的东胡,有学者以为:“乌桓之名起于西汉,而鲜卑之名,东汉始出,因乌桓介于汉与鲜卑之间,汉人先知乌桓而后知鲜卑也”(注: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126。)。基于这种同源关系, 鲜卑与乌桓有着大体相同的语言习俗。乌桓有送亡灵西归赤山的习俗,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注: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80。)赤山所指尽管不太清楚,但从地处辽东西北数千里的距离分析,它应该指大兴安岭。匈奴击溃东胡后,大兴安岭山脉就成了匈奴与鲜卑乌桓的分界岭。乌桓在鲜卑之南,赤山在乌桓西北,对世统幽都之北的拓跋先人(即两汉鲜卑)来说,赤山恰在其西。因同俗关系,鲜卑的葬俗也应与乌桓大同小异。由于鲜卑在乌桓之南,乌桓送亡灵西北归赤山,拓跋先人送亡灵归赤山,则是西归。神魂西归,迎神灵自然应该采取西向方位。这或许就是拓跋鲜卑的西向祭天与祭亡灵传统的最早出处(注: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487。)。
拓跋部落的传统祭天并不是完全的祀无定时,它有偏重夏季祭天的迹象。北魏统治者西郊祭天之所以选取夏四月祭天,与拓跋部落偏重夏季祭天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前述天兴元年前的三次祭天,具体时间是夏四月两次,正月一次。另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魏之旧俗,孟夏祀天及东庙,季夏帅众却霜於阴山,孟秋祀天於西郊。”(注: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84。)拓跋传统祭天时间又有这孟夏与孟秋之说。综上所述,拓跋传统祭天时间有六,即元月、四月(孟夏)、七月(孟秋)、八月、十月、十一月,分跨四季。这足以反映出在西郊制度确立前拓跋鲜卑对祭天时间的选择还有较大的随意性或不确定性。不过,拓跋祭天时间选择并非完全的随意,与两汉乌桓鲜卑的祀无定时不同。造成这种差别,既有拓跋鲜卑自身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更不能排除匈奴祭祀文化对拓跋鲜卑祭祀文化方面所带来的直接、深刻的影响,因为拓跋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对匈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拓跋传统的祭天时间与匈奴的祭天时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拓跋传统祭天的三个时间,即元月、孟夏四月与孟秋七月,分别跨春、夏、秋三季,三季之祭中,夏祭与秋祭为“魏之旧俗”,应是常祀。而夏、秋之祭相比较而言,又以夏祭最为频繁,天兴元年前所举行的三次祭天中有两次都在孟夏。上述情形与匈奴祭天时间很相似。匈奴祭天时间也有三个,即元月、五月与八月或九月(注: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52。),也分别跨春夏秋三季,与拓跋的祭天时间相仿佛,只是在具体月份上稍有出入,匈奴的夏、秋之祭比拓跋的同季之祭晚了一两个月。对这一细微差别的合理解释或许是,因拓跋鲜卑的居地纬度比匈奴的居地纬度要低,故其季节的到来也相应要早半月或一月不等。匈奴的三季祭天,春祭为小会,夏、秋之祭为大会,表现出对夏秋祭天的重视,与拓跋传统祭天以夏秋之祭为常祀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匈奴的夏、秋之祭中,夏祭为遍秩天地众神的比较正式且隆重的祭祀,而秋祭则侧重于校点牲口,如此重视夏祭的作法与拓跋传统祭天偏重于夏祭的情形不谋而合。
拓跋传统祭天与匈奴祭天在时间上的种种相似或相同,当然不能从偶合上解释,而应从其生存环境的大体相似与文化上的承传上去理解。陶克涛从自然地理与气候角度解释匈奴选择夏秋之祭(注:陶克涛.毡乡春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15。),这也同样适用于拓跋祭天时间的解释;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文化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拓跋鲜卑本来是鲜卑与匈奴混血后而形成的部落民族,作为匈奴之后裔,其祭祀上自然会继承匈奴祭祀文化的合理内容。匈奴有所选择的祭祀时间很显然要比两汉鲜卑的祀无定时要合理一些。在祭祀时间的选择上,拓跋弃两汉鲜卑的祀无定时而取匈奴有选择的祀有定时,应看作是一种进步。由两汉鲜卑的祀无定时到魏晋时拓跋有选择的祀有定时,再到北魏平城时代皇权制确立后的单一定时祭,其发展的顺序是一目了然的,表现了拓跋祭天从无序到相对有序、再到完全规范的发展规律。
(二)西郊祭天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拓跋传统祭天的“西向设祭”习俗与对孟夏祭天的偏爱已孕育了北魏平城时代西郊祭天制度的胚芽。由“西向”向西郊、由夏春秋之祭向独尊孟夏祭天的转变发生在太祖天兴元年,助成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太祖拓跋与汉族文臣董谧、邓渊、崔宏等人。《魏书·礼志四》载:“太祖天兴元年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宴、郊庙、社稷之仪。”(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17。)司马光《资治通鉴》载,晋安帝隆安二年,“拓跋命尚书吏部郎邓渊立官制,协音律,仪曹郎清河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而裁之,以为永式。”(注: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83。)这些史料告诉我们,作为郊庙制度的重要内容,西郊祭天制度是由清河董谧亲手草拟、邓渊与崔宏共同审定并征得太祖首肯后而正式出台的。太祖天兴元年是北魏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一年。拓跋在攻克晋阳、中山后,于天兴元年初又攻克了邺城,尽有了山西、河北之地。代国不再是龟缩于幽并塞外、人见人欺的小政权,它的军事实力及势力范围已仅次于南朝东晋。为了适应这一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拓跋于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并“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畿内的规划、都城的兴建与政治中心的形成,都必然要求北魏统治者对只适合于游牧部落社会的拓跋传统祭天及祭祖习俗进行变革。这正是北魏有固定地址与固定时间的西郊祭天制度在太祖天兴年间得以确立的时代背景。
天兴元年确立了西郊祭天的哪些具体制度呢,《魏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仅有两条:
(天兴元年)夏四月壬戌,……帝祠天于西郊,徽帜有加焉。(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
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耀,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4.)记载虽然简单,西郊祭天的初略制度却隐约可见。首先是祭天场所固定于西郊。祭天场所的固定化标志着拓跋原始祭天祀无定所历史的结束,和一种新的配合国家建制的郊祀制度的初步确立。西郊的位置按萧子显《南齐书》记载是在城西,“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边别立父子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注: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85。)祠天坛离平城多远,史书没有具体载明,不过,参考引文前后内容及魏晋郊天场所的一般距离,可推测它大概在平城西七里之地,与西北白登山父祖庙相对应。西郊建设比较简单,除却坛兆外,其它附属建筑物都还未修建。其次是确立了帝王亲祀西郊的制度。《资治通鉴》叙太祖天兴元年改革拓跋传统祭天时间云:“惟孟夏祀天亲行,其余多有司摄事。”(注: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484。)帝王亲郊制度的确立,表明北魏统治者已把传统的祭天习俗改造成为服务于突出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西郊祭天制度,而妃后祭天事情在其后再也没发生。其三是祭天时间的确定。夏四月的选定上引文已经提及,后文还将进一步论述。至于具体哪天,《魏书》及《通鉴》都未能指明,《南齐书》作者以为是四月四日,如此具体的日期可能是天赐二年进一步完善时确立的。最后是初步确立了祭天的仪式。前引《魏书》卷二,叙天兴元年祭天,只云“徽帜有加焉”,对仪式过于简单的叙述可能与建国初祭天仪式本不完善有关。天兴二年太祖进一步确立了包括郊天仪式在内的祭祀仪式制度,《魏书·礼志四》云:“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一曰大驾,设五辂,建大常,属车八十一乘……上下作鼓吹。军戎、大祠则设之……惟四月郊天,帝常亲行,乐加钟悬,以为迎送节焉。”(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813。)西郊祭天作为拓跋统治者最重要的祭天,自然属“大祠”范围,其仪式则相应享受“大驾”待遇。根据这两则史料可以推知,天兴年间已基本确立了备法驾、张卤簿、扬旗幡、奏器乐的西郊祭天仪式。
天兴元年为适应帝制需要而确立的西郊祭天制度,还远不能说完善,如祭天场所的建筑过于简陋,祭坛摆设未作规定,祭祀的步骤程序与时间间隔也未作要求。这一系列的完善工作完成于几年后的天赐二年,《魏书·礼志一》对此叙述得很详实:
天赐二年夏四月,祀天于西郊,为方坛一,置木主七於上。东为二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其方色为名。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内朝臣皆位於帝北,外朝臣及大人咸位於青门之外,后率六宫黑门入,列於青门内近北,并西面。令掌牲,陈於坛前。女巫执鼓,立於陛之东,西面。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拜。拜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天神主,拜,如此者七。自是之后,岁一祭(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6。)。从引文分析可以看出,天赐二年西郊制度的完善工作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其一,对西郊场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从引文关于门、垣、坛、陛的记载可知,西郊场所的主体建筑(祭坛)与附属建筑(亭舍)都已基本齐全。四门着色与取名各依五方所对应的颜色。祭天之坛筑成方形,与周礼关于祭天之坛应取象天之形的规定似乎不合,这大概是受了西晋礼学家王肃主张的合方丘于南北郊的郊祀思想的影响(注: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423。);而五方之坛取相于五方之形(注: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64。), 已是汉族传统礼制思想的基本要求。
其二,完善了西郊场所内的摆设。由“西向”拜祭的引文可知,天神主被置于坛之西边,面朝东而立,接受祭祀者西向的朝拜。主神既然存在,则定然少不了陪祭之神。太祖初刘后私祭天神时,“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亦以八月、十月。神尊者以马,次以牛,小以羊,皆女巫行事。”(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5。)从祭品的规格高低分析,多达四五十尊天神间已有一定的至今还不太清楚的等级关系。又据前述《南齐书》引文,西郊之坛置有四十九木人,这四十九木人应是陪祀的众天神,其数目与刘后所祀的天神数目暗暗相合,四十九木人天神也应有主陪神的区别。由此推断,天赐二年的西郊祭天也应存在众多天神陪祀主神的情况。北魏西郊祭祀的主陪神系统与汉族郊祀的主陪神系统存在着较大差别,汉族郊天以昊天上帝或感生帝为主神,以五方帝(或五精帝)、五人帝、众天文神及自然神灵为陪神;而西郊所祀之神多是不明身份及地位的胡神。从配祀对象看,汉族郊天以始祖或太祖配享,而北魏西郊祭天以七木主配享。七木主应该是七庙神主,显祖曾对七木主“易世则更兆”的“西郊旧事”(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40。)进行过改革,七木主易世而变更的特点与宗庙神主易世迭毁的特点相同。
其三,对参与祭祀的角色、祭祀步骤的详细规定。如主祭者为女巫,与汉族礼官主祭不同;助祭者必须是拓跋帝室“十姓”的子弟成员,与汉族政权以太尉“郊祀掌亚献”(注: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8。)不同;与祭者也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不同角色的处位进退、礼拜的先后顺序及次数、杀牲上祭品及释奠的安排,都规定的十分具体。天兴元年对祭品只作“用白”要求,而天赐二年则对祭品从颜色、种类与数量上作了详细规定。
其四,进一步完善祭祀时间。仅有天兴年间夏四月的规定,还不能保证西郊祭天的正常进行。西郊之祭是每年或每几年举行一次,还是一年之内的夏四月反复举行,过于频繁或稀少都有可能使西郊之祭失去意义或陷入废置状况。天赐二年“岁一祭”制度的规定从而显得极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汉族南郊上帝大多采取两年一祭(注:(日)金子修一.关于魏晋到隋唐的郊祀、宗庙制度[A].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C].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51~352。),唐代祭天采取与北魏西郊同样的岁一祭,我们无法肯定唐朝与北魏在祭天上是否存在着继承关系。不过,从天兴元年帝王亲郊的规定,到天赐二年“岁一祭”制度的确立,北魏统治者对具有其部落民族特点的西郊祭天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三)西郊祭天制度的特点
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与拓跋部落传统的祭天习俗是有着本质的区别。拓跋传统的祭天习俗主要反映拓跋部落与神秘自然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部落民众对自然力的依赖、恐惧与敬畏。而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反映的是拓跋统治者与天神的关系,表现为拓跋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天神崇拜意识来达到强化君权神授、不可侵犯的政治目的,是神道设教的产物。北魏平城时代的西郊祭天制度与汉族政权传统的南郊或圆丘祭天礼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北魏西郊祭天制度不同于汉晋时期汉族的南郊或圆丘祭天礼。与北魏西郊祭天制度相比较,汉族祭天礼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形式也要完善得多。汉族的郊天礼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为依据,并有着上千年的祭天实践作指导,它与其他礼仪制度相结合构成了统治阶级进行政治与精神统治的有效工具。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故而它不得不借用周礼;作为新的郊天制度,它的历史尤为短暂;由于没有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制度相配合,西郊祭天也很难发挥像汉族南郊祭天的政治与精神统治功能,也正因为此,平城时代的北魏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双轨祭天制,用南郊祭天作为西郊祭天的补充,以弥补西郊祭天发挥政治精神统治的不足。由此看来,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只能算作界于拓跋部落原始祭天习俗与汉族传统祭天礼之间的过渡祭天形式。
西郊祭天制度主要是由拓跋原始祭天习俗与汉族传统郊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以上对西郊祭天制度萌芽、确立与完善的具体勾勒可以看出,北魏的西郊制度内保留了大量的拓跋传统祭天的内容,如祭祀胡天神、女巫主祭、西向朝拜、“蹋坛”“绕天”(注: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91。)、七木主配祀、夏四月祭祀等。这些“夷礼”内容构筑了北魏西郊制度的基础与特色,抽去这些内容就不可能有北魏的西郊祭天制度。然而,仅有拓跋传统祭天习俗的“夷礼”内容,也不可能产生西郊祭天制度。由祭天习俗向西郊祭天制度的转变,须从汉族郊祀文化中引进形式、补充内容,须用汉族的郊天礼仪来对拓跋传统祭天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包装与改造。同样是巫觋主祭,于部落社会“专管祭天的事”(注: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2。)的巫觋一般是以通神者的身份进入祭祀角色,并呈现出神灵附体或灵魂出窍般的癫狂痴迷的精神状态。而北魏西郊祭天中的女巫则是以礼官的身份来主持祭天,其祭祀方式与汉族的司仪大同小异。同样是西向朝拜,传统祭天决不会出现汉族式的三叩九拜,而西郊祭天中的朝拜形式则已基本汉化。
北魏西郊祭天制度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西郊场所与夏四月时间。西郊场所的确定与时间的选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拓跋传统祭天习俗与汉族郊祀文化相结合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西郊祭天制度的形成与拓跋西向祭祀的习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拓跋西向祭祀的习俗实际上是受其先人神灵居于西方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神灵既然居于西方,故在引入汉族郊祀形式时,自然会选择西郊,而不可能选择东郊、南郊、北郊或中郊。如此则促成了由西向的向置向西郊的方位场所的转变。此外,汉族的方位五郊中,建立在西方属金、主杀伐五行观念基础上的西郊之礼有“迎秋”、“赏军师武人”(注:陈皓注.礼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2。)的规定,它与拓跋鲜卑传统祭天比较明显的征战目的很相合,似乎也不能排除汉族的郊祀观念对北魏西郊祭天的影响。西郊制度中孟夏祭天的选择,除了有拓跋先人偏爱夏祭这一原因外,也能从汉族郊祀文化中找到理论根据。《魏书·礼志一》云:“郊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注: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34。)。关于汉族夏四月郊祀,《礼记·月令》规定说:“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注:陈皓注.礼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2。)此处的南郊迎夏与南郊祭上帝并不相同。汉晋以来南郊祭祀上帝有元月与孟夏两个时间,以元月较为普遍,孟夏之祭只在西汉前期举行过(注: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13~1214。)。《通典》中有关于元月祭天于南郊的规定,“夏正之月,祭感生帝于南郊”(注: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61。),“若以祖之所自出,即禘祭灵威仰于南郊”(注: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164。)。灵威仰是立春东郊郊迎之神,祀东方神应在元月,故南郊祀上帝一般都取此月。但是,既然在南郊举行祭天,按五行五方四季郊祀的要求,南郊之祭理应在孟夏,这或许是西汉初以孟夏祭天于南郊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周礼对郊祀规定的不很明确导致了后世诸儒在祭祀时间上的莫衷一是,北魏确立以拓跋鲜卑较经常使用的夏四月为祭天之月,也就能从周礼中找到理论依据及历史上找到祭祀先例。北魏太祖在制度建设上动辄稽古、“用周典”即是明证。
如果说,拓跋鲜卑的传统祭天习俗适应了拓跋部落比较简单的社会结构现实,那么,随着拓跋部落政权向多民族统一帝国的转化,反映狭隘部落意识形态与适应比较简单社会结构现实的传统祭天很显然适应不了北魏据有中原后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的现实。作为一代雄主的拓跋,在天兴、天赐年间,大胆地起用汉族士人,借鉴汉族郊祀制度的形式与内容,对传统祭天习俗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改革。在这一改革基础上产生的西郊制度,基本上适应了以拓跋鲜卑占统治地位、农牧文化交织、多民族共存的平城时代的社会现实。然而,随着北魏政治中心的不断南移,随着游牧民族经济生活向定居农耕经济生活的逐步转型,随着拓跋统治集团汉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保留了较明显“夷礼”特色的西郊祭天又面临着重新适应时代变革的巨大危机。西郊祭天显然不能适应这种要求全面汉化的现实,为顺应时代要求,孝文帝逐步废除西郊祭天,取消双轨祭天制。西郊祭天制度在完成了对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由游牧部落社会向北魏统一封建社会的转型阶段——的社会适应后,也就退出了郊祀的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