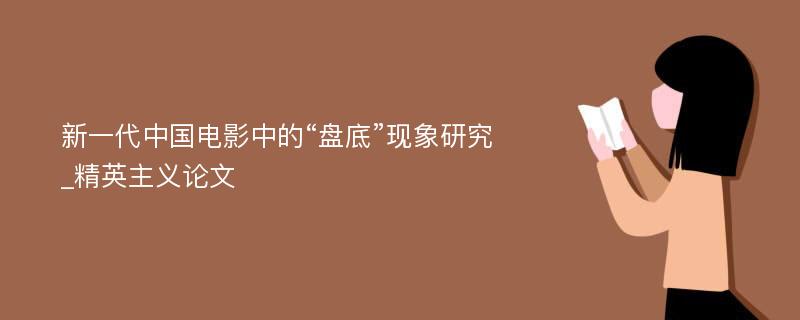
中国新生代电影的“泛底层”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中国论文,底层论文,现象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09)04-0079-05
一
底层之所以能和新生代的“先锋电影”联系起来,其内在的逻辑可能如下:“底层”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大众阶层,在作为审美对象时,却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部分;而“先锋电影”作为一种没有完备支持网络的电影群落,①具有突破中国当代电影传统拘囿的“创新冲动”和与中国当代现实密切相关的“及物焦虑”。这让中国新生代先锋电影力图找到一种在道义上靠近大众、同时又在审美上破除主流的遮蔽、为大众带来新奇和陌生化效果的表达。
稍微梳理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电影的历史脉络,就可以发现,所谓“先锋的底层转向”并非只停留在逻辑上。从章明的《巫山云雨》开始,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小武》《站台》《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王超的《安阳婴儿》《日日夜夜》《江城夏日》、王小帅的《扁担·姑娘》《二弟》、李扬的《盲井》《盲山》、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王全安的《月蚀》《图雅的婚事》、朱文的《海鲜》《云的南方》、盛志民《心·心》、王光利的《横竖横》、刘浩的《陈默和美婷》《好大一对羊》、方亮刚的《上学路上》等,乃至为数更多的独立电影都打上了明显的“底层”烙印。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题材选择的问题,也更是叙事策略的问题——“底层”题材的特殊性使得先锋电影在电影叙事方面不再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实验性、前卫的叙事方式和晦涩的影像,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平稳的叙事状态,甚至平稳到以“纪录”的方式刻意还原现实。实景、非职业或半职业演员、第三人称客观视点、长镜头,这些半个世纪前在巴赞写实主义电影主张里的“教条”变成了中国电影的新浪潮,再联系到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的“新纪录片运动”和DV出现后电影技术门槛的降低,“底层”题材从纪录片体裁向虚构电影体裁的辐射、实现手段上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以及“底层”和独立影像的亲缘关系,就很好理解了。
不仅如此,面对底层,中国新生代先锋电影的叙事视角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位移。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以一种“正/邪”、“善/恶”对立的思维方式评判人事和观照现实,这决定了传统电影的一种基本叙事模式。底层群众作为弱势群体,一般来说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态,对他们,人们在情感和道德上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而先锋电影的视点是下移的,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情感时是平视而非俯视的,不是单纯同情底层,仅把底层作为一个阶层来看待,而更是把他们作为普通的人群来看待,其关注点更多的是放在普遍人性的展现上;底层中善良和罪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界线不再那么明显,更生活化也更真实可信。
底层题材和底层视角的确立,使中国新生代先锋电影的“底层叙事策略”凸现无疑,这集中体现为“意识形态驱动”和“审美抽离”[1]两种力量的合力。
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文学领域内出现的“底层叙事”潮流类似,意识形态的驱动对电影同样有效:在前者那里,叙事作品不论是观念的抽象表达、现实的自发呈现还是以观念读解现实,对底层大众的道义靠近和价值认同都十分明确。作品中,以农民、进城务工者、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城市失业人群以及城市边缘群体往往承受多重苦难的叠加,伤痕累累,却不失尊严。相较于文学,新生代电影往往更不会直接针对底层状态背后的体制,或者说“意识形态驱动”表现得要弱一些。一个明显的例子,在电影里,底层人物的冲突往往是底层内部自发的,而非对底层外部的自觉抗争,他们也有抗争,这种抗争往往演化成了一种“寻找”的状态。《盲井》中的两个农民寻找出路,少年寻找父亲;《盲山》中女人寻找逃跑的路;《小武》中小武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寻找“猎物”,同时也在寻找友情、爱情和亲情;《苏州河》马达寻找牡丹;《十七岁的单车》打工少年寻找丢失的自行车;《卡拉是条狗》中老二寻找解救卡拉的办法;《图雅的婚事》中图雅寻找能接受前夫的丈夫等等。有希望、有所期待才执著地“寻找”,“寻找”成了底层人物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支柱和理由。
在文学层面的“底层叙事”中,一个经常遭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底层叙事作品艺术性低下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既有意识形态驱动对艺术性的抵消作用,又有文学底层叙事为了贴近现实而故意采取的“审美抽离”的策略问题,诸如传统的现实主义文风、情节推动的叙述模式等极大地冲淡了“先锋派”小说重视叙述策略、“新生代”小说寻找新的现实切入角度的形式创新色彩。电影的情况是:这种“审美抽离”把底层叙事电影象征性地拉下精英舞台,也冲破了所谓的制作技术指标的限制,艺术上平实的原生态风格和技术上的拙朴不仅成为理所应当的而且还是可以用来自我确认和自我标榜的东西。很明显的例子,贾樟柯之后的“长镜头”和“半DV制作流程”已经成为底层叙事电影“以退为进”的新教条。
反过来说,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底层叙事策略”其内在的进攻态势和妥协色彩,其合力是否可能使得“底层”脱离“先锋”的领域,并在何种向度上呈现了这种趋势,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尝试使用“泛底层”这个概念来涉及这样的问题。
二
如果说,社会学层面上“底层的泛化”——底层数量上的增加以及“新底层”的出现导致底层结构的变化,是在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下,社会阶层从“金字塔”结构经由“苹果核”结构向“纺锤体”结构变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文学和电影中的“底层的泛化”就有可能意味着底层的沦陷——价值观和美学观受到底层之外他者的倾轧或诱惑,加之“底层”的内在暧昧,使之失去了整体性和自足性。
说起底层沦陷和底层泛化,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两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电影:其一,电影《盲井》中底层内部因“抽刀向更弱者”而导致的底层分化。李杨想极力掩饰的精英态度、极力张显的平视的底层视角,指向的却是底层对于底层的戕残。底层作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整体不再具有说服力了,底层因内在角力而带来的生存的残酷性和荒诞性成了更重要的主题;其二,电影《立春》中,在兼有第五代精英启蒙思维习惯和第六代底层转向潮流的顾长卫那里,始终存在着两个悖论:(一)底层的外在符号上的悖论——女主人公形容丑陋但歌声动人,艺术青年长发、高腰皮夹克和蓝牛仔裤的朋克打扮,而他们的实际身份却是产业工人;(二)对待底层态度上的悖论——比如在“广场的群众文化演出”那场戏,“歌剧和芭蕾舞的艺术底层”,在面对非艺术的懵懂底层时的尴尬,前者被后者嘲笑的时候,后者却被导演以及“我们”嘲笑着,但是,这种嘲笑是应该的或者合法的吗?没有艺术标签和精英幻想的底层就应该被嘲笑和利用吗?“底层”(小地方和小地方的人)就应该成为个体追求梦想(去北京去巴黎)的反参照系或牺牲品吗?这是怎样的一种“底层视角”呢?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底层生活图景和底层人物命运只是被用来作为精英意识自我感动、自我标榜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底层,在电影中实际上已经被泛化和颠覆了。
从学理上说,底层的泛化与先锋性的丧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在“先锋的底层转向”这个前提之下,两者似乎又是同向运动的,最起码,从外部看是这样的。
新生代电影人通过展现底层构建民间话语空间,进而获得社会乃至主流的认可,影像上其“底层中国”的形象已经十分明确,就像当年第五代的“民族寓言”一般。不过,从一开始“他们所描述的底层世界,也针对与底层世界相对的那个世界,在这种开放性的民间立场中,被割裂的、彼此疏离的世界的各个部分重新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可能的民主的公共话语空间。民间立场保证了第六代电影底层影像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开放性,它未必真的能够揭示底层世界的真实状况,但民间立场的存在让这种底层书写具有了获得某种历史真实性的可能。”[2]
要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当第六代电影已经形成巨大的示范效应,甚至已经开始接受更年轻的电影人在作品中“致敬”的时候,这种“开放性”就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意识形态主流和商业机制主流把更多的带有诱惑性的因素(审片通过可以带来公映、媒体渲染可以促进票房)导入先锋电影,使之做出更多的妥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红》《左右》等作品中看出来。不仅如此,在作为先锋电影重要来源地的独立电影领域,小制作、独立意识、非国家意识形态,这些原本似乎天然地与独立制片联系在一起的因素,因第六代成功而具有的“示范效应”,变得越来越标签化、符号化,独立意识变成了这一小部分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镜头下的“底层”,以及如何用镜头展现“底层”都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而且是用表面上“穷尽所有底层生活样态”的方式的同质化。也就是说,“底层”被人为地扩大了,那些普通人的生活、个体的独特际遇甚至是一些奇观性的、负面新闻性的故事,统统可以被用独立的意识形态和底层叙事策略包装后打上“底层”的标记,在地下流传。
对于先锋电影来说,抵抗主流召唤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由于主流本身并不是单一的,最起码可以有意识形态主流、商业机制主流以及他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第三方“媒体权力”这样的区分,第六代的成功之处或者说尴尬之处就在于:以靠近某种主流因素去规避另一种对他们影响更大的主流因素的影响。比如,你反叛和挑战在原先的意识形态权力作用下形成的某种父辈的价值观,就可能故意摆出一副沉溺于物质化生活的样子;你感受到社会主旋律电影审美同质化的弊端,就只有从某些边缘化的题材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虽然你可能并不心属后者。在这样的尴尬中,各种主流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先锋电影中,“底层”本身就埋下了泛化的种子。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悖论来说,“国际电影节情结”和获得外国电影基金的青睐,可能是比前述的国内主流因素渗透更重要的促成因素。文化和电影链条中的资源分配和权力传递,使得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在面对西方主流社会时往往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它们和它们来自的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它们不仅是那个地方有独立意识符合西方审美标准的佼佼者,也是那个地方如何不好的讲述者。它们可以在国外获奖,取得合法性,但是这种合法性是牢牢扎根在符合“西方阅读期待”基础上的。它们“除了奇观展示之外,影片似乎还让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的‘愚昧’,正如中国的精英看到了中国底层的‘愚昧’一样。西方白种男人无疑处于链条的顶端。这些西方男人一边享受着上海宝贝们‘蝴蝶的尖叫’,一边在电影中欣赏着中国男性的‘愚昧’,而中国的导演与知识分子却也将‘愚昧’呈现给他们,而不反思整个‘文明的链条’的合理性,这不能不说是‘启蒙’视角所带来的遮蔽。”[3]
这首先是个事实,我们当然可以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批判“底层电影”所具有的“东方主义”内涵,不过,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国际化策略或者国际化想象,为什么会通过“底层”实现?这也许有所谓的底层世界和阶级差别的普世原则引起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共鸣,但笔者以为,其中起更大作用的恐怕还是西方对于中国现实的偏见和误解。很明显,底层苦难与愚昧中国、中国现实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多层面、多向度的,但西方的阅读期待往往又是直接的、一元的。所以,通过西方电影节,“底层”作为当代中国的影像寓言而存在:其一方面有被中国先锋电影人泛化的倾向,杂糅了一些新的主流元素,另一方面,却又把更多的中国社会问题归结到底层问题中,从而在迎合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更深的偏见和误解,“底层的泛化”进而具有了某种外部的宣泄口。
三
与从外部语境考察的“底层的泛化”相对的,是中国当代先锋电影内在的底层悖论。所谓“泛底层”,是指就意识形态、美学元素和影像风格而言,“底层”都逐渐变成一个没有统一内涵的指称,甚至变成了一种“公共资源”。由于其最早被关注,是前述的“先锋的底层转向”,故而以先锋电影为坐标出发,对其内在悖论进行讨论,一方面可以对“先锋的底层转向之后”的状况予以关注,也能从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对中国当代电影如何使用“底层”这个元素或者符号的情况有所涉及,并作为先锋电影的参照。笔者以为,“泛底层”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底层悖论。
其一,底层现实与精英意识之间的悖论。
如前所述,先锋的底层视角如何做到真正的平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随着先锋电影逐步获得主流认可的程度越高,其内在的这一悖论就会越明显,先前被策略性压抑的精英意识(精英潜意识)也会流露得越明显。面对底层现实,先锋电影人的启蒙焦虑虽不会像当年的陈凯歌、张艺谋那样直白,但也一直没有消失过,即便如贾樟柯那样对“故乡”的底层生活如此熟悉,但那也依旧是一个“返乡人”选择性记忆的熟悉而已,更何况大多数先锋电影人对底层生活是有隔膜的。在底层现实在电影中被完全忽视,而先锋电影策略性地寻找底层的时候,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它未必真的能够揭示底层世界的真实状况,但这种底层书写具有了获得某种历史真实性的可能;而当底层成为流行和教条时,底层现实就又一次被精英意识修正了。几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说《三峡好人》与《巫山云雨》的互文性显露的是“底层电影”自我发展脉络上从对普通的个体生命的寓言性表达到底层生命的观念性展示的话,那么《三峡好人》与《东》的互文性则体现了精英艺术家自我底层化后在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王超《安阳婴儿》中底层现实的“超前显现”,从一定程度上把导演对底层生活的陌生掩盖起来,而《江城夏日》里底层现实的“滞后编排”,则把这一点暴露无遗。《二十四城记》依托个体生命史的叙事策略已经带有向第五代经典模式回归的倾向。
其二,艺术青年自我边缘化的小资趣味与无产阶级新左热情之间的悖论。
“底层叙事”的流行,不管其在文学还是在电影中,毫无疑问和中国当代社会在思想史层面以新左观念反思自由主义思潮有关。具体到电影,从创作者角度上说,新左思想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精英知识界有一个长期处于边缘,又从边缘逐步靠近中心的过程,这和自我边缘化的先锋艺术和“被边缘化”的底层之间有着某种外在相似性,特别是在主体情绪上。先锋艺术家们不论对“新左”思想还是政策主张理解多少,在态度上往往有着某种亲近感。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真实焦虑和虚假热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一些影片,特别是在审美习惯上更容易“个人化表达”的女性导演的作品,当李玉的《苹果》、程裕苏的《目的地,上海》、尹丽川的《公园》因为各自的原因策略性地涉及底层的时候,就没有同样出自她们之手的《今年夏天》(女性同性恋)、《我们害怕》(酒吧、迷幻药和艾滋病)、《牛郎织女》(游走于异性同性间的暧昧情感)的非底层个体的边缘化生活来得舒服自然,而后者相比较于前者来说,恰恰是“小资”的。
从欣赏角度看,一方面有艺术兴趣的城市白领成为“独立电影发烧友”的主体,独立电影的底层题材和表达策略为什么能让这样一群人感兴趣,诸如应亮《背鸭子的男孩》《另一半》、高文东的《美食村》一类的作品能够受到欢迎,其中的原由恐怕不是情感共鸣,而是态度共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艺术兴趣的青年白领成为“底层”电影的爱好者,实际上同时又是左派最明显又最不可靠的同盟军。“新左的小资化”恐怕是这个层面“底层泛化”的另一种表述。
其三,底层的个体生命经验和类型化表达之间的悖论。
底层鲜活的个体生命经验的缺失或者说不充沛,使得有的时候,“底层”电影要借助类型化的艺术经验。底层喜剧、底层公路片、底层伦理片是最近几年“先锋的底层转向之后”的新生事物。《疯狂的石头》《鸡犬不宁》《疯狂的彩票》《好大一对羊》《我叫刘跃进》一类的电影,或热或冷的喜剧因素和“底层”之间虽非“战略同盟”,但最起码是“互惠合作”的。《叶落归根》(张扬)、《红色康拜因》(蔡尚君)典型的公路片模式穿起了众多底层生活的典型场景。《青红》《左右》(王小帅)、《我们俩》(马俪文)、《苹果》(李玉)则把特殊的伦理困境放置到底层生活中,似乎只有底层才有这样的困境。
很明显,类型电影天生带有商业和主流的意味,类型化的表达在整合共同经验、符合审美习惯和阅读期待上很有作用,但也会大大遮蔽底层个体生命经验的传达。我们注意到,虽有底层因素,但这其中的很多作品已经不是上面所说的底层视角和底层叙事的问题了,更不是先锋电影的问题了。
其四,底层的残酷(现实性)与娱乐(商业性)之间的悖论。
在前三者的基础上,这一点很好理解,在此不再赘述,笔者只想举几个极端的例子:《长江七号》的周星驰式的底层民工、《疯狂的石头》中的欢乐英雄、《苹果》中偶像化和欲望化的洗头妹和蜘蛛人,他们已经很难让我们想起诸如进城务工者劳动保护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工人失业与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娱乐行业中女性务工者性安全的问题了;这些在电影中并不是没有、甚至是刻意涉及了,但正是由于娱乐性极大地淡化直致掩盖了现实的残酷性。当然,就像前面说的,这已经不是在先锋电影范围内谈论“底层”了,但谁又能说,当“底层泛化”到一个极端的程度,先锋和底层还能联系在一起呢?
“底层的泛化”从消极的一面说,是中国当代电影先锋性减弱乃至丧失的表征。但不管怎样,从积极的一面说,“底层”电影却也修正了中国电影面向精英、面向海外、面向电影节的惯性思维,“底层”电影的大量出现,让“底层”不仅作为表现对象出现在银幕上,也有可能作为观众通过电影获得精神文化的满足。最后,笔者想起了一则报道:电影《红色康拜因》讲述了一对“麦客”父子开着康拜因——“康拜因”是英文收割机的中文音译,在茫茫西北大地奔徙千里、一路收获的故事。据说,它打动了受创作者邀请到场观看的20位民工代表,他们纷纷对影片的主创表示感谢。如果这样的情景是真实的,而且还有更多,那么中国当代先锋电影的“底层”悖论解决起来也就不那么难了。
收稿日期:2008-06-16
注释:
①参见程波《滞后的先锋性——一个关于中国1990年代以来先锋电影的文艺学解释》,《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