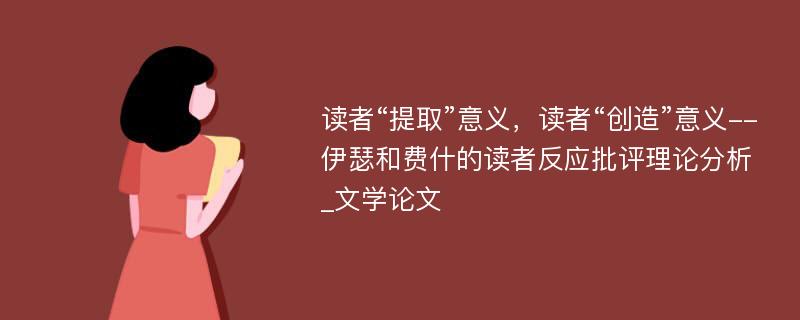
读者“提取”意义,读者“创造”意义——伊瑟与费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者论文,意义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将文学批评的中心从考察作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方面转移到文本自身上面,他们将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作品的结构与形式上,认为作品的结构和形式决定作品的意义,全然无视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文学作品的影响。本世纪六十年代,欧美兴起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则将文学批评的焦点转移到读者身上,强调读者在决定文学作品意义时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一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从以德国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中汲取了理论营养。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已经被十九世纪的科学确立了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向我们表明:科学中的“事实”的存在依赖于认识主体观察事物时所采用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认识主体处于主动的地位,一个具体的事物在不同的角度来看显现出不同的形象。在这种思想环境下产生的现象学哲学观点强调人(即认识主体)在决定客观事物意义时的中心作用。根据这一观点,客观事物的意义是客体在认识主体的意识中所显现的形象。它虽然强调认识主体与客体(被认识的事物)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但实际上是“人的主观意志是认识事物的中心,是决定客观事物意义的中心”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翻版。胡塞尔认为,“虽然我们无从确信事物的独立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清楚事物是如何直接显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无论我们所体验到的实际事物是幻觉与否。”〔1〕
现象学文学批评试图将现象学的工作方法用于文学批评,正如胡塞尔在考察事物时将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客观事物用“括号括起来”而不予考虑一样,产生作品的历史环境、作者本人以及作品产生时的条件和读者的状况都被束之高阁,现象学文学批评所关注的则是对于文本的一种完全是“内在”的解读,这种解读不被任何其他外部事物所左右。在现象学批评家们看来,文本的地位沦落为仅仅是作者意识的承载体,它的所有语言学的性质被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有机整体的粘合剂就是作者的意识;要了解作者的意识,不可依赖已知的关于作者的生平或历史知识,而是要依赖于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意识。
胡塞尔的学生,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则反对胡塞尔的这种“超验主义”的现象学说,他认为人类存在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被赋予性”(givenness), 人类的主观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物而且同时依附于客观世界,其标志就是人类生存在其中。海德格尔的哲学观点是一种典型的存在主义观点,他认为人类的这种存在首先是始终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的,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类主体正是因为我们依附于他人和这个客观世界,这种依附关系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附属于我们的生命。人类的认识活动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整个人类存在体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人类的存在决定人类的认识活动,由于存在具有着不可超越的历史性,所以人类的认识也就带上了深刻的历史特性。因此文学作品的阐释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完全主动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它必定受到产生文本的历史环境以及读者本人的状况的制约。德国哲学家汉斯—伽德默在1975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将海德格尔的阐释现象学(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方法应用于文学理论的,伽德默认为文学作品并不是象一只包扎得整整齐齐的包裹那样包含着完整的意义,文学作品的意义的产生取决于阐释主体所处的历史环境。不难看出,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海德格尔和伽德默,他们都没有将批评的责任完人推卸到读者身上,因为他们都没有完全放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只不过是更加强调了读者在整个阐释过程中的重要性罢了。他们的思想方法可以说为六、七十年代风靡西方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奠定了丰厚的哲学基础。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另一个支点是建立在不同的读者对于同一文本的反应不同这样一个事实之上的,但是读者反应批评的目的并不在于弄清不同的阐释中哪一种阐释是“正确”的,因为文学作品存在的意义在于不同的读者对它有不同的阐释,不朽的作品正是在读者的阐释过程中获得生命而流芳百世的。读者每读到一种文本时他所立刻获得的并不是文本提供的某种“定论”,而是一种责任,一种发现或提供“定论”的责任。读者在确定本文意义的过程中经过分析、推理、想象等一系列复杂的意识活动而得到美的娱乐,这个过程正是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所在。试想,如果一部作品的不同的读者对它的反应——即阐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不同的读者之所以会对于同一文本有不同的阐释,
是因为读者的“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2〕各不相同, 所谓文学能力是指“一整套的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规程”。〔3〕如同读者的语言能力要包括对语音、句法、语义等诸方面的谙熟一样,读者的文学能力也要求读者掌握一套阅读的“语法规则”。这套阅读的“语法规则”要远比单纯的语言能力的语法规则包罗万象得多,它首先将语言能力包括在内,除此以外,它还包括读者所既有的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经验等因素。然而,读者的文学能力的不同主要通过阅读时产生的歧义表现出来。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姑且将由于读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歧义归属于由于语音、句法、语义等语言学因素而产生的歧义之列。
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希曾以对弥尔顿的第二十首十四行诗的最后两句的分析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4〕
He who of those delights can judge,
and spare
To interpose them oft,is not unwise.
文学评论家们对于这两句诗有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其原因就归咎于“spare”这个词引起的歧义。“spare”既有“抽出时间做某事”的意义也有“克制自己不去做某事”的意义,因此对于这两句诗的第一种阐释是:弥尔顿对这些享乐表示欣赏——对于这些享乐能够做出判断并能经常参与的人是明智的;第二种简释则是:弥尔顿忠告说:凡能对这些享乐做出判断而克制自己不去参与的人是明智的。这可见,阅读过程中歧义的存在和产生是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的语言学基础。
二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是一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它的核心在于:文本自身决不会构建出任何意义,文本只有通过读者对于文本的反应而产生意义。沃尔夫冈·伊瑟认为,评论家的任务不是去解释文本作为客观事物的意义,而是去解释它所给予读者的影响。在《阅读过程:现象学方法论》一文中,他曾这样表述读者反应的重要性:“在研究文学作品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文本自身,而且要同样考虑到在对于该文本的反应过程中的读者行为。”〔5〕伊瑟将读者划分为两个层次:“隐含的读者”(implied reader)和“实际的读者”(actual reader)。所谓“隐含的读者”是指文本为其预先设置了一套可以诱发其反应的机制的读者,费希称之为“预期的读者”(intended reader), 他解释说:“预期的读者是指其教育水平、观点、兴趣以及语言能力使他能够感受到作者所要提供的经历的读者。”〔6〕虽然伊瑟和费希在各自的描述中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所要表达的都是理想化的读者。而“实际的读者”在阅读中获得某些意象,但是这些意象不可避免地被染上了读者既有经验的色彩。按照伊瑟的观点,文本能够向读者提供各种不同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作品的主题便会呈现出来,这种呈现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具体化”(concretization)的过程。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被认为具有两个层面:艺术性的层面和美学性的层面,其艺术性的层面是作者创作的文本,其美学性的层面是指读者将文本具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一部作品不仅仅是我们所能看得见和摸得着的文本,它还包括读者将其具体化的过程。文本只有被读者具体化以后才具有生命和意义,这一具体化的过程就是读者的阅读行为,它与某一个具体的读者的气质、素养息息相关,而读者的气质和素养也同时受到不同文本的影响。阅读就是文本与读者的有机结合,是文学作品生命的源泉,但是这种结合过程是非常维妙和难以名状的,它既不能完全以文本为依据来加以描述,也不能完全以读者的个人气质和素养为依据来描述。“阅读行为”,用伊瑟的话说,“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容不同观点、期望与反思在其中的万花筒。”〔7〕
笔者认为,读者的阅读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实际的读者”向“理想化的读者”不断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了曲折和挫败的过程,几乎没有哪一个读者有希望到达这一“光辉的顶点”,因为“一个文本可以有若干种潜在的不同的意义实现,没有哪一次阅读能够耗尽这些潜在的可能性,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填充这些空白而将其他的各种可能性排除在外。”〔8〕况且, 阅读活动也不是“一锤定音”的一次性活动,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采用的视角往往是在不断移动的,这种视角的移动构成了阅读活动的不同阶段。读者在初次阅读某一文本时,不可避免地要根据自己的既有经历来赋予文本以期望,这种期望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起到了参照系的作用。读者的期望可能会在阅读中得以实现,也可能会在阅读中破灭;但是,这种期望的破灭有助于读者修正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当读者完成一次阅读后再一次重读同一文本时,很显然会使用修正过了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本,对文本又会产生新的期望,因此文本的某些方面将可能产生读者前一次阅读时并没有注意到的重要意义,而其他一些方面则变得不再重要了。读者在第二次阅读时发现自己在第一次阅读时遗漏了许多内容,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读者第一次阅读时并没有“遗漏”什么,而是因为他第二次阅读时已经下意识地采用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面阅读一面变换自己的期望,修正自己的视角,继而做出更加“完善”和复杂的判断和期望。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中都蕴藏着对下一个句子的预览,并且成为一种对于预期内容的探测器;这一过程随即改变了‘预览’而使其成为已经阅读过的内容的‘探测器’”。〔9〕因此, 阅读的过程如同“摸着石头过河”,读者瞻前顾后、如履薄冰似地在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意义层次间缓缓移动。
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虽然有时进展缓慢、曲折,但是其想象力却是异常地活跃和快捷。伊瑟认为,作者只有通过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才有希望紧紧抓住读者以达到实现文本意图的目的。他将读者的阅读活动称作是读者获得作品意义的“完形认识”(gestalt)过程, 这其中读者的想象力固然重要,但是无论读者的想象力多么活跃和快捷,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在,因为所谓“完形认识”过程不仅要受到文本自身的限制,而且还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读者选择过程的烙印。换言之,它是文本与具有不同经历、意识和观点的读者思维活动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伊瑟似乎又在强调文本自身对于读者阅读活动的限制作用。他将文本自身的结构比作是夜空中的星星,其位置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如何用线条将“星星”连接起来组成“图形”(即文本意义)则是变化万端的。显而易见,伊瑟对于影响读者阐释文本意义的因素的描述是含混不清的。在这一问题上他步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误区,既然将文本自身的存在看作是一组“超验的图形”,等待不同的读者将其具体化,那么在没有将其具体化的前提下又怎么能够讨论这些超验的图形呢?
三
伊瑟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接受理论,它给予读者相当的自由度;但是读者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来阐释文本,他必须受到文本自身的制约才能保证自己的阐释是属于他所阅读的文本的。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保持灵活、开放型的头脑,随时能够对自己的信念提出质疑和修正。然而,费希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将读者和阅读合二为一,强调读者在阐释文本意义时的决定性作用。在费希看来,文本的意义并不是一件成品,而是需要读者参与去创造它。用伊格尔顿的话说,“读者现在推翻了老板,自己掌权。”〔10〕阅读对于费希来说,不是去发现作品的意义,而是要去体验作品对读者施加了什么样的影响,读者对于文本的体验即是文本的意义。他反对那种将文本意义看成是镶嵌在文本之中或用某种代码编写在文本之中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读者的参与活动,至多将读者看作是一部“一次性的提取机械”。〔11〕费希坚持认为,读者的参与活动应该是批评所关注的焦点,但是读者的参与并不导致文本意义的产生,而是它本身就具有意义。之所以说读者的参与本身就具有意义,是因为它包括了读者的慎思、明辨和质疑、解惑等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这些思维活动本身就是阐释性的,因此对于这些思维活动的描述即是阐释活动,换句话说就是作品的意义所在。不难看出,费希心目中的作品意义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自始至终地存在于读者的阅读活动中,不断地重新构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读者去发现之。
费希所描述的阐释活动显然具有极大的任意性和相对性。为了克服这一理论的主观性,他也试图给阅读活动设置某些制约机制以保证对于某个文本的阐释是“有效的”。于是,费希在他1980年的文章《阐释集注版本》(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中提出了“阐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观点。费希认为,虽然阅读和阐释是一种不受文本约束的“自由”活动,但是任何一种文本最终也不会被阐释得千奇百怪,这是因为任何一个读者都隶属于一个拥有许许多多其他读者的阐释群体,这个阐释群体的规章将会认可某些阐释而排斥其他阐释。
所谓“阐释群体”,用费希的话说是由那些共有一套阐释策略的人组成的。然而费希对于阐释策略的定义是含糊其词的,他的阐释策略并不存在于包括文本在内的任何客体之中,完全是读者的一种主观意识。实际上,他认为阐释活动本身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无需控制的。
费希在《论证与劝诱:两种批评模式》一文中,将传统的批评模式(如新批评)称作是论证式的批评活动,而将他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称作是劝诱式的批评。在论证式的批评过程中,实证是本来就有的,但是没有固定的信念,读者需要在各种互相竞争的信念中来判断和选择。这是一种近乎自然科学研究程序的批评模式,在这种批评活动中,各种不同的阐释被明确的事实所证实或摈弃。费希认为在这种论证式的批评中,批评活动被孤立的客体所控制,批评者根据阐释内容与客体的关系来断定该阐释是否恰当、有效。而在劝诱式的批评模式中,读者采取的是劝说、诱导的方式去说服别的读者相信自己的信念,试图使别的读者也意识到自己所用来支持自己的阐释的事实。费希认为在劝诱式的批评模式中,批评活动被寓于客体之中:“然而,在劝诱式的模式中,我们的行为是这些客体的直接组成部分。我们的行为不仅是用来描述我们的行为的术语,而且还是评价我们的行为的尺度。在这一模式中的批评家的责任的确非常之大,因为他不仅只是这场球赛中的运动员,而且还是运动规则的制定者和取消者。”〔12〕
显而易见,在费希的理论框架中,被传统的批评方式所忽视或贬低为“文本卑贱的奴仆”〔13〕的读者确实是扬眉吐气了,他由一部一次性的意义提取机械一跃成为文本意义的决定者了。
伊瑟和费希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都注意重视了读者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反对传统的文本主义。但是伊瑟依然肯定了文本在意义产生时的制约作用,他认为意义的产生来自读者与文本的结合,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读者在阐释文本意义时所受到的制约主要来自文本的内部结构。这一超验的内部结构规定了文本所固有的内在意义,因此读者阐释的任务就是将意义“提取”出来。费希与伊瑟的分歧就在于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制约机制上,费希的理论过分地夸大了读者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制约机制存在于读者的主观意识的自我控制之中。他否认文学作品具有固定的内在意义,将读者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读者是意义的主人,他的任务就是“创造”意义。然而,费希的的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无法摆脱众多读者在阐释文本时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又将意义的制约寄托在他的所谓“阐释群体”上。实际上,他自己始终没能给自己提出的“阐释群体”下一个满意的定义,所以当有人问到他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属于某一个阐释群体时,他的回答只能是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是常识和经验证明阐释群体是存在的。费希为了批评传统的文本中心论,从主观意识出发,将读者置于决定性地位,对于文本的客观存在视而不见,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只能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伊瑟认为,读者在阅读时文本的制约机构便会立即开始工作,而向读者提供一份精心准备的“菜单”。因此,读者必须熟知作品中所使用的文学技巧和规程,掌握文本中所蕴含的意义制约“代码系统”,才能做出对于文本的有效阐释。伊瑟将意义制约机构设置在文本之中,承认文本在意义产生时的客观规定作用,貌似客观公允,但是他同时又将文本的内在结构系统比作是天空中星星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而如何连接星星之间的线条可以是任意的,可以联成的图形是无穷尽的。换言之,也就是把读者的阐释活动看作是受文本内在结构制约的、将文本的内在意义具体化的过程,而读者具体化的方式是因人而异、千差万别的。如此说来,伊瑟最终也没有解决意义产生过程中的制约机制问题。他将制约机制建立在了一套只有在具体化以后才看得见的文本内在结构上,重新落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窠臼。
注释:
〔1〕〔10〕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University of Mininesota Press,1987,p.55,85.
〔2〕〔3〕〔5〕〔7〕〔8〕〔9〕Jane P.Tompkins,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101,105 ,50,54,55,54.
〔4〕〔11〕Stanley E.Fish,"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in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ed.by Robert con Davis andRonald Schleifer,Longman Inc.p.102,107.
〔12〕〔13〕Stanley E.Fish ,"Demonstration vs Persuasion :Two Models of Critical Activity "( 1980) in ContemporaryCritical Theory,ed ,by Dan Latimer,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Publishers,p.468,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