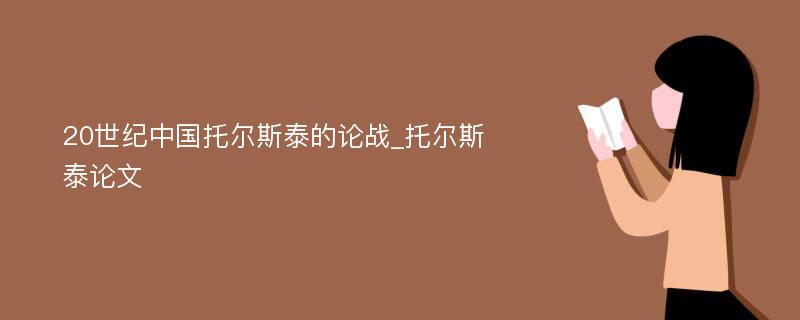
托尔斯泰进入20世纪中国所伴随的一场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而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步入20世纪中国的。而且,托尔斯泰步入中国,并不像我们一般认为,完全是中国人和谐地恭迎进来的。甚至可以说,托尔斯泰进入20世纪的中国,实际上,伴随着一场和中国维新派、洋务派的思想论争。继而托尔斯泰思想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中潜移默化地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又恰恰肇端于步入20世纪中国之门时的这场思想论争。
托尔斯泰和20世纪中国的姻缘,一般是从他和两位中国改良派知识分子的通讯讲起。这就是1905年托尔斯泰给张庆桐的复信和1906年给辜鸿铭的复信。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两封复信中看到“托尔斯泰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与尊敬”(注:戈宝权《托尔斯泰和中国》一文,见《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上海译文,1983,10页。),也有人指出托尔斯泰是辜鸿铭的“中国的知音”(注:李玉刚《狂士怪杰》华夏,1999,320页。),托尔斯泰给辜鸿铭的信是在“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注:黄松涛等译《中国人的精神》译者前言,海南出版社1996,2页。)但是,如果我们对张庆桐和辜鸿铭给托尔斯泰的致函和赠书,对托尔斯泰复信的背景不予足够的注重,我们就不能充分估计托尔斯泰复信中更深一层的论争性意义。这样,就势必妨害对托尔斯泰步入20世纪中国及其后的复杂影响进行深一层的研究。
一封没有完成的《告中国人民书》
而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我认为,首先需要再向前回溯到1900年托尔斯泰所写的一篇一直未引起我们注意的文章:《告中国人民书》。当时托尔斯泰针对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罪行而愤然提笔,但历时数月、三易其稿而终未付梓。该篇现存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34卷“未发表、未加工和未完成的作品”栏中(P.339)。
我们知道,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罪行,是当时托尔斯泰最关心的问题,每议时事必当提及。当时托尔斯泰正在研读孔子,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研究的热情正是和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紧密相关的。在他了解到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罪行时,这位年逾七十高龄的老人的心里,油然生起一种渴望,要和自己多年崇仰的东方文化的故乡的中国人民剖心而谈。他在日记和信函中都谈到这一心愿。
1900年10月30日,这篇酝酿良久的书信动笔了。托尔斯泰在日记里记道,“早上开始写《告中国人民书》,开头写得又少又不好。”
然而直至次年2月,托尔斯泰三次改写致中国人民书,但却终竟没有定稿。有人猜想认为,原因是托尔斯泰自度其向中国人民提出的抵御外辱的方法过于无力。(注:参见希夫曼《托尔斯泰与东方》莫斯科,1960,116页。)或者是1902年2月发生的东正教最高会议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事件把他的注意力引向了新的斗争。但是我想,这三易其稿而不发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托尔斯泰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可以从草稿的改写变化之沿革中,猜测托尔斯泰思路的发展变化。
看来,托尔斯泰提起笔来,先是要以千百万民众代言人的名义,写一篇庄严的宣言。所以文章一稿的标题叫《全世界兄弟友好联盟的参与者告中国人民书》。
一开始,托尔斯泰首先描述他想象中的“永远静止不动的东方的”中国人的合理的生活怎样被欧洲侵略者打破,而托尔斯泰正是要在这“永远静止不动的东方”,为危机中的现代社会寻找出路。所以托尔斯泰写《告中国人民书》的根本意旨是要捍卫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这一稿中,表现出的还首先仅仅是“我们对(中国人)无辜的受难的全心的同情”,而“在你们面前恢复真理的这种必要性,就是我们向你们呼吁的主要目的”。
在第2稿中,标题变为《基督教徒们致中国人民书》。开篇首先讲的就是:“那些现在在你们那儿犯下滔天罪行的明火执仗的人们,……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自称基督教徒,他们和基督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稿中都谈到,这些入侵者的“蛮横无耻的行径在你们的一些人中引起强烈的愤慨,表现为要用那些欧洲人对付你们的手段来对付欧洲人,从而在你们中间也开始了同样可怕的野兽暴刑”。托尔斯泰之所以认为这非常可怕,是因为这种以牙还牙的暴力行为完全违反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主义,它将造成整个人类精神的堕落。这在托尔斯泰看来,比中国人的现实灾难更为可怕。
第3稿的标题失去了主语,变成《致中国人书》。在这最短的一稿中,托尔斯泰把矛头正面地指向在那些侵略者之上的统治者——“他们的上司们、议员们、部长们、国王和皇帝们,他们坐在宫室之中,沉溺于荒淫腐化之中,而制造着那些在你们中发生的可怕的事情。”
而在最后的一稿中,标题变成《一个基督教徒致中国人民书》。这4份未完成稿的标题在不断更换。以什么人的名义写这封信,可能使托尔斯泰颇费思考。这里不但有主体立场角度的变化,更表现出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一个人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和可能代表别人。既然上帝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么“人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大家就会联合起来了”(注:《复活》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76页。)。所以,在第1、2稿中托尔斯泰总似欲言而难尽,唯有在第4稿中,以“一个基督教徒”的个人名义,他才自如地把自己的思想最充分地表露出来。
第4稿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对中国人民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正在和将要遭受的戕害突出了出来。文中重复出现了“腐蚀”这个词。而对于中国人以牙还牙的暴力反抗,托尔斯泰则认为正是这种腐蚀的结果,在前几稿述及中国人以牙还牙的地方,他又增加了一句:“他们——指欧洲侵略者——需要的正是这个”。
托尔斯泰进而阐述了自己的根本思想:
“你们面临的危险在于,你们一旦一方面,被那一伙强盗通过杀人来鼓吹和表现出的对暴力的崇尚所迷惑,一方面,被他们称为文化的那些淫技器物的华彩所迷惑,你们就会离开自己领袖们,离开伟大的孔子,是他教导着真正德行,及获得这种真正德行的内在努力之方。这样,你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你们美好德行:爱劳动,爱和平,敬重尊严,而沦落到那种可怕的势力之下,那种势力会渗入人的灵魂的最隐秘的角落,现在的欧洲人就是在这种可怕的势力之下奄奄待毙。”
最后,托尔斯泰提出他认为的“中国人最宝贵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真正的自由”:“这就是一个人能够反省、思考、写作、读书、讲他所想讲的一切,能够不参加政府的事务。他们知道并信奉皇帝是天的儿子,他掌有权力是因为他聪慧仁善,他倘若不是这样,他的所有臣属都有责任撤换他。而欧洲人那里则不是这样的。”
在这一稿中,两种文明的冲突——西方伪文明和东方固有文明的冲突被突出出来。托尔斯泰最痛心的是中国传统文明备遭蹂躏,他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明朗化为对中国固有传统文明的捍卫,进而以他想象中的中国人的自省、自修、自觉的“自由”,来引导出托尔斯泰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摆脱政府的自由。
然而托尔斯泰的这些崇尚赞美之语对于正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过于迂远了。它可以作为对文明冲突的深邃思考,却未能成为现实的解救之方。但是无论如何,这封终未定稿的《致中国人民书》成为托尔斯泰渴望和中国人直接对话的史证。同时,它也成为参照理解托尔斯泰和两位中国知识分子论争的一个背景材料。实际上,他后来致两位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中所表达的心思,在5年前已然酝酿在胸了。
是共赴欧洲“进步”之途,还是捍卫农耕文明传统——关于两国人民携手基础的论争
托尔斯泰和中国人直接对话的渴望是在1905年才第一次实现的。1905年12月,托尔斯泰头一次收到一个中国人张庆桐(注:张庆桐(1872-?)上海人,1899年由北京同文馆派至彼得堡政法大学留学,后任驻恰克图都护副使。)的来信和随寄来的一本梁启超写的《李鸿章,或中国近40年政治史》的俄译本。
实际上,这本书远不如张庆桐的信使托尔斯泰感兴趣,因为正是这封信给了托尔斯泰和中国人直接对话的契机。
张庆桐的信的实质就是谈,中俄两国人民应该并可以在“进步”的道路上携手共进:
“中日战争(指甲午战争)之结果深深触动了我,所以我致力于学习俄文。其激发我的因由是,世界上的主要民众属于俄国和中国,比于欧洲,俄国之进步较慢,而在中国,进步较俄国还慢,由此可见,俄国生活的现象比于欧洲,更近于中国,而现在俄国所实现的国家体制的改革,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而非欧洲,所以这两个民族的友好应该比其他民族更牢固。”
显然,张庆桐对于中俄两国关系的思考的基础是以欧洲为尺度的“进步”。他认为中俄两国都属“落后”,所以两国人民在“进步”的道路上因先后接踵而可以相互提携。张庆桐在其后来写的《俄游述感》一书中用中文重述给托尔斯泰的信时,更加进倾慕彼得大帝“强力变政,勃兴国事”,认为“天不欲兴中国则已,苟欲兴之,必有如彼得者以为主”,而他自己“愤国势骤落,乃弃旧文求新学”,为详闻彼得遗事而“决意习俄文”的字句。这充分表现出维新派的立场。值得注意的是,张庆桐在信中还讲述了中国近年社会思想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言及民众对西方科学及各种知识日益神往而求索的精神倾向,而同时,对于亘古不变的儒学教条产生了怀疑心理。张庆桐送给托尔斯泰《李鸿章》一书,正是为的“展示”这种“中国人民的道德风貌”,并希望托尔斯泰“对该书稍加评论”。
这些显然是托尔斯泰不以为然的。所以托尔斯泰在信中不仅说《李鸿章》一书自己“还未拜读”,而且旗帜鲜明地表示“从你的来信加以判断,我怕我不会同意它的倾向。”这是因为“从您的来信看,您是赞同(我想在书里也一样)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改革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本来,托尔斯泰可以对张庆桐的书信置而不顾,但是看来,托尔斯泰不肯放弃这样一次和中国人直接对话的机会。实质上,托尔斯泰给张庆桐的复信,可以视为托尔斯泰和中国改良派进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此来阐述自己积年而成的珍贵思想。
在复信(1905.124.)中,托尔斯泰实际上仅仅认同了张庆桐的一个思想,这就是两国人民应该建立一种民间的而非政府间的友好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基础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只字不提张庆桐侃侃而谈的中俄在那条“进步”路上的缘分,而开篇即谈对孔子、孟子、老子乃至墨子的景仰,指出自己“对中国人民向来怀有深厚的敬意,由于日俄战争的种种事件而在极大的程度上加深了。”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表现出传统文明熏陶下形成的“忍耐精神”。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中人民的联系的基础,绝不在张庆桐所说的“进步”之途上,而在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上,在于基于其上而形成的“俄中两大民族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上,在于他们应该寻求一种区别于欧洲进步的“新的生活方式”上。托尔斯泰看来,在欧洲进步的历史大势中,“我认为俄国,它的大多数的农业人口,是个例外。我期待从它那里出现新的生活方式,我也这样期待着中国农业人口的大多数。”这里托尔斯泰是在说,俄中两国人民的确“必须携手并肩前进”,但不是共赴欧洲“进步”之途,而是捍卫东方农耕文明的传统。
针对中国改良派力图仿效西方、改革社会的走向,托尔斯泰语重心长地说,“愿上帝保佑中国不要走日本的道路”!进而论述了自己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的思想:
“对于成长,发展、完善意义上的改革,是不能不表示同情的。但仿效式的改革,把那些在有识之士眼里已然在欧美完全站不住脚的形式输入中国那就会是一个致命的大错。改革应该是从一个民族自身的特质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形式的崭新的东西。”“中国人,也正象所有的人一样,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发展技术上的完善。精神的力量被歪曲了,技术上的完善只会起破坏作用。”
在托尔斯泰逆天下大势,反科学、反进步、反现代化的“最深刻意义上的反动”(列宁)之中,有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精神和物质关系、对于社会人生意义的更深邃的思考。今天,在经过百年血与火的历程之后,我们或许能对之也有所体悟吧。然而当年,托尔斯泰的争论之声却未通于国人,托尔斯泰主义大抵首先是作为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为中国革命家所接受的。这就是托尔斯泰在信的最后谈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理想:
“他们必须……制定出一些不受政府羁绊的社会生活的新形式,……就是除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则之外,人们无须依靠政府,也无须服从任何人而生活的自由”。
辜鸿铭的“尊王”立场和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宣言”
时隔不久,1906年3月,托尔斯泰又收到俄国驻上海总领事Л·博罗江斯基转来的中国学者辜鸿铭用英文写的《尊王篇》(注:实际上英文书名是《总督衙门论文集》,《尊王篇》是辜鸿铭题的中文书名。)和《当今,皇帝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部书。
而直至1906年9月13日,托尔斯泰才动手给辜鸿铭写回信。从托尔斯泰的信函和回忆录中,可知他为给辜鸿铭回信做了认真的准备。最后的第三稿日期是10月3日。看来,托尔斯泰为写这封《给一个中国人的信》(即给辜鸿铭的信),几经思索、准备,工作前后历时近2个月。这封信是否真的转到过辜鸿铭手里,现已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托尔斯泰的这封信绝不仅仅是写给辜鸿铭的。因为托尔斯泰立即请求切尔特科夫把信译成各种外文,并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一时引起世界关注。可以断言,托尔斯泰极为重视这封信,他是把这封信作为论述和宣说自己思想的武器。难怪托尔斯泰临终前还记起这封信,当有人称赞他的文学作品的永恒价值时,他清醒地摇头说,“我的这一切,皆属不足道也。余以为最有价值者,当为复中国人某一书也。”(注:李玉刚《狂士怪杰》华夏,1999,322页。)
实际上,托尔斯泰的《给一个中国人的信》是继给张庆桐的信之后又一次和中国人的论争。
在辜鸿铭的书中,托尔斯泰自然可以看到诸多和自己一致的思想,如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辩护,对效仿西方的反感(注:辜鸿铭谈及“改革党”时说,“用不着讨论这些观点拙劣和知识贫乏的年轻狂徒对‘进步和文明’的滑稽摹仿”云云。),对西方传教士作用的否定(注:辜鸿铭论述了传教士立下的所谓“提高民德、开启民智、慈善工作”的目标没有完成,“传播福音的工作已然失败”。),尤其是在《当今,皇帝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中,辜鸿铭大讲“当一个人,一个民族或多个民族的事务陷入困局时,……唯一正确的摆脱的方法,就是去找到其道德本性的中心线索和平衡状态,去寻找他们的真实自我,去恢复他们的心境的平衡,保持其评判的不偏不倚。”而“据我所知,除了托尔斯泰伯爵一人之外,还没有人公开提出过结束这场不幸的战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在圣诞献词中想到并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儒家办法,……要好好反省自己,或者,象孔子所说的,找回其真实自我——恢复其心理平衡、并保持其公正的判断力。”
但是,在辜鸿铭的书中,表现得最充分的还是站在政府立场上的尊王攘夷思想,以及洋务派力图利用西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君主制下进行改革的思想。
《尊王篇》中,辜鸿铭对朝廷,对中国传统体制的忠诚溢于言表。开篇第一节的题目就是《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他盛赞慈禧太后的“天生而老练的政治家的明晰而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极端保守派和过激派的首领以迅速、严厉而果断的打击”。继而又讲道,“在个人生活中,中国人热爱和崇敬其父母,……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现在热爱和崇敬其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王朝命运为之系赖的皇太后的意志指定的后嗣和继承人皇帝陛下。该王朝的统治已经惠泽中国人民250多年了,中国人心中的这种感情有多深,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已经充分地证明了……”(注:以上引文见《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26、32页。)这当然是指义和团一度和清王朝站在一起,扶清灭洋的“尊王攘夷”之举。这些都是托尔斯泰万难同意的。
所以我认为,托尔斯泰写《给一个中国人的信》,显然不是仅为了应和辜鸿铭,而更是针对辜鸿铭的书所进行的一场论争,是要批评辜鸿铭在书中表现出的站在政府立场上的尊王攘夷思想,批判包括洋务运动在内的改良道路,从而提出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
和给张庆桐的复信一样,托尔斯泰还是先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倾慕说起,而接着就引导出自己的不抵抗主义:
“中国人民虽遭受到欧洲民族这样多不道德的、极端自私的、贪得无厌的暴行,而直到最近都是用宽宏和明智的平静、宁可忍耐也不用暴力斗争的精神来回答加之于他们头上的一切暴行。”
但是,托尔斯泰马上指出,“我指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因为辜鸿铭的《总督衙门论文集》代表的官方立场,所宣扬的是“义和团小伙子的狂热”,是暴力攘夷,是对政府的效忠感情。所以托尔斯泰指出:
“我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的书中看到中国表现出的战斗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的暴行的愿望。”
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要失去忍耐,不要改变对暴力的态度”,因为“如果中国人民真是失去了忍耐,……那么这就可怕了。”到那时,“中国不再是真正的、切合实际的、人民的智慧的支柱,这智慧的内容是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
正是以捍卫中国传统的“和平的、农耕的生活”、“‘道’的生活”的名义,托尔斯泰针对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改良路线指出,“这就是我从您的书和从别的消息中看到的。中国的轻率的人们,所谓的改良派认为,这一改变应该是去做西方各民族已经做了的事情,即用代议制政府去替代专制政府,去建立西方各民族的那种军队,那种工业。这一决定初看起来是最简单和自然的。而根据我知道的中国的一切,这决定不但是轻率的和非常愚蠢的,而且完全不符合聪明的中国人的本性。”而坚守“和平的、农耕的生活”,这“对全人类都是真正的和唯一的道路”,这正是托尔斯泰拳拳期望于中国人民的:“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自己都对自己的老祖宗失去信心的时候,要让中国人民不仅自己守死善道,还要强作全世界人的领路人,何其愚也!
辜鸿铭的书以“尊王”为题旨,突出表现出尊崇王权,而托尔斯泰主义正是要否定政府的意义和权威,号召人民摆脱政府的控制。所以,托尔斯泰以大量篇幅论证“中国人民不能不感到必须改变自己和政权的关系。”
他指出,“电报和一切称之为文明的东西的出现使他们的政权变得过于沉重”,“使暴力政权从其本质上讲越来越腐朽,使被统治者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多,越来越认清服从政权的危害,”所以从西方民族到东方民族,都在“寻求……从专制政权下解放自己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5年前托尔斯泰在独白式的《告中国人民书》最后一稿,曾结论式地赞扬中国人民“知道并信奉皇帝是天的儿子,他掌有权力是因为他聪慧仁善,他倘若不是这样,他的所有臣属都有责任撤换他。”以此来印证自己关于人民有权利摆脱政府的思想;而在这封信中,托尔斯泰则彻底否定了自己上述的提法:
“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学说认为,君王,‘天子’,应该是大贤大德的人,他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臣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再服从他。但是我认为,这种学说只是为政权辩护。……”因为“中国人民不会知道他们的皇帝是不是大贤大德的人,同样,信基督教的各国人民也不会知道,是不是上帝赋予了这位君主,而非那位同他们斗争的君主以权力。”
在这里,托尔斯泰对内圣外王论、君权神授论都进行了批判,提出历史已经发展到“各民族无论如何都要改变自己和政权的关系”的时代。他宣布,“我们俄国人不应该服从现在的政权”,“我们也不应该去做我们的、还有你们的改良派、不聪明的人们所要做的事。不应该效仿西方,……我们必须而又可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并且是最简单的事:过和平的、农耕的生活,忍受可能施加于我们的暴力,不以武力对抗暴力,也不参与暴力。”
在中华民族面临内患外辱,汲汲于社会政治改革之际,从托尔斯泰的不参与暴力、不参与政府、力求自我完善,过“‘道’的自由”的生活的呼吁中,连改良派也很难取得什么实际上的思想资源,他们只能在托尔斯泰对中国传统文明的颂扬中寻找一点儿精神上认同的慰藉。倒是日愈兴起的无政府主义派和革命派从托尔斯泰主义中找到了否定现政权、反对满清政府的同志,找到了摆脱思想桎梏,追求自我反省、自我解放的思路。而从长远来看,不是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而是托尔斯泰反对摹仿,走自身发展道路的思路,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之路上,应和着中国各派间古今、东西、内外之争,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融入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之中。
“改革应该是一个民族自身的特质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形式的崭新的东西。”“中国人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实际上成为了20世纪中国人思考和争论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