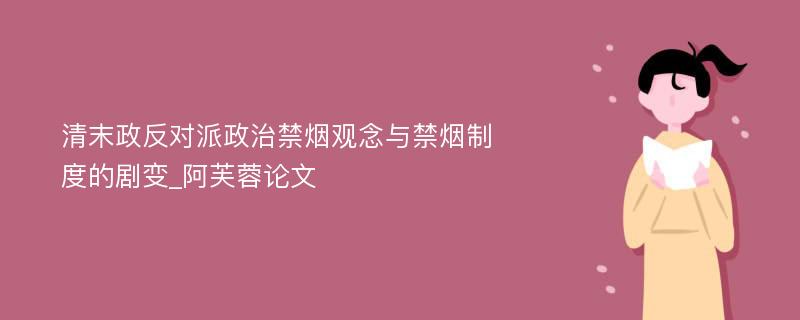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变论文,朝野论文,清末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2-0060-08
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观念间有差别,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和认知也较为复杂。这一问题成为相关著述中“失语”的部分,它与随后的辛亥鼎革关系密切,不可不察。禁烟激变包括因禁种罂粟所导致的农民反抗以及因增加烟土、烟膏的各种税捐而引发的商人抵制风潮。禁政关乎国家命脉之振兴,尤为新政改革之必需。百余年来鸦片始终被国人视为戕身耗财的毒品,不但清廷痛恨此物,即令民间亦视之为“亡国之疾病”,其害甚于“赌”和“妓”,迟早要禁绝。然而禁政实行后,各地却变乱频仍,酿成了大大小小的禁烟风潮。
本文通过对清末朝野关于鸦片禁政的不同认知以及禁政激变的讨论,意在阐明清廷处理禁烟善政面临的两难处境,藉以揭示清廷中央与地方官员、中等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以及下等社会在禁政问题上复杂而又微妙的态度,凸现学人在这一问题上曾经存在的并不恰当的关怀和定位。
一、官界与知识界
嘉道以降,规模较大的禁烟行动应是道光季年的禁烟运动和光绪朝后期的禁烟新政,其间,各省遵照清廷的旨意也曾采取过规模不等的禁种罂粟行动,尤以19世纪80年代贵州和山西两省的禁烟运动较为有名。历次禁烟运动中,清末新政时期的鸦片禁政最具规模,影响也堪称久远,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颇为复杂,耐人寻味。本文拟就这次鸦片禁政所暴露出来的禁政观念和禁烟激变问题略为疏证。
所谓“禁政观念”,本文特指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令的态度和认识。清末禁烟时期,对待鸦片禁令有两类不同的群体,一是基本支持禁政改革的群体,它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且掌握言说的权利,这类言说赋予鸦片禁政以各种积极的功能,表现在道义、经济、吏治、民生等诸多方面;二是部分罂粟种植者以及部分鸦片烟土、烟膏等运销经营者,甚至包括外人在华经营鸦片的商人。这一部分人群处于禁烟道义的对立面,他们或迫于生计,或羡于暴利,铤而走险,置禁令于不顾,兴风作浪。相对而言,对抗禁政的群体并未掌握言说的权利,其意见和呼声大多出现在官员的奏章和有关报道中。本文将这两个群体姑称之为“禁政中的两个世界”。“两个世界”的研究,过去更多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评价,对两者的褒贬截然不同。学术评价的路径一偏,学术即有误导之嫌。在时下有关禁政与新政的著述中,两个“世界”的对立趋向“意外地”陷入“失语”状态,鲜有置论。(注:禁烟学术史上颇负盛名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于恩德著,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影响后来同类著作甚大,然该书并未将各阶层的禁政观念分别揭示,即便是禁烟激变的问题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后来者述学,这一问题仍未引起足够的注意。秦和平著《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立足于四川省情,较多地涉及此类问题,但其他地区的情形限于论题,未能展开。)
1906年开始的禁政改革被朝野人士赋予了较多的意义,总括来说,主要是堵塞漏卮、强健国民体质、进取有为、刷新民族形象、转弱为强等,社会期望值较高。持此观点者多见于官界的各类言论、奏章和咨文,民间人士的各类说法等。[1]这个群体虽认定鸦片禁绝的必要性,但在就事论事时又有区别,甚至互为矛盾,朝臣疆吏的言行更具代表。《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在评价张之洞时,认为“所有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鸦片。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2](P496-497)还有人认为张之洞是官方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他曾经反对鸦片,但当他触及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时,就改变了语气。他在《劝学篇》中说鸦片之害足以毁人才能,削弱志气,浪费金钱。至少在1898年,他把中国吸食鸦片者归结于愚昧无知,认为发展教育是禁烟的妙方。然而三年之后,张之洞却在给皇帝的建议中说,鸦片税收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以便兴办洋务”,“像张之洞这种对待鸦片的矛盾心态并非独一无二。许多上层官僚和有影响的人士长时间以来一方面痛恨鸦片,一方面又承认鸦片贸易带来的税收利益”,论者尚列举出类似“张之洞矛盾现象”的其他著名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王韬等等。[3]外人关注这一矛盾现象,其实蕴含着“非此即彼”的逻辑认知。鸦片问题不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而是与英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在英人不予合作的情况下,国内禁烟目标很难达到,加之“鸦片经济”已经成型,难以在短时间内铲除,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大多是就事论事,难免互为矛盾。
其实,矛盾本来就是一种历史实态,这恐怕是中外历史本来具有的一种本相。有关媒介对这种鸦片禁政观念的复杂面相曾有描述:“自去年人心猛然醒悟,当道者统筹计划,日以禁烟之说闻。或谓宜速绝之,或谓宜缓图之,或谓财政之所关者大,或谓生命之所系者重,或谓商之外洋,或谓自我议决,或谓习俗难移,或谓士籍混淆,尤阻挠之甚,而不易查禁,迄今盈廷聚讼,纷然莫衷一是。”[4]对政府禁烟上谕,无人不表赞成,如何禁绝,看法却甚不一致,这类分歧导致各省州县政令不一,缓禁与速禁并存的格局持续了近三年之久。部分省份进展较缓,并非其不愿禁烟,多数是斤斤计较于鸦片税厘的收益。[5](P85,101)换句话说,即是财政利益对禁烟新政产生严重的制约和影响,朝廷如是,各省督辕也莫不如是。
对待禁政的态度,民间与政府的看法相当接近,但立论言说的角度稍有不同。禁政上谕发布的前一年,民间士绅已经成立了少数禁烟组织,在本邑开展鸦片禁绝活动,振武宗社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完全超然于清廷之外,纯系自发性社会改良组织。该社章程说:“为军国民非先强种不可,欲强种不首禁鸦片更不可,此固不待智者而后知。”[6]看来,振武宗社是以强健种性、养成军国民资格、堵塞漏卮为宗旨,符合当时趋新潮流。《万国公报》的社论也认定鸦片之害与军国民资格、尚武精神不相符合。[7]1906年初有人又明确将禁烟与新政相联系,有人提出反对官场嗜好,反对吸食鸦片,以响应新政开展。[8]民间在谈论实行新政以振奋民族精神时,首先将官场的鸦片吸食问题提出来。除此而外,还有人对鸦片禁政的巨大效益甚为看重,认为它可以“变易全国之脑筋,而为实行新政之大机栝”,关乎中国的国际声誉、国民公利以及军备强健。关于经济上的利益,他认为,“以十年计之,为国民保留赀财当不下五六百兆,以五六百兆为各省铁路商办公司,则不特外人所办之铁路不难依次赎回,而路旁矿产亦得免外人觊觎,待至民力稍裕,余利日充,一切国债皆得清债,又何事患贫为哉!而商业之进步不必论矣”。[9]鸦片一禁百业必兴,经济利益尤为显著,这一看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书生论道,虽未必切近实际,但却是当时实实在在的一种心态,对禁政与新政的复杂影响缺少洞见,实难苛求。的确,从理论上看鸦片嗜好与民族荣衰关系极大,与民族进取精神息息相关,晚清巨患的形成与鸦片问题密不可分。[10](P4)在鸦片税收与新政事业关系紧密而财政抵补缺少成效的背景下,清末禁政能否立竿见影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则难以断言。
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召开前后,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的态度与清廷官员的主张之间更是保持着高度一致,均对鸦片禁政抱有积极的评价。武汉地区是我国洋烟土贸易较为集中的地区,该地区的重要媒介对鸦片禁政的重要性评价说:“禁烟实强国之本,为我国内政最重要之事,而又须各国协助,故尤为外交重要之端,今日之会实我国转弱为强之关键也。”[11]该报称:“阿芙蓉种绝,是不但可起我已隶黑籍同胞之痼疾,并可以救我无数未隶黑籍同胞之生命”;“呜呼!我中原之世界为此黑烟毒雾所障蔽者久已混混沌沌,在醉死梦生间矣;今而后得复见烟消雾减之日月重光之一日也。”[12]知识界对鸦片问题的认识相对“舆论一律”,官界的态度则较为复杂,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支持鸦片利益,而是就事论事者居多数,互相矛盾的言论自然不可避免。即便如官场中的一个特殊人物——禁烟名士许珏本人也不得不讲究禁烟行动的策略。“珏两年来疏陈请加洋土药税,未敢遽言禁者,因言禁则众必以为迂图,势将置之不问;言加税则尚有裨财政,或冀采用其说;又税重则价昂,贫民无力者或可略减吸食,此不遽言禁之一端也”。[13]这一言论中的“众必以为迂图”,较能反映出官界对鸦片问题的心态,鸦片税厘自从与中央、地方财政结缘后,依赖性便日益突出,此处所言“众”当然是指包括朝臣疆吏在内的各类官员,在鸦片税与财政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兀然提出禁烟的要求,的确是令多数官员难以接受的,所以有“不遽言禁”而以加税为禁烟的曲折言辞。光绪三年驻英使臣郭嵩焘连上两疏请求朝廷主持禁烟,朝臣的看法不一,公开言论且不具论,私下表态尤为重要。刘坤一的观点即大体反映了各方对鸦片税厘的倚重,十一月初在私人信函中说:“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顾据实直陈,必触忌讳,不如暂缓置议,想朝廷不再垂询。”[14](P1831)
民间人士的观察更为深刻,“今中国所急者财用,而厘税之人,以鸦片为大宗……国家之利赖在此,官府之调剂在此,若设舍此项,则补救无从,此所以禁烟之举,近年缄默无言也”。[15](P215)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态颇具普遍性,经国济世的情感与财税依赖的现实恰成矛盾,单纯的反鸦片言论反而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自难为当道者俯允采纳。从这一角度看,在“反鸦片世界”内部,舆论态度并非单一,铁板一块,诸多言论之间的矛盾的情形并不少见。但是环境一变,当新政逼迫与外人压力联袂而至时,禁政大义仍被官界和知识界所认可,直至推许为“新政第一要务”,罕见有螳臂挡当车之流。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反鸦片世界”不算勉强。
二、烟农与烟商
反鸦片禁政群体的内部情形更为复杂。从构成上看,烟农所占据的比例较大,各地土商、烟馆营业者以及外国鸦片商人等阶层绝对人数虽多,但比例并不大,鸦片收益成为这一世界藉以分润的主要来源。清廷尽管确定了十年禁绝鸦片的计划,但在事实上实行的却是缩短期限禁种罂粟、禁运和禁吸鸦片,时间上提前了七年有余,导致这一群体以各种形式奋起反抗,土商风潮与禁种风潮愈演愈烈。
烟农遍布全国主要省份,尤以产烟土较多的云贵川晋甘等省为多数。清廷实施禁政时首先从禁闭烟馆开始,这一举措数月之内即告结束,随后就向禁种罂粟这一最冒险的领域推进。对烟农进行“生计抵补”是与“财政抵补”同样重要的事情。各省禁种罂粟政策实行后,清廷言官中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建议提倡“种植生计为先”,否则,“贫民狃于故习,得不偿失,非但良懦者贪顾目前小利,不免有阳奉阴违之患;而强壮者必以禁种之后,势将无利可图,小则流为匪徒,大则陷于盗贼;况西北地方民情素称强悍,若再迫以饥寒,难免不遇事生风,借端滋事”。[16]这项提议不为无见,而鸦片经济已经成型,数量庞大的人群赖以营生、活命和缴纳税款,短时期内实现种植抵补的目标谈何容易!
多年以来,烟农已经与鸦片利益密不可分,鸦片与其他农作物相比,收益巨大,小麦和鸦片的利润之差有时可达80%。[17](P48-49)鸦片的比较利益实在太大,即使劝令改植他物,烟农仍多方抵制。四川省的情形尤为典型,“川省因鄂加烟厘,出示劝种木棉,势颇难行。小农贪种烟之利,鄂厘虽重,商贩不因而裹足,则鸦片行销自若。若加商贩之厘,不过重累食户,无涉种户,因无所惧而改图也”。(注:杜云秋:《复周雪池》,《黄陵书牍》,卷上,转见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文献校勘的标点有误,此更正。)这类抵触情绪事出有因,除了比较利益较高以外,它还可以用来缴纳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宣统年间川省某些州府的捐税数量高于正粮税率的十几倍;[18](P150-152)涪陵地区烟农的鸦片收入除了缴纳这些捐税外,尚有剩余,用以购买生活必需品、馈赠亲友等项支出,“其一切捐纳、宾馈、薪盐零杂之需,多取给予售烟之资,故皆贪种罂粟”;(注:贺守典、熊鸿漠:《涪州小学乡土地理》,《涪乘启新》,卷1,第28课,转见秦和平前揭书第438页。)贵州的情形与此类同,早在19世纪80年代时贵州巡抚李用清就发现,“黔省跬步皆出,舟车不通,向来农有余粟,无处运售。自种栽鸦片以来,变为轻货,便于交易,地方较为活动”,[19](P5351)交通困难促使该省鸦片业兴起,并逐步获得发展。宣统年间,云贵总督依然发现烟农与罂粟利益的结合十分牢密,“上游则通衢大路,以至穷乡僻壤特种烟为恒产者,几于比户皆然,是以每届收获之时,常有东南商贩集合巨资来黔,购运挑载,络绎不绝于途,民间岁获厚利,通省动以数百万计”。[20](P544)这位总督的另一份奏折也谈到罂粟对当地人民生活和财政的重要性。[21]在缺少可以抵补收入良策的情况下,缩期禁种的决策无疑是导致烟农暴动最主要的原因。云南某些州县在缩期禁种罂粟时,烟农颇有意见,知府也认为抵补措施乏力,“查州属自禁种洋烟后,粮价大平,大害虽去,大利亦失。民情异常困苦,市集顿形荒凉。多有归咎于知州劝禁过严者。众口沸腾,民交谪庸人无远识,可为太息。惟物力艰难,系属实情。欲急筹抵补之法,舍赶办蚕桑,别无善策”。[22]该省率先实行缩期禁种,其善后问题当较他省更为窘困。罂粟被禁种以后,农民所遭受的打击,有人描述说,“从前川民种烟之进款,岁入四千余万,今烟禁綦严,种者寥寥,计去年岁入仅一千万上下,以致川中奇窘,民不聊生,群起为盗,劫场劫村之案,日有数起”,[23](P78-79)后果极为严重。川黔滇省如此,他省窘绌程度或有不同,但均面临抵补困难。在各地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仅有的振兴农政业绩也被抵消殆尽,短期内的禁种罂粟行动预示着烟农反抗鸦片禁令势所必然。
烟商是反对鸦片禁政中另一个阶层,也是与鸦片利益更为密切的一个阶层。鸦片战争前后,介入鸦片生意的人,几乎遍及各个阶层,除了一般的商人以外,另有军人、胥吏、官吏、宗室、太监等等。[24](P113)至1906年以后,介入这一领域的人群更加庞杂。英国等境外鸦片烟贩、国内形形色色的鸦片烟帮,尤其是与洋药贸易有关的潮州帮和广州帮等更是颇具声名。随着鸦片经济形态的发展和形成,介入这一行当的人越来越多,土商、洋商以及烟馆商人等从中赚取利润的数目肯定是极为可观的。张仲礼和陈曾年认为,仅在1907年至1914年短短的几年中,沙逊集团在中国贩卖鸦片中所得利润,就在2000万两以上。[25](P28)1905年主管川省土药统税的蔡乃煌说,“去年行商贩土,万金之本可获六千金之利。弟督办川省土税,调查最确,贩土巨商粤人、鄂人各居其半”。[26]由此可见,鸦片贩销颇具暴利特征。随着禁政推行,洋土药越来越少,价格飙升的情形更甚,(注:根据《北华捷报》1916年等报道,认为,“在沙逊等集团操纵之下,鸦片价格从禁烟协定前的每箱平均700两左右,到1913年上升为每箱平均5950两,1915年11月竟达9012两,达到最高峰”,见张仲礼前揭书,第27页。)其贸易利润可能更大。一旦清廷实施缩期禁烟,烟商暴利势必付诸东流,对抗行动自然纷至沓来。
禁烟实行初期,清廷采取首先禁闭烟馆的政策。各地官府与鸦片烟馆经营者的矛盾首先产生。上海烟馆业对上海道限期禁闭的饬令颇表不满,纷纷集议要求推展缓期。[27]江宁财政局因烟馆捐税欠缴甚多,连日派员清查,各烟馆眼看就将禁闭,拒不缴纳,并要求展缓半年后再议禁闭,聚议者多达3000余家。[28]苏省土商和烟馆商人更是态度强硬,对官府既加征捐税又限期闭歇的饬令抗议不遵,并开会聚议要挟官府。其中,广帮、潮帮土商由于有洋人作靠山,更是屡屡呈递禀辞,坚请缓行加税,延长禁闭时间。[29]后来各地筹议官膏专卖,土商仍加阻挠,湖南土商奋起反对该省的专卖计划。[30]苏州的广帮和潮帮土商为反对专卖,特意勾结英国驻沪总领事,干预该省专卖行动。(注:分别参见“英领又请停办官膏”,《申报》1907年12月24日;“面谕勒闭土膏各店之抗议”,《申报》1910年5月1日;“各土店罢市要挟原来如此”,《申报》1911年3月26日;“分期禁绝鸦片之反动力”,《申报》1911年5月5日等。)在土药统税征收过程中,陕西土商为了对抗统税制度,绞尽脑汁设法偷漏税款,其采取的办法十分巧妙:
将土药浓煮成膏,掺和为料,日晒极干,捻为细条,按寸截断,用口皮卷紧,复加皮纸包裹,名曰烟棒,每一烟棒约需净膏二三分,售钱十余文、二十余文不等,行销南北二山及山西蒲解等州,为数甚巨,实陕省本地销土第一大宗。[31]
希图漏税是鸦片商人对抗官府的主要形式。这类对抗有些是明火执仗闯越关卡,有些则绕险越阻暗中抵制。川省是缩期禁烟执行较为严厉的省份,1910年6月份总督赵尔巽决定将本省境内的存土一律限期运出省外,引起鸦片商人的不满和恐慌,众商滋闹扰乱,群起鼓噪,数省鸦片商联名禀请宽限时限。重庆商务分会在土商围困下,不得不电致总督、藩司和劝业道,请求宽限出境。[32]次日,赵尔巽研究后作出答复,准予宽限三个月,此后必须出境。缩期禁烟迫使鸦片价格飙升,[33]因而土药商人借贷巨款作孤注一掷之投机,适逢严令外运,土商叫苦不迭,得到川督宽限三个月的消息后,“商民感激,市面帖然”。实际上,土药商人届期仍未运出川境,该省只得设立烟土公行,收购后在此储藏,纳税后货主可以自由运出。由于大量收购烟土,致使该省银根严重吃紧,并且大量的白银外流严重,导致布匹资金甚为缺乏。[17](P316,323)1911年是禁烟的关键时刻,土商与洋商勾结,英国驻华使领人员成为鸦片商人兴风作浪的保护伞,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又掀起更大规模的风潮,只不过清王朝快要消亡了。
鸦片消费者的情形则较为复杂,既有顺从鸦片禁政令者,亦不乏敌视清廷谕令、阳奉阴违阻挠禁令实施者。换言之,吸食者间跨两个“世界”,很难明确地加以区分。总括两个“世界”的概况,可以看出,双方对待禁政的态度截然相反。官方与知识界乐观地预测了禁烟所带来的美好前景,对缩期禁政倍加支持,立论的基石仍旧是道义与现实的需求,或者还要加上外力的逼拶;而与鸦片利益密切相关的烟农和烟商,则是力图保有既得利益,在清末经济匮乏背景下,一旦眼前的鸦片利益严重受损,即不惜与官府对抗,最终演成规模不等的禁政风潮。
三、肇乱情势与朝野反应
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驻英使臣薛福成断言禁烟之事不可草率,“惟事体关系较重,非到机缘十分凑拍,究未敢轻于发端”,[34](P440)禁政决断之难可见一斑,“未敢轻于发端”一语实有多种含义。禁烟真正实行后,抵补维艰,烟商和烟农极易产生阻力,如何应对颇费周折。这一点被1906年以后的禁政实际情形所证明,烟商与烟农的确是阻力重重,变乱四起,风潮迭见,1910年后达到高潮。根据所见材料,(注:目前所见到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张振鹤、丁原英两位先生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和第4期发表的《清末民变年表》一文。作者根据《宣统政纪》、《东方杂志》、《中外日报》、《时报》、《汇报》、《大公报》等报刊杂志汇录了1902至1911年关于禁烟激变等有关材料,这是本文依据的主要材料之一;另外,《申报》、《盛京时报》等清末大报也有关于禁烟激变的大量报道,本文也将根据这部分材料进行分析。)下面将扼要探讨禁烟肇乱在1906年以后关于发生频率、地域分布、罂粟种植者与鸦片贩售者变乱比较以及变乱肇因等方面的问题。
1906年之前,由于各省对鸦片税厘进行整顿,各地纷纷增加土药、烟膏税捐,反对鸦片税捐的事件开始出现。1906年以后此类因税捐加重而引发的风潮更加严重,同时随着禁种、禁吸进程的加快,烟馆商、土膏商和烟农抵制禁政的风潮次第增多,频率增大,在地域、年度上呈现出密度和规模逐渐增加的趋势。如将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作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此前的风潮主要属于对抗清廷的鸦片税捐,其后爆发的风潮则大部分属于抵制禁种罂粟的行动。
根据各种媒介和官方记载,全国在190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各地发生的对抗鸦片禁政的事件共计67次,(注:有关统计甚不完整,就报纸报道而言,有一些规模较小,或者是类似对抗的事件并未收入,实际发生的商民、烟民对抗官府禁烟的事件,其总量恐怕远远高于这项统计数字。另外,因鸦片禁政推行,各种禁绝措施各不相同,导致吸食者购买烟膏困难,因而这一阶层也曾有过与官府为敌的记载,该类事件亦未收入。)其中,1906年和1908年各3次,1907年达14次,1909年6次,1910年为27次,1911年大半年时间也达到14次。1906年和1908年次数较少的原因,主要是禁种罂粟和税政苛扰两个主要乱源并不突出,禁政的力度较弱,所以肇乱次数较少;1907年则是各省禁闭烟馆行动较为集中的时期,鸦片商人屡屡对抗,因而惹致的风潮较多;1909年则是由禁政低潮向高潮过渡的年份,肇乱次数明显开始上升;1910年至1911年正好处于禁政高潮时期,各地在禁种罂粟和捐税整顿上均采取或激进或“寓禁于征”的做法,故引致的变乱陡然攀升。
在地域分布上,涉及的省份明显比禁政之前增多,由于罂粟种植和鸦片贸易消费的省份大部分集中于南方,所以乱源也就主要集中在南部省份。其间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云贵川晋陕甘六省是当时种植罂粟最多的省份,其因禁政而引致的变乱为18次,仅占禁政激变总数量的26%稍多一点,比例并不大。究其原因,主要的还在于地方禁政措施和方法相对较宜,民风民情的温顺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较而言,暴乱较多的省份主要是江浙地区,其中浙江一省肇乱次数多达19次之多,占总变乱量的28%还多;江苏一省也有8次,几占11%。这两个省份的情形又有不同,江苏省是鸦片消费大省,地方财政与鸦片税捐关系密切,因而土膏商抗议官府鸦片税政方面的风潮较多;而浙江省官府的禁政手段和禁政人员的禁政方式较为粗鲁,温台等处民情强悍屡屡为媒介所揭示,(注:葛庆华著《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一书对地方民情凶悍的情形亦有明确的揭示。)所以风潮主要表现为烟民抗拒禁种罂粟。其余各省情形颇不一致,而禁种罂粟导致的变乱在总体上占多数。在抵抗官府的方式上,烟农反对的手段主要是以武力对抗的方式,各村联合,规模多数较大,数万人反抗铲烟的行动亦不少见;地方官府的镇压力度相对较大,出动军队镇压的情形比比皆是,军事干预是禁种罂粟的最后手段。而鸦片经销者反抗官府的行动多集中于城镇,在与官府交涉不成后,一般选择抗议和罢市两种方式,武力对抗的情形基本上不存在。两个阶层由于采取的反抗手段不同,官方应对的手段也有区别,由此所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烟农在风潮过后,被武力镇压者居多,较多的反抗者被枪杀或被击伤的程度较重,不但罂粟被禁止种植,人身且受到摧残,代价高昂;相对而言,烟商采用温和的对立手段,损失的一般是经济利益,生命安全不至于受到严重的伤害。
1906年禁政决断之后,朝野一般的看法系采取渐进禁绝的办法,[35]希望在十年之内渐行禁绝,罂粟减种的期限定于九年减尽,最后一年查勘善后,并未设想后来采取的激进方式。万国禁烟会在上海召开是禁政进程的转折点,外人的压力成为禁政加快的重要原因。有人评论说,“近时所稍有起色者惟禁烟一事,扣其所以然,则外国人实为之迫促也”。[36]参加上海会议的国家对中国的禁政颇为关注,英国且软硬兼施,一旦中国按照计划实现禁烟目的,英国将派出亲王来中国祝贺;若届时达不到既定的目标,英人将几年的损失加三倍由中国偿还。(注:1908年夏季,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外务部:“据驻华各埠领事调查报告,洋药销路有增无减,皆由禁烟之令不严,将来印度入口洋药分年递减,转瞬十年,倘各省禁烟临时并无成效,虽现在未定罚约,必须照从前入口洋药每年最多之数,由中国按年赔偿”。代理日使也照会中国:各省禁烟不利,多半敷衍,必须重申禁令,以免十年后鸦片不能禁绝,英必索赔历年之损失,恐中国财力难以支持。禁烟大臣得知此事,决计从明年(1909)起,无论何省,一律禁止栽种罂粟,实行强迫命令,并电请端方转催驻沪各国领事,饬令租界居民报领吸烟执照(见“禁烟纪闻”,上海《外交报》,第221期,1908年9月20日)。但是,随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则对违约赔偿一事矢口否认,见“札行禁烟误造谣言请速行更正文”,吴剑杰主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从此之后,以云贵总督锡良要求缩期禁烟为契机,各省纷纷决定加快禁种罂粟的步伐,在种植抵补措施尚不到位的情况下,断然禁种罂粟,甚至是将已经出苗的罂粟予以铲除,断绝烟农的主要财源,双方的冲突必不可免,官方与烟民对立的局面由此形成。洋土药税厘与各项新政事业多有关系,中央和各省绝不愿放弃任何一个搜括的机会,对土药烟膏税收的整顿并未随着禁政开始而稍有减轻,各地官府将烟膏加税、凭照捐、牌照捐作为“寓禁于征”的措施执行得更为充分,由此导致烟商的对抗也越来越多。随着鸦片价格的不断攀升,官商之间对鸦片利润的争夺更趋紧张,官府的每种搜刮,时常引起鸦片商人的抗议、罢市、示威风潮,这类事件的频率越来越高,至1909年后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官商之间的对立局面由此形成。
清廷对禁烟激变的反应和态度十分矛盾,既要加快禁政步伐,又要避免民间抵抗,如何贯彻禁烟大计确有其难。1910年春天山西文水等县发生烟民对抗官府的风潮,军队介入后,民众死伤较多,酿成晚清禁烟史上著名的惨剧。有关处理这件事的谕旨说:“朝廷于禁烟一事,志在必行,此次该省酿乱,始由于地方之查察不利,而统兵官亦未能审慎办理,故予以处分。至于民间种烟,希图驰禁,胆敢聚众抗官,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自应严加惩治。嗣后仍著各该地方官严切查禁,毋稍懈弛。”[37](P8102)清廷采取的策略是各打五十大板,不偏不倚。1910年5月份,禁烟大臣也电致各省督抚,要求调查禁烟“贵劝导而不贵勒逼”,“近来各省多有因调查禁烟致启冲突大祸者,此虽由于民俗之蛮野,而其中之勒诈肆求情形在所不免。应即严饬各属所有禁烟各政,务宜谨慎从事,勿得再启风潮,致干参处”。[38]其实,真正有效地贯彻缩期禁种,难度之大是清廷难以想象的,既要实现禁烟目标,又不许产生风潮,更不许选择军事镇压的手段,这不啻是给地方督抚出了一个难题。在鸦片价格猛涨、利润率加大的背景下,禁政推行的难度可以想见。[39]因官方操作不当致使烟民变乱的情况在在皆有,但大多数情况下,事先劝谕,广为宣讲这些工作,各地官府还是较为认真地实行过。官督绅办、官促民办等保障措施也曾在各省实行。风潮发生有其内在的因素,诸如民众与鸦片利益结合的程度、执行禁种罂粟的具体季节和时机、地域民风民情与官府一贯的态度等等,皆不可忽视,这些方面的困难短时间内极难克服,禁政激变随之而来。
依赖罂粟利益与民风骠悍使得地方官员难于措置,这是各地选择军事手段的一个背景。浙江巡抚鉴于本省禁政阻力尤为巨大,特拟具专函称:“如有莠民暴动等事,准由文道等调遣军队,协力相助,并准酌带随员一二员,薪水川资核实开支;所有巡警道派往温、台各府属查禁烟苗。”温州、台州两属民情汹汹,抗拒尤烈,该巡抚特意嘱咐:“温、台州府属各县合同该府及防营统带,督县切实禁绝,务期尽绝根株。”[40](P540)即便实行军事手段配合禁烟,该省依然风潮连连,禁政后期充满了血雨腥风,成为禁政肇乱最多的省份之一。
禁烟过程中即使血雨腥风,风潮迭起,知识界仍旧呼吁清廷断不可因肇乱而放弃禁种的努力,称其为“禁烟最要之关键”。[41]对于禁政激变,知识界人士态度复杂。总体上是批评烟农阻碍禁种,巧于弥缝,迫使官府不得不搜查督催。对山西禁政激变,有人评论说,“报纸之所以归罪于官场者,非罪其禁烟也,乃罪其惨杀劫掠也”,留心时务者分析说:“迄今而犹未能戒净者,则皆罢钝无耻之尤也,百计千方,以从事于弥缝之术,其术愈工,害乃弥甚。于是有禁烟之责者,乃不得不从事于搜查,此即骚扰之所由来也。”[42]论者对地方官员鲁莽铲烟,无端需索,糟蹋百姓当然也深表不满,有人专门评论此事说:“禁烟而拔罂苗不得已也。乃至脱老妇之裤,而用非刑调笑少艾(女?),而肆其淫掠,如此而犹不激变者,五洲万国未之闻也。”[43]还有人认为禁政激乱的真正原因不在官员的操切和鲁莽,而在于地方政府“筹措苛碎之捐而酿成暴动”,这种说法似乎是针对烟商肇乱而言,而对烟民聚众抗拒禁种罂粟的问题,论者在严厉指责的同时,也对官府的激进行动表示理解,认定禁种罂粟过程中,有效的办法仍是严厉查禁,苛扰必不可免,“搜查取缔及铲除种苗,皆为从事禁烟者必经之手续”,否则就是敷衍了事。[44]知识界批评的是某些具体的肇乱实例,而清廷禁烟的大政方针却始终为各界人士所拥戴,这是清末少有的一个例外。
鸦片禁政系清廷着力推行的一大善政,符合社会道义和社会进步之需求。清廷由依赖鸦片税收转而作出禁绝鸦片的政策,显示出旨在改革社会弊端的决心。知识界人士对鸦片禁政则寄予各种积极意义,将禁政运动与国家振兴、民族兴衰以及祛除民族劣根性联系起来,视鸦片禁政为新政改革的基础。反抗禁政风潮的成因较为复杂,揆其大端,比较利益、种植抵补、官员鲁莽以及民情凶悍等均属要因。表面上看,禁政激变是民间力量对抗清廷的“起义”,近人治晚清史,或立足于革命,或着眼于清廷腐朽,常将禁政激变与其他类型的民变相提并论,认定两者在主观上均构成推翻清廷的政治因素,以此证明辛亥鼎革或清朝灭亡的必然性。然而细究开来,禁政激变恰恰揭示出清廷“正确”政策在特殊时势所遭遇的抵制,民间这类“抵制”也的确具有十分充足、“正确”的理由,笼统地将其定位在推翻清王朝的正义甚至是革命性运动,反而遮盖了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含义,历史信息的解读必定陷入偏狭。类似的述学和研究承担了太多的政治责任,妄加品评,反失其真。
收稿日期:2003-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