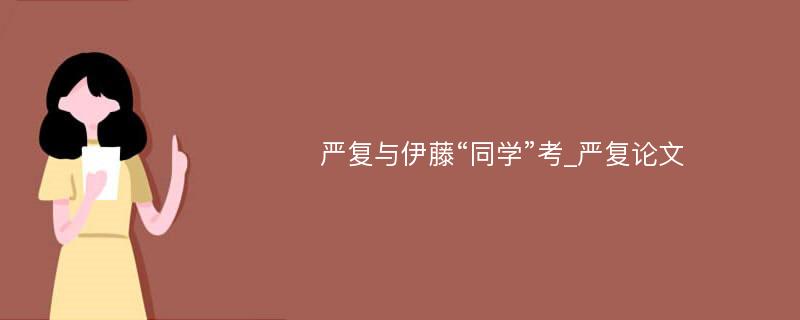
严复、伊藤博文“同学”说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藤论文,博文论文,同学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7—0037—10
清末民初,有关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留英时同班同学、回国后际遇大相径庭的传闻开始出现。该传闻最早可能见于官场②,但内容十分模糊。严复去世后,陈宝琛所撰《墓志铭》也提到:“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1](p1541)
1930年代后这条传闻成了信史,多家史著详略不等地沿袭此说,③ 其内容和细节在传播过程中也愈益翔实丰富:留学期间严复考试名次屡列伊藤博文之上,但两人回国后待遇大相径庭,前者备受冷落,清政府仅派一小官到码头接他,所任职务是福州船政学堂教员,使其富强祖国的大志不能实现,终日闷闷不乐,借抽鸦片消磨时间;而伊藤回日本时,天皇亲自前往码头迎接,让他担任首相要职,领导日本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因此富强,并以小小三岛打败了老大中国。严复的“同学录”也相继增加了日本近代政坛另一著名人物大隈重信,以及威震世界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虽然数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此说错误④,分析之所以形成并广为传播的原因⑤,但在大众传媒中仍时时再现⑥。近些年更藉网络迅速广泛流传,赫赫有名的近代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也加入了严复同学的行列。⑦ 不过,该传闻的萌生时间及始作俑者始终很模糊。
1990年代严复一些未刊书信渐次面世,其《致梁启超》一函中,严复自称留英期间曾与伊藤博文同学,但回国后的待遇,命运大相径庭。该函收入了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编《严复合集》(五)[2](p88)。与此同时,马勇先生依据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档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缩微胶卷,整理、刊布了59通《严复未刊书信选》[3](p90—93),其中“严复与梁启超”书,即《严复合集》(五)所收。孙应祥先生《严复年谱》全文转录该书札,认为“系伪作”⑤;稍后,《〈严复集〉补编》“附录三”有专文考辨[4](p384~393)。皮后锋先生赞同“这封所谓的严复致梁启超书是一份矛盾百出的伪作”的结论,但未详细分析[5](p59,p60注释2)。这些资料的刊布考订推进了严复研究的深广度,但仍有一些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进一步探讨。
一 史料差异
《未刊书信》与《合集》所收“严复与梁启超”书均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卷”,内容基本相同,显然来源为一⑨,仅点校、出版者不同而已。但二者互校,却有多处文字差异,点校者标示的写作日期也不一致。由于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先将言及“严复留英期间与伊藤博文同学”的《未刊书信》第53通〈致梁启超〉以及《严复年谱》转录的〈一、致梁启超·一〉⑩ 全文录人,对比其差异(分别以下划线标示),书信格式、页码、标点以及孙先生考证、注释的编号完全依据各原书。
A.见之于《年谱》者:(11)
〈一、致梁启超·一〉(11)
任公吾弟伟鉴:
返乡后得手教为之叹者再。(12) 兄与尊况大同小异,有何可称道者! 时势如斯,吾辈书生有何能为?忆惜居英伦时,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13) 各与国事皆有同感,然伊公回国后,所学竟成大用。而[ ]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11),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相形之下,彼此何悬殊之甚耶?吾弟负经国之才,抱救国之志,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继虽登论坛高座,然曲高而和寡,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是二人之际遇正复相同也。兄老矣,而弟正当年富力壮之时,私必其扬眉吐气者有日,固不可以目前悲欢,介介于怀,幸勉其前路耳。专布下忱,惟万千自卫。
兄复再拜
B.见之于《未刊书信》者:(12)
53.致梁启超
(1915年7月初)
任公吾弟伟鉴:
返都后得手教,为之叹息者再。兄与尊况大同小异,有何口遵之者?时势如期,吾辈书生有何能为?忆昔居英伦时,与日人伊藤博文氏同窗数载,各与国事皆有同感。然伊公回国后,所学竟成大用。而吾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都首次晤面即遭冷遇。此后[ ]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相形之下,彼此何悬殊之甚耶?吾弟负经国之才,抱救国之志,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经[今]虽登论坛高座,然曲高而和寡,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是二人之际遇,正复相同也。兄老矣,而弟正当年[ ]力壮之时,私必其扬眉吐气者有得。固不可以目前悲欢,介介于怀,幸勉其前路耳。专布不忱,惟万千句卫。此颂台安。
兄复再拜
两函的标点不同或可不计,仅从文字看,其差异至少有14处。笔者未见原件,仅以两书刊布的文字为依据,分析、比较。
1.信函日期。《年谱》采纳了《合集》编者的观点,“似作于1910~1911年间”,《未刊书信》则确定为“1915年7月初”,但都没有说明理由。(13)
2.首句。《年谱》:“返乡后得手教为之叹者再。”《未刊书信》:“返都后得手教,为之叹息者再。”
其中“手教”后虽以有逗号为佳,但没有也无大碍;关键是“返乡”还是“返都”。“乡”指严复故里福建阳崎,“都”,首都北京。寻常情况下本无所谓的“返乡”或“返都”,因涉及写作日期及严复思想、行为的判定而重要了(详后)。
3.第二句。《年谱》:“兄与尊况大同小异,有何可称道者!”《未刊书信》:“兄与尊况大同小异,有何口遵之者?”
有三个字不同,从上下文看,似乎《年谱》更合理些。
4.第三句。《年谱》:“时势如斯,吾辈书生有何能为?”《未刊书信》:“时势如期……”
以该信日期看,若写于1910~1911年间,新政、立宪、国会请愿、革命党起事、各地民变、会党造反、水旱灾荒、东北鼠疫……层出不穷;若写于1915年,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紧锣密鼓筹划称帝、各派争权夺利……无论哪个日期,中国都处于经济危机、民生困苦、政局动荡、内忧外患并起的状况。读一读严、梁此时的其他书信、文章,不难看出,此种局势绝不是他们期盼的。
5.第四句。《年谱》:“忆惜居英伦时……”《未刊书信》:“忆昔居英伦时……”从句意看,当以后者为准。
6.第五句(两处)。《年谱》:“而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未刊书信》:“而吾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都首次晤面即遭冷遇。”
严复长梁启超19岁,“兄”是自称,称梁为“弟”、“吾弟”,“吾兄”显然不通。“督部”与“督都”也有疑问。中国官制史上有“都督”,多指领兵将帅或地方军政长官。清代虽无正式的“都督”名称,但因总督领兵,常以之称;也作“督帅”,或省称为“督”。笔者未见原函,无法判断孰是孰非,但这两个词在《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和目前最具权威的《汉语大词典》[6] 中都查不到,不知汉语中是否存在,抑或皆为生造词?
7.第六句(两处)。《年谱》与《未刊书信》有“以后即始终寄人篱下……”和“此后始终寄人篱下……”的差别。
8.第七句。《年谱》与《未刊书信》分别作“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继虽登论坛高座”和“初遭时忌而流亡海外,经[今]虽登论坛高座”。
此句说梁启超生平。从文意看,“初……继……”十分通顺;“初……经[今]……”虽然能说通,但从通常写字习惯看,“今”多于字型相似的“令”字等混淆,写成“经”极为罕见,而“继”与“经”的繁体字字型(継、經)相似。手写书札潦草,或许点校者识为“经”后,感觉句子不通、原文有错,而以[今]字补。
9.第八句(两处)。《年谱》:“而弟正当年富力壮之时,私必其扬眉吐气者有日”《未刊书信》:“而弟正当年力壮之时,私必其扬眉吐气者有得”。从文意和汉语语词惯例推断,两处都可能是前者准确。
10.末句(两处)。《年谱》:“专布下忱,惟万千自卫。 ”《未刊书信》:“专布不忱,惟万千句卫。”
“下忱”,谦词,在下(我)的心意、诚意。布,宣告。若作“不忱”,岂不是公开告诉收信者,我特地宣告虚情假意,所说都是谎话?
“自卫”和“句卫”似乎都有疑问。无论中外古今,友朋函札的末句多为问候语,这是友情,也是礼节;讲究等级、礼仪的国人更是严格依照上下尊卑以及请示、请安、庆贺、问候、吊唁等不同场合而使用不同的敬语、谦词,严复也不例外。从王栻主编《严复集》(三)和《近代史资料》第104 期所收数百通严复致友朋书札看,除少数残缺不全以及致家人、挚友的部分信函外,绝大多数都有时人常用的“敬颂箸安”、“即颂台祺”、“谭寓万福”、“千万自爱”、“为道自爱”、“近祉”、“冬安”、“撰安”、“岁祺”、“旅祺”、“安吉”、“节哀珍卫”等问候语。即便给夫人朱明丽和子女侄甥的信,也有诸多“举家安好”、“闺福”、“自行珍重”、“珍卫千万”等问候语,但没有一函以“自卫”为问候语。该处或为特例?
“句卫”,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皆无此词,未解其意。
百年前的信札文字是时下称呼的繁体字,不仅有楷体、行草、狂草之别,还有大量在今日生活中已消失泰半的通假字、异体字,且系手写,每个人的字体、笔迹大相径庭,非熟识,难以辨认,以致古籍点校中常有“鲁鱼亥豖”的笑话。上述这些差异,不知系严复本人笔误,还是点校者错识。
二函件写作时间、真伪以及严、张晤面等问题
《合集》〈一、致梁启超·一〉函后有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卷。以下两函同。此信未署年月,似作于1910~1911年间。时严复被任为资政院议员、海军协都统,而梁启超仍流亡,清廷不予赦用”[2](p88)“此信未署年月”应是对该资料实际状况的描述,但没有解释推断为“似作于1910~1911年间”的理由。《未刊书信》则将该函写作时间明确为1915年7月初,也未说明理由(14)
孙应祥先生采纳了《合集》的说法,认为:“严复自1893年后,一直到1918年才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次年北上后,曾满怀深情地撰《怀阳崎》一首,中有‘不返阳崎廿载强,李垞依旧挂斜阳’句。可知‘1910~1911年间’严复并无返乡之事。此函所谓‘返乡后得手教为之叹者再’,纯属子虚乌有。”并考订:一、“严复与伊藤博文既非同窗,也不是什么前后校友。”二、“严复于1879年8月14 日后离英回国,约9月底回到福州,即至母校任教习。时张之洞任左春坊左庶子,系五品京官。两人一在北京,一在福州马尾,怎么可能‘晤面’?1880年8月, 严复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时,张之洞仍系五品京官。1881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 兼礼部侍郎,但还未官至‘督部’。不久, 他又离京赴晋任巡抚。 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十日’先生与陈宝琛书, 谈及甲午战争中张之洞‘想必有一番经纬’时,还乞求陈‘为之介(绍)’。可知他们从未交往过,怎么会有此函所云‘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之事呢?”(15)
孙先生依据“严复自1893年后,一直到1918年才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史实,得出“1910~1911年间严复并无返乡之事”的结论,笔者非常赞同。然而《未刊书信》的出现,使“返乡”还是“返都”有了新的探讨视角。
汉语中“返”的主要词意是“回归”,所以,“返乡”、“返都”、“返国”等都指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或者故里。戊戌维新期间及20世纪初,严复多次往返于京津沪,因此时长住天津或上海,书信、日记中皆称“入都”、“返津”、“返回”。(16) 其友朋、长子严璩及后人文著亦如是说。(17) 1909年,严复任审定名词馆总纂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谘议官等职,“寓宅已定顺治门内石驸马大街海军处间壁”[7](p748)。表述基点旋即转换为“告假出京”、“前往天津”,(18)、 “由津回京”、“由京赴津”,[8](p1495,1512),等等。由此也知1909—1911年间严复离京外出十分频繁,完全可以“返都后得手教”。
1915年严复仍居北京,虽有宪法起草委员会、筹安会等虚虚实实的活动,但健康状况日下,“肺疾缠绵,几于闭门谢客,不关户外晴雨”[7](p628), 离京与返都的次数、时日皆少。因该年严复日记缺失、信件保存不完整,各家年谱对是年行止的记述都不详。但作为社会贤达,不排除偶尔离京、“返都”,并给梁启超写信的可能性。
由此,在重新识别“返乡”与“返都”前,不能以之作为该通〈严复致梁启超函〉真伪的依据。
其次,函札真伪及书写日期,还得从收信人的言论行止考察。
此函中,严复从自己“返国后……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与梁启超“负经国之才,抱救国之志……虽登论坛高座,然曲高而和寡,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是二人之际遇正复相同也”的角度着眼,惺惺惜惺惺,劝慰梁启超。显然,此时梁氏应处境不佳、心情郁闷,方有是说。
戊戌维新期间,初露头角的梁启超曾“深受严复论文和译作的影响”,甚且一度“倾向于严复而背离了他的老师康有为”[9](p43~44)。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与严复保持了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1909~1911年梁氏仍居日本,以读书、著述、办报为主。虽然党禁仍在,但得到日本政府保护,清廷无可奈何,与地方及中央权贵亦无具体的个人恩怨。光绪、慈禧驾崩后,梁启超、康有为相继上书摄政王载沣、肃王善耆等,积极开展倒袁世凯的活动,袁氏也多方中伤康梁,结局却是袁奉命回籍“养疴”,其间关系不言而喻,“执事诸公”似无视梁启超为“眼中钉刺”的必要和可能。此一时期,梁氏信札、文章的主题也集中于宣统继位后的政局以及宪政、国会请愿、财政危机、资政院、谘议局、铁路国有,以及武昌起义前后的政局等方面。虽“生计狼狈”、“年来贫彻骨”,甚至“不名一钱久矣,并借贷之路亦殆绝,数月以来,节衣缩食,断粮时时而有,妇女首饰尽行典当”,但整体而言,“心境泰然,其乐乃无级也;”并自信,“吾辈十年以来,未尝敢以同志一文之血汗,自人私囊,而弟尤恃笔耕,自食其力,并未尝以家之计用一文公款,此则可以表天日者耳。”(19) 精神、气质依然振奋昂扬。从外在环境到梁氏本人心态, 似乎都谈不上“曲高而和寡,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的状况。
武昌枪响,清廷开放党禁,起用袁世凯组阁,以梁启超为法部大臣,梁辞职未就。1912年11月梁启超返国,宾客盈门,“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地方官纷纷宴请,应酬苦极”;“项城致敬尽礼”,“上至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吾一人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10](p65~652,653)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旋因各派争权、俄蒙协约案等项,“都中风起水涌”,“人才消乏,财政艰难”,“国势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吾性质与现实社会实不相容,愈入愈觉其苦”,以至“心力俱瘁……甚悔吾归也[10](p660,688,662,668)。但梁仍努力为之,“希望在可能范围之内有所展布”[10](p689.695.696等),“在各种计划均成空想”后,1914年7 月起不断请辞,“却求去不得”。或许在为国事、时局烦忧的同时,也牵扯了与“执事诸公”的个人恩怨,“执事诸公反以眼中钉刺目之”。由此,严复致函宽慰,亦在情理之中。
1915年8月,严复名列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梁启超则公开举旗反对,政见对立,两人关系急转直下。严复给熊纯如信中一再痛斥康、梁师弟是甲午、戊戌以来变故的“祸魁”,“亡有清二百六十年来社稷者”;“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来,项城不过因其势而挺之而已……康、梁以下诸公为其积极”。甚至说“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8](p631~632.645~646,652~653,675),不可能再以挚友的语气写信。只是《未刊书信》明定该函为“1915年7月”,不知何据。
第三,严复“返国后,与香涛督部(督都)”是否晤面。
孙应祥先生认为:“严复于1879年8月14日后离英回国,约9月底回到福州,即至母校任教习。时张之洞任左春坊左庶子,系五品京官。两人一在北京,一在福州马尾,怎么可能‘晤面’?1880年8月,严复调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时, 张之洞仍系五品京官。1881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还未官至‘督部’。 不久,他又离京赴晋任巡抚。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十日’先生与陈宝琛书,谈及甲午战争中张之洞‘想必有一番经纬’时,还乞求陈‘为之介(绍)’。可知他们从未交往过,怎么会有此函所云‘兄返国后,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之事呢?”[1](p565注(20)
严、张是否“晤面”,的确是考订该函真伪的关键点。孙先生以他俩“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十日”前的活动以及张之洞早年履历为据,认为两人“从未交往”,不存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之事”。笔者非常赞同。然而,严、张的生命都延续到20世纪后,是该时期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之前没有“晤面”,绝不等于此后没有可能性。1879年张之洞仅五品小京官,1881年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确没有“官至‘督部’”。但1884年即升两广总督,1889年调湖广,还曾代刘坤一督两江。即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看,也已官至“都督”整整十年。
笔者认为,虽然迄今未见明文记载,但从现存史料判断,1896年春严复与张之洞有通过他人传话介绍后“晤面”的可能。此时淮军各部已一败涂地,花费数千万银两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国人大愤,谤言四起,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有“李莲英与合肥换帖”之说。[12](p503) 北洋中人亦受牵累。 严复急于脱离是非之地(20),致陈宝琛信不断流露“仆燕巢幕上,正不知何以自谋,沧海横流一萍梗,祗能听其飘荡而已”[7](p498~499) 的情绪; 同时屡屡称道张之洞“素为公忠体国之人”,“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住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且关心其行止,“湖广张帅有何措施,走于此老慺慺之诚,□□无已,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还请陈宝琛转达劝张帅“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7](p498,502,501) 等建议。稍后又直截了当请陈引介:“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7](p502) 1895年10月中旬,严复同乡、密友、时任张之洞幕僚的郑孝胥由南京经上海转赴北京。抵沪当日,“严又陵来访,衣饰甚都,谈良久,与俱至雅叙园,饭毕而散。”(21) 以当时严复的言行推断,所谈应涉及其去留。显然,各方说项有一定成效,严复告诉四弟:“兄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22) 1896 年春更有年底“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23) 的信心与说法,并南下武昌(24)。但张之洞并不欣赏严复,“与香涛督部首次晤面即遭冷遇。”[3](p90),谋职南洋没有成功,自尊心大受伤害。从该年7月起,严复“在天津创办俄文馆,自任总办,并亲自拟订课程,聘请教员”[13](p8l~82),可见已放弃南行计划,决定在天津施展身手了。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也绝口不谈此事,外人无从知晓,仅于兄弟间的私函及这一时期频繁拜见督抚、亲王的活动中透露了些许蛛丝马迹。(25) 另一方面, 或许正因为“晤面”时的印象不佳,严复名满天下后,注重擢拔人才、喜好延揽名士的张之洞仍未青眼相看。
严复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但碍于张氏在世不便发作。1909年张之洞去世,严、张是否“晤面”、晤面时的情况已永远无法验证,张的声望、权势也不再构成威胁。因而该通〈致梁启超函〉无论写于1910~1911年,还是1914~1915年,十多年后重提此事,均有深意。
孙先生还提到常州市博物馆“收藏有20余封严复致梁启超、庄蕴宽……书,共20余函。致梁启超书也谈及与伊藤博文同学事”,不仅史实有误,“其字迹书法与严复真迹也相去甚远, 所用北京荣宝斋信笺, 经荣宝斋专家鉴定乃系严复死后的1925年所制,显系他人伪作。”[4](p381) 所以,此函为伪。
纸张、墨色、字迹的确是考订书札真伪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笔者曾数次打电话向常州市博物馆陈馆长及相关专家请教这批书札的情况,得知该书札系“文革”时收入,当时并未整理。后经北京专家鉴定为伪,约于1985年前后退回,目前情况不明。惜之孙先生没有说明所谓“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20余封严复致梁启超、庄蕴宽”信是否就是《严复合集》或《近代史资料》第104期刊登的“严复与梁启超、庄蕴宽书”;马勇先生也没有说明其所识读的“严复与梁启超、庄蕴宽书”是源于“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档案”还是“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缩微胶卷”,原函用何纸张,字体是否合于严复真迹,其中是否有从“常州市博物馆”转出者。若非同一书札,即便部分为伪,不能简单认定其它也为伪。笔者无缘得见原件,不敢乱下断语,甚望各位先生能重新校勘、鉴定,以嘉惠学界。
三 谁是该传闻的始作俑者
无论上述书札是真是伪,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的传闻毕竟出现了,且其萌芽、传扬的时间远早于该书札。换言之,即便书札为伪,也是在传闻的基础上作伪。当时船政局留英学生有十数人,其中不少比严复更优秀、地位更高,何以未见刘步蝉、林泰曾、罗丰禄等与伊藤博文“同学”的传闻?依据传播学原理,流言的始作俑者往往与流言所传达的内容密切相关,因而必须考察:谁是始作俑者?
1896年夏该传闻的模糊轮廓初现于官场,上奏的闽浙总督边宝泉是汉军镶红旗人,虽主管船政,但未曾出国,且多年任职于相对闭塞的陕西、河南等地,1894年始任闽浙总督,次年春到闽;与严复及北洋军人亦无甚关联,所奏之事应另有信息来源,这个人或者这几个人必须大体了解中国早期留英学生情况,并能将该信息传递至中枢。从当时情况看,与船政学堂首批留学生交往颇多、最了解内情的驻英公使郭嵩焘去世已5年,主管北洋的李鸿章虽知道1870年代有数百日本人在英国留学,其中包括“自治一国”的诸侯[13](p190),但具体情况不一定清楚;更何况,甲午战败,举国唾骂,1896年春又出访俄国,应无闲心与精力关心并传扬严复、 伊藤是否同学的消息。严的同学、同事刘步蝉、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萨镇冰、林颖启等人,非战死疆场即自杀于刘公岛,或因临阵脱逃受严厉惩处,都已失语。罗丰禄虽知情,但也因与北洋及李鸿章的密切关系噤若寒蝉。更何况,离了李鸿章,罗氏本人的地位决定了其言行还远不足以上达天听。
这样,最有可能者是严复与陈宝琛。
严、陈系小同乡,相交“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洽”[1](p1542)。严复提前回国后,经陈宝琛举荐,调往北洋水师学堂任教[14])(第一册),最高职务仅“总办”,人微言轻;当年不如自己、或至多比肩的同学,早已是远东最大最有实力的舰队的管带,相比之下颇有怀才不遇之感,且始终耿耿于怀。
陈宝琛曾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虽因故被黜,回原籍闲赋,但与朝中大臣及历任闽省督抚关系密切,能沟通上下。不过,他从未出国,不识洋文,与在华外籍人士亦无甚往来;虽与严复相交多年,但对其早年留学的具体情况不完全了解。甲午期间,两人都非常关心时局。任教北洋的严复可以说置身事外又在局中,屡以长函将战况告诉远在福建的陈宝琛[7](p197~501);旋因战败受牵累,灰头土脸,急于脱离是非之地,极有可能发几句中日学生都留学英伦、回国后境遇大相径庭的牢骚。由于此时张之洞、伊藤博文等均健在,不可能把他们牵扯进去。更何况,严复等人留学期间,确有二百余名日本人也在英国学习,虽然没有伊藤、大限等重臣,但也有小藩主[23](p183),该消息不能说全错。基于对国事、战局的关心及战败后中日地位倒置的愤懑、痛心疾首等共同情感,陈宝琛也有可能与闽省官员谈论战况、时局时,提到严复告诉他的信息,并有所议论;而后边宝泉又将此作为对战争及结局的思考和建议,写人奏折,上报朝廷。(26) 由于该奏折只是朝廷内部讨论时的一个建议,且所述十分含糊;并无社会反响。
1898年春末夏初,日本明治维新主持者之一、马关条约日方谈判代表、前首相伊藤博文即将来华访问的消息传遍京津沪。7月26日伊藤启程,经朝鲜仁川、 汉城等地,9月14日到达北京,19日谒见光绪帝。与李鸿章也有接触[16](p829 ~ 857.p108~116)。而后南下上海、武昌、南京等地。11月7日由长崎登岸,返回日本。
此时严复因《天演论》、《救亡决论》等文著已名满天下,且因参与通艺学堂工作,时常往来京津。伊藤博文抵京时,严复正在北京,14日觐见光绪,18日在通艺学堂演讲。如果他俩的确是同学,完全可以安排时间与20年不见的老同学会晤,谈论共读牛津、考试比肩等美好往事;何况伊藤博文已经辞官赋闲、非正式访华的日程安排也不紧张,理当十分乐意。即便没有时间,京津相距不远,早通火车,也可于伊藤南下时在天津晤面。更何况,此前就有人奏称《国闻报》虽归日本经理,而水师学生译报如故,应请饬查禁。然“劾报馆一层不过陪笔, 而实则劾又陵”[17](p1334)。朝廷派直隶总督王文韶调查。尽管王回护了严复[18](p447~448),但阴影犹存。严复觐见光绪时,两人所谈内容主要就是《国闻报》和严氏在报上刊登的《拟上皇帝书》,光绪命将该书“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19](p126)。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无论与私与公,严复都可直接说明他与伊藤博文是同学,使弹劾者立即闭嘴,从此不敢置喙。从另一方面说,《国闻报》曾刊登了严复反对俄国代保旅顺、大连的文章,沙俄“迭有违言”,不断向报馆施压,“虽屡行设法消弭,而终非持久之道”。不得已,夏曾佑等与日本驻华公使联系,利用日俄矛盾,“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17](p1330)。严复也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 求见老同学,请其出面说项,伊藤虽已下野,余威犹存;何况有危难找外国人帮忙,是当时的惯常做法(27),这不仅可以保护严复本人和《国闻报》,还可以保护与报纸有关的维新人士。
可是,这些都没有!
严复的同学多于中法、中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幸存者渐次凋零。至1909年,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张之洞等人相继驾鹤归去,带走了无数“经历”和“见证”,也使得留英时的“同学”或严、张“晤面”等情况永远无法查核。不过,伊藤访华时严复未能共叙“同窗情谊”,十年后再提旧事不免突兀,也难使人相信,而言论界骄子的社会影响和如椽大笔完全可以做到;三十余岁的梁启超不仅非常敬重严复,也无法洞察他出生前的事件。更何况,以劝慰梁启超的形式,将自己与“与日人伊藤博文同窗”的信息宣告于世,不仅合情合理,也更具可信性。于是,十多年前含糊其词的“日本同学”明晰了,“与香涛都督首次晤面即遭冷遇”可以抱怨了,各种细节更丰富了……由此,笔者认为,无论该函写于1910~1911还是1914~1915年,都有其内在合理性和可信度。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该传闻的“直接受益人”,严复从未公开或私下否定是说之虚。
严复去世后,陈宝琛应其家人请求撰写了《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一般而言,基于为尊者讳、为死者讳的文化传统,《墓志铭》常多谀词,以彰显其功绩、德行、词章、重要友朋。尽管严、伊同学说在坊间传扬甚广,但老于世故的陈宝琛仍然意识到,与伊藤相、大隈伯同窗共读是何等荣耀之事,但严复留英回国之初以及相当长时期内却从未言及,因而《严君墓志铭》仅含蓄地表示:“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对严氏初到北洋时的职务亦仅言“教授北洋水师学堂”[1](p541),而不是“总教习”。 这正是深谙朝廷规矩、官场惯例,又不得罪亡友、姻亲的高明与老道。(28)
皮后锋先生认为:“自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后,严复声名远播,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学界名流与教育权威,备受社会尊崇,与之有交往的上层权贵无不以宾师之礼相待。严复非常谦虚地承认自己‘浮名满世’,根本犯不着在晚年借口与伊藤博文同学来抬高自己的身价。”(29) 此说有一定道理。但“浮名满世”云云,可能客套多于真实。“中国国民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人治思想”的长期流传,社会大众固然是其“根本载体”[5](p6o),但同样影响并塑造了生活于该时代的严复,否则他就不必长叹“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四十不官拥皋比……嵚奇历落不称意[20](p361), 且始终讳言在北洋水师学堂所任课程和实际职称;还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希望换得文职,而不是“参将”、“副将”之类的武职,皆未果。不得已,“尽弃去”历数十年辛苦才从学生到教习、总办,“以海军积劳叙副将”的军职,回归旧有的升迁途径,“入赀为同知,洊擢道员”[1](p1542)。何况严复好名,亦非与伊藤同学一事也。 严复初到北洋水师学堂时担任“洋文正教习”,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后才升总教习(30)。1917年,池仲佑撰《海军大事记》,提到“(光绪)六年庚辰,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以严复为总教习”[21](p479)。池氏是后辈,不了解北洋水师学堂的早期情况,略有差池无可厚非。此时严复早已名满天下,海军“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前大总统黄陂黎公、今海军部总长同邑刘公”尚不过是其中“彰明较著者”[2](p477), 社会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为该大事记作序时,仍十分在意不足为道的早岁“职称”,默认其误,且藉此传扬,可见一斑。
林保淳先生认为:“据说和严复同时就学的外国人中,有日本的伊藤伯文、大隈重信和德国的稗斯麦(Bismarck)等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而严复每次考试的成绩,都远超过他们,当然,这只是个不实的谣传而已。但是,从这个谣传中,我们却可以发觉到,严复此番负笈英伦,以一个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却得以与后来的‘铁血宰相”、马关条约的操纵者、著名外相相提并论,其间隐含了多少的尊敬与赞赏。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出这次经历对严复的意义了。”[22](p16.54 ~55)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严复默认并听凭这个“不实的谣传”恣意蔓延的根本原因。
严复致梁启超信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兄返国后……始终寄人篱下,不获一展所长。相形下,彼此何悬殊之甚耶?”陈宝琛与梁启超并无多少往来,不可能直接从梁氏处读到此函,但《严君墓志铭》中却也有类似的说法:“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31) 以两人长达40年的密切交往看,不排除日常晤谈及信函往来中,严复时不时抱怨“怀才不遇”,给陈宝琛留下的深刻印象。
然“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云云,也有可探讨的余地。
第一,严复始终没有参与北洋海军的机要,的确是事实。但在任何国家(无论强国或弱国),一学堂教习、总办企求并参与海军建设、装备、情报、作战等国家“机要”,恐怕都是天方夜谭。何况执教津门的十几年中,“严复对自己所从事的海军事业其实兴趣不大,他一直追求的,是另外一条入仕道路,而那条路,在当时士大夫看来,才是人之常情的正途。”[23](p240) 留洋多年, 理应是本行的数理化基础及教学水平也不敢恭维。严复学生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24](p36卷6期) 即以中国文化衡量,严复的经历、所受教育也使其不可能成为传统学术的一流学者,在人才济济的李鸿章幕中,自然轮不到他起草奏章,参与机要了。汪荣祖先生的论断更直截了当:不是李鸿章不用严复,而是严复有吸食鸦片的恶习,不能被重用。[25](p36~39) 陈宝琛所说“不预机要,奉职而已”,是为故友讳。
第二,严复性格中原本就有“能坐言而不能起行”的弱点,尽管挚友吴汝伦对此有所辩驳(32),但就其一生看,此说并非全系空穴来风,这种弱点不能不影响他的实际工作能力。
第三,严复抱怨“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同时,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也没有平等待人,更别说民主、自由了。与严氏同办《国闻报》,“夜则过谈,谈则竟夜”,交往密切的夏曾佑,1900年初给汪康年的信中写道:“海军学堂……此局全权在于侯官,然其教习之不可居甚于大学堂。盖侯官之于中西各教习,均以奴辈蓄之也。[17](p1349)可见其在水师学堂权势以及对同僚、下属的专横, 已远远超出“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的程度。由此亦知,“中国国民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人治思想”同样体现于严复的言行中,这也正是他后期思想之所以转向“权威政治论”的内在根源之一。
作为近代中国的启蒙大师,严复自有其永远屹立的历史地位,但从“人”、“一个人”的角度看,这些细微之处也表明了他并非超然物外之辈。或许,有那么点人性的弱点,反倒更真实、更有血有肉。
收稿日期:2005—12—04
注释:
① 2005年10月,南开大学召开《严复与天津国际学术研讨会》。 笔者提交此文,与会专家议论热烈,王天根先生、严复后裔严明先生等也有专门指教,非常感谢。笔者考虑各位先生意见,惟因该函原件始终没有公开,真伪尚未定论;即便的确为伪,其他已刊史料也有立论依据,因而修订时保留了主要论点。
②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壬午(1896年7月28日)总理衙门奏军机处抄交闽浙总督边宝泉查明船政情形折:“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不用则日就颓落”等事。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版,第3823~3824页。
③ 如: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352页;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严复传》,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版;杨荫深《中国文学家列传》,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488页,等。
案:王民说:“北京大学刘复(刘半农)教授曾在其所著诗中赞扬严复的名次屡列伊藤博文之上的事。”《谈谈严复研究中的几处失误》,历史教学,1983年第5期。皮后锋所说更明确:“1926年, 北新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的《扬鞭集》,他在该诗集中赞扬严复考试屡屡名列伊藤博文之上。1936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云……1936年,王蘧常所著《严几道年谱》则综合了以上两种说法。”(氏著《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此说颇有疑问。第一,刘半农《扬鞭集》有上、中两卷,皆为北新书局1926年出版,仅月份不同,两位先生皆未说明该引文出自何卷及页码。但遍阅《扬鞭集》及刘半农自序,未见“严复”、“伊藤博文”二字,更不用说“赞扬严复考试屡屡名列伊藤博文之上”的话语,抑或出自世人未知的“下卷”?第二,刘半农文章的确数次提到严复,但多有不屑、讥讽之意,如严复将Logic“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履’的毛病”;(王敬轩)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等(徐瑞岳《刘半农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8~39页)。 可知留学多年的刘半农,恐怕不会“赞扬严复的名次屡列伊藤博文之上的事”。第三,钱基博已经明确指出,严复于“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而复试辙最上第”(《现代中国文学史》,第352页),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基本重复了钱基博的说法,而非“综合”。何况《扬鞭集》丝毫无涉严复,怎能“综合”其说法?
④ 60年前,陶菊隐《六君子传》(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249页)已指出此说为误。近年诸多学者进一步考证,如:卞僧慧“伊藤博文和大限重信是严复的留英同学吗”(《学林漫步·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251页);王民《谈谈严复研究中的几处失误》(《历史教学》,1983第5期);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林保淳《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6、54~55页);徐立亭《晚清巨人传:严复》(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经盛鸿《严复传记研究中的几处错误》(《学海》,1997年第2期,第94~95页);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注1,第564~565页);皮后锋《严复大传》,第57~60页,等。
⑤ 如卞僧慧认为,尽管“从以上并不那么冷僻难考的史实看陈宝琛, 特别是钱基博的文章,错误是显然易见的。可是陈、钱的说法,在旧社会流传很广。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就接受了,并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是想以此“发泄对用人不当,将召致国家败亡的不满”的情绪(氏著“伊藤博文和大限重信是严复的留英同学吗”《学林漫步·初集》,第250~251页);皮后锋认为:“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这种传说之所以能长期流传,表面上是学术界误导了社会,而实际上,中国国民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和人治思想,才是这种无稽之谈的根本载体。”(《严复大传》,第57~60页)
⑥ 如1980年代末影响甚广的电视剧《河殇》第六集《蔚蓝色》,1989年10月7日北京《团结报》(才子的不同命运),前两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等。
⑦ 如2005年2月4日博客论坛“联合光子”的帖子, 怀念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
⑧ 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编写凡例”第十二,以及第564~565页“附录二·严复合集(五)所收严复与梁启超、杨度、庄蕴宽书〈一、致梁启超·一〉的相关注释。
⑨ 王庆成等编《严复合集》原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卷。以下两函同。此信未署年月,似作于1910~1911年间。时严复被任为资政院议员、海军协都统,而梁启超仍流亡,清廷不予赦用。”(《严复合集》〈五〉,第88页)
⑩ 案:笔者写作时,未能查得王庆成等编《严复合集》, 不得不转录于孙应祥《严复年谱》所载。
(11) 见孙应祥《严复年谱》,第564~565页。斜体字为有两个文本有差异者;①、②、③为孙先生考证时所加注释号,因拙稿与之有关而保留。
(12) 《未刊书信》,《近代史资料》,第104期,第90~91页。有差异的文字加了下划线。
(13) 孙应祥《严复年谱》,第564~565页。《未刊书信》,《近代史资料》,第104期,第90~93页。案:《严复未刊书信选》共收59通严复信函, 除对收信人及信中提到的人物作简单介绍外,皆仅加标点,没有注释。
(14) 《未刊书信》,《近代史资料》,第104、90~93页。案:《严复未刊书信选》共收59通信函,除对收信人及信中提到的人物作简单介绍外,仅加标点,没有注释。
(15) 《严复年谱》,第564页注②、③,第565页注①; 《严复致梁启超书等考辨》,《〈严复集〉补编》,第384~386页。
(16) 如1899年11月,严复为在总理衙门谋一职务,赴京活动,“七日而返,所图颇有头绪。”1901年秋冬,“凡三度入都,每次皆作十余日勾留。”严复《与张元济书》(七、十三),《严复集》(三),第536、546页。
(17) “戊戌……政变作,孝钦后垂帘听政。府君即日出都返津。 ”(《严复集》〈五〉,第1548~1549页)1906年,“由京回津,住于馆中,话至十二点后。”(“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转引自《严复年谱》,第290页)“隔日乘船返沪。”(《严复大传》,第315页)
(18)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五十一、四十三、三十九、四十一)等。 《严复集》(三),第770、763、759、761页。当然,由于福建是故乡,夫人、孩子仍居上海,言及这两地,有时也称“回闽葬埋母妻两棺”,“于封印前后,准拟回沪一行”。(《严复集》〈三〉,第765、841页)
(19) 详见梁启超给梁启勋、梁仲策、徐佛苏、徐君勉等人的信。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90~492、555~556页。
(20) 王宪明先生已经提到,甲午战后北洋高级官员中许多人, 包括跟随李鸿章20余年的盛宣怀,“不满李鸿章的所作所为,并相信李鸿章的政治生涯已经从此终结”,想方设法调往张之洞处。见氏著“《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1)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一),第518页。郑氏未记“谈良久”的具体内容,但从严复当时心态言行及郑氏在张之洞幕中的地位、与李鸿章的良好关系推断,应谈及改换门庭事。
(22) 《严复集》(三),第781页。案:此函作于1895年1月15日。 从后来的结果看,“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恐有疑问。不过,是语至少表明,此时严复对南下就职仍充满期盼和信心。
(23) 《严复集》(三),第731~732页。案:此函日期不详, 因提到李鸿章使俄及仍有投奔他处的期盼,应写于1896年春。
(24) 目前尚未见确切记载。但张之洞此时并无北上京、津的相关记载, 何况朝廷对督抚出行有严格规定和控制,而学堂总办不受此约束,故严复南下求见张之洞的可能性极大。因结果不如意,不愿留下痕迹。正如其晚年日记1912、1914年“失踪”一样,目前所知的史料中,严复1896年上半年言论、行止阙如,7 月以后才有记载。
(25) 19世纪末,严复频繁拜会直隶总督王文韶及继任者慈禧宠臣荣禄、 护理直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新任直督裕禄(见丁酉十二月;戊戌闰三月、四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国闻报》,等)。稍后,为在总理衙门谋职,又去北京官场活动,“所图颇有头绪……许以提携”。1909年5月任宪政编查馆谘议官后, 除拜谒本馆堂官外,“如庆王、张、鹿两中堂,他如泽公、肃王,皆经见过……大约做官一事正恐不免耳”。在此前后,还多次拜访直隶总督杨士骧、陈夔龙,两江总督端方、张人俊等(详见《严复集》〈三〉,第530、534、746、759、832页; 〈五〉第1482、1483、1485、1494、1495页)。不难看出,他很注重与权势者的关系,一再走上层路线,且有收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在自己权力范围中,也“喜欢任用亲信和闽籍人士”,“多有自己的亲朋好友”(见皮后锋《严复大传》,第302、232页)。或可推测1896年为调南洋,求见张之洞并非偶然。
(26) 该折上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壬午(1896年7月28日),但当时的信息传递方式使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天。
(27) 数日后,政变发生,康、梁等维新人士就是在日本、 英国的帮助下逃离中国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不例外。
(28) 参见拙稿《“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的相关论述,《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9) 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案:从当时情况看,严复的确是“社会名流”,但不一定就是“学界名流”,更称不上“教育权威”。详后。
(30) 案:黄克武先生《走向翻译之路: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严复》,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四十九期)论及“‘正教习’应等同于‘总教习’”,似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31) 陈宝琛《严君墓志铭》《严复集》(五),第1541页。再,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有类似说法。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2) 吴汝伦《答严几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八日),施培毅、 徐寿凯校点《吴汝伦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74页。 案:[美]史华兹先生已提到,严复“作为思想家之大胆和在实际行动上的消极”。见氏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