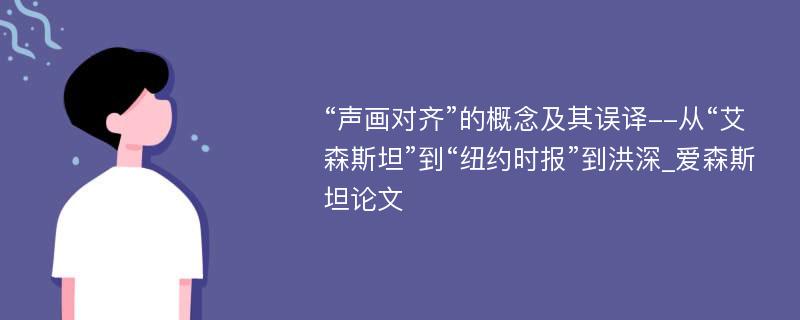
“声画对位”概念及其误译——从爱森斯坦到《纽约时报》和洪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坦论文,纽约时报论文,概念论文,误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电影理论术语,声画对位(audiovisual counterpoint)截然不同于声画同步、声画和谐或声画一致,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粗心的理论家们加以错误地混淆,直到今天也是如此。这一术语的提出,有其明确的历史来源;而相关的误译和误解,几乎从一开始就与之伴生。 本文拟从史料勘比的角度,来还原“声画对位”理论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最初的偏移。首先我们将依据可靠的英译本来梳理爱森斯坦(S.M.Eisenstein)等人《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这篇重要理论文献的核心观点。然后考察这篇文章在问世的当年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和中国《电影月报》上的译文,着重指出“蒙太奇”和“声画对位”的概念如何被曲解,尤其是对于声画关系,《纽约时报》的译者和洪深的理解都正好跟爱森斯坦的原意相反。最后,我会尝试在更大的电影理论史的视野中,去定位“声画对位”概念的错失及其重新阐发,一方面是希望以此辨析这一重要术语的真实义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激活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对于声画关系的想象力。 一、理论原点: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 声画对位,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蒙太奇,它最先由爱森斯坦等苏联电影人在1928年的一篇《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①中提出,其基本义涵是强调应充分利用电影中声音空间与画面空间之间的裂隙,制造声音与画面的冲突、碰撞和它们彼此不相契合的戏剧张力,以形塑更为丰富、复杂的表情达意。 这篇文章是由爱森斯坦、普多夫金(V.Pudovkin)和亚历山德罗夫(G.Alexanderof)联合署名发表的,但是其主要观点带有明显的爱森斯坦印记。文章一开始便称赞了世界电影发展的新方向,特别是对在声音技术的探索方面走在前列的美国和德国不吝溢美之辞。的确,当时的苏联在技术条件上还不具备全力投入到有声电影的研发、创制中去。然而,就像是在十年以前,当新兴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生胶片短缺,反而促成了苏联蒙太奇学派的诞生。现在,爱森斯坦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这也正好是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理论性的方面提出一系列原则性的前提”。原因在于,苏联电影人注意到,“电影中的这一进步正在错误的方向上被应用。”因而声音这一令人兴奋的新发明,有可能反倒为电影艺术的发展制造障碍,“甚至还有摧毁现有的全部形式成就的危险。” 爱森斯坦等人所说的形式成就,当然,就是蒙太奇。行文至此,苏联电影人的姿态已从最开始的谦恭,变得多少有些倨傲。文章声称,蒙太奇是创造了电影如此强有力的艺术效果的唯一手段。要使有声电影沿着既有的艺术发展道路更向前进,就必须要将声音元素也纳入到蒙太奇的理论与实践中来。他们以一贯的偏颇和自信认为,“只有那些深化和拓展了感染观众的蒙太奇方法的时刻才是真正重要的历史时刻。” 如果不是循着这一正确的方向探索,声音技术这把“双刃剑”的另一面就会展露出来,尤其是当时已开始普遍起来的“对白片(Talking Films)”,被爱森斯坦等人视作“商业化的剥削”,它寻求准确的声画一致,让银幕上正在开口说话的人、正在发出声响的物在同一时间被观众听到他们的声音,乃是满足于提供一种自然主义的幻觉,是完全不足取的。“以这种方式来使用声音会摧毁蒙太奇的传统,因为每一次把声音附着到一个视觉的蒙太奇片断上都会增加它作为一个蒙太奇片断的惰性,都会增加它的意义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简单的声画同步会导致每一个声画单元的惰性滞留,从而损害片断与片断之间的动力关系,最终效果是用“并置(juxtaposition)”取代了蒙太奇。 因而,爱森斯坦和他的同事再次强调:“只有将声音与视觉蒙太奇的片断关联起来的对位式的使用可以提供一种发展和完善蒙太奇的新的潜能。”这样一来,在电影中对声音的实验,就“必须是沿着明确非同步于视觉形象的路线来进行……引领我们随后创造出一种声音和视觉形象的管弦乐式对位(orchestral counterpoint)”。这大概是爱森斯坦首次提出“管弦乐式对位”这一说法,写作于十年之后的《垂直蒙太奇》即由此而来,即把声音和画面的整体看作是一部管弦乐总谱,这将成为爱森斯坦后期理论的核心议题。②影像本身就像交响乐或协奏曲中的一个声部一样,它所展开的旋律线处在和声轨的旋律线之间的极其复杂关系中,这种关系是由运动、手势、调性等等来决定的,根本无法用和谐或同步来概括。这些可能引申得出的论点在《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中尚未做出充分的说明。而在后期爱森斯坦的理论探索中,他主要是围绕色彩和音乐的关系展开他极为深奥、博杂的论述的。 不过,就1928年的这篇文章来说,其主要观点至此已很明了:反对声画同步,确立管弦乐式对位。接下来,针对默片艺术发展的瓶颈,几位作者又补充说明,声音技术的加入可以帮助解决字幕、解说性片断等问题。最后,他们竭力申明,“建构有声电影的对位法”不会削弱电影作为国际性艺术的地位,不会使有声电影变成局限于一国之内的市场范围,相反,它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促使电影工作者“要创造比以前更大的可能性,使一种用电影的方式表达的理念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二、从《纽约时报》到洪深的误译 就在1928年,《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先后发表在法国的《艺术生活》、德国《福斯报》、美国《纽约时报》和中国的《电影月报》上面,发表时题目都有改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是英文和中文的译文,并且中译文是从英译文移译的。更重要的是,两个文本中对“蒙太奇”和“声画对位”概念都产生了极大的误解。这个误解不仅是字面翻译工作的失误,它直接牵扯到对于声画关系的认识问题。 英译文刊载于1928年10月7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题目改为《俄国人论有声电影》(“Russians on Sound Films”),未署名。③对比原文(即我们所依据的完整、可信的全译文),这篇英译文属于编译性质,篇幅上有明显的缩减,并根据内容加上了分节标题(“声音的双刃剑”、“死胡同”),为了使作者的观点层次体现得较为清晰,还用数字标号予以提示。文章最前面即说明这是爱森斯坦等作者在近期柏林《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上发表的一篇声明,显然这篇英译文也是从德语转译的。至于英译文中出现的错误,有多少应归咎于德文原译,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考察从爱森斯坦等人的声明初衷到同年发表的英文移译,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偏移。 《纽约时报》的英译文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在蒙太奇的问题上。《俄国人论有声电影》在原文照录“montage”之后,用括号补充了对它的说明:“置景(setting)”。的确,在当时的英语世界,源自法文建筑术语的“蒙太奇”一词还不很为人们所熟知,即便是这篇文章的译者显然也无法理解它的重要义涵,因而就做了这样一个画蛇添足的补充说明。于是,译文原句就变成了这样:“众所周知,使得电影变得如此强有力的基本,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蒙太奇(置景[setting])。”接下来的几段文字中,译者只是遵循字面上的意思进行翻译,对于“montage”、“orchestral counterpoint”等词均照录无误,但是到最后,这一误译带来了对原作者核心论点的曲解还是暴露了出来:“声音,作为蒙太奇的一种新的元素,作为一种与视觉形式自然配合的元素(as an element naturally coupled with the visual form),肯定会带来具有巨大能量的新方法”。这与爱森斯坦等人原文在这里再次强调声音是“与视觉形象相分离的元素”,意思上就完全弄反了。在英译文自身的上下文里,这也造成了同样的自相矛盾,因为前面的段落中已经表达了文章观点,是反对用声音自然地应合影像中的人物对话、物体坠落以制造某种幻觉的。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英译者虽然按照字面意思从德语译文进行了移译,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原文的实际内容,尤其是对“蒙太奇”概念的疏失,使他不能真正把握爱森斯坦等人对于声画关系的真实看法,所以使某种自相矛盾的认识被保存在了英译文的文本当中。 了解了英译文在偏离原意的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就不难理解当洪深再从《纽约时报》转译此文时对上述错误的进一步加强。洪深是留美归国的著名戏剧家,很早就投身电影界,1928年发表此译文时洪深正在明星电影公司担任编剧。这一年,《电影月报》组织了一期“有声电影专号”,集中了近十篇文章并附图多幅,以尽其全面地介绍这“电影界的革命军”④。所收入的文章多数都属编译性质,记录美国好莱坞电影对声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意图是为中国电影人做紧跟世界电影发展脚步的参考。洪深转译《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署名即“洪深”),显然也是同样的用意。《电影月报》上刊载的这篇译文,题目改做《有声电影之前途》,⑤格式、段落,完全依照《纽约时报》那篇《俄国人论有声电影》,只是在篇幅上更有缩减。 内容上,洪深重复了英译文的主要错谬,他对英译者在“蒙太奇”后面用括号加以说明的“置景”还做了进一步解释:蒙太奇“就是人众或物事的背景”。在后面的文字中,洪深显然是依据他自己加入的这一理解,来译出以下这一关键段落:“只有将声音,完全用做montage的衬托,而后montage可以更为发达与完美,如今的有声电影,当然还是图画是图画,声音是声音。将来当有一日,那作者情感调和了,可以做到声音与图画的调和,视与听才是一件事了。”这个段落正好是爱森斯坦等人提出“管弦乐对位法”的段落,洪深既无法理解“montage”,也不能像英译者那样在拉丁字母的拼写范围内直录“orchestral counterpoint”,便只好用“声音与画面的调和”来译解声画对位,从而造成意思的完全误解。也就是说,声音只是烘托画面中人或事的背景,特别是环境声,以使电影所表现的戏剧情境更趋近于完整和真实。 至此,我们可以稍做总结,整理一下1928年美国《纽约时报》和中国《电影月报》上的两篇译文对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做了怎样的误译。首先是对于“montage”的陌生,使他们生硬地用“置景”、“人众或物事的背景”去进行译解。因此,他们也就完全没有可能理解,在爱森斯坦那里,“蒙太奇”意味着冲突、碰撞、矛盾,意味着不调和、不和谐,因此声画对位是以声音“非同步于视觉形象”为前提的。其次,洪深比英译者遭遇更多一重难题,是在于他无法在中文里直录“orchestral counterpoint”而不得不对它进行译解,所以“调和”就成为他选择的字眼儿(当然这也导源于英译者“自然配合”等措辞),来解释他所认为的声音应成为画面的背景这一原则。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种误解不仅仅是出自翻译者的个人疏失,它也是当时世界电影史(以及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趋势使然。因为整体上看,特别是就古典叙事电影的发展而言,有声电影的最初阶段总的目标仍然是追求声画一致,以营造时空的连续体;声音从一开始时作为制造新的吸引力的异质性元素,到后来被画面和叙事充分地吸收,成为内在于影片情境的组成部分,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的。但是,爱森斯坦等苏联电影艺术家所看重的,恰恰是声音元素的那种异质性,而不是它的整合力。因此,无论是美国《纽约时报》还是中国《电影月报》对于《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的误译,是以这一大环境为前提的,他们不能充分理解苏联蒙太奇学派的意旨,尤其是不能理解爱森斯坦独树一帜的蒙太奇理论,实在也是不能过分苛求的。 三、“声画对位”论争:影响与评价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本身对于声音与画面的“管弦乐式对位”并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论说,也是造成翻译和理解中的混淆的重要因素。的确,爱森斯坦等作者(实际体现的是爱森斯坦个人的观点)仅限于提出这一概念,而未能清楚地解释到底什么是声画对位;同样,他(们)只强调了应使声音“非同步于视觉形象”这一前提条件,至于究竟怎样实现声画对位,仍然未做任何说明。这些欠缺不仅给同时代其他国家的电影人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其概念本身遗留的理论难题也一直延续至今。 在爱森斯坦自己的理论发展中,声画对位既预示了后来的“垂直蒙太奇”,但在两者之间又存在某种认识上的断裂,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从音乐类比到音乐思维的渐显。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爱森斯坦来说,在电影声音的几个构成元素当中,他对人声(voice)和环境声(sound)大多是不屑一顾的,而唯有音乐(music)被纳入考量,他那时的全部思考实际是围绕(同样非现实性的)色彩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而这一区别在《关于有声电影的声明》还很不明朗,1928年这篇文章中所谈及的“管弦乐式对位法”的确还只是一个修辞性的构想。 后来的电影学者并不是总能够很好地把握从声画对位跃升到垂直蒙太奇的这一关键区别,从而对爱森斯坦的理论发展做出不甚精确的历史评价,例如尼克·布朗(Nick Browne)的论述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后期爱森斯坦致力于探索视听复合的声画关系,因而更关注形式与人物或叙事的适应,从而使他早期电影中占主导的“冲突范畴让位于和谐的配合和复杂的协调”。这一判断是稍显粗糙和站不住脚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未能区分,对于爱森斯坦的理论探索而言,电影中的声音就只是音乐,而不包括现实的人声和环境声;进而也就未能审慎地把握,爱森斯坦始终关注的基于运动的电影形式的展开,并不能等同于叙事。特别是他根据爱森斯坦的个别表述得出结论,认为最终“爱森斯坦理论中蒙太奇核心作用的这种失落,是与叙事电影的回归和有机形式作为一个和谐统一体的模式的复兴同时发生的。”⑥这更是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导,而且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误导与前述《纽约时报》和洪深对爱森斯坦等人的文章所做的误译在内容上有着共通的倾向性的。总之,我们不能基于自然主义的幻觉理论和它所服务的叙事的时空连续体,来理解爱森斯坦的对于声音与画面关系的认识。 把声画对位混淆为同步、和谐、一致,并认为它是服务于叙事,固然是背离了爱森斯坦的原意;但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正好相反的理解也是引起了颇多争议的,这就是认为声画对位仅只意味着声音与画面的对立、冲突、矛盾。让·米特里(Jean Mitry)就曾对这后一种看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不能只要银幕上出现“音乐表现的情感和影片表现的情感的对立”时就称之为声画对位,这种说法是不求甚解的,是对那个严格的音乐术语的滥用;他认为这种效果的唯一合适的表达是“反差”⑦。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的观点与米特里如出一辙,他同样反对在对立冲突的意义上执著于“声画对位”,他认为这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化约论,是把本来极为丰富的电影表达删刈成为非此即彼的意义选项:“这里存在着千百种可能的方法来把声音加到一个给定的画面上去。在这无数多的选择当中,有一些是完全惯例式的。另一些,没有在形式上构成对画面的矛盾或‘否定’,而是把对画面的感知带到了另一个层面。”基于他所说的这“另一个层面”,希翁提倡一种“自由的对位”,即只要能够服务于电影的表情达意,声音与画面之间的组合是存在着多种多样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可能的。⑧ 现在,我们可以综合这些颇具洞见的观点,来整理一下“声画对位”概念的局限和启示性了。无论声音与画面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严格的同步或一致,还是把它纳入爱森斯坦早期的理论脉络而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冲突,都只是声画组合的极端状况。在更多的情形下,尤其考虑到在爱森斯坦的理论语境里他对人声、环境声和音乐所做的实质性的区分,声音和画面的组合方式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无论米特里所说的“反差”,还是希翁所说的“自由的对位”,都在描述声画对比的程度区别方面,具有理论表述上更大的覆盖性:它们既包容了截然对立与完全一致这两种声画组合的特定状况,更呈现出保持声音与画面之间张力的戏剧性空间,那里存在着值得去推敲的多种选择。 在电影理论史这一相关论争的参照之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声画对位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理论旅行过程中产生的最初的偏移。在世界电影史刚刚进入有声片时代的开端处,爱森斯坦等人就提出声音应该非同步于视觉形象,应该说,是具有艺术想象的前瞻性的,尽管他们的语焉不详使得这一概念成为遗留给后人的理论难题,但同时它也为辩证地看待声画关系的可能预留了思考和创作的空间。而从《纽约时报》到洪深的曲解和误译,则使爱森斯坦等人颇具历史穿透力的艺术创见与世界电影发展潮流之间的格格不入变得更加戏剧化了。在1928年之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声画同步技术日臻成熟和完善,然而画面与叙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驯服了声音这个幽灵,仍然是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研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疑难问题。而在中国的电影银幕上,默片不再作为默片而存在,而是成为了声音匮乏的影片,它和国族主体身份的匮乏以及作为转喻性书写舞台的性别焦虑耦合在一起,成为193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个影音主题。 注释: ①Eisenstein,Sergei,Pudovkin,Vsevolod,Alexanderov Grigori."A Statement[on Sound]",Mast,Gerald,Cohen,Marshall,Braudy,Leo: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Introductory Reading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317-319. ②(俄)谢尔盖·爱森斯坦.蒙太奇论[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330. ③"Russians on Sound Films".New York Times[J].Oct.7,1928. ④诰.卷首语·谈谈有声电影[J].电影月报,第八期(有声电影专号). ⑤洪深.有声电影之前途[J].电影月报,第八期(有声电影专号). ⑥(美)尼克·布朗.电影理论史评[M].徐建生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31、38. ⑦(法)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心理学[M].崔君衍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313. ⑧Chion,Michel.Audio-vision:Sound on screen[M].translated by Claudia Gorbm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