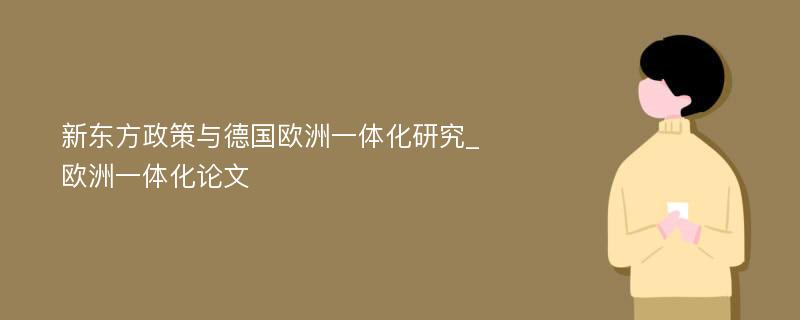
德国“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东方论文,欧洲论文,德国论文,政策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9)01-0102-07
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前提下,阿登纳时代以来所坚持的“哈尔斯坦主义”使德国外交面临着被孤立的危险。勃兰特执政后,出台“新东方政策”,正是德国想摆脱外交困境积极寻求适合德国现状的外交政策。然而,“新东方政策”引起了西方阵营的疑虑,担心德国会靠近苏联,这样既会破坏欧洲联合进程,也不利于西方阵营的团结。他们认为,“西德对一体化政策本质上不是渴望为统一欧洲,而是仅仅想实现重新统一德国。”然而,这种观点遭到强烈的反对,“德国对海牙会议成功的举行所作出的努力,证明了在西欧统一中存在着联邦德国的真正的利益”[1](第55页)。如果没有欧洲联合力量的支持,“新东方政策”缺乏与东方阵营讨价还价的资本。德国只能在欧洲联合中寻求依靠,获得他们对新外交政策的支持。于是,德国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政治上通过“达维农报告”(Davignon Report)开创了欧洲政治联合的先河;经济上支持“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打开欧洲经济合作之路。德国“新东方政策”再次打开了欧洲一体化的大门,同时也为其成功实施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后盾。
一、突破外交困境——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提出
雅尔塔体系分裂了欧洲和德国。为了保持德国的统一性,战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对东德推行“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即只有联邦德国才能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十几年来未曾有很大的变化。另外,阿登纳又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苏联等东方集团采取极其强硬的外交手段,其意图是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步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凭借实力把东德统一过来。
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阿登纳对东方僵硬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遭到质疑。如果说,1955年5月5日德国加入北约标志着阿登纳的外交政策达到成功顶峰的话,那么1961年8月13日建立“柏林墙”时,西方集团的妥协立场对阿登纳强硬的东方政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其实,在他执政后期,对“哈尔斯坦主义”也产生了怀疑,也在考虑改变自己的东方政策。1963年6月,他同柏林市长勃兰特谈到如何评价“哈尔斯坦主义”时说:“有些东西只要还可以捞回些什么,就应该脱手。”[2](第58页)但是,在德国的东方政策中他有两点是不能突破的:第一,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承认奥德——尼斯河一线是德国的最终边界。阿登纳终究还是不能从自我封闭的东方政策中走出来。1963年10月,艾哈德被选为新总理,这位曾创造德国经济奇迹的经济部长,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也继承了前总理的衣钵,并不打算终止“哈尔斯坦主义”。从50年代到1966年间,虽然艾哈德总理对外交政策作了一定的调整,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是坚持以吞并东德来完成德国统一,并没有放弃“哈尔斯坦主义”,这使德国未能突破外交困境。直到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上台执政后,德国的东方政策才开始发生实质的变化。
从60年代初期以来,美苏两大国开始从冷战对峙转向竞争性合作,德国对其统一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已是必然了。在“柏林墙”事件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两国明显互相承认对方的势力范围,开始奉行一项维持现状的政策。当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缓和政策之时,德国再坚持原来的冷战政策既毫无意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柏林墙”建立时,勃兰特是西柏林市长,“后来表明是西方无能的表现使他开始考虑新的德国东方政策”[3](第171页)。因为他知道,“目前的重新统一政策已经失败了”[4](第41页)。“哈尔斯坦主义”不但没有发挥孤立东德的效果,相反“它已经威胁到孤立波恩而不是东德。70年代,阿登纳重新统一德国的政策注定使联邦德国与盟国和非盟国之间产生的矛盾日益突出”[5](第410页)。在此情况下,德国在外交上有被孤立的危险。
为了摆脱外交困境,为未来重新统一德国创造机会,德国只有改变同东方关系,缓和欧洲局势才有现实意义。“总理和外交部长都相信已经到了在中欧降低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时候了”[6](第150页),这预示着“新东方政策”的出台。“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就是德国为自己的外交事务担负起责任以来绝对是第一次,德国把与东方的关系放在和西方一体化、欧洲一体化和在北约内的西方安全利益同等重要的位置上。”[7](第128页)但是,每届德国政府都向德国人民保证重新实现统一的目标,但除非苏联垮台,否则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德国不能等待苏联的垮台,必须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来处理德国分裂问题。于是,“新东方政策”正式被提出。
德国重新统一只能靠德国人自己的努力,“柏林墙”的建立事实上已经关闭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门。“东德没有被孤立而是与东方集团联系更加紧密了,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没有被削弱而是更加强硬,提高了处理德国问题的难度而不是降低了。”[8](第140-141页)在德国重新统一的僵局下,两个德国以及东西方关系上,只有通过相互接触增进了解,使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勃兰特认为希望通过缓和两德关系,东西方关系才会“大踏步”前进,终归有一天“为某种形式的(对德)和约铺平道路,从而打开通向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道”[4](第111页)。其实,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表面上是缓和两德关系和东西方紧张的局势,可鼓点子却是敲在德国重新统一上。相比较而言,新东方政策要比阿登纳完全倒向西方来达到重新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蕴涵着更深远的战略思想。
二、“新东方政策”与欧洲政治合作的“达维农报告”
“新东方政策”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两德和解,为未来德国重新统一奠定基础。可是,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引起了盟友的忧虑,担心德国会通过中立的途径来实现重新统一。德国中立,势必会削弱西方的实力,无论对美国还是对西欧各国政治和经济都是极其不利的。另外,“新东方政策”在政治上可以为德国提供更广阔的外交空间,经济上通过与东方集团合作,将会更加壮大德国的力量,这肯定会打破共同体内的力量平衡,引起了共同体成员国的担心。这种担心尤以法国为重,“两个德国和解的可能性重新点燃了对德国强权的恐惧”[9](第138页)。对德国来说,如果没有西方盟友的谅解和支持,“新东方政策”也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还给西方阵营以从中渔利之嫌。因此,德国只有坚定地立足西方阵营,加紧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来消弭盟友对“新东方政策”的疑虑。所以,在“新东方政策”处在酝酿阶段之时,勃兰特就已经将自己的东方计划告诉了法国总统蓬皮杜,其目的就是防止“新东方政策”使外界认为德国的注意力会偏离欧洲一体化。勃兰特此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尽管法国对“新东方政策”有点不安,毕竟“蓬皮杜对德国实施‘新东方政策’的态度是中立的”[10](第94页)。
勃兰特始终把推进欧洲联合与实施“新东方政策”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1969年的海牙会议上,共同体各国确定了要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德国提议欧洲不仅要在经济上一体化,而且还要加强政治合作。在德国的建议下,各国外长成立了达维农委员会(Davignon Committee)正式讨论政治一体化问题。由于政治一体化的敏感性,各国对欧洲政治联合方式还是纷争不断。反对者主要还是法国。虽然它不再反对共同体扩大,但继续贬低政治合作的重要性,明确要求以各成员国外长峰会的政府间合作方式作为共同体政治合作主要形式,降低共同体理事会的权力,削弱超国家主义因素,“明显的与法国长期以来所坚持反对任何加强超国家主义的政策保持一致”[10](第87页)。
欧洲政治合作对德国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既对欧洲缓和产生一种潜在作用,又符合德国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1970年11月19日将在慕尼黑(Müchen)召开第一次政治合作会议,六国将研究欧洲安全会议和与苏联关系等问题。由于德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联合国,欧洲政治上的成功合作“对德国‘新东方政策’,不仅是一种认可和援助,而且它对波恩在欧洲以外推行的外交政策建立了一个潜在的重要平台”[10](第88页),这增加了德国对欧洲政治合作的决心。“新东方政策”不仅要获得欧洲的认可,而且还迫切需要共同体对其大力支持,否则就会遭到失败。德国作为西欧的经济大国,它对共同体的态度将注定要在欧洲政治合作中发挥主要作用。
在达维农委员会中,德国要积极推进超国家主义一体化欧洲合作方式,陷入了与法国等共同体其它成员国的纷争中。“富歇计划”的流产,1965年的“空椅子危机”所导致的“卢森堡妥协”等都是法国从中作梗,是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在达维农委员会的计划中,如果德国赞同超国家一体化联合方式,可以预见不但会遭到法国强烈的反对,还会影响到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成败。这时的外部环境对德国也不利,“美国深陷越南威胁到减少其在欧洲的驻军,引起波恩对美国未来政治和军事支持的有效性表示严重的怀疑,更需要一个统一的西欧来弥补缺少美国政治支持时,(欧洲)能够支持东方政策”[10](第82页)。而此时德国正与苏联进行关于签订和约的谈判,急需得到法国及欧共体的支持,迫使苏联作出让步,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德国权衡利弊,经过德法举行双边会晤,决定对法国妥协,终于达成共同体政治合作意向。
1970年5月末,委员会提出欧洲政治合作的“达维农报告”。该报告主要还是按照法国对欧洲的设想来完成,即政府间合作方式。这“不仅只达到交换政治观点目的,而是要更加公开实现共同体的政治目标,那就是要在有关欧洲外部政策中,共同体达成一致立场,为了向整个世界表明,欧洲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使命”[10](第87页)。欧洲政治联合终于取得一定进展。自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富歇计划”胎死腹中,欧洲政治一体化一直未能获得巨大的突破。“达维农报告”毕竟建立了欧洲政治合作的机制,使欧共体政治合作开始走向制度化,欧洲政治一体化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达维农报告”达成的欧洲政治合作意向意义相当重大。对德国来说,在欧洲联合的氛围下,“短期内‘新东方政策’达到了与苏联集团和苏联本身关系的缓和,这也是在德国的西方政策的框架内才获得的成果。如:继续是北约成员国、支持进一步欧洲一体化,包括扩大共同体将英国纳入进来和提出加深货币联盟的建议”[11](第29页)。1970年8月12日,德苏共同签署了《莫斯科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一致同意互相放弃使用武力并承担义务,只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承认欧洲现存边界,承认民主德国是主权国家(但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承认)。《莫斯科条约》开创了德国和苏联关系新的局面,构成了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在欧洲实现缓和以及使欧洲局势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0月,共同体六国外长批准了“达维农报告”,规定合作的目的是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采取共同行动,并在10年内建立起“欧洲政治合作”制度。11月,欧共体首次外长会议在慕尼黑如期举行。
三、“新东方政策”与欧洲经济合作的“维尔纳报告”
如果说欧洲政治合作是由于德国主动让步而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则复杂得多。60年代末严峻的国际金融形势又把建立经济货币联盟问题提上日程。二战后,美国凭借它的经济、政治实力,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认了“两个挂钩”原则: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第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
5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到第一次严峻的危机,导致美元疲软和1960年发生的国际黄金市场混乱。1961年德国货币重新计价,引起了共同体成员国对在共同体内保持内部汇率稳定的忧虑。随着共同市场的建立,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各国经济货币政策的相互合作。因为“通货膨胀和紧缩的趋势往往会从一个独立集团中的某一成员蔓延到另一成员,所以共同来控制这些趋势是符合总体利益的”[12](第130页)。1963—1964年,意大利发生了支付危机,共同体再次遭遇严峻的金融困境。于是,“1965年(欧洲)理事会决定把固定汇率作为一个目标来实现”[12](第130页)。1968年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金融货币危机,抛售美元抢购黄金风潮迭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出现崩溃的征兆。世界金融货币危机导致法郎贬值和德国马克升值,引起欧洲共同体金融货币市场一片混乱,共同体成员国认识到稳定货币的重要性。
在1969年海牙会议上,六国曾经决定制定一个经济货币联盟的计划,保护共同市场不受货币差价和经济危机的干扰。由于经济货币政策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在考虑建立经济货币联盟时,共同体内部矛盾就已产生。德国认为应该优先考虑经济合作,这一观点得到了荷兰的赞同。法国则强调建立货币联盟,得到了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支持。德国认为共同体经济货币联盟之所以没有取得进展,是由于共同体有关机构缺乏超国家权力,强调把经济政策的决策权由国家让渡到共同体,更从政治意义上看待欧洲经济货币合作。同时,一旦涉及国家主权让渡的老问题时,当然会遭到法国顽强的反对。
1970年10月,委员会提交“维尔纳报告”(Werner Report)。该报告对以德法为主的共同体成员国不同观点作了妥协,被认为是德国的“经济学派”和法国的“货币学派”的混合体。报告要求在1980年前分三个阶段在共同体内实现经济货币联盟,重点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对中间阶段没有作具体的时间规定。第一阶段将于三年内完成,中心任务是缩小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波动幅度和彼此间的波动幅度,建立货币合作基金以帮助各国稳定汇率。第三阶段要求达到经济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建立共同体中央银行体系,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共同体经济政策中心。更重要的是,经济货币联盟与改革共同体机构事项牵涉在一起,还要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做出必要的修订。显然,这与德国的要求一致。但是,“维尔纳报告”中的超国家倾向遭到了法国戴高乐分子的强烈反对。“法国的主张是同它一贯维护国家主权相一致的,凡是触及削弱国家主权的决定,法国一概不与接受”[13](第192页)。法国对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热情消散了,还引发了共同体内新一轮的争吵。
德国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经济货币联盟的成果必须要实现政治目的,是实施“维尔纳报告”中第一阶段的前提条件。它的经济货币联盟的观点与法国分歧较大,引起法国愤懑。但是,法国参与经济货币联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法国拒绝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将意味着欧洲一体化进程遭受沉重的打击,这迫使德国准备对法国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就像勃兰特1971年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德国对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真的没有兴趣,只在乎经济货币联盟的政治意义。其它的西欧国家国小力弱,对德国“新东方政策”不能发挥更大的支持作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分散了它对欧洲所承担的责任。勃兰特希望通过加深欧洲一体化为其实施的“新东方政策”获得更多的安全保证。
此时,德国与东方集团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分量,德国必须维持并加强同西方的团结,理由有三:第一,如果勃兰特政府被视为是西方的一部分来作为谈判的对象,为获得满意的谈判效果增加了无形的砝码。无怪乎德国人巴赫感慨道:“在谈判中有北约的支持对联邦德国是多么的重要啊!”[14](第26页)这正是德国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原因之一。第二,“新东方政策”不能忽视西欧联盟和大西洋联盟对其的疑虑。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就说过:“在我看来,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用不很慎重的手段转变为德国古典民族主义的新的形式。从俾斯麦到拉巴洛,自由驰骋于东西方之间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外交政策的本质。”[5](第409页)美国人认为,“新东方政策”与欧洲一体化,对德国来说就像鱼和熊掌两者不可兼得,基辛格对此表示认同。“英法对基辛格的看法也表示赞同”[14](第27页)。第三,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在德国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反对党承袭阿登纳对东方的实力政策,主张通过实力来吞并东德重获统一。勃兰特政府就算与东方国家的谈判取得成功,要获得国会的批准也是相当艰难。通过以上的分析,勃兰特政府必须采取新措施来向西方盟友保证德国是作为西方的一份子来实施“新东方政策”的,“勃兰特希望用西方政策来补充他的东方政策,也就是说加强德国与西方,特别是与法国和共同体的关系”[12](第132页)。他向盟友保证,“新东方政策”“决不意味着减弱与西方的关系和所承担的义务”[7](第129页)。因此,德国就必须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既可以使共同体成员国减轻对“新东方政策”的误解,还可以为其顺利实施获得欧共体的支持。
在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中,改善与波兰关系也具有重大意义。德波关系如何,是涉及中欧局势的重大问题。1970年2月5日,德国国务秘书访问华沙,揭开了两国谈判的序幕。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与波兰总理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协定》。双方确认,“两国现有的边界,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保证无条件地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宣布“彼此对对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提这类要求”[15](第263页)。这就意味着勃兰特突破了阿登纳所不能突破的边界问题。此时,“新东方政策”在德国国内遭到反对党的激烈批评。勃兰特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他支持超国家主义的经济货币联盟,遭到法国反对;另一方面,实施“新东方政策”承认欧洲的现状,又引起了国内反对党的反对。就连西方盟主美国对“新东方政策”也表示怀疑,“对此政策既不热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不相信它是可行的”,甚至还“暗示在波恩突然被拉巴洛(Rapallo)情绪所笼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官员发出他们对(新东方政策)怀疑和失望的声音”[16](第82-83页)。德国渴望超国家主义的欧洲一体化,希望获得西方和法国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面临的困境使德国意识到“必须通过新的动力来摆脱西欧一体化的停滞的局面”[14](第27页)。为了使“新东方政策”顺利实施,德国决定对法国妥协。勃兰特知道:“没有法国支持,‘新东方政策’将不能获得成功。”[11](第41页)
德国不能允许西方盟友对其的误解继续下去。1971年1月25日,勃兰特作为政治“请愿者”出访巴黎,与蓬皮杜举行双边会晤,寻求其对德国东方政策的支持。法国报界猜测认为,德国将会进一步升级经济货币联盟的讨论,想使讨论久拖不决,这样德国才可以集中精力实施自己的“新东方政策”。与法国意图正好相反,勃兰特表示“我们希望在西方取得进展,这正有利于我们的东方政策”[2](第328页)。他非常清楚,德国没有西方联盟的支持和保护,就没有东西方的均势和自身的安全,更没有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本和将来重新统一的希望。总之,“新东方政策”没有西方的支持是行不通的。他强调指出,“大西洋联盟和西欧伙伴关系是我们取得同东方和解成果的根本前提”,“我们同东方和解的任何行动都是与我们的西方伙伴密切协商,联邦德国同东方的协定将明确各缔约方现有的条约和协定的义务不受影响”[2](第442-443页)。蓬皮杜也表示,他丝毫不反对把某些权力交给共同体,可并不是把权力交给共同体理事会。实质上,法国还是坚持共同体政府间合作方式。最终,勃兰特接受了蓬皮杜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严格的政府间合作方式,并向法国总统保证:“在创建新的欧洲机制中,波恩不再坚持任何夸大其‘完美主义’”,相反,勃兰特“同意对经济货币联盟采用‘现实主义’解决办法”[10](第92页)。《经济学家》对此作出评论说:“维利为他的东方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欧洲经济一体化终于取得进展。
勃兰特与蓬皮杜就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取得了一致。德国就可以实现三大外交目标:第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把德国捆在西欧就可以消除西方盟友对其的疑虑,为其推行“新东方政策”奠定了前提。正如蓬皮杜说的那样,“美苏迟早会越过欧洲而彼此达成协议,把欧洲压制在美苏之间。所以,德国应该系在欧洲使之不能摆脱”[14](第27页)。德国建设经济货币联盟,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就消除了西方对“新东方政策”可能会导致德国脱离西欧和西方阵营的担心。第二,启动经济货币联盟进程及时地把德国马克融进欧洲货币,表明德国不倾向使用其货币坚挺的力量,来获得经济上的优势,从而再一次成为欧洲执牛耳者,也可以消除欧共体成员国对德国马克力量的恐惧,为“新东方政策”扫除了障碍。第三,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步瓦解对共同体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混乱。如果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将使制定共同欧洲货币政策较为容易。这对德国、对欧洲都有好处。
法国对德国的让步较为满意,为共同体理事会建构经济货币联盟打开了方便之门。经过成员国反复讨论之后,欧共体理事会于1971年3月22日通过一项决议,采纳了经过修订后的“维尔纳报告”。毫无疑问,修改后的“维尔纳报告”淡化了超国家主义色彩,应法国的要求,删去了制度层面上的东西,尽管被某些国内权威人士批评为是德国的失败。对勃兰特来说,必须防止共同体空转,以此来证明德国在加紧实施“新东方政策”的同时,也存在积极主动的西方政策。这样既可以逐渐消除西方盟国对德国“新东方政策”将会产生“拉巴洛阴影”的担心,也可以立足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对苏联施加一定的压力,还可以减轻国内反对党对勃兰特政府削弱欧洲一体化的批评。
对德国而言,“新东方政策”是最重要的,它只有在西方接受并支持下才能取得成功。从短期来看,德国为建立经济货币联盟付出了代价。但从长远利益来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共同体内部建立共同的经济政策和固定的汇率对德国经济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更重要的是,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过程中德国的让步既消除了盟友的误解,也赢得了它们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例如,在德国联邦议院中,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头目巴泽尔(Rainer Barzel)告诉蓬皮杜,基督教民主党准备在联邦议院对“新东方政策”的主要成果《东方条约》的表决中投反对票。法国总统“劝他不要那样做。德国反对党最终放弃了,《东方条约》才得以表决通过”[14](第29页)。可见,赢得西方盟友的支持对德国“新东方政策”的成功推行是何等的重要!
70年代德国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埋葬了二战后僵化的“哈尔斯坦主义”,开辟了德国外交新领域,打破了同东方的隔绝状态,打开了通往东方的大门,获得了在东西方行动自由的机会。在政治上,新东方政策提高了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缓和了欧洲冷战局势,降低了对美国的依附程度;在经济上,扩大的东西方间贸易,为德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故此有学者就认为,“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是德国大企业,特别是依赖出口钢铁工业重压之下的产物”[17](第173页)。在外交上,摆脱了孤立状态,为德国在东西方开辟出了广阔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在“新东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收稿日期:2008-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