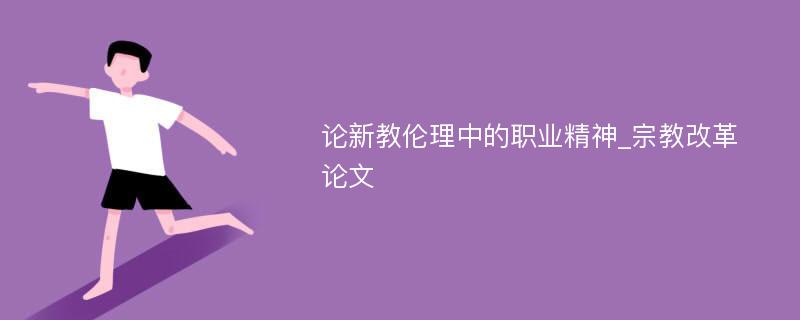
论新教伦理中的职业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教论文,伦理论文,精神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履行职业劳动在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眼里是同胞之爱的外在表现,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个人道德生活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一宗教改革后出现的职业思想使人们日常的世俗生活有了宗教意义。如此这般,由职业思想便引出了一切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路德用“职业”(Calling)一词把世俗的工作和劳动与宗教的生活联系了起来,这为宗教直接影响现实生活开辟了道路。基督新教伦理中的“天职”思想就像一粒种子,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职业”为生活重心的基督新教伦理态度构成了西方人的普遍生活方式。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同样认为,基督新教伦理的人生观在财富的生产上,相当排斥那些“为财富本身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唯有因职业劳动的结果来获得财富,才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换句话说,基督新教伦理思想鼓励一种“不休不歇,有系统的俗世职业劳动”;西方这种视职业为天职的思想对于西方社会和个人的成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然而,在我们国家,人们选择职业时,无论男女都会这样想:“是否下一个公司的待遇比现在的公司更好?”
很少有人会想“我是否履行了契约?我是否应该在此投注全部的忠诚和精力?”人们往往淡化或忘记了工作与生命信仰一致的价值,缺乏西方人对天职思想和职业伦理的深刻理解和领会。这样一种相当普遍存在的现实状况,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一简要探讨,以唤起人们对职业及其价值的重新思考。
一、基督新教伦理
(一)新教伦理的形成和内涵
在16世纪的欧洲,与世俗的人文主义思潮同时兴起的,还有宗教内进行改革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即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背景是15世纪以来欧洲经济的发展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教职人员的道德堕落。新教(Protestantism)是自16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各个教派的统称,以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为代表。这两个主要教派都赞成和接受在实质上同一的宗教和共同的价值观念、伦理准则以及思维和生活方式。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不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动摇和瓦解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而且还摧毁了天主教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并以新教伦理取而代之。
“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① 教伦理就是新教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含义,而不是它的基督教含义。从新教主义所引申出来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一是路德的“职业”概念所培育出来的新的人生观。路德在把《圣经》翻译成德文时,把《圣经》中“神的召唤”概念改造为“职业”(德文:Beruf,职业,天职;英文:Calling,职业,神召)概念。路德认为,职业,亦即神的召唤,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终身任务。二是加尔文的“预定论”所引申出来的进取精神和功利主义。加尔文认为,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因为人们浪费了为上帝争光的机会,并提倡不劳动者不得食,鼓励乐于从事工作。
新教这种把职业看作神的召唤或使命的教义,把工作上升到信仰的高度的思想,使人们对生活目的有了一种新的理解。人们不再等待“最后审判”的来临,而是努力于自己从事的职业,这一教义要求人们抛弃人间的淫荡乐趣,通过辛勤刻苦的工作取得事业的成功,并为上帝争光。这样,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的教义就不再歧视世俗的劳动。
(二)韦伯对新教伦理中职业精神的阐述
在韦伯看来,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带来了不少新的改变,像天职的观念被放到重要的位置,世俗劳动也被承认有高度价值,一个有现代意味的职业伦理似乎已渐具雏形。以“天职”的实际含义而言,路德主张这表示每个人都有他“既定”的身份阶段和职业地位,这来自于神意的直接结果,所以不能轻言改变。
身为一位社会学家,韦伯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首先引用的文献记录,不是宗教领袖的言谈或教义,而是美国政治家和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于1748年在《给年轻商人的忠告》中写下的句子,如“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如果你是以谨慎、诚实而为人所知的人,那么一年六磅可以给你带来一百磅的用处”。② 并竭力推崇个人信用、信誉和谨慎、诚实。这就是韦伯所发现的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表现的那种无形的精神。韦伯认为这些“座右铭”式的警句,乍看之下和宗教没有直接关联,但他恰恰认为这正是以典型风格道出的一种独特的伦理、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代表着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宗教伦理根基最传神的表现。无怪乎韦伯要说,富兰克林所表达的这种“带着伦理气味的特殊作风”,在其他文化中并不显见,甚或完全缺失,它是西方近代文化的独特产物。
韦伯进而提到了富兰克林所标榜的诚实而有信用的人的理想,“在于把自己资本之增加看作目的本身。这项说教的内容并非单纯是立身处世之技巧,乃是一种特殊的伦理。违反了这种伦理,不仅被认为愚蠢;而且被认为有疏职责。这就是此事的精奥。这里所教的不止是生意上的谨慎机敏,一种具有伦理气味的作风却表明于此”。③ 的确,仔细咀嚼富兰克林的这些“生意经”,似乎这中间真的流露出某种“伦理气质”,就如韦伯所指出的,所有富兰克林的道德教训皆带着功利的气息,诚实是“上策”,因为它能确保“信用”;守时、惜时、勤勉、节俭之所以是“美德”,是和宗教信仰紧密相关的。从宗教信仰这方面,出现了时间乃无限珍贵的概念,因为对“选民”来说,丧失每刻钟时间就是丧失为上帝光荣而服务的时刻,这样想下去,人生真是太过短促,每一分钟都应该用来“确知”自己的蒙恩,并加倍努力以报答这莫大的恩典。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喜劳动者必不为上帝所喜”。懒惰、倦怠乃是缺少神宠的象征,劳动则是上帝所指定的人生目的本身,任何人都应当遵守“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戒律,即连富人亦不例外。这条戒律出于保罗之口,在很早便成为修道院内的清规,因为以劳动来磨炼一个人的意志,自古以来便是公认的“制欲”技术。
具体来说,新教伦理所引申出来的职业精神主要有:第一,工作作为目的本身而被珍视。一个人“在他的职业活动中具有一种责任感是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伦理中最具特征的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这一伦理的基础”。第二,致富和利润不仅是个人职业成功的证据,而且是对个人德行的证实。“在现代经济秩序中发财只要是合法获得的,被视为美德和精通本行的结果与表现”。④ 正是有一批为数众多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把上述的职业观念和态度当作追求的目标,在他们逐渐成功之后,资本主义才能够发达起来。难怪韦伯会写道:“宗教上认为不休不歇的、有系统的俗世职业劳动,是制欲的最高技术并且是重生与纯正信仰的最确实、最彰明的证据。”新教伦理所倡导的人有义务工作、有义务过自我克制的生活,这些都是早期商人的朴实、节俭、刻苦的美德,新教伦理所体现出的职业精神“哺育了近代经济人”。⑤ 新教教义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奋斗,正是职业精神所需要的心理因素。
二、新教伦理中的“天职”(Calling)观念
(一)“天职”观念的来源
人的工作不具有信仰价值,毫无神圣的意义,这种观念曾长期主宰了东西方各国。在西方,影响人们职业观等价值观念的思想主要来自基督教教义。传统基督教教义是反对盈利性工作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将追求财富的欲望贬斥为卑鄙无耻,他认为劳动只是为了维持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自然事物,并无赋予劳动特殊的伦理意义。这一论点在当时被奉为真理,在宗教改革前的教义中,将放弃现世、离世修道、最后进入天堂作为人生的目的。阿奎那进而认为,默想的生命就是优于行动的生命。显然,这种只认为牧师的神职具有信仰价值的职业观,将大多数人的工作与他们的生命信仰严重地隔离开来,天主教会始终不承认俗人的行业在伦理上有什么可贵之处,它漠视世俗的劳动和营利活动,这一切大大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1517年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恢复了信仰的真义,使人们真正树立起了正确的职业观:从16、17世纪开始,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西方开始了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城市化和全球拓殖运动,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改变。一种积极人世、“人世修行”的人生信仰开始主导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对财富、牟利、工商业等经济活动,人们也给予了有力的肯定。而把职业看作确证自己人生信仰的一种方式,甚至推崇为“天职”的职业观念也开始形成了。这样,宗教改革者就不再视俗世内的劳动为“低下卑贱”,它大大提高了职业生活的道德性,并予以宗教上的奖励。这种来源于新教伦理“天职观”的现代职业精神(不是自古就有的,它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确立而确立的)也真正从这里开始奠基。由此可见,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和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的思想对西方职业观的革新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职业”一词的历史渊源
“职业”一词源于西欧,马克斯·韦伯指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词在文明语言中的历史,那就会发现,无论是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诸民族的语言中,还是在古代民族的语言中,都没有表示与我们所知的‘职业’(就是一种终身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这种意义而言)相似的概念的词。”⑥ 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马丁·路德。他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时,把《圣经》中“神的召唤”概念改造为“职业”。“职业”一词,在德语中是Beruf,在英语中是Calling,Calling是Call的动名词形态,是呼叫、召唤、呼召的含义。在现代英文中,Vocation是“工作、职业”的意思,但它也是“天职、神召”之义,Vocation来自拉丁文Voco,是个动词,意为“召唤”。路德认为,职业,亦即神的召唤,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终身任务。可见,“职业”一词是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并且从“职业”的词源上,我们看到职业与呼召的密切关系。
中国基督教所用的《圣经》,有一节经文是,“要尽你的本分,并为之勤勤恳恳”。希伯来文的“本分”,原为一般意义上的任务工作;但希腊文《圣经》用的是带有“天职”意义的Kleesis,意为出于上帝的召唤、出于上帝的使命或上帝所安排的职业,暗示着一种宗教观念,即上帝安排的终身使命。韦伯进而指出:“和这个词的含义一样,这种思想是新的,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产物。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从而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为具有了宗教意义,并且由此创造出这种意义上的天职概念。于是,这种天职概念为全部新教教派提供了核心教义。”⑦ 据这种新概念,要求个人履行他今生今世应完成的任务,即他所承担的“天职”。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都是神的召唤,所有的职业都是正当的。
我们知道,路德提出职业的思想是为了反对天主教的传统教义和修行方式,修道士生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修道士放弃现世的生活义务,是自私的、逃避世俗责任的表现。与此相反,履行职业道德在路德眼中则是同胞之爱的外在表现,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个人道德生活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这一思想使人们日常的世俗生活有了宗教意义,这样,由职业思想便引出了一切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路德用“职业”一词把世俗的工作和劳动与宗教的生活联系了起来,这就为宗教直接影响现实生活开辟了道路。可见新教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伦理中解救出来的心理功用,新教不仅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直接视作上帝的旨意,即职业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这样一来追求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而非自己的贪欲,将俗世中的工作当作信仰对待,这就是职业精神的本源。
(三)天职与呼召
“呼召”的内涵。既然“职业是神的呼召”,那什么是呼召呢?在西方世界中,“呼召”一词含有非常神圣的含义,在《圣经》中,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受耶和华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一节经文的名字就叫" The Call of Abram" (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离开本地、回应召唤,成为富甲万国、繁衍众多的君王。以色列人的另一个大英雄摩西,被赋予了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使命。" God called to him out of the bush,Moses,Moses"。⑧ 上帝在何烈山上呼叫:“摩西!摩西!”摩西应承呼召,排除了千难万险,最终将以色列人从受压迫的埃及带出来了。
但是,在近代以前,人们认为只有牧师的神职是呼召,只有神职具有信仰的价值,才是神圣的,而一般人的工作只是惩罚或者是无可奈何的存在。宗教改革后,路德和加尔文高举“人人为祭司、人人有呼召”的口号,认为呼召不限于灵魂得救,也包括了我们的职业或工作;不仅牧师的神职是呼召,而且人间的任何合法职业都是呼召,商人、医生甚至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当牧师。这样,任何工作都可以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事业,一切正当的行业都具有神圣的意味。呼召就是你在心灵深处受到生命的呼唤,这种呼唤在叫着你的名字,并且赋予你干什么的职责。呼召实际上就是人生的职责、生命的天职。
伯坚斯的《论人的天职和呼召》中写道:“牧羊人看守羊群的行为,若像我所说的一样去执行,那么在上帝的眼中,他们做的就和下达判决的法官,或执行统治的官员,或是讲道的传道者一样,都是良善的工作。”我看到美国《生命·工作》一书中写道:“对于那些认为生命已呼召自己的做某一特定工作的雇员来说,每天在办公室或其他工作场合所发生的波折对他们的影响是极小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而是他们的依托完全在于生命本身。”西方国家对那些认为工作就是自己生命呼召的雇员的评价是这样的:“他们比较稳定,有信心和热情,愿意负责任,乐观、自信且可靠。”
最后要说明的是,生命的呼召中包含了生命的全部内容:工作、家庭、生活、游乐等。尽管工作是呼召的重要内容,但它决不能代替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喜乐和满足。这一切正像英国作家R·肯特·休斯(1900-1976)所说:“无论生命召你做的工作是什么,你都要为此做好准备,就像鸟类准备飞翔一样。如果你干的正是生命召你做的工作,你就既能在工作中变得越来越出色,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真正的自我。”的确如此,人们只有对工作树立了一种神圣感,只有当工作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做到勤奋敬业、遵守道德操守,工作也才有意义。同时,呼召的思想使我们拥有对工作坚定的态度和永恒的信念,这种屹立不动的态度和信念让我们能不断地战胜工作中的困苦和烦恼,永远走在生命的真道上。
三、新教伦理中职业精神的现代意义
基督新教伦理中的天职思想提高了世俗工作的地位与价值,肯定了工作具有的神圣意义,弥合了信仰与工作的分离。尽管西方社会与我们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宗教背景,但在职业观的发展更新上,新的思想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是的,职业具有神圣的意义,它是确证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是人类生命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尔文给现代人指出:人应该积极地在这个世界上确证人生意义,应该“入世修行”,因为“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而人的职业就是我们在世界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
马克思曾经针对这一运动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宗教改革把僧侣变成俗人,而把俗人变成僧侣。”的确,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都成为无比神圣的敬拜。我们的工作开始具有了无比崇高和神圣的价值。建国初期的美国人认为:“建造工厂的人就是建了一所圣殿。”
“职业是呼召”虽然有着西方文化背景,但我们同是人类,就同有生命,同有生命的召唤。职业是生命召唤的思想,是现代职业精神的精髓,它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它使日常工作获得了尊严和神圣感,使得不事生产的有闲阶级和默想的行为失去了卓越的地位。它也使工作、勤俭及理性计划等类实务获得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准备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它还使卑微的人及其职业获得与他人的同等重要性,成为走向现代和民主社会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曾有学者解析为什么德国人能够生产出宝马、奔驰等世界一流产品?因为德国是新教改革最早的地方,德国人出于对宗教的虔诚而工作。德国人在职业上跳槽的很少,因为他们认为工作无贵贱之分,只要是上帝安排给自己的工作,都是神圣的,一定要将工作做好,来荣耀上帝,并且不会轻易违背契约。正是德国人的这种职业伦理将德国产品造就成为世界精良的产品。正像美国作家比尔·海贝斯所说:“工作不是一种惩罚,也不是人们经过思考后想干的事。工作是一种神圣的安排,是造物主用快乐和有意义的活动填补人类生命的一种方式。”在他们看来,工作是实践生命信仰的方式,职业的终极目的在于生命的丰盛与完满。如果我们树立了这样的职业观,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人生信仰与工作融为一体,如果我们在职业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我们的工作与职业就恢复到它最原初、最完美的状态之中。的确,基督新教认为人们工作最深刻的动机是事奉上主,有着宗教的内涵,但我们在工作中缺乏的就是这种神圣感,就是这种将工作当作生命召唤的精神。
一个伟大的事业背后就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在起作用。这种将工作上升到信仰高度的职业精神和伦理观念,是西方国家教育、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综合国力和影响力日益提高的重要精神动力和支撑点之一。西方国家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观由于其文化宗教背景,未必完全适合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职业界和从业者,但其对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益合理的部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借鉴。新世纪,对于一个要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更好发展的国家来说,内在的对职业精神的敬畏和信念远比外在的制度重要得多;对于一个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来说,对生命信仰的追求和对职业的忠诚态度远比对物质追求重要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也应该为现代社会中的“职业”注入更多信仰内涵和责任意识,将“现代职业精神”上升到我国国家意志和精神层面上,真正从文化观念上倡导、动员全社会和职业界,教育、培养和弘扬全民性的职业精神,从而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步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更多更深的内涵。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0页。
②[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22页。
③顾忠华著:《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④根据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⑤[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6页。
⑥[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8页。
⑦[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
⑧曼德著:《新职业观》,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