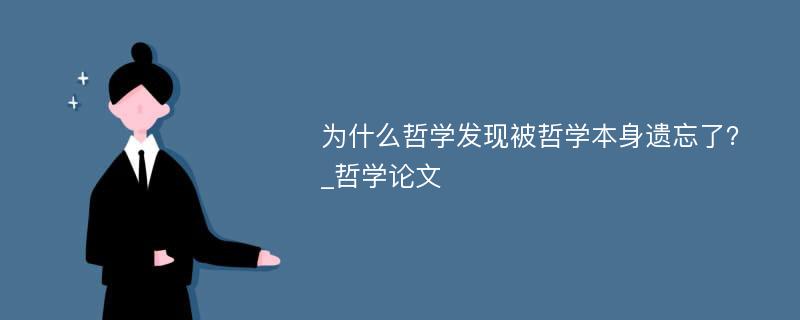
哲学发现为何被哲学自身所遗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科学发现问题不仅是科学家的兴趣所在,而且是哲学家的关注对象;科学哲学的兴起更使其成为哲学的前沿问题。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哲学发现问题非但没有进入任何科学家的理论视界,而且一直为哲学家们所忽视或遗忘。这种理论状况无疑极其不利于哲学的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哲学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哲学发现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作为这种探究的“抛砖”之作,本文拟对哲学发现的合法性及其被哲学自身所遗忘的根源作一初步探讨。
一
任何理论活动都是主体的功能性活动。哲学研究作为主体的一种功能性活动,必然将“发现”设定于自身的目的结构之中。这是因为,任何功能性的活动都是一种探索性的活动,而探索性活动的结构要素之一便是对未知或不明性存在的寻求与发现,而理论的探索意味着主体认识的“内乏”,意味着探索主体欲以“发现”克服自身认识的“内乏”。理论的发现对主体认识“内乏”的克服,是一无限过程,从而任何发现对主体而言,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哲学的发现同样如此。
波普尔曾说过:生命就是发现新的事实、新的可能性。①哲学是生命的高级表现方式,从而必将以“发现”为己任,只是其所欲发现的对象与它种探索活动所欲发现的不同罢了。事实上,哲学本身的生命力正是以哲学上的“发现”得以呈示的。哲学倘若不以“发现”为己任,便将失去其存在的动因;若不能有所“发现”,便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哲学固然是哲学“发现”的“居所”或“家园”,而哲学“发现”却是哲学的“心脏”、“主核”。哲学发现永远离不开哲学的“家园”,而哲学同样不能脱离哲学发现而生存。
哲学是从“寻找”或“寻求”宇宙万物的“始基”开始其生命历程的,而任何“寻找”都内在地设定了“发现”的“在场”。没有“发现”的冲动,便没有“寻找”的生成。发现既是寻找的动因,也是其唯一有意义的结果。当泰勒斯宣称万物的始基是水时,他正是将之当作了自己有意义的“发现”。
范畴是哲学理论的细胞。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范畴恰恰“暗示”了哲学与“发现”的不可分割。例如,从柏拉图到胡塞尔都一直使用的“Idea”(理念)范畴,在希腊文中正是来自“eido”(发现)。再如,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现象”与“本质”,也将“发现”内设于其中了。因为,本质作为现象之中或背后的一种相对稳定性存在,并不是直接呈现给主体的。本质的“呈现”须有一番经过中介的“发现”过程。本质的突破现象而“呈现”,依赖于主体的“发现”。
所有进入哲学“圈”内的哲学家都是被“发现”的冲动“推入”的。被发现的冲动推入哲学的哲学家们,有的虽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哲学发现”这一概念,但却通过自己的实际探索“默认”了哲学发现的“在场”;有的则明确“标识”了哲学发现的概念。
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标识:“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譬如,苏格拉底,我们可以说,曾经发现目的这一范畴。”②文德尔班把下面这一结论称作是黑格尔的哲学发现,即:哲学史既不能阐述各位博学君子的宠杂的见解,也不能阐述对同一对象的不断扩大、不断完善的精心杰作,而只能阐述理性“范畴”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意识并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那种有限过程。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叫作笛卡尔的“发现”。④此显然是哲学发现。后来,在《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一文中,他又曾提到黑格尔与胡塞尔的哲学“发现”。前苏联哲学家、《康德传》的作者阿尔森·古留加认为,理性的“二律背反”是康德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的发现”。⑤穆尔则这样说过:“描述词理论是新颖的。这是罗素在哲学上的最大的发现。”⑥艾伦·伍德也曾反复提到罗素“哲学上的发现”。
波普尔更是多次明确提及哲学上的“发现”。他认为,哲学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也是可以列入其最高成就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一个谜、一个问题。他将“逻辑上可能的将来观察不可能和过去观察的类相矛盾”,称作为“休谟的发现”。在《历史上的猜想和赫拉克利特论变化》一文中,他又一再指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发现”的重要意义。⑦他还特别强调:“一个哲学问题的发现可能是最终的,它是一劳永逸的。但是一个哲学问题的解决却决不是最终的”。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理论视界中,哲学发现的概念同样有其明确的“合法性”。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而唯物史观正是其哲学上的伟大发现之一。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又将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和他以及狄慈根的哲学发现。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⑨列宁也认为,狄慈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⑩
显然,哲学发现的“合法性”并非一种自我生成,而是由其对思维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意义所赋予的。
任何真正的哲学发现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并非世界之外的遐想,“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1)而具有初创或再创性质的哲学思想,正是哲学上的“发现”。哲学发现是哲学思想的创造性映现。哲学的一切功能首先是由哲学“发现”实现的。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发现,总是程度不同地掌握着时代的脉博与流向,定规与整合着人们的思维视角。
哲学“发现”对于思维进步与社会发展的意义,是在作为其“家园”的哲学的历史运演过程中,不断得以呈示的。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没有别的手段”。(12)所谓“学习以往的哲学”,首先是学习、“消化”历史上作为“哲学发现”而生成的哲学观点和理论。在哲学发现中,最主要的是哲学问题的发现,而哲学问题的发现,正如赖欣巴哈所说的,“其本身就是对于智力进步的重要贡献”。(13)事实上,哲学史上的许多问题的发现,都启迪了科学家的思维,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并通过科学推动了社会的前进。“社会若不明哲学则盲”(14),而哲学用以照亮社会的,主要是作为哲学发现的哲学思想或理论。
由上可见,哲学发现问题之被哲学自身所“遗忘”或忽视,既不是由于哲学中无发现,也并非因为哲学发现无意义。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追问”哲学发现问题被忽视的根源。
二
任何追问都是一种努力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其所寻求的对象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15)哲学发现作为哲学的“主核”,其特征与机制之被探究只能是哲学自我反思的“最后一站”。认识之为认识,首先是外向性的认识。只有经过外向性认识的中介,认识才能返回自身,达到自我反思。哲学作为主体认识的一种基本方式,同样如此。哲学的自我反思是哲学的“成熟”表现,而任何成熟,都不是在成熟者的初始历程中实现的。成熟需要孕育,需要“锻炼”。哲学正是通过对“非自身性对象”的认识的“锻炼”,方“孕育”出自我反思之“成熟”的。
哲学之自我反思固然从其诞生初期便已露出端倪,然而,这种“自我反思”并未经过外向性认识的中介或“锻炼”,因而不是作为“成熟”表现的自我反思,或者说就根本不是自我“反思”。它只是一种理论交往之前的“自我介绍”。诚然,任何“自我介绍”都须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为准备,但作为自我介绍之准备的“自我反思”,尚是一种不成熟的自我反思。它只停留于对自我表象整体的反思,并未深入自身的内部,更未对自我进行“解剖”,以达深刻、成熟之自我反思。
当然,纵使哲学进入真正的“成熟”之自我反思,也并不能将之瞬息完成。“成熟”的哲学自我反思虽然经过了外向性认识的“锻炼”,但仍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乃是更加成熟之自我反思之前的继续锻炼”。
本来,哲学已是一种反思,所以,哲学的自我反思便是认识的“自我反思之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反思之自我反思”之前的自我反思,恰好构成了其准备与“锻炼”。相对于哲学的自我反思,其之前的作为一般认识的自我反思,只能是外向性的认识,因此我们前面说,哲学的自我反思必须经过外向性认识的准备与“锻炼”。当然,这种外向性认识,就其是一种自我反思而言,仍是一种内向性认识。
经过了外向性认识之“锻炼”而生成的哲学的自我反思,并不能直接指向作为其“主核”或“心脏”的哲学“发现”。哲学对哲学发现的反思,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这条件首先便是哲学的“纯化”。所谓哲学的“纯化”,就是哲学“交出”本该属于科学的地盘,只为自己留下作为纯粹反思之对象的“思想”。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16)哲学的“纯化”是哲学与科学分化的彻底完成。显然,只有哲学与科学分化的彻底完成,哲学才能将反思的方向无碍地瞄向作为其“主核”的哲学发现。哲学与科学的分化倘若尚未完成,那么,它就须为本不该属于自身的对象而“分神”,于是,便难以进入成熟的自我反思,更难进入对作为自身“主核”的哲学发现的反思。
自然,哲学的“纯化”作为哲学反思哲学发现的首要条件,并不能绝对保证这一反思的生成。事实上,对哲学发现的哲学反思,不仅须有哲学的“纯化”为前提,而且须有哲学对其自身“合法性”或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倘若在哲学内部,其存在的合法性或积极意义得到充分的肯定,那么,对哲学发现的哲学反思便难以实际生成。此在于,如果哲学自身的合法性或积极意义得不到其自身的充分肯定,那么,作为哲学之“主核”的哲学发现,便同时失去了其“在场”的地位和积极意义。离开了哲学发现的“在场”和积极意义,也就难以实现哲学对哲学发现的反思。而实际上,在哲学与科学的分化完成之际,一股贬低哲学的价值、否认其存在合法性的思潮已经涌起。正是这股思潮使得哲学对哲学发现的反思被“耽搁”或“遗忘”了。
海德格尔曾抱怨,“康德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17)我们在此不欲抱怨“反哲学家”们耽搁了哲学对哲学发现的反思,但却须明确承认,对哲学发现的哲学反思,确乎由于贬低哲学价值和否认哲学存在合法性的思潮的冲击,而被哲学“耽搁”或“遗忘”了。
西方“反哲学”的思潮最初是从实证主义流出的。实证主义者公开打出“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帜,对一切传统的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虽然并未明确宣布整个哲学的死亡,但实际上却通过科学对哲学的“同化”,取消了哲学。孔德声称,“合法”的哲学只能是他的“新哲学”,即“实证哲学”。在他看来,“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是同等的东西。(18)孔德将“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相等同,当然不是欲以哲学来“同化”科学,而是要以科学来“同化”哲学。以科学同化哲学,实质上是要取消哲学。在实证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斯宾塞那里,“哲学乃是最空洞的东西”。(19)
实证主义对哲学价值的贬低和否定,得到了海德格尔的同情。他接过“反对形而上学”的大旗,对哲学进行了无情的“摧毁”。他声言,“哲学消散在几种特殊科学中了:心理学、逻辑、政治学。”而控制论的兴起则直接“代替”了哲学。(20)最终,他毅然宣布哲学已经“终结”。
分析哲学的崛起,使国际范围的“反哲学”思潮势不可挡。罗素早就指出:“只要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问题。这并不是由于任何偶然,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每个哲学问题,当经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时,就可以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是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含义的逻辑问题。”(21)罗素事实上正是企望用数理逻辑的分析来取代全部哲学。他甚至把哲学说成是“一个骗人的学科”,并且规劝年青人不要在哲学上白费时间。他说:“牛津哲学家已表明哲学是胡说。我如今只能不胜懊悔我那虚掷的青春。”“我痛苦地被迫相信,称为哲学的东西十分之九都是骗局。那唯一完全明确的部分就是逻辑,既然它是逻辑,那它就不是哲学。”(22)于是,哲学在罗素那里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维特根斯坦不仅否定哲学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将“消灭哲学”当作自己哲学活动的唯一目标。他曾对他的学生说:学哲学犹如下地狱,教哲学如同活生生地在死!维特根斯坦的具体哲学观点虽然曾多次发生变化,但他消灭哲学的目标却始终没有改变。他始终不渝地在为消灭哲学而奋斗。他认为,死亡(指作为哲学家的死亡)对于他和所有其他哲学家都是无法逃脱的。(23)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之所以必然“死亡”,是因为哲学命题和问题的无意义。他指出:“大多数有关哲学的命题和问题不是错误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所有这种无意义的陈述我们是不能回答的。”(24)既然哲学命题和问题是无意义的,那么,作为一种学问的哲学当然也就成为“多余之物”;既然哲学是多余的,也就必然死亡。
反哲学思潮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思潮,是由许多“反哲学家”的思想汇合而成的。根据美国学者R·霍林格尔的分析,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为一切知识奠定阿基米德点,并给人生指示可靠的行为准则。而“反哲学”则要对哲学的这种“雄心”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在“反哲学”看来,哲学寻找知识阿基米德点的“冲动”,“根本上是乌托邦的”。在“反哲学”看来,随着基础主义的死亡,作为一切学科基础的哲学也必死无疑。德里达宣称,要通过“解构”,摧毁形而上学的“暴力”。拉康公开叫喊:永远不要求助于任何实体或存在,要“与一切被称为哲学的东西断决关系。”列维纳斯表示要与巴门尼德--哲学之父决袭。福柯宣布,作为寻求终极知识的哲学已经寿终正寝。(25)罗蒂则把“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作为写作《哲学与自然之镜》的目的之一。(26)
在强大的反哲学思潮的冲击下,“哲学经历了一种明显的贬值,即使未被消灭,也降低了威望。”(27)其合法地位受到了普遍的怀疑。
反哲学思潮所酿造的贬低、反对哲学的情绪,也波及到中国当代哲学界。在这种情绪熏染下,“哲学危机”、“哲学无用”几乎成了哲学圈外圈内的“共识”。一些哲学学者无可奈何地宣布,哲学只不过是陈词滥调加胡说八道。如果说哲学圈内尚存有哲学的一丝信心,那便是对应用哲学的寻构。然而,这种寻构似乎并未获取什么成功。至今,尚无成功之应用哲学问世的息讯。
哲学是哲学发现之“家园”。反哲学思潮的汹涌冲击,使世界哲学大厦有摇摇欲坠之势。于此局态下,以哲学为“家园”的哲学发现,当然难以进入哲学家们的兴趣域内。于是,哲学发现问题的探究便被哲学本身“遗忘”了。在科学发现问题不断萦绕于哲学家脑中之际,哲学发现问题却从哲学家们的理论视界中“隐退”了。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必然中的偶然。
然而,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对于主体而言,都非应取代应然。哲学发现问题不应该在哲学家的理论视界中“隐退”,它应凸现,它必须凸现,因为作为哲学发现之“家园”的哲学不应该死亡,也不会死亡。在哲学危机的时代氛围中,哲学应该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应该接受“反哲学”的挑战。事实上,就在哲学危机肇始者海德格尔宣布哲学的“终结”时,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却已在极力为哲学之合法性辩护了。这位哲学家便是与海德格尔齐名的雅斯贝尔斯。在《哲学之信仰》一开头,雅斯贝尔斯便发出了这样的呼声:“不能废除哲学”!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哲学是“常青的”,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讨论。他不象海德格尔那样以“反哲学”的态度皈依“本源”,而是以“超越的”(transzendental)态度回归“哲学之信仰”。(28)事实上,就连一些反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哲学之难以死亡。罗蒂便这样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均无哲学‘日暮途穷’之虞”(29)所以,他在宣布以往一切哲学之“终结”的同时,不得不开创“后哲学文化”。
历史表明,反哲学思潮之消灭或摧毁哲学的目标是无法达至的。在经历了与反哲学思潮的交锋之后,哲学必将以新的态势运行于人类知识的航程中。它将在与科学彻底分化的基础上,系统反思自身的历史行程和存在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人说当今的哲学家“比以往更加是元哲学家”。(30)
哲学系统反思自身之历史行程与存在价值的重要层面和径途,便是探究作为哲学之“主核”和价值基础的哲学发现。只有哲学发现的价值及生成机制等问题得以阐明,整个哲学的合法性方能得以有效的辩护;只有哲学的合法性得以有效辩护,哲学方能得以顺利地运作与发展;只有哲学得以顺利运作与发展,方能更加有效地促动科学、并通过科学促动社会的向前发展。
注释:
①参见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53页。
②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11页。
③文德尔班:《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页。
④(15)(1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7、30页。
⑤〔前苏联〕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页。
⑥转引自〔英〕艾伦·伍德:《罗素:热烈的怀疑者》,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⑦⑧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226、287页。
⑨(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53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⑩《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7、465页。
(13)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5页。
(14)〔台〕沈清松:《现代哲学论衡》序言,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
(18)(19)(21)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3、435页。
(20)参见1966年9月23日《明镜》记者与海德格尔的谈话,载《外国哲学资料》第五辑。
(22)转引自〔英〕阿伦·伍德《未完成的哲学》,载《外国哲学资料》第七辑。
(23)参见拙文《究竟有无哲学问题--评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的论战》,载《学术界》1992年第4期。
(24)转引自麦克斯韦·约翰·查尔斯沃斯:《哲学的还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25)参见王治河:《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非哲学”》,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26)(29)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
(27)N·弗拉瑟、L·尼柯尔森:《没有哲学的社会批判》,载英国《理论、文化与社会》Vol5(1988)。
(2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30)〔比利时〕G·赫特斯:《次要性:当代哲学的一个中心概念》,载《哲学译丛》199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