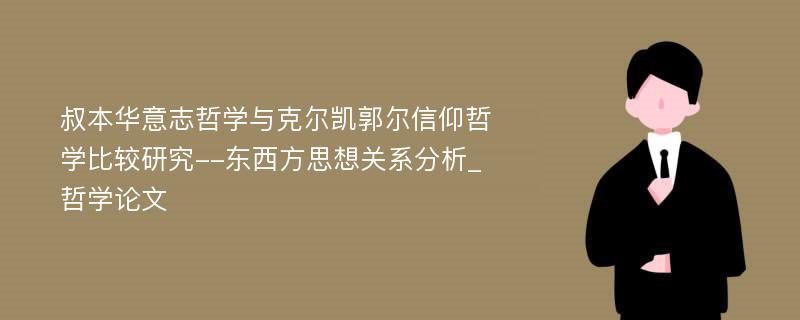
叔本华意志哲学与克尔凯郭尔信仰哲学的比较研究——兼析东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尔论文,哲学论文,东西方论文,意志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0)03-0008-07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是两个值得关注的人物。这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与传统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以传统宗教为归宿,但同时又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源泉。具体说,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通向东方古代的印度教和佛教,克尔凯郭尔的信仰哲学则企图回到使徒时代的原始基督教,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却并未妨碍他们一同成为在现代西方影响广泛的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本人也对他与叔本华之间的关系感到迷惑不解:他既为竟然存在着与他如此相似的哲学家而惊奇,同时又发现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对立。其实,从哲学史上看,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都处于近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汇点。对他们俩人哲学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了解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变,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东西方思想关系之谜的钥匙。
一、从神到人
要了解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现代转折的作用,就必须首先了解他们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换句话说,要弄清他们为什么要否定近代哲学而要求回到传统的宗教中去。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植根于西方近代哲学本身的矛盾,是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他们的哲学都是在批判近代哲学,尤其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从他们与康德、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弄清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都是起源于康德。康德划分了现象和自在之物,他一方面认为纯粹理性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认为实践理性能够达到自在之物。这样康德就利用实践理性把纯粹理性所不可认识的东西变成了可以认识的,从而指出了一条通向自在之物的道路。叔本华正是走在这条道路上,他说:“他(康德)没有直接在意志中认识到自在之物,但是他已向这认识走了开辟(新途径)的一大步,因为他论述了人类引为不可否认的道德意义是完全不同于、不依赖于现象的那些法则的,也不是按这些法则可以说明的,而是一种直接触及自在之物的东西。这就是用以看他的功绩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注: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75页。)这意味着,叔本华在康德关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划分的基础上,将其实践理性可以认识自在之物的观点发展为人可以通过直觉直接认识到自在之物是意志,从而建立起意志哲学。反之,克尔凯郭尔是从另一个方向继承和批判康德的。康德曾说自己划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目的是要限制理性而为信仰留地盘。这实际上预示着只能通过信仰来达到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这样康德同时指出了通向自在之物的另一条途径:自在之物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信仰的自身。克尔凯郭尔是由此出发的。他将基督教的基础建立在信仰而不是认识的基础上。人企图通过认识(不论是理性还是直觉)来达到自在之物是徒劳的。与叔本华认为康德的错误在于未能认识到存在着认识自在之物的另一条途径即直觉的途径相反,克尔凯郭尔认为康德的错误在于企图通过认识达到自在之物本身,因此解决康德自在之物困境的出路在于必须放弃认识而去信仰,因为惟有通过信仰而不是认识才能达到自在之物。从这里可以看出,叔本华意志哲学和克尔凯郭尔信仰哲学都继承了康德关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划分即理性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从而转向其他的途径。他们的区别在于人究竟能否认识自在之物,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叔本华在认为理性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另一条途径即直观的途径达到对自在之物的认识,而克尔凯郭尔则完全否定我们对自在之物的所有可能的认识。对于叔本华,意志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因而他用意志取代了自在之物。
在自在之物可以认识这一点上,叔本华和黑格尔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黑格尔用思辨理性认识自在之物从而得到绝对理念,叔本华用直观认识自在之物从而得到意志。但对于克尔凯郭尔,自在之物是我们根本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对于我们就是自在之物。在这里,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继承康德实践理性能够达到对自在之物的认识相反,他在康德否定理论理性能够认识自在之物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实践理性能够认识自在之物。这样他也就进一步割裂了康德关于现象和自在之物的关系。自在之物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因而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的。自在之物能否认识决定了叔本华、黑格尔同克尔凯郭尔对基督教的态度大相径庭。不论采取何种途径,只要认为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这就等于用人取代了上帝,因为自在之物是康德为上帝留下的地盘。叔本华和黑格尔否定自在之物,就消除或改造了康德哲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取消自在之物即认为人能够认识自在之物是从基督教走向无神论的关键一步。叔本华和黑格尔都迈出了这一步,尽管他们各自的方向并不相同,一个将自在之物意志化而走向印度教、佛教,另一个将自在之物理性化而步入绝对精神。叔本华用意志取代自在之物,意志的内在性取代了自在之物的超越性。他由此象黑格尔一样否定了作为超越者的上帝,成为走向彻底的无神论的先驱。尽管途径不同甚至相反,上帝对于叔本华和黑格尔都不再是不可达到的,因而上帝也就不再是原来的上帝。所以叔本华和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蕴涵着对基督教的颠覆。这在他们各人的后继者尼采和马克思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康德哲学中基督教因素的真正继承者是克尔凯郭尔。他既站在与叔本华一致的非理性的立场上反对黑格尔的理性,同时又站在与康德相同的基督教的立场上反对叔本华的意志(能够达到自在之物)。克尔凯郭尔把信仰建立在我与自身的分裂之上,信仰只是由于这种分裂才成为可能。我与自身的分裂就是人与上帝的分裂。如果说,叔本华用内在性抵消了超越性从而最终达到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那么,克尔凯郭尔则在我与自身分裂的基础上同时肯定了内在性和超越性。
从自在之物可以认识出发,叔本华和黑格尔都使上帝发生了从在我之外向在我之内的转变。就象上帝对于黑格尔变成了理性可以达到的绝对理念一样,上帝对于叔本华也变成了可以用直观达到的否定意志的象征。其实,意志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本身就蕴涵着意志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即意志的肯定本身就蕴涵着意志的否定,也就是虚无。正是因此叔本华才从正统基督教人与上帝的分离转向基督教神秘主义者“人与上帝的合一”。所谓“人与上帝的合一”的另一面就是虚无,因为这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此时已没有表述者和被表述者的区分。同时,解脱所谓“无我”的另一面也就是“真我”,只是由于“真我”不可表述而成为“无我”。这种“上帝—虚无”“无我—真我”都是对“我”的否定。“人与上帝的合一”和“解脱”都不是建立在我与我自身的分离,而是建立在我与我自身的统一的基础之上。“人与上帝的合一”是指我自身在我的里面,我也在我自身的里面,因而我是我自身,我自身是我。解脱则是指我自身在我里面,我也在我自身里面,因而既不存在“我”,也不存在“我自身”。因此,基督教神秘主义强调上帝在人的里面,当人寻找到自己里面的上帝而与他合一时,与上帝分离的人和与人分离的上帝也就不存在了。印度教和佛教强调“无我”“无物”、这种“无我”“无物”同时也就是“真我”(我自身)“真物”(物自身),因而当我达到“无我”“无物”时,我也就达到了“真我”“真物”,也就是我得到了解脱,因为此时再没有“我”与“物”,“我”与“我自身”的对立和区别了。可见,不论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还是印度教和佛教都要求人在自身之中,而不是外面寻找与上帝合一或解脱的途径。
与叔本华所谓“人与上帝的合一”基于人与上帝本来是同一的相反,上帝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基于人与上帝的绝对分离。上帝具有超越性和内在性意味着,一方面,上帝是超越者,因而是人的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信仰是荒谬,克尔凯郭尔引用《圣经》中亚伯拉罕服从上帝的要求,用他的独生子以撒献祭来说明这一点。虽然同是反对黑格尔理性能够认识上帝,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立足点不同。在叔本华看来,人不能认识上帝的根源在于人从外面寻找上帝,上帝其实是在人里面。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人不能认识上帝的根源在于上帝的超越性和内在性。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上帝绝对在人之上,因而人是不能凭自己达到的,自己是人与上帝之间的障碍。人只有否定自己,上帝才会成为他的上帝。亚伯拉罕正是因此才献出他的独生子以撒的。另一方面,上帝又具有内在性。上帝不仅高居于人之上,而且深藏在人里面。但这并不是象叔本华以及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那样要人在自己里面寻找上帝以达到“人与上帝的合一”,而是说上帝存在于人同他自己的关系之中。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祭的不是他的羔羊,而是他的独生子。这正体现出上帝和人的关系不是一种外在的可有可无的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具有必然性的关系。恰是由于上帝要求人献出的不是他的东西,而就是他自己,人才能被上帝所肯定。因此上帝对人的否定就是对人的肯定。由此人才必须严肃地对待上帝,因为上帝直接关系到他的存在本身。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特别强调“孤独个体”的原因(the solitary individual)。 只有在个人中才存在着上帝,因为只有在个人中才存在着人同他自身的关系。克尔凯郭尔将信仰建立在人同他自身的关系之中。人同他自身的关系是内在性的,不需要任何外在性的东西。这种外在性的东西是人脱离同他自身的关系,也就是脱离同上帝的关系的标志。正是在此意义上,克尔凯郭尔攻击丹麦国家教会背弃了基督教的真义,因为它把祈祷礼拜当成了对基督教的信仰,而基督教信仰的实质乃是人同他自身的关系。
叔本华从自身之中寻找上帝和克尔凯郭尔把人与上帝的关系理解为人与他自身的关系都改变了传统基督教人与上帝的关系。这是他们批判康德“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认识方式的结果。叔本华将康德“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认识方式改为“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的认识方式,从而彻底消除了我与我自身的分离,达到了“我是我自身,我自身是我”(人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人)。后者相对于前者的“我”和“我自身”来说是一种解脱,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后者又是对我和我自身的绝对肯定。从这里可以理解叔本华何以作为印度教和佛教的信徒同时又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最早流派意志主义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克尔凯郭尔则继承并发展了康德“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认识方式从而肯定了我和我自身的存在。我自身既是内在于我的同时又是超越于我的。当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时,一方面,我自身可以视为绝对在我之上,因为我自身因我把自身当成对象而在我之外,我也在我自身之外。另一方面,我自身可以视为仍然在我之内,因为我自身不可能成为我的对象,即使我把我自身当成对象。这意味着上帝从一方面说是对我的绝对否定,我惟有否定自己才能达到上帝,从另一方面说上帝又是对我的绝对肯定,对上帝的肯定就是对我自身的肯定。从这里可以理解克尔凯郭尔何以作为一个神学家同时成为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存在主义的先驱。因此,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尽管都具有强烈的宗教倾向,并且他们的宗教倾向截然相对,但他们的哲学却蕴涵着共同的结论即都是对人和现实世界的肯定和对神和彼岸世界的否定,尽管他们本人对此并无清醒的认识。(虽然他们都对传统宗教表示了强烈的怀疑甚至达到与之决裂的程度,但他们主观上的目的却仍是要恢复和拯救这一传统信仰的实质和核心)这反映了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他们既代表着西方古代传统宗教的终结,同时又是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开端。
理解了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在古代和现代哲学关系上的殊途同归,也就理解了他们在东西方思想关系上的地位,也就是为什么叔本华是东方似的宗教无神论者而克尔凯郭尔却是基督教神学家。对于叔本华,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因而对于我也就不存在什么在我之外的自身,而对于克尔凯郭尔,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因而我必须肯定在我之上的自身。作为宗教无神论者的叔本华和作为神学家的克尔凯郭尔既是对立的,又是相通的。叔本华表现的是在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前提下的我与自身的关系,而克尔凯郭尔表现的则是在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前提下我与自身的关系。在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前提下,我不寻求自身,因为自身不是我的对象,我寻求自身反而会失去自身(失去自身是寻求自身的前提,因而寻求自身必导致失去自身)。但在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前提下,我必须寻求自身,因为自身对于我变成了我自身和对象自身。我必须寻求我自身,因为只有在我自身中我才能存在。但我自身对于我又表现为对象自身,因而又是我所不可企及的。我与自身之间的分裂就是造成人和上帝的隔绝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信仰才能使我和我自身、人和上帝重新融合。因此,理解我与自身的同一才能理解叔本华,而理解我与自身的分裂才能理解克尔凯郭尔。理解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也就是理解东方的印度教、佛教和西方的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都从康德出发,从非理性的角度反对黑格尔的理性哲学,但他们一个通向意志(印度教、佛教),另一个通向信仰(基督教)。
二、意志和信仰
在康德证明理性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之后,叔本华用直观代替理性,克尔凯郭尔则用信仰代替理性。从方向上说他们是正相反的,因为直观是建立在我与自身的同一(我就是自身,自身就是我)之上,而信仰则建立在我与自身的绝对分离(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之上。因此,叔本华的意志和克尔凯郭尔的信仰既存在着一致性,同时也存在着对立性。
所谓理性其实是“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意识。“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从一方面说,确实是从对“我是自身,自身是我”的误解而来,因而通过“我是自身,自身是我”就可以解除由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而产生的我与自身的分离的问题。这一过程表现为“我是自身,自身是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我是自身,自身是我。从另一方面看,“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也的确造成了我与自身的绝对分离,因而只有通过“我把自身当成自身”才能消除这种分离,实现我与自身的统一。这一过程就是“我是自身,自身是我”→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我把自身当成自身→我是自身,自身是我。这里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遭遇代表着东方和西方,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两大传统的遭遇。印度教、佛教正是从“我是自身,自身是我”出发否定“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因此它们才反对人求佛求道。显然,求佛求道就会导致“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而所谓“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其实只是“我是自身,自身是我”的反面。就是说,“我不是自身”其实仍是“我是自身”,“自身不是我”仍是“自身是我”。反之,基督教则是从“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到“我是自身,自身是我”,因此基督教才如此强调人必须信仰上帝。我从“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不可能达到“我是自身,自身是我”,因为“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是对“我是自身,自身是我”的否定。基督教把“我是自身,自身是我”和“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理解为彼此绝对对立的关系。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在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正是因为“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不再信仰上帝,而是把上帝当作认识的对象。亚当和夏娃企图通过偷吃智慧果而使自己也象上帝一样心明眼亮)才导致了我从“我是自身,自身是我”(伊甸园里人与上帝的和谐)堕落到“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尘世上人与上帝的分离)。因此我只有通过反向的运动即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到“我把自身当成自身”(放弃认识而去信仰)才能使我摆脱“我不是自身,自身不是我”,而重新回到“我是自身,自身是我”(人与上帝的重新和谐)。因此,与印度教、佛教否定“我寻求自身”相反,基督教执著于“我寻求自身”。
这正是造成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上尖锐对立的原因。印度教和佛教说的是自身无论如何都并不在我的外面,因而我不能追求自身——追求自身反而使我离开了自身。基督教说的则是我在自身的外面,因而我必须追求自身,否则我便不能存在。因此,印度教和佛教是从我自身对我,基督教则是从我对我自身的关系上说的。我自身对我,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我自身的外面,所以不能有我;我对我自身,我无论如何都在我自身的外面,所以不能没有我自身。前者的重心放在无我上面,后者的重心则放在我自身上面。这就使得印度教和佛教解脱的清静超然与基督教的狂热信仰形成鲜明对照。尼采指出,再没有什么东西象使徒保罗那种信仰的狂热更不适宜于佛教的了,反之亦然。
然而,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在信仰上的这种对立都是产生于人本身所固有的同一困境:对于人来说,自身是什么?自从人作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有意识的自觉的存在者产生以后,自身是什么对于人就形成了一个必须回答而又无从回答的谜。对这个谜的不同提问和解答方式导致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传统。追根溯源,造成“自身是什么”形成困境的根源在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因而要回答“自身是什么”就必须否定“我把自身当成对象”(这表明宗教是伴随着人的意识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人的意识的存在而存在)。东西方宗教在否定人的意识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是由宗教回答“自身是什么”的问题的使命所决定的),正象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所做的那样。这说明东西方宗教尽管取向相反,形态各异,但却有着共同的人自身的根基。不过,否定“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却有着两种相反的方式: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与我把自身当成自身。正象地球被区分为东西两个半球一样,东方和西方也采取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也正象地球尽管分为两个半球,而实际上仍是一个地球一样,东方和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也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因而既没有我,也没有我自身。我与自身是印度教和佛教“圆融无二”的关系。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因而我必须把自身当成自身,我与自身是基督教所谓人与上帝绝对分离的关系。前者是要在理性产生的萌芽时期就将其消除,方法是把理性与信仰融为一体。理性即是信仰,信仰即是理性(佛教被称为“智信”,而非“迷信”)。后者却将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因为理性否定信仰,所以信仰否定理性。信仰高于理性。(西方文明由古希腊理性文明和古希伯莱信仰文明构成并不是偶然的。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与我把自身当成自身是对立的,前者是我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我与自身之间的关系,但两者都蕴涵着我——对象——自身,只不过前者是我从对象到自身,后者则是我从自身到对象。)我把自身当成对象造成“我在自身之外,自身在我之外”,因而我只有不把自身当成对象,把自身当成自身才能使我重新在自身之中,自身重新在我之中。因此前者的途径是“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后者的途径则是“我把自身当成自身”。前者面对的是“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与“我把自身当成自身”之间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佛教说迷和悟,基督教则说罪和信的对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
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我把自身当成自身
对于前者,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代表着迷。而对于后者,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则代表着原罪。前者的方向是指向过去(本来),后者的方向则是指向未来,即前者是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回到我不把自身当成对象,后者则是从我把自身当成对象走向我把自身当成自身。
叔本华从理性走向意志进而从基督教转向印度教和佛教与克尔凯郭尔从理性走向信仰进而回到原始基督教信仰,是他们分别以与黑格尔不同的方式克服康德的自在之物的结果。黑格尔通过把自在之物看成是空虚的对象而予以抛弃,叔本华则认为自在之物就是主体自身而否定自在之物,而对于克尔凯郭尔,自在之物不是对象,而是自身,因而自在之物不仅没有被取消,反而变成了上帝。抛弃自在之物(对象)而使主体成为唯一的东西,这是导致黑格尔绝对哲学和叔本华意志哲学的原因。使自在之物变成上帝则使对象自身成为唯一的。这是导致克尔凯郭尔只有上帝是万能的神学思想的原因。可见,面对康德自在之物的困境,黑格尔是通过回到古希腊理性传统而给予理性的解决,叔本华是通过走向东方印度教、佛教的古老传统而给予意志即直观的解决。克尔凯郭尔则是通过回到古希伯莱的宗教的传统而给予信仰的解决。在非理性的解决这一点上,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一致而与黑格尔相反,但在非理性的解决的途径上,克尔凯郭尔与叔本华相反而与黑格尔相似,他们都隶属于西方文明传统,而叔本华则已走到东方文明的传统上来,这表现在克尔凯郭尔对黑格尔的了解远比叔本华更为深刻。他是把叔本华直接作为对立面来批判的,他与黑格尔的对立实际上代表着信仰与理性,或者说构成西方文明两大传统的古希伯莱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之间的对立。相比之下,叔本华对黑格尔其实并不了解。他是把黑格尔作为间接的对立面来批判的。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对立代表着西方理性的文明与东方直觉的文明之间的对立。这两种文明基本上是各自孤立发展起来的,尽管叔本华也想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认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可能来自印度。克尔凯郭尔认真地思考过黑格尔,他对黑格尔思考得越深,他越是能够看清黑格尔的要害——他的庞大的理性体系缺乏自身。叔本华却不需要这样做,他正是因为不了解黑格尔,才得以从直觉上批判黑格尔哲学不是对自身的认识。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仅止于漫骂。
对黑格尔的这种不同特色的批判是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分别用信仰和直观来否定理性所决定的。叔本华用“我与自身的直接同一”否定了康德“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认识方式,这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历史。叔本华对此有所意识,他说:“我的哲学在其深层次的基础中有别于所有现在的哲学(但在一定层次上柏拉图的哲学除外)。”(注:G.F.贝霍夫斯基著.刘金泉译.叔本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叔本华所指出的方向是回到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和东方古代的印度教、佛教传统——尼采正是从这里出发开始批判苏格拉底,要求回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尤其是赫拉克里特的非理性主义传统。叔本华是从“我与自身的直接同一”出发的,所以任何导致我与自身分离的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理性即“我把自身当成对象”正是导致我与自身分离的活动。“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使我脱离了自身,使自身脱离了我。因而,对于“我是自身,自身是我”来说,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就只是一种迷误。尼采自觉地看到了这一点,把西方现代哲学重新回到古希腊哲学,尤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看作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正象克尔凯郭尔把“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作为非信仰予以否定一样,尼采也把“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作为一种迷误予以抛弃。正是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尼采才得以跨过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发出震撼西方的惊呼:形而上学成了假象,“上帝死了”,剩下的只有“成为你自己”。与叔本华相反,克尔凯郭尔是从“我与自身的绝对分离”出发否定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在他看来,任何脱离这一起点的把我与自身直接统一起来的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统一活动不再把自身当成自身,而是变成了对象,这实际上是从“我把自身当成自身”到“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即从信仰到理性。我把自身当成自身只能是信仰,而不能是理性。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就只是理性,而不是信仰。换句话说,我把自身当成自身是对我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否定,反之亦然。正是因此,克尔凯郭尔才跨越了中世纪以来长期统治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要求直接回到使徒时代的原始基督教那里,他要求的是作为个人实践和信仰的基督教,而不是空洞理论的基督教。这意味着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成为“孤独个体”,因为真实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在“孤独个体”之中。
可见,尽管叔本华“我与自身的直接同一”与克尔凯郭尔的“我与自身的绝对分离”截然对立,但他们在否定“我把自身当成对象”上则是完全一致的。否定“我把自身当成对象”对于叔本华意味着“我是自身,自身是我”,而对于克尔凯郭尔意味着“我把自身当成自身”。这样,尽管途径不同,他们都消除了我与自身之间的距离。对于“我是自身,自身是我”来说,自身并不在我的外面,我就既不把自身当成自身(信仰),也不把自身当成对象(理性),而是我就是自身,自身就是我(直觉)。这意味着我既不再是信仰的我,也再是理性的我,而是直觉的我。叔本华的圣人和尼采的超人都是由此而来。与此不同,“我把自身当成自身”表现为自身对我的一种绝对的要求:我只能把自身当成自身,而不能当成对象。只有在我把自身当成自身的情况下自身对于我才是自身。把自身当成对象,自身对于我就不再是自身,而是非自身。表面上看来,我把自身当成自身造成了我与自身之间的无限的距离,而实则将我与自身之间的距离无限地拉近了。我与自身的无限的距离只是就我不能把自身当成对象而言,自身永远在我之上,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自身。我与自身的无限接近则是指我因把自身当成自身而使自身在我之中——自身是否在我之中取决于我是否把自身当成自身。只有在我把自身当成自身的条件下自身才在我之中。在克尔凯郭尔看来,是我如何信仰决定了我信仰的对象是否真实,这就是说,我信仰的对象是否真实取决于我如何信仰。信仰的重心就随之从信仰的对象那里转移到信仰者自身那里。这样殊途同归,从基督教转向印度教、佛教的叔本华,要彻底否定基督教的尼采就与要回到原始基督教的克尔凯郭尔走到了一起。
叔本华意志哲学和克尔凯郭尔信仰哲学的殊途同归不仅表现了西方哲学在现代开始摆脱传统的基督教而转向现代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向,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东西方思想在宗教无神论和有神论上是正相对立的,但这种对立必须同时被视为仅仅是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不同理解方式和解决方式。在根本的意义上,东西方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彼此融为一体的。这就是说,东西方思想都植根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这一基本问题,因而它们之间并不仅是相互对立、斗争,或此或彼的关系,而且是相互补充、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后者正代表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东西方之间这种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反侧面的复杂的关系,诗人柯普宁曾在一首诗的的开头和结尾做过生动的描述:“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一对孪生子从不相遇。”“但是当两个壮汉面对面之时,既没有东方也没有西方,界限既没有孕育也没有产生,即使他们来自天涯海角。”(注:A.J.巴姆著.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叔本华意志哲学和克尔凯郭尔信仰哲学的相反相成就属于这种情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把东西方思想看成是简单的对立或同一的关系,而必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从一种动态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它们,但在现实中却往往不乏这种简单化的例子,如当代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从西方文明出发,将东方文明看成未来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威胁,而东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走向衰落,21世纪将是东方文明,甚至中国文明的世纪。这种看法从整体上说并不符合东西方思想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是片面的和危险的。历史已经表明,东西方思想从一开始的确是“殊途”——西方思想走的是古希伯莱信仰和古希腊理性的道路,东方思想走的则是印度教、佛教以及儒教、道教等宗教无神论的直觉的道路(冯友兰认为概念和直觉的差异是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宗教有神论和宗教无神论才是这种根本差异),由此造成东西方思想在相互理解和交流上的困难,但也正是因此才使得这种交流对双方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通过吸取东方思想而开创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其后继者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也都是通过关注和吸取东方思想而发展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同样,在中国,梁漱溟、冯友兰等人也是通过学习和吸取西方哲学才得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哲学。正象诗人的诗句所形容的,东西方思想为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共同的问题必将走到一起,一同为人类创造美好的未来。
收稿日期:2000-7-18
标签:哲学论文; 克尔凯郭尔论文; 叔本华论文; 康德论文; 基督教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印度教论文; 佛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