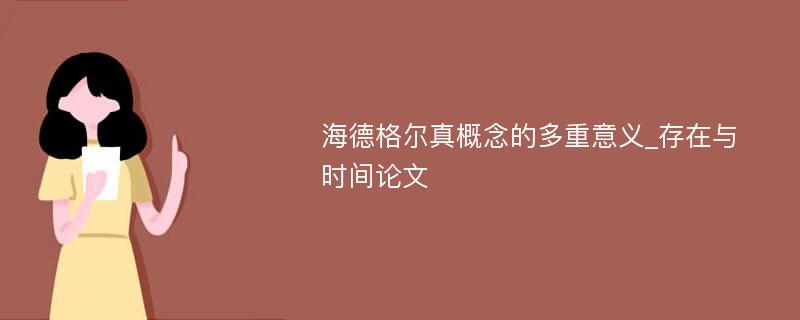
海德格尔本真概念的多重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本真论文,意蕴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德格尔区分了此在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和非本真性(Uneigentlichkeit),但对于本真概念的内涵及其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作用,学界并没有足够重视,似乎其含义是自明的。其实这个概念问题颇多,而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思想来说又意义重大。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并展示其重要性:首先,此在的非本真和本真状态的分析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上、下两部,因此要理解《存在与时间》的思路、结构及其在海德格尔整体思想中的地位,这个概念不能回避;其次,海德格尔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卷入纳粹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权,对于那些试图证明其政治迷失根源于其思想或与其思想无关的人来说,本真概念都是核心;第三,海德格尔区分了本真和非本真生存,而中国思想中有圣人、真人、活佛等“非俗人”,围绕本真概念所做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还是牵强的比附,仍然在于理解本真和非本真两方面共存的方式。尤为重要的是,澄清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地着眼于“结论”,而是要着眼于海德格尔独特的思维方式。反过来,本真概念的内涵也只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才能得到丰富的展现。
一、《存在与时间》中提出本真概念的意义及本真此在的个体性
对于《存在与时间》,普遍流行着一种误解,认为这部书之所以成为残篇,是由于海德格尔意识到了他自己本意是消解主体哲学,却因为思路不当而将主体哲学进一步极端化,因此才有了后来的转向。而极端化了的主体就是本真的此在,按照这种误解,从孤独的个体——本真此在中,可以产生出他人、世界乃至世界历史,因此下半部《存在与时间》虽有些灵气,但还是钻进了死胡同。与此看法相应的观点于是就顺理成章,认为《存在与时间》上半部的分析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精髓,他打破了近代“现成性”的、“主客二分”的、“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前存在论”的上手状态,超越了科学技术与物打交道的“现成在手”方式,论证了由此在之生存勾连起来的因缘关联的生存论世界,超越了作为物之总和的流俗静态世界观。人们完全无视《存在与时间》整个上半部的标题只不过是“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是对此在非本真状态的分析。由于忽视了这种至关重要的定位,本来是此在非本真生存状态的准备性分析,因为对抗主客二分的或现成性思维方式,被错误地提升到本真的层面,而非本真这个词仅仅留给了对象性的科学技术活动;下半部“此在与时间性”对本真此在的分析,因为做了基础主义的理解,就被贬低为主体哲学的残余;由于思路不当,海德格尔走投无路了,才有了所谓后来思想的转向。
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的思路,没有理解本真概念的意义和作用。《存在与时间》作为海德格尔1926年完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蕴涵或预示了他一生追问的内容和思路。《存在与时间》在扉页中就明确道出了该书的任务:“具体而微地把‘存在’问题梳理清楚,这就是本书的意图。而其初步目标是对时间进行阐释,表明任何一种存在之理解都必须以时间为其视域。”① 具体的追问计划则在该书的第八节中明确列出来,海德格尔始终都没有抛弃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篇是“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占用了这部残篇的上半部,随后的第二篇叫“此在与时间性”,就是该书的下半部,这两部分顺利完成了,而再往后的第三篇“时间与存在”以及整个第二大部分“依时间性问题为指导对存在论的历史进行现象学解构的纲要”没有在该书中完成。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些工作没有进行,海德格尔后来完成的《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和《现象学基本问题》就是在完成第三篇的工作。然后,他的大量精力就转入了对哲学史的解构工作。从内容的“量”上来看,海德格尔《全集》的绝大部分是解释或解构其他思想家的手稿。因此我们综观整体,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存在与时间》的地位,它是整个工作的一个“路标”或准备性阶段。海德格尔引领我们领会存在之意义的主要现实途径就是解构哲学史,通过动摇其形而上学框架而使我们“切身”领会存在之遗忘,进而在解构实践中领会存在本身,而这一切要求在本真的时间中完成。那么人为什么能够身处本真时间中而成为唯一能够领会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者呢?这就首先需要一个资格论证,证明人或此在本身就是由时间性结构所规定的。而时间性结构本身是两方面的,我们日常沉沦于世,极端地表现为疯狂地扩张技术的生存方式,也是由时间性结构所规定的,但这是本真结构的非本真变式。然而虽说是变式,毕竟和本真时间性结构同根同源,因此,要展开领会存在意义的本真视域——本真时间,就必须首先揭示此在非本真生存的时间性结构:“此在在分析之初恰恰不应该在一种确定的生存活动的差别相中来被阐释,而是要在生存活动的无差别的当下情况和大多数情况中来被发现。此在的日常状态的这种无差别相并不是无,而是这种存在者的一种积极的现象性质。”② 日常操劳的此在不是他自己而是常人,他所处的时间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共的。公共时间的无终性,使得常人无休止地追求或专注于将来的事物,消散于外物而失去自身,对这些事物的判断以常人意见为标准,而不是自己对真正的他人或事物本身的领会,存在之意义被遮蔽着。但即使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由此在的时间性所决定的,因此可以通过对这种积极的现象进行分析而逼显出操心结构,即此在的将来—当下—已在的三维绽出结构,只不过非本真的绽出“绽向”非本真的、被常人赋予了意义的人或物。同样还是这种绽出结构,当不指向具体事物而是绽向死的时候,此在就会因为直面“无”而被逼回到他自己赤裸裸的“有”或“存在”,他的个体性、被抛性和无缘性突显出来,日常操劳所处的无终的非本真时间似乎“到头了”,由此,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对此在显现出来,这就是本真时间,在这样的视域中,个体的此在所面对的就是真正的他人和事物本身,其存在的意义昭然若揭。
我们可以看出,本真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至关重要。《存在与时间》中虽然透露出一些反现代性的“纳粹”情结,对于现代技术对人的异化的现实关切也非常明显,但不应过分夸大。作为成名作和代表作,《存在与时间》毕竟担负着奠定批判现实之基础的“理论”层面的重任,本真概念非但不是主体哲学的残余,而且恰恰是对抗主体哲学的基础存在论的必要准备,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就是生存论语境中的“主体”,此在必须先从主体中抽离出来,断掉各种日常因缘和社会关系,成为个体性的、在非本真眼光看来“无意义”的自己,才能彰显本真的时间,进而领会本真存在之意义,因此,本真环节是《存在与时间》乃至其整体思路的必经阶段。海德格尔思想的革命性如果仅仅被定位为反对近代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那么就被严重低估了,上半部《存在与时间》就可以完成这样的初级任务,但如果意在解构主体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甚至哲学本身,解构一种理论性建构的生存方式——现代技术的疯狂摆置活动只是其极端表现形式——首先就要从芸芸主体中逼出本真的独立人格,彰显本真的时间,为进入解构哲学史的本真境域做好准备。从这一点看,海德格尔思想的革命性恰恰从论证本真状态才刚刚开始,本真此在首先是断了因缘的本真个体。但与此同时,切不可忽视非本真状态的分析对于揭示时间性三维绽出结构的意义,这种浪推浪式的现象学揭示方法,典型地体现在《存在与时间》中。
二、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本真此在的历史性内涵
如果说在作为宣言和纲领的《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概念更多地担当着建构基础存在论、逼显本真时间的“学理”重任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卷入纳粹事件的事实,就迫使我们从纯学理中退出来,从现实事件洞察海德格尔的现实关切。在《存在与时间》中,本真此在主要是指从常人、从“我们”中抽离出来的、断了因缘的、卓尔不群的“我”自己,而这个个体性概念到了三十年代,突然转化成了“人民”、“国家”、“德意志民族”等集体词汇。对于海德格尔纳粹事件的争论,不管是认为其政治迷失基于他的思想的学者,还是反对从其思想解读其政治行为的学者,双方都围绕“历史性”、“决断”、“民族之天命”等概念展开论证,而这些概念仍然以“本真性”为基础。可见,理解海德格尔的这段历史行为,可以进一步丰富本真概念的内涵。萨弗兰斯基在《海德格尔传》中说到:“《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个人对自己自由的自身关切视为生存理想,但海德格尔并不想让人们将其理解为个人‘个体主义’。所以他十分强调共同体和民族中生存理想的‘现实’人生此在的力量。……他被抛在一个民族中,降生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中。个人的人生此在与‘共同体与民族的活动进程’之间的这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被海德格尔称为天命(Geschick)。”③ 这段话的核心,就是此在被“放大”成集体并被“投入”历史。换句话说,此在不是仅仅能够领会存在的无力的本真能在,而且具有卓越的现实创造性,拥有尼采的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那里,甚至不幸地发展为某种历史事件中的暴力。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存在与时间》中就已经有的、只是在海德格尔三十年代的政治活动中更加强化或极端化了的现实关切。《存在与时间》中所谓的常人或非本真的此在,指的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而被摆置了的、异化了的、千人一面的现代人,他后来对广义现代技术之本质——摆置的思考,更是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揭示得淋漓尽致。现代技术的这种控制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无法通过局部革命而克服,只能寄希望于一种“绝对拒绝”,即全盘否定,但他承认,仅从理论上看,这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治形式”。看来,本真此在对抗现代性不能单凭个人力量或只停留在理想中,而是要投入历史而现实地“决断”,而尼采“积极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决断的方向。利用暴力手段摧毁资产阶级的钻营算计的商业体系、软弱无力的民主政治、纸醉金迷的低俗生活以及虚伪矫情的人道主义,一句话,砸烂现代性生活方式。这种思想在德国源远流长,当时持这种思想的人被称为“保守的革命派”,斯宾格勒、布鲁克、施密特、荣格尔都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激进主义者都以被有意曲解了的尼采为精神领袖。“保守”指思想上敌视现代性,的确,“理解海德格尔早期著作的历史决定性的一把钥匙,是德国士绅阶层顽固的反现代主义倾向”。④ 但海德格尔本真意义上的“决断”就一定指向纳粹的极端行为吗?如果从《存在与时间》的“学理”角度来看,本真此在作为孤独无缘的个体,恰恰是要从任何轰轰烈烈的“集体”运动中抽离出来,否则无以成其本真性,他的“决断”是没有内容和现实指向的,只是一种本真的“我能”,不涉及具体能做什么,拥护集权主义还是民主政治都有可能,主张把海德格尔思想和行为分开的学者们大多是这样论证的。而主张其政治行为源于其思想的学者,则利用“历史性”、“天命”、“民族”等概念论证“本真的自我只有在历史的特定‘集体性’中才得以实现”。⑤ 虽然这些论证有的略显牵强,但从“历史性”概念着眼,无疑是真知灼见,历史性是本真性的放大和具体化。
海德格尔非常注重对莱布尼茨的研究,在很多场合都把“单子”解释成他本人的此在概念。莱布尼茨的单子是单纯、统一的单元,“单子没有可供某物出入的窗户”,不受外界干扰,只依其欲望而自由活动,因此,数量意义上的“大小”并不重要,只要是统一而自主活动的东西都可视为单子。同样,本真的此在也可以因考察的着眼点不同而随意大小。海德格尔在1934年夏季学期的逻辑学讲座中说:“那个自己并不是‘我’之最富代表性的规定,具有奠基性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只有在我们中才找到自己。……在‘我们’这个层次上,也有本真本己性与非本真本己性之分。非本真本己的‘我们’是‘常人’,本真本己的真正的‘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像一个人一样维护着自己的存在。‘人民整体就是一个巨大的人’。”⑥ 虽说本真此在无所谓个体或共同体,但要作为本真的此在,就必须自由地创造,要有能力改变现实和历史。但本真决断无法顾及非本真的价值层面,因为本真和非本真不是可以割裂而存在的两种“状态”,就像一片叶子有两面一样,世界上真实的事物没有哪个只有一面。由于本真的决断只是内容空洞的“能”,落实到具体的决断,就只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性质,即“破”而不“立”,砸烂已有的不自由秩序,而不顾及重新建立什么。此外,本真的行动是超常规的,从非本真层面看是非理性的:决不能让命题和“观念”成为你们存在的规则,元首本人并且只有他,才是现在和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律。由于本真和非本真的同构性,海德格尔的本真决断事实上支持了独裁政治。
如果我们不去过多评价海德格尔的纳粹事件本身,而只是要借助这个事件充实本真概念的话,那么,海德格尔战前积极的“否定性”决断,即打破现代技术的疯狂统治,与战后顺从“天命”的消极态度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他很清楚本真此在与历史之关系的辩证性,他对纳粹本身的态度同样是辨证的,“尤其是今天还作为纳粹主义哲学传播开来,却和这个运动(即规定地球命运是技术与近代人的汇合的运动)之内在真理与伟大性毫不相干的东西,还在‘价值’与‘整体性’之混水中摸鱼”。⑦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内在的真理与伟大”,只是因为它“破”的一面,而纳粹哲学本身所“立”的,同样是浑水摸鱼的货色。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存在与时间》中的含义外,本真的此在还应该具有现实的历史创造性,本真此在“能”自由决断,具体到海德格尔时代,就是“能”打破现代性的全面统治,本真此在有现实的能力,可以是一个实际的共同体。但由于本真和非本真的同构性,这种“否定性”的创造无法决定其非本真层面的后果,正如康德的道德命令,必须设定上帝存在来保证现实行为的道德性,由此所突显出来的,是历史性本真此在彻头彻尾的有限性。本真此在的能动性与其有限性的这种悲剧性冲突,恰恰是海德格尔思想最深刻的地方,本真的此在就是这样能动而自由地创造历史,但又必须被抛地承受其命运,领会世界历史之天命。“这个世界之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以及它如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不能是通过人做到的,但也不能是没有人就做到的。”⑧ 历史性概念充实了本真性概念的内涵。
三、中国传统思想参照下的本真此在的斗争处境
此在之本真性及历史性内涵展现出来之后,此在究竟如何历史性地被抛于本真与非本真状态的相互牵连之中,或者说,本真与非本真同构性的具体发生形式仍然有待说明。我们不妨以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为参照,充分展示海德格尔和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以便进一步说明本真性的独特发生结构,丰富本真概念的内涵。虽然海德格尔和中国思想有缘,在其中后期著作中也曾引用老庄文本来阐发其思想,他的思想本身从某些“结论”上看,确实和中国传统思想有相通之处,本真概念在比较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表面上相近的地方恰恰就是根本差异之所在。有人认为道家思想中描述了很多“类似”海德格尔“本真境界”的例子,比如《庄子·养生主》篇庖丁解牛的寓言就是一例,庖丁解牛时的境界相当于海德格尔说的物的上手状态,是一种物我两忘、主客不分的本真境界。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解,尽管双方都没有把物当成现成的抽象客体,但相似仅限于这个最低层面上。
海德格尔所指的本真还是非本真,并不取决于实体性的还是关系性的、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此在在日常操劳中从“彼”处领会他的“此”,双方对象性地相互赋予意义,称手的锤子使此在消散于其使用,在这种“忘我”的使用中,双方都失去了自身的本性,此在变成了常人,物沦为被常人赋予意义的对象,日常生活只能表现为非本真方面。庖丁解牛的境界则不然,“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这讲的是抽象对待客体的阶段;“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技术长进之后对牛的熟悉,大致相当于海德格尔讲的物的上手状态;而到了“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完全超越了对象,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但又不失本己的非对象直接同一境界,这是“技”与“道”、非本真与本真的直接同一。所以,当文惠君赞叹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时,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一方面“道进乎技”,但另一方面“技”直接体现“道”,技的方面既专注于物又持守自身不失本性,和通道境界中的物我两忘并不矛盾,这种独特的一而二、二而一的方式,是中国思想所特有的辩证法。《达生》篇描述的佝偻丈人粘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表达了同样的“技境”,秘密同样如佝偻丈人所言:“我有道也。”这种“物”、“我”、“技”、“道”直接合一,物我两忘但各自不失本性的境界是西方思想传统无法理解的,西方人大多会认为非对象直接同一是抽象的,就像黑格尔所言:“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是知识空虚的一种幼稚表现。”⑨ 海德格尔虽然试图超越传统,但这种直接同一的表达对于他来说毕竟是陌生的,《存在与时间》中本真状态所涉及的“境界”,是借西方传统基督教体验而描述的超越处境。从积极方面讲,本真处境并非无对象,就像信神的人赤诚面对邻人,本真此在面对本真对象,此在同样是从本真的物或他者、“彼”的本真状态领会自己的“此”之本真意义,有对象,就决定了同一性必须被矛盾地辩证揭示,尽管不同于黑格尔的形式。从消极方面讲,信奉神意味着对任何世俗的功业或荣誉说“不”,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硬要求它颁布实际教导的话,只能说:你要“能”超越现实因果关联之必然而自由地“不”行不道德之事。由于海德格尔骨子里的无神论,他恰恰在本真处境中,把这个绝对的“不”转义成了现实的“破”,即对现代性的“绝对拒绝”,导致了政治迷失。这种“不”用《存在与时间》中的话说就是本真此在从日常状态“抽离”,有一种明显的克服或争斗的含义,本真必须在与非本真的争斗中彰显,非本真的描述甚至占据更大篇幅,这就形成了与中国思想的根本差异。
庄子描述日常技艺活动的寓言都与“生”有关,庖丁解牛出现在《养生主》篇,佝偻承蜩、津人操舟、梓庆销木出现在《达生》篇,海德格尔视野中日常消散于物的操劳活动,在道家看来却是生命超越有限而通达无限、与道合一的切实途径。具有高超技艺的日常操劳者,通过超越技艺之技术层面而进入到一种无限自由的艺术境界,顺天道、任自然而成就物我双方之本性,技术活动本身就是道。按照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本真和非本真状态可以无中介地直接同一,达到这种境界的俗人本身就是真人,真人实际存在。这种道在草木瓦砾、禅在劈柴打扫的思维方式,同样成就了儒家的圣人、佛家的活佛,这对海德格尔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虽然他同样强调本真与非本真的同构性,但这种同构性绝非直接的同一,而是在矛盾斗争中相互牵制、相互彰显,是生存论意义上的“相反者相成”。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从此在实际生存方面表达与这种本真观相应的真理观:“此在的实际状态中包含有封闭和遮蔽。就其完整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来说,‘此在在真理中’这一命题同样源始地也是说:‘此在不在真理中’。”⑩ 他后来不再频繁地使用本真和非本真概念,而更多地转向对真理—非真理发生事件的描述,后者虽然不能完全说就是前者的替换,但这与海德格尔从此在生存论和时间性分析转向对存在之真理的发生和时间本身结构的描述相对应。不可否认的是,存在之真理发生的场所无疑仍然是此在,真理和非真理的发生结构与此在的本真和非本真状态,实际上还是同一事件相互“感应”的两方面,海德格尔经常用“stimmen”(调校)这个词,仿佛收音机的接收频段和电波的发送频率相协调,存在之真理就会在此在之“此”发生。真理之发生要求本真此在,此在秉承天命揭示真理的同时,由于其有限性而遮蔽真理,从而成为非本真的,但极端的非本真处境中又包含着进一步揭蔽的可能、本真的萌芽,通过对真理发生结构的描述,本真概念又突显出一种生成性和斗争性内涵。海德格尔把真理按希腊意义理解为无蔽,这个褫夺性的词汇本身就意味着与某种遮蔽状态的争斗,“可揭蔽性,对遮蔽之克服,如果它本身不是一种与遮蔽的原始争斗的话,就根本不会真正地发生,一种原始的争斗(决不是争论):这意味着那种争斗,它本身首先形成它的敌人或对手,并帮助他们成为它严格的敌对方,无蔽不是简单的此岸,遮蔽是对岸,毋宁说,作为可揭蔽性的真理之本质,是桥,更确切地说:从此岸向对岸搭桥”。(11) 此在被抛地承受揭蔽之天命,从而不断地被抛于真与不真之间,类似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命运。越往后,海德格尔的真理观中越注重对非真理环节的描述,非真理甚至成为庇护真理的更重要维度,这一点突破了西方的传统理念,但并不因此就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互通。本真此在根本无法单独持守本真状态,或因真俗直接同一而成为真人,海德格尔要彰显的恰恰是位于争斗之核心的此在最根本的有限性。如果真有什么本真此在的话,那就是领会其卷入争斗而势必成为非本真的有限此在,与道家所讲的有限生命通达于无限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人只有被卷入真与不真的争斗之中,才真正成为其所是的东西,成就其有限的本质,此在只能永远处于求真之途中,勇敢地承受这种被抛的争斗之命运,才是顺应自然和人性。本真此在在斗争中方生方死,皆因赫拉克利特所言,斗争乃万物之父,万物之王。
四、小结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海德格尔本真概念的丰富内涵就得以显现了。首先,本真此在的个体性、了断俗缘的性质,是赢获本真时间、直面本真他人和事物本身、领会存在之意义的前提,是基础存在论的重要环节,海德格尔思想的革命性始于此。而本真个体的决断一定要落入非本真层面,本真与非本真的同构性规定了此在现实的历史性,此在要想具有现实的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放大为某种共同体,但必须具有不被现实因缘关联或因果必然性所左右的绝对能动性和创造性,绝对的“不”、绝对的否定虽然不一定指向罪恶,但否定性、超越性一定是其重要内涵。本真与非本真的同构性,同样决定了绝对能动性必然依天命而转化为绝对被动性,由此彰显本真此在最根本的有限性,被抛性是海德格尔最关键也最有特色的术语之一。本真和非本真状态的相互归属和争斗性,断绝了人成圣、成仙、成佛的可能性,把人逼回到其世俗的历史生存中,并决定了在其中的思想的只能采取不断与遮蔽、与非真理无休止争斗的现象学方法,这种解构性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哲学”、“世界观”的反面。海德格尔思想虽然在结论上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本真概念的价值取向,对于现代人有所警醒和启发,但最接近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大的差别之所在,洞察差异或融通的关键在于领悟哲学之外的东西。
[收稿日期]2009-03-14
注释:
①②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51页。
③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靳西平译:《海德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83页。
④⑤ 理查德·沃林著,周宪、王志宏译:《存在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6、81页。
⑥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靳西平译:《海德格尔传》,第360页。
⑦ 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8页。
⑧ 海德格尔著:《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307页。
⑨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页。
⑩ 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第255页。
(11) 海德格尔著,赵卫国译:《论真理的本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