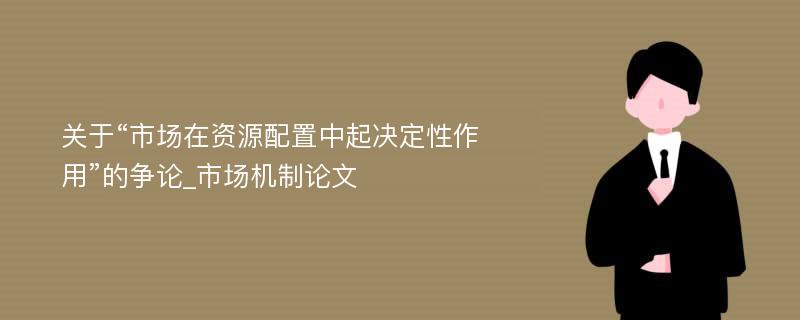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决定性论文,中起论文,作用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舆论界和政策界对该《决定》的解读,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的思路是:该《决定》明确提出了“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高尚全,2013;林兆木,2013)。据考察,中共的十四大报告中就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后该提法又经过了几次变化,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其正式的表述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高尚全,2013)。虽然许多专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含义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但如果从经济学学理层面,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本文将从经济学学理和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两个层面,解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力图回答目前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经济制度,“腐败”是什么样的一种经济现象,以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代价”是什么。 一、中国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吗?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几乎全部经济学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基础的经济学常识。萨缪尔森在其编写的基础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是从“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出发,开始对经济学论述的。按照萨缪尔森的表述,“每个经济社会的中心问题”有三个:第一是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即“What和How Many问题”;第二是如何生产的问题,即“How问题”;第三是为谁生产的问题,即“Who问题”。只要存在着普遍的资源稀缺,或者说,只要人仍存在着未得到满足的欲望,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必须要面对这三个问题。通常经济学家将这三个问题统称为资源配置问题。不同的制度安排,对这三个问题或资源配置的解决方式是不同的。根据萨缪尔森的分类,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三种制度安排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第一种制度安排是习惯和本能。这是传统社会主要采用的方式;第二种制度安排是市场机制。这是人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主要采用的方式;第二种制度安排是计划和命令。这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主要采取的方式(萨缪尔森,198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改革上所做的大量努力就是从以计划和命令方式进行资源配置,转向以市场机制方式进行资源配置。这就通常所说的经济制度转轨。论述这一转轨过程并不是本文的主题,本文关心的是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演进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看“What和How Many问题”。这实质上是资源分配机制问题。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下起决定性作用或基础性作用的情况下,生产企业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自主决定如何进行资源分配。在当今的中国,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已经很少了,除了非竞争性产品或服务之外,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受到市场供需法则的调节。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要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做出判断,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即使政府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许多场合下,也要到市场上进行采购,通过市场招标方式来完成。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主决策“是生产还是不生产”、“应该生产多少”。 仔细想想,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类产品和服务可能要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其中哪一样不是根据市场价格自主选择的呢?真正需要政府直接配置的产品和服务已经很少了。消费者是这样,生产企业也是如此。这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识。而消费者或需求者所做出的自主选择,实际上就是通过货币对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投票”,也就是“出价”。生产企业根据消费者或需求者的“出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其次看“How问题”。这实质上是成本效益计算问题。在市场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或基础性作用的情况下,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成本效益计算的基础上选择生产方式。在当今中国有哪一家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不是在成本效益计算的基础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呢?甚至许多公共服务部门如医院、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公共基础服务部门如公共交通、供水排水、城市绿化等部门也是将收益最大化作为本单位的一个重要目标。总之,在当今中国,追求效率最大化,实现收益最大化已经是企业,甚至是政府及事业单位从事各种活动的通则。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最后看“Who问题”。这实质上是产品和服务分配机制问题。在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或基础性作用的情况下,产品和服务分配的基本原则是“价高者得”。在当今中国,除了特殊产品和服务如保障性住房和最低生活保障之外,消费者所需的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是通过市场,通过“货币投票”方式取得的。谁出的价高,谁就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只要有钱,在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 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与他的学生曾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中文译名为《变革中国》。其书原名为《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直译就是《中国如何变成资本主义的》(注意书名中的“Became”的过去式,不是现在进行式)。在科斯的语境内,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可见,按科斯的标准,目前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了。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着纯粹的市场经济,纯粹的市场经济只是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里,只是存在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例如,在任何制度下,家庭特别是核心家庭中,萨缪尔森所说的“习惯和本能”仍然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主导方式。在国防和公共安全领域,“计划和指令”在任何制度的国家中,都是配置资源的主导方式。 总之,如果我们不太追求语义学上的严谨,也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经济中,市场机制已经起“基础性的”作用,或者说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了。因此,中国政府在国际经贸场合上力争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有充分理由和根据的。 二、“腐败”是怎么回事儿? 在中国过去30年的市场化取向改革过程中,在经历了产品及服务和生产要素市场化、货币化过程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政府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货币化机制。在经济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由于缺少足够的对政府官员权力的制约,政府公共权力往往会成为部分政府官员私人所有的“有价资产”,可以为政府官员个人创造私人财富。这就是“腐败”的经济学基本含义。 如果我们暂不考虑“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观,不带感情因素,单纯从经济效率来分析“腐败”现象,就会发现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货币化机制在某种场合下,往往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首先,分析“腐败”的类型。 粗略的分类,“腐败”可以分为“掠夺型腐败”和“分蛋糕型腐败”。“掠夺型腐败”是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掠夺”现有的“存量蛋糕”。在历史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中饱私囊,大肆贪污伪敌产就是典型的“掠夺型腐败”。在当今中国现实中,有些贫困地区的官员贪污私吞扶贫款或私吞国家用于扶持落后地区的工程建设款,也是“掠夺型腐败”;大多数发生在军队中的腐败行为也应该属于“掠夺型腐败”。 “分蛋糕型腐败”则是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其权力管辖范围内做大“增量蛋糕”,并“分享”之。“分蛋糕型腐败”的官员行为类似于中外历史上广泛存在的“包税商”。征税权本来是一种政府的公共权力,但政府这种公共权力承包给“包税商”,变成了“包税商”自己的私人权力。“包税商”的征税额越大,其取得的收益就越大。两者的差别是“包税商”往往是明码标价的,是有制度保障的,而“分蛋糕型腐败”则是官场的“潜规则”,既不能明码标价,更无制度保障。 还有一种“腐败”类型是“买官卖官型腐败”。如果“买官卖官”只是单纯的“腐败”行为,不与上述两类“腐败”相联系,也就是说,“买官”者的“买官”目的只是为了“进步”,不是为了得到官位和权力后再去“分蛋糕”或“掠夺”,那么,“买官卖官型腐败”只是破坏了官场中官员升迁的规矩,对社会整体资源配置影响并不确定。例如,有钱“买官”的人可能就是有本事的人,应该“进步”,当然也可能不是。“买官卖官型腐败”的实质性问题是官场竞争规则的缺失或模糊不清。这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畴,本文不做进一步的分析。 其次分析“掠夺型腐败”和“分蛋糕型腐败”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掠夺型腐败”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这种类型的“腐败”无异于“抢劫”,是用“掠夺”的方式改变现有的财富分配,而且是一种“帕累托退步”的财富分配,使社会资源从边际效益更高的地方流向边际效益更低的地方。即使不考虑难以用货币估价的“公平、正义”因素,“掠夺型腐败”也会使社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降低。 “分蛋糕型腐败”则有所不同。“分蛋糕型腐败”是建立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的,如果“蛋糕”不能做大,那么也就无“蛋糕”可分。从理论上讲,政府官员私人化的公共权力,也是一种私人化配置资源的权力。然而,这种来源于公共权力的私人化配置资源权力与纯粹的私有财产权不同,这种权力的实现必须通过用于公共目的,才能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具体到现实,政府官员必须要通过“招大商、招大项目、大开发、大建设”,“做大”其权力管辖范围内的经济总量,才能为自己获取最大化的收入。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的“腐败”就成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润滑剂。与历史上“包税商”有足够的动力去扩大税基,创造税源行为相类似,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货币化,也为政府官员发展经济、做大经济总量,建立了激励相容的刺激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官场腐败有所不同,当前中国官场腐败的典型特征是“分蛋糕型腐败”。许多大贪官在下马前曾经是“发展经济”和“招大商、干大项目”的“一把好手”,为所在的地区或行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可能现在被关在狱中的腐败官员会觉得自己很冤。他们可能会想:“我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为国家和地方创造了数百亿、数千亿的经济收入,但我只‘分享’了其中的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这样做过分吗?” 最后再来分析“腐败”的代价。 政府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货币化机制,实际上是一种用市场原则分配公共权力及其收益的机制,是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引入官场。但这是一种“坏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从短期来看,这种“坏的”机制可能对促进经济增长有一些“正面”效应,但长期来看,无论哪种类型的“腐败”,社会都要为之付出巨大的成本。 政府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货币化机制的社会成本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降低市场的可竞争性。在这种机制下,政府公共权力越来越多地深入“侵入”到各种经济领域,特别是有可能“做大蛋糕”,且对政府官员来说是“有利可图”的领域,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石油产业、铁路业、资源型产业,以及优质的高等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等领域。一些官员可以利用政府行政性垄断地位,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为自己谋利。在当今中国现实中,上述这些领域正是“分蛋糕型腐败”频发的重灾区。政府垄断的存在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与民争利”,就会抑制竞争,抑制私人企业的自由进入,降低市场的可竞争性,造成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失。 二是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扭曲。在正常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下,配置资源的权力来源于个人或企业能力,即市场竞争力。市场竞争力高的人就可以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能够获取更多的财富积累,有了更多的财富积累又可以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源。在政府公共权力私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下,其配置资源的权力来源于公共权力,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并且还会以扭曲的方式传导到“腐败”的“行贿方”,而“行贿方”往往是私人企业。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私人企业主的个人或企业不再仅仅要有能够经受市场竞争考验的能力了,而是还要包括是否具有与官员“打交道”、“拉关系”的能力。如果市场竞争中,后一种能力比前一种能力更为重要,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就会被完全扭曲,“官商勾结”成为了一种规则,这将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并抑制能够经受市场竞争考验的个人和企业能力的正常发挥。 三是政治成本。“腐败”的最大成本是政治成本。政治成本之所以巨大,是因为“腐败”瓦解了一个社会良好运行的价值基础。对于政府而言,“腐败”的政治成本是降低了其执政能力,动摇甚至危及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这一点已成为包括政府在内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府厉行“反腐”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从根本上说,要想改变这种“坏的”市场竞争制度,消除“腐败”,就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当前中国政府力推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要减少可以“变现”为政府官员私人权力的公共权力范围,形成“无污可贪”的制度环境,也就是目前中共中央纪委所说的建立“不能贪”制度。 三、如何看待“浪费”? 按照樊纲的思路,限制政府的权力,尽可能地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应该明确政府“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对此问题明确之后,剩下的都是由市场主体或社会组织来做;对政府管制边界的限定,应该采取“正面清单约束”的方式,约束政府对经济运行任意干预的行为(樊纲,2015)。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尽可能地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既有“得”,也会有“失”。 在理论上说,以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分析:一是资源配置的最终状态层面。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以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其资源配置的最终状态一定是有效率的,即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对于这一点无须再讨论。这就是“得”的方面;二是资源配置过程层面。实际上,“帕累托最优”只是存在于经济理论模型中,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中,是经济学家为了进行经济分析所创造出来的有效思维工具。而“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在现实中存在着的是资源配置过程,也就是市场出清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趋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过程,而且这种“趋近”,永远是“趋近”,但永远不会“达到”。因为如果真的“达到”了,竞争就停止了,市场机制也就不能发挥作用了(柯兹纳,2012)。然而,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最终状态是“美好的”,但其市场出清过程却是“痛苦的”。在市场出清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浪费”。这就是“失”的方面。 所谓的“浪费”可以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品或服务及其产能的“浪费”。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过程实质上就是竞争过程,有竞争就必须要有产品或服务的过剩,也就是产品或服务及其产能的“浪费”。如果市场需要100万台电视机,正好10家电视机企业生产总量也是100万台,供给与需求相等,这样就不会出现“浪费”,但是这样的话市场上就不会有竞争。没有竞争,市场机制也就不起作用了。正是因为存在竞争失败者,资源才会向竞争胜出者集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是部分产品和服务及其产能因其过剩而被“浪费”。这本来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但这个基本常识一遇到现实,往往就不会被接受了。例如,当现实生活中出现钢铁过剩、水泥过剩、煤炭过剩、白菜过剩、萝卜过剩、牛奶过剩等等时,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就会呼吁政府采取措施,进行干预。这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理由。因此,对存在过剩的产业和项目,国家发改委就要限制、就要审批;国资委就要进行资产重组。例如,前些年,政府以行政的手段进行钢铁企业、煤炭企业和电信企业的重组,包括最近发生“南车”和“北车”的兼并重组,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避免所谓的“无序竞争”、“过度竞争”,避免由此产生的产品及其产能的过剩,也就是避免“浪费”。 二是时间的“浪费”。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市场主体在竞争过程中发现的过程(哈耶克语)。众多的市场竞争主体在市场中不断发现各种可能的盈利机会,这种被发现机会日后有可能证明是成功的,但也可能是失败的。这种竞争过程本身就要耗费时间。而且,被发现的机会或项目也要有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用于企业自身能力、资金、市场开拓的积累。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特别对于资本品产业、基础原材料产业、高端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在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如果仅仅是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自主选择进行产业转型升级,那么,也要经受较长时间的阵痛期。这些时间的消耗也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的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结合当今的现实,我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赶超发达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往往就不能容许这种时间的消耗所造成的“浪费”。为此,各级政府就要抢抓机遇,积极引导市场,制定各类产业政策,出台各类产业规划,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发展高端制造业,发展“大国重器”,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等等。这也是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理由。 三是管制的“浪费”。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对市场进行管制的问题,都有行业监管,例如,对食品卫生行业的监管、对药品行业的监管等等,并制定各种产品质量标准;政府还要建立市场规制,例如,保护消费者权益、反垄断行为等等。这些管制和规则的建立都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这种成本的支出也是一种“浪费”。比较“省钱”、“省力”的管制方式是对市场准入主体进行严格限制。例如,石油行业的管制。2000年以前,在某种程度上说,石油行业是放开经营的,大量民资进入石油的中下游经营领域。2000年以后,政府开始以行政力量对石油行业进行重组,消灭了中小民营和地方性的石油企业,逐步形成了以中石油、中石化为主体的四大国有石油企业垄断格局。政府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量民资进入石油的中下游领域造成了市场混乱,石油走私成风、石油产品质量难以控制。中石油高管反击柴静的“雾霾成因说”时就质问:“如果真像柴静说的那样开放几千家私营企业开采销售油气,必会鱼目混珠、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他们的加油站你敢进去加油吗?军队的坦克飞机军舰敢用吗?”上世纪90年代,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将具有民营性质的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收为国有,取缔民间基金会,其理由也是其引起市场混乱,金融风险实在太大了。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行业的所有制管制替代行业的市场监管,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行业管制方式。从节约监管成本、避免“浪费”的角度来看,行业的所有制管制确实比行业的市场监管更为节约、更为省事。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如此。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政府出于工具理性主义的考虑,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好的”方面,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对经济的深度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克服了市场机制“坏的”方面,避免了上文所说的种种“浪费”,特别是时间的“浪费”,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绩效,一跃成为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对此现象本文的解释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经验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前车后辙”,我们可以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引进,避免走很多弯路,也就是避免很多“浪费”。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有关经济发展的知识具有很高的“可集中度”。中央政府及其智囊可以利用“可集中”的经济发展知识,制定发展规划和相应政策,设计各种制度,把握和指导全局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方向;地方政府及其智囊利用可以“可集中”的经济发展知识,根据本地和本行业的条件,确定经济发展方向,“招商引资”,进行土地开发、产业园区建设,并以问题导向,进行大量制度探索。以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为例,如果任凭证券市场自生自发的成长,中国的证券市场要想发展到当今的水平,可能需要几百年。许多基础性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之手的“第一推动”也是非常有成效的。这也是在国际上广泛认可的“中国模式”的精髓所在。 然而,随着经济成熟度越来越高,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无知之幕”(罗尔斯语)状态,知识越来越多地会分散在无数的市场竞争主体的头脑中,也就是有关经济发展的知识“可集中度”将越来越低。在未来,市场上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出现越来越多的“惊讶”。这种“意想不到”和“惊讶”,不是政府能够预先想象到的,更不可能是政府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只能是无数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为,有利可图的机会只能是他们在市场竞争实践中被发现出来的。因此,本文的初步判断,在未来,政府干预经济的正面效应将递减,而其负面效应将递增。另外,再重复一遍,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的最大代价,就是前文所述的官场“腐败”现象频发。 当前中国还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即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受限。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引导市场,落实其产业发展意图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土地。政府利用其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以地招商”、“以地换线”、“以地融资”。这种特殊的土地制度是“中国模式”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可建设的土地资源逐步减少,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的加重,“寅吃卯粮”的现象越发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方政府想干预经济,以“政府之手”引导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也将会感到力不从心。 总之,要真正认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不是看其“得”的方面,而是要看其“失”的方面。如果我们只看得市场机制“好”的方面,不能充分估计其“失”的和“坏”的方面,不能容忍“必要和必需的浪费”;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政府有能力,可以避免市场配置资源所“需要”的“浪费”,并且无须付出什么代价,那么,一旦遇到现实的具体问题,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就会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介入进来,难以约束其行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就不免成为一句空话。标签:市场机制论文; 公共权力论文; 资源浪费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竞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