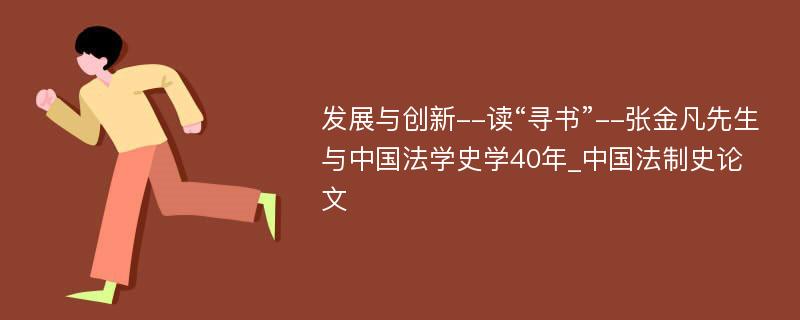
开拓与创新——《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四十年论文,法制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求索集》出版的学术意义
在国内法学界尤其是中国法史学界,说起张晋藩教授,总爱把他与中国法制史这门学科联系起来。〔1 〕笔者最近专门拜读了《求索集——张晋藩先生与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是:该文集汇萃了张先生研究中国法制史四十余年的代表性成果,展示了张先生四十余年学术“求索”的心路历程,也透现出前辈中国法制史学者为建立中国法制史学科的艰辛探索。现在学界普遍对于重建“学术规范”有所自觉,反思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术史,寻绎其中的学术传统和已有的“学术规范”,已是当前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内在要求。此时,出版一部中国法制史研究大家的代表作品集,自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笔者有此感觉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无论从研究“范式”的形成,还是研究领域的拓展以及研究的深度来讲,均有必要加以认真总结和反思。其二,张先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在中国法制史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可以说是大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典范之一;因此,对于张先生有关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思想的检讨,可以作为有关学术考察的一个重要个案。其三,这部文集虽然是张先生的个人文集,但是在两位主编陈景良和张中秋先生的独特设计下——重要论文写有“导读”,不便收入的学术专著写有“介绍”,同时还收入了一批张先生为各类法史著作写的“序言”,使文集的容量和信息大大增加;另外,文集取名“求索”,并且标以“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也与新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求索精神和发展历程相始终;所以,笔者以为这部文集可以成为我们进行学术史反思的一个典型和切入点。
要对这部文集的所有具体学术观点进行评论势不可能,也非笔者学力所及。以下只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术史界域出发,就笔者感兴趣的问题,略述几点看法和体会,是否恰当,还请学界同仁指教。
二、《求索集》与学术史研究
1.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文人学者对于学术的源流和师承。向来比较重视,认为“学问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而“类例既分,学术自明”;〔2〕所以十分注意“辩章学术,考镜源流”。〔3〕从中既可以见出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也可以窥见学术知识的累积与增长,更可以认清学术的权威及规范。但是,传统学术研究的主要门径和向导是目录和学案。然而,就传统律学来说,我们迄今尚未见到相应的著述。到了近代,著名修律家和法学家沈家本曾经写过《法学盛衰说》,对中国传统律学的发展沿革有过简要回顾和评说。〔4〕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律学的源流与师承关系,很少有人予以总结,以致现代学者难以窥得其中的奥妙。张先生的《清代律学及其转型》一文〔5〕, 则对中国传统律学的特点、基本精神、形成原因以及近现代的转型,作了很好的条分缕析。值得指出的是,该文真正做到了于传统律学学术史中揭发其意义和价值,见出其思想史、制度史特色;既避免了单纯的学术史资料的铺陈罗列,也避免了缺乏学术史基础的空疏浮泛。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有突出进展;但是,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少,主要表现在:学风浮躁,缺乏学术规范,方法陈旧等。因此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法制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学术基础,培植严谨的学风,导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均有必要进行严肃的学术回顾。在这一方面,张先生的工作非常引人注目,先后撰写了《中国法制史学四十年》和《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6〕;另外,还主持撰写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这一大型学术回顾著作〔7〕,其中涉及论文1500篇,专著150部, 对于有关论著的介绍和评论均详尽注明出处,使人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法制史研究四十年来的发展与成果,以及有关的治学门径,以嘉惠后学。当然,公平地说,这些学术史回顾著作也有其明显的弱点,即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缺乏学术方面的严肃评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检讨;沿着这一学术路径,还有必要重新整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道统”与方法,从而裨使中国法制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2.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及其学术史。对于中国传统法制较为系统的记述和评论,现在可以见到的,当首推东汉班固的《汉书·刑法志》,其后历代正史均有《刑法志》予以记述;另外,中国传统的律学家对于历代法制也有所研究。但是,所有这些记述和研究,笔者以为均偏重于“术”,着眼于“用”,而对法律中“学”,律学中的“理”,则往往不甚讲究,也未予阐明。这里所谓的“术”,是指探究事物(法律)运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所谓的“学”,则是指学术研究(律学)本身蕴含的“原理”和“思想”。中国古代的律学大致就是这样一门学问,因而与西方的法学有着根本差异。〔8〕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在本世纪初,有学者以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制史,从而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基础学科,也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当时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有如下突出特点:其一,史料有余而方法不足。例如,杨鸿烈先生的巨著《中国法律发达史》,厚达1250余页,史料相当丰富翔实,然而缺乏必要的方法予以诠释;其二,描述有余而论证不足,其间对于各朝各代的法律史料予以纵向排列,以及对于每个朝代相关的法律资料也予分门别类的描述,但是缺乏应有的评论和阐发;其三,视界相对狭隘,基本上是“就制度谈制度”〔9〕,缺乏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必要解释与阐发, 显得比较浅显。
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及其学术史。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要发展,张先生已在本文提及的上述文章和著述中有所讨论。例如,张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以及研究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等等〔10〕。笔者认为,根据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还可以概括如下:其一,研究领域有所开拓,从刑法史为主体到行政法史、经济法史、民法史、诉讼法史,从通史到断代史,从法典法规到习惯法等等。其二,研究方法有所创新,从制度本身的内部分析到政治经济的背景分析,进而深入到文化解读以及法律文化的比较诠释;引人注目的是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自觉地借鉴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更有学者自觉地在方法论上予以总结〔11〕。其三,研究史料有所拓宽,从法典正史到甲骨青铜铭文、秦汉简牍、敦煌文书、档案卷宗、神话传说、民间传说以及戏曲小说,乃至民间习惯调查材料等等,无不进入研究领域。其四,学风有所改善,从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宏观描述者多,有的显得比较空疏;近年来的研究有了明显改善,问题提得比较具体,注重论证过程,既关注原始资料的诠释又注意最新研究成果的运用;其间,学术规范开始受到重视,同时也关注学术知识的累积和增长。虽然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并不代表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全部,但是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缩影、一个标本。上述绝大部分内容,我们在《求索集》中均可以读到。
三、《求索集》反映的学术特色
1.确立中国法制史教材编写的“范式”。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al Kuhn)曾经提出科学研究的“范式”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尽管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颇为复杂,不易把握,因为仅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2〕一书中,库恩就对“范式”作过20余种不同的解释;但是,它的基本要义还是可以把握的。所谓“范式”,简单地说,就是指“某一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13〕笔者认为,库恩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评估张先生在中国法制史教材编写方面体现出的学术特色和学术贡献,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知道,新中国的中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的初始“范式”是脱胎于前苏联的“国家与法权历史”,〔14〕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三部《中国国家与法历史》。而在八十年代初,我们有了一部新的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司法部教材编写组,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由张先生主编,具有广泛的影响;其所确立的体系结构,也为后来绝大多数教材所蹈袭。到了九十年代初,我们又获得了一部新的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也由张先生主编。这部教材的特点是反映了张先生近年的学术思考,体现了张先生的“民刑有分”理论,扩大了行政法、民法和经济法等部门法的容量。这一安排,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法制史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去年,我们又看到了一部新的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律史》(司法部教材编写组,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同样由张先生主编。它的特点是制度史与思想史互相结合与相互诠释,可以说是一种新“范式”的尝试。这其中,张先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必须提出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笔者以为:其一,对于法律制度的界定过于狭隘,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传统正式法典、法规的描述。换言之,这一研究“范式”仅仅局限于对法律大传统的描述,而基本没有涉及民间习惯、规则的分析和诠释;〔15〕所以,它的解释力是极为有限,无法呈现中国传统法制的整体面貌。其二,这一研究“范式”满足于对法律制度进行静态的描述,而对于传统司法过程则缺乏动态的探讨,而后者恰恰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为,由于中国传统法制的文本规定与法制实践有着明显的差别;换言之,文本中的法律和规则,并不意味法律的“实现”。这些均是亟待改进和完善的问题。
2.从三个“?”说起。对于如何真正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王子今先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其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质,是不是已经有了全面的把握?其二,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不是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其三,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不是已经有了真切的体悟?〔16〕笔者以为,这对于我们探索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同样是极为切合的;换言之,如果要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那么,同样可以用这三个“?”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张先生对此是如何回答的呢?《求索集》中的有些篇什为我们提供了张先生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思考、理解和把握。
首先必须予以说明的是:张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的特质、内涵和精神的理解和诠释,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微观方面与宏观方面的进一步深入思考、研究后取得的。这里,我们不妨稍加引述。例如,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华法系特点探源》和《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17〕两篇广有影响的论文中,就比较充分地体了张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历史特质的把握以及基本内涵的理解和主体精神的体悟。在张先生看来,中华法系的独特之处在于:(1)皇权主义;(2)儒家伦理精神;(3)家族本位;(4)诸法合体和行政司法合一体制;(5)法律样式多元; 并且对其形成原因予以充分的分析阐发。到了九十年代初,张先生在文化理论的宏观视域上进行思考,提出了把握、理解和体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十大方面的问题,写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论纲》〔18〕,内容包含了上述的三个“?”。笔者将其概括如下:(1)反映小农经济的法律文化;(2)体现宗法精神的法律文化;(3)礼法合一的法律文化;(4)融合法、儒、道、释学说的法律文化;(5)多民族融合的法律文化;(6)在人类法律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法律文化;(7)兼具统一性、 包含性与孤立性、排它性的法律文化;(8)国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法律文化;(9)从比较视域看中国法律文化;(10)以历史态度评估中国法律文化。而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张先生认为就是“礼”。为此,张先生专门写了《论礼——中国法文化的核心》〔19〕一文,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见解和看法。
张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把握、体悟和阐释,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其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获致的结论也是精辟的。但是不用讳言,其中也并非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既深且巨的“天人合一”思想未进入分析视域。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讲,笔者以为“天人合一”是最为根本的表现。此外,有些具体的论证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表述上尚须清晰一些。最后,笔者浅见,要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首先必须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独特路径,并且在此大前提下来观察中国法律文化问题。笔者以为,梁漱溟先生的研究取径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和《乡村建设理论》诸书当中多有论述;虽然其中某些观点尚可讨论,但是,他的研究取径迄今依然颇具借鉴意义。
3.历史解释与现代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它的困难是多方面的,而最为突出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如何对待史料?因为我们探讨历史,它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揭示历史的真相。然而,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是被“封存”在史料当中的。例如,我们阅读古代的所谓“原始材料”实际上仅仅是古人对于历史的诠释;可以说它只有存在于“文本中的历史真相”,它与实际发生过而在历史学家记载以前已经消逝的真相有着一定的距离。对此,笔者以为,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成果来与传统法律文献资料进行相互释证,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充分利用史料方面,张先生的研究可谓涉猎广泛。例如,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这部巨著中,举凡“甲骨文、铭文、简牍文献、帛书文献;同时还包括经、史、子、集文献、编年体文献、传记体文献、古今原始资料文献,如起居注、实录、古文书、档案、文史资料、年鉴、少数民族历史文献。”〔20〕就研究取得的成果而言,我们可以举张先生对于中国古代“象刑”的解释为例。对此问题的解释历代众说纷纭〔21〕,张先生的解释,实际上是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的资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而后得出的;认为“象刑”是氏族社会的习惯。〔22〕
其二是,如何解释历史?真正的历史已经消逝,而所谓的“历史”只是保存在史料中的,由一种独特“话语”系统构建起来的“历史文本”或曰“文本历史”。对于这些文本,应当如何解释,这不仅涉及到历史哲学观,而且关系到历史方法论;当然也涉及到“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中西双方均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方法,这且不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已成为最为基本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公正地说,在解释历史方面,尽管学说纷纭,流派迭出;但是马克思的学说(当然,不能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拘泥于具体的论断和观点,而必须在总体上予以把握)依然是最具解释功效的。笔者甚至认为,自从有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学说,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它,都是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的。张先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红线”。其中的范例我们无法一一例举。如果一定要举的话,1992年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是一绝好例证。众所周知,在台湾出版大陆学者的著作,是不便直接引述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的。而《求索集》的编者认为:“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没有引用一句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但却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23〕张先生取得的成就恰好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在此笔者并无意否认其它历史解释方法和功效;恰恰相反,对于其它历史解释方法我们还必须认真予以研究,加以吸收和运用,从而使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通过各种解释方法的运用得以呈现和揭示。对此,张先生也有充分认识。例如,近年来张先生有志于从文化视角来解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即是。
研究历史,解释历史,其意义究竟何在?这是每个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实用主义的流行,历史著述的基本目的往往在于“资治通鉴”;所以研究历史是极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具有为政治而历史的特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泛政治文化”在思想学术领域的极端反映,这从历史王朝每每将修史作为“盛典”便可见一斑。此外,还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就是“为历史而历史”。笔者以为,如果从历史研究本身要求的脱离政治干预的独立性而言,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角度讲,则是与理不通的。通读张先生的有关论著,笔者感到,他对于中国法制史的诠释是忠于历史真实的,对于历史资料的分析也是严格的、谨慎的。可以说,在张先生看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的首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历史。在此基础上,张先生的研究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忧患意识”和现实的责任感、使命感;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法制的“历史借鉴”问题,为此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了一家之言。那么,在中国传统法制当中,有何值得借鉴之处呢?张先生的研究结论是:(1 )盛世与法治;(2)改制与变法;(3)礼乐刑政综合治理;(4 )治法与治吏等方面。所以在张先生看来,研究历史的意义还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法制建设提供借鉴。当然,在笔者看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的“智力游戏”,有时它的意义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但是,对于人类智力的进步和发展,则是非常有益的。
这篇读书笔记或者说评论,写到这里已显太长。但是,笔者以为,对于张先生《求索集》的评论还是显得太短了;因为,文集中可以讨论、分析的话题实在太多了。张先生自己也还在不断地学与思。所以,笔者想在此借张先生的话结束本文:“我仍然在前进着。”
注释:
〔1〕陈景良:《林园求学记——记我的导师、 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秋季号;也见《求索集》附录二。
〔2〕郑樵:《校雠略》。
〔3〕章学诚:《校辩通义》。
〔4〕沈家本:《寄簃文存》卷三。
〔5〕原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4期;也见《求索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1—598页;以下凡是引用该书文字,仅注页码。
〔6〕参见《求索集》第172—194页和第660—665页。
〔7〕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类著作尚有曾宪义和郑定编著:《中国法律制度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曾宪义和范忠信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通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当然,单篇的文章也有,此不枚举。
〔8〕关于律学与法学之间的这一根本差异的讨论, 可以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六章“法的学术:律学的法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274页。事实上,我们从张晋藩《清代律学及其转型》当中也大体可以见出中国传统律学的根本特性。张先生指出:“传统律学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法学”,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着眼于实用”。参见《求索篇》第562页。
〔9〕《求索集》第173页。
〔10〕参见《求索集》第172—194页和第660—665页。
〔11〕参见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4卷(总第5期),第119—143页;梁治平编著:《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72页。
〔12〕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Chicago,1962.
〔13〕夏基松、沈斐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关于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详细讨论, 参见本书第168—181页。
〔14〕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求索集》第6—13页。
〔15〕即便是近年出版的那些冠以法律文化史研究的优秀著述,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例如梁治平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武树臣等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基本上都是对于法律文化大传统的诠释。笔者以为,这种研究“范式”虽然有其解释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也即人数众多的小民百姓的法律意识、他们对于法律的认知态度、调整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其法律文化史意义如何?例如,被人们毫无质疑地接受的关于中国古人的所谓“厌讼”观念,在笔者看来,便是文化精英用关于法律的理想“话语”构建起来来的一个法律文化中的“神话”;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关于“厌讼”的理想“话语”,以及基层衙门讼案不多推导中国古人“厌讼”的结论;更何况中国古代讼案不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利益”的考虑更是至关重要的(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拙文:《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诉讼观念》,《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最后, 日常生活经验也可告诉我们,中国人是颇为“好争”的。当代的例子可以举著名的“秋菊打官司”中的所谓“给个说法”,有的学者以此认为当代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有了发展;抽象地说,这种观点似乎不错。但是,如果问一下“果真如此吗?”便不无疑问。因为对于“给个说法”的诉求,我们必须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予以体认,方可了悟(有关的质疑,请参见苏力:《现代法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东方》1996年第4期)。
〔16〕王子今:《中国文化遗存的深层发掘——读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中国书评》(香港)1996年5月总第10期,第214页。
〔17〕参见《求索集》第220—251页。
〔18〕详细的分析,参见《求索集》第621—635页。
〔19〕参见《求索集》第636—641页。
〔20〕参见《求索集》第555页的概括。
〔21〕有关的史料和分析,可以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344页。
〔22〕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也见《求索集》第556页。
〔23〕参见《求索集》第5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