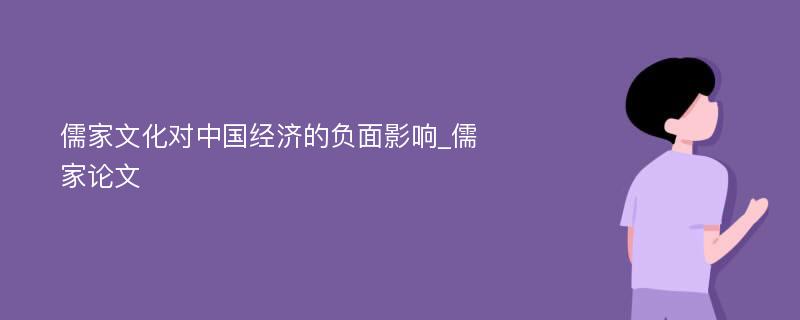
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负面影响论文,儒家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文化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它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产生过深远广泛的影响,经济生活也不例外。本文试就其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加以探讨。
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国经济主体的被动性
国民经济主体应该说是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善人类自身生存状况,主要靠人本身。然而,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命”成了人之外而又主宰人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不屑一顾、不知天命。孔子说:富裕如果是可以追求的,那么为人赶车他也不在乎。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我行我素,任其自然吧。言外之意,富贵在天,并非人为。
儒家这种经济主体天命观,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停滞。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都埋没了。到处可以看见的是一种奇怪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人贫困不堪而内心并不骚动,贫于财富而富于情感,生活清寒却对赚钱之事冷漠。
经济主体天命观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有关。中国封建经济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社会里,即使赋役和地租剥削率不变,人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天时地利的变化也会波动很大。岁美则穰,生活相对宽松;岁凶则恶,生活极端拮据。“靠天吃饭”这种想法就自然形成。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政治是一种高度发达的专制政治,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贫富带有明显的偶然性。一个人勤勤恳恳地从事耕作或工商业,很难成为富翁,相反各种机遇(如政治提拔、商业垄断、科举道路、裙带关系等等)却能让人腰缠万贯、权倾一时。而机遇并不具有规律性,人们觉得好像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玄妙而虚幻的力量在左右这一切,这就是天命。在这种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和极少数权贵,绝大多数人都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生杀予夺全在统治者,区区贫富算得什么?因此,国民经济天命观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残酷的专制政治合成的产物。
二、“存天理,灭人欲”——中国经济动力的绝弃
禁欲主义几乎是所有宗教所倡导的。儒家文化虽不是一种宗教,但近于宗教,这已是哲学和宗教界所共同承认了的。
佛教、伊斯兰教都提倡禁欲,但这里只用新教的禁欲主义同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进行比较。
新教禁欲并不否定追求物质财富的必要性。《圣经》有关经文甚多。如“财富保护富人”,“勤劳致富”,“收获季节大睡特睡的家伙不光彩”,“穷人挣扎生活,富人享受生活”等等。新教的禁欲仅仅表现为对财富的珍重、爱吝和追求,其结果为资本的不断积累。
儒家的禁欲则不同。首先它不鼓励人们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对发财致富欲在舆论上持否定态度;其次儒家的禁欲并不表现为对现有财富的爱惜,结果并不促进资本积累,因为节余下来的财物总会在某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花掉。因此儒家的禁欲,实质上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因素里,没有比存在于社会成员心中的原始的强烈致富欲更巨大。恩格斯讲过,卑鄙的贪欲是私有制社会的动力,追求个人财富是私有制社会唯一的具有决定性质意义的目标。而儒家文化却要消灭它,岂不是对经济动力的绝弃?
新教既宣扬为了上帝而节俭,又宣扬为了上帝而致富,把禁欲等同于反消费,如此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都成为可能。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上肯定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源泉的。与此相反,儒家的禁欲却表现为知足知止、安贫乐命,远离经济生活,而不注重为积累而节约。该禁的欲没有禁,不该禁的欲却特别认真。因此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步。孔子说,放乎而利行,多怨。孔子对于人的利欲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儒家文化指导下的政府对于经济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和压抑的,人们对经济生活缺乏热诚,整个经济气氛沉闷。
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经济效益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注重经济效益,既没有投入产出概念,也没有机会成本概念,纯以道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千百年来,很少有人计算过农业劳动耗费量,怀疑过家庭手工业的合理性,认识到自然经济造成的巨大浪费,研究过经济核算问题,为追求生产力进步、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催促新经济现象诞生的社会土壤十分瘠薄。
然而另一方面,非难功利的说教却不厌其烦,讲得头头是道,义正辞严。它宣称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那些儒化官吏无不讳言财利,从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一心只想如何束缚人们的思想,按照封建道义(亦即所谓“天理”)摆布天下。
我们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思想的毒害。
修铁路、建工厂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以其代替人力畜力运输、家庭手工业本无什么惋惜可言。然而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还为此等问题争论不休呢!反对派指责,这些近代生产力象征严重伤风败俗,破坏风水,有碍男女之大防,使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破产,瓦解自然经济及其相应的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明知新的生产力那巨大的效益,却因为担心封建道义的破坏而没有坚决反对,以至于花钱买下外国人修的铁路而拆掉,捣毁近代民族实业家惨淡经营的企业……你说,多么荒唐啊!
明清以来实行愚不可及的海禁政策也是一例。许多进步人士反复劝告朝廷开放国门既可以增加关税收入,促进对外贸易,又能保证沿海人民的生计。可是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就是充耳不闻,他们害怕中外接触,会动摇封建道德体系,宁愿让沿海人民生计窘迫,贫困不堪,也决不对外开放。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打开国门,但中外接触仍有许多限制。要是外国人愿意的话,反动政府还想关门大吉呢!
类似例子还很多,像所谓“奇技淫巧”当禁、货币流通当限、祭祀凭吊当铺张等等。它“遵循”伦理却忽视经济规律,只顾一时经济平衡,往往牺牲经济增长。其消极影响十分严重。
四、“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
稍具中国经济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在战国时候,就已广泛采用牛耕铁犁。而时至当今,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要象征仍然是铁犁牛耕。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经济文化为什么如此滞留不前?
假若我们将中国的其他农业生产力象征、手工业产品数量和质量、商业组织形式、货币流通理论和制度、交通状况、都市建筑等,同西方同期相比,我们会发现,历史愈是接近近现代,我们愈是惭愧。
中国是最早采用纸币制度的国家,可是直到近代,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发达的货币经济;二千年前就出现了十分繁荣的都市,可是在统一的帝国政治下,城市始终软弱,没有独立的意义;长期以来只有伦理和礼仪规范,缺乏完善的法规制度,尤其是商法之类,缺乏近代资本主义投资所要求的理性的法律程序,以世袭制、宗法和政府首脑兼任这一切。在儒家那里,物质福利不是诱惑的源泉而仅仅是彰扬道德的重要手段。先秦诸子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后世不敢越雷池一步,西学东渐时,仍有人在津津有味地咀嚼而丝毫不觉陈腐……
这究竟是为什么?儒家文化是不是有问题?
儒学告诫中国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在这种观念指导和激励下,数千年来具有一流头脑的中国人都走上了读书、作官、食禄这条路。“学”的是仁义礼智、治国安邦之术,“官”的是正义明道、吟诗作赋之事。对于那些名落孙山的不幸儒生来说,如果不想作小人的话,也不会投入经济生活中去的。正像马克斯·韦伯所说,儒学培养出一批高级书呆子,除了哲学、文学,其它知识极少,尤其是科技、经济、法律方面的。相反,清教徒则受到《圣经》中如法律知识和经营管理思想的教导,他们把自然科学知识看成是在职业劳动中合理控制自己的手段,而把哲学看成是浪费光阴的把戏。
儒士的智慧没有注入经济生活中去,中国经济文化的贫乏就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创造过优美的文学和独立而深刻的哲学,却让经济文化长期停滞落后,为什么中国人贫于财物而富于情感。
五、“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中国消费的特殊性
宗教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绝对地起阻碍作用。教义不同,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不同。新教伦理已为马克斯·韦伯证明为资本主义精神源泉。根据他的分析,新教中的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使自己服从于这笔财产,他必须厉行节俭,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同时必须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增殖财富。这样新教就以上帝的意志向人们宣布了两件神圣职责,一是赚钱,二是节约。人生的总目标无非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争做上帝的选民而积累财富,显然这对积累、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作用巨大。与新教伦理相比,儒家文化不仅对财富保值和增殖缺乏责任感,而且提倡轻视和浪费财富。儒家在提倡崇俭的同时,对某些特殊的消费项目不仅未加限制,反而为之辩护、鼓励。这些项目包括宗教迷信开支和家庭外交开支等。儒学认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因此儒学中的节俭不过是为了往后某一项浪费。因此许多人平时节俭,而始终又处于贫困之中。为了娶媳妇、建房子、奉老归山或者为了某一件根本不值得大肆庆祝的事情而耗尽积蓄家产。“破家尽业,以充死棺”,“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死以后,乃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旅以求名”,“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节俭与浪费并存,省约与铺张相随,使资本积累无以形成,“贫穷、节俭、浪费、贫穷”的恶性循环难以摆脱。
(摘自《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