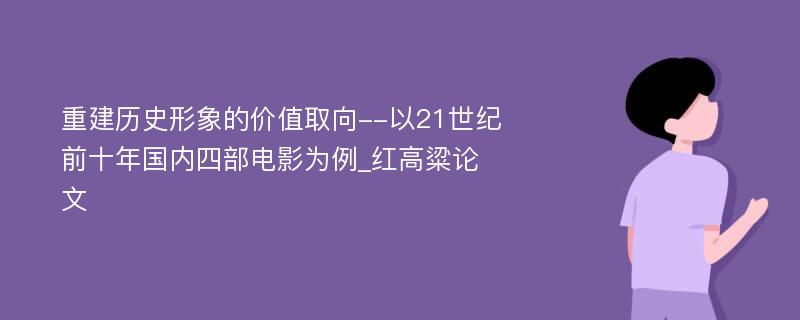
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取向——以21世纪头十年四部国产片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影像论文,世纪论文,国产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1世纪头十年过去的时候,盘点这十年间中国大陆电影状况,虽然可以欣慰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势头,特别是影片生产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观众数量的疾速回升,但真正令我难以忘怀的优质影片或堪称经典的影片却并不多。相比之下,我记忆里最具影像修辞效果并值得回味的国产片有四部:《英雄》(张艺谋执导,2002年)、《三峡好人》(贾樟柯执导,2006年)、《集结号》(冯小刚执导,2007年)、《让子弹飞》(姜文执导,2010年)。也许还可以开列其它一些影片(如《天下无贼》、《孔雀》、《唐山大地震》、《疯狂的石头》、《立春》等),但我以为上述四部影片不仅可以在这十年中国电影艺术史的推进上留下深刻印记,而且也可以在这十年中国电影文化的演进中刻下醒目路标,并且还会对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电影产生重要的影响。我在这里的探讨将不会集中到它们是否将成为“经典”的问题,而主要是叩问它们在文化价值问题上遗留的症候。①
一 《英雄》:崇高也卑微
在《英雄》结尾处,当李连杰饰演的英雄无名疾速行走在刺秦道路上时,残剑拦住了他,在地上写了两个大字:“天下”。在这两个大字面前,个人及其家庭的仇恨似乎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在天下需要秦王以统一而带来天下和平的大势下,刺杀秦王无异于阻挡历史车轮向前。正是这种内在意念的驱动,迫使无名与秦王之间的烛火摇摆不定。秦王将剑掷在无名桌前说:你选择吧!当秦王背过身去,无名面对这把宝剑,不禁想起残剑写下的那个巨火的“剑”字,立时明白了残剑在三年前领悟到的东西:“第一重境界,手中有剑,心中亦有剑”;“第二重境界,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第三重境界,手中无剑,心中亦无剑”。无名做出了艰难而正确的决断,垂下双手,转身走出大殿。三千黑衣侍卫急速拥上,发出“杀,还是不杀,请大王定夺”的请示。秦王沉吟着:“若不杀,则有违大秦律令,有碍统一大业。”随之果断挥手,万箭齐发,无名缓缓倒下。
崇高而又渺小的无名倒在似乎遮天蔽日的黑色中这一幕,在全片中具有重要的总体象征意蕴。影片表现了由无名、残剑、长空、飞雪、如月等组成的侠客群体向秦王复仇的故事。他们面对秦王,试图“知其不可而为之”地阻挡其统一天下的强有力步伐,显示了可贵的崇高品质。但影片竭力想告诉观众的是,这批英雄虽令人景仰,但在个人命运服从于历史演变大势的局面中,在个人利益归于群体利益的大趋势下,不得不显出某种渺小。也就是说,面对天下需要和平的大势,崇高的个人其实终究是卑微的。
影片站在历史趋向统一以便结束内战的大势下,为秦王残暴无度的统一全国的战争寻找到了一种历史合法性。这种历史兴亡感的表达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电影毕竟不等于史书,而是艺术。而艺术是应当立足于人的命运的,也就是应当从个人命运的角度去反思历史。影片在为秦王的残暴战争寻找到历史合法性的同时,却没有为那些无辜而受戮的千千万万个人寻找到生存的合法性。他们的死难道不需要哀悼和惋惜?战争的残酷性难道不需要控诉?超个人的历史兴亡感固然需要,但来自个人的人性诉求其实应有更具实质性的意义。一位当年曾致力于为个人权利发出有力呐喊的导演(如其影片《红高粱》、《菊豆》、《活着》等),现在却竟然轻易忽视个人价值,这是影片至今还留给人们的遗憾和不解。当然,也可以同情地理解说,当编导把更多的精力投寄到中国流视觉盛宴的精心打造时,当视觉美学效果的重要性被视为远胜于那些可有可无的精神内涵探求时,这样的遗憾和不解便是不奇怪的了。
二 《三峡好人》:卑微也崇高
与《英雄》中舍身刺秦的侠义英雄群体的悲剧故事相比,《三峡好人》所讲述的无疑处在另一极端:一群卑微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从男女主人公韩三明(挖煤民工)和沈红(护士)到三峡库区寻亲的经历,观众可以目击处于高风险社会中个人生存状况的变幻莫测及命运的交错组接。韩三明来奉节,是要寻找分离十六载的“前妻”麻幺妹和女儿;与此平行的是也来自山西的护士沈红对离别两年的丈夫郭斌的苦苦搜寻;中间还可见到一位喜欢模仿影星周润发式侠义做派的男孩“小马哥”。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卑微的底层“小人物”。
从影像所再现的生活世界看,这群小人物却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当今三峡库区的一群或几群人,各有其符合自身阶层身份和生活状况的生存合理性。他们也拥有自己有限的或实用的生活“理想”或“幻想”,并以自身特有的不得不如此的奋斗或抗争方式去加以追求。他们明知身处生存的巨变风险中,却能处变不惊,体现出一种生存的韧性。韩三明和沈红性格上的一个共同点正在于展现出生存的韧性。一方面,他们都拥有跨越差异鸿沟而寻求沟通的巨大的情感动力;另一方面,他们也都能妥善地控制这种情感动力,并使这两者正好达成一种大体的平衡。这意味着,他们对当今人际鸿沟现状诚然有着沟通的强大需求,但同时也有着清醒的承认。作为银幕呈现给我们的新一代底层“小人物”,他们既清楚生活中金钱、地位、情感等无情鸿沟的存在现实,但又力图加以跨越;既力图跨越但又承认这种跨越的艰难。他们正是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坚韧地寻求自己的生活梦,由此不难体察到一种新世纪生存风险语境下特有的异趣沟通精神。
这种异趣沟通精神的具体呈现,可在韩三明与“小马哥”交往的四度重复上集中见出。小马哥在全片中的角色看起来并不起眼,且韩三明无论从年龄还是生活趣味看,本来都不大可能与那个怀旧而又故作侠义的“小马哥”牵扯上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四度相遇却导致新的可能性发生。第一次相遇“小马哥”按周润发式做派自己点烟,捉弄了新来乍到的韩三明,表明两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个人差异。第二次相遇是在小马哥被韩三明解救后一块喝酒,当看见他那保存完好的写有麻幺妹地址的芒果牌香烟盒时,两人之间的鸿沟就在彼此都有“怀旧”之情的领悟间融化了。第三次相逢,这个带有某种崇高幻想的“伟大的小人物”,在前往参加自以为行侠仗义的“摆平”举动前与韩相约喝酒庆贺,表明他们的沟通在持续深化。第四次相遇是通过韩三明向“小马哥”遗像默默敬烟时实现的。从这四次相遇可见,他们之所以能从个人差异走向相互沟通,是由于内心都有着一种淡隐而坚韧的关爱他人的温情。韩三明走上漫漫寻妻路,可见他是个有情人。而这种关爱之情也体现在他对萍水相逢的“小马哥”生前的照顾和死后的追挽上。同样,“小马哥”从外表和身份看几乎就是个“小混混”,但言行举止中透露的英雄品位、对韩三明的真诚关切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等,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那颗幼稚、卑微而又坚韧的关爱之心,这是仁爱与侠义在卑微中的一种奇特融汇。其实,在卑微而又仁爱和侠义这三者的结合上,这两人是颇为相近的。在这个充满生存风险的社会里,他们虽然根本不具有足以改变现状的巨大力量,并且还显得过分软弱,但却是务实的、真情互动的,带着人际沟通的温馨,远比某些艺术作品中的“假大空”和网上虚拟社区或“爱情”更有价值。这种异趣沟通的社会价值显然表现在:让生活在动荡、孤独与忧患中的个体之间能跨越彼此鸿沟而实现相互抚慰。韩三明与“小马哥”凭借珍藏的芒果牌香烟盒互叙怀旧感,并用手机交换《好人一生平安》(电视剧《渴望》插曲)与《上海滩》插曲彩铃,从而实现真情融汇的场景,无疑可以作为当代人与人之间达成异趣沟通的经典镜头之一而流传下去。②
诚然,《三峡好人》没有取得多高的票房业绩,说明其观众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极其有限,但这样的影像再现却自有其独特的现实价值。重要的是,在社会大变迁导致个人生存充满高风险的当今时代,卑微个人的实实在在的生存改变之举,或多或少也会呈现出某种崇高品质来。卑微也崇高!影片所呈现的这种可能性至今仍具有意义。
三 《集结号》:小义也大
在社会大变迁时代,个人的命运包括其崇高的英雄壮举本身也许终究显得渺小,但是在《集结号》中,看起来渺小的个人却可以凭借其不懈的义举而赢得崇高美誉。
《集结号》前半部在外观上颇像以视、听觉奇观引人入胜的战争片。但随着剧情的进展,战争奇观越来越只像故事动人耳目的外形,而处在故事内核的却是那种“义”或“义气”,它具有真正动人心魄的神奇力量。影片似乎毫不吝惜地吸收儒家伦理中的“舍身取义”精神并加以表现。谷子地甘为上级命令奋勇献身、为死去战友顽强讨回公道,这种“取义”精神可以说是对古代儒家仁义传统的一种当代弘扬,更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今老百姓在生活中激发的对于“正义”的强烈诉求。通过这部片子,他们能够象征性地宣泄其积压的“义气”,得到一种虚拟的满足。不管刘恒和冯小刚自己的编导意图怎样,我们从影片中看到的是,谷子地身上有效地聚集了当前主导价值系统所认可或容纳同时又为中国公众所普遍接受的“舍身取义”、战友情义、誓死讨回公道等“正义”之举。影片的客观效果在于,其所寻求的以“义”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与以“社会和谐”为“本质”的当前主导价值观顺畅地实现了有缝的“缝合”,从而促成了娱乐片的儒学化。可以说,强化儒家“义”的价值观的感召力,实现娱乐片的儒学化,成为《集结号》同时赢得公众和政府的一个法宝。
《集结号》传达了社会巨变中的个人正义诉求。与社会变迁的博大、浩瀚相比,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照《英雄》的内在价值逻辑推演,个人利益是完全可以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被牺牲掉的,例如无名最后为了“天下”而忍痛放过罪恶昭彰的秦王,被后者下令射杀。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却把阵亡战友的身后尊严俨然看做自己的命根子,必须全力加以追求和守护。这种对个人尊严或名誉的维护之义举,同社会巨变相比实在属于再大也小。但是,就个人生命价值的神圣性本身来说,这种小义其实也终究通向大义,所以再小也大。它属于社会大义链条中的个人小义诉求,小义也通向大义,所以小义也大。
四 《让子弹飞》:大义也小
《让子弹飞》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民国乱世,土匪张麻子(牧之)打劫县长专列后冒名顶替上任鹅城,端掉恶霸黄四郎并解放全城百姓。尽管故事的背景是在民国乱世年代,但由于编导匠心独运,其蕴含的体验领域和意义空间却实在广阔而又多义,因而让观众看片后心情同现实中的反贪官、反腐败、反恶霸等胜利息息相通,单从这点看,影片让观众在畅快的娱乐中领略其兴味蕴藉(或现实教化意义等)确实属成功之举。
按理说,《让子弹飞》体现了姜文为首的制作团队的过人电影才华和创造力,为21世纪头十年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句号。这样的影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但不知怎么的,我的脑海里又总是闪现出23年前观看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时的那些影像,总觉着这两部佳片分别营造的两个影像系列之间,精神气质颇为近似,突出地表现在追求个人生命强力的热烈和狂放上:《红高粱》通过颠轿、野合、酒誓等镜头,试图揭示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对个人生命强力的追求和享受,这是那个文化启蒙年代知识分子竭力求取的阶层大义;《让子弹飞》则透过张牧之对鹅城恶霸黄四郎的快意复仇和对全城百姓的解放,仿佛成功地当然又是想象地发泄了市民积压于心的对贪官、不义、不公等世相的愤懑之情,这应是市民全力求取的大义。不同的是,《红高粱》打造的是生命强力的悲剧,而《让子弹飞》奉献的却是生命强力的喜剧。
真正导致这两部影片相似的地方,是在一些细节处理方式的相似上。与《红高粱》倾力渲染颠轿、野合、酒誓等野性镜头相一致,《让子弹飞》中有小六子自掏肚腹证明清白的血腥镜头。同样,前者中“我爷爷”余占鳌据传干掉了麻风病人李大头并自己取而代之,后者中张麻子一举杀掉黄四郎的替身,从而导致除恶义举出现重大转机。这两部影片的共同点在于,虽然都狂放地张扬生命强力,但在生命强力的价值取向上却陷入迷乱:张扬个人生命强力难道就必须以其他个人生命力的必然灭绝为代价?按这样的逻辑演化下去,难道不等同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了吗?我猜想,这两部影片编导在主观意识层面当然不会这样做,只不过是在上述细节的处理上出现了这样的无意识的逻辑陷阱而已。他们似乎都是为了让故事“好看”而听凭自己的直觉和才华纵横驰骋的。但正是这种潜伏在直觉或才华中的无意识的价值迷乱,恰恰需要引起警觉。因为,这种无意识的东西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探寻到位于这个时代价值体系深层的隐秘症候上。
就《让子弹飞》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为观众所拥戴的一身侠肝义胆的张麻子究竟富有何种侠义?也就是其言行的侠义内涵到底在哪里?当片中大家跟随张麻子冲进黄四郎碉楼欢庆胜利时,是否来得及清醒地想过,这张麻子身上到底蕴含有何种大义而让我们倾心跟从?我们到头来难道不会成为他们以暴易暴的简单工具或炮灰?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他颠覆县长后却自己取而代之,希图的是通过官位赚取钱财,不然,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代替县长“占有”其夫人(虽然都是假冒的)呢?这一细节让人感受到他的性爱品位低俗,缺乏应有的侠士风范,并且同影片结尾时他为了成全老三而忍痛放弃自己心仪的花姐这一潇洒风度之间,构成一种自相矛盾。由于这样的细节处理上的迷失和混乱,一种隐匿于无意识深层的价值迷乱就必然显露无遗了:我们享受到一出几乎精彩绝伦的乱世强力喜剧,却没能从中品尝到它应有的富于正面价值的兴味蕴藉。在这部乱世强力喜剧中,乱世时代的民族大义感虽然竭力要呈现,但因在整体价值理念构架上陷入迷乱,到头来实际上是大义也小。价值迷乱,在这里是指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迷失和混乱。衡量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得失,关键不仅在于其正义行动的结果,而更在于这种正义行动的运行方式及建设目标蕴含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其中隐伏的当下现实生活世界的价值尺度及其重心。在这样的价值尺度及其重心上陷入迷乱的影片,是不可能享有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化软实力的。③
五 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迷乱
电影是要通过镜头去尽力再现历史影像的,由此达到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这种影像解释自然会蕴含着解释者或明或暗的历史理性及其具体的价值尺度。也就是说,影片无论褒扬或贬斥什么、同情或鄙夷什么,总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④。但我们看到的是,影片虽然在历史影像再现方面取得令人惊艳的修辞效果,但却在其蕴含的价值取向上陷入一种迷乱。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特别是当中国电影正在力求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向“电影强国”目标迈进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及其原因更值得关注。
从上面四部影片看,价值迷乱的出现是基于复杂的原因的,其中之一,不能不从历史视点的选择上去考察。这里的历史视点,是指看待历史或社会问题时所采取的带有某种价值评价意味的立场或观察点。当《英雄》中奋勇刺秦的几位崇高个人(英雄)被放到宏大的“天下”视点上,崇高也就必然地转向了它的反面——卑微或滑稽。真正崇高的似乎不再是为正义而牺牲的个人,也不是完成天下一统大业的秦王,而是类似黑格尔“永恒正义”概念所指称的那种绝对理性之物。问题不在于去论证“永恒正义”该不该取胜,而在论证“永恒正义”合理的取胜时,个人的牺牲该不该同时得到某种同情式惋惜——基于当代个人视点上的合理化惋惜。缺乏这种足够的合理化惋惜,就必然导致整体评价上出现个人价值的缺损,所以令人生出崇高也卑微之感。同样,当《让子弹飞》把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义都狂欢式地凝聚到张麻子身上,而张麻子本人没能呈现出足够清晰的价值取向,群众也只是一帮毫无独立个性且唯利是图的小人时,整部影片的集体正义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走向大义也小之途。显然,历史视点选择上的混淆、特别是个人视点的迷失,是导致价值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价值迷乱现象的出现,又与影片创作团队的创作力量分布重心有关。为让影片变得好看,就难免忽略价值视点的清醒而又明确的选择。而一旦注重价值视点的选择,或许又必然出现观赏效果上的缺失,让影片只顾思考或教化而丧失观众,顾此失彼。这或许表明,中国电影存在着某种创造力旺盛而又底座脆嫩的症候。
归结起来,出现这种症候的原因,不能只是从影片创作团队(含编剧、导演、表演、美工、摄影、录音等)的综合水平去看,而且还应从影片评论、报道、研究环境看,或许更应从当下整个文化界的文化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基础看。这里不妨从社会革命年代电影到社会改革年代电影的转变中去稍作分析。谢晋的“反思三部曲”曾经代表了社会革命年代电影的终结,其当时呈现的价值体系是基本完整的,体现了谢晋一代导演对中国社会革命年代历史状况的一种基于知识分子立场的价值反思。许灵均、罗群和秦书田等形象凝聚了谢晋一代有关中国社会革命年代何为正义与不义的反思。而今的中国电影,体现了从社会革命年代电影向社会改革年代电影的转变趋势。上述四部影片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改革年代电影的一组范本,它们在价值体系建构方面还处在生成途中,是变动不居的,还有待于形成自身的完整性。从对秦王与刺客群体之间、对张麻子与愚昧的群众之间的刻画上,可以见出一种犹豫或含混:是要群体和谐还是要个人正义?群体和谐与个人正义之间难道就是必然对立的吗?归根到底,我们这个年代对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没有想清楚,从而客观上还不能向影片提供一种相对清晰的价值构架。
在当前,这种历史影像再现中的价值迷乱问题,已到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步了。因为,这类问题不仅出现在《让子弹飞》里,其实也或多或少地出现在这十年的其它影片里。诚然,在中国历史的秦代时段出现过以国家大义无情地取代个人正义的历史悲剧,但在我们这个愈来愈重视个人价值的“以人为本”的时代,却不能不需要对此表达一种当代人的历史反思态度。因为,重要的不是再现什么历史,而是如何为当代人的生存尊严而再现既往历史。也就是说,当代人为了当代而对历史场景的影像再现,以及对历史场景的当代意义的评价与吸纳尺度,才是真正重要的。
中国电影在通向世界“电影强国”的征途中,需要仰赖多方面的合力。在这些不可缺少的合力中,就应当有文化价值上的理性建构立场。缺乏清醒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取向,是不能奢谈什么“电影强国”的。中国电影要想成为真正的“电影强国”,不仅要强在影像观赏方面,而且更要强在其蕴含的价值理念上。这样,向内建构和向外传播起来的才是真正的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7&ZD037
注释:
①本文原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成立30周年论坛之约撰写并宣读,此次作了一些修改和调整。特向章柏青会长等致谢。
②参见笔者此前的相关分析,见《新编美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279页。
③参见笔者短论《〈红高粱〉的忘年兄弟》,《电影艺术》,2011年第2期。
④[德]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
标签:红高粱论文; 英雄论文; 让子弹飞论文; 韩三明论文; 三峡好人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武打片论文; 西部电影论文; 喜剧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