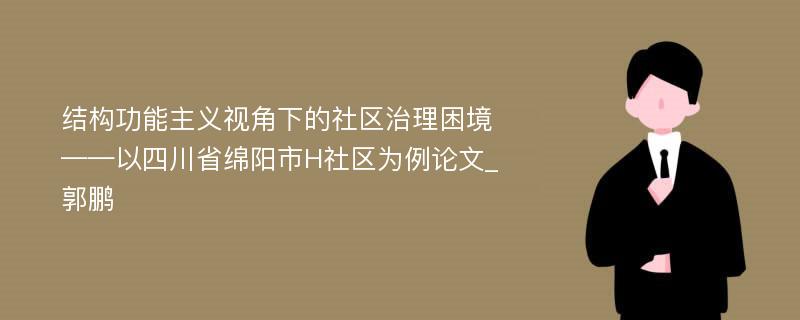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原有的村落组织逐渐被城市社区所代替,但是由于我国社区治理工作发展较晚,这一时期社区治理过程中突显出很多问题,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不够、基层管理人才配置不足、非政府组织有待完善和社区服务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分别对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进行分析,为解决这些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机制、提供社区管理工作人员薪资待遇和引进青年人才、加强对社区非政府服务组织的管理与支持和推动社区治理民主化建设。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社区治理;城市化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结果显示:1949年-1999年,中国用了50年的时间才将城镇化率从10.64%提升到了30.89%,增幅为20.25%;1999年-2017年,中国用了18年的时间将城镇化率从30.89%提升到了58.52%,增幅为27.63%。[1]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11月2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化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9.58%。而四川省作为全国人口大省之一,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79%,大量因城镇化失地或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在城市站住脚跟成为城里人。[2]但是随着农民搬出村落住进高楼和“农转非农”身份的转变,导致以生产队为组织结构的管理形式逐渐没落,同时也使得我国自1982年建立农民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失去原有的作用。由于他们对城市社区管理方式不熟悉和对自身权利的不了解,使得这些新市民较少参与到社区治理的活动中,这不仅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还使新市民的自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一、绵阳市某社区的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绵阳经济发展飞速,城区由原来的两个区发展为现在的三个区,城市面积将近扩大了两倍,城市人口常住人口达到79.46万人,城镇化率为52.51%。[3]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城市周边的村落转变成社区,原有的组织管理模式逐渐被社区自治所取代。
以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H社区为例,该社区成立于2003年11月,地处绵阳市政治中心,紧靠绵阳市委、市政府,辖区面积3.8平方公里,东至双碑中街与双碑社区相邻,西至普乐街布鲁斯国际新城,北起绵兴东路,南至滨河北路中段枫璟398小区。辖区有驻区企事业单位5个,大中型企业109家,商住小区13个,在建小区4个,征转型居民小组2个。辖区有常住居民15600余户、26000余人,流动人口20800余人。社区服务中心的专职工作者5名。[4]在这样大的社区里,居民的社会背景也非常复杂,由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资料来看,发现该社区居民的从事职业主要有:政府公务员、学校老师(包括小、中、大学的教师)、个体户(从事大、中、小型商品贸易)、事业单位职员、商品销售人员、公司职员、建筑工人、学生、医护人员、餐饮从业人员、司机和其他职业。
关于社区成员职业占比:政府公务员占2.5%、学校老师占1.4%、个体户占23.3%、事业单位职员占5.5%、商品销售人员占17.2%、工厂工人占15.1%、公司职员占10.2%、建筑工人占8.7%、学生占8.2%、医护人员占2.3%、餐饮从业人员占4.1%、司机占1.2%和其他职业占0.3%。而关于社区成员性别占比,男性占51.3%,女性占48.7%。另外社区成员年龄占比,0-14岁的青少年占33.6%,15-64岁的成年人占45.6%,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20.8%。
通过对该社区的走访和抽样调查可以发现,该社区人员层次非常复杂。首先从居民数量来看,属于两万多人的大型社区;从人口结构来看,男女比例较为合理,在年龄比中青少年和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这是属于一个较为年轻的社区;从居民的职业来看,从事行业复杂多样,其中从事个体、销售和工厂工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该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占绝大数,以租房的形式居住在社区。
二、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社区治理是社区范围内的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机构,依据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社区规范、公约、约定等,通过协商谈判、协调互动、协同行动等对涉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增进社区成员社会福利,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5]
在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的同时,但在近几年随着城市迅速扩张,当前社区居民呈现出数量多、流动性大、从事职业复杂化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等特点。就以绵阳市某社区为例,该社区政府性质的服务机构有街道办和居委会,非政府性质服务机构有物业公司、志愿者服务中心、退休职工活动中心和业主委员会。政府性质的服务机构主要承担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性委托事务,即街道办事处向社区居委会摊派任务,这导致社区委员会的工作过于“行政化”,使社区委员会对政府部门的行政资源有极强的依赖性,一旦政府行政资源供给出现问题,那么基层服务将会出现短缺,这显然与其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背道而驰。[6]非政府性质服务机构主要通过多元社会力量参与志愿活动、公共建设、公益服务及公共文体活动,来增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并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但是,社区居民依赖观念根深蒂固和习惯性“搭便车”行为,使得非政府性质服务机构如同摆设,只要不涉及到居民最直接的利益,一般社区居民是不会参与社区治理过程。同时,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还表现在参与治理的居民不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目前不管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性质的服务机构中,主要由离退休老人、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和物业职员等组成,这很显然参与社区管理的主体具有局限性。
三、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
(一)治理主体:普通居民和治理精英
在目前城市社区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普通居民和治理精英。普通居民自然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没有他们的参与,社区治理将不能体现出基层自治的功能。治理精英是指对社区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包括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党员干部、退休领导干部、民间精英、社会人员等。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讲,广大的普通居民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投票、选举和决定社区重大事务。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就如前面提到的绵阳市H社区,普通居民多达上万人,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职业和学历的不同,这使得他们对公共事务考虑的角度不同,导致他们在社区重大事务决定上的态度不同甚至盲目跟风,另外还有一部分居民在处理公共事务上选择回避。这种结果最终导致普通居民在重大社区事务上难以协商出合理的结果,导致上级领导与普通居民对于这种决策方式失去信心,而选择治理精英代表居民来做决定的方式,这种方式相比之前充分体现了决策的效率。因此,在以后的重大事务上都会让这些治理精英来代表居民做决定。但是,这种方式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另外还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二)治理结构: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社区治理就是社区公共权威机构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所谓社区治理结构就是指作为整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威机构之间形成的关系和制度性安排。学界一般从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来划分治理机构,街道办和居委会属于政府组织,而业主委员会、老年人活动中心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等都属于民间组织。
1、政府组织:人员配置不齐,社区治理乏力
居民委员会按照居民的居住状况和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设立,一般以100~700户居民设立一个居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5~9人组成。[7]但是通过这次走访发现,该居民委员会所管辖的居民已经远远的超过700户,同时该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只有5名,这些工作人员还身兼数职,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2、非政府组织:发展不成熟,职能行使有限的社会职能
在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平时都是关闭状态,工作具有临时性,业主委员会都是由小区业主来担任,但是这些业主多数都有自己的工作,平时都在忙工作,这导致业主委员会如同摆设;老年人活动中心成为棋牌室,志愿者服务中心直接关闭。正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发展不成熟,使得很多机构如同虚设,没有履行服务大众的社会职能。
(三)治理过程:民主监督的缺失
对社区民主监督的渠道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级部门的监督;二是同级权力机构之间的监督;三是社会大众的监督。上级部门通过制定工作指标来对社区工作进行监督与管理;同级监督主要依靠组织内部机制监督权力;社会大众的监督是通过邀请群众代表参与决策、决策和财务公开等形式。但是调研过程中发现,对社区权力监督仍然是上级政府的约束,而其他两种监督方式在实际过程中也只是以“财务公开”和“社区官网”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由于居民治理自治的意识不够和民主观念薄弱等原因,这两种监督方式未能发挥出真正的功能。
四、对于解决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思考
综上所述,影响社区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不够、基层管理人才配置不足、非政府组织有待完善和社区服务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对于当前社区治理困境提出几点思考:
(一)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社区管理机制,提高普通居民参与积极性
通过几天的走访,发现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不高,是因为社区管理过程中的信息不透明和管理机制不完善,打击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就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社区管理机制, 通过创建QQ群、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多种现代数字技术形式,及时将社区的各项事务公布出来,保障居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只有居民真正了解了社区事务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他们才会积极参与社区管理的工作中。
(二)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在社区基层管理工作岗位上有很多职位空缺,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大多是中老年人为主,这导致社区工作效率不高和缺乏创新。社区基层管理岗位之所以难以吸引年轻人,主要是基层管理岗位的薪资待遇较低,工作繁杂。为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基层工作中,首先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基层人才引进机制,为社区管理工作人员提供公务员编制,吸引青年人才投身于基社区治理的工作中;其次要提高基层工作者的薪资待遇;另外还要完善基层工作的工作环境和提供明确的职位升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区管理工作的服务质量。
(三)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财政资助,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工作
目前非政府组织社区服务机构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绝大多数都依赖政府的参与,能真正独立开展活动的非常少。在以后社区服务工作中,政府应继续加大扶持力度创新模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最重要的是财政资助,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从政府得到的资助占非营利组织的35%,在我国的香港地区达到80%到100%,而我国政府对于社区治理的财政资助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因此,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财政资助,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区服务质量。
(四)加强社区治理的民主监督,推动社区民主政治的建设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要做到选举公开、决策公开和财务公开,邀请居民代表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中,加大公开的范围和力度,如可以开通手机短信平台、政府网站平台等确保留居人员和外出人员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定期召开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向居民代表汇报社区相关事宜,允许居民们的质疑和提出建议。
总之,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提高非政府组织服务质量,转变政府的社会管理观念,引进更多基层管理人才,共同参与社区基层治理,提高社区治理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李扬林.略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J].九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3):80-82.
[2]连倩倩,安乾.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及特征分析[J].当代经济,2018(15):8-12.
[3]绵阳市统计局.绵阳统计年鉴[J].方志出版社,2017,(01):17
[4]虹苑路社区居民委员会.虹苑路社区概览[EB/OL] http://www.mydsqw.cn/shome.php/Index/index?alias=hongyuanlushequjuminweiyuanhui,2017–08–16/2019–02–04.
[5]段俊霞,赵宇.我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现状、问题与对策[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9,34(01):130-133.
[6]陈伟东,熊茜.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1):57-64.
[7]王妮丽.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思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01):108-113.
[8]曾奕婧.边界、制度与资源:一个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分析框架——以TJ市H区Y社区为例[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8(06):94-99..
作者简介:郭鹏(1995.01-)男,四川省绵阳市人,硕士研究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方向: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论文作者:郭鹏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8月2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5/7
标签:社区论文; 居民论文; 政府论文; 组织论文; 绵阳市论文; 基层论文; 服务机构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8月24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