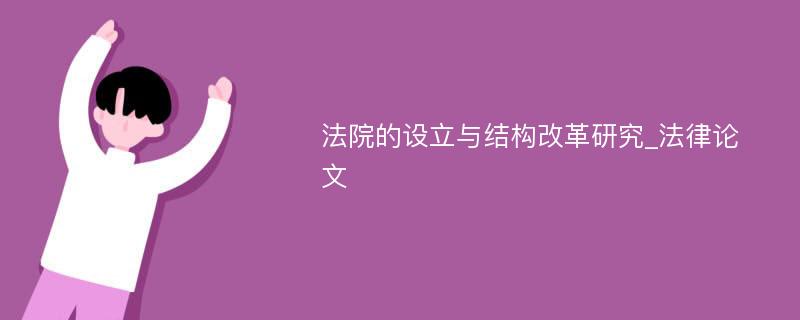
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院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院的设置与结构是法院组织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中最稳定、基础的内容之一,也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结构是制度的支撑,结构的合理性直接关乎法院作用与功能的发挥。因此,结构的设计必须服从、有助于法院功能的发挥。本文介绍了国内学界对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的观点,着重分析了美国法院设置的经验和启示,并对我国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及所涉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最后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建议方案。
一、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的指导思想
西方现行的理想或标准法院包括四个要点:1.独立的法官;2.适用业已存在的法律规范;3.经过对抗的诉讼程序后;4.达至一个“胜者通吃”的裁决。(注:Martin Shapiro:《Court:A Comparative and Political Analysis》,U.of Chicago,1981,P1-29.)但是,如果人们审视所有社会模式的话,就会发现法律程序并不必然或全部是法庭程序,因为我们经常发现折衷而不是两分的解决方法;我们发现,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互相协商而不是通过法庭对抗而达至互相满意的解决方案,也叫“双赢”。传统的截然划分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判决结论,强调的是对过去的说法,而对将来的行为和事件则无法顾及,而且很可能会出现三方(原告、被告、法官)中的两方对抗一方的强制结论,它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维系。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法院的功能和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按照西方的法治原则,法院在原则上只能对诉至法院的案件并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做出裁决。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只能是被动的、不系统的,其裁决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政策导向也必然是零碎的、不系统的,缺少可持续的、及时的反馈与调整。(注:Roger Cotterrell:《The Sociology of Law:An Introduction》,Butterworths 1984.(Chinese Version),P247、277。)在司法独立原则的引领下,西方的法院和法官十分强调作为机构和个人的独立性,这也使得法院组织结构在布局上比较分散、随意,在工作中也体现出各自为政、缺少合作。因此,独立并不总是好的,有时候也会带来惰性和政治交易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影响独立所带来的好处。(注:Guido Calabresi:"The Current,Subtle-and not so Subtle-Rejection of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May,2002,P646.)
法律制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注: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Arts & Licensing 1983.(Chinese Version),P222-295。)“地方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范围和大小都是不确定的。强调法律地方性的同时,也表明了法律多元性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走到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主张中国的法律根本就应该用中国自身的范畴来研究。(注:刘星:《法律是什么?一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80页。)
法院的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因为,过于封闭的、自我防卫式的、特别是精英人物主导的改革,往往会失去公众的支持和认同。过于强调法院的结构、管理、规则制定、财政保障,以及法官选举、教育培训和纪律惩戒,这样的改革给人的感觉是:请你离法院远一点!我们自己知道怎样做才是最好的。必须要改变这种印象。法院的改革要更加外向化和人文化,集中在社会问题上,与民众和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式的法院。(注:Robert Tubin:《Creating the Judicial Branch:the Unfinished Reform》,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1999,P8-10.)法院改革必须要将自己融入到本民族法律文化的核心之中去,这样才会有出路。
笔者的结论是:不同法院组织结构制度并存、多种司法功能在同一个法院组织结构中并存,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补充,不仅是合理性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中国法院组织结构的设计原则正如中国的文化一样,不能过于刚性,要有相当的包容性,尤其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层法院这一级。便利快捷、平纷止争是基层法院最主要的司法职能,同时它也在代表国家行使国家的审判权,因此,在解决问题与符合法律这两者之间必须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二、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分析与建议
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的最初设想是源于1995年法院组织法修改时已经在运行的“六类法院”(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和高新技术产业区法院以及行政新区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林区法院、垦区法院、铁路法院、海事法院等)的定性和法律地位,它涉及宪法、法院组织法的统一、协调,也是法院实际面临的具体问题。随后,针对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与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似乎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举措。在学术界,先后有不少颇有见地的文章论及该项改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下面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司法系统。(注:曹思源:“为现代包公松绑—法院管辖制度不改不行”,载《南方周末》1997年1月19日;蔡定剑:《历史与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388-397页。)根据他们的观点,现行的法院制度可以简括地说,山东人与山西人打官司,要么由山东的法院审理,要么由山西的法院审理。而无论哪一方法院审理,都难免有厚此薄彼之嫌。地方法院的人财物大权全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法官胳膊肘向外拐的难度会很大。所以应当将目前民事案件由诉讼一方当事人所在地法院受理改为由诉讼各方当事人共同所在地法院受理。当事人如分属不同的县,则改由这些当事人共同所在地的法院受理,依此类推,跨省的则由最高法院受理。由于这势必极大地增加最高法院的工作量,因而有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区域分院或分院。这样一来,我国就形成了两套法院体系:一套是地方法院体系,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省、地(市)县三级法院不变,专管省市区范围内的案件;一套是中央法院体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分院组成,管辖跨省市区一审案件以及某些上诉案件。
地方保护主义反映在司法上,就像是足球场上的“主客场”。(注:盛晟:“官司的‘主客场’”,载《南方周末》1997年8月15日。)“主场”不败的神话时有耳闻,可见其威力。球场上的主客场是比较公平的,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主场比赛,但打官司却不同。虽然打官司也有两审,但这二审实际上是纵向的关系,第二审是上诉审,是对一审进行复审,而不是两地各审一次。如果两审都控制在自己的“主场”,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在也会在司法上附体。在我国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权是一种横向的权力从属关系。地方政府对法院人财物大权的掌控,使得地方法院形成对其隶属和依附的关系。法官的吃、住、行不是社会化的,而是行政化的。因此,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和统一,就要实行司法辖区与行政辖区分开,中央法院系统与地方法院系统分开。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建立单一的垂直的司法体制。(注:张愍、蒋惠岭:《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5页。)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两级司法行政权归属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余两级(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归中央。与此相适应,法官的任命分属于省级人大和全国人大。其初衷是强化全国法制的统一,避免由于现行体制条件下司法机关过于分散的行政隶属关系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司法机关远离同级政府和人大而获得独立,强化司法的政治监督功能。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获得提升,更加符合宪法的规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建立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即设立大区分院,专门负责审理跨省的上诉案。(注:《人民法院组织法》1995年修改意见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章武生、吴泽勇在2000年《中国法学》第2期上转述了上述观点,见其“司法独立与法院组织机构的调整”。)最高法院在全国设若干个分院,在其辖区代行最高法院职权,受理部分高级法院的上诉案件。全国划分十个左右的大司法区,每个大司法区设一个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在本辖区内的较大城市设若干分院;高级法院及其分院作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院行使职权。高级法院辖区(大司法区)内划分小司法区,设中级法院;中级法院视需要设若干派出机构;中级法院及其派出机构作为一般案件的初审法院。将基层法院改为简易法院(但附设普通法庭),主要受理简易、小额案件;大幅削减城市基层法院的数量,农村基层法院基本上仍以县为单位;取消城市人民法庭,合并整顿农村的人民法庭。
第四种观点认为,应当建立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注:夏峰:“关于建立巡回法院的思考”,《中国律师》,1998年第7期。)专门受理跨省之间标的额较大的民事纠纷案件,或者有权管辖涉及管辖争议的案件。巡回法院有权享有司法审查权,监督地方法院的工作,对发现有重大疑问的案件可要求原审法院重审。
第五种观点认为,应当打破现有的按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的做法,跨省区设置各级法院。(注:沈德咏:“司法体制改革略论”,《法学》,1996年第8期。)在全国省区市以下划定独立司法区,改变现在的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完全重合的局面。在司法区重新设置相应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以摆脱现在的地方法院对地方行政客观上存在的依附关系,从而有效地消除影响司法公正的种种弊端。法官任免实行上管一级,人员、经费和管理实行计划单列。
第六种观点认为,将若干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为一个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立一个上诉法院,其级别相当于高级人民法院。如在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设立北京上诉法院,在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设立广州上诉法院,等等。当事人对中级法院做出的裁决不服,既可以向所在地的高级法院上诉,也可以向所在司法区的上诉法院上诉。高级人民法院和上诉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这样可以避免过多设置分院所带来的增加审级的弊端。同时,在较大的地(区)市、州可以设立一个中级人民法院,较小的地方则可以共设一个中级法院。同理适用于基层法院。原则上撤销乡镇人民法庭,边远地区除外。(注:谭世贵:《中国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06-107页。)
第七种观点认为,在保持现有法院体制的基础上,由最高人民法院往各省、市高级法院派法官组成巡回法庭,负责审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案件,以及有关死刑复核案件。(注: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设立巡回法庭不是要形成一级法院,因为增加一级法院将改变目前的四级两审制,如果案件在大区或巡回法院作为一审审理后,当事人就不可能上诉。因此,由最高法院往各地派出巡回法官,与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共同组成巡回法庭,它们仍然是各省、市、自治区的法庭,在案件审理后,当事人仍然可以上诉至最高法院。巡回法官虽属于最高法院委派的法官,但一旦确立为巡回法官后,就不应在最高法院审理案件,以防止案件上诉后在二审期间审判活动受不正当影响。同理,各省、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也应向中级法院派出巡回法官,组成巡回法庭,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实行法官定期交流。
三、美国的经验和启示
(一)联邦法院的改革
巡回区上诉法院的建立。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宪法只设立了联邦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除了坐堂问案外,还要外出办案。联邦巡回法院最初就是最高法院法官巡回办案的地点。1789年设立了三个巡回法院,作为联邦初审法院。与此同时,还在每个巡回区设立了两个以上的地区法院,当时的每个州都是一个单独的联邦地区,每个地区设一个联邦地区法院,也作为初审法院,但其管辖权比巡回法院要小许多。在有些情况下,不服地区法院裁决的可以上诉到巡回法院。这样,联邦法院就有了两个初审法院即地区法院和巡回法院和两个上诉法院:巡回法院和最高法院。(注:Robert Carp & Ronard Stidham:《Judicial Process in America》,CQ Press 2001,P23-53.)虽是联邦法院,但地区法院的辖区都不超出州的边界,这也是联邦向州的妥协,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是,巡回法院却是跨州的,打破了州的边界,在巡回区内法定的地点办公,法官来自巡回法院所在地的地区法院法官和最高法院拟巡回该区的法官。随着最高法院工作量增多,最高法院的法官巡回办案已经不现实了,到后来,地区法官就成为了唯一的联邦初审法官,而此间在最高法院与初审法院之间并没有任何中间上诉法院。1891年,国会免除了最高法院法官巡回审判的职责,同时建立了单独的上诉巡回法院。每个巡回区都有一个上诉巡回法院,并有自己的法官,地区法院则成为了主要的初审法院。1948年,上诉巡回法院更名为巡回区上诉法院,由巡回法官组成。(注:Russell Wheeler:《Origins of the Elements of Federal Court Governance》,Federal Judicial Center 1992,P10.)
建立全国上诉法院的提案。20世纪70年代是诉讼爆炸的年代,蜂拥而至的诉讼使得最高法院整日应接不暇、疲惫不堪。因此,在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之间设立一个全国上诉法院的议案得到了热烈的反应。该法院由7名来自全国巡回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组成,受理所有提到最高法院的复审请求,同时接受最高法院委托的案件,以及联邦上诉法院、索赔法院、关税和专利上诉法院(现在的国家贸易法院)移送的案件。对是否需要对这些案件进行复审有终审裁决权。当然,设立该法院除了合理性和有效性的问题外,还涉及是否违宪和有损联邦最高法院的崇高地位等一系列问题。反对者认为设立该法院的构想是在并未对改进现有制度做充分努力的前提下做出的,也没有从各方面估算成立新机构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在削弱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权力及威信方面将是重大的;同时,在许多案件中还将造成法院的第四个层次,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额外的花费和延误,以及在管辖权上潜在的冲突。建立新法院要付出巨额的开办费和经常的财政费用,这只是将矛盾转移至一个新设的上位法院。(注:F.J.Klein:《Federal & States Court System-A Guide》,FJC 1976,(Chinese Version),P199-204.)
从历史的角度看,法院在美国的发展只是一个松散网络的铺设过程,并没有按一个逻辑的、必然的方向发展。期间具有明显的政治烙印,在联邦与州双轨制以及分权制衡的框架下,形成了很强的集中化和地方化特征。美国法院组织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增加地理单元内法院和法官数量来实现的。以地域为基础一直是法院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在划分联邦地区法院时,充分尊重了州的边界走向(联邦地区法院没有跨州设置的),但在上诉法院这一级却打破了州界的约束,形成了跨州的巡回区模式。从历史上看,在基层法院这一级(不管是联邦还是州),地方的“掌控”已成为法院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既是对地方的关注和尊重,也是保证基层法院正常有效地运转的前提。但是,再往上一层,联邦的集中制特点就十分明显了,在州的上面设大巡回区,实行跨州管辖,确保联邦法律在全国的贯通。
以地域为基础来设置法院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的选择。一个联邦法院可以对整个国家内的某一特定类型的所有案件都拥有管辖权,而不是只对某个地区内的不论什么类型的所有案件都享有管辖权。而且,某些联邦制定法(比如反托拉斯法)涉及某种很高程度上的技术难度和分析困难,这会使得某些按地域设立的法院在审理案件上感到困难。(注:Richard Posner:《The Federal Courts:Challenge and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5-8.)因此,加强联邦法院的管辖权就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若允许地方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的话,不同法院间的管辖权冲突也会给案件的审理带来影响。另外,随着教育、通讯和交通的越来越便利,狭隘的地方观念逐步弱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逐步趋于标准化、全球化,审判成本在不断地降低,这一切使得以前的诉讼困难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些因素注定了专门法院的兴起和逐步盛行。
(二)州法院的改革
罗斯科·庞德在一个世纪前就看出了州法院组织结构的混乱,指出州法院在设置上层级复杂、重叠所造成的低效和繁复。对当事人而言,选错法院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诉讼请求被驳回往往是基于技术理由;对于法官而言,法院的不同会造成工作量的明显不同。(注:Pound:《The Causes of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Address before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t.Paul Minn.August 29,1906,in 40 American L Rev,729(1906),reprinted in 8 Baylor L Rev.1(1956).)在司法独立的理念下,法院和法官,甚至是法院的辅助机构和辅助人员都在强调独立性,所有这些都是缺少合作的充足理由,那么效率将何来?浪费和拖延将无可避免。因此,统一与合并法院,使所有的同级法官都汇聚在一个法院之中,使法院和法官的管理,包括工作和任务的分配,变得容易和有效,避免过多的重审和资源浪费。(注:Fannie J.Klein:"A Brief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deral-State Court System",《The Improv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ABA 1981,P8-10.)美国律师协会早在30年前就在其“法院组织标准”中推荐建立单一的初审法院体系。(注:Standards Relating to Court Organization(1990),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今天,全球化和标准化方兴未艾,法院组织结构的“简洁与统一”似乎也可以成为当今世界司法改革的一个主旋律了(注:Ralph Kleps:"Reorganiza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Court Structure",《The Improv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6th Edition,1981 ABA,P17-35.)。但实际上,初审法院的统一与合并工作在美国却还只是一种改革的建议模式,30年间,仅有一、两个州的法院结构改革是以其为蓝本进行的。
庞德等人提出的司法机构改革设想一直没有得到热烈的响应,虽然此间也有不少州法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由于结构改革牵涉的问题多、领域广,且改革难度大,所以更多的法院是做一些相关的技术性工作,尤其是行政管理改革,以解决法院结构混乱所带来的问题。虽然在形式上还没有做到结构的统一,但大部分法院的实际运作已经简化和规范化了,很多法院除了名称没改,其他基本上都该了。(注:David Rottman & William Hewitt:《Trial Cour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A Contemporary Reappraisal》,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1998,P81.)90多年的时间足以发生不少观念上的转变:法院不应再是一个由一些独立的法官和管理人员组成的松散集合体,而应成为一个能够制定并执行统一司法政策的、协调连贯的有机体;改革者在制定方案时必须要考虑司法活动的所有方面,而不能将裁判活动从管理事务中割裂开来;法院管理职责一定要与法院的最终目标——做出公正、公平的裁决结合起来,仅仅靠结构改革来实现法院的改革目标是不够的。(注:Thomas Henderson:《Structuring Justice:The Implication of Court Unification Reforms》,U.S.Department 1984,P83-95.)美国州法院的结构改革进程向我们展示了一场静悄悄的百年革命史。但是,由于法院的结构和形式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统一与合并仍然是法院改革的一项基本议题。但在实质上,却已经慢慢被转换成另一个议题:法院结构改革是否以及在哪些领域,能够提高法院工作水平或促进法院职能的发挥?
美国州法院近一个世纪的结构改革历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对于那些对改革没有兴趣的法院首脑来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对于那些致力于机构改革的司法领袖来说,改革是美好的。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美国州法院的任何改革都是自觉自愿、各自为政的。是否改革、如何改革取决于各州的实际情况,在很多情况下是取决于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个人的意愿和能力。因为,在各州的司法工作都排得很满,而且比较稳定的背景下,推行一个触及地方利益和众多人员的改革方案,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受欢迎的,阻力可能来自各个方面:涉及管理和财政的改革,需要寻求议会的支持;涉及法院统一与合并的改革,需要得到各级法院法官的普遍支持。而且,美国司法机构首席大法官的权力远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大。在独立意识极强的司法机构中,每个法官都是自己的主人,首席法官对他们也奈何不得,“(首席大法官)你可以控制法院,但无法控制你的同事”。(注:Carl Baar:《Trial Court Consolidaton:Michigan in Context》,in Judicature,Number 3,2001,P137.)所以,很多时候首席法官都知难而退,不愿意趟这潭浑水,自己给自己找事。
(三)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
一般来讲,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三点:专门法院的设置是按照特定的组织系统或基于特定的案件;专门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就案件的性质而言,具有专门性;专门法院法官的产生和任免不像普通法院那样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法律上对专门法院的规定并不多,也不明确,在我国,一般都认为,专门法院主要是指军事和海事法院,铁路和林业法院则存在较大争议。从世界范围看,专门法院的概念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许多国外所称的专门法院在我们看来很多都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法院,比如家庭法院、青少年法院等,与其说是专门,还不如说是特殊。实际上,“专门”一词译自英文的“Specialized”,而将其译成“特殊”也许更合适。
一般认为,在一些非传统的法律领域适宜设立专门法院,以处理一些传统法院不受理,或较难处理的案件。在这些领域,专门法院具有明显的政策和技术含量,作用和功能与普通法院不同。(注:Lawrence Baum:《American Courts:Process and Policy》,Fifth edition,Houghton Mifflin,P51-52.)专门法院的建立旨在促进某类案件审理的专业化和集中化,提高办案效率,避免一些普通法院诉讼固疾,如成本高和拖延,同时,在案件管辖范围上明确与普通法院的区别。
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中,专门法院虽不是主流,但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除了12个联邦普通上诉法院外,还有一个联邦巡回法院,即专门上诉法院。波斯纳认为,这已经形成了类似大陆法国家那样将最高法院一分为二的格局,即最高法院被分成宪法法院和管辖其余所有问题的普通最高法院。这甚至意味着从普通法院体系为主的司法体制转向一个专门与普通并重的法院组织结构体系的转变。(注:Richard Posner:《The Federal Courts:Challenge and Refor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265-270.)在有专门法院的国家,一项重要而基本的工作就是要明确专门法院或法庭的管辖和收案范围,以及与普通法院的关系。(注:James Crawford:《Australian Courts of Law》,Oxford U.Press,1988,P251-275.)
笔者认为,在我国宪法框架内,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内容,可以考虑组建一个单独的、完全由专门法院组成的法院组织结构体系,在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分院的指导监督之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与专门法院相结合的法院组织结构体系。
四、我国法院设置与结构问题分析
学者们的解决方案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却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主要目标没有对准,或主要的问题没有找到。结构是功能的表现;结构是制度的反映。中国法院的设置与结构改革不能仅从结构重组如手,结构调整不是分蛋糕,重新切几刀就行了,不能简单地头痛医头。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地方保护主义和法院人财物的管理权限,更有从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法院设立以及人员任免等方面问题。诸多的因素从不同的领域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并发挥作用,以至于法院的设置只是这些问题汇聚后的集中表现罢了。
(一)行政区划与法院结构设置
我国司法辖区与行政区划基本是一致的,这种设置的重叠就形成了学者们所说的司法地方化。这是一个泛泛的命题,实际上,不独有“行政区司法”一说,而且还有“行政区经济”的说法。但是从理论上讲,重叠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司法的地方化,还要看其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以及其自身的独立性程度。
依托于行政区划的司法辖区,其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行政区划的合理性。所以,正在酝酿中的我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如果进行的好,那么法院设置和结构中存在的相当一部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笔者认为,现有的省域划分不尽合理:省区范围偏大,导致行政管理层次繁多,容易助长官僚主义(比如省和县之间增加的中间层次——地级);省级政区大小过于悬殊,层次混乱,不利于统一行政管理;省级行政区域边界犬牙交错,破坏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性,政区间纠纷不断,使区域经济一体化难以实现。
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地方仍保留地区的行政建制,并相应地设立了地区行政公署作为行政机关。地区行政公署不是一级政府,而是省的派出机构,代表省人民政府管理该地区的行政事务。派出机关与同级行政机关的主要区别在于,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府,不设置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注:夏海:《中国政府构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根据1995年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可以在地区设立工作机构。其性质为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派出机构,统称“工作委员会”或联络处,(注: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第505页。)目前,它还只是一个承接上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工作机构,不是权力机构。地区一级的“一署两院”中“两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也是省检察院的分院,而唯有人民法院被冠以中级人民法院的“头衔”。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区时代”,现在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当时被称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分院或分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除了传统的地域型政区外,新的城市型政区发展迅速。“地改市”、“市管县”逐渐成为行政改制方向。我国宪法规定,行政区划分为省、县、乡三级,(注:宪法第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一)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二)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三)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并没有“市管县”一说。县和市是两个有各自辖区的平行行政区域主体。我们现在进行的“市管县”体制改革严格讲,并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注:刘君德等:《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第446-453页。)由于与行政区划间的这种“连带关系”,那些在行政区划改革试点地区设立的法院,都存在合法性不确定的问题。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院结构改革
如何设立法院?什么机关可以设立法院?美国宪法则明确规定,国会可以随时建立除最高法院外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是唯一按照宪法的明确规定而设立的联邦法院。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故意把法院体系搞得含混不清,因为他们就是否需要设立联邦下级法院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注:美国宪法第3条第1款。)我国宪法只规定了设三种法院,以及法律另行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注:第12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而作为最应明确规定法院组织内涵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却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只是将法院的种类细化,(注: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下列人民法院行使:(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三)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中级、高级人民法院。)甚至将专门法院的组织和职权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注:第29条: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而且,从1984年11月1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地区城市设立法院的决定》,可以看出,人大常委会已经行使了这一职权。虽然宪法中没有规定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人民法院的设立,但在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似乎表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其职权范围从专门法院扩大到普通法院的设置。司法虽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是上下级法院之间并不像政府和检察院的上下级之间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注:宪法第127条: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所以,在司法管理上(包括法院的设置),最高法院的职权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法院设置上的模糊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对人大常委会行使法院创设权并没有太多的异议(因为可以将其纳入人大行使其他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内)。主要是如何理顺其中所涉法律的协调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人民法院。(注:第3条(第3款):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院的设立密切相关,即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来源是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出现真空的情况。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理论原则建立的,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他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审议本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并选举任命这些国家机关的领导人。这些国家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与人民代表大会构成从属关系。(注:第62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第63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第128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而在当前的制度下,一些地区“一府两院”中的法院(普通法院),以及专门法院和上述六类法院,尚没有相应的权力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因此,其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如何与人大制度衔接?使审判权的来源合法化,便成了法院设置与结构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宪法第124条最后一款规定,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而本应进行规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却回避了其中的专门法院这部分内容。法院组织法第29条规定,专门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实际上,没有一个系统的另行规定,只有两个针对性较强的具体决定,一个是1984年11月1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港口地区城市设立法院的决定》,(注:海事法院院长由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海事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海事法院院长提请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另一个(不典型)是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作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立若干中级人民法院;在生产建设兵团农牧团场比较集中的垦区设立基层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任免。)
根据宪法第124条的规定,除最高人民法院外,人民法院的设置,一是根据行政区划设置地方各级(普通)人民法院;二是依照案件性质设置的专门人民法院。我们目前所说的这六类法院既很难归入地方普通法院,又很难归入专门法院(1984年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沿海城市设立法院的决定也只是明确了这些法院人员的任免问题,并未对这些法院本身的性质问题进行定性,换句话说,海事法院是否属于专门法院法律并未明确)。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把这六类法院纳入宪法第124条中的任何一款,则这些法院的存在就会有违宪之嫌;但是,不管是纳入地方法院,还是专门法院又都不太准确。因为,由于这些法院的人财物大多是来自部门或行业,而诉讼的当事人往往是为该法院提供支持的部门行业一方,在诉讼三方的关系中,两方已经在开庭前就坐在了一起,这样的法院至少无法在形式上称为是公正的,所以,这些法院如不在人财物上脱钩,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部门及行业烙印。
我国的管理体制有两种:部门管理与地方管理。地方各级政府实行的是“块块”管理;中央部委或行业则是“条条”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条块管理”问题。(注:林尚立:“集权与分权:党、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见陈明明主编《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85-186页。)表现在法院上,就是海事、铁路、林区法院在“条条”管理体制下,虽是中级法院规模,其管辖范围却能纵贯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像武汉海事法院,以长江为界,横贯六个省市),彻底打破了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块块”界限,形成了只能由中央(部委)直管的格局。按照宪法的规定,地方各级法院的人员选举和任免是按“本级”原则(地区、市管县和直辖市中院除外),(注:宪法第101条(第2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而海事法院则是按法院“所在地’原则。(注:海事法院院长由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海事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海事法院院长提请所在地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问题是有的海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与其所在地人大机关的权力范围相同,如青岛、大连;而有的则与所在地人大机关的权力范围不相同,只是在行政级别上与所在地人大相同,如武汉、天津、广州海事法院(都是跨省市管辖)。既然这些法院不归属于任何地方人大,那么就不存在一个相应的本级人大,而由法院所在地的人大任免法官显然既不合情理,又不符合宪法第101条的精神,最终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执行流于形式。
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词汇上的区别。宪法中的“本级”强调的是相同或同一辖区内的同级,是一种实质上的同等;而“同级”则强调的是行政级别上的相同,至于是否在同一个辖区中则不是重点,是一种形式上的同等。二者在名称和含义上都是不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4年关于在沿海城市设立法院的决定中,将“本级”的概念换成了“同级”。这样的规定就使得法院所在地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其管辖范围不同于法院的辖区,大多数情况是小于司法辖区)在行使权力时有可能越权,或侵犯其他地区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行使。由于专门法院的设置并不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的,所以其人员的任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规避宪法的合法操作。
另外,在实践中还会造成任免上的差等格局。“所在地”是个新概念,涵盖面十分广。用“所在地”,而不用“本级”,表明“行政级别”在这里变得不重要了。换句话说,法院所在地归属于哪一级,就由该级的人大常委会任免。如此一来,同是中级法院的海事法院院长,就可以由不同级别的人大常委会来任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宪法第3条应是法院设置的基本原则,即人民法院要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宪法第101条则是一个具体原则,即本级人大产生本级法院。由于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关于专门法院人员的任免问题并不明确,所以只能根据宪法第3条这一基本原则来推导。首先可以明确,专门法院要由权力机关(人大)来产生;其次,宪法第101条的“本级”原则是否适用于专门法院并不明确;再次,在基本原则的框架下,如果专门法院的特殊性存在,那么其人员的任免可以不拘泥于“本级”原则。第四,从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关于在沿海城市设立法院的决定和1998年关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决定这两个具体立法实践可以推出,在法院设置和人员任免方面已经突破了宪法和法院组织法中的有关规定;第五,从“两个决定”的运用方式看,我国对专门法院的组织和职权似乎并不准备做一个专门、系统的规定,而是在有需要时,通过一项专门的决定解决问题。
专门法院的设置和有关人员的产生无论在宪法上,还是在法院组织法上,都还是空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宪法中法院设置和人员产生这部分内容的重要补充或者说是一种扩张解释。当然,这对这两个决定是否与宪法协调一致也不是没有争议的。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规避法律的行为与制度创新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关键看你愿意用什么态度去理解。如果专门法院的院长可以通过任免而不必向地方普通法院那样选举产生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说这是一项制度创新呢!
五、结论:我国法院设置改革建议方案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习惯于将法院与银行、金融、海关、税收、铁道、工商这些部门进行比较,认为它们之间有很多共性,这些部门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它们必须实行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法院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它的职能是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和法制在全国的统一,因此,审判权的行使应当集中而不是分散。(注:王怀安:“关于法院体制改革初探”,见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第444页。)但事情的发展却远非如此,我们经常引介的银行业改革进程(注:“金融办成破竹之势,暗含银监会未来雏形”,见《经济观察报》2003年1月13日(第1版)。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跨省区的九大分行,形成了央行与证监会、保监会分业监管的体制。其初衷极为明确:保证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但是,这种方案有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大区行在实际监管中面临着银行监管不力,体系内较乱等一些尴尬。事权、财权、人权分离,管理绩效较低。虽然地方政府对货币的政策干预上明显减弱,但监管工作缺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分行所在地以外的省区的监管成本上升等等。原本希望通过大区行解决银行就地监管的问题,绕开地方干预的障碍,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不与政府打交道将难上加难,因而出现了地方监管乏力而中央监管有鞭长莫及的苦恼。由于金融市场是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是必需的;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状况各异,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工作的确又需要政府的参与,尤其是考虑到未来地方金融发展的空间,因此,中央银行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愈加扑朔迷离。按照十六大的既定原则,国家与地方在国有资产方面是分级所有,分级管理,那么银行是不是也在改革范围之内?按道理说,地方性、社区性的金融机构将来应当放到地方去管,没有必要统统由中央来管。多元化的地方性金融市场体系需要地方综合的管理机构。中央和地方的监管权划分很难。金融机构交叉业务越来越多,地方的金融办一般是银行、保险、证券等管理混为一体,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却反过来给了我们上了一课(注:社评:“银行改革:依行政区分布拆分”,见《经济观察报》2003年1月17日。目前中国银行改革方案中又出现了依行政区分布拆分的建议。)。鉴此,我们在设计法院的组织结构时,必须处理好运行与管理上的条块分割的问题,尽量做到中央与地方在利益与责任上的平衡。
简言之,关于中国法院组织结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可以概括为“实现四化”:一,基层法院“地方化”;二,中高级法院“交叉化”;三,最高法院“集中化”;四,专门法院“职业化”。
(一)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区分院”
以美国13个具有跨州司法管辖权的联邦上诉法院为参考,组建我国跨行政区划、有单独司法辖区的若干个最高法院司法区分院,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仅仅涉及诸如法院辖区的划分等在法院重组方面的技术问题,而且还涉及行政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同时,更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其重大意义不言自明。如果跨行政区划的最高法院分院能建立的话,其具体设想包括:
管辖区域:在50年代六大行政区的基础上,按地理区域设置六至八个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区分院,以及一个按专业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分院。司法区分院不一定按目前的行政区划设置,可以重新拆分、重组。
受案范围:司法区分院受理跨省重大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的上诉、以及死刑复核案件;专门分院受理海事、商事、反倾销、知识产权等专门上诉案件。
法官来源:法官从最高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中抽调补充,分院法官有一定的任期(一般为期四年),人员定期流动转换,完成任职后,可以回原法院继续工作,或易地任职,继续在其它分院工作。最高法院副院长兼任分院院长。
法院院址:在司法区的经济政治中心省份建立一个新院,或者租用专门的办公用房,但不能租用当地法院的办公用房,以避免当地政府的干扰。美国联邦法院也是租房办公,但不与所在州的法院同在一个办公楼办公。
(二)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分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
如果上面的方案过于宏大以至于短期内无法实施的话,可以考虑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分院或巡回法庭。作为最高法院巡回分院,具体设想包括:
管辖区域:全国只设一个,为非常设机构(也可以是一个常设机构)。
受案范围:受理跨省重大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上诉,及死刑复核案件。
法官来源:法官来自全国各高院(每个省出两名法官,民事、经济各一人),为避免产生新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法官们不按大区分片管理,而是随机地被分配案件。最高法院副院长兼任分院院长。
法院院址:没有专门的院址,法官们分别在他们各自所在法院工作,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解决审判合议庭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意见交流。只需在全国设几个办公点受理和分配案件。
作为振荡最小的改革方案,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是新设的与行政庭、民庭、刑庭等业务庭室并列的最高法院审判法庭。该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外出巡回办案,也可以在最高法院受理案件,其管辖范围与上面最高法院巡回分院相同。除部分法官来自最高法院外,其他法官均来自地方高级法院的借调法官,工作期限一般为4年。
(三)设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分院”
我国目前有关专门法院的法律规定十分不完备,作为司法审判重要组成部分的专门法院长期以来未受到相应的重视,这不仅反映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未对专门法院作出明确规定上,而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针对专门法院的性质、设置、组织原则、人员产生、管辖,以及与普通法院、部委和地方的关系等方面内容的研究都十分有限;于法无据、规定之间相互矛盾、甚至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时有发生。专门法院这种状态,也造成了其发展的严重滞后。从整个法院组织结构体系看,一方面可以考虑制定一部专门法院组织法,另一方面,应着手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分院,作为所有专门法院的终审法院,既有利于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又有利于保障公正执法、促进审判质量提高。
最后需要谈及的是关于“分院”或“巡回法庭”提法的法律依据问题。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并没有巡回法庭的提法,只有在基层法院设立人民法庭的规定。法庭似乎是一个更灵活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在美国的法院设置中也是如此。从美国关于切分第九巡回区法院的建议中也可以看出,与其创建新的法院不如设立新的法庭,以解决洲际间的冲突问题。由于设立法庭不像设置法院那样涉及体制的变革、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甚至可以说是法院自己内部的事情,因此,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相应的法庭,包括派出法庭或巡回法庭,可以说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
关于“分院”的提法,在法院组织法上更是没有体现。因此“分院”一词在四级法院中应属哪一级不明确,职责、权利都不明确;另外,“分院”一词的用法在司法实践中也不统一,比如在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院”就是低一个级别的机构,而不是我们所规定的,是最高法院、高级法院的组成部分或派出机构,其判决和裁定就是高院的判决和裁定。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兵团设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决定》在这方面是一个突破,可以说为今后设立法院分院,包括最高法院分院,提供了法律依据。
设立分院是为了理顺整个法院组织结构,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体制性问题,仅从法院组织结构上进行改革是不能根本解决的,而应从地方、党政的合作、以及体制改革上彻底解决。同时,设立分院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提高了审级,使跨省、自治区的一审案件没有了二审,不符合我国二审终审制原则。另外,巡回法院的产生也不是没有问题,至少对谁负责不好解决。相比之下,巡回法庭可能更简单一些。
从效果上看,设衙门与派钦差大臣是不同的。
总之,上述三种建议方案的出发点是要重新定位并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的作用与功能。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责并不是要通过特定案件的审理确保实现正义。它的职责是监督并指导全国法院系统的协调运行,从战略上进行干预,使司法维护正义、实现公正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所要做的是对法院如何才能最有效的利用其不是很丰富的审判资源履行其基本职责,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指导。因此,在建议方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宏观指导和管理作用得到了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