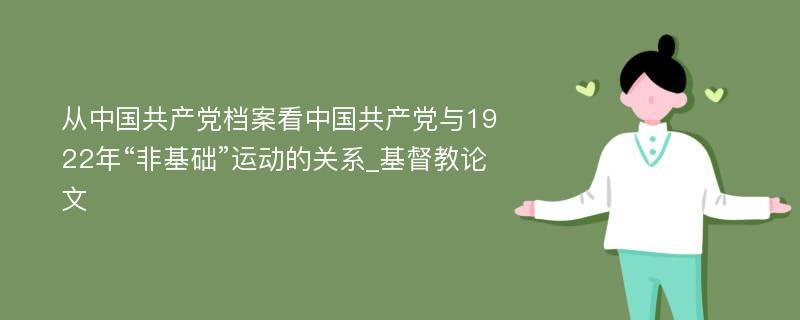
联共(布)档案所见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见论文,中共论文,关系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2年3月初,中国的青年学生在反帝争民主的“五·四”运动余威中,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全国性非基督教运动(以下简称“非基”运动)。运动之初,纵然“许多人认为这场运动非常荒谬、太过原始、太不爱国亦不切实际,因此毋庸关注良多”①,但是诸多人士仍然对运动中出现的“过激”因素产生了恐惧。例如,1922年4月2日发表的非宗教大同盟表明其立场的“东电”就强调:“有意挑拨的话,又说我们非宗教运动的人,好像是有些过激党,这也是动人片时的疑想。这又大错了。我们要很诚恳的对他们说道,我们的非宗教,就只为以科学胜宗教,毫无别的作用,讲社会问题的,是另一回事,与这同盟无干。”②再如,1922年5位反对“非基”运动的北大教授之一的钱玄同在其4月8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列宁”一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忧,他说:“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直觉害怕,因为这……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栗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所能治,非请神禹不可的了。”③而张钦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积极从事攻击基督教及其事业的团体,表面上自然是‘非宗教大同盟’,但在它背后,自然有许多团体,最显著者有三:其一为共产党,其二为国民党,其三为国家主义团体”④。
这样,无论是“非基”运动的参与方否认“过激党”参与运动还是钱玄同等反对“非基”运动的另一方面坚持“中国列宁”参与了运动,都引出了一段公案:成立未及一年的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参与、甚至组织领导了1922年这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
关于中共是否参与领导1922年的“非基”运动,学术界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究,半个多世纪来已经就这个问题形成三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新生的中共无论是组织能力、组织机构,还是组织力量都没有达致领导组织“非基”运动的地步,因此,只能说中共参与了“非基”运动,而不能说中共组织、领导了这场运动。例如,瓦格(Paul A.Varg)在1958年指出:1922年“非基”开始时,民族主义的反基督教改革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更为广泛的支持。共产党加入了这场改革运动,为之提供了新的口号⑤。1971年,研究中国教会史和“非基”运动最为著名的美国学者鲁珍晞(Jessie G.Lutz)撰文指出:“很明显,在1922年的“非基”中,一些与共产主义有密切联系的组织和人士起了突出的作用。是否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蓄意发动这场运动以扩大初生的党的影响,这仍是一个疑问。”⑥在1988年的专著中,她指出:“由于非基督教运动从未发展起提供其分支机构的纪律或策略,因此,该运动缺乏一个载体性运动以提供持续和组织。……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尚未准备提供指导和组织。”⑦1989年,四川大学赵清递交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中指出:“从现有材料看,参加发起的有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邓中夏等;国民党人蔡元培、汪精卫等;但认为是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组织领导的都证据不足。”⑧1994年,杨天宏指出,“政党的作用早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在陈述1922年的运动时,却不能夸大了政党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难以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⑨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场反基督教运动是由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但是经过政党的推动才发展壮大。例如,日本学者山本达郎和山本澄子夫妇在谈到中共与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关系时,认为“1920年代初期共产党之运动尚无力量可言时,其在反基督教运动中扮演着被忽视的角色,特别是在早期。然而事实上,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中共是否居于领导地位,他们认为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是有组织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直接领导的运动,再由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党派加以助长。”⑩这种观点的核心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共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虽然没有居于领导组织地位,但是起了“推动”这样一种重要角色。台湾学者叶仁昌亦在其博士论文《五四以后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一书中认为:1922年“这一波的反教风暴,几乎是在学生与共产党结合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1922-1923年期间,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许多群众运动,如‘民国裁军运动大联盟’、‘女权运动大同盟’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过是其中之一类”。“此次的反教,固然共产党扮演重要的角色,却仍有许多与政党毫无牵涉的参与者。……总括来说,共产党的发动参与固为事实,然而整个发展与回应又非共产党可涵盖。”(11)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共参与领导、组织了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例如,留美华人叶嘉炽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我将特别指出学生与两个革命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指明这两个政党在这场反基督教运动扮演的重要角色。”具体而言,“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在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的发起时明显扮演了领导角色。”(12)再如,1993年,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撰文指出,1922年和1925年的两次反基督教运动“都有遵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共产党人参加和领导。”(13)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也认为:“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发起和组织了这场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先驱》半月刊进行宣传,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教会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的罪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配合革命运动的发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
综合上述有关中共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关系的三种主要观点,即“参与说、推动说和领导说”,其共同点是学者们都认为中共参与了1922年的反基督教运动。然而,即使中共参与1922年“非基”运动为目前学术界一个公认得结论,学者们所能依据的证据也不多,所依赖的材料最为重要的有三份,即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提及的“1922年3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15)这一条信息;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于1922年3月份刊发的第4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特刊以及叶嘉炽先生首先引用的刊登于《中国画刊评论》(China Illustrated Review)上的一则材料,即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查抄俄国驻华大使馆所获俄方文件《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报告》中明确记载:“(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并领导进行的。”(16)
这三份材料虽然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共参与了1922年的“非基”运动,但是对于中共参与程度的论证显然不足,这也是上述三种主要观点分歧之所在,也因此造成一些学者对中共参与领导“非基”运动的怀疑。例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薛晓建根据1922年前后团组织的组织力量等情况从逻辑上推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未发起和领导(第一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17)。由此,有关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这一段公案的结案尚需要新的原始资料、档案等的发现才能推进。
1994年俄罗斯整理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以下简称“联共(布)”档案),在该份联共(布)档案第一卷中有两份编号为20号和21号的文件,详细地论及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问题,为这一段公案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原始资料(18)。这两份档案所提供的核心观点是“中共组织领导了1922年‘非基运动’”,与上述叶嘉炽书中所提及的1927年张作霖查抄俄国驻华大使馆所获俄方文件《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报告》中的记载是一致的。随着1997年这一档案资料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同时翻译出版,一些党史著作和学术论文均引用这两则档案,逐渐确立了这一段公案的主流观点:中共参与领导了1922年的“非基”运动。
例如,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一书根据这一份联共(布)档案,认为“1922年3月,在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团地委的发动、领导下,从北京开始发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非基督教运动。”(19)再如,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根据这份联共(布)档案,认为“我们现在大致可以认为1922年在全国迅速引起巨大反响的非基运动,不是一次自发的运动,而是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青年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也包括国民党等组织成员参与的政治斗争,同时,正是由于政党有组织的发动,才能形成在全国许多城市一呼百应的声势。”(20)嘉禾、牟德刚也持这一观点(21)。
至此,有关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这一段公案似乎已经了结,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本文认为联共(布)档案中存在诸多不实和夸大之处,因而在利用这份档案资料时必须谨慎,不能完全依据此即得出“中共领导了1922年‘非基’运动”这样一个结论。
联共(布)档案所提供的资料主要有两份:第一份为编号第20号的“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这一则档案非常简略地提到:“现在我们组织了广泛的反基督教运动,她起因于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基督教代表大会,是一种抗议行动,尔后变成了广泛的运动,现在在号召为国家的统一而联合起来,已在更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目前要把这场运动纳入政治运动轨道,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伪装的合法组织。”(22)第二份为编号第21号的档案,即题为“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该则档案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有关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的细节。利金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青年学生中却很大影响。在一些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具有威信和很大影响的。……这种影响在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反基督教的两次运动中部分地得到了证实。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间开展大规模的运动。”“尽管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存在着基本的决定性的弱点,……但是应该指出,这些小组过去和现在确实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就是出版工作和宣传工作,我在那里逗留时,表现为搞一些宣传运动,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所谓反基督教运动。”“所谓非基督教运动则无可争辩地表明,这些小组能够把大批的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吸引到广泛的运动中来,如果这场运动的基本方向涉及当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的话。”“非基督教运动形成了广泛的战线,……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利金多次强调中共对整个反基督教运动的领导权,例如利金强调“这场运动形成了由我们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局领导的强大社会浪潮”,“中央局巧妙地掌握住了运动的领导权”,“在我看来,非基督教运动的教益在于,这场运动不仅说明我们有可能掌握,而且也证明了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掌握中国社会激进阶层的人民革命运动。”(23)
联共(布)档案中收录的“利金报告”是目前有关中共与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关系的最为详尽的档案材料。但是,正是这份目前学术界依赖颇重的档案资料,存在诸多不实和夸大之处。
第一,利金报告中存在明显的与史实不符合之处。例如,利金说因为中共的组织领导,“基督教代表大会被搞垮了”,(台湾译本说“基督教代表大会被取消了”)但是,在一个脚注中,利金又指出,“除破坏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大会外,计划的基本条款都实现了。”(24)一个最为明确历史事实是,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并没有被“搞垮”或“取消”,相反,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顺利召开。大会召开当天,北京《晨报》刊登了李大钊等人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称:“我们相信在宗教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昌明,自由不能确保,故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召开第十一次大会的时候,联合非宗教的同志,作非宗教的宣传运动。”(25)
第二,利金报告强调说“在北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立大学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而所谓的“国立大学”,首先指“北京大学”,利金说:“李守常教授(即北京大学颇孚众望的讲课人)参加我们的小组,起了很大作用。”(26)但是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显示,中共,特别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遭到驱除。例如,教育部训令第189号饬令北京大学驱逐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杂志(27),北京大学在致教育部的函中说:“查本校各种印刷物并无《先驱》之名,且该刊编辑者系属匿名,亦不知何人所办。即使各校学生有课外外论,其言论亦由作者自负,与学校无涉。”(28)而根据邓中夏年谱记载,《先驱》杂志前三期在北大出版后,由于北京政府查禁,从第4期开始转移到上海出版(29)。
利金报告中的不实之处提醒我们在利用这份解密档案证明中共组织领导1922年非基运动时必须谨慎。利金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组织领导了“非基”运动,这也正是本文需要考证的核心点。本文认为利金报告中所谈到的“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这种说法夸大其词,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中共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非基”运动“伪装的合法组织”,在其影响范围所及的学校和地区组织领导参与了“非基”运动,但是这种组织和领导仅仅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并且很快就被淹没。
关于中共对整个非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效的信息。达林于1922年春天时到达上海,与中共中央局成员经常举行会谈。达林回忆说:“在后来几次会见时,有一次谈到了基督教青年会。这个组织1922年4月将在北京召开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亲美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力求揭露基督教青年会的帝国主义实质。”因为“非基”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第二次大会被推迟(30)。如果说在这次会谈中,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和中共中央局就“非基”运动达成一些决议,如利金报告中所指出的,“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那么,达林和作为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将对“非基”运动进行全权领导。而事实是否如此呢?考察达林,特别是陈独秀的言论和行动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从达林的情况看,当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C.A.达林离开上海到达北京时,世界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同盟会议正在召开中,“非基”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非常凑巧的是,达林正好与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们住在同一个旅馆。达林以一个旅行者、旁观者的身份观察了双方的活动,但是只字未提中共或共产国际与“非基”运动的关系(31)。这就表明,共产国际或中共对于北京的“非基”运动没有起组织和领导作用。
而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提供的证据看,中共中央对于“非基”运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但没有在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这场运动。早在1920年,陈独秀就发表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强调对基督教的批评应该区分为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个层面,对于基督教教义,陈独秀认为“不必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缺点特别攻击”,而对于后者,陈独秀认为“至于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恨而且战栗!……教会在中国所设学校无不重他们本国语言文字而轻科学,广东某教会学校还有以介绍女生来劝诱学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关系(而且是重婚)诱惑某教育家入教的,势力金钱之外,还要用美人计来弘教,是何等下流!”因此主张应该特别攻击基督教(32)。
陈独秀的这篇文章,被重新刊登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第4号《反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上,以作为中共对此的立场之一。陈独秀此篇旧文新刊,是否表明陈独秀其实于1922年“非基”运动之前就已经对“非基”运动有思想准备,从而顺理成章地组织领导了最先于上海发起的1922年“非基”运动呢?答案是否定的。第一,“非基”运动爆发后,陈独秀虽然发表了对周作人等5位北大教授以信教自由为据反对“非基”运动的言论,但是这只能表明陈独秀支持“非基”运动,而不能表明陈独秀领导了“非基”运动。例如,1922年4月7日,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等5人的信中表达了对“非基”运动的支持,他批评周作人等5人说:“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有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33)第二,随着“非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陈独秀改变了早先无条件支持“非基”运动的态度,对“非基”运动作出更为理性的分析,甚至谨慎地表达了反对意见。这就是1922年5月22日他在《广东群报》发表的《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一文。在文中,陈独秀强调:“我对于非宗教同盟并非根本反对,但是从社会上群众运动及生活内容上看起来,不无怀疑之点。……试问主张非宗教同盟者诸人,是否都对于一切学说、主义一概取怀疑的态度而无诚笃的信仰?研究及分析这样复杂的问题,是大学校研究室之事,若拿他做群众运动的目标,实在要令人迷惑。群众运动的目标,还是非基督教同盟可以使群众得着一个明了正确的观念。”接着,陈独秀列举了赞成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10大理由,“警告非基督教的学生,若没有猛勇的觉悟与改革,在优胜劣势的原则上,我恐怕不但不能战胜教会学校,还要让他的势力蔓延全中国教育界,此事宁不痛心!”(34)
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对非宗教同盟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两个组织做了区分。陈独秀区分的意义在于:第一,陈独秀所反对的非宗教同盟,正是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积极参与行动的“非基”运动组织。陈独秀的反对表明中共中央并没有对全国的“非基”运动作统一规划,中共党员也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到“非基”运动中。因为如果中央做出统一规划或者中共对整场运动居于“领导地位”,或者说通过青年团有效地掌握了“非基”运动的领导权,那么,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不可能反对利用“非基”运动作为扩大自身影响的“群众运动”的非宗教同盟,反对李大钊居于重要地位的非宗教同盟。第二,陈独秀反对非宗教同盟和支持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原因在于上海的中央局领导组织了上海青年团首先发起“非基”运动。
之所以说上海的中央局领导组织了上海青年团首先发起“非基”运动,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3月15日发行的《先驱》第4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可以看出。第一,《先驱》半月刊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在3月15日刊登了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这是全国最早有关非基督教运动的群体行动的共同声明。第二,这份《同盟宣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写成的,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表明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社会主义”性质。宣言内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各国资本家“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主义了。而现在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演成资本家底良善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即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国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35)第三,该号特刊还刊登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规定“以反对基督教为宗旨,凡赞成本同盟之宗旨,热心本同盟事务者,皆得为本同盟之会员。”(36)第四,该期特刊所刊登的文章中,绮园所发表的《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文,明确解释了中共发动“非基”运动的原因和“非基”运动的内容、对象。文章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向宗教作战,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严格分别的。一方面与那宗教宣传之特别组织底教会作战,他实在是诱惑愚昧的人民和制造宗教的奴隶底工厂。一方面大多数无产阶级中那流传久远,根深蒂固底缪说作战。然而我们尤其不要忘记,中国的基督教后面隐藏着个资本的侵掠主义。外国的教士没有一个不受资本家或政府所豢养,以作他们侵略底急先锋的。”(37)第五,一些时人,例如张钦士也证实,《先驱》所刊登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是由布尔什维克人主笔的。张钦士指出:“一个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学生小团体,在上海读到了这篇特别的报道(刊于《青年进步》杂志,系有关在1922年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会议者),就开除在他们团体中的惟一一位基督徒会员的会籍,并且写就了一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这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广泛地被流传开来了。”(38)
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发起了1922年在上海的“非基”运动,其组织机构是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从这一点回看利金报告,发现利金报告所谓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这一点具备部分的真实性:上海的非基督教运动的确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组织发起的,说领导权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也未尝不可,因为陈独秀对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表现出的是全力支持。但是这种部分的准确性绝对不能夸大。
紧接着上海的非基运动,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很快成立了北京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根据1922年4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区负责人道培给上级领导子由的信所提供的信息,北京党组织在“非基运动”开始后,积极发起并试图使之作为发展团员、扩大影响的合法机关。该信说:“此间非教运动,原有两种组织:一是非基教同盟,一非宗教同盟。后以非宗教团体人较多,势较大,便归并作为一个永久机关,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的附属宣传机关。此于主义宣传及团员扩充,不消说可以得到许多助力,自当一致努力进行。”(39)但是,正如笔者所提出的,中共组织领导的“非基”运动,力量非常薄弱,组织力度不够,并没有形成为利金报告中所谓的全国规模,并且很快就没落了。关于这一点,上海和北京两地均有几条直接的证据可供查证。
上海方面,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1922年4月7日在《民国日报》撰文指出:“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40)这就是说,即使利金报告中所谓的“运动的领导权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和共产党中央局对“非基”运动制定详细的运动计划,如成立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等均属实,那么,短短的20余天后的4月初,正是全国“非基”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中共就失去对运动的领导,所制定的详细计划也无从继续。因此,利金报告说“共产党中央局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北京方面看,第一,3月11日,紧接着上海3月9日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发表后两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就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3月21日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并不如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一样,是用初学的“布尔什维克口吻”写成的,而是用民族主义的口吻拟就的,更为重要的是,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明确强调其“非党派”特性。宣言说:“我们组织非宗教大同盟,实属忍无可忍。同盟宗旨,仅非宗教,不牵涉一切党派,亦丝毫无其他作用,尤无种族国家男女老幼之别。”(41)在4月1日解释“东电”的公开声明中,“非宗教大同盟”再次强调:“(有人)说我们非宗教运动的人,好像是有些过激党,这也是动人片时的疑想,这又大错了。我们要很诚恳的对他们说道,我们的非宗教,就只为以科学胜宗教,毫无别的作用,讲社会问题的,是另一回事,与这同盟无干。”(42)这就是说,作为1922年“非基”运动主体力量的“非宗教大同盟”,是从根本上反对政党力量在其间发挥作用的,它所强调的是“以科学反对宗教”,并以此区别于义和团式的反对基督教运动。从这一点看,无论中共还是国民党,均没有在以“非宗教大同盟”为核心的“非基”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虽然在该宣言的最后签名中,中共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等十余人,甚至没有达林在回忆录中提及的被委派到北京领导“非基”运动的张太雷。而国民党代表则有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另有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但是这些所谓的政党代表的党派属性,仅仅是后来的研究者以后见之明赋予他们所已经具有的党派特征,并非这些党派代表在署名时表明的身份,例如,李大钊署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这就是说,在1922年这场“非基”运动中,中共仅仅是适逢其会而没有取得领导权,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仅仅以个人身份参加而淡化政党属性;中共参与领导组织的“非基”运动仅仅局限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
第二,北京团组织在1925年、1926年所撰写有关北京非基督教运动的总结报告显示,1922年中共领导青年团在北京发动的非基运动是微不足道的。1925年9月团北京地委关于“非基”运动报告的回顾部分指出:“北京有一非基督教大同盟组织,人数大约有百余人,由我们的同学主持之,在五卅以前工作不甚积极,亦未在各学校成立支部。虽亦在各学校小有接头,但没有什么成绩。”(43)中共北京市委在1926年6月4日关于半年来北京非基运动的总结报告的回顾部分也指出:“北京非基的工作是做的很久,但是在1925年11月20日以前,北京城的非基空气可说丝毫都没有,没有人知道北京有一个‘非基督教大同盟’,它的原因大概是以前团体没有注意这个工作,而负责的同志也搁下不干,所以就默然无闻了。”(44)
本文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档案馆、北京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等馆藏的原始档案以及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其他原始资料,辨析了联共(布)档案中有关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的记载,得出一些看法:
第一,中共的确参与了1922年这场非基运动。中共的参与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个人身份参加,例如李大钊等;第二种是通过青年团参加。根据1922-1923年青年团负责人施复亮的回忆:“共产党的组织当时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45)中共通过所属的青年团参与“非基运动”。
第二,中共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组织,领导了青年团范围所及地区的“非基”运动,但是由于党员不多,团员稀少,尚不能有效地组织影响巨大的运动。“据团中央统计,至(1924年)10月上旬,团员总数为2500余人,但是工人成份很少,2/3以上为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其中在校学生又约占了一半有余,学校一放假,团务便陷于停顿,有的甚至无人接受信件,几乎等于解散。”(46)党员和团员的人员局限严重影响到“非基”运动的组织和影响力。例如,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回忆说:“为了领导北京青年团非基督教运动青年会的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张太雷到北京。”(47)而根据张太雷本人的著作,他的确做过一些反基督教的活动,但是规模和效果不甚明显。张太雷在1924年发表的文章中回忆说:“基督教的宣传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是最危险的东西。虽然在以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做过了一点反基督教宣传功夫而给他一种打击,中国青年学生仍旧有许多受他的影响。只有继续的有系统的宣传,指出教会帝国主义侵掠的背景和基督教现在在欧美的破产,才能打破他在中国青年中的势力。”(48)
第三,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领导了1922年的“非基运动”,但是中央并没有制定统一的领导“非基”运动的计划,运动的“总指挥部”从未掌握在中共中央局手中,也没能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控制整个运动,因此才在诸多人士中造成一种“初学布尔什维克”的感觉。例如,当时著名的教会人士刘廷芳评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时说:“这篇文章有三样特色:1.这是一篇很好的白话文,措辞很清顺;2.这是一篇很嫩的文章,全凭意气,不讲理性;3.这是一篇鼓吹作用的文字,从头到尾偏执激烈。这篇文章是反对基督教,因此反对基督教的产物‘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但反对的论调,是像初学布尔什维克的口吻,不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平心静气、切实具体的研究和由研究后细心精确的批评。”(49)刘伯明也指出:“俄国过激党,……其与今之非宗教运动,有无因果之关系,尚不可知。惟事实上有类似之点,则确然无疑。”(50)而与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关系非常密切的日本学者吉野作造在《朝日新闻》撰文说:“若就此次反基督教运动的本体论,那么恐怕不外一种翻译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因为该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有许多是我的知人,而他们都是极热心的社会主义者。”(51)
联共(布)档案的记载虽然能够从某些方面补充中共在这场“非基”运动的情况,但是,如果据此即认定中共领导了1922年的“非基”运动,则明显不能令人信服。关于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这段公案的一个初步结论是:中共参与了1922年的“非基”运动,也在影响所及范围内领导了“非基”运动,并且,中共参与并在一定范围领导“非基”运动的行为,对此后中共关于“非基”运动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1923年后,中共对基督教会在华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从“帝国主义急先锋到文化侵略论”的思想转变,从而使得非基运动更具理性和号召力,为1925年中共发动有组织、影响巨大的非基运动奠定了组织和思想基础。
注释:
①C.S.Cha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ovement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Church",in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Ⅶ,A pril 1922,No.2,p.103.
②“非宗教同盟之东电及应声”,《晨报》,1922年4月2日,第三版;张钦士:《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北京: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第197页。
③“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见《鲁迅研究资料》9,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此信发表时所署时间为1932年4月8日,据杨天宏先生考证,1932年当为1922年之误,本文采纳之,感谢杨天宏先生提供的信息。见杨天宏:“信教自由论战——二十年代一次重大的思想文化之争”,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第84页。另见氏著:《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该书为修订版,初版参见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张钦士:《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序言。
⑤Paul A.Varg,Missionaries,Chinese,and Diplomats: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90-195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⑥卢茨(Jessie G.Lutz):《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巨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⑦Jessie G.Lutz,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Nortre Dame,Indiana: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INC,1988,p.67.
⑧赵清:“从反‘孔教’运动到‘非宗教大同盟’——‘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反宗教道路剖析”,载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8页。
⑨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第249页。
⑩Tatsuro and Sumiko Yamamoto,"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1922-1927",i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Ⅻ,No.2,Feb.1953;刘尼玲译,“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颁,第208页。Also See Yamamoto Sumiko,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China:the Indigenization od Christianity,Tokyo: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2000,pp.128-129,p.139.
(11)叶仁昌:《五四以后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国政教关系的解析》,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80—82页。
(12)Ka-Che Yip,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Western Washington,1980,p.3/p.25.
(13)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1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15)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2004,第213页。
(16)See Ka-Che Yip,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p.25.
(17)薛晓建:“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非基督教运动的关系”,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7卷第3期,第38—39页。
(18)РЕДAКЦИОННAЯ КОЛЛЕГИЯ,BКП(б),КОМИНТ-
ЕН и НAЦИОНАЛЬНО—РЕBОЛЮЦИОННЦОЕ ЛBИ-
ЖЕНИЕ B КИТAЕ,ДОКУМЕНТЫ,Т.1 1920-1925,МОCКBA,1994.(本文在使用这份联共(布)档案资料时,根据俄文原本,对照中文翻译本,感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肖宇博士在俄文翻译方面提供的帮助。)
(19)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20)陶飞亚:“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原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亦见氏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21)嘉禾:“非基督教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次重大政治行动”,载《北京党史》,2001年第4期。牟德刚:“中国共产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立场态度及其历史意义”,载《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
(22)"№20:ПИCЬМОB.Д.BИЛЕННСКОГОCИБИРЯ-
КОBA К.Б.РAДЕКУ,Пeкин,6 aпреля 1922r.",РЕДАК-
ЦИОННAЯ КОЛЛЕГИЯ,BКП(б),КОМИНТЕН и НAЦИОНA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Ц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11920-1925,л 77.中译文见“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拉狄克的信”,1922年4月6日于北京,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1页。亦见李玉贞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台北:大东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57页。
(23)"№21,ИЗ ДОКЛАДA ЛИЛИНА В ОТДЕЛ ДA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ККИ О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Б.м.,20,мая 1922г,"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ВКП(б),КОМИНТЕН и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Ц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11920-1925,л 83,л 83—84,л 86—88,“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87、88、90-94页。
(24)"№21,ИЗ ДОКЛАДА ЛИДИНА В ОТДЕЛ ДA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ККИ О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Б.м.,20,мая 1922г,"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ВКП(б),КОМИНТЕ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Ц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11920-1925,л92,л 88,“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3、92页;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第67页。
(25)“反对宗教之文电又一束”,载《晨报》,1922年4月4日。
(26)"№21,ИЗ ДОКЛАДА ЛИДИНА В ОТДЕЛ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ККИ О РАБОТЕ В КИТАЕ,Б.м.,20,мая 1922г,"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ВКП(б),КОМИНТЕН и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Ц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ДОКУМЕНТЫ,Т.11920-1925,л83,л 84,“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载《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87,89页。
(27)“教育部训令第189号”,1919年4月14日,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200010。
(28)“北京大学为本校无《先驱》半月刊复函教育部”,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22015。
(29)“邓中夏同志年谱”,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卷号:BD19200016。
(30)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张亦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页。
(31)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64页。
(32)陈独秀:“基督教与基督教会”,载《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33)“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7日。
(34)陈独秀:“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广东群报》,1922年5月22日。
(35)“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载《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36)“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载《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37)绮园:“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载《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
(38)Neander C.S.Chang,"The Anti-Religion Movement",in Chinese Recorder,Vol.54,No.8,1923,p.480.
(39)“道培致子由信——关于非基督教运动组织情况”,1922年4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6年),内部发行,1991年版,第15页。
(40)“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7日。
(41)“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晨报》,1922年3月22日,第七版。
(42)“非宗教同盟之东电及应声”,《晨报》,1922年4月2日,第三版。
(43)“团北京地委关于非基督教运动报告”,1925年9月,载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6年),第400页。
(44)“北京非基工作第一次报告”,1926年6月4日,原件不全,标题为原文标题,日期为文件收到日期,载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6年),第502页。
(45)“施复亮谈1920年-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年1月,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一集,1982,第141页。
(46)赵朴:“青年团的组织史资料”(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二集,1983年版,第76页。
(47)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第64—65页。
(48)Chantal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少年国际》,第1期,1924年7月。
(49)“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生命》月刊第2卷第7期,1922年3月。
(50)刘伯明:“非宗教运动平议”,《学衡》第六期,1922年6月,第1页。
(51)田汉:“日本学者对‘非宗教运动’的批评”,《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九期,1922年4月1日,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