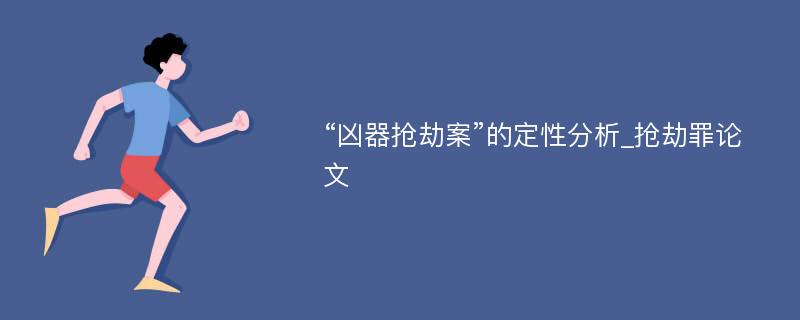
“携带凶器抢夺”的定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性分析论文,凶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抢夺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罪名。在犯罪构成上,抢夺具有与抢劫相似之处。但是,抢夺行为具有的非暴力性特征,成为抢夺罪与抢劫罪的重要区别。由于抢夺罪不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所以立法上以抢夺财物的数额是否较大作为罪与非罪的量的界限。而具有侵犯人身性质的抢劫犯罪,抢劫财物的数额大小并不影响犯罪构成。可见,刑事立法对抢劫罪和抢夺罪的社会危害性评价是轻重有别的。然而,依照刑法规定,实施抢夺行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依法以抢劫罪论处:一是,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抢夺之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转化为抢劫犯罪;二是,根据第二百六十七条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量刑。在此,笔者准备对第二种情形的法律规定的适当性进行分析。
一、犯罪构成性分析
“所谓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这个刑法专用术语,一般来说起源于德国刑法学的犯罪论。早在一七九六年,德国刑法学家库莱茵在诉讼法上开始使用构成要件一语,后来逐渐作为实体法中的用语来使用。”[1] 不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犯罪构成都被作为一种模式,以此对某种行为进行犯罪性评价。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更是罪刑法定的基石。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是犯罪论中的重要内容,不论是区分罪与非罪,还是辨别此罪与彼罪,都离不开犯罪构成理论。所以,我们首先对抢夺罪与抢劫罪的构成进行比较分析。
“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2]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3] 根据概念分析,抢夺罪和抢劫罪的基本构成差异可以归纳如下:(1)客体上存在差异。抢夺罪只侵犯财产权,不侵犯人身权; 而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又侵犯了财产权。(2)客观方面表现不同。抢夺罪是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抢劫罪必须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取公私财产。(3)主体要求有差异。 抢夺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必须是年满16周岁;而抢劫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年满14周岁。(4)主观方面存在差异。抢夺罪的故意内容只能是对夺取财物具有认识和希望的心理;抢劫罪的故意内容既包括对夺取财物的认识和希望,还包括对人身侵害的认识和希望心理。因此,抢夺罪与抢劫罪性质有较大的差异,而其主要差别就在于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抢夺罪的特点在于强力抢夺财物,强力作用于物。而抢劫使用的暴力,直接作用于持物人。正是基于这一影响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关键特征,刑法在两罪的量刑上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必须认真区分两种犯罪类型。
但是,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携带凶器抢夺”在犯罪构成上是否具备了抢劫罪的性质呢?笔者对此提出质疑。
第一,从侵犯的客体来看,携带凶器抢夺,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该行为是否具有侵犯人身权利的性质呢?从词语的一般意义上理解,“携带”只能表明一种状态,即行为人随身带有凶器。而行为人是否利用和如何利用凶器,“携带”一词并不能表达。有观点认为:“携带凶器实施抢夺犯罪,比没有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得多,携带凶器极易强化犯罪心理、极易造成暴力犯罪的最终后果,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应当从严打击,故对于实施抢夺行为时携带凶器的,应以抢劫罪定罪量刑。”[4] 这种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推断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推断不能作为认定行为人侵犯人身权利的充分理由。因为行为人携带凶器,存在使用和不使用两种可能。第一种情形是:携带并使用了凶器行凶或者显示凶器威胁而夺取财物。这种行为既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又侵犯了财产权利,其行为性质是抢劫而非抢夺;第二种情形:携带凶器没有使用,或者非针对人身的使用(如用刀割断皮包带)夺取财物。此种行为因为并未侵害人身权利,认定抢劫与犯罪构成原理相背。从法律规定的本意分析,第一种情形用抢劫罪的现有规定完全能够解释,不必另行规定。“携带凶器”抢夺,显然是针对第二种情况进行的规定。如果一定要将此种“携带凶器抢夺”行为认定为抢劫,就会形成理论上的悖论:侵犯人身权利不是抢劫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如此推理,抢劫罪与抢夺罪根本无法区分。
第二,从行为特征上看,“携带”凶器的状态与侵犯人身的后果不具有因果关系。从抢劫罪的行为来看,侵犯人身的方式有暴力方式、胁迫方式和其他方式。其中,暴力方式是直接对被害人身体实施物理打击,阻止和压制被害人的反抗。胁迫是对被害人实施非物理性的精神压制,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抢劫的其他方式是指能对使被害人处于不敢或不能反抗状态的、暴力和胁迫以外的方式,如药物麻醉、致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所表达的,只能是行为人没有针对人身使用的状况,首先它不属于使用暴力。“携带”凶器所描述的只能是一种状态,不能表明行为人是否使用凶器。那么,“携带”凶器的意义能否与抢劫罪的胁迫和其他方式等同呢?作为抢劫罪的胁迫和其他方式,是指可以使被害人不敢或不能反抗的方式。单纯的“携带”凶器是否会使人不敢或不能反抗呢?事实上,对此问题回答“是”或“不是”,都只能证明“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量刑”的表述不合适。如果作肯定回答“是”,则承认“携带凶器往往会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或者精神受到强制,从而不敢进行反抗”。[5] 而此种情形已经符合抢劫罪的行为方式,没有另行规定的必要(何况我们还不能作出这种回答)。如果作否定回答“不是”,携带凶器抢夺便不具备使人不敢反抗的胁迫性质,因而也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例如,抢夺的行为人在未出示凶器的情况下夺取了财物,那么,他所携带的凶器根本不会对被害人产生任何作用。即使行为人显露了凶器,只要没有针对人身,也不可能达到精神强制的胁迫效果。所以,将“携带凶器”作为独立的行为特征来判断,并以抢劫罪论处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从主观方面来看,仅以“携带凶器”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并以此作为定性的根据是不可靠的。因为“携带凶器”并不表明行为人一定具有实施人身伤害的意图。我们只能通过行为人“使用”或“利用”的进一步行为才能判断其主观心理。如果仅就“携带”状态对行为人的心理作出某种推断,必将导致客观归罪。“携带”的状态相当于刑法上的“持有”,刑法上对“持有”犯罪的规定已经表明,不能从某种状态(如非法持有违禁品)来推断行为人具有的可能心态,并以此推断定罪量刑。例如,不能因为行为人持有了毒品,就当然认为行为人会运输或贩卖毒品(虽然这种推断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并以运输或贩卖毒品定罪量刑,而只能以“持有毒品罪”来定罪量刑(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退一步分析,从“携带”的表象推断,即使不能排除行为人可能存在人身侵害的意图,也只能作为行为人一种内心活动状态,在其未外化为具体行为时,不能认定其犯罪故意内容。
综上所述,“携带凶器抢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原理。
二、罪刑均衡性分析
对某种犯罪行为的定性评价,最终要通过刑罚予以实现。法律规定“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定罪量刑,不仅改变了该行为的性质,更使该行为的刑罚发生了变化。与一般抢夺罪相比,“携带凶器”的抢夺在刑罚上有如下变化:(1)法定最低刑提高了。构成一般抢夺罪可判处拘役、管制,以抢劫罪定罪后起刑点是三年有期徒刑;(2)法定最高刑提高了。抢夺罪最高刑仅是无期徒刑,抢劫罪最高刑可判处死刑;(3)法定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低了。抢夺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是16周岁,抢劫罪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是14周岁;(4)构成犯罪的条件降低了。 构成抢夺罪要求抢夺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携带凶器抢夺”的财物数额不影响定罪。这表明“携带凶器抢夺”与一般抢夺罪比较,在刑罚力度上整体提高了。这是否与“携带凶器”抢夺的性质相适应呢?
根据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刑事责任是归责的基础,它决定着犯罪人是否承担和承担多大的责任。刑事责任的归责要素决定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的归责要素包括主观恶性、客观危害、刑事违法。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有机统一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印证。通常,主观恶性大时,客观危害就严重;反之亦然。刑事违法,是对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在法律上的认定,它确立了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法律特征。[6] 如果根据这种观点,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携带凶器实施抢夺犯罪,比没有携带凶器进行抢夺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得多”,因此主观恶性大,因此客观危害就严重,也因此就应当承当更大的刑事责任。然而,仅以“携带凶器”就断定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或称主观恶性)的作法显然是一种主观臆断。就“携带凶器”的表述而言,不仅“携带”的状态不足以说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而且,何为“凶器”也是含混的。在凶残的罪犯手中,刀、斧自不必说,就连普通的木棍、砖头、石块都可以成为凶器。因此,判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在于通过其携带的物品,而在于其如何使用物品——行为的手段来分析。
日本著名学者指出:“责任非难基本上应该以行为人所进行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个别行为为对象。极端地把行为人的性格所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看成责任的基础的性格责任论有模糊责任的范围之嫌。”“团藤重光博士也认为,责任第一次应该是行为责任,必须以作为行为人人格的主体性现实化的行为为基础来论说……第二次应该考虑人格形成的责任(团藤.刑法纲要总论第239、240页)。”[7] 因此,犯罪行为是评价的基础,主观恶性只能通过具体行为来判断。
上文已经论述了“携带”的状态不能表明行为人对凶器的利用心理,因而,不能成为判定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依据。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来看,携带凶器抢夺和不携带凶器抢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实践中,某些行为人虽然“携带”了凶器,但在实施抢夺行为时,并没有使用凶器对人身造成伤害或威胁,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将凶器拿出来。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行为人就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呢?某被告人仅仅因为事后从其身上搜出了尖刀,就依抢劫罪定罪量刑。[8] 而这把尖刀,在抢夺行为时和抢夺行为后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却导致了行为性质和刑罚上的重大差异。对此,我们是难以解释的。所以,仅仅“携带”凶器的抢夺,不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危害,不应该施加更重的刑罚。
三、结论
“携带凶器抢夺”在犯罪构成上与抢劫罪有本质区别,在刑罚上缺乏加重处罚的根据,不应该以抢劫罪定罪量刑。
该款规定,混淆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本质区别。单纯从行为的表面状态进行主观推理,没有从行为的实质进行客观判断,不仅违背了刑法研究的科学性,也破坏了刑法理论的严谨性。导致了定性不准和罪刑的失衡。在实践中,可能存在难以区分“携带凶器”抢夺对被害人是否产生胁迫,但立法者将此种情形实行“一刀切”的定性,则必然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后果,不利于对被告人的保护。
该规定反映了“重刑”观念。面对犯罪的严峻局面,某些人相信加重刑罚就会遏制犯罪。他们认为将“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定罪量刑,就会控制抢夺之后转化为恶性伤人、杀人案件。这种愿望是好的,但效果可能是出人意料的。它可能促使“携带”凶器的行为人,不再实施对人身没有危害的抢夺,而直接实施抢劫。因为只要携带了凶器,使用和不使用,抢夺后的法律后果是相同的。其结果是,促使更多的人实施抢劫而不是抢夺,对人身安全产生更大的威胁。也许有人提出,“携带”凶器的人极有可能使用凶器并对人身造成危害。对于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案情处理:没有危害和威胁人身的,“携带”凶器的情节不能改变罪行性质,只能以抢夺罪的标准量刑;危害和威胁了人身的,性质就是抢劫,不必要依照“携带凶器抢夺”的模式来认定。所以,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完全可以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