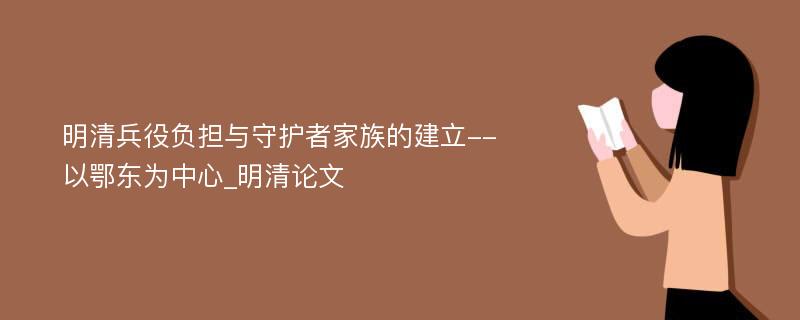
明清军役负担与卫军家族的成立——以鄂东地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区为论文,负担论文,家族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的各种户籍类别中,除民户外最大的职业役户首推军户,对之,学界亦给予了一定的重视。①台湾学者于志嘉的研究表明,明代的军户主要分为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两大类,前者指驻扎于卫所的军人及其留居本卫所的家属,后者是指卫所军人在原籍地的亲属,即明人尹耕所谓的“兵役之家,一补伍,余供装,于是称军户”者。②在赋役形态上,两者存在着重大差异,卫所军户承担军差,缴纳屯赋,而原籍军户平时则服民役、纳民赋,与一般民籍无异,只是另外还有对卫所军户补役、帮贴的义务,主要表现在卫所缺丁时由原籍勾补户丁继役,军丁赴卫时由原籍军户供应军装、盘缠,平时则对卫军提供经济上的支援。③并且,二者从属的管理机构也有所不同,卫所军户作为国家军队体系中的一员,由直接隶属的各卫所进行管理,而原籍军户则由所在州县负责管理。④正如前言,由于原籍军户与一般民户并无太大的区别,因此研究重点应当偏向于卫所军户这一特殊的群体,而且以往论者强调的军役负担沉重,通常也是针对这部分军户而言的。⑤
明清时代是庶民宗族得以成立并蓬勃发展的时期,最近的研究表明,宗族作为一种特定时空的文化创造,受到了国家的赋役及宗教、礼仪等制度;地方社会的族群关系及权力斗争;地方经济的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⑥对于卫所军户而言,军役负担的沉重更是其宗族得以成立并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于志嘉曾以豫章罗氏与山阴白洋朱氏两个宗族为例,讨论了原籍军户家族在事业、婚姻上的发展情况,同时对军役负担在两个家族中造成的影响或实际分担的情形也有一定的说明,限于材料,对于卫军宗族的讨论则付之阙如。⑦
笔者在鄂东地区进行乡村调查时,发现了黄冈《李氏宗谱》及黄冈《蔡氏宗谱》两部卫所军户宗族所修的家谱,它们分别编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民国七年(1918),记载了这两个卫军家族的发展情况,并对军役有着详细的论述,该谱亦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因此,笔者希望以鄂东地区为中心,透过方志与宗谱等资料的记载,通过对黄冈李氏及蔡氏等个案的讨论,对此缺憾略加弥补,以期完整我们对于有关军户家族的理解。
一、卫所军户的演变与军役职责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在取得了湖广控制权之后,分遣指挥黄荣、赵应清等屯守蕲黄,遂于鄂东地区建立卫所。洪武二、三两年(1369、1370),分别改为黄州与蕲州守御千户所,洪武十二年(1379)改所为卫,自是确立了明代鄂东地区蕲、黄两卫的格局⑧。入清以后,议罢天下卫所,然由于仍然肩负着为京师运输漕粮的重责,蕲、黄两卫得以延存。咸丰初年,南漕改由海运,漕运卫所及其屯田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卫所裁撤,屯田归并州县。⑨本文所要考察的黄冈蔡氏及李氏正是黄州卫治下负担漕粮运输的军户。
雍正七年(1729),黄冈蔡氏的第十四世孙蔡景尚作《黄冈蔡氏漕务纪略》(以下简称《纪略》)一文,详细记述了蔡氏这一卫所军户在清代前中期如何处理本族漕运的情况,并对明代的情况亦有所追述,下面分段录之,以便分析:
漕运之设,肇于汉唐,以迄宋元,然皆兑运也。至明太祖定为长运,上以裕国储,下以便民生。每军十名共运一船,如民户之一里九排,每军一名,给屯粮六石为一分,使之自耕自养,是即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焉。无病于民,无累于军,法诚良也。而且飞挽、天庾有行粮以膳军,月粮以宁家,三修有费,诸般杂项有费,厚恤夫军者无涯矣。我祖寿卿公实肩厥任,户名蔡黄郎,载在黄州卫版图。迨本朝定鼎之初,人苦明季之累,黄卫全军八百五十户逃亡几尽,全屯八百五十分荒芜不治。⑩
由于蔡景尚本身即为康雍时人,因此《纪略》中对清初的记载尚属可信。文中称此时“黄卫全军八百五十户”,然按明初的规定:“凡卫所额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内外卫所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二百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其有卫分军士数多,千百户统则一”,(11)而黄州卫早在洪武十二年(1379)便已改所为卫,虽有可能存在全卫不足额数的情况,但其军额应远不止八百五十户,何以清初的情况与明初相比会悬绝若是?而且按照《纪略》文意,“黄卫全军八百五十户”的情况似乎在明末便已形成。另外,“户名蔡黄郎”又有着何种含义?它到底揭示出在卫所军户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这些便成为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黄州卫的这种变化并非特例,在鄂东地区的另一个卫所——蕲州卫的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据方志记载,清代蕲州卫“运班舍军共六百六户”(12),按万历《湖广总志》称黄州卫军额数四千四百三十五名,蕲州卫军为五千七百四十名,(13)由于黄州卫设右、中、前、后四千户所,蕲州卫设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14)因此,万历《湖广总志》记录的额数实为洪武年间两卫设立时所属卫军的原额。由此可见,蕲州卫军的额数同样变动甚巨,进而言之,明清时期以漕运为主要任务的各个卫所应当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卫所的这一变化,古人已有所识,光绪《蕲州志》卷7《职官志·武秩表》对此便有很好的说明,据载:
自古兵戎之制,莫善于井田。明之屯卫,实师其意。承平既久,玩愒成风,至末季耗敝尤不忍言。国朝更制,议罢天下卫所,惟近漕渠郡县间存。漕船既减,屯丁亦仅取足供役,余则尽隶有司。各卫止设守备千总等员,督领漕运,兼理屯粮,而地方防守,别置副将参游,训练兵卒,人由选授而来,兵由简练而聚,可谓至周且详。
其文简略地指出了鄂东两卫在明清两朝的变化情形,显然,在两卫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文中所言明代卫所“承平既久,玩愒成风,至末季耗敝尤不忍言”之情,反映的应当正是卫所内部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在卫军身上则体现为洪武之后,两卫实际控制的卫军数量日渐减少,耗敝异常。
不仅是清人,更早一些的明代时人对此亦有深刻的认识,如成弘时期的重臣马文升曾曰:“(太祖时)乃于湖广地方设立三十六卫所,官军三十余万,并江西沿江又多设卫所控御上游,以为金陵之屏蔽……迨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而南京、湖广、江西沿江卫所官军已割其十之五六矣,加以逃亡、事故埋没者,又不知几何。”(15)此段记载反映出,在永乐时期,明朝政府迁都北京,曾调拨大量湖广卫所的军丁移师北京,此时,蕲黄两卫隶属的军丁亦有不少随明成祖移镇北京。如果说军队的调防尚属正常情况的话,那么之后则更由于卫军的逃亡事故,鄂东两卫的军队数量愈益减少。延至清初,《蕲州志》卷7《职官志·武秩表》中“漕船既减,屯丁亦仅取足供役,余则尽隶有司”的记载,说明部分的卫军转移至地方州县的管理体系之内,与一般民户相混淆,致使卫军数量进一步减少。不过此段记载乃是指全国的情况,对于鄂东两卫而言,“黄(州)卫全军八百五十户”(16)、蕲州卫“运班舍军共六百六户”(17)的额数似乎直至光绪年间两卫被裁撤之前,在册籍上一直维持不变。
卫军数量的减少尚且容易理解,毕竟有关军户逃亡,以及政府对之进行整顿清理的记载史不绝书,其实,与之相为表里的更为关键之处,在于单名卫军的本身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初由于战争的摧残,各地经济急需恢复,政府于是规定正军户下除充当军役的“正身”及其“当房家口”外,其余人丁仍需回到原籍负担民差,因此这些卫所军人通常是单丁,或是以卫军为主的核心家庭。他们与身在原籍的亲属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如卫军有时会回原籍索取军装等财物,以补偿其服役的开销,亡故之后,继役者亦在原籍军户中进行勾补,并且即使某些军人以逃亡的方式来躲避军役,在明初严格的清勾政策之下,仍需从原籍亲属中选补。然而对于那些卫军家庭所繁衍的子孙而言,回到原籍还需应役当差,而留在本地反可免除差役的负担,于是留居本卫“在营余丁”日渐增多。(18)据于志嘉考证,大体上在宣德八年(1433)以前,政府对在营余丁的基本态度仍是希望他们回原籍负担民差、粮差,但如果原籍差役供办不缺,则多顺其自然,不加干涉。(19)之后,随着在营余丁的日益增多,明王朝也相应地调整政策,允许这部分人落在本卫所的户籍之内,如嘉靖《蕲州志》中记载的刘瑄、金兰、田鹏、华霁、陈僖及宋良臣等人均是在正统、成化、弘治年间以卫籍的身份考取科举功名者。(20)由于在营余丁仍然是附着在该名卫军正身的名下,这样就使得原本只是单丁或是核心家庭的卫所军户逐渐蕃衍成一个同姓的血缘群体。从正统年间即有卫籍考取功名者这一事实来看,这种变化在宣德正统间便已出现。
以上变化落实到黄冈蔡氏的身上,即表现为“我祖寿卿公实肩厥任,户名蔡黄郎,载在黄州卫版图”。按《蔡氏宗谱》卷2的世系记载,始祖蔡祯洪武初考入黄冈县庠,于是由江西南昌府南昌县迁至黄冈县上伍乡校鱼村定居,生有蔡荣卿、蔡寿卿及蔡昭卿三人,其中荣卿回江西,昭卿住麻城县望花山,而寿卿则以蔡黄郎为户名,“载在黄州卫版图”。
这里,蔡祯由江西考入湖广的黄冈县庠,实属不可思议,很明显他应当是一名卫所军人,作为余丁的长子荣卿回到江西,应是当时政策的要求;次子寿卿以蔡黄郎为户名入籍黄州卫,应属蔡祯因亡故或是年老不能正常履行军役之后,顶补军役的情况,由于该宗谱并未载明蔡祯及蔡寿卿的生卒年月,因此以上两种情况俱有可能。由是可知,在寿卿自立户之后,他的子孙都留居于本卫,并且该族谱中也未见有他们与原籍亲属往来的记载,这样他们便逐渐形成为一个卫军户名下承担军役的血缘群体。按照前述明廷政策的规定,寿卿的子孙入籍本卫,应当发生在宣德八年(1433)之后,此时距离洪武初始祖蔡祯迁至黄冈已近六十余年,这里就可能存在着寿卿的子孙在宣德之前便已留居本卫的情况,从当时明廷的态度来看,亦属正常,只是他们入籍的时间在宣德八年之后而已。
三子昭卿入麻城县民籍,可能是属于寄籍附近州县的情况。明代存在着卫军家属寄籍附近州县的情况,不过为了确保卫所军役有足够的人来承担,明廷曾对卫军家属寄籍附近有司的现象加以限制,如景泰元年(1450)规定:“官军户下多余人丁,有例除存留帮贴正军外,其余俱许于附近有司寄籍纳粮当差,中间有一家或三五人、十余人,止用一二人寄籍有司,其余隐蔽在家,不分年岁久近,其该纳粮草仍于有司上纳,其人丁尽数发回军卫”。(21)
《纪略》又云:
我朝命所存之军各垦各屯,相为挽运,我族独运一船,虽上、中、下、西,四六之分,或分歉于人,或人歉于财,而疲苦为甚。伯父调九公及甘吉公、叔祖公长公与先大人恪奉大例,或两船合一,或三船合一,本族于康熙二年(1663)起造,与李信保共足额军十名,合为一船,改名蔡李保。
姑且暂置此段记载反映的其他信息,它首先反映了蔡寿卿所立“蔡黄郎”之卫军户名一直保留到康熙二年(1663),与另一卫所军户李信保合并漕船,共用一个卫军户名“蔡李保”为止,纵贯了整个明代,这里亦再次证明留居本卫的寿卿子孙均附着在“蔡黄郎”这个卫军户名之下,户名一直未变。明代卫军户名保持不变的情况并非绝对,如咸丰《蕲州志》记载了蕲州卫47名百户“伍下”所属的屯粮数,(22)对照该志所载明代曾任本卫百户的名字,无一相符,(23)虽然方志的记载并不完整,不过显然百户的户名并没有被固定化。当然,于军官而言,由于其职务世袭,负有督运漕粮之责,明廷的管理亦较一般卫军严格,因此百户的户名变化似乎不能与普通卫军一概而论。然不管户名变与不变,卫军留居卫所的子孙附着在一个卫军户头之下的情况则属史实。
按咸丰《蕲州志》卷5《军卫》所记百户姓名及“伍下”的屯粮数,系抄录旧志所得,而明代州志中并无此项记录,清代蕲州于康熙三年(1664)及乾隆二十年(1755)编修过方志,因此这种情况至迟在清前期便已形成。在此之后,光绪《蕲州志》对这一数据则仍旧照抄不误,看起来清代卫所百户的户名似乎亦被固定。如前所述,清廷在“各卫止设守备千总等员,督领漕运,兼理屯粮”,(24)此时百户正因为守备千总等员的设立而失去了督领漕运的职责,亦可能就此失去了世袭的职务,已不再受到当局的重视。因此,对之的理解就不能停留在户名固定这一层面上,其意义可能存在于官府只是重视有多少屯田可以收受屯饷、支撑漕运,对于这些百户的户名则不予理会之上。
明初卫所的军役仅只涉及正军一人,在营余丁并没有受到军役的牵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军役内容渐趋多样,卫军逃亡人数亦不断增多,这也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苦心积虑设法增加兵源,在营余丁被用充卫所工役乃至正役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常见。(25)这个重大转变的背后,是政府逐渐放弃了从原籍勾补军丁的做法,以至于卫所军户也渐渐地与原籍失去了联系,从而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于是,沉重的军役负担逐渐完全由卫所军户来承担。
因所处地方不同,明代全国各卫所的军差内容亦呈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差异,于志嘉概括了明代卫所的军种主要有屯军、班军、操军、局匠军、巡捕军、运粮军、备倭军、马军等项。(26)据黄冈《李氏宗谱》记载:“军户之设,始自前明,至我朝开张,圣恩体恤周至,诚为善政。然立法过久,不无小变,造船之岁,军户苦于供应,故充其籍者,甚至子孙不能安枕,非制度之不善,而人力之有限也。其例十年一役,五军并用,五军者,班、抄、城、舍、运也,共三十二人为一旗,旗运一船,旗之中为运军、为帮军,运之中为正运、为副运、为随运,其差惟运军独苦,正运一二人,又其苦之最者也,其他除风火大故外,无恙焉。”(27)据此可知,明代鄂东卫所的军差应当包括有班军、操军、城守军、运军等项名目。由于鄂东深处内地,军事征伐任务不似沿边及沿海地区重要,加之湖广为京师漕粮供应的主要省份之一,因此运军是卫所各军种中人数最多的一种,马文升即云:“迨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后令官军漕运,以备京储。该用官军一十二万,而南京并湖广、江西沿江卫所官军已掣其十之五六矣。”(28)
由于明代奉行“以屯济运”的原则,蕲黄两卫的运军亦应是由原来的屯军演变而来。咸丰《蕲州志》卷13《人物志·孝友》记载了明嘉万时蕲州卫人李同春负责漕运的情况,据载:
袭职领漕运,运军折米五百余石,先是自解囊完纳,众免破产追赔累。归至途闻亲病笃,号泣思归,水浆不入者五昼夜。忽梦河神曰:“吾念汝孝,许只艘先归,可速行,明午冻河矣。”如是者三。同春曰:“神不我欺。”遂行抵淮。淮抚怒超次,以神语对,抚因以观验,至午,狂风骤起,须臾水冻,奇而释之。
由这段传记可以看出,漕运途中损失漕米,运军负有赔纳之责,并且在运河之中有着漕运班次的规定,如果不依规定先行或是滞后,均会受到惩罚,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中后期对于漕运事宜的管理仍然较为严格。
入清以后,随着绿营兵制的建立,湖广地区的卫所完全丧失了镇戌地方的功能,诸如鄂东两卫这样明代遗留下来的卫所,其任务便更加单一化为只是负责漕运事宜,前述《李氏宗谱》的记载显示,黄州卫属的军户都只负责漕运的任务,诸如“班、抄、城、舍”等军之名目都已名不副实。正如李氏所言“其差惟运军独苦”,运军在其存在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承担着沉重的军役负担。首先,他们要负责漕船的修造。据《漕船志》记载:“(明代)湖广船只木植及料价银两多寡不同,有用杉楠木者,十年一次改造,连底船该价一百三两;有用株杂木者,七年一次改造,连底船该价银九十两五钱;有用松木者,五年一次改造,连底船该价银七十四两九钱”,(29)造价甚高,到了清代,漕船造价更有增无减。(30)如此昂贵的造价也就造成了“造船之岁,军户苦于供应,故充其籍者,甚至子孙不能安枕”的局面;其次,在漕运过程中如果发生事故而损失漕粮时,运军还要负责赔补,明代如此,清代亦同。如黄冈李氏在康熙年间“失风两次,族有号则吾、嘉乐者,皆死之,又加赔米赔船,合族骚扰,而李氏之困始此矣”;(31)再者,他们仍不免受到交兑仓口的差吏们各种额外的需索。另外,对于军户中具体承运的个人而言,运输途中亦充满艰辛,所谓“风火之患苦、供应之烦苛、伙伴之险诈,非智力兼全者动辄得咎”,(32)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
因此,卫所军户的后代在同一个卫军户名下繁衍生息,为家族的成立奠定了人口的基础之后,军役负担便直接成为了其家族成立的主要动力之一。
二、卫军家族的成立与军役负担
《黄冈蔡氏宗谱》卷1《黄冈蔡氏漕务纪略》中:
我朝命所存之军各垦各屯,相为挽运,我族独运一船,虽上、中、下、西,四六之分,或分歉于人,或人歉于财,而疲苦为甚。伯父调九公及甘吉公、叔祖公长公与先大人恪奉大例,或两船合一,或三船合一,本族于康熙二年(1663)起造,与李信保共足额军十名,合为一船,改名蔡李保。又于康熙八年(1669)奉例拨班补运,拔班军十名撑驾,自是而通族之困稍甦矣。而挽运究叹艰难也,调九公独运三回,皆捐己资,通族宁逸,乃非一年。至屯田坐落堵城者,不惟草宅是嗟,而亦无人认著也,调九公捐资建屋市生,招佃开垦,付户众收租以帮运费,其亦创业焉,笃本之意欤?又有额屯冯长寿、老冯、贾伏四屯地,除完钱粮外,亦收租以帮运费。
又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因李姓额军七、班军三,运船一半,我族额军三、班军七,运船一半,额班之不同,而轻重大异,额则与我同船之军,我能运彼亦能运,班则不过撑驾而已。参以氏控道,批黄州府李太老爷审明,将各军配搭,分立有点、无点二阄,我族拈得有点:额军五名,蔡黄郎、冯长寿、李五保、袁三儿、徐卿;班军五名,左应科、李实、曾福、倪酉儿、官田一,李姓拈得无点:额军五名,李必信、袁九仅、云朝儿、胡才、倪春保;班军五名,左廷智、雷辰二、邵辛保、张应元、徐秀生。当堂拈定,详道批允,发卫永遵。又拨减存之军张军保、郝本清、郑受公收,通族之困愈减,此乃参以公之力也。
雍正元年(1723),李姓郁华控准黄州卫方,希翻前案。侄承夏念祖调九公、参以公为族人运船辛苦,调护数十年,不甘听李人翻案,同又玉控准黄州府,蒋太老爷行卫,仍照前案,而李人之狡灭矣。此皆功垂后裔,永毗世世,非有自私之心,祖宗之灵爽,讵不默相乎第竭心力以安户众者。长厚者之责,阐文词、纪旧事以表于不朽,未必不赖有人也,倘不序其事以著于刊,则后之人或侵食公租,或吞噬屯地,只知利己,不恤族人焉。知前此者之为户众虑,至深且远哉!因而纪其略于右。
以上这段有关蔡氏在清初承担漕运的记载,真切地反映出军役负担在其家族成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其他记录,我们或许会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从此前的记述来看,在蔡景尚的眼中,明代本族承担运军之责,似乎因为朝廷的各种体恤政策而显得较为轻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亦有可能。张金奎曾对以往学界有关明代军户地位低下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指出除了少数人丁稀少的卫所军户之外,其他卫军对于军役则尚能自如应付,且由于明初卫军有免除杂役的优待,致使一些民户也冒充为军,这种情况在明中后期亦不少见。(33)笔者以为,明代这种军役负担较为轻松及其地位并非低下,均是针对于一般民户而言,明初之后,在整个赋役趋向沉重的情况下,卫所军户同样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前述运军负有赔补漕粮之责的情况即为明证。至明季,由于战争的原因,运军负担大增,他们更是藉明清鼎革之机逃亡殆尽,如上述引文中黄州卫属“冯长寿”等军户虽然名存卫册,实则均已逃亡,这些名字只是代表着挂在其名下的屯田额数,而文中“康熙八年(1669)奉例拨班补运,拨班军十名撑驾,自是而通族之困稍甦矣”的说法,实际上是指由实存的班军户补贴,或是将名存实亡的班军户所有的屯田拨给运军补充运费。这里说明了黄州卫属“全军八百五十户”的额数同样亦非实际的卫军户数,其中仍有很多虚额,所代表的只是屯田的份额,因此就整个清代而言,由于实际负担者的减少,存运军户的漕运任务较明代更为加重了。而蔡景尚对明代运军“美好时光”的回忆一方面是清代漕运负担加重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亦可能是藉此进一步强调此时的负担。
对于军户的逃亡,清初亦有过整饬卫所军额的举动,其间曾发生妄扳民户为军籍之事,如黄冈《李氏宗谱》卷首1即云:“吾乡李旻户,运军籍也。光绪乙未岁(1895),余客于春溪公家数月,问其充籍之原因,得览其家藏遗迹,与其故老之传闻。呜呼,何其冤哉!我朝之兴也,大鼎初定,军户脱落甚多,官府按册稽查,颇有讹误。册有班军李铭者,脱籍也,卫督以字异音同之故,误旻为铭,遂充之。”虽然李氏对于本户被妄扳军籍的说法并不见得可信,然此仍然证明了当地存在这种事情,如清初蕲州即有类似的情况,光绪《蕲州志》卷11《人物志·尚义》“(胡正伦)有族兄立嗣,已六十余年,军户胡姓诬为逃旗,几濒于危。正伦代白之,俾承宗祀。”对于被划入军籍,李氏以“何其冤哉”来表达心中的愤恨,可见军役负担的沉重成为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对象,另外,在其谱《李氏宗谱》中还对本户出任运军之苦做了生动的描写,所谓“自是富者不安于土,贫者不乐其生,负戴逃亡,遍于数省,而李氏之毒遂成附骨之疽矣”。自然,那些仍留居本地而没有逃亡之人就不得不联合起来以共同应对这种局面,于是,军差的负担在这些卫所军户的宗族成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卫军家族在应对军差时采取的措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也与其家族的成立密切相关。从上段“我族独运一船,虽上、中、下、西,四六之分,或分歉于人,或人歉于财,而疲苦为甚”的记载来看,黄冈蔡氏在应对军差之初,首先是在上、中、下、西等不同的房支中进行分配,这种安排在最初应该是考虑了各个房支当时的实际情况,“四六之分”当有一定的公平性可言。然而随着各房支日后的发展不平衡,“或分歉于人,或人歉于财”,以至于本户的漕运任务难以落实,至清初,蔡氏第十三世孙调九公则捐己资,独力承担了数回漕运的任务,致使“通族宁逸,乃非一年”。蔡调九捐资助漕的情况亦非特例,清初蕲州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据咸丰《蕲州志》卷13《人物志·孝友》记载,王柱德:“国学生,父早卒,事母至孝,以兄国学生琳承运漕艘,遂废学持家,节省家用,捐金数千入户济漕,族人德之。”不过,很显然这种以一己之力为通族解困实非长久之计,必须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方可使问题得到更为妥当的解决。为此,调九公将本军户名下因明清之际的战乱而荒废的屯田重新进行了整顿,“付户众收租以帮运费”,这些屯田地因此而成为了蔡氏宗族的公产,而上述记载中“其亦创业焉,笃本之意欤?”之语亦正说明了蔡氏宗族藉此之机得以逐渐形成。
此后,蔡氏名下的屯田便以祖先的名义来进行管理,他们将名下及帮贴的军屯数详细记录在一世祖的祭田之内,(34)由此亦证明屯田的整顿在蔡氏宗族的成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以屯田作为宗族的公产几乎是每一个卫所军户在建设宗族时都会采取的方式,因为这是国家法定给予他们以资助漕运的财产,而当漕运负担成为卫军宗族成立的重要因素之后,屯田也就很自然地变成宗族公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黄冈《李氏宗谱》卷首1《顶充军籍辩》亦做了很好的说明:“李氏有屯粮六石,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后即停漕无费,以其田之出,分八股而生息之。非有所利也,有鉴于先人之艰苦,积以待不时之需耳。”可见李氏即使在停漕多年之后,仍以屯田作为本族公产,以备不时之需,这显示了运军对于漕运苦役的后怕,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漕运军差对于李氏宗族得以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清廷对于运军的负担过重同样有所认识,根据上述蔡氏《纪略》的记载,清廷在康熙二年(1663)合并漕船,及康熙八年(1669)拨班补运等举措使得运军的负担有所减轻。不过官府的这些措施却导致了一个他们所未曾料想的情况发生,这便是同船军户之间对于漕运苦差的相互推诿。由于同船的各个军户之间有负担轻重之别,《李氏宗谱》卷首1《顶充军籍辩》即曰:“旗运一船,旗之中为运军、为帮军,运之中为正运、为副运、为随运,其差惟运军独苦,正运一二人,又其苦之最者也。”蔡氏对拨班补运也做了说明:“额班之不同,而轻重大异,额则与我同船之军,我能运彼亦能运,班则不过撑驾而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运军之间难免会出现避重就轻的局面,于是相互吵闹乃至于付诸诉讼等手段也就无法避免了,如蔡氏曾先后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及雍正元年(1723)等数次与同船的运军“李信保”户构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是转嫁自己的负担。这种与其他运军户的争斗,对于军户家族的整合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军户之内的每一个人都对本户的军差负有责任,与其他军户争斗的胜负输赢也必然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于是在共同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势必要联合起来以争取在争斗中胜出,这无疑便从内部增强了户内之人的向心力。
同时,在争斗的过程中一些户内才干出众的精英人物的出现,也为宗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领导权威阶层。上述蔡氏中捐己资独自承担数回漕运的蔡调九,以及与其他军户构讼的蔡景尚(即参以氏)等人都是其宗族整合中的关键人物,在康熙壬午年(1702)蔡氏修建祠堂中,两人就担任了“督匠事”的职责。(35)黄冈卫军李氏的例子则反映出军户之间因其他原因而发生冲突时同样需要精英人物的出现,据《李氏宗谱》卷首1中李发贵的传记称:
先是,公族有屯粮六石,其田离家居将百里,地名芦洲,皆依堤傍水。同治间议筑堤防,掘压屯田甚多,计粮六百余石,例许减粮二百石。有军户史册芳者,冈邑庠生也,总理堤务,连结数百户,将附近屯粮移派公田,以致压其田而仍其税。公以“办公不公,摊派不平”讼于官。会审之际,合族有退志,公聚族众议曰:“诸公固长者,事至此,退将为害,虽然贵之亲老矣,离家大讼,吉凶不可决,能兼顾乎?试与公等约,贵所不能为者,公等共为之,公等不能为者,贵独为之。”众皆唯唯。公曰:“若然,则赴汤火、蹈油鼎,贵不惧矣。”议毕,慷慨赴郡。抵城甫二鼓,史人侦知之,乘其猝而无备也,赂差役迫公对质,公从容无难色。比登堂,卫督盛气,坐史党六十人,皆缙绅冠带者。爱公者,莫不为公危也。公侃侃陈辨,堂折数十人。督不能屈,以裁田减税结案。后遂无小觑李氏者,由公之先声之夺也。
前已言明,同治年间虽已停漕,但屯田尚未并入州县,此时李氏对于漕运军差仍然心存后怕,对屯田亦保护甚严,因此当“军户史册芳”在修筑堤防时意图“压其田而仍其税”,必然就会遭到李氏的反抗,而在与史氏打官司过程中,同样因为有了李发贵等户内精英分子的果敢,才使得李氏的利益在此次冲突中没有受损。由于李发贵敢于任事,日后被李氏举为户首,并领导户众建祠堂、修族谱,从而成为了宗族的领导人物。
军差的沉重负担还影响到卫所军户与附籍于州县的其他房支之间的关系,对此可从居住在邻邑麻城县的蔡昭卿的后裔不敢与蔡氏军户相往来中窥见一斑。《蔡氏族谱》卷1《蔡氏族谱告成序略》曰:“两邑(麻城、黄冈)境界相连,相距不过三十余里,而子姓之蕃衍,为两邑望族,但昭祖系麻邑民籍,寿祖系黄冈民籍兼领黄卫军籍,麻邑子孙畏军差之累,遂各分户族,不相往来,虽明知为同祖,而且讳其自出,视之若秦越矣。至康熙乙亥岁(1695),黄邑子孙念一本之不可忘,祖茔之不可失,因誓以军差永不扳扯,而麻邑子孙亦知其无累,由是涣者复合,惟辰克父子祖孙,其往来更为密切。”按于志嘉的考证,有明一代附籍于卫所附近州县的寄籍军户对卫所军役仍有帮贴之责,(36)在蔡氏的个案中,附籍于麻城县的昭卿后裔似乎未受军役牵连,并且极力与身为军户的寿卿后裔划清界限。若于志嘉的考证属实,则有可能是蔡氏昭卿一支在明清鼎革之际乘机摆脱了这种军役的牵连,日后对此也不予承认。不过,这里显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即这种血缘关系是虚构出来的,他们之间原本就是军民攸分的两个不同蔡氏宗族。
此种现象在鄂东地区还有他例,光绪十三年(1887),黄冈郑氏宗族在吸收另一属于卫军系统的郑氏时,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据该族谱中“军民辨”载(37):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谓之民,何别之为军?军之说自屯田之制始。由汉以下,明制辨军最详,凡入军者,就卫所旷土,分军以立屯堡,有卫即有屯,大率令兵受田,得屯田者即军,则入军者为军,未入军者民也。吾族籍于黄七百余年,皆民人也。去岁重续家乘,军籍启荣公裔孙有仁、有礼谓:“荣公系为佐公所出,愿附焉。”应曰:“收族之道宜,然恐军民无辨耳,前嘉庆辛未(1811)、咸丰乙卯(1855)两次纂谱,吾先人未采入。”仁与礼曰:“我荣公被明时兵掠入军,受田顶黄卫军屯,名郑张,帮王应轸船,迄今数百年,荣祖名载在版图。累代承顶军者,该荣祖裔孙也,与廷桂、廷佐、为礼、为辅、为弼诸祖支下无与。”即曰:“根本一源,荣祖被兵顶军,军仅自荣祖始,不敢以军而上诬其祖。国朝例载森严,军民必辨,而产业亦不得混,凡祖业门差,属军者,该荣祖支下承当管绍,祖业门差属民者,该廷桂诸祖支下收租管业。我分祖业自荣公始,荣公以上属之民定矣。在后荣祖支下属军,廷桂诸祖支下属民,二比子孙两无异说,可立据。”族人曰:“据所言,合浦可以还珠矣。”于是诹光绪十三年(1887)岁在丁亥季春月望五日,附载荣公于锠祖下,启易洪,有更耀,以归划一,其中派仍其旧,因合立辨以为之据。(38)
很显然,郑氏“被兵顶军”的荣祖支下与其他房分的血缘关系同样有虚构之嫌。
卫所军户与所在州县的民户进行联宗,是其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表现,这一现象姑且称之为卫所军户的“着地化”。明清时期,鄂东蕲、黄两卫的屯田均坐落于数县地方,以蕲州卫为例,其屯田即分布于湖北、江西及安徽等三省,蕲州、广济、蕲水、黄梅、兴国、大冶、德化、瑞昌及宿松等九州县。与之相应,卫所军户的具体生活地点也较为分散,因其世代生活于斯,都已“落地生根”,对于居住地亦有着与周边民户一样的“土著者”心态。由于明初卫军的调动较为频繁,以及之后落居时间不久、其地位可能高于一般民户等原因,明代卫军这种融入当地社会的愿望似乎显得并不十分迫切。到了清代,随着漕运负担的加重,卫军在地方社会中日显另类,因此,趋同的心态促使其逐渐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
很显然,除了“军民攸分”的户籍类别不同之外,卫所军户要想与民户联合以融入当地社会,还需要克服以下两重障碍:其一是当卫军居住地是在卫所治所的邻县甚至是邻省时,如何克服这种行政上的隶属与实际居住地之间的错位;其二是众多的卫所军户是由外地调来本卫的(39),如洪武十二年蕲州千户所改为蕲州卫时,朱元璋就曾“以无粮民丁屯田凤阳者为军以实之”,(40)相对于民户来说,卫军的移民性质更为明显,那么,如何模糊这种移民色彩,或者使两者趋同,亦是其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第一点,由于资料的限制,这里暂先不作讨论。至于第二点,以上蔡氏及郑氏则是利用血缘关系的比附,来达到这一目的。
至迟在清中期之后,鄂东乃至于两湖地区便已流传着元末明初“江西填湖广”的移民传说,与此相同的是,部分卫军亦是在明初鄂东设置卫所时调入本卫的,对于他们来说,与周边民户的主要区别则不在于移民的先后,而仅只是军民户籍的不同。黄冈李氏作为这类卫所军户的代表,在与其他李氏联宗时,就将始祖装扮成“青衿”,以此来模糊卫所军户的色彩,从而弥合了两者之间在血缘关系上的缝隙。此外,亦有一些卫所军户是在此之后调入鄂东卫所的,以前述作为卫军的郑氏为例,则是将其始祖改造为周边土著郑氏一支的后裔,从而实现血缘关系上的比附。
然而,从以蔡氏为代表的卫军,以及以郑氏为代表的民户两方面的表述来看,这一“着地化”的努力由于有军差苦役的阻碍而颇为周折。在清代长期被民户所排斥的环境下,卫所军户只有一方面继续争取民户的认同,如以上蔡氏及郑氏卫军均是在承诺不将军差牵连民户的情况下最后得以完成联宗,而另一方面在一个不被见容的环境中,卫所军户的内部认同感更会得到进一步地加强。
三、结语
明初朱元璋继承元代的户计制度,将民众分立入军、民、匠、灶等不同的户籍类别,且役皆永充,此项举措深刻影响了明清中国社会。以本文关注的卫所军户来说,军户的世袭使得部分家族世代为军,由于清代某些卫所仍因承担运输漕粮的任务而得以保留,这种世袭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晚清光绪年间。一般而言,军户大致可分为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两大类,对于卫所军户来说,由于在营余丁的增多,且都附着在同一个卫军的名下,日后他们逐渐与原籍之间失去联系,因此军差也转而完全由其承担。明代卫军负担似乎并非难以承受,加之国家礼制对祭祀祖先代数等方面的限制,卫所军户进行宗族建设的情况较为少见。
入清以后,漕运负担日渐沉重,开始成为卫所军户难以摆脱的附骨之疽,对此,他们只能联合起来应对军差,于是,军役负担亦成为了其家族形成并发展的最直接动力之一。并且,因为军役的沉重而衍生出来的其他现象,诸如如何在本户内分配军差、分担军役时与其他军户之间的斗争、户内精英阶层的出现,以及不被周围民户所认同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卫所军户家族的形成与发展。
在本户内分配军差方面,卫所军户所采取的措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以黄冈蔡氏为例,首先是按户内不同的房支进行分配,而后因各个房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安排渐趋瓦解,其户内的一位精英人物在自己捐款承担数次之后,开始进行宗族建设,以公产的收入来支撑漕运。为了减轻运军的负担,清廷采取合并漕船及“拨班补运”等措施,但相应地引起了同船军户之间的相互推诿等现象,在与其他军户的斗争过程中,产生了敢于任事的户内精英阶层,他们在整合宗族时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卫所军户因世代生活于斯,还致力于融入当地社会,在清代,即表现为与当地民户联宗,不过由于军役苦差的障碍,使得其努力显得异常艰难,这种长期不被见容的环境同样增强了卫所军户内部的认同,亦对其宗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
国家各项制度的设计都有其合理化的一面,然而当这些政策制度在各地具体落实执行时,却往往因面对各地不同的省情、县情、乡情而产生变异,所谓“活的制度史”研究,意指考察制度与制度的执行之间的差距,以及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由上看来,明清时期卫所军户的演变即远远超出了明初朱元璋的设想,本文正是希望通过以上对卫所军户的研究,来深化这种“活的制度史”研究。
注释:
①张金奎:《二十年来明代军制研究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②谢国桢选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153页。
③(26)(36)于志嘉:《明清时代军户的家族关系——卫所军户与原籍军户之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一分,2003年。
④另外,州县在本地的户籍管理上通常仍然将原籍军户与一般民户分开,对此可参见韦庆远先生关于军黄册与民黄册的讨论,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54-72页。
⑤王毓铨:《明代的军户——明代配户当差之一例》,见《莱芜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⑥参见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及Michael Szonyi(宋怡明).2002,Practicing Kinship: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⑦于志嘉:《再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几个个案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三本第三分,1992年。
⑧参见弘治《黄州府志》卷4《宫室·公署》;光绪《蕲州志》卷7《职官志·武秩表》;《明太祖实录》卷125洪武十二年六月辛已,及卷126洪武十二年八月丙子。
⑨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9页。
⑩(16)《黄冈蔡氏宗谱》卷1《黄冈蔡氏漕务纪略》,民国戊午年九思堂刊本。
(11)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137《兵部二十·军役》,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
(12)(17)封蔚礽:《蕲州志》卷5《赋役志·田赋·军屯附·蕲州卫》,清光绪十年重校本。
(13)徐学谟:《湖广总志》卷30《兵防·戎额》,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19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14)卢希哲:《黄州府志》卷3《官职·职役》,《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15)张萱:《西园见闻录》卷58《兵部五·江防》,民国二十九年哈佛燕京学社印。
(18)在营余丁的说法正是相对于原籍余丁而言的,参见于志嘉:《试论族谱中所见的明代军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2月。
(19)(25)于志嘉:《明代江西卫所军役的演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六十八本第一分,1997年。
(20)甘泽:《蕲州志》卷7《科举·乡试》,《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21)霍冀:《军政事例》卷1《余丁寄籍纳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政书类》(第5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22)潘克溥:《蕲州志》卷5《赋役志·田赋·军屯附》,清同治二年修鋟本。
(23)潘克溥:《蕲州志》卷7《职官志·武秩表》,同治二年修鋟本。
(24)封蔚礽:《蕲州志》卷7《职官志·武秩表》,清光绪十年重校本。
(27)(31)《黄冈李氏宗谱》卷首1《顶充军籍辩》,光绪乙未年务本堂刊本。
(28)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62《题为因灾变思忠豫防以固南都事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9)席书、朱家相:《漕船志》,转引自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22页。
(30)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5-208页。
(32)《黄冈李氏宗谱》卷首1《登仕郎长光公传》,光绪乙未年务本堂刊本。
(33)张金奎:《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4)该族谱(《黄冈蔡氏宗谱》卷1《祭田记》民国戊午年九思堂刊本)云:“一世祖茔,诚佳兆也。湮祀之所需,不可无田。礼云:惟士无田,则亦不祭,而田之祭诚两相需者也……其有军屯详悉开列于左:额军袁三儿屯地三十四厢,坐落杨叶洲,经营袁翼仓云子章,每年贴银八两;徐钦住马家渡口下,每年贴银七两;蔡黄郎屯地,坐落堵城,租银二十两;冯长寿、老冯、贾伏四,坐落麻扬湾、冯家墩、赤山等处,鲁占军承佃,除完堵城本军钱粮五石九斗零外,又除额屯三分钱粮外,实出租银一十三两五钱,有字据;班军李实、李必信等公贴银四两;左应科住巴珂摄湖,贴银四两;曾福住巴河掉军山,曾应三每年贴银二两五钱;官田一住五潼口,钱希贤贴银一两六钱;倪酉儿拔补李五保;公存随船张均保住兴国州,每年贴银十二两,路费一两在外。”
(35)《黄氏李氏宗谱》卷1《祠堂记》,光绪乙未年务本堂刊本。
(37)黄冈《郑氏族谱》卷2《军民辩》,1991年四修,书带堂刊本。
(38)文中“启易洪,有更耀”之语是指辈分字派的合一,即原来的“启”字辈改为“洪”字辈,“有”字辈改为“耀”字辈。
(39)于志嘉曾检讨了前人所谓明代刻意将卫军调离原籍,南北互易的说法,指出明初卫所草创之时并没有统一的安排,其间仍有众多卫军于附近州县服役的情况。参见于志嘉:《试论明代卫军原籍与卫所分配的关系》,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本第二分,1989年;另,张金奎亦有类似的见解,参见张金奎:《明代军户地位低下论质疑》,《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然以上两位学者亦指出,由于明初征伐任务仍然较多,卫军的调动频繁,致使众多卫军的服役地点并非在原籍附近。
(40)《明太祖实录》卷126洪武十二年八月丙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