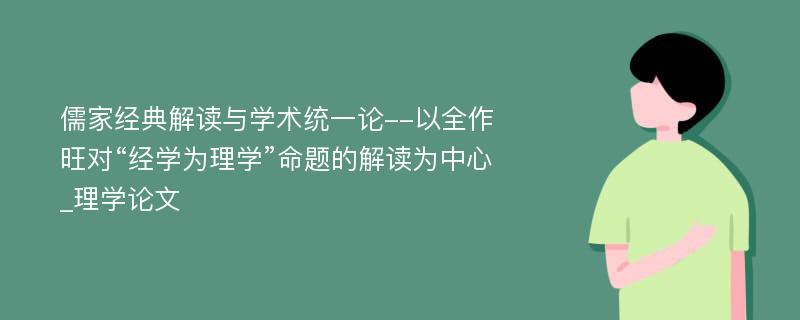
经学诠释与学统观——以全祖望对“经学即理学”命题的诠释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理学论文,命题论文,中心论文,全祖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2-0071-05
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史料与学者的学术观、学统观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其研究结果也很难作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本文所理解的史料是学者研究对象的统称,主要指历史文献典籍。学术观指学者对于学术的态度,主要包括学者的学术宗旨、对史料的态度(主观或客观、严谨或随意)治学的原则、方法等。学统观指学者对自己学派统绪的认定,包括学者的师承传授、所处的立场(心学或理学、古文或今文)等。一般来说,史料是客观的事实,而学术观与学统观则是主观的看法。学术观与学统观可以与史料相一致,即史料可能会支持学者的学术观与学统观。与此相反,史料与学术观和学统观也会有冲突,而且学术观与学统观二者之间也会有冲突。因此,史料、学术观、学统观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本文主要从“经学即理学”命题的形成入手来探讨全祖望的学术观与学统观之间的矛盾。
一、“经学即理学”命题的提出及其影响
当今的许多学术史著作都认为“经学即理学”命题是顾炎武提出的,实际上该命题是全祖望对顾炎武的命题进行修改后提出来的。
“经学即理学”虽然不是顾炎武提出的命题,但是却和他有密切关系。明朝末年,王学末流空言“明心见性”,而不讲求实际学问。“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弥漫整个社会。正如颜元所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对这种空谈误国的弊病,顾炎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中,他这样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顾炎武明确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清谈孔孟”,其观点虽然偏颇,但他这样讲的目的是为了扭转学风。面对学风之弊,他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在《与施愚山书》中他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2]顾炎武认为,“理学”的名称从宋代才有。“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就指的是宋代的理学,是从经学里边提炼出来的。不经过长期的钻研,就不能通达。就如同晋代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中所说“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研究《春秋》一经,需终身而学才能有所得。宋代的理学研究也不能脱离经典,也需终身而学。而今天的经学却不是这样。“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今之所谓理学”指的是明末的王学,已经流入禅学。根本不通读经书,只求助于语录及八股帖括。是一种清谈之学,无根之学。连贯前后文字,可以看出顾炎武对宋代理学是肯定的,而对明末理学——阳明后学,则是批判的。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对空谈心性学风的批判往往明确以时间的限定,如“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3],批判的对象为“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指的是阳明后学无疑。也有明确指明批判对象是王学的,如《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条下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4]钱穆先生在《经学大要》中对顾炎武“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这样来理解:“要读经学才有理学,舍掉经学就没有理学了。粗看这句话好像只要讲经学,不要讲理学,顾亭林是处在反理学的态度。这样说最多讲对了一半……顾亭林是这样的意思,他是反王学,不是反理学。”[5]钱穆先生的理解虽然还受梁启超“舍经学无理学”[6]观点的影响,但他也认为顾炎武是反王学,而不是反理学。可见不能笼统地说顾炎武反理学,也不能说顾炎武是用经学来代替理学。
清中叶学者全祖望在其《亭林先生神道表》中,根据《与施愚出书》中的那段话改写成:“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7]全祖望这段话把顾炎武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改为“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为后人理解顾炎武的思想造成了很大混乱。“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完全抹杀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别。“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否认了理学的独立存在,否认了理学家通过“进学致知”而“上达”“天理”的致思方向,也消解了“天理”的超越地位。“经学即理学”命题为乾嘉汉学反对宋学树立了一面旗帜。
近人梁启超又进一步修改了全祖望“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说:“炎武未曾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独立”,“‘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8]梁启超根据全祖望“经学即理学”命题,进一步曲解为“以经学代理学”,更是错上加错。甚至他把全祖望的观点强加在顾炎武的头上,他说:“顾亭林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9]由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巨大影响,使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普遍认为,顾炎武是既反程朱,又反陆王的反理学思想家。
当代台湾学者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就沿袭了梁启超的观点,他在该书中这样说:“亭林对宋明儒学之理论及其流派,皆无明确了解,然其反对‘理学’及‘心学’则是一明确态度”,“亭林以为‘理学’应以‘经学’代之,此是人所常言者”[10]。这和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最近研究顾炎武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吴长庚认为顾炎武“黜(宋明)理学,尊(汉唐)经学”[11],张敏、李海生认为顾炎武“高扬反理学大旗”[12]。当然也有与此不同的观点,如龙飞认为顾炎武“并不是理学的反动者,而是理学的实践者”[13],陈国庆认为顾炎武“既不属于汉学也不属于宋学,对汉学宋学既有兼采,也有批评”[14]。可见,对“经学即理学”命题与顾炎武思想关系的辨析是十分必要的。
二、全祖望命题与顾炎武命题的异同
由以上辨析可知,“经学即理学”是全祖望提出的命题,与顾炎武的本意还是有不少区别的。下面我们比较一下顾炎武的命题与全祖望命题的异同。为方便讨论,我们把顾炎武的《与施愚山书》和全祖望的《亭林先生神道表》中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中的表述:
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15]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中的表述:
(顾炎武)最精韵学,能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黄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于同时诸公,虽以苦节推百泉、二曲,以经世之学推梨洲,而论学则皆不合。其书曰《下学指南》。或疑其言太过,是固非吾辈所敢遽定。然其谓经学即理学,则名言也。[16]
比较以上两段文字,可以看出顾炎武和全祖望都提倡两汉经学务实的学风,主张改变宋明理学的学风为两汉经学的学风。虽然全祖望对顾炎武的命题有所修改,对顾炎武批评阳明心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但对顾炎武的学术主旨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他认为顾炎武所说的“经学即理学”命题,是“名言”。可见对于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全祖望是认同的。
但是两段文字的差别也还是明显的,全祖望与顾炎武不同的主张反而是通过借助顾炎武之口表述出来。《亭林先生神道表》中有这样一句话“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全祖望借顾炎武之口所表达的观点却与顾炎武的实际主张差别较大,主要表现为二者批评的对象不同、目的不同。顾炎武在《与施愚山书》中把“古之理学”与“今之理学”作了鲜明的对比,其目的在于批评“今之理学”,即阳明“心学”的空疏学风,倡导“古之理学”,即“经学”的务实学风。而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则隐去了“古之理学”与“今之理学”的对立,以“经学即理学”来概括顾炎武的学术主张。批评的对象则是整个理学,认为“舍经学而言理学”,即是“禅学”。其目的在于倡导用经学来取代理学。前者侧重于“破”,后者侧重于“立”。由此不同,我们可以看出全祖望的表述实际上是混淆了理学与心学的区别。
在《与施愚山书》中,顾炎武对心学的批判是很严厉的,认为“今之理学”就是禅学。而全祖望认为顾炎武对心学的批判“甚峻”,其言“太过”。全祖望也借顾炎武之口说明了心学流于禅学的弊端在于“舍经学以言理学”,但批评的意味要淡得多。“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其语气更多的是对心学流于空疏学风的遗憾。《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对顾炎武和心学都有所批评,而“经学即理学”命题则是全祖望折衷的结果。从这一命题我们看不出顾炎武对心学的严厉批判态度,给读者提供的信息是:经学就是理学,不必再讲其他的理学,要恢复传统中的经学。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导向无疑是正确的,对以后乾嘉考据学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乾嘉学派推崇顾炎武为始祖,与全祖望的提倡是分不开的。从《与施愚山书》中也可看出顾炎武的学术宗旨是明道救世、通经致用。顾炎武对当时空疏的学风进行严厉的批评,对心学束书不观的流弊深为痛恨,其目的还是为了扭转一世学风,倡导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使学人的研究中心从宋明理学转向两汉经学。这不仅是全祖望的观念,也是顾炎武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学即理学”命题与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并没有偏离太远。这一命题不仅是全祖望学术观的流露,也可能是当时进步学人的普遍观念,即要求由宋明理学转向两汉经学。正因为这一命题符合了当时学风的发展要求,它才会在以后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全祖望“经学即理学”的命题与顾炎武的学术宗旨仍然是有一定距离的,特别是它掩盖了宋明学术内部理学与心学的区别,未能突出晚明心学空疏学风的流弊,这一点恐怕是与顾炎武的本意不相符合的。
三、全祖望为何要改顾炎武的命题
全祖望为何要改顾炎武的命题呢?这与全祖望的学统观学术观是分不开的。
从学统上来看,全祖望无疑属于浙东学派。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这样讲:“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17]。章学诚认为顾炎武是“浙西之学”,在学脉上归属于朱熹理学。而把全祖望归为黄宗羲所开创的浙东学派,在学脉上可以上推王守仁、刘宗周以至陆九渊的心学流派。
全祖望自己也认同于浙东学派。他虽然没有受业于黄宗羲,但他“私淑梨洲”,可以认为是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虽生于黄宗羲死后十年,但他私淑梨洲,与万氏兄弟确有渊源。他们在学统上一脉相承,显然属于一个学派。”[18]由此,可以把全祖望归为浙东学派。
从学术观来看,全祖望也继承了浙东学派“博洽”的特点。浙东学派具有规模宏大、兼容并包的气象,以经史见长。全祖望也继承了这些优良的传统,少有门户之见。在这种学术观的基础上,全祖望确立了他治学的原则。王永健先生把他的治学原则总结为三条:“第一,谢山治学力主‘荟萃百家之言’,反对墨守一家坚僻之学者”;“第二,推崇‘经世之学’和‘救弊之良药’,抨击迂疏陈腐之论”;“第三,论人之学重视人品,敢于标新立异。”[19]
由此,我们对全祖望的学统观与学术观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一般来说,学统观能影响甚至决定学术观,如全祖望也继承了浙东学派“博洽”的特点。但任何一个学派都有它的宗旨,认同这个学派的个体也必然会回护、坚持这个宗旨,而不可能不考虑他的“门户”,虽然他主观上也确实没有“门户之见”。全祖望“没有门户之见”的学术观与他的学统观不可避免会有矛盾和冲突,而“经学即理学”命题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我们再来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中对顾炎武的评价。这段话大概讲了四层意思:第一,顾炎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音韵学和经学;第二,顾炎武的学术主张是“经学即理学”;第三,顾炎武的学统本于朱子;第四,顾炎武对心学的批评是不恰当的。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全祖望先是对顾炎武的学术贡献和学术主张进行褒扬,接着却是对顾炎武“今之理学,禅学也”命题的委婉批评。全祖望认为顾炎武之所以批评心学是因为他接替了朱子、黄东发一系的学脉,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其言太过”。虽然全祖望也十分尊重推崇顾炎武,虽然他也谦虚地说,对于顾炎武“固非吾辈所敢遽定”,但实际上他还是对顾炎武进行了批评和论断。那么,全祖望又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批评和论断?为何又要修改顾炎武的命题为“经学即理学”呢?原因就在于他的心学立场与学术观的冲突。毫无疑问,全祖望是站在心学的立场上作出那样的评价的。一方面,全祖望非常注重表彰顾炎武这样的“明季忠义”,也认同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另一方面,全祖望他也认同自己的心学立场,私淑梨洲,上承陆王。当顾炎武批评阳明心学为禅学时,当自己的学术观与学统观矛盾时,全祖望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忠于事实,要如实地反映顾炎武的学术观;另一方面,又不能表露出顾炎武批评心学的态度。这对于作为经史学家的全祖望来说,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权衡的结果就是全祖望修改了顾炎武的命题,隐去了“古之理学”与“今之理学”的对立。而且针对顾炎武对心学的批评,全祖望站在心学的立场上也对顾炎武进行了委婉的批评,这种批评可能是不情愿的,但又是不能不做的。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全祖望是顾炎武的私淑弟子,认同于理学的立场,则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多费周折,按照顾炎武的原话如实表述就可以了,不必要煞费苦心地对顾炎武的命题进行修改和变通了。可见,“经学即理学”命题是全祖望学统观与学术观矛盾冲突的表现,是全祖望经过权衡后折衷调和的产物。
四、余论
在学术史上,象全祖望遇到的这种两难选择的例子并不少见。学者研究的史料与他的学统观学术观往往会有冲突。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学者可以回避这些史料,只采取能支持自己观点的史料。但有些史料是不能回避的,比如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记录与评价。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就处于两难的境地,其结果往往是修改了这些史料。
《论语·述而》记载了这样一段材料: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鲁昭公娶同姓吴孟子为夫人,显然是非礼的,但孔子为什么还要说昭公知礼呢?
我们再来看《春秋》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春秋·哀公十二年》经文有这样的记载:“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春秋公羊传》对此段经文的解释是:“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
吴国与鲁国同属姬姓,鲁昭公娶吴女是非礼的。《公羊传》的作者明白这一点,孔子也并非不知道。经文之所以简略地记为“孟子卒”,书孟子不书夫人,甚至也略去吴字,书卒不书薨,都是因为孔子要为尊者讳。由《论语·述而》和《公羊传》对同一史实的不同记载,我们可以推断,《春秋》经文“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一定是经过孔子修改了,可能删去了昭公娶同姓吴孟子的基本史实。但是处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又不能明说君主非礼,所以《春秋》在记载这段史实的时候,孔子就用了“曲笔”。《论语·述而》中孔子的回答很能说明孔子的两难处境。当巫马期把陈司败说的昭公娶同姓吴女的事实告诉孔子时,孔子仍然没有直说昭公不知礼,而说是他自己说错了。因为他不能说他自己隐讳了国君之恶,也不能说娶同姓为知礼,所以他只能说是他自己错了。
在《春秋》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史记·孔子世家》所说:“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20]我们不必相信《春秋》的每一句经文都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但如果相信《春秋》记载的全是史实,那就错了。
与此相类似,王夫之在《尚书引义》中也有修改经文的例子。在其中的《旅獒》篇的开头这样说:“老子曰:‘轻为重根,静为躁君’。惟其然也,故乐观物之‘妙侥’而聊与玩之。以轻为根,以静为君,其动以弱,其致以柔;以锐入捷出之微明抵物之虚而游焉,良可玩也。”[21]其中王夫之引用了《老子》的话“轻为重根,静为躁君”,但这句话在《老子》通行本中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王弼的《老子》注本很早就流行,王夫之这样的大学问家所引用的版本不可能错,而最大的可能是王夫之把“重为轻根”改为“轻为重根”。那么,王夫之又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王夫之修改《老子》经文也是为他写作的目的考虑的。《古文尚书》中《旅獒》一篇的本义主要是召公劝谏武王要慎德重贤,不可玩物丧志。而王夫之《尚书引义》中的《旅獒》篇则是主要批评道家的态度也是玩物丧志。王夫之认为君子应该刚健有为,以心志作为根本,率志治物。而道家却以柔弱清静为根,“逃虚择轻”,逃避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心役于物。王夫之批评道家“逃虚择轻”,而《老子》中“重为轻根”显然不能支持他批驳的论点。当史料不能支持他的论点时,他的选择是修改史料,把“重为轻根”改为“轻为重根”。
其他的例子也还很多,如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把孔子列入《世家》,显然与他自己编写《史记》的体例不符。朱熹为《大学》补“格物致知”一章,与《大学》的本意很难契合,也与朱熹一贯严谨的学风不相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经文不合己意而宣布经文为伪造。这些都体现了史料与学者学统观学术观的矛盾。
本文主要探讨了“经学即理学”命题与全祖望学统观学术观的矛盾,这绝不是一个特例,在学术史上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我们今天研究前人的思想也是有重大启示的。最起码可以引起我们以下两点思考:第一,史料不可能完全客观,即使被认为是权威的史料;第二,要了解作者的学术观学统观,即“知人论世”。我们不必相信史料中一定有作者的“微言大意”,但就作者对史料的取舍中一定蕴含有作者的情感态度,了解这种情感态度会加深我们对史料的理解。
收稿日期:2011-10-24
标签:理学论文; 顾炎武论文; 儒家论文; 亭林先生神道表论文; 经学论文; 全祖望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心学论文; 论语·述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