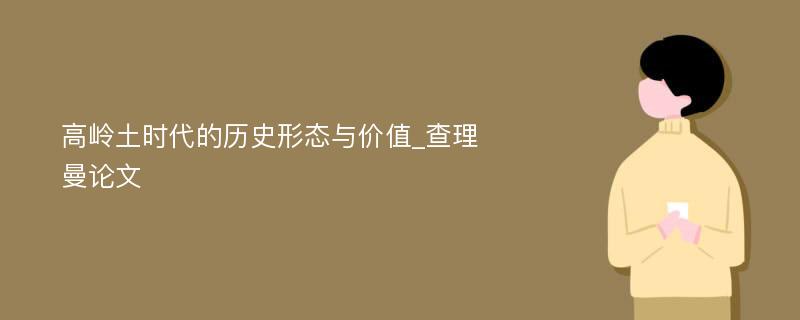
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形式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林论文,史学论文,形式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2)09-043-051
一、传记体的历史价值
在加洛林时代,无论是教会还是世俗,史学的旨趣都发生了转向。从教会的角度而言,教父时代所着重的是构建基督教的教义理论、驳斥基督教内部出现的异端倾向以及确立以基督教纪年为主线的历史结构。但是历史发展到加洛林时代,随着蛮族在罗马的废墟上建立国家并立稳了脚跟,基督教会的任务发生了转变,它主要的工作是教化蛮邦,并与新兴的世俗国家结合。在这种新形势下,所需要的不再是满腹经纶、学问高深的教父,而是深入民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奇迹感动民众的圣徒。在世俗层面,蛮族王国经历了一个从混乱走向统一的历程,其间的兴起和衰落、纷乱和整合、战争与建设,都需要英雄般的人物引领潮流。因此,那时人们都相信是贵族的事迹和虔诚人物的功绩塑造了世界。反映在历史的编纂中,这一时期人物传记体的历史非常流行,君主、修道院长、主教和圣徒不仅成了历史的主角,而且成为历史的主线,各种事件的进程都围绕着他们展开。
圣徒传的流行是宗教传播兴盛、基督教徒数量日益增多的结果。由于当时社会需要的不是独特性而是代表性,所以圣徒传的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带有模式化的特点。“圣徒的年轻时代要么是异乎寻常地虔诚,要么有很大的缺陷,直到皈依基督教而改变了一切。他们行使奇迹并忍受苦难;死后他们的尸体会保持不朽。人们并不介意这种类似性,因为这些传记所希望呈现的不是新奇的故事,而是典型性地体现此世的圣徒。”[1]98阿尔昆的《威利布劳德传》(Life of Willibrord)以及威利巴尔德(Willibald)的《博尼法斯传》(Life of Boniface),都是当时圣徒传的代表。
圣徒传的写作方式与一般的传记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传记的选材和和所要勾勒的圣徒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和人们在圣徒身上所寄托的理想,因而也构成了独特的模式化的特点。在他们的笔下,一位圣徒一般都具备三个特点。
首先,圣徒一般都出身非凡。阿尔昆在描绘威利布劳德的出生时说,他的母亲在深夜熟睡时梦见一个幻象:“她似乎看到了一弯新月,正当她观看时,新月慢慢增大并变成了满月。当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时,这轮明月快速掉到她的嘴里,吞咽了月亮后她的胸中充满了光”。一位教士对此的解释是:“这轮明月是她那晚所怀的孩子。他将用真理的光芒驱散错误的暗夜,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展示天国的绚丽和满月的完美。”[2]Chap.1.在威利巴尔德的笔下,圣人博尼法斯在四五岁的时候便“有了侍奉上帝的渴望,并开始深深地思考修道生活的益处。甚至在这么小年纪的时候,便弃肉体而趋精神,深思永恒事物而非易逝的东西”。[2]Chap.2.他的父亲虽然对他百般溺爱,但是不能忍受他有这样的想法,于是用世俗的欢乐、财产等引诱他,劝他回心转意,但博尼法斯意志坚决。他的父亲最终生了一场大病,无奈之下将他送进了伊克萨姆切斯特(Examchester)修道院,于是他“诀别了世俗之父而投入救赎的养父怀抱”。[2]Chap.1.
其次,这些圣徒都为传播基督教、教化异邦作出了重大贡献。加洛林时期,正是政教结合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教会借助世俗权力推广基督教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为传教而四处奔波的教士和僧侣,其中的佼佼者便成为人们颂扬的对象。在阿尔昆的笔下,威利布劳德很早就进入了修道院,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播教义,他渡海来到欧洲大陆,得到丕平等世俗统治者的欢迎,由于他传教很成功深得丕平的尊敬。他还亲自前往罗马拜见教皇,在罗马受到了热情的接见,并被授予了大主教一职。此后,他从罗马返回继续传播福音的事业。在欧洲北部,他的传播事业获得了很大成功。他不仅在法兰克王国的边境内传教,而且越过边境,尝试将福音传播给仍为异教徒的弗里斯兰人和丹麦人。但由于这些人“野蛮如野兽,顽固如磐石”,所以成效不大。此后他全身心在法兰克境内传播福音,“每天都有新的进展”。丕平死后查理继位,弗里斯兰人被纳入了法兰克王国,而威利布劳德又被委以重任,负责在弗里斯兰人中间传教。这一次,他“不容许忽略任何错误或过去的无知,在撒播福音之光方面也不浪费任何时间”。[2]Chap.13.
同样,博尼法斯也是在虔诚和传道中成就了自己的名声。作者说他严格按照教规原则来要求自己,“他总是在夜祷前几个小时就起床,勤奋地进行祈祷活动。愤怒不能削弱他的耐心,狂暴不能动摇他的忍耐。在他的纯洁面前欲望无能为力,美食不能破坏他的节制”。[2]Chap.3.教皇派遣他到还未皈依的日耳曼人那里传教,于是他遵命前往巴伐利亚和弗里西亚等地传教。他到处奔走,传播福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就像忙碌的小蜜蜂,煽动着柔软的嗡嗡响的翅膀,轻快地掠过田野和草地”。[2]Chap.5.在这期间,他还主动帮助当地的大主教威利布劳德履行宗教职责,但当威利布劳德举荐他担任主教时,他以一贯的谦卑态度拒绝了,而再度投身到使异教徒皈依的事业中。最终,博尼法斯和他的门徒们在一次传道中营地遭到异教徒的攻击,死于异教徒的屠刀之下,成为殉道者。
最后,圣徒们异于常人的地方是他们的一生都充满奇迹。阿尔昆记述了威利布劳德的许多奇迹:不信教者用剑攻击他,但在上帝的保护下,他毫发未损,打人者后来却被魔鬼抓住,下场悲惨;一位土地主阻止这位圣人穿过自己的玉米地,但却突然死亡;在旅途缺水同伴干渴时,他依靠祈祷获得了清泉;他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水瓶给干渴的乞丐们喝,但水瓶中的水却始终不会减少;一个人因侮辱这位圣人而无法饮水,后因向这位圣人表示悔改而康复;他用祝福过的水治愈了修女们的瘟疫……在完成了传播福音的大业后,他与世长辞。即使死后,他的尸体也是奇迹不断,治愈了患各种各样疾病的人。
在上述的圣徒传中,作者勾勒了作为圣人的典型形象:他们出身不凡,有坚定的信仰,在传播福音方面有坚定的毅力,更重要的是,其一生伴随着奇迹,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所向披靡。我们不用去追究作者描绘的内容是否真实,因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将其描绘为传播宗教的教会人士的典范。就所叙述的历史事实而言,圣徒传可能有许多虚构,但是,它们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在法兰克王国,尤其是丕平和查理曼时期,传播福音推广基督教是当时仅次于战争的重大事件,信仰的统一是王国巩固的主要手段。正如泰勒所言:“修道式基督教最高尚的情感就是为了基督而游走,在异教徒中间传播信仰;这一基督教历史中最有趣的片段,是其领导者们四处漫游,进行传道和创设传道团体的故事。”[3]这种历史环境为圣人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反过来圣徒传无论从时代情感的表达上还是事实的叙述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除了圣徒传之外,传记体的另外一个重要类型就是著名君主的传记,描绘社会转型和中世纪文化生成时期世俗君主的作用。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和阿瑟(Asser,约去世于908/909年)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传》。
历史学家们对艾因哈德及其《查理大帝传》给予了高度赞扬,说他是该时期最著名的和最有能力的传记作家;他的《查理大帝传》是整个中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传记;说他在作品中追随古典的表达方式,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超越了其他早期的中世纪历史学家;称赞他的著作在各个方面都是价值不可估量的历史文献。[4]
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在结构上明显受到苏埃多尼乌斯(Suetonius)《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的影响。他首先描绘查理曼的事迹,然后描绘查理曼的性格。并没有如当时流行的传记那样,把查理曼描绘成神,而是将他描绘成一个如罗马皇帝那样的世俗国王。
艾因哈德详细说明的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查理曼的世系以及他如何成为国王。然后,《查理大帝传》用了很长的篇幅关注查理曼在军事上的勇敢。从第五章开始,艾因哈德描绘了阿奎丹战争以及查理曼如何将他父亲的事业进行到底,而且对此“充满了精神”。他接着描绘了查理曼如何得到了当时正遭受伦巴第人攻击的教皇的帮助。在此,他说,查理宣战后,永不停息,直到通过长期的围攻后耗尽了国王狄塞德留的精力,并迫使他无条件投降。这是查理曼在战争方面坚忍不拔和富有作战技巧的另一明证。作者花大量的时间描绘查理曼所从事的战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为王国增加了多少土地,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观念:加洛林社会不仅强调权力,同时也能够积极地展示军事力量。在描绘每一次战役时,查理曼总是被描绘为可怕的和不屈不挠的勇士,对手不投降,他永远不会停止攻击。“在他所努力争取的目的完全达到以前,他怀着不屈不挠的毅力,既不间断,也不松懈。”[5]9查理曼不仅因为作为军事指挥官的能力而备受赞扬,也被赞誉为一位勇士,能够忍受与萨克森人战争中的各种艰苦。这充分强调了加洛林社会不但重视军事上的勇敢,也能够忍受随战争而来的各种艰辛。
除了表现查理曼能够运用军事力量和使用权力外,艾因哈德也表现加洛林时代柔软的一面,这凸显在他的仁慈和重视教育方面。仁慈是查理曼整个肖像中关键的特征。艾因哈德描述说:“由于他在友情方面具有一种高尚的品格,他很容易接受友谊,并且忠实地保持它,他对一切列在朋友范围以内的人,都尊重到极点。”[5]24同时,艾因哈德表现了查理曼对教育的重视,认为他的孩子们必须接受“文科教育”。他对教授各科的人极为尊敬,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为了学习书写,他以身作则,常常把用来写字的薄板和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头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刻使自己习惯于写字。在当时的时代,虔诚也是不可缺少的品格。在艾因哈德的笔下,查理曼是一个圣徒般的国王。他从小在宗教生活中长大,对基督教极为热诚和虔信;说他只要健康许可,在清晨、傍晚、夜间和献祭的时候,经常到教堂里去;他还热心于救济困苦,发放救济金或救济物,怜恤任何贫困的基督徒;说他爱罗马的圣使徒彼得的教堂超过一切神圣和可敬的地方,向这所教堂的库藏输送了大量的金银、宝石等。
在艾因哈德眼里,查理曼是一个完美的人,作战勇敢、坚忍不拔、注重友谊、爱护家人、注重教育、信仰虔诚。他对所记述的主人公没有任何怀疑,唯有极力赞扬。所以他的描绘方式也经常遭到后人诟病,认为他太盲目地模仿苏埃多尼乌斯,把查理曼完全描绘成了罗马帝王的形象,其次,他出于某些原因粉饰或者完全忽略了查理曼国王早期的不名誉的行为;最后,为了宣传加洛林王朝,强调加洛林时代的光荣,艾因哈德极力抹杀墨洛温时代及其统治者。当然,考虑到艾因哈德作为查理曼同时代的人,又是查理曼的宠臣,要求他非常客观地评判自己所经历的那段历史,未免有些苛求。
无独有偶,阿瑟的《阿尔弗雷德大帝传》也是当时帝王传记的代表性作品。作者在传记中赞美他近乎十全十美的特性,“他的父母甚至所有子民对他的宠爱,超过他的所有弟兄,而且他在王宫里接受了全面的教育。他度过了婴儿和青少年时代后,长得比所有弟兄都更加英俊;无论言谈举止都超过他们。从摇篮开始就植入他身上的高贵性,使他热爱智慧超过一切”。[6]Part Ⅰ在作战方面阿尔弗雷德同样勇猛异常。阿尔弗雷德继承王位后,独自承担起反对抗丹麦入侵的重任。但他接手时,正是丹麦人进攻最为猛烈的时期,而撒克逊人的士兵却数量很少,因为“一年经历了8次对抗异教徒的战争,撒克逊人已经筋疲力尽”。但阿尔弗雷德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与丹麦人周旋,“与异教徒打了许多次战役,获得许多次胜利”,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王国。作者还把阿尔弗雷德塑造成一位虔诚的国王,非常注重探讨和抄录圣经的内容:“他像最勤劳的蜜蜂,飞到东飞到西,询问问题,最后他热情地和不停顿地收集了圣经的许多花朵,他用这些东西丰富了自己的内心”。[6]Part Ⅱ不仅如此,在编纂了圣经摘录后,他将其翻译成撒克逊文,并教授其他人。不仅如此,他还大力兴建修道院,促进慈善事业。
基于当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作者还是把阿尔弗雷德国王塑造成一个圣徒般的形象,并不时地强调神意在指导历史中的作用,这同样反映了当时人们在中世纪时期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的思维方式,无不受到基督教影响的时代特征。
总起来讲,这一时期的传记对所叙述的对象充满了溢美之词,而且将他们描绘成完美无缺的楷模。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虚构的成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它们的历史价值。因为它们在另一种意义上都很好地保存了历史,尤其是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的情感以及僧俗两界的英雄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二、年代记:历史记录的新方式
加洛林王朝时期,具有中世纪特性的年代记开始出现。之所以说这时候的年代记具有中世纪特性,是因为年代记并不是到了此时才有的。罗马时期就有年代记,大祭司用它来记录重要的公共事件和行政官的名字。早期的基督教的年代记,主要记录某些宗教仪式的确切日期。中世纪的年代记并非对原有年代记的继承,而是有自己独特的起源和特点,它主要起源于复活节表。复活节表之所以必要,并不是说复活节比任何节日都更重要,而在于复活节日期的特殊性。比如,圣诞节纪念耶稣的诞生,其日期是固定在12月25日。但复活节却是不固定的节日,需要计算,但到底如何计算,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早期基督教会有许多不同的复活节日期而且有许多不同的证明方法,比德在他的著作中就表明了当时英国教会和罗马教会计算复活节日期方法的不同。由于不同复活节计算方法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在此一一详述。但为了准确地了解复活节的庆祝日期,有必要事先构建一系列的复活节的表格,这样才不至于把庆祝复活节的日期搞错。这一系列推算时间的表格,就是中世纪年代记的雏形。
复活节表并不必然就是年代记,但是这些年表提前数年就确定了复活节,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日历的模样。也同现代人使用日历一样,那时的人们也特别喜欢在时间的间隔处和空白处记录某些重要的事件。这样,日期和所记录的事件自然结合,就成了新型的年代记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
这种年代记的历史记录方式并不是历史编纂者们有意创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因而它也具备了独特的特点。首先,年代记的基本格局是一边是耶稣纪年和复活节日期,一边是所谓的历史记录,对应每一年的记录可以是一个事件也可以是多个事件。即使没有任何事件记录,年代的连续性照常继续,是事件依附于年代,而不是年代依附于事件。其次,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无论重要与否,基本上都是非常简单的,各行之间的空间和边缘的宽度决定着它必须简洁。第三,由于这种年代记的编写最初往往是无意的,因此,时间和相对的事件本身经常会出现无法对应的情况,如果后来的人以此作为素材进行传抄,容易产生错讹或误抄。另外,年代记常常把大事和小事混杂在一起,没有什么重点或非重点之分,也没有什么分类。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往往批评他们缺乏历史意识,其实这也是后人对他们的误解,因为“年代记作者只是满足于描绘那一世界,而拒绝这样的观念,即平凡的现象经过他们精挑细选,可以产生意义,出现解释和发展的意识。上帝的命令统领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秘密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对各种事件的记载,除了告诉发生了什么,还包含着给人类的神圣信息。一次地震或一群蝗虫是警告人们,一则幻象则会唤起希望,个人的命运则提供教训”。[1]102
我们看一下《圣高尔年代记》的片段,对这些特征就会一目了然。如709年,严冬,哥特弗雷德伯爵去世;710年,灾年,庄稼歉收;712年,洪水肆虐各地;714年,丕平宫相去世;718年,查理践踏摧毁了萨克森;720年,查理与萨克森人战斗;721年,修德将撒拉逊人赶出阿奎丹;722年,庄稼丰收;725年,撒拉逊人首次前来;731年,受祝福的比德主教去世;732年,查理星期六在普瓦提埃与撒拉逊人战斗。[7]
在这个片段中,我们看到,时间的排列非常整齐,但时间旁边所记载的事件却是断断续续的,有许多时间旁边是空白,没有任何事件。这充分说明,在年代记中,时间先于事件而存在。同时,在所记述的事件中,无论是主教去世、重大战役还是灾荒都不加区别地并列在一起,而且就连查理曼与撒拉逊人战斗这样重大的事件都是一句话带过,没有详细的细节,也没有任何评论。尽管年代记谈不上成熟的历史,但是年代记在发展非常充分的时期,它也以其简洁和便利而记录了许多当时的历史事件,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许多一手材料。这反映在《圣高尔的年代记》(Annals of St.Gall)、描绘查理曼时代的《大洛奇年代记》(Greater Annals of Lorsch)以及续编到829年的《法兰克王室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富尔达年代记》(Annals of Fulda)、《圣波尔廷年代记》(The Annals of St.Bertin)等诸多年代记中。
《大洛奇年代记》是有关法兰克历史的年代记,涵盖的历史时期从703年到803年,并附有简短的前言。785年以前的条目是在洛奇修道院里写就的,剩余的年份则构成独立的素材。这部作品在开篇的前言中描绘它的时间结构,吸收了奥罗修斯《反异教史七卷》的设计,认为从创世到耶稣诞生为5199年。正文则使用公元系统来记录事件。最初的65年(703—767)是用散文方式进行叙述,并没有划分出一年一年的条目。从768年岁开始,该年代记划分成章节,每一条都单独成行。手稿中还包含着从777年到835年的日历,这显然是为了推导复活节。洛奇年代记最后记载,802年查理曼宫廷接受了阿布·阿拔斯送来的大象。803年查理曼在亚琛度过了复活节,在美因兹召开了会议,全年没有进行战争。年代记至此结束。在这部年代记中,对两个重要事件的描绘经常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所引用。一个事件是关于矮子丕平如何以宫相身份取代墨洛温王朝而自立为王,从而开启了加洛林王朝的历史,以及丕平如何与教皇结盟,从而巩固了教会和法兰克的关系。另一个是关于查理大帝的加冕。据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记载:由于罗马人残酷迫害利奥教皇,于是他到罗马使惨遭破坏的教会制度得到恢复,并在那里度过了冬天。就在那个时候,他接受了皇帝和奥古斯都的称号。查理曼非常不喜欢这种称号,并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4]30这样的描述暗示说,查理曼根本不知道利奥三世教皇打算在800年的12月25日为他加冕。而《洛奇年代记》则提供了与此相矛盾的记载,这也是迄今所见唯一提供矛盾记载的原始素材。洛奇编年史中描述说,在查理曼达到后罗马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此进行讨论,讨论日期是11月30日或12月1日。这一条是在查理曼801年返回法兰克后计入的,因为799年的条目记录了阴谋推翻利奥的阴谋家们被流放。这些人最终被流放是在801年早期。这种记载与艾因哈德所描述的查理曼根本不知情的说法是相冲突的。冈绍夫认为年代记的记载比艾因哈德的记载更加可靠。
《法兰克王室年代记》所涵盖的是加洛林早期君主的历史,时间从741年到829年。这部年代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查理曼对萨克森的战争,并描绘了丹麦人对法兰克的入侵。以针对萨克森人的战争为例,书中讲到查理曼数次对萨克森人进行征服,萨克森人数次屈服而又反叛,因此战争不断反复,异常复杂。它讲述了775年查理曼召开会议决定对萨克森人进行攻击,尽管萨克森人进行了抵抗,但是在上帝的帮助和法兰克人的努力之下,萨克森人最后四散而逃,许多部落都向查理曼表示效忠,并提交人质。当萨克森人再次进行反叛时,查理曼毫不留情地继续派军队镇压,大量屠杀了萨克森人,并且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776年,在查理曼到意大利平定了伦巴第人的叛乱后,萨克森人再次叛乱,并攻击法兰克人的城寨。但是,上帝始终眷顾法兰克人。书中讲述某一天,当萨克森人准备攻打法兰克人的兵营时,许多人看到,在建有教堂的那座建筑之上显现了上帝的荣耀。他们看到了两块盾牌的形象,盾牌呈红色并燃烧着火焰,在教堂之上来回移动。当那些异教徒看到这一标志后便马上大乱,在极度惊恐中逃回到自己的军营。由于极度恐惧,他们甚至自相残杀。此后,随着查理曼带领军队攻破他们的防线,萨克森人彻底投降,答应接受基督教并臣服于法兰克人。这部年代记不但记录了当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而且为以后的年代记编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以记录西法兰克历史为主的《圣波尔廷年代记》继续延续了这部传记,而以记录东法兰克历史为主的《富尔达年代记》的早期编辑者们大量借用了这部著作的内容。
《圣波尔廷年代记》是关于加洛林后期法兰克的年代记,因为发现于圣波尔廷修道院而得名。其内容所涵盖的时期是830—882年,正好接续了《法兰克王室年代记》的内容,是有关9世纪法兰克的重要资料,尤其它是详细记载了秃头查理时期西法兰克所发生的事件,正好与反映东法兰克历史的《富尔达年代记》相呼应。年代记所叙述的内容大部分是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教皇的信件和各种会议记录。该年代记最具特色的,是密集地记载了来自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维京部落的攻击。在9世纪,维京部落沿着塞纳河、洛尔河和莱茵河上溯,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并劫掠了加洛林修道院。当时修道院有大量的不动产,而且当国王们与维京人达成和解协议需要支付款项时,往往由修道院支付账单。在841年之后,只有874年和875年没有相关的维京人活动的记录。该年代记还特别记载了一个叫做罗斯(Rhos)的维京人部落,这是有关该部落的最早记载。该部落可能是早期俄罗斯人。据年代记记载,这些人在838年访问了君士坦丁堡,由于返程时害怕遭到马札尔人的攻击,他们与拜占庭的使节一起出发,希望得到法兰克的同意途经德国返回。在国王的皇家驻地,“当皇帝仔细询问他们前来的原因时,他发觉他们属于瑞典民族”。[8]
从上面所列举的加洛林时代的重要年代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年代记的一些特点。首先,年代记基本上不是官方所编纂的历史,而主要出自个人或民间,而且主要的编纂者基本上都有教会背景。之所以如此,当然同当时教会人士是社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阶层有关,也同教会普遍认为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上帝的启示有关,跟同年代记起源于复活节表的现实有关。其次,我们看到年代记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的年代记基本上是在时间表上简单记事,继而叙述的事情越来越多,每一事件的叙述越来越详细,年代记也就从一个基本上不具备历史功能的形式变成了书写历史的重要形式。另外,年代记的事件记录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很少有对事件本身的评价。尽管不同的作者可能记述的重点不同,但是很难看出个人的观点和倾向性。也正因如此,一部年代记可以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完成,而且一部年代记可以完全照搬与其所记载年代重合的其他年代记的内容,不做任何变更或批评。尽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年代记缺少了历史的批判精神,但是它们仍然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些看似零散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加洛林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其按照年代顺序记述的方式,对我们复原当时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了解历史转折时期关键事件的作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它不加分类、事无巨细兼收并蓄的风格,为我们了解当时多面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场景。
三、编年史:多视角的欧洲历史呈现
加洛林时期不但出现了年代记这样的编纂历史的形式,而且也广泛出现了编年史的题材,并出现了大量的著作,全面反映了当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历史。
编年史题材也不是加洛林时期的创造,因为在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编年史,如攸西比乌斯、奥罗修斯等的编年史。就本质上而言,基督教的编年史是总体史,描绘上帝如何在时间中实现自己的意志。编年史和年代记一样,都与时间密不可分,这个词本身就是来自希腊词汇chronikos,意思就是“属于时间”或“有关时间”。而且,编年史的起源和发展直接和年代记的发展有关。年代记主要是当代人所记录的每年的记录。编年史更加全面。它通常是基于一个或多个系列的年代记而总结成更长时期的历史,然而却保留了年代记严格的年代安排。一些记录的事件也许发生在编年史家自己所在的时期以前,这就需要综合不同年代记中的记录,从而获得更加全面和完整的故事。
在加洛林时代,有些编年史明显继承了早期基督教编年史的风格,将编年史和神干预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加洛林帝国衰落的阶段,面对混乱的现实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人们开始写作世界史,由于在上帝计划中的加洛林帝国处于危机,某些加洛林历史学家着迷于帝国序列的概念:加洛林帝国是否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延续,或者完全是一个新国家。随着查理曼之后加洛林帝国受到许多麻烦的困扰,当代人特别希望找到合适的答案,它不仅能够使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更好的理解,而且也指示他们未来的命运。[1]104当然,对加洛林帝国是否延续了罗马帝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肯定这种连续性,如圣高尔的诺科特(Notker of St.Gall)以及维也纳的阿铎(Ado of Vienne)的《总体编年史》(Universal Chronicle)。一派否认这种连续性。如助祭保罗的《罗马史》。普鲁姆的修道院长雷吉诺(Abbot Regino of Prum)则从另一层面否认两者的连续性,认为曾经强大的加洛林王国的衰落恰好证明了天意和所有世俗国家的暂时性。最正确和永恒的是基督教的教会,它的命运不依赖于任何特定帝国的命运。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分歧,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他们编纂历史的目的,都与早期基督教编年史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就大多数中世纪编年史而言,还是与早期基督教编年史有很大的区别。这时候的编年史作者有些人所记载的是某种经历,有些是地方史的个人叙述,有些人则保留了某个修道院的记录,反映其内部的生活和外部的联系。同样,一部编年史会记录某个特定城镇所发生的事情,如有关伦敦、佛罗伦萨、热那亚和科隆的著名年代记。因此,他们很少人有早期编年史家的整体史眼光,也不太在意自己的风格,缺乏系统性的神学教义理论,只有最著名的编年史才会上升到地区或国家记录的层面,才会冒险叙述欧洲国际间的事件。[9]66因此,中世纪的编年史和早期基督教编年史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的年代记的扩大。
比较而言,这时候的编年史更加缺乏历史意识。作者处理古代过去的历史时并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而是根据中世纪社会的趣味来解释它;在处理比他们的时代早的中世纪时期时,他们也不能进行精确的辨别,他们没有能力区别他们使用的各种材料的价值。只有在处理自己的时代,尤其是作为所描绘事件的目击者时,才能比较好地分辨事物的曲直。甚至在这方面他们也具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偏见和倾向,因为大部分编年史家都是僧侣,他们的记述只是代表了僧侣的观点和僧侣的解释。他们也不太关注题目和主题,因此,他们的作品都不加区别地叫年代记或编年史。尽管如此,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记载形式之一,编年史还是广泛记载了当时发生在各地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都纳入了编年史家们的视野,编年史家也在各地兴起,从而展示了比年代记更加丰富的历史画面。
在法国,比较著名的编年史历史著作是尼撒德(Nithard,800—844年)的《四卷历史》(Four books of History)。[10]尼撒德是查理曼的外孙,是查理曼的女儿和一位修道院长安吉伯特的非婚生子。在前言中,作者述说他写这部著作是因为主人秃头查理的请求,后者要求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尽管对他来说,记录当时那样纷繁复杂的事件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坚持记录,一方面是要完成主人交给的任务,一方面是害怕后人会曲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他的历史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第一篇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其余三篇是当代史。第一篇所涵盖的时间是从814年到虔诚者路易于840年的死亡,后面的部分则是从840年夏天到843年春天。
在第一篇中他对从查理曼之死到虔诚者路易时期发生的事件进行了简要叙述,构成了他所探讨主题的序曲。它的历史明显偏向秃头查理,它在著作的开头就宣称他属于秃头查理一派,这种偏向也影响了他的历史。当事实似乎对查理或路易不利时,他就保持沉默。他没有提到833年分割王国时查理完全被排除在外,也没有提到虔诚者路易834年在苏瓦松进行的不光彩的公开赎罪。他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洛塔尔,贬低从817年就担任共治皇帝的他的地位,称他为不守诺言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他的偏见在于当时的环境,在于虔诚者路易的宫廷对年长的几个儿子的敌对。然而这种环境和氛围也并没有导致尼撒德自甘堕落。他相信查理的母亲朱迪斯与伯纳德公爵有通奸行为,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如此进行记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坦率地指责那位伯纳德滥用职权,尽管此人是朱迪斯和查理最忠诚的臣属。在著作的结尾他指责他的主人娶了有影响的阿德哈德的侄女,目的是通过这场婚姻为自己获得大量的支持者。
尼撒德历史的其余部分试图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虽然他是查理的热情追随者而且是帝国的反对者,但是他非常忠诚和客观地记载了当时的事件。这三篇的内容主要集中描绘当时的政治动向、军事战役、外交活动和不断变换的同盟关系,同时描绘帝国分裂的条约草案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烦恼,最后以《凡尔登条约》而结束。第二篇显然是根据记忆而写成的,但是第三篇和第四篇则完全记录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部著作中查理始终是事件的中心,但是在著作后面的部分中,记载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然,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尼撒德对这项工作感到厌烦;在最后一篇的前言中,它不仅希望暂缓这一写作工作,而且想完全摆脱公共事务。只是渴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帮助后人驱散错误的迷雾,才支撑他继续写作。他逐渐地开始不关注主题的一致性,也开始跑题。在最后两篇中,它开始谈论天气、预兆、他的家庭以及当路易和查理的军队在842年合并后士兵们进行的战争游戏。他的记述没有明确的计划,事件的联系非常勉强,只是靠他所记载的主角把事件串联起来,但他也描绘了撒克逊的社会、撒拉逊人的入侵、地震和月食等。
尼撒德写作的这部历史,得到史学家高度的评价:“他目击了大部分他所描绘的内容,他非常有鉴别能力地使用所参考的书面材料。他用直接的明白易懂的风格,不允许东拉西扯来获得戏剧性的效果。尽管尼撒德属于秃头查理一派的人,而且严厉批评洛塔尔二世,但是他的历史写作经得起我们时代专家的严格考察。甚至他对洛塔尔的严厉评判现在也总体上为人们所接受”。[9]63因而,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加洛林后期最有能力的历史学家。
在英格兰,也出现了著名的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编年史用古英语写成的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的年代记作品,是由不同的作者先后续编而成的。这部编年史首先在序言中追溯阿尔弗雷德大帝的世袭,追溯其祖先的源头,然后一步步从祖先描述到阿尔弗雷德大帝,这说明最初的作者可能是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期的人。正文首先追溯了罗马人到来的历史。然后,叙述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这里的主人。接着描绘了格里高利教皇如何派遣奥古斯丁①前来不列颠传道,开始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的历程。接着分别讲述了肯特王国,东、西撒克逊,诺森伯利亚,麦西亚等撒克逊人王国的王位继承、战争以及接受基督教的情况,并夹杂着叙述了教皇和主教的更替,同时也同当时的编年史一样,讲了不少关于各种自然征兆的内容,如671年鸟儿大量死亡,678年出现彗星,685年不列颠出现血雨,牛奶和黄油都变成了血等。它记载690年西奥多大主教去世,以前的主教都是罗马人,此后的主教变成了英格兰人。787年,编年史记载第一批丹麦人来到英格兰,此后异教徒侵扰的内容开始进入历史的记载,并成为历史的主线。针对丹麦人的入侵,作者评价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由于政策糟糕才降临到我们头上,糟就糟在从来不曾及时向他们交贡金,也没有加以抵抗。可是等到他们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时,才趋同他们议和停战。尽管有了这一切停战协议和贡金,他们却依然分成小股到处乱窜,骚扰我们可怜的人民,抢他们,杀他们”。这种议论清楚地表明,当时英格兰对丹麦的入侵,显然已经处于劣势。最后丹麦人克努特成了统治英格兰的国王。其后在爱德华的统治下虽然有所复兴,但随着他的去世,因为王位继承而导致了诺曼人入侵英国。诺曼人的征服又成为历史叙述的主线。但作者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是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立场上的,所以对威廉征服和威廉的统治充满敌意。因此在记载到威廉的死亡时,作者的语气带有强烈的讽刺的味道:“哎呀!尘世的繁荣兴盛是多么虚假,多么不可靠啊!他这个曾经是一位强大的国王,又是许多土地的主人的人,当时在所有的土地当中却只占有7英寸之地;它这个衣服上曾经缀满黄金珠宝的人,当时却覆盖着泥土躺在那里”。
这部作品并不是不偏不倚的,与其他中世纪资料相比,有些时候续写编年史的人遗漏了一些事件或者只讲述故事的一方面。有些地方不同的版本则相互矛盾。但从总体上而言,这部编年史是有关罗马撤退和接下来的诺曼征服期间英国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这部编年史中提供的很多资料现在已经无处可寻。另外,这种手稿也是有关英语历史的重要素材。从资料上来讲,这部编年史汇聚了各种不同的素材。有些段落内容记载得非常详细,甚至引用了参与事件的人的讲话,说明这些段落来自当时流传的传奇故事。有些早期的叙述来自当时流行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材料。有的素材来自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有些则是当时的目击资料。从时间上讲,由于这部编年史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完成的,所以有些日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还会在不同版本中以讹传讹。同时,不同的续写者由于身居不同地方和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因而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偏见。汤普森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准确的:“就像对比德的著作那样,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书也是主要阅读一遍,就能对它那包括万象、丰富充实、活泼泼辣得到恰如其分的印象了。虽然它实际上是一部宫廷编年史,但其文字朴素、直率而有力,表面形式尽管堂皇虚饰,但在这些装潢底下确实可以咂出真实情况的味道”。[11]
中世纪编年史的出现和丰富,标志着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进步,因为与年代记相比,编年史转换了历史叙述的视角,不再把历史看成纯粹计算复活节的工具,而是将其看成记录所发生历史事件的载体。编年史把记述的重心从时间图表转向了事件的进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的内容,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是一个文化重新建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古典的文化已经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告一段落,文化极度落后的蛮族王国和基督教文化的结合,迎来了一个新兴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是在信仰的主导下,通过各种文化要素的妥协和整合完成的。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历史必然要反映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现实,必然要体现当时人的思考,脱离了中世纪历史学家和那些历史著作所存在的语境,我们就无从对他们做出客观的评价。因此,尽管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种种的“荒谬”,包括他们用虚幻的神意来解释历史;用毫无根由的神迹来构筑历史;用毫无个性化的标准来塑造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著作同样在述说着中世纪确实存在的“事实”。历史事实不仅仅意味着所述的事件的客观和准确,也意味所叙述的内容是否能够反映时代的情感和特征。这些历史记录了中世纪人们所坚信不疑的东西,记录了能够激荡中世纪人心灵的内容,它反映了构成中世纪人思维的要素,体现了中世纪之所以为中世纪的特征。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通过他们的著作了解了中世纪人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方式,从而使我们得以把握中世纪时代的脉搏。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哪怕是在我们看来并不客观真实的历史内容,同样向我们“客观地”传递着中世纪的信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记述中世纪历史的著作本身也是中世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成为向我们当代人展示中世纪世界之特色的重要窗口。
注释:
①此处的奥古斯丁,后被称为“英国教会之祖”,与写作《上帝之城》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同名,但并非同一人。
